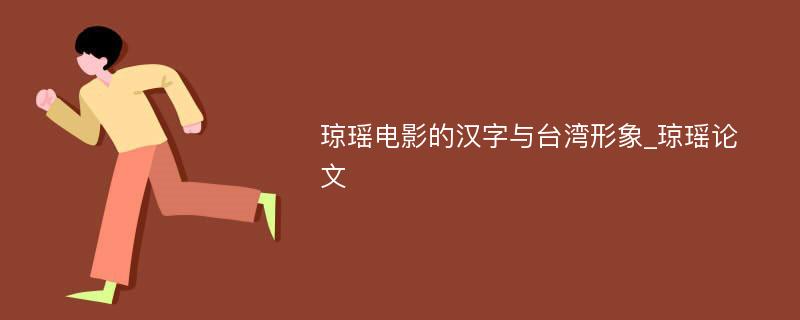
论琼瑶电影的中国性与台湾图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琼瑶论文,图像论文,中国性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0)01-0045-10
影评界对在台湾电影史上曾创造票房佳绩的琼瑶电影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至今也未有明确的定论。其中正面的评价大多因其所获得的高票房来肯定其商业性对台湾电影产业的刺激,而负面的评价则多与文学评论界对琼瑶小说加以“琼瑶公害”的罪名相类似,批判其中的言情模式有害于观众、读者的精神健康。这种争论式的评价、研究在台湾影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电影为商业与艺术之综合体,电影研究者对影片所取得的商业成就加以积极肯定应为十分必要。而本文所集中探讨的重点,便在于对琼瑶电影所蕴含的“中国性”(Chineseness)进行辨析,以此肯定它在文化身份表达上的独特意义。
一、言情与琼瑶文艺片的类型传统
琼瑶电影时代在台湾电影史上创造的辉煌距今已经三十余年,而仍旧活跃于当今台湾电影界的文艺片类型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可见,琼瑶文艺片已成为台湾电影史上一页撕不去的标签。为琼瑶影片冠以“文艺”二字,更可以突出这一类型电影的特征。蔡国荣在《中国近代文艺电影研究》开篇指出,文艺片这一类型影片主要是指:“大凡以现代或清末民初为时代背景,在感情方面用力描绘,加强刻画,全片核心经由感情凝成,题旨也在彰显感情的影片。”[1]琼瑶电影特指的是在1965至1983年期间,根据琼瑶原著小说改编拍摄的影片。除了具备上述文艺片的特点之外,这类电影以讲述男女之间纯情、浪漫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与其它文艺片相比更有其独特之处,因此可以将这类电影称为“琼瑶文艺片”,这类影片具有非常统一的风格化特征。在这近二十年期间,以琼瑶小说改编的文艺片一度成为了台湾电影的主流。在这一时期的台湾影坛,同时存在着大量模仿琼瑶小说模式的电影。这类影片集体制造了具有台湾特色的爱情奇幻梦境,曾经掀起一个时代的流行风潮。
琼瑶小说的走红始于20世纪60年代,将其小说改编成电影的热潮紧随其后。1965年,李行导演的《婉君表妹》上映,并引起较大反响。随后,琼瑶小说开始成为电影拍摄制作的宠儿。在这一年,一共有四部由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另外三部分别为张曾泽导演的《菟丝花》、王引导演的《烟雨濛濛》和李行导演的《哑女情深》。《烟雨濛濛》中的女主演归亚蕾更是凭借这部影片摘得了当年金马奖影后的桂冠。这四部影片的相继亮相,也使得“琼瑶热”由文坛扩展到了影坛,成为当时电影界一时的盛况。在此后以李行导演为主导的琼瑶电影时代,李行、甄珍、邓光荣被称为文艺片的“铁三角”,20世纪70年代的“二秦二林”组合更成为了琼瑶文艺片中的金字招牌,也使这几位明星成为台湾电影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琼瑶至今一共创作了六十几部小说,其中就有五十部左右被改编后搬上银幕,并在华语电影观众中受到极大的欢迎。琼瑶文艺片使台湾电影在历史上掀起了两次时间较为持久的观影热潮(分别出现于1965至1969年、1973至1983年),这也成就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电影界在商业票房上的一度辉煌。
这些影片的出现是当时电影创作力匮乏、竞争力薄弱的台湾电影市场的一道曙光,其创作和生产都始终保持着非常独特的风格和审美旨趣,也在同时期及以后影响了除琼瑶电影之外的其它台湾影片的制作风格,最终在电影界形成了风格化的电影模式——琼瑶文艺片模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影坛,除了琼瑶原著的作品之外,还出现了不少模仿这类风格的影片,如《三朵花》、《欢颜》、《蒂蒂日记》、《天凉好个秋》、《风儿踢踏踩》等,这些风格相似的电影在故事上讲述浪漫超脱的爱情,在影片制作上选择与琼瑶影片相同或形象类似的演员、明星、制作班底,紧随“琼瑶热”的步伐,推动了台湾爱情文艺片潮流的发展,不少影片也受到了观众的追捧,赢得不错的票房。
琼瑶文艺片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台湾电影的发展开辟了富有特色的类型片传统,它同时也继承了自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不断发展的通俗文化色彩浓重的商业电影传统。从这点上看,琼瑶电影的产生、发展以及在华人社会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事实上也是两岸文化同源同根、传承发展的有力证明。
从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来追溯,1921年的《阎瑞生》为电影在商业上的成功创造了开端。在此之后,“鸳鸯蝴蝶派”文人如张恨水、包天笑等人纷纷参与了电影的制作,以言情为主的影片成为早期中国电影市场的主导力量。根据郦苏元的《中国无声电影》中的描述:“爱情片始于上海影戏公司的《海誓》和《古井重波记》,因此它的出现,要早于社会片。……很快便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社会片,到1926年,它已占影片生产总量之大半。”[2]
在华语电影的研究中,研究者对台湾电影的研究多侧重于其特有的人文特质部分,对台湾电影史的关注点往往也是从早期的台语片、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直接跳到台湾新电影;而对在台湾电影黄金时期的主力如琼瑶电影、武侠电影等则因其商业色彩的浓重而较少进行深入的探讨。近年来,随着华语电影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对琼瑶电影进行评价也成为这一类型电影研究的新的突破口。“这种类型化的影片,相对于1920年代中国影戏传统下的‘鸳鸯蝴蝶派’电影,1960、1970年代琼瑶影片以及其所延伸的爱情文艺影片,将是台湾当下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3]
琼瑶电影的爱情文艺色彩显然并非凭空而出,而是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积累。从唐代传奇到民国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作为中国俗文学发展的代表,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曲折离奇的情节发展、通俗易懂的叙述方式、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坚持等固有的模式从古至今都受到大众的喜爱。由此可见,琼瑶小说的故事模式并没有走出中国通俗文学的传统框架。再从琼瑶电影的故事内容、结构来看,从小说改编为电影基本上也并未见有太大出入。
从“鸳鸯蝴蝶派”小说到“鸳鸯蝴蝶派”电影,从琼瑶小说到琼瑶电影,它们的发展轨迹、社会背景、文化基础都是极为相似的。同样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下,市民文化中试图逃逸于现实的阅读、观赏动机更为突出。略有不同的是,“鸳鸯蝴蝶派”文学更倾向于描写有情人之间的悲情故事,但刚经历过战乱分离时期而诞生的早期琼瑶电影十分接近于这一特征;到了后期,琼瑶电影风格开始转变为轻快、活泼。这也是由当时的作者经历、社会经济及市场环境所决定的,可视为早期“鸳鸯蝴蝶派”传统在台湾这块特殊的文化土壤上的新发展。
近年来,对“鸳鸯蝴蝶派”电影、“软性”电影的认识,研究者们也从“落后、倒退”的批判论调逐渐地转变为肯定它对中国早期电影基本形态的影响。那么对于在台湾地区曾经出现的琼瑶电影热潮,我们也需要以一种新的眼光去评判它的价值。另外,台湾电影的起步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台语片,随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琼瑶影片缔造了台湾电影的繁荣景象,为台湾电影商业体系的完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这也是在台湾电影发展初期对其进行类型塑造的一种形式。
二、琼瑶电影中的中国性(Chineseness)
虽然琼瑶文艺片以“文艺”冠名,但电影仍是以商业赢利作为最根本的目的,因此它具备了类型化的商业影片的基本特征,也具有可以将其特征归纳、总结的模式化特质。简单地来看琼瑶电影的模式化,可以包括影片故事情节、场景设置、男女主角形象、表演方式、人物对白、影片制作过程等各方面的模式化。其中着力于发挥琼瑶小说中的故事性是这些电影吸引观众的重要法宝之一。琼瑶文艺片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偏于模式化,许多戏剧性的桥段频频重复出现在影片中,包括两代人的冲突、巧合与误会的发生、曲折多变的多角恋爱等。
琼瑶影片善于模仿好莱坞电影传统的通俗情节剧模式。这种通俗剧的模式主要是,用简单、粗暴甚至荒谬的方法处理剧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同时用夸张的戏剧语言来渲染人物的感情,并试图达到某种道德教化的效果。因此,剧中突如其来的灾祸、出乎意料的巧合或者是爱情的阻碍者突然醒悟而成全男女主人公等情节频频出现。另外,琼瑶影片经常较简单地搬用精神分析这种老派好莱坞影片的桥段,如《菟丝花》(1965年)中雅筑这一中产家庭中疯狂、失意的女主人形象,《我是一片云》(1976年)中精神分裂的段宛露对于“云”的意象的执迷,《燃烧吧!火鸟》(1982年)中对姐姐意外将妹妹致残的童年记忆的描述等等。但是在琼瑶电影中这样的处理往往较为简单化、表面化,对精神分析方法的利用只是成为制造影片趣味的一种手段。
电影利用通俗情节剧的模式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够给观众带来抚慰、教化、宣泄的作用,而在中国电影史上,将通俗剧模式与中国的道德伦理、政治问题、文化反思等方面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从1923年的《孤儿救祖记》到1947年的《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通俗情节剧模式的运用,这些电影达到意识形态层面与市民文化层面上的共赢,成为在视觉政治表达上的巧妙之举。
在中国内地,与琼瑶电影在发展时间上属于同一时期的是谢晋电影,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这两种电影分别在两岸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谢晋导演同样将这种好莱坞式家庭情节剧模式运用得非常准确、成功。他的电影利用这种情节剧模式的魅力来抒发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并受到了广大中国观众的喜爱。但是在当时两岸所处的不同政治环境和社会背景下,谢晋电影显然具有更浓厚的政治色彩。通俗情节剧的观众容易受影片剧情的吸引而在观影过程中暂时忽略这种政治力量的存在。但是国家政权的政治话语始终是高于一切,在谢晋电影中这是直接而有力的。而在琼瑶影片中,这种为当局者发言的动机是暧昧而隐晦的。同样是对通俗情节剧的模仿,在对白语言的复杂、表演上的夸张、道德上的教化等方面,两者没有离开这样的模式规范。但从影片的道德教化意义来看,谢晋电影更注重营造关乎国家荣誉的大叙事背景下的道德感,而琼瑶电影则更多表达的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尊重和传承。
琼瑶文艺片对社会矛盾的调和方法,或者说是对观众的抚慰方法,绝不会去挑战势力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而是单纯希望用人性、真情等来解决这些矛盾,这或许也可以看做是琼瑶文艺片被指为狭隘、缺乏深度的主要原因。从当时台湾电影政策的执行来说,这也是为何琼瑶电影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胜于刚刚兴起的武侠片,在影坛上一枝独秀的原因,因为相较于武侠片中的忠肝义胆和侠义狂狷,琼瑶电影的柔和、浪漫、妥协的姿态,更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和方向。
在琼瑶文艺片中,男女主角之间的爱往往是一种违背常规的爱情,逃离了等级的差别,忽视身份的悬殊,不顾家人的反对和社会伦理的束缚。除了贫富悬殊的恋爱,正常人与生理有缺陷的人之间的爱情,更是超越了现实的标准,如《燃烧吧!火鸟》就是在称颂英俊有为的凌康与盲人卫巧眉之间的婚姻,《在水一方》(1975年)也讲述了一段跛脚的朱诗尧与美丽落寞的杜小双之间纠葛多年的爱情。而在主人公看似“出格”实际上又发乎于情的举动,我们可以窥探出其中的内在无意识,在于一种对除爱情之外的其他事物的无视。通过对爱情的虚构,琼瑶电影希望展示的是一个没有现实压迫、没有阶级约束、没有国仇家恨的台湾社会幻景。
琼瑶电影有意地规避了政治、现实上的重压,但是却在人性、人情方面深深打动人心。琼瑶的爱情世界与现实世界既有相同之处却也是永远不可能等同。如人物所处地理环境、生活形态、社会背景等方面,可以与观众的现实世界相类似,但是在其中所发生的奇情唯美却是现实中的观众可望而不可即的。电影对人生流逝、历史风云变幻的感叹、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动人描述,最容易激起当时观众的共鸣,在早期的琼瑶电影中,更直接地表达了从大陆来台的人们对旧人、旧时、旧事的追忆和遗憾,而在后期,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电影中的中国情结则被概括为一种恋乡的情结和归属于传统的伦理规范。
琼瑶祖籍湖南衡阳,1938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49年随父迁至台湾。从小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下,她的文学作品常常出现一些古诗词来表达优美的意境,如《心有千千结》、《聚散两依依》这样的书名,无不体现出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诗意。另外,她的歌词里也往往配合着这种古典诗意的演绎,如《在水一方》是对《诗经·秦风·蒹葭》中的白话文书写,很贴切地说明了影片中男女主角之间无法表白的情感纠葛。另外,在琼瑶电影中所表现出的文学性方面,也透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尤其是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古典诗词、戏曲中的意象,均展现了古典文学优美、脱俗的特点。
琼瑶对传统文化的偏好,除了表现在片名的命名、电影主题曲的填词上,更是深入到电影所传达的价值观方面。在她的电影里,往往很重视传统的家庭结构,即父严母慈、男主外女主内、郎才女貌这样的人物关系。剧中人物恪守孝道为先、尊老爱幼,女性应遵循温柔敦厚、贤良淑德等传统道德规范。剧中女性即使是冲破传统道德的束缚,最终只有得到传统道德力量的支持,才能获得完满的幸福,否则就是落得个悲剧的下场。如早期的《菟丝花》中雅筑破坏他人的家庭,最终精神失常,自杀身亡;《我是一片云》中的女主角段宛露在婚后仍徘徊在丈夫与恋人之间,最后遭遇丈夫在工地分心而发生意外,自己则精神分裂的悲剧。
早期的琼瑶电影作品(1965-1969年)善于营造一种怀旧的氛围,并塑造了可望而不可即的近代中国的形象,对旧中国的古典意蕴和传统道德精神怀有留恋、赞赏的态度。因此在如《婉君表妹》(1965年)、《烟雨濛濛》(1965年)、《哑女情深》(1965年)、《几度夕阳红》(1966年)这些作品中,故事发生地选择在东北、重庆、云南、上海等这些位于中国内地的地方,并且在剧中以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为背景,使得影片更具有历史感、时代感。另外,作品会出现意境悠远的诗词以增添作品的古典意蕴,并透露出赞美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的价值判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影响下,对于曾有逾越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的人物,总是经历内心痛苦的折磨,甚至遭遇悲惨、不幸的结局。如《烟雨濛濛》中复仇的陆依萍,《几度夕阳红》中不顾母亲反对与何慕天恋爱的李梦竹等。
在20世纪60年代的琼瑶影片中,最激烈的戏剧冲突发生在两代人爱情观与婚姻观的差异上,最典型的是《窗外》(共有两个版本,分别为1966年崔小萍导演,1975年宋存寿导演)中父母与女儿在对待师生恋的看法上的冲突。下一代人追求自由浪漫、爱情至上的精神,而上一代则按照传统的价值观,重视亲情、伦理,遵循传统道德规范。在上下两代人发生冲突,爱情故事发生各种转折之后,这两种价值观的斗争会出现互相妥协的结果。在这一时期,下一代在经历恋爱的失败之后,往往接受了父母的安排而走入婚姻。如《窗外》中的江雁容是个单纯甚至有些无知的少女,她与老师相爱,但也不能离开家庭,最后妥协嫁给看来门当户对的李立维。但这段父母安排的婚姻又存在着种种不幸,而与老师康南之间的爱情,却不得不面对康南经受社会的压力、贫病交加的现实。另外如《哑女情深》中静言接受了上一代人指腹为婚的安排,与哑妻方依依成婚并最后爱上了德容兼具的妻子,在经历出走、丧妻等一系列变故之后,在追悔与自责中度过余生。
20世纪60年代琼瑶电影中较多地将故事背景放在民国年代,而70年代之后的琼瑶电影的故事发生地多是现代化的当下台湾社会,而电影所传达的则是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甚至其中还不乏“封建”说教的意味。这与当时的政权统治不无关系。在六七十年代经济大发展的台湾社会,也是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时代。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仍以宣教大中华文化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但是文化是必须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内容来进行教育,而不能涉及孕育这一文化的“原乡”——祖国大陆。这些作品也表达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在新旧观念、政府与民间观念的冲突下,需要在一个自己创造出来的梦幻空间,与问题重重的当下社会和抱有乡愁的旧中国社会均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此来实现逃避现实冲突的愿望。
晚期的琼瑶电影,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李行、白景瑞等人拍摄的几部由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一直到70年代中期以后,由琼瑶的巨星公司所投拍的电影。其中以《我是一片云》为代表,从1976年到1983年所拍摄的13部影片,大多是以台湾当代社会为背景,讲述年轻男女的多角恋爱故事,以曲折的爱情作为唯一的故事发展线索,制造浪漫、美好、诗意的情愫,而在后面几部由琼瑶特别指定的刘立立导演拍摄的影片中,这一风格化的特征倾向更加突出。
这十几部影片中的故事背景多选在台湾,人物都是现代都市中的台湾人,而场景多是设置在来自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咖啡厅、舞厅,剧中人物也在尝试着美国化、西方化的生活方式,但是作者并没有表现出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赞同和认可。虽然在生活中西方的影响无处不在,但是在思想上,剧中人物仅将西方社会看作是一种遥远的、暂时的避难所。他们可能会远赴欧洲、美国这些西方国家逃避感情的纠葛或是实现心中的理想,但最终,人物仍然会选择回到台湾,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与相爱的人在一起,这样的剧情在《庭院深深》(1971年)、《海鸥飞处》(1974年)、《聚散两依依》(1981年)等作品中都有所表现。1977年的《人在天涯》完全在意大利实景拍摄,讲述海外华人的生活与理想,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众人一起坐飞机回到了台湾,表明“艺术的内涵离不开民族的情感”这样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而这种认同也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早期琼瑶电影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暗示,而可以看做是,经过数十年生生不息的耕耘,台湾本土的日常生活印记已经深深烙于在台湾生活多年的人们的心里,在他们心中形成了另一个“新的故乡”。
可以说,无论是早期或晚期的琼瑶电影都不乏对古典意象的营建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宣扬,而这些都蕴含了对中国这一文化母体的感情。这也为台湾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基本的精神支持,那就是迁徙至此的台湾人在新的土地上的浓烈乡愁。
三、琼瑶电影中的台湾图像
台湾文化界的评论者往往将琼瑶作品所引发的现象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他们以整体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诠释,由此投射出他们心目中不同阶段的台湾社会的意象:所谓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过渡期、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等等名词”。[4]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不同阶段的琼瑶电影中,都能找到每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在影片中的投射。由此可见,文学界对琼瑶作品的关注大多是放在作品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上,着重的是琼瑶作品的读者接受与社会的关系。而在90年代以后,随着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介入,在对琼瑶作品进行探讨的过程中,这种对反映台湾社会生活状况的关注更加深入,并有研究者开始运用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等新的理论角度,对琼瑶作品中的性别关系、国族认同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批评。
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世纪末,琼瑶小说借助影视传媒等大众文化传播方式,一直在华人世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琼瑶电影曾是琼瑶热最早的推动力量,在创造高票房的奇迹的背后,依靠的主要是观众对其编织的梦幻的认同。琼瑶电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产生较高的票房效益,制造了几位耀眼的明星,促进了台湾电影事业的发展,更是在于通过电影的方式,传播了当代台湾的文化特色,构建了台湾社会的自我形象。
琼瑶电影反映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台湾社会重要的转型时期,台湾人在社会伦理思想、价值观、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变化。在60年代的琼瑶影片中,我们从《婉君表妹》、《哑女情深》中模糊的旧中国背景,《菟丝花》中发生在贵州的往事,《烟雨濛濛》中所设置的军阀混战的年代背景,《窗外》中的国文老师从大陆到台湾的漂泊和孤独,《几度夕阳红》中大陆战乱、流亡至台湾的故事背景等等,都暗示着早期琼瑶电影所存在着的浓厚的“中国性”特征,而这也正是代表了当时台湾人民的普遍心态。他们从大陆迁至台湾,初到岛上即遭遇一系列高压政治事件,使他们对这片土地陌生而畏惧,愈加想念在大陆的亲人和故土。而在这个时候,电影中所创造的旧中国景象使他们产生了“返乡”的幻觉,短暂地抚慰了他们强烈的思乡之情。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初期,在政治上的重心就是希望实现“复国之梦”,始终抱有“反攻大陆”的幻想,因此在这一时期台湾民众的意识里,中国内地始终是作为“沦陷的家国”的形象存在,而他们虽然不能身处地理上的中国内地,但是文化上的中国意识仍然得到了延续,中国内地这一文化上的母体仍然广泛地影响着台湾民众。而历史进程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民党的反攻幻想基本已经破灭,国民党政权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悄悄发生改变,威权政治开始面临重重危机。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逐步地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也由此涌现了大量的女工。在当时,琼瑶电影的观众群大部分是琼瑶小说的接受群体,主要以女性为主,多为工厂女工、在校女学生、家庭妇女等。琼瑶编织的梦幻精彩美丽且通俗易懂,正好满足了观众对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慰藉了其内心对现实生活中的不满和恐慌。琼瑶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多出身在富裕家庭,尤其是男性,往往来自中产阶级家庭,衣食无忧,使女性能够在婚后安心在家中相夫教子;女主人公不是娇俏可爱的富家公主,就是温柔多情的灰姑娘,她们从未有过或可以完全忽略现实的生计问题,唯一的烦恼就是来自爱情。这种脱离现实的情节设置,也为这群观众找到了压力发泄的出口。琼瑶片浓厚的梦幻气息,填补了当时台湾民众的空虚心灵,也成就了琼瑶片长达20年的辉煌期。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琼瑶电影的外在特征由古典转型为现代,并从各个层面展现当代台湾社会的面貌。西方化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在琼瑶电影中有所表露。年轻的主人公在剧中常常强调“自由”、“民主”的婚姻和爱情。如《一帘幽梦》(1975年)中叛逆的女儿紫菱与父母的冲突,表现在紫菱要嫁给年长的费云帆,最后父母妥协同意。《海鸥飞处》中叛逆的富家小姐陈羽裳,性情开放,在各地捉弄恋人俞慕槐,最后因不能得到他的谅解,任性接受了败家公子欧世澈的求婚。同样,在是否赌气接受欧世澈的问题上,父母与子女也达成了一个妥协,但是以女儿的意见为主。最后,陈羽裳只好默默忍受丈夫的折磨,吞下婚姻失败的苦果。琼瑶的电影通常会塑造一类在传统道德观念上趋于完美的女性,美丽、温柔、贤惠、顾全大局、懂得牺牲和容忍。而在这部影片中,少女时期的陈羽裳虽然顽劣调皮,但是在婚后还是成长为了这一类的完美女性。在这个情节设置上,也表明了冲突的妥协方虽然发生了改变,但是在琼瑶的影片中传统的伦理道德仍深刻地影响着人物的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发展,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人对于台湾本土的认同感也在加强,而此时的影片也转向了对台湾社会面貌的描写,这个时期琼瑶文艺片的故事背景多发生在台北,表现都市的中产阶级趣味,并突出了时代富足、积极、乐观的一面。从这点上说,琼瑶文艺片不仅是为女性观众们制造了爱情的梦幻,也为普通的台湾人构筑了一个美好、没有冲突的台湾,这也符合了在经济腾飞的时期,当局促进同一的认同感、缓和社会上的政治冲突的希望。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琼瑶电影中,对上一代的威权力量的处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个人意志、追求的重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以上所提到的60年代的《窗外》中,父母的威严可能决定了女儿的命运,然而在70年代之后,如《海鸥飞处》、《我是一片云》等,父母虽然知道女儿的任性和错误,但却仍然做出了妥协。这也可以看做是台湾当局威权制度有所妥协的暗示。事实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政治体制开始逐渐走向民主、宽松,的确成为影响文艺创作的重要社会背景。
影片中新一代青年的任性和自我,也可以看做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新兴力量的崛起。而旧的传统势力的影响开始在影片中表现出衰落的趋势。虽然新一代人在面对自己的选择之时,仍然遭遇了失败和挫折,但从故事的结局来看,作者还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乐观。这种反差在1981年的《梦的衣裳》里,就是直接地对其进行了叙述,几年之前,少女桑桑因为上一代人的反对,不能与穷困潦倒的吉他手在一起,被强行送到了美国,最后郁郁而死。而几年之后叛逆的现代女孩陆雅晴戏剧性地出现,得到了桑家上一代(奶奶)的喜爱,最终与桑尔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一种对过去遗落的美好事物的补偿,在这一部戏中,上一代人从残酷的反对者转变成为了慈爱的促成者。而剧中钟镇涛饰演的吉他手万浩然却只能承受爱人已逝的痛苦,这个角色延续了早期琼瑶电影的忧郁和绝望,也为影片增加了一个经典怀旧的看点。
琼瑶电影发展的这20年,正是台湾社会经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人们的价值观念也经历着强烈的冲击,新一代青年的现代观念开始成长的同时,大批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从大陆迁台的社会人群一直沉浸在怀乡的情绪中,这也使得在当时台湾社会中这种传统、现代、怀乡等情绪交织在一起,东西方的价值观念不断碰撞。在电影中这三种复杂的情绪不断地对观众产生刺激和安慰,并试图在这三者之间寻找到平衡,这也是电影中的人物总是从冲突走向妥协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的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现代化的转型更为深入,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台湾的影响逐渐扩大,上一代人的乡愁逐渐被这一代人的移民现实所取代,西方化的生活方式、精神理念广泛地影响了新一代台湾人。在这20年之后,初至台湾的“外省人”也已有了“新台湾人”这一新的称谓,这样的称谓也表明了从大陆到台湾的移民们经历二十多年的历史变迁之后,所完成的在地理、心理位置上的转换。
但如上文所述,琼瑶电影虽在物质生活上对西方化的生活方式进行美化,但是在价值观念上仍然归于传统。这也成为琼瑶电影最终隐匿于历史的一种预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映的《梦的衣裳》、《聚散两依依》等都提及美国的生活,透露出80年代初期台湾人的移民倾向,但影片中的人物多是将其视为逃离在台湾所发生的现实困扰的避难所,剧中女主角贺盼云、陆雅晴最终还是决意留在台湾,俨然已将台湾作为新的故乡,拒绝去进行一次新的异乡漂泊。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台湾社会的政治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琼瑶电影的模式化以及其中日渐显得保守的思想观念,也开始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格格不入。1982年吹响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号角为台湾电影揭开了新的篇章,这也是琼瑶文艺片在1983年之后不得不告别台湾影坛的重要原因。
总之,琼瑶电影中将台湾人独特的怀乡意识、中国情结和现代观念交汇在一起,真实地呈现了一幅台湾社会图像,琼瑶电影也因此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与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取得的票房成功所带来的商业价值,必然使琼瑶电影位列于台湾电影史上的重要一席。
收稿日期:2009-11-09
标签:琼瑶论文; 电影论文; 几度夕阳红论文; 我是一片云论文; 烟雨濛濛论文; 琼瑶小说论文; 海鸥飞处论文; 哑女情深论文; 婉君表妹论文; 台湾电影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古装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