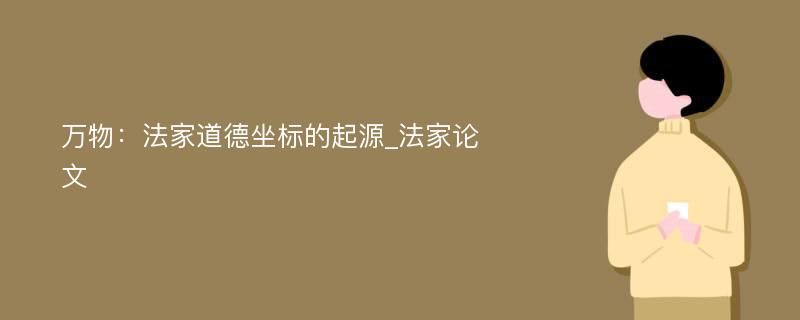
万物——法家道德坐标的原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家论文,原点论文,标的论文,万物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6;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0)05-0008-08
法家在中国得到定位的关键自然不是道德,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不仅如此,更为严峻的是,法家往往还与反智、反道德主义的称号相联系。在这样的氛围里,尽管法家研究在不断翻新,诸如儒家法思想、法家的儒家倾向等问题,成为一些学者所热衷的话题。其实,这些最多也是比照儒家思想而结出的果实,而不是依据法家思想原典而得到的自然演绎。究其原委,当与我们的研究长期以来脱离原典而基于客观现实的需要分不开,在这样急功近利的追求中,原典仅仅成为阐述现实的工具或润色的添加剂,在这样的价值氛围里,原典本有的价值始终难以得到阐述和总结,法家研究的深度推进也只能成为美好的乌托邦寄托,属于中国哲学的个性化研究总结也只能成为一纸空文。
众所周知,在深思道德问题时,首先必须直面的问题就是道德所面对的对象是什么?法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答案毫无疑问是“万物”!但它至今为人所遗忘或无视,这不仅对法家思想的合理化是一个阻碍,而且对优化中国道德哲学思想的资源也是一个巨大损失;正是在中国学者无视或者零问题意识的万物问题上,倒是西方学者一语中的地道破了一些天机,他们在谈到《管子》“名”、“实”、“德”、“理”、“智”、“当”等问题时,认为名实一致的社会,是一个人人可以也能够各尽其责的完美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形式里,“德”只有在“产生于自己在万物之‘理’中的位置”(《天人分途》)[1]327,那里才能得到显示。这虽然是针对《管子》说的,但适用于整个法家。这无疑提醒我们,不能简单而机械地从“行政技能”的角度把法家局限在人自身这个非常狭隘的领域里,法家的视野是万物的。
一
“道法”是法家的一个重要概念,这昭示了法家与道家的关联性,依归这一关联性自然是研究合理化的前提之一。就天人而言,道家是非常重视的,这从概念出现的多少中可以得到自然的诠释,例如,《老子》里,“天”字的出现约92次,“天道”概念约有7个(包括“天之道”5次),“天地”概念约有9个,“天下”概念约有61个;“人”字的出现约85次,“人之道”概念约有2个;“民”的用例约有33个,“百姓”的用例约有3个,“民心”和“民利”的用例各约有1个。“人”和“民”合计有118个用例,明显多于“天”的用例,这也充分说明演绎中国道、德辩证最初图式的老子,立足点仍然是现实的。
法家的思想发展,虽然前后经历的时间比较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无法均衡地来衡量所有的思想家,加上诸如《管子》不是一时、一人之作的特殊情况,就更难以具体量化这些不均衡性,故只能从总体上来立论。在这个前提下,可以说,法家比道家更张扬人,希望通过人的张扬来外化人的内在力量,从而服务于多事的社会。下面的基本数据可以说明这个事实。法家思想家的“天”字的用例约有1260次,其中包括“天下”784个,“天地”85个,“天道”36个①。“人”字的用例约3388次,其中“人事”的用例约有11个,“人道”的用例约有3个;“民”字的用例约2325次,其中“民力”的用例约有32个,“民心”的用例约有28个,“民众”的用例约有19个,“人民”的用例约有16个,“民利”的用例约有14个,“民生”的用例约有5个②。如果“人”与“民”合计的话,就有5693个之多,是“天”用例的4倍多。人自身完全在法家思想家那里得到聚焦,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尤其必须注意的是,“人事”这一概念的使用,表明着人对自身认识的进步。
通过上面的资料揭示,可以质疑的是,在商鞅那里没有人道、人事的用例,这的确与管子、韩非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商鞅虽然没有人道概念的使用,却有“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商君书·开塞》)[2]73的论述,“民道”就是人道,不过更富有政治哲学的色彩罢了。另外,在法家道德的坐标里,“人民”、“民众”、“民力”、“民生”等概念也得到普遍的使用,而这些是在老子那里无法找到的,这也是应该重视的环节;“百姓”概念的用例也达到144个之多③。
法家虽然重视人的因素,不过,总体上是在“三材”和谐的关系上来认定的。在法家看来,“天地设,而民生之”(《商君书·开塞》)[2]73,天地创立以后,人就产生了;人是随着天地的创立而产生的,先由天地,后有人的产生;在人的视野里,“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管子·宙合》)[3]58,天地不仅行进在各自的轨道上常则地行事即“不一时”,而且公平地对待万物,使万物在宇宙中找到适宜的位置即“不一利”。就人而言,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能够基于各自独特的本性特征而与社会所设置的职事实现顺利的对接,从而为发挥各自的能力而获得实际的位置即“不一事”,这实际上就是比附天地自然之道来演绎整治社会的道途,也就是“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管子·霸言》)[3]145,政令是人道的范围;施行爵禄离不开物质,而粮食是当时的主要形式,所以这是地道的业务;其他的大事情必须依据天道的规则来处理。
上面提到的天道、地道、人道的关系,都是概括性的设定,而“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观矣”(《韩非子·八经》)[4]1063-1064,就是具体的说明了。“言”成为“言”必须经过一个过程的甄别验证即“徵”,符合标准后才能成立,不然就不能成为“言”,这个过程里有四个成员即地、天、物、人,如果“言”在四个成员那里的证验结果相同,这“言”就可以成为衡量标准的“言”了。韩非这里通过“徵”这个环节,惟妙惟肖地把天地人的关系进行了诠释。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家重视的人,是在“三材”关系里的人,这显然与儒家表面上以人为中心,实质上是以自己为本位的价值取向是完全相异的[5]。对此,商鞅下面的论述可以作为总结。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事徕。开〔徕〕则行倍。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 夫弃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务过也,而上下事之,故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为国任地者,山陵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陵薮泽溪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商君书·算地》)[2]61-62
这里描绘了人与自然如何实现动态和谐关系的运思。人类社会的治理必须奉行“任地”的原则,具体社会事务的施行规则就是“任地待役之律”。“任地”就是依任地利的意思,这也与前面管子把爵禄作为地道的内容相一致。因此,不能离开地利来运思社会的整治,地利直接与民众的基本生活相联系,“足以食其民”、“足以处其民”、“足以供其利”、“足以畜”都是强调的这一点。所以,法家追求的是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的关系,人不能脱离地利来满足自己欲望的追求,即管子所说的“天地和调,日有长久”(《管子·度地》)[3]305,这在今天的启发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
最后,不得不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上面揭示的法家使用概念的构成中,天道有36个之多,人道仅3个,人事也只有11个,自然,这只具有相对的参考意义,但它仍然显示一个强烈的信息,重视法制的法家仍然是推重天道的,而且对此持有更多的熟虑。因此,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它仍然行进在用自然之道来治理社会人事的轨道上。
二
法家不仅重视天道,而且其道德坐标的原点是万物,上面引用的韩非的例子中,实际上在“三材”关系之外,还有一位“居民”,就是“物”,这是不能无视的因素,那里物和人是分开的两个概念。显然,在韩非那里,人就是人,物就是物。人不是物,物不能是人。但是,人与物的联系在万物,人是万物之一的存在,万物理当是物的世界里的一个大家族。
考虑到“物”与万物的关联性,在进行万物内涵的界定之前,有必要辨别一下“物”与万物的相互关系。词语学告诉我们,在一般的意义上,“物”的出现在先,“万物”的出现在后;先有单词,然后再有术语概念的出现,这是常例。在这个意义上,“物”具有万物的意思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物”是形声词,从牛,勿声。“勿”是一种杂色旗,表示杂色。《说文解字》:“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6]53用“万物”来解释“物”,也充分说明存在用“物”来表达“万物”这个现实的情况。为什么要用“物”来表达“万物”,不能直接使用“万物”呢?这是因为从“物”到“万物”的出现,经历了一个进化发展过程的道理。关于这个,可以来梳理一下法家思想家“物”与“万物”的使用情况。不难发现,《管子》“物”大约出现340次,其中“万物”的概念约有123个;《商君书》“物”大约出现28次,其中“万物”的概念约有5个;《韩非子》“物”大约出现100次,其中“万物”的概念约有26个。总的情况是,“物”的使用大约有468次,其中“万物”有154个使用例,“物”的用例约是“万物”的3倍。
所以,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就是“万物”的出现,标志着人理性认识能力的提高。“万物”不完全与“物”相同,在外延上,它无疑要小,因为它仅仅表示有生命的存在,诸如动物、植物。所举的韩非的例子,也不难推测。在语言发展的阶段,“物”、“万物”、人的区别已经进到精当的地步,所以,在韩非的场合,物中五万物,物中无人。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的推断,语言发展实际当是一个曲折而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不仅同一地区出现差异不是怪事,而且不同地区因交通等手段的限制,出现一些因差异打破时限的情况也是常见的,这是必须有思想准备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些思想家那里,实际上也不难找到反证的例子。下文拟在梳理“物”、“万物”的具体关系中,来详细彰显法家人是万物之一存在的宇宙居民的运思轨迹。
1.“事物”的误解
熟悉中国文化特征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喜欢使用事物这一概念,而不用万物的概念,对事、物、万物、事物概念,缺乏理性差异的辨明。
首先,“事物有所比”。实际上,事物的思想史用例,在《管子》那里也能找到:“故口为声也,耳为听也,目有视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当生者生,当死者死。言有西有东,各死其乡。”(《管子·白心》)[3]226嘴巴能够发音,耳朵能够听声,眼睛能够视物,手能够通过手指形状、姿势表达具体的意思④,足能够走路,具体的事物都有一定的归属;诸如生死、东西都有各自的归属。这里的事物,一般中间没有隔开的标点,所以,就把它解释为事物,对此,应该说没有例外的情况。
不过,这里“事物”的具体内涵,显然不同于今天正在使用的事物的意思,“事物”当为“事、物”,包括“物事”和“物”两个方面。如把“口为声”作为一个行为的话,在这一行为过程里,起码有“口”和“口为声”两者的参与。“口”肯定不是“事”,只能属于“物”的范围;“口为声”却不是“物”,只能归入“事”的内容,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管子使用的“事物”,就包括“口”和“口为声”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他的情况也一样。因此,简单用“事物”来加以现代的解释是错误的。
其次,物事的重点在“事”。当然,“物”也有“事”的意思,诸如“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管子·形势解》)[3]323,就是证明之一。这里的“山”,是无生命的存在物,与“惠”、“慈”、“忠”、“孝”等具有相同的语言作用,因此,“惠”、“慈”、“忠”、“孝”的道德行为自然也属于“物”的一种。可以说,这是最原始的“物”的用法,相当于我们具体所说的“事”即物事;商鞅的“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商君书·农战》)[2]35,也是这种情况。这里的“使官制物”就是使用官吏来制御物事,“物”就是“事”⑤,最为精当的表述就是物事。在这个意义上,“物”、“事”是同一的,这也是今天事物这一词语成立的语词基础。关于这个,“或曰:人主执虚后以应,则物应稽验,稽验则奸得。臣以为不然。夫吏专制决事于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计书以定,事以一岁别计,而主以一听,见所疑焉,不可蔽,员不足。夫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则耳不得不闻。故物至则变,言至则论。故治国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见遁心”(《商君书·禁使》)[2]175-176,也可以说明问题,“则物应稽验”、“物至”的“物”,其意思是相同的,指的都是物事的意思,或者说记载的事件,但称为“物”。
2.“物”与“万物”的置换
可以毫不隐讳地说,“物”与“万物”之间的演进关系,实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中,这方面的拓展又长期处在一个停滞的阶段,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就更如大海捞针了。只能是依据资料进行推测。
首先,“物”就是万物。最初的“物”概念的使用,仿佛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万物都囊括其中了,“‘怀绳与准鉤,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故圣人博闻多见,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对形,曲均存矣”⑥(《管子·宙合》)[3]60、“‘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楟,擿挡则击’,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恶声美,是以圣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类来也。故君子绳绳乎慎其所先。”(《管子·宙合》)[3]63这里的“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对形”、“物之性”的“物”,显然都是万物,不限于人类。可以推测,这个时段上的人类,自身与物没有形成明确区分的意识。
其次,“物”与“万物”的置换。在这个阶段,思想家心目中的物就是万物,诸如,“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商君书·农战》)[2]36、“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商君书·靳令》)[2]109,“知万物之要”、“知物之要”,指的是同一件事情,所以,这里的物就是万物,万物就是物,在具体运用上并没有严格的限制分工。
最后,“物”实指人以外的万物。随着理性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实践,使人开始明显意识到自身与其他种类之间的差异,这时已经具备了类意识。这里有几种情况。
第一,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辩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国故不治”(《韩非子·扬权》)[4]141-142,“物者有所宜”的“物”,指的就是鸡、狸等生物⑦,不包括人自身。
第二,人与他物的区分。“圣人裁物,不为物使”(《管子·心术下》)[3]223、“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韩非子·难三》)[4]914、“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韩非子·八说》)[4]1030,“圣人裁物”以及“因物以治物”和“因人以知人”,前者是从人到物的方向,后者是物到人的向度,人、物之间界限非常分明。
在这个层面上,有时为了强调人与他物的区别,就用“外物”来表示,“凡人之为外物动也,不知其为身之礼也”(《韩非子·解老》)[4]376,就是这种情况。标明了物是外在于人的存在,从表达上也明显可体会出理性的进步。
3.“万物”与人的对应
这当是人的自我意识得到深入发展的产物。如果说“圣人惟能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举要以致万物”(《商君书·赏刑》)[2]134,只是昭示了圣人在万物中具有绝对地位的信息,人仍然是万物中居民的话,那么,下面的例子就能在更为普遍的层面上说明这一问题,“地广,民众,万物多”(《商君书·君臣》)[2]169、“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管子·形势》)[3]43-44、“地生养万物,地之则也。治安百姓,主之则也……地不易其则,故万物生焉。主不易其利,故百姓安焉”(《管子·形势解》)[3]324、“然而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管子·白心》)[3]224“民众”和“万物多”显然是两个主题,这里的万物中没有百姓,而“万物之于人”的表述也显示,万物已经成为人以外的客观存在,显然,这是一个新的视野,这也为人对万物负有不可推卸伪责任的机制设定了理论前提。当然,不能排除人对万物控制欲客观存在的任何可能,这完全依赖于具体调节实践的发展情况。
“生养万物”是“地之则”,与之相对的是“治安百姓”的“主之则”;“万物生”的前提条件是“地不易其则”,地不能随便改变规则、规律⑧;“百姓安”的前提条件是“主不易其利”,君主不能改变整治社会的规则即法度。下面的情况也一样。天与明君圣人相对,“一物”与“一人”相对,“一物”是万物中一物,“一人”是民众百姓中的存在;“行其所行”的意思就是按本有的自然规律运行,这样就能实现万物、百姓“被其利”的客观效果。显然,这里所显示的价值追求取向是依顺天道来进行社会的整治即演绎人道,这跟法家重视天道客观规律而并非一味人道相一致,这一点是至今的研究一直忽视乃至无视的事实,也是情感先行而抛弃法家资源的关键所在,这有失理性。
总之,法家的世界是宇宙的,呈现的是“万物交通”(《管子·度地》)[3]305的祥和景象;万物和谐地相处,各种物类在各自的疆界里,从事着属于自身而不得不为的事务,即“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管子·五行》)[3]241-242;人不过是万物之中的一个存在,人与万物相对,是为了肩负自身对于万物宇宙不可推卸的责任。显然,法家具有明显的宇宙居民的意识,区别于儒家的自己中心,这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关节点⑨。
三
在上面的分析中,万物是法家道德哲学的坐标原点的问题已经得到确认,人是万物之中的一个存在的定位也已明辨。那么,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依据是什么呢?
1.“地知气和,则生物从”
在比较原始的思维层面上,涉及万物生成的问题时,没有不与天地相关联而审视的,诸如“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管子·度地》)[3]305,实际上这不仅是一幅万物在动态形下层面活动的图画,而且昭示了万物如何产生的信息;万物由气而产生,具体的过程是经过“天气下,地气上”的作用,天地之气的运作达到和谐的时点,万物就会自然产生,即“会请命于天,地知气和,则生物从”(《管子·幼官》)[3]305,应该说,生物是有生命的万物,是万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道家、儒家思想家没有使用的概念,也是法家思想家对中国和世界文明的贡献。
生物里包括人民、鸟兽、草木,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即“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管子·七法》)[3]28。就数量而言,与无生之物相比,有生之物并不占多,不过种类比较齐全,即“均有”,生物之间客观存在着无形的生态平衡和谐的机制,而且在时代的发展过程里,这没有改变,所以,称为“未尝变”,这是宇宙的自然规则。显然,天地是万物的本源,是万物的父母,即“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管子·水地》)[3]236,人自然在万物之中,“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就是这一道理的具体而充分的回答。
2.“道无根无茎……万物以生”
上面虽然聚焦万物生成的问题,明确地界定了万物有天地之气的和谐而产生,但严格而言,这仅看到了万物与天地自然的密切相关性,而在万物具体如何产生的关键环节上,并没有实现实际的连接。这里以管子资料来说明,因为其他思想家仅偏在万物与道的关系的设定以及万物本有概念的使用上,据此也就不难推测,法家当是万物自然生成论思想的代表之一,在他们的视野里,万物是自生自灭的,这与道家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诸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51章)[7]136-137、“天地立名,〔万物〕自生,以随天刑”(《黄帝四经·经法·正乱》)[8]511、“参〔于天地,稽之圣人。人〕自生之,天地刑之,圣人因而成之”(《黄帝四经·经法·兵容》)[8]514,就是最好的证明。
至此,不得不质问的是,万物在天地之气层面里的规定,不过是万物形下运动的情况。在形上的意义上,万物的生成是由道决定的,“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管子·内业》)[3]269、“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韩非子·主道》)[4]66,就是答案。道虽然没有根茎,无叶花,但万物依赖它以生长,依仗它以成就。具体而言,“道”一方面是万物生命开始的象征,万物的起始离不开“道”的推动;另一方面,“道”还是“是非”的纲纪即标准,在法家的心目中,“万物莫不有规矩”(《韩非子·解老》)[4]422。也就是说,万物的是非标准在自身,这个标准对个物来说都是相异的。换言之,个物自身掌握着自身的命运,根本不需要外在于自身的他者来左右。显然,这充满着对个物价值和权利的重视。
正如前面明确的那样,人类社会的整治,就是运用天道来演绎人道的实践,对道的“始”和“纪”,落实到社会统治者的角色上,就是“守始”和“治纪”的事务。由于“始”是万物的初始,即万物之所以为该物的本初样态,故“守始”的工作到位了,“知万物之源”也就落实了;由于“纪”在个物本身,相异的个物具有相异的“纪”,故“治纪”的事务就是依据个物的特性来进行实际的治理,这样才能知道治理的方法是否实际对每个个物起作用,即了知“善败”的情况。所以,在这个视域里,无论是“守始”还是“治纪”,其目的是了解“万物之源”和“善败之端”。因此,“始”、“纪”是“守”、“治”行为所依归的惟一对象;显然,这也是“道”的不同表达。
3.“道者,万物之所然”
在法家的视野里,道不仅是万物生成的元素,而且“道者,诚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民治财育,其福归于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管子·君臣上》)[3]166、“道者,万物之所然也……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道与尧、舜俱智,与接舆俱狂,与桀、纣俱灭,与汤、武俱昌……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事得之以败,得之以成”(《韩非子·解老》)[4]411、“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商君书·农战》[2]36)道是万物之所以为该物的根本性存在,“诚人之姓”的“姓”是“生”的意思,“诚”即“成”;在静态的层面上,它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物即“非在人”;但是,在动态的连续境遇中,它却在宇宙一切万物之中。具体而言,天的“高”,地的“藏”,圣人的“成文章”,都与得道相关切。
就人类社会而言,道实际演绎的实践表明,“常道”、“常法”是其具体的形态。“常道”是道在治理民众实践中的静止样式,“常法”是处理财物事务的客观凝聚样态,离开它们,就无法解决治民和生财的实际事务;所以,圣人只要“执要而待之”就非常充分了,如果不是“待之”,而是依归个人的臆想而有为,那显然是没有“执要”的缘故。因此,“执要”的行为一定是自然无为的行为,这样的必然结果就是“民治财育”,这是“重道法”行为的最为现实的效应。道之所以能够在万物纷繁的现实生活中,与万物实现默契的对接,关键在于“道”的内涵是无限的,道与尧舜、接舆、桀纣、汤武的“俱智”、“俱狂”、“俱灭”、“俱昌”的情况,就是具体的说明。本来“智”、“狂”、“灭”、“昌”是尧舜、接舆、桀纣、汤武各具的特点,“道”能与他们构成“俱”的关系,说明“道”的内涵的无限广泛性,以及在形上的道家式的“无模式”⑩;它不分具体的对象,施行即物而形;一律公平对待,实践即物而德。可以说,这仿佛海纳百川的胸怀一样。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万物死生、万事的败成,在经验形下的层面,道并不直接作用于万物,也不直接演绎万事。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实际上直接取决于道的实际参与的程度,这种参与程度并非为道本身所决定,而为社会的统治者所决定。因为,人类文明史的实践鲜明地告诫人们,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虽然是自由自在的,但并不适宜于人类生存,人类必须过群居的生活,从而来聚结力量以有效地对抗自然界其他力量的侵犯。群居生活的有序化,要求有具体人类管理群居的集体,这是历史上最早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出现,人类以后的社会,无论社会的形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人与人之间这种在群体中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一直没有变。在社会整治的实践里,如果君主能够按照道的精神来治理社会,那万物必然生机勃勃,万事势必硕果累累;如果君主不能依归道来行为,那万物一定死路一条,万事只能以失败告终。道对一切都是一视同仁的,关键在当事人实现的体道的程度,这直接决定着当事人最终能够实现的合本性规律发展的程度。对个人的行为实践也是一样的,在这种境遇里,个人体道的水准就决定着自身心境等的调适程度。
实际上,“道”的“无模式”不是强行给予你,让你没有任何选择地接受,而是抱着谦恭的态度,让你自己决定在多大程度上选择它,对你选择的结果它始终本着一种“接受的态度”(11)。这是整体上的情况,在具体的领域,“道”还有具体的反映和价值实现,这也是“道”的“无模式”对象化的实现。如果说,在“道”与万物的坐标里,“道”是“万物之始,是非之纪”,是在静态层面上得出的结论的话,那么,“道”是成就万物并规定万物的发展方向,就是在动态视域里做出的总结。
四
自然作为中国自然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人们不难在《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那里找到用例,这个在《先秦道家的道德世界》的《绪论》中已经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12);中国的自然与西方、印度的自然观念是相异的(13)。大家知道,西方在20世纪70-80年代,自然哲学的重新燃起和热唱,主要是诸如美国等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在经济的飞速发展过程中,无形中发现,虽然得到了可见的经济利益,却失去了与人息息相关的美丽的自然环境,尽管两者的发生不同时,但相隔的时间并不遥远。所以,一些学者提出了经济的发展不能无视自然本有的价值,这要求企业的行为必须在尊重自然价值的基础上进行;随之,环境伦理学也应运而生,并成为至今全球面临危机时的重要启示因素。
法家在当时的潮流下,选择法度作为拯救社会的武器,这主要在于它以万物为对象的公正性。但是,如何能够保证这种人类宇宙居民的思想得到日常的自觉,就是问题的关键。法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武器在“自然”的设定。当然,具体的情境与上面所说的上个世纪自然哲学的热唱是有区别的。法家重视“道法”(14),道法是由道而法的标志和具体落实。在这个意义上,法家推重的法度,自然是大道精神的化身,是公正的使者,这是儒家式仁义无法企及的地方,“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此万物之利,唯圣人能该之”(《尹文子·大道下》)[9]10,“圣法”之所以为“圣法”,在于由道而法的“道法”,这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人的个人情感无法左右它,所以,能够实现“无不治”,万物都能够享受其实惠,这是强调仁义之爱的个人榜样感化的方法所不能比拟的。为什么“道法”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答案自然在其内在实质的公正无偏处,“倍其公法,损其正心”(《管子·任法》)[3]257,所以,“法之侵也,生于不正”(《管子·法法》)[3]91-92,在现实生活里,“不以私害法”(《商君书·修权》)[2]110,贤明的君主,“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韩非子·饰邪》)[4]366,最后达到“万物崇一”(《管子·正》)[3]254的效果。这是因为,“夫道,所以使贤无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无奈愚,何也?若此,则谓之道胜矣。”(《慎子逸文》)[10]9-10这是道法具有威慑力的枢机所在。
那么,为什么“道法”能够产生如此的效果?其奥妙自然在法家思想的内在设定。人道是天道的形下演绎,无处不在的道,在形下的现实层面呈现的是“无模式”,诸如“无德无怨,无好无恶”(《管子·正》)[3]254、“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韩非子·解老》)[4]411,就是具体的佐证。法家之所以承继道家的“无模式”,其关键也在对万物本性自足的认定,因此,万物时刻实现着自得。大道的“无模式”,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对应,这种对应显然不是毫无根据的随意,而是紧紧依归个体本性特征而抉择的对应,所以,就有“夫道者虚设,其人在则通,其人亡则塞者也”(《管子·君臣上》)[3]166、“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命之”(《管子·兵法》)[3]325-326的故事,大道的无形在万物那里显示的是鲜活的通灵,没有不可以成就和化育的情况,而在没有万物的情况下才是真正僵死的“虚无”。但是万物之间相同的是各自本性的自足,本性之间的差异始终是客观的永恒,这就是“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管子·形势》)[3]41-42、“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管子·白心》)[3]225所包涵的奥妙。出现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就在个体与道实现实际对接的状态,因为,道是接受性的,不是强行给予性的,这在上面已经提及。这既是大道所体现的“一”,也是万物在本性上所显示出的统一特点。
完全不能排除个体本性本有之间的差异,这是万物五彩缤纷的内因,没有这些差异,就不可能出现多样的万物,如果个体违背自己的本性而以外在的标准为依据来进行行为运思的话,这就是背道的行为,“因自然”(《韩非子·大体》)[4]555的枢机和重要性就在这里。其实,因自然就在于尊重万物的个体特性,“故不乘天地之资,而载一人之身;不随道理之数,而学一人之智;此皆一叶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丰年大禾,臧获不能恶也。以一人力,则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故曰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韩非子·喻老》)[4]451、“鸟飞于空,鱼游于渊,非术也。故为鸟为鱼者,亦不自知其能飞能游。苟知之,立心以为之,则必堕必溺。犹人之足驰手捉,耳听目视,当其驰捉听视之际,应机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须思之而后可施之,则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济。”(《慎子逸文》)[10]14对人类而言,不得不行的是“乘天地之资”、“随道理之数”,这是“随自然”的行为,自然就是老子所说的“万物之自然”,即万物的自然本性。
由于万物的自然本性都是自足的,所以,只要充分因随万物本性、创设适宜他们本性发展的最佳条件,就能实现财富的最大收获。如鸟会飞、鱼会游、耳能听、目能视,这些都是本性已经装备的能力,无须任何思考,只要自然而为就行;“任自然”的自然,也是自然本性的意思(《尹文子·大道上》第2页)。
毫无疑义,法家道德哲学的坐标原点是万物,而不是人,人仅是万物之中的一个星座,绝不是全部,这与法家强调依据天道来演绎人道紧密相连,也是法家与道家同在人之外寻找依归准则的共通之处。所以,仅仅看到法家执法严峻的一面,就妄断法家残忍而无情,这是有失理性而不全面的;当法家把人与万物相对时,也并非儒家思想家那样强调人是万物之灵而自鸣得意的表现,而在昭示人对万物所肩负责任的重要性,“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淡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故使人无离法之罪,鱼无失水之祸”(《韩非子·大体》)[4]555,就是最好的回答,“人无离法之罪”指的是人类社会有法可循的规范性,这是人的和谐的方面;“鱼无失水之祸”指的却是宇宙环境的和谐合理的完美性,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方面。法家的道德哲学就是一部以万物为原点,具体演绎完成的叙事诗。万物的视野是至今的法家研究所忽视的死角。我们应当从原典出发,让资料说话,以史引论,任何前识最多也只能是一时的产品,不可能成为永恒的可以依归的真理;古代文化的价值,永远只能在启发后人的问题意识那里得到确证,而不是成为为人所用的一成不变的程式!这是为21世纪文化资源生发效用而营建具体条件的当务之急。
[收稿日期]2010-03-08
注释:
①详细的情况是:《管子》“天”字约出现827次,其中“天下”的用例约有466次,“天地”的用例约有69次,“天道”的用例约有34次(其中包括“天之道”的用例12次);《商君书》“天”字约出现66次,其中“天下”的用例约有59个,“天地”的用例约有1个;《韩非子》“天”字约出现367次,其中“天下”的用例约有259个,“天地”的用例约有15,“天道”的用例约有2个(包括1个“天之道”)。
②详细的分布是:《管子》“人”字的用例约1543次,其中“人道”的用例约有3个,“人事”的用例约有10个;“民”字的用例约1267次,其中“人民”的用例约有6个,“民众”的用例约有6个,“民力”的用例约有16个,“民心”的用例约有22个,“民生”的用例约有3个,“民利”的用例约有11个。《商君书》“人”字的用例约183次,“民”字的用例约529次,其中“人民”的用例约有1个,“民众”的用例约有10个,“民力”的用例约有8个,“民生”的用例约有2个(动词用法)。《韩非子》“人”字的用例约1662次,其中“人事”的用例约有1个;“民”字的用例约509次,其中“人民”的用例约有9个,“民众”的用例约有3个,“民力”的用例约有8个,“民心”的用例约有6个,“民利”的用例约有3个。
③《管子》“百姓”的用例约有105个,《商君书》“百姓”的用例约有6个,《韩非子》“百姓”的用例约有33个。
④尹知章注释“承从天之指”曰:“指,意也。”(《管子·侈靡》)可以参考。
⑤高亨解释“制物”为“断事”。参照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第36页注释30。
⑥《管子·宙合》在形式上由“经文”和“解文”构成,单引号里的表示“经文”;下同。
⑦管子有“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管子·七法》)的说法。
⑧参考“《解老》中关于考察事物之‘道’与‘理’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像《管子·七法》中的‘则’被理解为自然的客观规律,人们利用它或者付出代价地忽视它。”(《天人分途》,〔英〕葛瑞汉著、张海晏译《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第328页)这里是从自然规律来加以理解的。
⑨万物也是道家的标志性概念之一,诸如《老子》里“物”约有37见,“万物”约有20个用例。
⑩参照“‘无’形式会解放那些维持专门哲学必需的抽象认知和道德感受力的精神力量,允许它们当前无需任何概念、理论和精心设计的道德规令的中介,而成为为日常事务输入灵感的具体情感。正是通过这些具体情感,我们才得以理解这个世界并最优化我们对人类经验。”(《哲学引论》,〔美〕安乐哲Roger T.Ames、郝大维David L.Hall著,何金俐译《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44-45页。)
(11)参照“道家的心理状态在根本上就是科学的,民主的;儒家与法家是社会的,伦理的。儒家的思想形态是阳生的,有为的,僵硬的,控制的,侵略的,理性的,给予的。道家激烈而彻底地反对这种思想,他们强调阴柔的,宽恕的,忍让的,曲成的,退守的,神秘的,接受的态度。”(《道家与道教》,〔英〕李约瑟著、陈立夫等译《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71页)。
(12)现在列出墨子的自然资料,即“正五诺,若人于知,有说。过五诺,若负,无直无说。用五诺,若自然矣。”(《墨子·经说上》,孙诒让著《墨子闲诂》,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第214页)另外,参照《绪论》,许建良著《先秦道家的道德世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29页。
(13)具体可以参考“Man in Nature”,Alan Watts.(2002) The Tao of Philosophy.Boston,America:Turtle Publishing,pp.17-34。
(14)《管子》《韩非子》“道法”的用例约有9个;《荀子》约有3个;《黄帝四经》专门有《道法》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