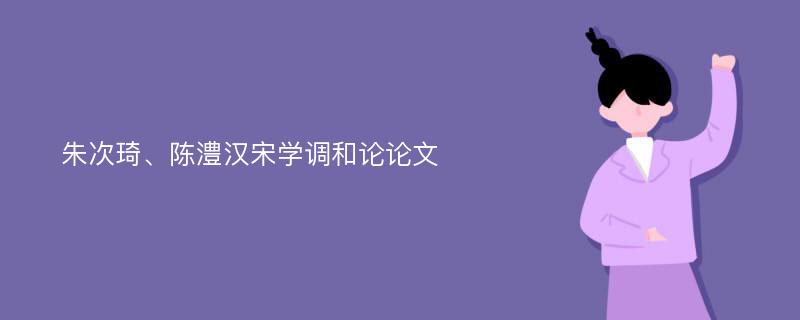
朱次琦、陈澧汉宋学调和论
张纹华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文法学院,广东 茂名 525000)
摘 要: 同治年间广东宋学的发展,为汉宋学对话提供了可能性,以朱次琦、陈澧为代表的广东学者使嘉道年间由阮元、林伯桐奠定的广东汉宋学调和显得脉络清晰。无论朱次琦、陈澧主张的汉宋学调和差异有多大,汉宋学调和都有益于广东近代儒学的健康发展,与广东近代传统儒学繁兴互为表里,但它无法改变儒学相对衰落的结局。
关键词: 咸同年间;广东汉宋学调和;朱次琦;陈澧
1852—1882年广东汉宋学调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广东汉宋学的同时繁兴为时代背景的。1852年身在山西的朱次琦(1807—1882),已潜生归隐乡土之念头。1858年朱次琦创建礼山草堂,以学孔子之学,去汉宋学之别,加入由陈澧推动的广东近代汉宋调和的大讨论之中。早在1852年,陈澧(1810—1882)已结束其长达19年的会试生涯,开始纯粹的读书人生活。1852—1861年广东汉学衰落之时,陈澧及其门人桂文灿等都潜心著述,既为广东汉学复兴奠定文献基础,也沿承嘉道年间广东第一代汉学家倡导的汉宋调和。因此,朱次琦、陈澧几乎同时登场,成为此期广东汉宋学调和的关键人物。1861年陈澧为朱次琦编纂的《朱氏传芳集》亲题书名,是目前可知的朱、陈相遇并留下重要文献记载的唯一一次。相似的人生轨迹没有让朱、陈走得更近,源于他们大异的学术旨趣。从汉宋学调和的本质、路径到目标,朱、陈都是大异其趣的。不满阮元推尊专经,且重视考据而疏于阐述义理,沿承由阮元、林伯桐奠定的嘉道年间广东近代汉宋学调和,是朱、陈有此巨大分歧的根本原因。
立足自身特色,保证客流量;提高旅游产品的吸引力,要有区别于其他旅游地的特色;了解游客的心理,游客来到农村就是想要品味乡村原汁原味的特色文化;不可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应加强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
一、朱次琦、陈澧汉宋学调和的本质
汉宋学是先秦儒学发展至汉代、宋代的产物,分别以《六经》《四书》为其治学的主要范围,形成或重训诂考证,或重义理阐发的两种注解经典的形式,产生以本本为重,还是以经世为任的彼此争论不休的话题。迄至近代,虽然调和汉宋学成为广东近代传统儒学的主导方向,但调和后的汉宋学到底是旨在通经、致用、服务科举,还是专经、本本、摒弃科举更多一些,是存在明显的分歧的,而这些分歧直接影响着汉宋学家的经学生涯。
(一)朱次琦以通经致用、重视时文制艺作为汉宋学调和的本质
朱次琦调和汉宋学是以“五学”(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治学章体现出来的,因此,“五学”的本质即是其调和汉宋学的本质。以在“五学”中居于尤其高的位置的经学、史学与史学发展至近代的新支掌故之学来看,通经致用就是朱次琦调和汉宋学的本质。
那时,他是北京K T V的常客,发稿多、收入少的梁璐是典型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家里有六个姐姐,父亲是一位医生,生活并无多大压力。他有更多机会探究兴趣的部分:辞职、旅行、在丽江开旅店,他与前妻的潇洒生活曾经登上了2 0 0 8年的《鲁豫有约》。
广东经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提出专经是由学海堂开始。学海堂以“通经服古”标榜,但在如何通往通经的道路上,无论是阮元、卢坤还是郭崇焘都提到以“自择一书肄习”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自1835年以后,学海堂每年一届的公举专课肄业生评比活动,这是以政策导向的方法推动专经。在1904年“癸卯学制”实行之前,学海堂、菊坡精舍、广雅书院都是以经学、史学、理学、文学为课士内容的,且将“学求致用”作为“四学”的方向。与朱次琦尤其重视经学、史学不同,陈澧之学以经学为本,“我之学在分四科,而以经学为本”[2]385。陈澧视界下的经学即是专经,虽然他在某些言论中反映其是重视经世致用的,但他的经学生涯明显是尤重本本的。
从范仲淹、王安石到黄宗羲、顾炎武,他们均面向社会现实,讲求将学术应用于社会实际。这些人都入经出史,善于从史学中寻找解决当下政治、经济问题的办法,将史学的功能与作用发挥至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显然与程朱理学家有巨大的不同。一方面,朱次琦主张通经致用。他认为:“吾闻经师之法,日诵三百言,数以贯之,不及三年,虽在中人,《五经》皆辨。……然则通经将以致用也,不可以执一也。”[1]16-17“经谊,所以治事也,分斋者歧矣。经学,所以名儒也,分门者窒矣。”[1]16通经致用的治学思想必然使朱次琦将经学重于理想、上追三代的精神与史学重于现实、当取法近世且穷其源的治学思想相结合,以提出经史结合,并将史学的价值定位于经世致用,而且,经史会于道并以此复兴儒学是朱次琦提出经史结合的根本原因。就是在这一点上,朱次琦是有别于明末清中叶以来顾炎武、章学诚、龚自珍、魏源等与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的通经致用思潮的。另一方面,朱次琦对将嘉庆、道光年间出现繁兴的掌故学摆在一个等同于经学、史学的高度。朱次琦认为:“《九通》,掌故之都市也。士不通《九通》,是谓不通……掌故之学,至赜也。由今观之,地利军谋,斯其亟矣……知掌故而不知经史,胥史之才也……经史之谊,通掌故而服性理焉,如是则辞章之发也。”[1]17-18凡关涉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水利、文物、制度等均属于朱次琦所指的掌故学的范围。日后,门人简朝亮将掌故学从中国古代的旧学拉进了新学的领域,与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重视掌故学是相当一致的。
以上之学即是朱次琦倡导的所读之书,是必须遵循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一言以蔽之,则是朱次琦明确提出的“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1]16。朱次琦赋予“五学”以通经致用的本质,并将它与能写时文制艺相结合,使门人“应天下国家之用”拥有实践的路径。虽然收入《广州大典》的朱次琦的《四书讲义讲稿不分卷》(以下简称《残稿》)残缺不全、字迹模糊、编排凌乱等,但它解决了朱氏门人多科场显赫的疑问,就在于朱次琦附以《残稿》作为开馆讲学的讲义。明清科举考试制度规定的八股文,其内容必主《四书》《五经》,形式则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8部分组成,后4部分为正式议论,中股为全文的重心。《残稿》以《四书》摘句为文,它没有按照这8部分摘抄会试文章,但其轻重有别还是体现了八股文以中股为重心。因此,朱氏门人具备熟练运用经学、史学、文学等知识驾驶八股文的写作能力,朱氏门人科场优秀则为自然。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集成电路企业通过政府搭建的产学研商平台,与大学、科研机构进行良好高效的互动,一方面研究满足市场要求,实现利益共享,另一方面推动科技领域的基础前瞻性研究,达到经济发展与科学研究两不耽误。同时,集成电路企业之间要互相学习、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打破传统,构建战略技术联盟,共同开发,最大效益地利用好经济、科研、人力等资源,共同促进集成电路的技术创新。
朱次琦以“实学”赋予“五学”,纵论经学。他以儒道作为治学的旨归,因此,虽然其重视声音训诂与以训诂明义理,但反对以考据为一学。“注疏者,学《十三经》之始也。古今名家声音训诂,去其违而终之经谊焉可也。”[1]17朱次琦本人即是科场的显赫者,但他没有注疏任何一种儒家经典。反之,以其临终前焚毁的7种出处经史的著述的命名来看,多是阐发儒家大义的。因此,朱次琦提倡的汉宋学调和的本质影响其学术人生。
(二)陈澧以专经、尤重本本、摈弃时文制艺为调和汉宋学的本质
宋学重经世明道,顾炎武认为“经学即理学”,朱次琦也以经学倡明正道,经学自然居“五学”的首位。朱次琦认为:“《六经》者,古人已然之迹也。《六经》之学,所以践迹也。践迹而入于室,善人之道也。”[1]16将《六经》作为具体历史经验的记载,后人必须从古籍的记录中学习儒道,这是朱次琦将经学作为主导地位与分析汉宋明清诸儒治经得失的根本依据,更是他有别于王阳明、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说的主要方面。
甘肃省临泽县辖鸭暖、倪家营2乡,新华、蓼泉、板桥、平川、沙河 5镇,74个村,76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4.6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2.52万人,占总人口的86%。近年,临泽县在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着力解决农村饮水卫生、供水量不足等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34项,解决了44个村1.8万户6.92万人的饮水问题。
陈澧以经学为本之学,是有进退二途的,进者是通经,退者是专经,且是循序渐进的,或者说是以专一经而逼近通经。“讲《论语》必二年而毕,《大学》《中庸》《孟子》一年而毕,使其学者三年而通《四书》,而后进而讲《五经》。”[3]83在难以通《六经》的情况下,陈澧主张通一经之学,通读一部注疏。“夫治《五经》而不通,不如治一经而通。”[3]79“夫《十三经》疏,治经者原不必全读,经学以专经为贵,专某经则专读某经之疏,其余乃旁涉耳。”[2]359虽然陈澧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专经作为通经的手段,但他是认同专一经的,且以专经为培育人才的手段,就是在这关键点上大异于朱次琦。由于提倡专经,陈澧肯定胡瑗的分斋教学法,认为此法敦尚行实,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在其太学,有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使各以类群居讲习,故分斋教学是孔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的遗意,可尽其材[2]24。
一方面,陈澧强调必须阐发经学之义理,提倡以经学治世。“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遂至于终年读许多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此真与不读书等耳。此风气急宜挽回也。”[2]358“经学所以治天下,无经则不可以治天下矣。……然则经学之治天下,乃其大义耳,名物训诂之小者,与治天下无所关系也。”[2]360在反对汉学家纯粹之考据,重视经学之修、齐、治、平的功能上,陈澧是一致于朱次琦的。陈澧还明确将学术、治术二合而一,将此作为“学风变而人才由此出,世运由此转”[2]359的关键,认为此举“有益于身,有益于世”[2]359。另一方面,陈澧本人的教学独重学术而罕言政事。“近儒则博闻者固已多矣,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谈,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3]175朱次琦、陈澧都推崇顾炎武,朱次琦以顾炎武提倡的经学放于理学以充实理学的经世特征,陈澧则取顾炎武治学之“博证”而舍其“致用”,因此,陈澧强调的经世致用是有片面性,他更多的是学术而殊非治术,是本本而殊非经世。
虽然陈澧试图以学术疏离、回避当下,但他是主张读书必须与当下相结合的。“详细思绎,引而入于身心,实而验之于今日之事。”[3]176因此,陈澧反对时文制艺。“省城及近县大馆,师十余人,弟子千余人,所讲授者《四书》《五经》。……然则学术日衰,人材日少,何也?但为时文计,而非欲明圣贤之书故也。”[3]83由于门人失却将读书作为科举之门街,门人之所学难以体现在仍然是以科举选择人才的制度下的“应天下国家之用”,难以将学术转化为治术。因此,陈澧反对时文制艺,表面来说是锐意改革的教育实践,但当它与专一经、尤重本本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即传递出陈澧之学试图游离社会现实、自我边缘化的诸种迹象。
实用性是指融合标准应符合当前军民标准的基本情况,即可用于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军民融合的具体工作中。为保证标准的实用性,必须同时考虑军民双方标准的实际情况。
二、朱次琦、陈澧汉宋学调和的路径和目标
郑玄集汉学之大成,朱熹是宋学的创立者,郑、朱是孔子以后最著名的儒学家。在汉宋学调和中,孔、郑、朱的定位如何,决定了汉宋学调和的路径与目标。正是于此,朱次琦、陈澧是有明显分歧的。
有学者认为,秦汉以来,“皇帝号称天子,权力登峰造极”[1]515。笔者认为,该观念是值得商榷的。从表面上看,汉代皇帝似乎拥有最高的立法权,最高的司法审判权。但是在两汉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皇帝的权力却是受到诸种因素限制的。
(一)朱次琦以朱熹稽郑玄,旨在去汉宋学之别,学孔子之学
一方面,朱次琦以汉儒、宋儒都传承儒道而反对分裂道统,反对在《儒林传》之外另立《道学传》。“儒有君子小人,然《儒林传》外,立《道学传》焉,则《宋史》之所失尊也。《汉书》郑康成,《唐书》韩退之,皆列传也,奚必标异乎?”[1]16另一方面,朱次琦在郑玄、朱熹之间,尤其重视朱熹其人其学。“宋末以来,杀身成仁之士,远轶前古,皆朱子之力也。朱子百世之师,事师无犯无隐焉者也。”[1]14-15朱次琦由此开出以宋儒义理为基础的“四行”(敦行孝悌、变化气质、崇尚名节、检摄威仪)修身条。朱次琦重视声音训诂与以训诂明义理,在他看来,二程、朱熹等就是能以训诂明义理之人,即所谓“穷理格物”,由是朱次琦提出朱熹是汉学之稽的结论。“汉之学,郑康成集之。宋之学,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汉学而稽之者也。”[1]14朱次琦是绕过汉学,以程朱理学本身就兼容了汉宋学,于是“五学”治学章不容考据之学,朱次琦赋予了程朱理学丰富性与时代性。
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以诸经在学术史上存在的分歧、阅读诸经所需注意的问题、诸经之关系等为内容纵论《孝经》《论语》《孟子》《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可见陈澧本人是博通诸经的。陈澧本人虽然殊非科场显赫,但依然是中了举人的。陈澧1866年以前撰写的《汉儒通义》《汉地理志水道图说》等,多在考证文物、制度的基础上阐述汉宋学义理,随后点校、刊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十三经注疏》《通志堂经解》《通典》《续通典》《皇朝通典》《经典释文》《古经解汇函》附《小学汇函》等用去了他大量的心血。以上校点的经史著述,无疑已经违背陈氏自言的汉宋儒都是以训诂明义理了,也是朱次琦所言的独为治学之始,而非其终的与经义合。因此,陈澧的经学生涯是尤重本本的。
表面来说是推崇郑、朱之学,实则立足汉学,以宋学寻求义理的方法充实汉学,孔子之学在郑、朱之间的关系,则不在陈澧考量的范围之内,这是陈澧调和汉宋学的路径与目标。
CFRP具有比重小、强度高、耐疲劳、耐腐蚀、抗蠕变、热膨胀系数小等优异特性,并且具有一材多能、一材多用的特点,已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轮船、汽车、风电叶片、化工、机械、纺织、医疗器材以及文体用品等各个领域。对于轨道交通承载结构,CFRP能从以下几方面满足车体技术提升的需求:
(二)陈澧兼重郑玄、朱熹,旨在以宋儒义理助汉学
朱次琦将朱熹作为汉宋学的集大成者,以《六经》《四书》会通古人之义,将儒学的源头溯至孔子学说,以学孔子之学而去汉宋学之别,彰显孔子之道。“学孔子之学,无汉学,无宋学也。修身读书,此其实也。”[1]15明儒治经单刀直入,讲求明心见性,经学遂显精微,故《六经》皆我注脚。朱次琦的关注点殊非《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区别,而是心学家是否切于事与达于道。“陆子静,善人也,未尝不学,然始事于心,不始于学,而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虽善入乎,其非善人之道也。”[1]16清儒治经以训诂、校勘、考证为工夫,此乃治古书,殊非治人事与明道义。故朱次琦说:“古今名家声音训诂,去其违而终之经谊,焉可也?”[1]17朱次琦以越明清、会汉宋与溯诸古的治经方法彻底平息汉宋学之争,复兴孔子之道。朱次琦去汉宋学之别的考虑点并不是经世致用,也不是晚清汉学家以义理充实汉学的意图,而是寻找儒道,以此拯救世道人心。这种儒学彻底的回归,其实是不利于近代社会变迁所出现的思想大解放的。但回归经典本身无疑又代表了一个时代学术的终结,并可开具出新质的思想文化。
虽然1835年朱次琦被评为学海堂专课优秀肄业生,但他拒之,且终其一生不受学海堂空以待位的学长之职,并于1858年自创礼山草堂,开馆讲学,有与学海堂分庭抗礼之意。反之,陈澧任学海堂学长20多年,且由其主讲的菊坡精舍有“接学海”之誉,因此,朱、陈对嘉道年间广东汉学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他们迥异的汉宋学调和的根本原因。
陈澧以为重汉儒之行则可经世,学宋儒之义理阐释则可弘扬实学学风,经世、求真遂在咸同年间广东汉宋学调和中合体,孔子之学在郑、朱之间扮演何种角色,完全不在陈澧视界之下的。出其门的桂文灿撰写的《朱子述郑录》,以为“郑君、朱子皆大儒,其行同,其学亦同”[6]。从陈澧撰写《郑学》《朱学》到桂文灿著《朱子述郑录》,郑、朱合流依然是师徒二人汉宋学调和的对象,并蕴含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经学观。与此同时,桂文灿以汉儒《六经》为本,而略讲宋儒义理之学,著《经学博采录》,再次有力说明陈澧及其门人是立足汉学而调和汉宋学的。
三、朱次琦、陈澧对嘉道年间广东汉学的态度
一方面,陈澧在《郑学》一文中指出,惟郑学是真汉学,郑学殊非独考据学。陈澧不仅挖掘郑学是重视义理的,而且指出郑学是强调践履的,经世致用是汉学的本色。另一方面,陈澧在《朱学》一文中指出,朱学殊非独义理之学,国朝考据之学实源出朱子。因此表面来说,陈澧是以兼重郑学、朱学调和汉宋学的。但是,陈澧是由于目睹道咸年间汉学家更加普遍地忽视探索义理的现象,是旨在弥补今人讲训诂考据而不求义理的缺失而重视宋学,并由此形成其汉宋学调和的思想的。“合数百年来学术之弊细思之,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有如乾嘉以来之肤矣。况汉宋各有独到之处,欲偏废之而势有不能者,故余说郑学则发明汉学之善,说朱学则发明宋学之善,道并行而不相悖也。”[2]337因此,陈澧之学术思想即钱穆所云:“东塾所谓汉宋兼采者,似以宋儒言言义理,而当时经学家则专务训诂考据而忽忘义理,故兼采宋儒以为药。至于发明义理之道,大要在读注疏,而特以宋儒之说下侪于汉注唐疏之笺焉。”[4]而殊非徐世昌说的“兼以郑君、朱子为宗主”[5],郑、朱在陈澧视界下是有轻重之别的。虽然陈澧提倡以儒家经典原文寻觅义理,对程朱义理并没有排斥,但陈澧重视阐述义理仅仅是为了弥补汉学空疏学风。陈澧是立足考据而称许朱学的,是推崇郑玄而兼容朱熹,是讲经学而兼讲理学,这些都体现在他的经学生涯与学术著述中。除辑录《朱子语类日钞》以外,陈澧没有留下专门阐述宋儒义理的著述,反之,陈澧彰明汉儒重义理,撰写《汉儒通义》,“又著《汉儒通义》七卷,谓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2]11。陈澧著《切韵考》《声律通考》《水经注考西南诸水考》《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等,都是以考据为主,略释义理。正是由于陈澧精研郑玄学术,故迄今以来留下以“郑氏学”为主题的陈澧研究的系列学术论文。
(一)朱次琦反对嘉道年间广东汉学
朱次琦是在嘉道年间广东汉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宋学家,在13岁这一年,朱次琦由乡人有“广东汉学第一人”之誉的曾钊带着见到阮元,阮元对朱次琦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自叹不如。正是出于对学海堂提倡专经,汉学家重视考据而疏于义理阐释的不满,朱次琦自觉疏远学海堂,在讲学中多次反对以阮元为中心的嘉道年间广东汉学。
钱大昕、阮元等清代汉学家都指出汉学是以“实事求是”与“由训诂而明义理”为治学的原则与方法。阮元说:“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7]遂以“专勉实学”作为学海堂的办学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提倡乾嘉汉学。朱次琦重视声音训诂与以训诂明义理,只是他强调的义理是必须不违背儒道,并以儒道作为治学的旨归。因此,朱次琦反对学海堂人编纂《皇朝经解》,以为这是阮元在消耗广东人力。“纪文达,汉学之前茅也。阮文达,汉学之后劲也。百年以来,聪明气魁异之士多锢于斯矣,乌乎!此天下之所以罕人才也。”[1]16“《皇清经解》,阮文达之所诒也,殆裨于经矣。虽然,何偏之甚也。”[1]16朱次琦以此为“鱼虫之学”,没有留心经学著述的微言大义,故“丛脞无用”[1]15。
(二)陈澧沿承嘉道年间广东汉宋学调和
以汉学为主导,将宋学寻求义理的方法充实汉学,且其义理是越过宋儒而直指先秦两汉,由阮元奠定的广东近代汉宋学调和的路径,对林伯桐、陈澧等提倡汉宋学调和产生了重要影响。
渐兴于嘉道之际的广东汉学欠缺中原乾嘉汉宋学之争而直接与晚清渐盛的汉宋学调和接轨,并由于阮元的关系,广东近代汉学家更多的是呈现皖派学者“分析条理,皆缜密严,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的治学特点。这种不盲从汉注疏,信古而存疑,必反复考证经典原文方下结论的治学路径其实就是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等的治学主张,为通向汉宋学调和打开了方便之门。虽然阮元以王应麟《困学纪闻》、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三跋作为学海堂的首次命题,明显可以看出他崇尚汉学,但这3人尤其是清学第一人顾炎武只是反对将禅学掺杂于理学,尤反对阳明心学,而对程朱理学并无贬词。钱大昕虽不喜宋学,也不否定以训诂求义理,只厉斥部分宋学家凭空抒发义理的治学方法。有学者认为:“综观清代中叶以戴震,以及凌廷堪和阮元为代表的朴学家的学术实践,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义理探索的方式,一种是借助训诂考据的方法,来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一种是根据经籍考证的成果,恢复儒家经说和圣人之道的原始面貌。”[8]凌廷堪、阮元就属于后一种。与凌廷堪不满宋明理学不同,阮元不仅没有正面否定程朱理学,而且在晚年提倡汉宋学调和。不过,阮元强调义理、训诂两不废,其义理是从先秦儒家、汉儒中寻找,而与宋儒不涉。因此,阮元只是借助宋学寻求义理的方法,或者将寻求义理作为充实汉学的手段。他是越过宋儒而直指先秦两汉的。
林伯桐既尊推汉儒郑玄,也服膺宋儒朱熹,其在清儒中最服钱大昕,游走于汉宋清儒之间,这种博采众家之长的治学路径,其实就是对阮元兼治今文、古文与汉宋学两不废的传承。有学者指出,林伯桐汉宋学兼采思想表现为四个方面:主张“道一”观,反对汉宋学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提倡“学其所学而衷于道”;客观评价汉宋学,指出学问之事为“古今通义”;肯定程朱理学;正视汉学流弊,提出修正建议[9]。林伯桐是以朱熹不废汉学而肯定程朱理学的,是由于汉学家疏于义理而形成空疏学风而重视宋学。因此他专门撰写《朱子不废古训说》,并在《题目下偶笔》一文中提出“取二者(训诂、义理)之得而戒其失”[10],就是这种将朱熹治学拉近、纳入汉学体系的做法,林伯桐就可以平视郑、朱,从而平议汉宋学,汉宋学共冶一炉,学术门户就此打破。因此,以汉学为主导,兼采宋学,其宋学又殊非探寻程朱义理,而是直指先秦儒学古义,林伯桐汉宋学调和体现了汉学家的本色,并恪下阮元的治学特色。
梁启超不仅以“咸同两大儒”指称朱次琦、陈澧,而且指出二人皆沿承阮元主张的汉宋学调和,只是二人治学风格不同。“而东塾特善考证,学风大类皖南及维扬。九江言理学及经世之务,学风微近浙东。然其大恉皆归于沟通汉宋,盖阮元之教也。”[11]笔者以为,朱、陈治学风格之不同,既是以宋学为主还是以汉学为本的不同,也是汉宋学调和是否要逼近孔子之学的不同。如钱穆说:“是子襄虽亦主融汉、宋,而与陈东塾之见复异。东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论,则在纳康成于朱子。”[12]正是这些不同,朱次琦否定其学海堂及汉学之出身,陈澧则彻底沿承由阮元、林伯桐奠定的汉宋调和的路径。
咸同年间广东汉宋调和,是汉宋学家对于广东社会危机、儒学危机同时到来的应对,因此,即使朱次琦、陈澧主张的汉宋学调和差异有多大,汉宋学调和都有益于广东近代儒学的健康发展,与广东近代传统儒学繁兴互为表里,只是它无法改变儒学相对衰落的结局。虽然朱次琦指斥汉学过于专门,但汉学这种窄而深的研究特点其实是有益于近代社会变迁下的学术分科的,它通往的就是近代学科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1]朱次琦.朱九江先生集[M].简朝亮,编.香港:旅港南海九江商会,1962.
[2]陈澧.陈澧集: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陈澧.陈澧集: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81-682.
[5]徐世昌,陈祖武.清儒学案:4[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6058.
[6]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287.
[7]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1.
[8]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243.
[9]孙运君.试论林伯桐的汉宋兼采思想[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0-14.
[10]林伯桐.修本堂丛书:卷3[M].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11]梁启超.文集之四十一[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79.
[12]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8[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314.
The Reconciliation of Han-song Studies Made by Zhu Ciqi and Chen L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Wenhua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and Law,Guangdong Institute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Maoming 525000,Guangdong,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ng Dynasty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Tongzhi period,the possibility of dialogue between the Han and Song scholar was provided. The Guangdong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Zhu Ciqi and Chen Li made the Guangdong Han and Song dynasties established by Qi Yuan and Lin Botong in the Jia Dao period clear. Even i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advocated by Zhu Ciqi and Chen Li,the harmony between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is beneficial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nfucianism in Guangdong,and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in Guangdong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each other,but it cannot change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Confucianism.
Keywords: the Tongzhi period;the Han and Songscholar advocated in Guangdong;Zhu Ciqi;Chen Li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092(2019)03-0029-06
DOI: 10.16858/j.issn.1674-0092.2019.03.007
收稿日期: 2018-11-28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专项课题资助项目“简朝亮经学研究”(2018GZY26)
作者简介: 张纹华,女,广东南海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中国史博士后,主要从事广东儒学与广东文学研究。
【责任编校 杨明贵】
标签:咸同年间论文; 广东汉宋学调和论文; 朱次琦论文; 陈澧论文;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文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