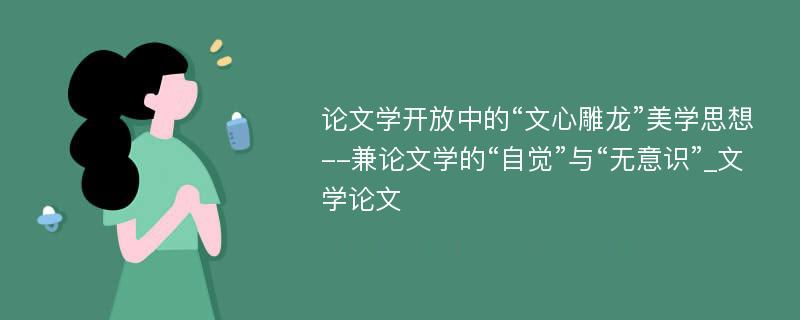
《文心雕龙》辟文学之美学思想刍议——兼论文学的“自觉”与“非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觉论文,文心雕龙论文,刍议论文,美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人们以近世习用的文学观念解析《文心雕龙》时,一系列方枘圆凿的问题便出现了:比如刘勰之“文学”是什么文学,他为什么将那么多的历史文献和文化现象统统纳入文学的范畴,他究竟是个什么家?尽管人们习惯于“历史是在由浅入深由低向高发展”的观念,但是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博大精深仍然是那样令我们震撼。如果我们摆脱今人的自负,进而用刘勰“自然之道”的思路去考索,那么看到的将不仅有刘勰似乎在注释我们所谓“文学之为文学”的一面,而且有其“文学不是今之谓文学”的非文学的一面。文学是文学而同时又不是文学,这就是笔者所说的辟文学。《文心雕龙》在辟文学方面的贡献颇有深意。
20世纪中叶至末叶,西方出现了反思文学的思潮,其中Paralittérature一派很值得一提。Paralittérature由Iittérature(文学)及其前缀Para组成。Para同时具有接近、围绕、反对、悖于等含义。国内文学界将Para一词理解为“副”或“泛”,Paralittérature因此被译成了“副文学”或“泛文学”。这类译文抓住了Paralittérature的一些积极的特征,但是还未切入要义。不仅中译者有欠深入考究之嫌,Paralittérature一派的思想家也程度不等地忽略了Para这个前缀还有导引、避开、经过、兼顾等一语通关的统筹义项。如Paratonnerre(避雷针)就既有避雷、又有导雷电的双兼含义。Parapluie(雨伞)也有遮雨和导引雨水的双关义。笔者认为,用“辟文学”一词最能体现Paralittérature的命意。
中文古汉语的“辟”(pi)字非常有趣。许慎的《说文解字》指出:“辟,法也。从卩从辛,节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也。”这一解释尚嫌拘谨。其实辟字的含义非常丰富,兼有创制/效法、典章/用度、打开/偏离、开拓/躲闪、治理/偏蔽、怪诞/大方、邪恶/清除等对折/融会的意思。辟(pi)通辟(bi),有君侯/官吏、法度/罪行、征召/斥退、畏缩/勇为、破解/搓合等悖谬/通化的内涵。质言之,以辟字作前缀,足以包容Para一词的通关义项,而且还可以补足Para所不具备的贯通文脉和熔铸典范的意蕴。Paralittérature是西方学术界针对18世纪末以来俗文学扩张所出现的理论调整。弥足珍贵的是刘勰在中古时期就开发过Paralittérature的智慧。他当时固然没有用辟文学一词,但是其《文心雕龙》对文学的理解和阐释,有效地发挥了辟文学的思想。他对文学高下精粗和成败利钝的剖析,充分展示了辟文学思想的学术力量。
一、辟文学思想原始要终的求索
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学之辟,集中地体现在辟创、辟学、辟合三大端。他在这部论著中并未专门考究辟之理念,但是辟之精神贯穿始终。
1.辟创——范文学的自信与谨慎 刘勰与他的前代和同代人不同,他不仅寻找和创造文学范型,而且也提防范型僵化。提挈枢纽,模拟经意,铸造范式,裁决文体,是辟创的规范化追求;注重圆通,默化潜移,比兴成文,放飞神思,是辟创的防范性举措。《文心雕龙》题目本身就是辟创的最佳例证。“文心”含二义,一是从作者言,指为文之用心;二是从著作讲,即所传之精神。此二义在论文处合一,通解为文之神。“雕龙”也有二用,一是比喻本著如雕龙,旨在琢磨为文之巨型叙述;二是指本书自身的作文华采问题。此二义于雕琢中聚集,体悟为文之功德。文心与雕龙并称,是对为文之神用的再一次辟合:文心深藏,隐而虚;文用凸透,显而实。文心雕龙作为标题横空出世,既有后来考据者从驺衍、驺奭处发掘出的思想——谈天雕被,也有庄子关于“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庄子·天运》)的指称——聚散华章。文心依体,雕龙贵美,体与美的崇尚凝聚着辟创的范式追求;文心空灵,雕龙尚实,灵与实的砥砺绽露出辟创的矛盾处境;文心隐约,雕龙浮华,隐与浮的褒贬反衬出辟创的去范深旨。惟此后一层,看破者不多。人们大都被文心雕龙正面的华美的用意所遮蔽,而对该标题包含的矜持、自戕、矛盾甚至贬义的警示则往往有所忽略。刘勰的辟创思想,在《文心雕龙》的书名勘定方面表现得非常深刻。其立意命篇很好地体现了文学规范与防范的平衡与补充。
2.辟学——反文学的胆识与深沉 辟创主要倾向于范式的熔铸,即使文学成为文学的创制,其作为偏正复合词的防范方面仅属纠补的成分;而辟学则更多的是反向的循环,即不使文学成为文学的可逆性运思。文学成就文“学”,是踵事增华甚至锦上添花的过程,是文学规范化、体系化和疆域化的演进;文学逆反文“学”,是删繁就简由博返约的异动,是文学自由化、潇洒化和开放化的耕作。刘勰在文之枢纽中逆反文学的成分居于上风,在文体20论中,祭祝诔诰等多种形式实际上作为非文学的因素突破了文学的行头,且不说《文心雕龙》以朴、实、质、直、真、贞、中、正、隐、晦、謔、讔、杂、俗、古、骨等一系列足以牵制或虹吸文学华采的术语,对过于文学化的分类和淫靡文学的时风起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这里还应该指出,刘勰对天地鬼神圣贤良知过去未来的敬畏,也从人文彼岸或道德底线方面,给文学误区竖起了一块块警戒碑。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反文学的信证也是促成文学的事物,重要的是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的悖论在“暗渡陈仓”。刘勰此举是对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反拨。在“采丽竞繁”病入膏肓的晋宋齐梁时代,其擘画文学的胆略和拆解文学疆域的深沉,远在三曹、七贤、陆机、沈约、萧统、徐陵、锺嵘等人之上。我们可以把刘勰非文学自觉的胆识视为“反文学”,也可以说这是他在文学“学科”庭院初具规模之时的一次多元化的变革。
3.辟合——泛文学的淡化与涵养 刘勰对文学的多元化变革毕竟具有波诡云谲的一面。而他对纯文学的辟合,则充分展示出反璞归真的博大境界。泛文学或曰文学的泛化,是文学对自身之辟,也是文学与大人文之合。《文心雕龙》对泛文学的勾兑,几乎达到殚精竭虑的地步。文原于道,已经让文学的七宝楼台进入了养异存同的浩大氛围。自经、纬开始,缘诗、骚而下,刘勰详赡地论述了33种文体。其中经纬、颂赞、祝盟、诔碑、哀吊,与文学牵连而不顺化;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与文学关联而不同化;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与文学毗邻而不通化。不顺化、不同化、不通化,却又藕断丝连,若是若非,文学的篱笆蜂蝶纷飞,审美的蓬门声息开放。从《神思》、《体性》到《程器》、《序志》,25个精彩的篇章,圆赅地揭示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系列原理性的问题。与之同时,刘勰仍然在文学基础的建设中引入了泛文学原则的构设。《神思》、《通变》、《定势》可用于任何文章的构思;《熔裁》、《章句》、《练字》适应于任何文体的修辞;《事类》、《附会》、《总术》有补于所有的著述方略;《隐秀》、《指瑕》、《知音》足以和多种文笔切磋;《体性》、《风骨》、《情采》能给各类文本启迪;《比兴》、《物色》、《时序》自是天人物我的户牖;《养气》、《程器》、《序志》当为文人雅士的通则。此处的文学辟合,无异于对过于贵族化的文学进行洗心革面的改造。文学既在人文的广阔天地中淡化,也在华夏的肥田沃土中滋养。
不难看出,辟创切入了范文学的本旨,辟学紧扣反文学的本真,辟合则涉及到泛文学的本源。上述“三辟”贯穿着一种泯合前后脱却生死的基本方法,即刘勰从《周易》中提取的“原始要终”思想。在始终、成毁、济未、偏正、繁简、生死等事关文学大局的吃紧问题上,刘勰在逐波讨源,在振叶寻根,在循环往复,在叩两得中,在通合首尾,在触类旁通。他把握住了文学生生不已的命门,而且用言外之教告诉我们,如果谈文学只知一个范文学或纯文学,那就会陷入文学人自我设置的水晶瓶中。
二、辟文学思想起承转合的运作
辟文学是一种生发/回归的可逆性运思,是创范/解放的同步性互动。它的活力孕含于有机的演化过程,它的奥秘体现在起承转合的变数当中。《文心雕龙》作为“体大思精”的鸿篇巨制,其深邃的辟文学思想十分丰富。此处摘其大要,仅从启蔽、隐秀、通变三个要点略作分说。
1.潜题——辟文学的启蔽 辟文学的前缀是一个辟字,其根本则是“山穷水尽”处的潜题探索。潜题是潜在疑惑对人们的召唤,因而它是对前遮蔽事物的见(xian)蔽;潜题同时是对所述现象的剖析,因而它也是对已有遮蔽的揭蔽;潜题更是新问题的发现,因而它还是新蔽的开始。启蔽一词,恰好是这三层意思的同属:见蔽、揭蔽、新蔽。刘勰潜题思维非常深沉。他谈文学不像魏晋南北朝的其他哲人就诗文论诗文,而是首揭其道,潜入文渊深处;由道而文,高屋建瓴,揭示了前人和时人所未见所未道;而文学的许多方面又牵扯到哲学、历史、宗教、神话、鬼怪、天赋、政治、风俗等复杂问题,所以刘勰在潜题思考时行于可行,止于当止,悖论归悖论,存疑付存疑,留得心田后人耕。这在《原道》、《征圣》、《正纬》、《颂赞》、《祝盟》、《才略》、《知音》、《程器》等篇都能见出端倪。潜题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前逻辑或曰潜逻辑思维。众所周知,前逻辑或曰潜逻辑思维是华夏文化的强项,汉字的会意特点本身就是潜逻辑思想的杰作,同时也是前逻辑思想的业师。该思维蕴涵却不执着于西式逻辑的大小前提和正题设置,它得出的不是严密而科学的体系,但却是博大而深邃的人文智慧。《文心雕龙》50篇并不是严丝合缝的逻辑建构,而是体大虑周的文史林苑,其中花草摇曳,疏密相间,哲思泉涌,天人互答。这样说吧,潜题如人参、当归、山药、土豆、花生、莲藕、美人蕉……块根抱大地,枝叶礼苍天,既抒发了刘勰自身思想之睿智,又蕴蓄着华夏文质深衷之守谦。
2.拟题——辟文学的隐秀 如果说刘勰的辟文学思想在隐秀中找到了寄托,那么拟题则是隐秀特点的精妙说法。《隐秀》云:“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深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龙学家大都将注意力集中在隐秀的修辞学意义上,实际上隐秀的价值远在修辞功能之外。(参见栾栋,2001年)隐秀是刘勰辟文学的重要方法。拟题论文正好是刘勰辟文学隐秀的一套绝活。在《神思》、《体性》、《风骨》、《时序》、《物色》等关涉创作与批评的重大方法论上,从篇目提炼到行文推阐,隐秀眼光无所不在。拟人、拟物、拟天地、拟有无,解析阴阳交变,物我互渗,几达出神入化境界。其“深文隐蔚,余味曲包”,将隐秀“重旨”与“独拔”的互生互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龙学家从刘勰那里读出了自然气脉,读出了易理象数,读出了璇玑星宿,读出了时空倒错。质言之,刘勰以拟题强化隐秀,隐秀启蔽拟题,隐秀与拟题浑然一体。拟题是拟态思维,以致万类有灵,“物动心摇”。拟题是生态人文,可让文理自然,互通声息。拟题是咸在曲光,促使“文之为德”,与六合同辉。西式逻辑之第二题是反题,而刘勰思想之第二题是拟题。拟题拥抱着反题,而不是反题,其祥和意韵不言而喻。
3.会题——辟文学的通变 刘勰思想的第三题是会题,这也和西式逻辑的第三题(合题)有别。合题意味着正题反题的统一,而会题则是潜题拟题的交集。合题侧重的是前二题的同一性和必然性,会题关注的是潜拟二题的会通性和可能性。刘勰辟文学的思想贯穿于《文心雕龙》的各个章节,而在《通变》篇中阐述得最为精彩。“通变”是战国时语。《易传》对道器变常的思想有过深刻的论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公孙龙《通变》一文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变而不变”。这些思想均被刘勰吸纳。刘氏的通变论继前哲而集大成。一是主张对向背诸端融会贯通、疏导歧义和而生辉;二是倡导文思情采“参伍相革”,出入矩式化解陈说;三是坚信“律运周,日新其业”,穷通变久承前启后。这样的通变理论深入浅出,实际上将辟文学思想落实到了文学以及文化生命的关键部位。不少惯于援引西式逻辑的学者喜欢将通变思想等同于批判与继承的关系,这无疑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还应看到,通变思想作为辟文学精神的方法论原理,很好地概括了潜题之启蔽、拟题之隐秀和通和之致化,批与承、沿与革、继与开的关系囊括于其中,但是并不能仅仅作此类解释。我的业师寇效信先生曾从融会贯通的角度指出过这一点。通变精神在辟文学思想的视野中开发,其功能必然可以融洽古今思想,勾兑中外学术。
辟文学智慧的运作艺术在启蔽、隐秀、通变中得到收发自如的舒卷。其起承转合的人类思想构成可用潜题、拟题、会题道说。潜题、拟题、会题把西方正反合的逻辑情理化,启蔽、隐秀、通变则将西方辩证逻辑三大定律艺术化。辟文学的思想在与西式逻辑的比照下益显其独特的风采。
三、辟文学思想圆观宏照的意义
在探讨过刘勰辟思的真如和变数之后,有必要关注该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从刘勰辟思的圆观宏照方面聚焦,领略其对中国乃至人类文学、文化、文明的特别投光。
1.化觉——中国文学“自觉/反自觉”的魂魄
文学的自觉一向是人类的自豪,这自有其一定的根据,因为人类力求在其中得到而且也确实获得过自由、解放和超越。此处要指出的是自觉后的反自觉以及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自觉的文学必然形成自身的格式、规范、科别,此其一;成为社会的教条、块垒、重负,此其二;成为人类的误区、灾害、荼毒,此其三。这又为反自觉问题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西方人往往从文学的自律/他律、本体/异体、主体/客体等关系中抽绎克制文学自觉场域弊端的各种因素。中国古代儒道墨佛等不同流派也在各种文学观的切磋磨合中触及到了相关问题。而刘勰的辟文学思想在这一点上的动作尤其发人深思。首先他不遗余力地批判各种有背于天地神人良性关系的文学现象;其次他不失时机地推演大文学或曰泛文学理念;此外他还把文学放到“文化/非文化”的视野中观察。如果说自觉与反自觉使文学肝胆分裂,那么刘勰将魏晋文学自觉的势头接过来而又做了化解性处理,形成了双觉合一奇观。中国文学的精气神真正实现了出神入化的大气象。换言之,《文心雕龙》很睿智地化解了文学“自觉/反自觉”的悖论。化觉是“自觉/反自觉”的会通——彼此互渗又不拘一格,是“自觉/反自觉”的双解——两觉合一而却不执一偏。其结果就是云龙腾飞的万千气象:处处讲文学,而又处处超文学;处处有文学,又处处非文学。刘勰是文学家,是诗人,是文学理论家、文化思想家,但又什么都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正是双觉之化觉者必然的归宿,也是中国文学“自觉/反自觉”的魂魄所在——化解着物/我、主/客、彼/此诸般对峙的化觉境界。(参见栾栋,2003年)
2.化文——华夏道学“文化/非文化”的精髓
化文举措是刘勰道学的终极性思索。刘勰道学是涵盖了天地人的“三才”通化,由之肯定了人文前、人文中和人文外都有非人文和非文化的方面,通化是三文互动过程的去执去蔽性概括;刘勰道学把文化/非文化的通化看作非常重要的头绪,因此《文心雕龙》前五篇才被称作“为文之枢纽”;由于天文、地文、人文一脉相承而又互通有无,所以才会出现“天地定位,祀遍群神”的“祝盟”,才有“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物色”;正因为刘勰将自然和人文看成了“家族相似”、“神用象通”的可疏证关系,才有“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的骈文,甚至以骈文论文的美文;也正是由于文之可化,刘勰才把历史文体和文学文体、广义文体和狭义文体统而论之,才把文学置于学类泯会、“邻里”通和的生存态,才把“三才”之文还原到一个更为深邃、更为广博的境界。近百年来,学术界把主要心事放到了《文心雕龙》与近现代西式文学观相契合的方面,却遮蔽了刘勰道化论中“文化/非文化”的思想。他的道化理论不局限于《原道》一篇,而是交织在文体论的方方面面,渗透于创作论和批评论的字里行间。道学是刘勰《文心雕龙》的思想底蕴,化文是《文心雕龙》的精髓所在。从思想文献索隐的角度讲,连山、归藏、周易之化是研究刘勰及其化文思想的一个重要课题,涉及到了深化龙学的根基性追问。从《原道》与49篇的内在关系来说,化文是道学寻踪的重要切入点。“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可文而有凭,文能化而不僵,在化文的问题上,大有文章可作。
3.化生——人类生态“文明/解文明”的脉络文化(la culture)养育了文明,文明疏离着文化。文明(la civilisation)是人类机心的释放,是文化秩序化、强制化的表现,某种意义上也是人性的异化和文化的灵魂出窍。文明作为人类命运的双刃剑亟待化解性的处理。刘勰的道论将文化和非文化融为一体,强调了文化是人与自然商量培养的根本理念,实际上包含了化解“文明轴心”戾气的良苦用心。化文将人与自然的气脉贯通,由之产生出了一种“文明/解文明”的化生意识。刘勰知道“摛文必在纬军国”,但是极力推崇的却是与天地共生的文之大德。他不得不说一些“皇齐驭宝,运集休明”之类的明哲保身的话,铭心刻骨的却是征圣宗经的人生追求。他看到了金钱权势不可一世的显赫,但是却用道德文章的阐扬对抗着社会的黑暗和龌龊。他清醒地知道焚坑惨烈祸患无穷,可是终生执着的仍然是“百龄影徂,千载心在”的伟大事业。他经历了那样一个文学自觉的大趋势,而持之以恒的则是兼通自觉反自觉的大眼光。他高度赞誉历史上经典文本的伟大创制,但是也非常冷峻地透视了各种文体的潜移默化和利钝成败。他对儒家的思想非常敬仰,可是对道佛兵农各类文献也有精深的理解和得心应手的取舍。看好实践理性精神是其论文的主要倾向,但是敬畏天地鬼神且对未知留白始终是他的审慎态度。一言以蔽之,《文心雕龙》是文明/解文明生态的祥和脉动,是生化/化生万物的健康培养。(参见栾栋,2004年a)
人们经常说《文心雕龙》是严密的文学理论体系,是完整的审美学说构架,事实上它是天地神人共鸣的泉石激韵,是诗语史思互答的林籁结响,至少应该说它是全方位开放的学术时空。当我们探索刘勰辟文学思想的各种意义之时,其“圆观宏照”的学术追求和三才通化的人文抱负可谓自身价值的中肯评判。尤其在人类文明进入自戕式裂变的全球化局势下,上述“三化”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刘勰所发挥《周易》的“原始要终”的思想,为辟文学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焦点和方法依据,揭示了范文学、反文学、泛文学的辟创、辟学、辟合深衷。其启蔽、隐秀、通变的神思,体现出潜题、拟题、会题的起承转合,凝聚着贯通天地鬼神的学术真谛。辟文学圆观宏照的化觉、化文、化生意识,披露出华夏道学、人学、文学的韵外高致,孕育着人类自我、非我、超我的追远精神。当然,刘勰的思想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有辟文学之实绩,却未提炼出辟文学之名目;有辟文学索隐发微的努力,而未能达到归藏思想的深层;有雕龙巨匠的大手笔,但缺乏潜龙勿用的界外思考。尽管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体现出的辟文学思想的美学价值是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