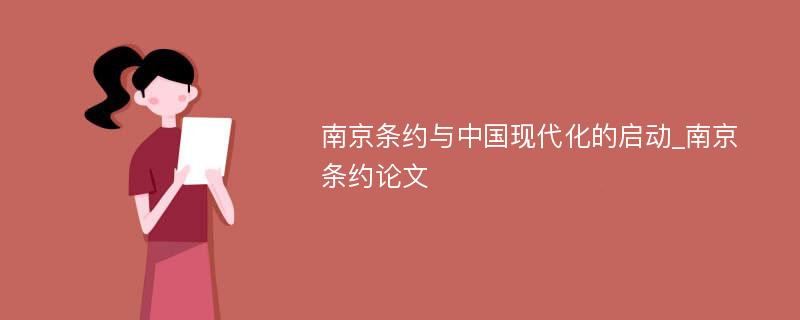
《南京条约》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条约论文,中国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林则徐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
纵观中国近代化所经过的历程,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即它的启动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当时重视了解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学习外国而引发起来的。这是近代最早的一批先进中国人,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林则徐。论者誉之为“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他是当之而无愧的。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有人开始介绍有关世界的知识了。例如,康熙时陆次云著《八纮译史》和《译史记余》、雍正时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乾隆时郁永河著《裨海纪游》等书,或收有海外某些大国情况的摘录,或记述前人和时人也入东西洋各地之耳闻目见。嘉庆以降,欧洲殖民者来华日趋频繁,中国人对欧洲国家的记述因之渐多。象王大海所著《海岛逸志》和由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而成书的《海录》,不仅记述了欧洲人的政治、法律情况及风土人情,而且还介绍了欧洲人在医学以及包括制造火轮船在内的工业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进入道光朝后,最值得注意的是萧令裕所撰之《记英吉利》,可算得上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有关英国国力和动向的最详细的记述。其中第一次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作了详尽而具体的介绍,并指出英国正在推行其侵略扩张政策:“英吉利恃其船炮,渐横海上,识者每以为忧。”“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于是精修船炮,所向加兵。”还建议一面仿效英国船炮制造,一面注重训练用器之人和军纪,“以讲求用器之人与行军之纪律,尤为制御之要。”[1]可见,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实为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说之先声。但是,萧令裕的建议并未受到当道者的重视。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十年之后,患必及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于今日。”[2]果不其然,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了。
由于长期闭关锁国的影响,一般封建士大夫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不但毫无所知,而且也是毫无兴趣的。时人批评他们“竟不知海外更有九洲”[3],尤其“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4]皆非夸张之语。当时的西方报刊曾以极其轻蔑的语气评论道:“中国官府全不识外国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国事务,故中国官府之才智诚为可疑,中国至今仍旧不知西边。”“如在广东省城,有许多大人握大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5]林则徐初到广州莅任时,他对外国的知识比一般官员也强不了多少,还闹出一些笑话。但是,他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象那些故步自封的封建士大夫那样,认为外国的事情一概“与中国无涉”,“实亦无从探考”,而是汲汲于探访外国情况,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弥补自己的贫乏的世界知识[6]。他了解外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预防侵略,因为“现值防夷吃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7]。
林则徐认识世界的主要渠道,除亲自调查访问外,主要是对外文书报的翻译。例如,他组织翻译美国出版的"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以《四洲志》作书名,不仅介绍了各国的经济、地理和军事力量等情况,还叙述英、美等国的政治制度,开近代中国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先河。特别是他在叙述美国的共和政体之后,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诸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善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之局而自成世界者。”[8]有研究者将其与原著相对照,发现有关语句并非原著本有,并非译文,而是林则徐在修改定稿时加上去的个人体会[9]。后来,魏源在撰写《海国图志》时,对美国的政体多有赞美之词,甚至认为“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10],实际上是受了林则徐的影响。这给受数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室息的中国社会透进了一点外界的民主空气,应该说在当时具有启迪民智的意义,而且对近代社会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也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然,林则徐是一位非常务实的官员,他最为关注的问题是要摸清敌我双方的强弱形势。他从外文新闻纸了解到西人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价很低,如称:“论及中国海上水师之船,较之西洋各国之兵船不但不能比较”,且“不肯与外国人在海面打仗,惟有关闭自己兵丁在炮台内”。“自知不善战,故每事只用柔治,其防守之兵,有事只闻炮声而已。水师船遇西洋并无军器之商船,尚抵挡不住,何况兵船,且军器亦多废铁造成,年久并未修理整新,火药则烟方出口,子即坠地矣。”“炮身又多蜂眼,所以时常炸裂,又引门宽大,全无算学分寸,施放哪能有准?又用石头、铁片各物为炮弹,并用群子、封门子皆粗笨无力。”[11]诸如此类的评论甚多,林则徐认为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他反复强调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认为英国“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而中国师船“震于英吉利之名”,“一至夷界,则畏英夷之强,顾后瞻前。”[12]至于英军火炮之精良,更为清军所望尘莫及。“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它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只恐供临敌之一哄。”正由于此,他才产生了“师夷长技”的思想。他说:“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夷船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并再三强调“船炮乃不可不造之件”[13]。
根据制敌取胜的迫切需要,林则徐在研究西洋“长技”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他曾组织编译有关西式大炮瞄准发射技术的书籍,其中即有专门论述重炮的内容。起初,为了尽早地掌握敌人先进的作战手段,但又“恐筹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14]因此,他先后购置了西洋大炮近200门。随后又仿造西洋大炮,仅在佛山一地便铸造了8000斤大炮14门。
但是,林则徐考虑得最多的还是仿造坚船、即西洋战舰的问题。在抗英斗争的实践中,他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不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是无法抵御外来侵略的。并且多次指出:“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逆船在海上来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屡变。若在在而为之防,不惟劳费无所底止,且兵勇炮械安能调募如此之多,应援如计之速?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而且“今所向无不披靡,彼已目无中华,若海面更无船炮水军,是逆夷到一城邑,可取则取,即不可取,亦不过扬帆舍去,又顾之他。在彼无有得失,何所忌惮?而我则千疮百孔,何处可以解严?”[15]他在这里所说的“船炮水军”,指的就是近代海军。所以,林则徐又是中国近代倡建海军的第一人。
林则徐所构想的是这样一支海军:“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果能如此,则“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岸上军尽可十撤其九。”[16]然而,造船非仓卒可成,为及早提高海上的防御力量,他决定采取买船与造船并行的办法。他先购买了一艘英船“剑桥”号(Cambridge),此船原是美国旗昌洋行商船改装的一艘兵船,装有34门英制大炮,排水量为1200吨。此外,还购买了两艘25吨重的帆舰和一艘小火轮[17]。这是中国购买西船之开端。与此同时,他还开始仿造西船。奏称:“今春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18]当时有西方人士曾目睹这种仿造的西船下水,记述道:“1840年4月25日,两三只双桅船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都是按欧洲船式建造的,可能加入帝国海军了。”[19]这又开中国建造西式船只的先例。
以师夷“长技”为方针而筹办外海战船,是林则徐海防思想的核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他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长技”,“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20],不令外国人专擅,以期做到“防夷”和“制夷”。在当时说来,这是林则徐海防思想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一思想的提出,开一代风气之渐,从而导致了以仿造西船热潮为特点的海防运动在中国的兴起。
纵观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的发展,其突出的特点是,每次都是以造船筹办海军为其开端的。也可以说,造船筹办海军,实际上是和中国的近代化同步的。当时的西方海军还处在由帆舰向蒸气舰的过渡阶段,尽管已经开始使用蒸气舰,也只是用于引导兵船、投递文书诸项,其所拥有的战舰仍是以帆舰为主。林则徐所仿造的西船主要是帆舰式的,这正反映了中国早期近代化启动时期的特点。于此可知,林则徐所倡导和推动的海防运动,究其实质乃是一场早期近代化运动。他成为中国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初的早期近代化运动的真正启动者。
二、《南京条约》与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之夭折
海防运动作为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林则徐的大力倡导和亲自示范下,终于启动起来了。当时,一些有识之士起而应之,于是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广东、福建两省,迅速掀起了一个仿造西式战船的高潮。
从1840年开始,广东便有不少爱国官绅激于保国卫乡的抗敌义愤,自动捐资造船。如在籍户部员外郎许祥光捐造战船两艘,广州盐茶商、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捐造战船一艘,批验所大使长庆和广州知府易长华各集资承造战船一艘等等。其中尤以潘仕成捐造之船为最佳。此船“仿照夷船做法,木料、板片极其坚实,船底全用铜片包裹”。船舱分三层,安2000斤至4000斤大炮22门,数百斤至1000斤大炮18门,共40门。全船可容300余人,共用工料银19000两。逐日演放大炮,“炮手已臻娴熟,轰击甚为得力。”[21]潘仕成捐造之船,其船式和效能接近于中型西式帆舰,这表明当时仿造西式战船已获得了初步成功。
在广东掀起造船热潮的同时,闽浙总督邓廷桢也开始仿造西式战船。1840年夏,他曾与钦差兵部尚书祁隽藻、刑部右侍郎黄爵滋等联名上奏,建议朝廷通筹熟计海防之策。其奏称:“此造船、铸炮二者,费帑需时,计似迂缓,实海防长久最要之策也。”主张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添造大战船60艘,每船安炮30至40门;再在福建、浙江二省添铸4000斤至8000斤大炮200门,分配应用。另外,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各省应添船炮一处,亦应一律筹议。通计船炮工料费用,约需数百万两。并针对当时造船铸炮“费帑”之说,申明理由道:“臣等亦熟知国家经费有常,岂敢轻言添置?惟当此逆夷猖獗之际,思卫民弭患之方,讵可苟且补苴,致他日转增糜费?且以逆夷每年售卖鸦片,所取中国之财不下数千万两,今若用以筹办战备,所费不敌十分之一。彼则内耗外侵,此则上损下益,权衡轻重,利害昭然。”[22]邓廷桢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以实施其造船计划。他在厦门创设船厂,购置木材,仿照西船建造了一艘300吨的快速夹板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东南各省除纷纷仿造西式帆舰之外,还有人在开始试制火轮船。先是在1840年7月,嘉兴县丞龚振麟调到宁波,在海边望见洋帆林立,继而了解到其中有火轮船“以筒贮火,以轮击水。测沙线,探形势,为各船向导,出没波涛,维意所适,人佥惊其异而神其资力于火也。”[23]遂开始了仿制的试验。其后,晋江监生丁拱辰研究蒸气机的原理及其应用,制成一台长4尺2寸、宽1尺1寸的小火轮模型,“放入内河驶之,其行颇疾。”[24]歙县人郑复光又在丁拱辰模型图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写成《火轮船图说》,详细地讲明“气动中柱,则边柱同动,而曲拐运转飞轮”的蒸气机原理,并解释了人们对火轮船逆风而行、“帆虽设而不用”的疑团;“殆谓寻常逆风,他舟袖手,此可径进,风若稍顺,则息火张帆,未尝废帆不用也。其巧在三角帆以破风,立版以破浪,行船巧在轮,运轮巧在曲拐。若夫风浪之力所以大者,气法也;水火之力,亦气法也。分风擘浪,则彼气之力失气;火炽水沸,则此气之力得势。彼失此得,其加减比例诚有不可拟议者,则逆风能行,理有固然。”[25]到1842年春间,还有广州绅士潘世荣对制造火轮船甚感兴趣,雇用洋匠造成了一艘蒸气船,虽形模粗具,然“放入内河,不甚灵便”。于是准备全按洋轮之法,“雇觅夷匠仿式制造”[26]。当时这些仿制蒸气船的活动虽还处于初步试验的阶段,然对于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来说,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质性的意义。
但是,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却未能顺利地发展下去,反而初兴不久便遭到了夭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美国约翰·劳林逊(John L·Raw—Linson)教授的解答是:“所有这些活动,无论是因袭仿制还是开展新的试验,总的看都是一些分散而孤立的事件。对此,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并不是中国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试验,纵然相对地说中国没有优秀轮船制造人才的养成,也不是缺乏这方面的技艺。主要的问题还是中国官方的态度阻碍了试验的进行。”[27]此说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影响了上述造船活动的继续运作。
确实,起初道光皇帝是反对仿造西船的。如果说对各省自发捐资或集资仿造西船他还睁一眼闭一眼的话,那么对拨公帑仿造西船他是绝对不同意的。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是,当林则徐提出以粤海关关税之十分之一300万两制炮造船时,他竟大发雷霆,批曰:“一片胡言!”[28]这倒不完全是出于吝惜经费,而是反映了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后来,道光皇帝追溯当初对英军的认识时说:“逆夷犯顺以来,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海上,荼毒生灵,总因内地师船大小悬殊,不能相敌,是以朕屡隆谕旨,饬令将军督抚,但为陆守之计,勿与海上交锋。”其实,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观点,也是绝大多数官员的普遍看法。如称:“至逆夷习于水战,向来议者,以彼登陆后即无能为患。”甚至当英军攻陷厦门后,有的官员认为:“惟有多雇壮勇,预备陆战,庶以我所长攻彼所短,可期制胜。”[29]在这种“但为陆守之计,勿与海上交锋”方针的指导下,当然根本不会去考虑仿造西船的问题了。
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道光皇帝对造船一事的态度逐渐有了变化。自英军占领厦门后,又继续北犯,先后攻陷定海、镇海、宁波,内外臣工皆提不出切实的御敌之策。到1841年12月上旬,道光皇帝鉴于英军主力北上侵扰浙海,拟用釜底抽薪之计,谕令靖逆将军奕山等趁机规复香港。并严厉斥责说:“乃竟袖手旁观,隐忍苟安,不图攻剿之谋,只为退缩之计,老师糜饷,是诚何心!”[30]翌年1月初,再次严饬奕山等“及时进兵,收复香港”,并警告其再若“置若罔闻”,“惟有执法从事。”[31]在这种情况下,奕山才不得不据实情回奏:“水师例修之船,止可捕盗,不能御夷”;“与之争胜于外洋,既难操必胜之权,而中国元气为之大损”。并奏明现有在籍候补郎中潘仕成捐造战船一只,仿照西船做法,一俟其竣工,即用于保护虎门,“再行进战,收复香樭”[32]。3月中旬,浙江巡抚刘歆珂因扬威将军奕经连遭败绩,向朝廷建议:“水战尤为该逆之所习,我欲制其死命,必当筹海洋制胜之策。”[33]并委婉地表达出应该制造“坚大之战舰”的想法。此奏竟未遭到道光皇帝的批驳,于是奕山和两广总督祁埙正式建议朝廷:“现在夷务尚未大定,然欲作经久之计,亦应为先事之谋。英逆肆行猖獗,所恃者船坚炮利,内河水浅浪平,若夷船闯入,尽可用以小胜大之法。……海面宽阔,风浪掀簸,非大船不能得力。向来巡洋各项师船,平日止可巡缉盗匪,不能安放重炮,驾出海洋,与夷船对敌。是防御逆夷,必须另造大号战船,以冀制胜。”[34]此时已是4月中旬,道光皇帝并未对此批驳,且谕旨语气已有所缓和,表明他对造船的态度已开始转变了。
6月中旬,英军先后攻陷吴淞,并占领上海。到7月6日,英国海军舰队自吴淞口溯长江西犯,形势更加危急。在此之前,有一位不得志的书生的造船建议,竟引起道光皇帝的兴趣。这位书生叫方熊飞,是安庆府监生,他的这份请造战船的禀呈不知怎样递到了道光皇帝手中。此禀一开头即开门见山地指出:“英夷犯顺,荼毒生灵,所以猖獗日盛者,以我军徒守于岸,无战船与之水战耳。”认为“战船一造,即操必胜之权”。并在禀呈的最后特别强调说:“长治久安,在此一举!”[35]道光皇帝正焦思无策,这些话句句说到了他的心里。于是,在7月15日,即英军攻陷镇江的这一天,他一面饬令将方熊飞原呈抄给奕山等阅看,一面降谕称:“思逆夷所恃者,中国战船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是以肆行无忌。若福建、浙江、广东等省各能制造大号战船,多安炮位,度其力量,堪与逆夷海洋接仗,上之足歼丑类,次亦不失为尾追牵制之计。……著福建、浙江、广东各督抚,各就本省情形详加筹画,密为办理。”[36]并对广东的捐造战船之义举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几天后,再次降谕,指出:“设我沿海各省亦有大小战船,可以多安炮位,一闻夷警,各处应援,主客之势既殊,劳逸之形迥异,彼以孤军深入,我可首尾夹攻;且跨海远来,后无所继,我能制其死命,逆必不敢跳梁。”并要求“赶紧制造,务须十分坚固,度其力量堪与逆船接仗,方为适用。”[37]及至8月,英军舰队驶抵江宁江面后,又于16日、20日连续下旨,催令“购买木料,制造战船,以备水战”;同时谕知为应急需,“倘一时不克凑齐,如有可购买之处,著先行设法购买。”[38]这正所谓临急抱佛脚,为时未免太晚,然而对于当时东南沿海的造船工作来说,终究是一个推动,有助于早期近代化的继续开展。
朝廷既已做出了制造战船的决定,广东随即提出了一个造船的具体方案。先是潘仕成在上年捐资仿效西洋做法造成一艘战舰后,“续又造成新船一只,照旧船加长,工料亦仍旧坚固。”[39]并且准备按此船式再造两艘。本年夏,适有两艘美国兵船驶至黄埔,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和南韶连总兵马殿甲登船参观,逐细察看,并寻觅巧匠绘出该船图样。此船长13丈,有两层甲板,安大炮49门,约可容300余人[40]。潘仕成所造之船与此船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船上止有桅杆,并无桅盘,不能悬放大炮。”[41]当时,西洋最大的帆舰,身长十七八丈,有3层甲板,可安大炮70余门,“制造维艰”,因此只能就这种“中等兵船式样,如法制造。”计划“先造大号战船30只,再造小号船三四十只,既可为大船羽翼,又可资海洋面缉捕”。并“将粤东现届拆造年分例修师船,暂停制造,以冀节省经费,为改造大船之用。”[42]这里所说的“大号战船”,就是中型帆舰。这个方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经朝廷批准的仿造西船计划。
这个造船方案终于姗姗而来,比邓廷桢原先提出的粤、闽、浙三省添造60艘大战船的方案,差不多迟了两年的时间。然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如果此项造船计划能够真正地实施,必定会将海防运动引入正常的发展轨道。然而,由于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这项大规模造船计划的执行便出现了问题。因为朝廷明谕江苏、福建、浙江、直隶、山东五省督抚,按广东所进西洋战船图说,“各就该省洋面情形,详加履勘,何者合用,奏请制造”。但又规定:“如果合用,将来均需粤省制造,分运各省。据奏潘仕成所捐之船,坚实得力。以后制造船只,著该员一手经理,断不许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减。所需工价,准其官为给发。并不必限以时日,俾得从容监制,务尽所长。”[43]上谕自相矛盾:一面说工价由官给发,一面说不让官吏涉手,何所适从?况且,潘仕成何人,敢独力担此重任!所以,这道谕旨实际上无从执行,成了一纸具文。这并不奇怪,因为既已“罢兵息战”,道光皇帝主要考虑的是,一切通商事宜如何与英方“逐款议定,俾得日久相安,无滋流弊”[44],已不将造船事放在心上了。这时,林则徐正在遣戍途中,听到饬令五省造船的消息,在致友人信中说:“船炮水军之不可缺一,弟论之屡矣,犹忆庚秋获咎之后,犹复附片力陈,若其时尽力办此,今日似亦不至如是束手。今闻有五省造船之议,此又可决其必无实济。”[45]他根据自己切身的体会,断定朝廷决无造船的真正决心。果然,为时不久,道光皇帝即针对广东试造火轮船一事,饬令停止工作,“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46]。从此,仿造西洋战船的计划也随之搁浅了。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道光皇帝对仿造西船的必要性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尽管他起初反对造船,后来终于赞成造船,只是由于《南京条约》的签订,后来才又放弃了大规模造船的计划。所以,全面地看,是英国的鸦片侵略激起了海防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又是英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造成海防运动的中断,从而使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遭到了夭折。
三、中国近代化的第二次启动
虽然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难以为继,而渐趋于式微,但随运动而来的海防思潮却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由于前此林则徐的倡导和推动,造船一时蔚为风尚,究心海防大势者渐多。《南京条约》的签订更进一步刺激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感到不议海防不行,“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47]。正如一位时人指出:“盖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校,……其他可骇可耻之事,书契以来所未有也。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愤恨,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疆。”[48]正是在这种爱国忧时的思想激励下,他们发愤著述,将应时而兴的海防思潮推向其发展的巅峰。
继林则徐之后,论海防者虽不乏人,然足称道者,当以魏源为巨擘。在此期间,魏源完成了两部有关之巨著:一是《圣武记》14卷;一是《海国图志》50卷。前书完成于《南京条约》签订之日,后书完成于《南京条约》签订的4个月后,皆发愤之作也。魏源在书中总结了林则徐师夷“长技”思想,并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来概括之,将其更加系统化了,这就把海防思想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西洋“长技”,首推船炮,故船炮为海防必需之物。在这一点上,魏源和林则徐的认识并无二致;然认真比较起来,魏源的认识似更为深刻。他主张,船炮务求精良,起初固可购自外洋,但仍以自制为根本之计。盖“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平常”,中国人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的。他建议:“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计每艘中号者,不过二万金,计百艘不过二百万金。再以十万金造火轮舟十艘,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49]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设近代军工企业的方案。
魏源还发展和丰富了林则徐创建“船炮水军”的思想。他指出,西洋“长技”并不限于船炮,除制造船炮之外,养兵、练兵也必须贯彻“师夷长技”的原则。“无其节制,即仅有其船械,犹无有也;无其养赡,而欲效其选练,亦不能也。”其具体办法是,“汰其冗滥,补其精锐”。即以广东水师而言,经过汰冗补精,“以三万有余之粮,养万五千之卒,则粮不加而足”。若能如此,即以粤洋之绵长,“今以精兵驾坚舰,昼夜千里,朝发夕至,东西巡哨,何患不周?”[50]“舟舰缮矣,必练水师。”[51]经过募练,“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52]然后,仿粤省之例,由粤海而闽浙,而上海,“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53]。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魏源认为,造船厂也好,火器局也好,都是铸造之局。通过铸造的具体实践,中国工匠“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而且积累经验之后,推而广之,既能制造各种类型的火器,又能由制造军用产品扩大到制造民用产品。“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是造炮有数,而出鬻器械无数。”不仅如此,船厂之设,制造战舰,必可促使民间商船制造业的兴起,从而推动国内贸易以至海外贸易的发展。“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而内地商舟皆可不畏风飓之险矣。”并且建议,规定出洋贸易的商船,经商家禀请,可派战舰护航,以保安全:“凡内地出洋之商,愿禀请各艘护货者听。”[54]
于此可知,在《南京条约》的刺激下,魏源作为关心国事的“积感之民”[55],探求中国自强的道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林则徐的师夷“长技”的思想,使之更为具体化,提出在创设近代军工企业的基础上还要扩大到近代民用企业,并且大力发展商业、航运业和海内外贸易。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最早提出的全面发展经济的近代化方案,从世界范围看虽不足为奇,但对中国来说却是一种超前的思想。他的这些思想虽在当时不为当政者所重视,但其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二十多年后,洋务派正式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终于再次启动和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漫长历程。
总括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三点认识:(一)中国的早期近代化有两次启动,而不是一次启动。先是启动于19世纪40年代初,因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而被中断,才有60年代中期的再次启动。(二)中国的早期近代化之所以能够启动,是由于具备了两方面的动因;一是西方国家的侵略使中国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这是外因,是启动的外在条件;二是先进的中国人因应危机形势,而开始了解和学习外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内因,是启动的内部根据。无论如何,后者才是主要的动因。(三)不能认为中国的早期近代化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外国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恰恰相反,英国侵略者所强加给清政府的《南京条约》,不是促进了已经启动的中国早期近代化,而是使之遭到严重打击而告夭折。即使说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再次启动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也不能因此而归功于英、法侵略者,因为从根本上说来,当时只不过是将搁置达20年之久的师夷“长技”思想重新付诸实施罢了。所以,简单地认为西方列强侵略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化,这一认识是不正确的。
注释:
[1]魏源《海国图志》(60卷本)卷三五,第6—7页;卷五三,第17、24—25页、第1—4页、第20—21页、第8页;卷五四,第2、5—6页。
[2]转引自胡秋原主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1辑第二分册,第766页。
[3]魏源《海国图志》(50卷本)卷三八,第36页。
[4]《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奏稿中,第644页、第765页、第676、765页、第865页、第885页。
[5]《鸦片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丛刊(二),第411—412页。
[6]拙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7]《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奏稿中,第644页、第765页、第676、765页、第865页、第885页。
[8]《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2帙,《四洲志》,第42页。
[9]陈华《有关〈四洲志〉的若干问题》,《暨南学报》1993年第3期,第76页。
[10]魏源《海国图志》(100卷本),《后叙》第5页。
[11]《鸦片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丛刊(二),第524、543页。
[12]《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奏稿中,第644页、第765页、第676、765页、第865页、第885页。
[13]《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173、132页。
[14]《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5]《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183—184、182页。
[16]《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17]John L.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P19。
[18]《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奏稿中,第644页、第765页、第676、765页、第865页、第885页。
[19]拙著《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20]《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奏稿中,第644页、第765页、第676、765页、第865页、第885页。
[21]魏源《海国图志》(60卷本)卷三五,第6—7页;卷五三,第17、24—25页、第1—4页、第20—21页、第8页;卷五四,第2、5—6页。
[2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23]魏源《海国图志》(100卷本),《后叙》卷八六,第1页。
[24]丁拱辰《演炮图说辑要》卷四,第13—16页。
[25]魏源《海国图志》(60卷本)卷三五,第6—7页;卷五三,第17、24—25页、第1—4页、第20—21页、第8页;卷五四,第2、5—6页。
[2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27]John L.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P21。
[28]《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奏稿中,第644页、第765页、第676、765页、第865页、第885页。
[2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3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3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3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3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3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35]魏源《海国图志》(60卷本)卷三五,第6—7页;卷五三,第17、24—25页、第1—4页、第20—21页、第8页;卷五四,第2、5—6页。
[3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3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3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3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40]魏源《海国图志》(60卷本)卷三五,第6—7页;卷五三,第17、24—25页、第1—4页、第20—21页、第8页;卷五四,第2、5—6页。
[41]魏源《海国图志》(60卷本)卷三五,第6—7页;卷五三,第17、24—25页、第1—4页、第20—21页、第8页;卷五四,第2、5—6页。
[4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4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4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儸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45]《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
[4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第12—13页;卷六三,第16页;卷五四,第38页;卷三二,第4、14页;卷三八,第36页;卷四○,第31、32页;卷四一,第17、18页;卷四四,第30页;卷四五,第35页;卷五四,第39页;卷五五,第44页;卷五八,第22、37页;卷六一,第38页;卷六一,第38、40页;卷六一,第41页;卷六一,第26页;卷六三,第16—17页。
[47]《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208页、第186页;下册,第869—870页、第874—875页、第870页、第870、873、871页。
[48]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第10页。
[49]《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208页、第186页;下册,第869—870页、第874—875页、第870页、第870、873、871页。
[50]《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208页、第186页;下册,第869—870页、第874—875页、第870页、第870、873、871页。
[51]魏源《圣武记》(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8页;《圣武记叙》。
[52]《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208页、第186页;下册,第869—870页、第874—875页、第870页、第870、873、871页。
[53]《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208页、第186页;下册,第869—870页、第874—875页、第870页、第870、873、871页。
[54]《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208页、第186页;下册,第869—870页、第874—875页、第870页、第870、873、871页。
[55]魏源《圣武记》(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8页;《圣武记叙》。
标签:南京条约论文; 林则徐论文; 中国近代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道光皇帝论文; 造船论文; 潘仕成论文; 魏源论文; 西洋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明治维新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文化史论文; 中世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