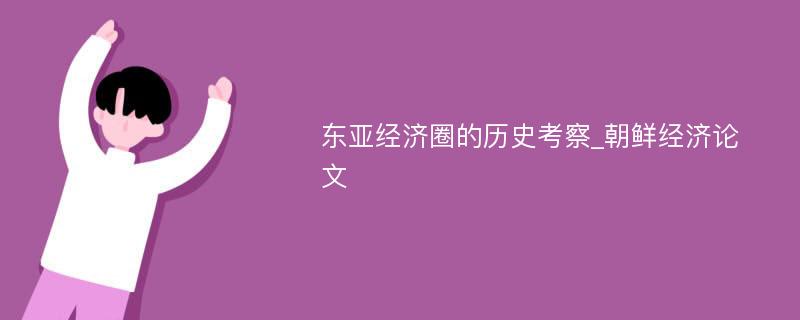
对东亚经济圈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经济圈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兴起,东亚史研究也在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在历史上,东亚地区存在独特的国际关系结构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许多方面受到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深刻影响,构成一个完整的东亚世界。东亚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区域,不仅内部联系密切,而且与外部世界也有普遍的经常的联系。如果从历史的视野来看,东亚经济圈同东亚历史一样的悠久,远比世界其他地区内容丰富和复杂多样。
一、交流的区域限制与东亚经济圈的初步形成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由于生存的需要,不同部族、民族、地区与国家间形成一定的交往与交流,形成一定的交往圈。但是人类的交往受到来自自然的、社会的和技术方面的许多限制。只有生产力水平提高,国家形成统一的力量之后,对外交流才能进一步扩大。秦汉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形成对东亚经济圈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的意义在于,东亚地区出现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地区性大国,开辟了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的关系。古代东亚地区是否存在一个区域体系呢?我们的初步看法是,在近代以前东亚存在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区域关系或称区域秩序,存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上的密切联系。在东亚史研究上,我们主张把东亚历史看作是一个区域性鲜明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解释既有的史实方面应突破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分析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冲击一反应”模式的理论框架,建立以实证性研究为基础的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使长期受到忽视的东亚经济史得到研究。对于东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长期领先于世界一些地区,国外学者已有许多精湛的研究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自己对此问题的研究长期裹足不前,没对东亚史作出合乎历史实际的解释。
我在《东亚区域意识的源流、发展及其现代意义》② 一文中指出,东亚区域史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整体世界,关注的是本区域内跨民族、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互动,孤立的国别史研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今天形势发展的需要了。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主张加强对东亚经济史的研究,以宏观的研究视角审视历史,尤其对横亘东亚历史若干世纪的经济圈给予足够的重视。当前的形势发展不断对学术提出新的问题,因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对过去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作出概括与总结已成为当务之急。加强区域经济史研究,有助于发现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和根本动力。扩大研究的视野,转换研究的思路不过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欧美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诚如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说:“我们感兴趣的是亚洲的历史底蕴,可是我们得承认这一历史不易把握……再说东方学家往往是些优秀的语言学家和文化专家,并不专攻社会史或经济史。”③
对于区域经济史研究,日本学者已有较多的探索。例如国内读者熟悉的滨下武志、中村哲、杉原薰、宫岛博史、堀和生、黑田明伸、川胜平太④ 等都是在东亚经济史研究上取得成就的,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把具有内在联系的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纳入世界历史研究当中,对历史发展进程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解释。东亚经济史研究强调的是它的区域性与互动性,但这并非盲目的自我为中心或贬低其他地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成就。我们看到,古代东亚地区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为外围的交通贸易圈,内部有着独特的运行规律与特点,不同于伊斯兰世界和地中海世界。
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的经济交流远比其他国家和地区频繁密切,几条贸易通道使东亚各国联系在一起。一条是从库页岛到北海道、本州岛的路线;另一条是经朝鲜半岛南部到达九州岛的航线,这是大陆文化传入日本列岛的大动脉;第三条航路是从中国东部沿海直抵朝鲜、日本的航线。交通线是联系东亚各国的神经网络和物质文化交流的载体。这些国家在地理空间上比较接近,便于国家间的接触交流。中国与日本的官方贸易较早。中国正史《汉书·东夷列传》、《汉书·光武帝纪》中有“倭奴国奉贡朝贺”、“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等记载。“奉贡朝贺”、“献生口”、“遣使奉献”等活动,具有政治、经济活动的双重性质。虽然海路交通时常受到气候、政治形势和技术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奴国王遣使奉贡和接受‘汉委奴国王’的称号,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日本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构成了东亚世界的一部分”⑤。日本进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世界,有利于推进与中国的海上交通和贸易,有助于东亚地区贸易网的形成。日本与朝鲜半岛的交流也很久远,早在它们建立国家之前就有了频繁的文化交流了⑥。不仅如此,中国还与中亚、西亚、地中海区域建立了商业联系。向西发展由于受到高山峻岭的限制,故不宜把与西方的交往估计得过高。
两汉时期开辟的中国与东亚、中亚、西亚、地中海区域各国的海陆交通,有力地推动了商品流通与交换,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几个重要的文明中心之一,形成重要的经济区域。“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比,贸易自然也是汉代中外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⑦ 统一的汉帝国的建立,把中国历史推进到第一个发展高峰,国内出现了数百年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与规模远远超过秦代,农业、工业、商业以及人口方面有长足发展。据统计,汉代人口已达到5959万人,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构成东亚经济圈最基本的条件已经形成。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东亚就是世界几个重要的文明区域,它的影响是不断向外扩散的,影响周边国家和地区。在农业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突出地表现为耕地面积扩大和社会财富增多,国内出现几个重要的经济区域,以至出现“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情况;工业方面的突出成就是众多部门的涌现,包括土木建筑、纺织、陶瓷、冶铁、采矿、造纸、制盐、兵器等,出现了许多工业中心。农业发展带动了工业的发展,也把半农业区域和游牧区域带入帝国的版图,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了,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商业发展得益于农业和工业的进步,在发展农业和工业的基础上,国内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成都等。城市发展是国家文明与富强的重要标志。自汉代以来,在东亚逐渐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西太平洋贸易网,通过区域内部贸易交流,构成了古代东亚经济圈。
汉帝国崩溃后,中国北方地区陷入了近400年的分裂与动荡,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但中国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在黄河流域经济受到重创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南方得到开发,开拓了后来成为中国经济中心的江南⑧。东南沿海对外交流扩大,贸易与人员往来增多。根据韩国学者统计,自东晋至隋唐300年间高句丽来中国朝贡173次,百济朝贡45次,新罗朝贡19次⑨。在整个东亚经济结构当中,中心与外围的层次关系非常明显,日本、朝鲜以至东南亚各国并不拒绝加入这个经济体系。就古代东亚历史来看,各国经济联系的力量远远大于政治联系的力量,也正是这种力量才使各国走到一起。对于东亚地区存在的以生活资料贸易为纽带的国家关系,只有深入到东亚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理环境当中才能理解。
作为东亚经济圈重要环节的东南亚地区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到底是怎样的呢?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东南亚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只是欧洲人来到之后才促进了东南亚社会发展,使其接受了欧洲文化与文明,走向了近代。这是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典型表现。根据近年考古研究资料可知,古代东南亚有着灿烂的古典文明,公元前2000年前后有些国家能够以金属制造出青铜工具,公元前500年前后普遍出现了铁器,公元前后东南亚人已同非洲东部海岸有了商业联系。该地区的富庶情况屡屡为欧洲殖民者、商人和旅行家所道及,以致为近代欧洲人所觊觎掠夺。东南亚在东半球南部海域的文化发展方面占据重要的位置⑩。东南亚的情况不同于欧洲殖民者对于北美和澳洲这些尚未开发的土地,也有别于英国对印度的影响,因此欧美殖民者在东南亚的作用不能用“建设性”作用来附会。
东亚经济圈的形成,表现在活跃的区域贸易上。人类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相互交流与交往,通过对外交流满足最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一经交流,一切缺少甚至不能生产的东西即可在短时间内获得,大大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中国成为东亚世界的中心不仅表现在文化上,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对外贸易上,强大的对外输出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源泉。由于地理条件所限,在空间上只能是相邻国家的交流交往,利用自然提供的有限条件进行文明的构建。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和广大的东南亚国家进行经贸交流,周边国家也以自愿互利的形式同中国互通有无。相对于中国西面的高山峻岭与北方的寒冷大漠,东亚海洋间的交流就方便得多,日本学者堀敏一指出:“从异民族方面而言,朝贡是将丰饶先进的中国物资弄到手的手段。”(11) 只有如此,才能促进社会进步变迁。贡德·弗兰克写道:“在世界经济中最‘核心’的两个地区是印度和中国,这种核心地位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存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铜钱以及后来的茶叶。”(12)
从上面的材料分析中可以看到,一个经济圈的形成一般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经济圈内经济发展的规模与质量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形成自己的优势,社会财富有较多的积累;第二,公路网和海外航运网的建立,技术、贸易对外交流以及商业发展,形成其他地区无与匹敌的条件,并呈放射状对外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第三,社会政治、经济具有开放型的特点,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与辐射力,向外输出文化,推动外围地区社会发展;第四,具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农业发展依赖于劳动力的数量。在农业文明时代,社会发展较为缓慢,经过长期发展才能在世界各地区当中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的发展优势。这是古代农业社会发展的特点。
二、交流区域的扩大与东亚经济圈的发展
隋唐帝国的建立,结束了近400年的分裂与动荡,把中国历史带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在经济、科技、文化和对外关系方面的建树,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顶峰,当时世界任何其他文明区域都无法与其匹敌。我们认为,仅仅从政治史层面看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东亚区域意识和经济圈的发展与扩大当中。由于长期的社会稳定,隋唐时代中国社会出现了发达的景象,国内出现多个重要的经济区域,中国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国际地位得到加强。唐代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使中国保持了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先进地位,保持了自秦汉以来对周边国家影响的巨大优势。人口的大量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唐代天宝年间,中国已拥有900余万户,5000万至6000万人口,垦田800—850万顷(13),疆域空前扩大,国力影响远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以至欧洲。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远距离交易,唐代中期以后货币经济已超越国界有了广泛的发展(14)。日本学者堀敏一把隋唐帝国看作是具有东亚特殊形态的世界帝国,不同于通过征服完成的罗马世界帝国(15)。著名经济史家亨利·皮朗指出,14世纪初欧洲最大的城市人口可能为50,000至100,000左右,一个拥有20,000人口的城市就算得上是大城市了,而且在大多数城市里居民人数一般介于5,000至10,000之间(16)。相比之下,中国城市蔚为大观,气象不凡。
隋唐至宋元,对外贸易完全走向世界,一个世界性海上贸易圈已经形成。陆路交通和海路交通把中国和日本列岛、朝鲜、南洋各国、印度、伊斯兰世界以至欧洲联系在一起。从中国河北、山东及东南沿海到朝鲜、日本的航路早已开辟了。中国商人通过海路直接到达朝鲜,商队人数最多时达到百人,也有朝鲜商人乘船跨过鸭绿江进入中国,最远到达唐都长安。7世纪新罗统一朝鲜后,中朝贸易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国内许多城市有朝鲜商人,带来的商品有人参、马匹、药材、金、银、毛皮、水果和饰物,从中国购回的商品有书籍、瓷器、铜镜、绢、谷物、食品、染料和药材等。朝鲜半岛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也在很早之前就已开辟。日朝物质文化交流具有地理毗邻上的优势,人员往来与商业活动频繁。海上风浪与航海技术条件上的局限并没有阻止东亚国家间的交往。这些物品在东亚国家间源源不断地交流着,使各国在短时间内共同受益,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发展。朝鲜、日本以至南洋各国正是通过这种贸易与中国保持着政治经济联系,成为东亚经济圈的有机组成部分。
东亚经济圈走向鼎盛与成熟,主要表现为对外贸易区域的扩大,经贸活动向域外传播和扩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际贸易中心。它的显著特征是构成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对外相互联系与互动,形成内外循环机制。国际贸易港的出现是对外交往发展扩大的表现。广州、交州、泉州、扬州、明州等都是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口,每年在这里进出的商船就有数千艘。广州是唐代对外贸易最繁盛的城市,扬州则以国内商业称雄(17)。唐朝对海外贸易采取了积极的开放政策,率先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专事南海贸易。虽说其规模与运作方式不同于近代,但无疑说明唐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发达的商品经济。近些年的经济史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阿拉伯帝国兴起后对东方的贸易颇感兴趣,商人大举东来,足迹遍及中国与南洋各地,有力地衔接远东、南洋、印度洋以至红海和波斯湾的贸易,推动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西太平洋贸易圈的形成。“由唐而宋,中国南部与波斯之间,大开通商,波斯湾各港皆依东洋贸易而繁昌。”(18) 中国与南洋、印度以及阿拉伯世界的交流主要以经贸为主,同时伴有文化的传播与移民的迁徙。
进入宋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对外贸易向海洋方向发展,规模扩大,出现贸易兴盛的局面,“市舶之利”已成为当时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有时候宋朝还利用使臣出使国外之机招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对外输出多以金、银、铜钱、绢、瓷器为主,输入以象牙、犀角、药材与珠宝为多,“贸易既盛,钱货遂湧湧外溢。当时宋之铜钱,东自日本西至伊士兰教国,散布至广”。(19) 由于对外国商客采取了宽大的政策,故许多港口成为外国商客的栖息之所,即“蕃坊”。《蒲寿庚考》指出:“宋代奖励互市,故侨蕃甚蒙优遇,纵有非法行为每置不问……蕃汉之间有犯罪事,苟非重大之件,亦听以彼等法律处分。”(20) 由此可以窥出宋代对外国商人来华政策之宽松。新的港口城市的兴起,大大带动了国内市场的发展,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宋代的城市都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当时人口达到1亿之数。国内经济长足发展,粮食产量增加,耕地面积扩大,南方许多地区成为中国对外出口的生产基地。总体来说,宋代的城市发展与社会文明程度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科技进步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宋代的造船技术与航运是世界一流的,船只可容纳六七百人。造船技术“降至宋元,益臻其极”(21)。造船技术与航运的发展,盖得益于指南针的应用。正是应用了这个新技术,中国商船远航于南洋、印度洋、波斯湾和非洲东部海岸,同国外进行着有无相通的贸易交换。科技进步直接促成对外交往的扩大与便利,从广州至阇婆国(今印尼爪哇),“顺风连昏旦,一月可到”(22)。阿拉伯商人到东南亚贸易者络绎于途,将本国所产带到东南亚的三佛齐,然后再贩卖到中国(23),以图厚利。在东亚大陆上孕育出来的中国古典农业文明是不同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的,它有自己的独特的运行规律,如果认为中国古典文明是封闭的或停止的,那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据《岭外代答》、《诸番志》等史书记载,两宋时期中国对外交往通商的国家与地区达50多个。中国为什么能与如此众多的国家有政治经济往来呢?除了中央政府支持外,技术进步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元代对外贸易与交通持续发展,规模超过前代。中央政府采取了开放的政策,不仅有中国商船抵达亚非数十国家,而且允许大量的外国人进入中国,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当时的京城大都是世界著名的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世界各国商人、学者、旅行家、传教士纷纷东来,把域外的文明带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文明带到世界。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元大都——汗八里的情况:“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人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24) 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元大都城市发展与经济繁荣的情况。元朝采取了较为宽容的对内对外政策,都城内各民族与教派和睦相处,城内居民语言文雅、见面行礼甚恭,王公贵族喜欢舶来品和奢华生活等。这些都是国际大都市生活的具体反映。在对外贸易方面,元代被认为是中国对外交通发展的新阶段,交通范围东起日本、朝鲜经南洋,西至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区。西太平洋地区形成的巨大的贸易网络不仅使东亚各国联成一体,也有力地衔接了东亚与印度以及伊斯兰世界,从而形成从东亚到东南亚以至印度洋的范围广阔的交流圈。为了便于管理贸易,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元政府承袭了前代的市舶司制度,对来华贸易税额大体十分取一或十五分取一。此时的欧洲还没有走出大西洋,有的国家尚处在分裂与动荡之中。
一个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不仅表现为区域内各国经济相互联系与互动,也表现为文化上的相互吸收与借鉴,与经济相互促进。中国文化、科技、律令以及佛教对东亚各国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建筑、书法、文字、绘画等方面。可以说,东亚世界表现为文化东亚的特征。日本学者井上秀雄指出:“中国文化给予古代朝鲜文化以更大影响的是隋唐时代……隋唐文化为适应朝鲜内在发展趋势而受到了欢迎。”(25) 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随着国家的建立与发展,吸收外来文明已成为当务之急,律令、典章制度、治国思想甚至灾异祥瑞观念也成为它们的一时之需,日本学者田中健夫指出:“特别是作为国家统治理念的儒教给了日本以极大影响。”(26) 堀敏一认为,日本对律令法典几乎是逐条移植的(27)。文明的交流带来的是东亚社会的整体发展,使文明的成果在短期内为各国共享,缩短了与中国的差距。长期以来中国文明对东亚文明的影响是显见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忽视东亚各国的创造精神,各国都参与缔造了区域的辉煌。
在研究东亚经济圈时,有必要关注东亚历史上的朝贡贸易,视朝贡贸易圈为经济圈并不为过,有时候朝贡贸易担当着国家间贸易的主要角色。周边国家与民族也愿意与中国进行有无相通的贸易交流,“除了政治、文化上的要求外,还有通过朝贡与中国朝廷贸易,想得到中国物资的欲望,特别是游牧民族这种要求比重更大,但是农业国家也不例外。朝贡本身就是交易的一种形态,可以从中国王朝获得回赠”(28)。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指出:“特别是15、16世纪以来,随着对中国的朝贡贸易及互市贸易等官方贸易的经营发展,民间贸易也在扩大。以华侨、印侨为中心的帆船贸易和官营贸易一起,形成了亚洲区域内的多边贸易网。”(29) 朝贡贸易带来多元受益,它以和平互利为纽带推动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交流与共生,使物质文化生活增添了多样性。
东南亚在东亚经济圈中的重要地位不容置疑。据16世纪初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者多默·皮列士在《东方志》中记载,从中国驶往马六甲港的商船载有大量的生丝、明矾、硝石、硫黄、铜、铁、大黄、瓷器和盐等物品,仅盐船就有1,500艘(30)。马六甲是联系印度贸易圈与东亚贸易圈的中心,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华商充当了主要角色。朝贡贸易关系其实质就是官方主导下的国家贸易关系,在于满足宫廷贵族消费,既是政治活动又是经济贸易活动。据史籍记载,占城国“曾贡方物”,“又进贡,有诏赐钱二千六百缗,其慕化抑可嘉也”(31)。它们来华从事朝贡贸易并非认同中国的天朝上国地位,从中国得到回赠与交流上的好处才是真正的需求,或者说是促进朝贡贸易的持久动力。根据成书于明代的《西洋朝贡典录》可知,郑和下西洋后中西商道大开,出现20余个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交流的情况,在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三佛齐国“其交易用中国铜钱”、“其交易用中国历代钱及布帛”(32)。明代中外交易的商品有金银、器皿、犀角、象牙、宝石、胡椒、白绢、薰衣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线香、纸扇等。清代中期以后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对粮食需求日益增长,雍正、乾隆时期对来自泰国等南洋各国的粮食贸易实施了奖励政策,广东、福建还根据商人购入米量的多少授予职衔和顶带(33)。17世纪,华商在东起日本、经朝鲜半岛到东南亚的广阔区域从事多角贸易,输出的商品有红毡、白丝、白纱、陶器、鼎釜,输入商品有苏木、白锡、胡椒、象牙、大米、海米、纹银等。赴长崎的船只装载的生丝和织物购自苏州、杭州、广州,染料来自安南,砂糖来自福建(34)。从明至清代前期,中国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国际地位是无与匹敌的,但社会发展已经明显缓慢。
许多学者都认真地探讨过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国际地位问题,也试图从多方面寻找造就中国国际地位的诸多原因。在贡德-弗兰克看来,当时全球经济有若干中心,但在整个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中国(35)。明代的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当时的欧洲支离破碎,“比起这个时期最强盛、最先进的明帝国和勃然兴起的中东奥斯曼帝国和萨菲帝国,西欧黯然失色。中国当时的财富和人口都遥遥领先”(36)。清代前期,1750年中国在世界工业生产所占的份额为32.8%,印度为24.5%,整个欧洲为23.2%;到1800年情况发生一些变化,中国为33.3%,印度为19.7%,整个欧洲上升到28.1%(37)。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文明的重要中心之一,也是数千年来绵延不绝、不曾中断的文明。
在清代前期中国经济发展时,日本经济也有了相当的发展。日本国内陆路、海路交通密布,商品经济发展,江户、京都和大阪成为全国最为发达的城市。18世纪江户的人口为110万,大阪、京都也有40多万,同时遍布全国各地的城下町(最大的城下町是名古屋、金泽,人口有10万左右)也有了很大的发展(38)。东亚城市与农村人口高度发展是传统社会内部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连续性的产物。在对外贸易方面,江户时代有对东南亚国家的朱印船贸易。所谓朱印船贸易,就是持有幕府颁发的朱印状(即官方许可证)的贸易。商人从幕府那里得到经商许可,从事海外贸易。幕府为了增加收入,鼓励海外贸易,对海外贸易具有特殊的兴趣。从1604—1635年,幕府共颁发300多张朱印状,朱印船达350—360只,航行的港口多达30多个,遍布赤道以北南洋各岛,尤以越南、柬埔寨、泰国、菲律宾为多(39),盛极一时。东南亚是中国和日本商船最为活跃的地方。得到朱印状的不仅是日本人,日本的华商、英国人和荷兰人也都得到了朱印状,参加东亚区域贸易(40)。贸易兴盛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之一,反映一个地区的发展程度。
暹罗、爪哇、旧港各地船只也北上日本交易。长崎和对马是著名的贸易港,这里因出口铜而出现繁荣。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担当了对外贸易的主要角色,到达朝鲜、东南亚、印度和欧洲等地,1700年前后仅从长崎输出的日本铜就有800万斤左右(41)。在近世时期虽说日本“锁国”,但并没有中断与中国、荷兰、朝鲜等国的对外关系。明朝初期执行了只许外国船只来华朝贡贸易而不许国内船只出海的海禁政策,但这一政策并没能从根本上限制住东南亚各地和琉球商人同倭寇接触的走私贸易,况且出现日本与朝鲜通商的新情况(42)。朱印船贸易的出现说明日本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对商品与市场的需求,靠固定的地租收入已经不能满足社会上层的消费和维持日益庞大的财政支出了,也说明日本封建关系在松弛,传统的封建关系难以维持。这符合16世纪以来世界各大区域逐渐被整合到近代资本主义市场与体系发展的总规律。
三、西方世界的兴起与东亚经济圈的衰落
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了印度果阿,1511年占领东南亚马六甲王国,1537年来到中国澳门。以16世纪初葡萄牙人东来为嚆矢,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又联翩来到中华帝国的外围,东亚传统的政治经济秩序受到欧洲殖民主义的最初冲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殖民者力量弱小,无力与东方国家进行竞争,故不得不进入东亚经济圈当中与东方国家进行有限的贸易。他们被限制在几个海岛及其沿岸地区。这一情况只是到了19世纪才发生根本性改变,南洋、印度洋航线上的贸易为欧洲人所垄断。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该公司鼎盛时期基本上垄断了自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的海上贸易权力,其船只最多时达到160余艘,“荷兰东印度公司实力之大,其他各国的印度公司不能望其项背”(43)。后来受到英国、法国的有力竞争。到19世纪,英国已经占领了马来亚、新加坡、文莱、缅甸等国,法国占领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荷兰控制印度尼西亚群岛,葡萄牙占领了东帝汶,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整个东南亚地区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欧洲列强通过各种途径使东南亚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从属于西方。
东南亚的沦失成为古代东亚经济圈的破坏力量,造成东亚经济圈的急剧萎缩。原来由东方人开辟的古代海上香料丝绸贸易航路为近代欧洲人垄断了,东方商人也沦于欧洲商人的从属地位。欧洲人开辟的近代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及西太平洋的贸易把东亚与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世界统一市场的条件已经形成。欧美国家的冲击限制了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因而被局限在朝鲜、日本等少数几个亚洲国家,对外贸易锐减。西方殖民者东来造成与中国近300年的贸易冲突,例如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二年的40年间,前往日本长崎的中国商船共有1,584艘,其中最少的年份为9艘,最多的年份为76艘,平均每年不到40艘(44)。殖民主义在东亚进行一个多世纪的掠夺性开发,无止境的财富外流使东亚各国付出了沉重代价,以至造成人口锐减,特别是爪哇岛的情况更为严重,1815年人口减少7%,1890年减少3%(45),与欧美国家城市化现象相反而出现了城市衰败与人口减少情况;在经济方面,仅英国统治下的缅甸每年被掠走的柚木就有27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70%;英资公司在缅甸垄断的石油达75%(46)。东南亚传统的国际秩序被打破后,中国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疏远与松弛,从而造成传统的东亚古老的国际关系结构逐渐瓦解。“从商品结构方面来看,明清时期形成的远东市场也很不完备。”“尤其是在海外市场方面,江南产品出口的大量贸易余盈,并未换回江南工农业发展最急要的物资。其所换回的,主要是白银以及鸦片……后者则严重地危害了江南经济的发展。”(47) 在物资的交流与交往中欧洲人逐渐强大,置东亚国家于弱者与失败者的地位,区域性的贸易遂为全球性的贸易所取代。
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越南、朝鲜相继脱离与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关系,古老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彻底解体。东亚传统的政治、经济秩序被打破,从根本上改变了东西方国家正常的关系,因而造成东方被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抛向世界边缘的被动局面。据统计,1830年中国工业生产占世界总额的29.8%,尚可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但50年后,下降到只占世界总额的12.5%。这与蒸蒸日上的欧洲形成鲜明对照。从东亚输出的商品来看,一般以茶叶、瓷器、陶器、古董、药材、香料、书籍等生活消费品为主,西方国家对中国输出的商品一般是工业革命后的商品,或经过工业革命后的思想、文化与科技。商品的不同反映出国力的不同,或许由于这个差距形成后来东西方发展差距的天然分野。亚洲诸国,除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对外扩张、实现了国家崛起外,其他国家都处在停滞甚至倒退当中,作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而成为宗主国的附庸,其经济日益畸形化。总体上看,东亚国家经济增长极为缓慢,农业、畜牧业和人力技术为社会提供非常有限的剩余产品,许多方面出现某些停滞的趋势。这里所说的停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停滞和不变状态,而是指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文化领域缺少新因素,很难突破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发展在很低的水平上运行。
长期以来,东方社会发展领先于西方,16世纪以后东西方关系悄然发生变化。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指出:“1500年以前,是世界冲击欧洲;1500年以后,是欧洲冲击世界。”(48)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欧洲人开始走向世界,到处伸张它的力量,把世界变成了它的市场。威廉·麦克尼尔说:“简而言之,欧洲找到了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使得其军事扩张可以持续下来,而这一机制所依赖的经济和政治扩张却是以地球上其他国家和人民为代价的。”(49) 进入19世纪以后,长期落后的西方率先在经济、技术、军事、文化等方面实现了快速发展,并获得对非西方世界的统治优势。工业文明具有东方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无法比拟的巨大力量。科技进步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提高国家的竞争能力。经过两次工业革命浪潮,欧美大国完成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相比之下,东方国家大都处于农业文明的阶段,缺乏抗拒西方冲击的力量,在东西方较量中普遍落伍。工业革命造成欧洲高速增长的生产方式和社会财富形式的转变,使生产力的质量与结构空前优化,因此在物质力量和社会财富方面形成巨大优势,形成工业—西方、农业—东方的天然分野,拉大了东西方的发展差距。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欧洲不仅成了世界的银行家,而且已成为世界的工业工场。1870年,欧洲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4.7%,而唯一的对手美国仅占23.3%。到1913年时,虽然美国已向前发展,达到了35.8%,但这一年欧洲工厂的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47.7%。”(50) 这是西方国家通向近代崛起的物质技术条件。
长期以来欧洲的经济每年增长率极为缓慢,人均收入每年增长率只有0.11%左右,只是到18世纪下半期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引人注目的发展速度。自18世纪下半期以来,欧洲国家的发展是加速的,尤其是进入19世纪下半期,科技已成为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因素。1850—1870年的20年间,世界工业生产增加了1倍多,而1870—1900年的30年间世界工业生产增加了近2倍,工业生产速度大大加快,社会财富急剧增多。以钢铁和电力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已成为国家实力与强盛的主要标志。铁路和公路网的建立,技术、投资与贸易的扩大以及商业的发达,使欧美成为新兴工业化的中心。东方的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都处在急剧衰落之中。欧洲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地区脱颖而出,从根本上说是科技革命、制度创新与思想变革相互作用的结果,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带动了社会的整体发展。贡德·弗兰克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为什么在同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里,到1800年前后原来一直落后的欧洲、接着是美国‘突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赶上和超过了亚洲。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努力和胜利乃是统一的全球经济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正是这个全球经济的结构和运转产生出这种变化。也就是说,欧洲(西欧)和美国先后出现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技术进展和其他方面的进展,而且把它们应用于新的生产过程中。”(51) 离开了制度创新与科技进步,就很难理解欧洲的历史。
为什么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实现崛起、走向世界强国之列,东方国家普遍衰落甚至沦为欧美强国奴役掠夺的对象呢?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绝不是靠单一因素可以解释的,必须根据多方面条件加以具体分析。其中有一条最为重要,那就是工业文明已成为其社会文明的主宰力量,新的生产方式带动的社会变革全面加速,提高了国家的整体竞争水平。东方文明主要来自传统的农耕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普遍缺乏对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竞争力量。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出现了物质生产加速增长的趋势,重大科技发明与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大大缩短。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崛起不仅是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经济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且实现了社会制度创新和思想观念的进步。国家崛起是一个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整体演进的过程,并非某一方面的单项发展。美国学者布莱克指出:“它是近世以来知识爆炸性增长带来的结果。其特殊意义,来自于它的动力特征和对人类事物影响的普遍性……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发生着急速的功能变迁——它伴随着科学革命而到来,反映了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从而使人类控制环境成为可能。”(52) 他以“知识爆炸”、“制度变迁”和“科学革命”来形容现代化的威力,是非常形象而准确的。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经济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存在一个长波周期。一般来说,在农业文明时代,一个国家的兴起和另一个国家的衰落时间相对较长,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进入工业文明后,国家间、地区间的竞争与兴衰比以前剧烈得多,发展极不平衡也不稳定。一个经济中心可能很快衰落或另一个经济中心可能很快崛起,相互交替地演变发展。一个国家可以超常规的方式超越其他强国,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史上屡见不鲜。因为工业文明是科学—技术—生产的有机结合,完成了科学社会化和社会化科学,直接创造财富,推动社会进步。例如1870年英国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第一位,美国占第二位,德国第三位,法国占第四位,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已超过英国占第一位,英国占第二位;到20世纪初,德国又超过了英国,居第二位。使欧洲和北美成为近代人类两个重要的文明区域。需要指出的是,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带有很大的相对性,即便是衰落也仍保持先进国、强国的地位,发展规模与质量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在以科技和经济质量为主要内容的竞争时代,竞争成功的周期相对缩短,不像农业社会时代那样漫长。这是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通过上述东西方发展差距的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到东亚进入近代以来社会经济落后的重要特征:第一,低下的农业、手工业只能为社会提供极其有限的剩余产品,生产力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无法带动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变化;第二,科技贡献率极低,发展速度与质量明显的低于世界其他地区,传统的科技优势丧失;第三,政治上处于依附地位,自身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外来因素影响,丧失了原有的凝聚力和对外辐射功能;第四,思想文化上丧失了国际先进者与输出者的地位,浓重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外来文明产生强烈的抗拒作用。以上四点归纳得不一定很准确,但基本上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衰落的情况。
四、东亚经济圈的复兴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东亚社会发展从古代的领先地位到近代的衰落,从近代的衰落再到今天的重新崛起,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和内部的矛盾运动规律。东亚崛起使长期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发展模式受到挑战,“东西方力量结构的变化,使两者间原具有依附性的不平等的关系开始转变为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东亚对西方亦步亦趋或受遏制时代正在成为历史。西方对东亚经济优势的丧失,具有对东亚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的丧失的连带性后果”(53)。按照美国学者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在《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一书中的观点,国家也同人一样具有幼年、青年、老年和暮年等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对意大利城邦、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崛起的考察虽有不完备之处,但有一定的可参考价值。过去社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基础已完全不同于今天。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以及众多复杂因素的推动,使东亚在普遍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东亚经济圈的复兴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将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及其未来走向。
战后东亚国家实现了跨世纪变革与重新崛起,以较强的经济活力和增长率使东亚形成新的文明区域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这是东亚历史发展的重大突破。吉尔伯特·罗兹曼指出:“东亚地区在历史上就了不起,直到十六七世纪甚至18世纪,至少在过去的两千年时间里,东亚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现在只要看看该地区的诸多国家以及那些举家移居海外的东亚人所取得的最新成就,大多数研究者都会同意,东亚将拥有一个辉煌的将来。”(54) 东亚重新崛起是20世纪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多样的、丰富的,并非只有西方现代化道路之一端。
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圈即北美经济圈、欧洲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圈遥相辉映,竞相发展。西太平洋地区崛起并不意味着大西洋经济圈的衰落,而是昭示着人类社会进入了多强并存与竞争发展的时代。在这三大经济圈中尤以东亚经济圈发展最引人注目。它不仅拥有162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面积,而且有接近世界人口1/3即超过20亿的人口,更为重要的是它拥有悠久的历史以及隐藏在悠久历史背后的强大的发展潜力,经济总额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迅速提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0年东亚在世界所占GNP为13%,1970年升为19.5%,1980年达到21.8%,1999年达到25.9%(55)。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为3.3%,90年代下降至1.1%,而同时期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率达到8%左右。这一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地区。20世纪70年代日本率先实现经济起飞,接着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进入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创造出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新经验与新模式。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作用不断加大。
东亚经济圈的复兴并非简单的历史轮回,而是显示了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与世界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历史发展过程就是旧的经济中心衰落和新的经济中心不断兴起发展的过程,新旧两种经济中心相互推动地演变着。由于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不同,因此发展道路也是不同的,世界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正是不同模式的相互借鉴补充,才形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世界。我们不赞成孟子所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即把历史看成五百年一循环的历史轮回观点,也不赞成21世纪是东亚的世纪,但我们认为在21世纪东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许多发展迹象表明,在未来的东亚地区形成一个新的知识、财富与文化中心是完全可能的。
注释:
① 本文为外交学院“东方外交史”研究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谢丰斋教授对本文的写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向他表示谢忱。
② 陈奉林:《东亚区域意识的源流、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世界历史》2007年第3期。
③ 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73页。
④ 他们的代表作是,滨下武志:《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岩波书店:1997年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亚洲交易圈与日本工业化1500—1900》(藤原书店2001年版);中村哲:《近代东亚经济史结构》(日本评论社。2007年版)、《东亚近代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日本评论社2005年版)、《近代东亚史像的再构成》(青木书店1991年版)、《东亚专制国家与社会、经济》(青木书店1993年版)、《1930年代的东亚经济》(日本评论社2006年版);杉原薰:《亚洲间贸易的形成与结构》(米涅瓦书房1996年版)、《亚洲太平洋经济圈的兴隆》(大阪大学出版会2003年版);宫岛博史:《近代交流史与相互认识》(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1年版);黑田明伸:《中华帝国的结构与世界经济》(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版);川胜平太:《亚洲太平洋经济圈史1500—2000》(藤原书房2003年版)等。
⑤ 沈仁安:《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⑥ 佐伯有清:《古代的东亚与日本》,教育社1977年版,第23页。
⑦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⑧ 堀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中华世界与诸民族》,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04页。
⑨ 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
⑩ 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11) 堀敏一:《律令制与东亚世界》,汲古书院1994年版,第138页。
(12)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13)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14) 堀敏一:《东亚中的古代日本》,研文出版(山本书店出版部)1998年版,第269页。
(15) 堀敏一:《律令制与东亚世界》,第167页。
(16)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165页。
(17)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页。
(18) 桑原骘藏著,杨炼译:《唐宋贸易港研究》,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7页。
(19) 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考》,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54年版,第31页。
(20) 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考》,第47页。
(21) 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考》,第99页。
(22)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8页。
(23) 赵汝适:《诸番志·大食国》,《酉阳杂俎·岛夷志略·诸番志·海槎余录》,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209页。
(24)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237页。
(25) 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编:《隋唐帝国与东亚世界》,汲古书院1979年版,第329—330页。
(26) 田中健夫:《东亚通交圈与国际认识》,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第25页。
(27) 堀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中华世界与诸民族》,第168页。
(28) 堀敏一:《律令制与东亚世界》,第166页。
(29) 滨下武志著,朱荫贵等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30) 多默·皮列士著,何高济译:《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01页。
(31) 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第77页。
(32) 参见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4页。
(33) 山本达郎编:《越南中国关系史》,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第436页。
(34) 廖赤阳:《长崎华商与东亚交易网的形成》,汲古书院2000年版,第159页。
(35)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168页。
(36)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世界史便览》,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95页。
(37)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我国学者李伯重先生指出,如果以西欧经验作为近代化的标准,至少自明末以后我国江南地区在商业化、城市化、农村工业、交通条件以及人民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均已走在18世纪中叶英国的前面,若以18世纪中叶的西欧标准,江南地区可以说已经十分“近代化了”。参见李伯重:《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02页。
(38) 中村哲主编:《东亚近代经济的历史结构》,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5页。
(39) 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40) 滨下武志、川胜平太编:《亚洲交易圈与日本工业化1500—1900》,藤原书店2001年版,第105页。
(41) 川胜平太编:《亚洲太平洋经济圈史1500—2000》,藤原书店2003年版,第29页。
(42) 田中健夫:《东亚通交圈与国际认识》,第20页。
(43) 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45页。
(44) 陈高华、陈尚胜:《中国海外交通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页。
(45) 安索尼·里得著,平野秀秋、田中优子译:《大航海时代的东南亚1450—1680》Ⅱ,法政大学出版局2002年版,第89页。
(46) 梁英明、梁志明等著:《东南亚近现代史》上册,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47) 李伯重:《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第400页。
(48)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世界史便览》,第295页。
(49) 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等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62页。
(50)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62页。
(51)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382页。
(52)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53) 李文:《东亚社会变革》,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54) 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等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第3页。
(55) 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等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第388页。
标签:朝鲜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