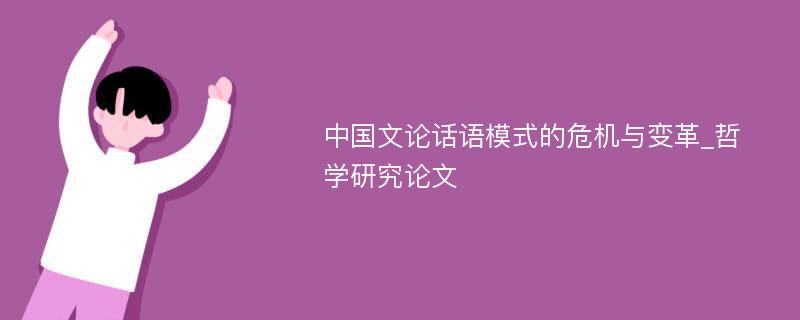
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危机与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论文,话语论文,危机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社会生活、思想资源、文艺样态的急剧变革,特别是西方文论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论濒临“秦砖汉瓦”式的博物馆生存状态,存在着基本观念与研究方法失效的危机。这个过程至今仍未完成,还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因而值得引起特别的关注,这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深刻的变革。这个变革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环节是话语方式的变革。我们过去在讨论中国文论的现代变革时,对观念范畴等内容性的因素关注较多,而对于话语方式这样一个形式性的因素则较为忽略。
话语方式是思考和阐述问题的方式,因为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是思想的外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也就决定了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来阐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论话语方式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论问题,在其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为哲学话语方式所支配。从中外文论史的发展来看,历史上的哲学经典著作,往往也是美学和文论经典著作,尽管关注的话题和领域有异,但是在话语方式上往往具有本质的同一性。换言之,文论话语方式是哲学话语方式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继续和延伸,这意味着对文论话语方式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价值。对于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探究,是推动未来中国文论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中国传统文论的话语方式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前辈学者罗宗强、卢盛江不无忧虑地写道:
古文论特有的表述方式使它的确切含义在今天有许多已经不易了解,如何解释和评价确实存在问题。比如说,古文论中有一种点悟式的评述方式,往往三言两语,给了比喻、暗示,借助形象引发联想,以说明某一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往往带着模糊的性质,可以作多种解释。一方面,它容量极大,意蕴无穷;一方面它又极不确定。①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呢?罗宗强、卢盛江引用并赞同王元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二版跋中的观点,主张“用今天科学文艺理论之光去清理并照亮古代文论中的暧昧朦胧的形式和内容”,他们明确指出,“只有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语言给以确定阐释,才谈得上继承的问题。……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几十个独特的理论范畴的阐释问题。这些理论范畴的阐释,不借助现代科学方法、现代文学理论的成就,是很难做到的”②,他们进一步做了这样的具体阐述:
对于这些含义模糊、且极不稳定的范畴的阐释,如何加以科学的界说,需要借助现代科学的方法,以古证古是不可能做到的。……以古证古无非两途,一是传统的疏证方法,如释“兴象”,或以此“兴象”释彼“兴象”,诸如此类。这样的疏证方法,当然无法确切解释含义极不稳定的理论范畴。另一途,是运用古人使用的点悟式的方法,范畴既模糊与不稳定,也以模糊与不稳定之方法释之:运用象喻、描述诸方法,这当然也只能是以不甚了然对不甚了然。这两途,都不可能达到科学解释范畴的目的,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比附之病。③
怎样用科学的方法去清理和照亮古文论中暧昧朦胧的东西呢?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阐述对我们具有指导意义。在谈到西方哲学时,冯友兰把研究方法置于首位并明确指出:“西方哲学对中国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④。在他看来,我们学习西方哲学,“重要的是这个方法,而不是现成的结论”⑤,他引用了“点石成金”的中国神话并反其意而用之,说“逻辑分析方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⑥。冯友兰认为:“对于儒家以外的古代各家的研究,清代汉学家已经铺平了道路。汉学家对古代文献的解释,主要是考据的,语文学的,不是哲学的。但是这确实是十分需要的,有了这一步,然后才能应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古代思想中各家的哲学观念。”⑦
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以古证古”包括传统疏证或点悟式的研究方法,为进一步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但是中国文论研究要继续前进,避免“以不甚了然对不甚了然”,我们还需要应用来自西方的逻辑分析的方法来加以研究。冯友兰评论说,“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中国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⑧。冯友兰是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说这些话的,英文讲稿于1948年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这里所说的时代精神,是指民国时期国内学界的通行的研究方法,即“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中国古代的观念”。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冯友兰倡导的这种方法效果如何呢?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居于中国近百年现代学术的巅峰时期,这已经没有疑问。文史哲诸多领域在此姑且不论,就中国文论研究而言,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即中国文学批评史,从上个世纪20年代陈钟凡草创到30—40年代郭绍虞为之奠基,就是发生在民国时期。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等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学术大师,他们主要学术成就也是完成于民国时期。近些年来,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不能阐释中国文论的观点在国内学界颇为流行,一些学者对以西方文论解释中国文论多有诟病,这些指责和民国时期包括中国文论在内的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不吻合。
就中国古代文论自身而言,其话语方式确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这和中国古代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样态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历史上中华民族活动的区域,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东北平原、珠江流域等,土壤肥沃,雨量充沛,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对农业生产极为有利,历来是富饶的农业生产区域。由于古代技术条件水平的限制,历史上我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不利于经商,更不利于展开海外贸易。中国先民充分发挥了在农业生产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农业一直非常发达,而商业则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仅有微小作用并且受到抑制,“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的一项基本国策,商人在我国社会中历来地位很低并与“无商不奸”的伦理判断联系在一起,“自给自足”和“男耕女织”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典型生活图象。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具有强烈的农业性特征,由于农业劳动力的需要,人被固定在土地上,不尚迁徙,流风所及,中国至今仍是世界上为数极少的实行严格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之一。在这种农业社会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崇尚安贫乐道,冒险和旅行非常稀少,遵循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起居有时”的有规律的生活,人们每天所经历的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用钟嵘《诗品·序》中的话来说,中国古代诗歌所描写的都是“即目所见”,也就是古代农业社会里随处可见的日出日落、云起云飞、春花秋月、月缺月圆等日常景观。这种农业社会从生活样态上讲,种地是“靠天吃饭”,取决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从文学体裁上讲,形成了以抒情短诗为纯文学的基础文类的中国古典文学,从中国哲学关注的重心来看,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而不是形而上学和认识论⑨,从思维方式来讲,不需要精密的计算和严格的推理,更多地依赖农耕技术直接经验的积累,来自父辈的耳提面命。中国古代“由于缺乏纯粹的逻辑训练,将知识限制在直观经验的范围内,对理论科学的长足发展极为不利”⑩。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经验性特征,体现在社会生活,就是老人享有智慧的权威,体现在文化领域,就是远古的典籍具有毋庸置疑的崇高地位,使整个社会笼罩在崇古和学古的浓厚氛围之中。中国古代“万世师表”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有志于文献整理而不是理论创新,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特征的典型化。在中国古人看来,“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颜氏家训·文章》),这是天经地义的,“依经立义”和“微言大义”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古代哲学话语的基本方式。
在中国古代正统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看来,六经包括了全部真理,许多学者把一生的精力与才智用在为六经作传疏上。这种经学笺注主义的思维把某一学科的原始经典神圣化,采取“述而不作”的态度,“有了经验知识,不去另作一本书,却往往通过笺注的形式附加到经注中去,这样就使得一门学科始终维持在原来的体系上”(11)。这种注经式的话语方式,其优点是长于整理和阐释传统典籍,但是对现实提问和解答的能力则明显薄弱。中国传统哲学以经学形式发展,经典注释不需另立新说,更不需要详细的理论论证和繁复的逻辑展开,甚至可以达到“一字褒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的程度。
希腊传统诞生和孕育了西方哲学。希腊哲学传统和古希腊的地理环境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希腊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南端,西濒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相邻,南隔地中海与非洲相望,东面是爱琴海,过海便是亚洲,处于东西方交通要冲。从岛内情况来看,群山环绕,土地贫瘠,崎岖不平,不利于农耕。但是希腊人从别的方面获得了丰厚补偿,这就是海上贸易。大海有着便于发展海上贸易的优越条件,特别是在古代内陆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希腊半岛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必经之途,这使古希腊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形成了以工商业城邦为核心的古希腊社会的商业性特征。
在古希腊商业城邦中,海上贸易的开展、财产诉讼的频繁、民主政治的斗争、雄辩术的兴盛等,无不需要雄辩的逻辑和严格的论证,以及在商业活动中精准的计算。浩瀚的大海美丽动人而又神秘莫测,海外贸易生活富于传奇性,它与探险、旅行、战争、掠夺、财富的寻求和未知地理领域的开辟等联系在一起,奠定了惊险刺激而不是平静如水的生活基调,刺激了西方人大胆开拓的勇气和敢于冒险的精神,不利于形成崇古的社会氛围,也难于盲目地迷信远古典籍的权威。
这给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以决定性的影响。西方人很早就有了自觉建立知识体系的意识并划分了学科。古代西方哲学不仅包括我们当今所理解的哲学,也包括其他诸多学科,古希腊人已经自觉意识到算术、几何、天文学、音乐等相互关联但又彼此区别的领域,并称之为“学科”(12)。如果说中国古代哲学更多地建立在人文学科的基础上,那么,西方哲学则更多地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因此西方哲学很早就系统地发展出了用逻辑分析来进行精密研究的方法。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希腊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13),在古代西方,逻辑学是哲学的一个主干学科,逻辑分析的基本方法被运用于哲学的所有分支学科(14)。
从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哲学的目标不仅是建立知识体系,而且就其自身性质而言,是“爱智慧”(15),因此重视逻辑思维能力是西方哲学的重要传统,亚里士多德最早奠定了逻辑分析的思想。“亚里士多德首先出来分析人的思想,找出人类思想原来亦有一定法则可循,这就是他在哲学上最有贡献的地方,也是影响后世最深的一种哲学方法”(16),亚里士多德把逻辑学称为分析学,他认为逻辑是获取真正可靠的知识和方法的工具,我们必须掌握这种方法和工具,才能进行科学的研究(17)。中国古代哲学中尽管也有公孙龙子关于“白马非马”的逻辑问题的思考,但总体上讲,就逻辑思维能力重视程度和思考的深度而言,我们远不及西方哲学,这给予中西文论不同的话语方式以深刻影响。
亚里士多德指出,“辩证法”探求方式的中心之点是怎样提出一个“论题”或“问题”,因为它要讨论的是一些重要的意见及其分歧。讨论首先要把这些分歧的意见集合在一个“位置”,使之相遇形成一个恰当的论题或问题,才能正确地通过对问题开展讨论,分辨真理与谬误,达到探求真理的目的。辩证法思维学说的第一条,就是要研究如何善于提出问题(18)。我们通常把辩证法简单地理解为对立面的统一,很少从这样的思维形式上来把握辩证法,其实善于正确地提出问题,是建立知识体系的前提,也是思维能力训练的重要内容,这构成了西方哲学话语的重要特点。
西方文论从一开始就不是以顺向继承为主,不是古籍整理式的“述而不作”,而是面向现实不断提问,在批判和否定中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西方文论史上柏拉图第一个自觉地建立了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并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从话语方式来讲,其特点是“柏拉图反对以前的文艺最力,破坏多于建树,他的文艺理论,总的说来,与其是阐明文艺的理论,不如说是反对文艺的理论”(19)。柏拉图的摹仿说是对德谟克利特摹仿说的彻底否定,柏拉图反对智者学派提出的“美是视听引起的快感”的观点,提出了美是理念的学说,柏拉图反对希腊社会流行的推崇艺术教育的观点,激烈批判艺术的危害性,并引发了中世纪教会对世俗文艺的仇视。这种话语方式后来被亚里士利多德概括为“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思想传统,即在对前人的否定和批判中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对后代西方文论产生了重大和深刻的影响。
中国文论的话语方式有着不同的特点。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中,曾经从一个西方学者的独特视角,批评了严羽《沧浪诗话》的话语方式,他指出,“《沧浪诗话》的流行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或许是最严重的),那就是把盛唐诗经典化了,盛唐诗从此成为诗歌的永恒标准”(20),“让读者感到,如果有任何不忠,都将受到嘲笑。本来有许多可供选择的风格,一旦信奉《沧浪诗话》,正确的选择就只剩下了一个了”(21),如果我们参照孔子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就不难了解这种独断式的话语方式在中国文化和文论所具有典型意义。这种话语方式以顺向继承为主,反对任何与主流和传统相悖的具有异质性的东西,不利于新异和叛逆的文艺理论生长。
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悲剧艺术非常繁荣。针对当时的文艺创作实践,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系统总结了古希腊悲剧艺术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并由此建构了他的文艺理论主体部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逆向继承了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摹仿说,针对柏拉图认为艺术对现实是依样画葫芦的描摹,亚里士多德肯定艺术的创造性,针对柏拉图认为艺术是“照镜式的摹拟”,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创造性的摹拟”(22)。柏拉图认为诗诽谤神灵,有伤风化,贬低英雄,对青年有很坏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净化”说,认为艺术是正当和高尚的有益活动,给人以“无害的快感”而达到伦理教育的目的。
这样的话语方式对后代西方文论产生了积极和深刻的影响。黑格尔彻底否定了摹仿说,在《美学》中黑格尔睿智地指出,按照摹仿说的观点,艺术只是纯形式地按照自然的本来面貌来复制(copying nature forms just as they are)一遍,这纯属多余,因为自然原已存在着,如果依靠单纯的摹仿,艺术将无法和自然竞争,这犹如小虫爬着去追大象(23)。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现代西方富裕社会用消费需要控制人的自我意识并加以全面奴役,从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等方面,对包括艺术在内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性研究,试图给现代人指出一条摆脱“消费控制”的道路,把艺术、审美同反对异化、追求解放、自由、人的全面发展等结合起来,进而重建马克思主义文论(24)。俞吾金、陈学明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内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了如下概括: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对本世纪初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所提出的问题的一份答卷。……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中之所以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之所以留下了一连串富于创发性和开拓性的理论著作,因为它从来不使自己与现实生活绝缘(25)。
现代西方文论所发生的消费文化转向、图像转向、生态转向以及女权主义和少数族裔文论研究等,无一不是对现实文艺生活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积极回应的结果。随着近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感于当今世界文论格局中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强烈不对等地位,海内外华人学者忧心忡忡。黄维梁写道:“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二十世纪是文艺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中华的文评家也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26)对于这样一种文艺现象,我们不仅要看到它是什么,更要解释它是为什么,仅仅归结为西方文化霸权,未免失之肤浅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在复杂多样的因素中,就学术因素而言,中西文论话语方式的差异,作为文艺思维规则的差异,是比个别的理论观点的差异更为重要和深刻的东西,毫无疑问地构成了我们反思的核心内容之一。
冯友兰简洁地概括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话语方式,他写道:“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这是很明显的。但是,甚至在上面提到过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27)。早在作为中国思想源头的先秦哲学那里,孔孟的语录体和随感式,老庄的寓言化和格言式,都为后来的中国文论,奠定了一个诗性话语的言说方式,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干的儒、道、佛(特别是佛教中国化以后产生的禅宗)三家,莫不如此。
中国古代文论中常用的语录体,就是用名言隽语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注重而且通常也没有逻辑展开的过程,《论语》就是这样的典型文本。作为用语录体撰写的儒家经典的开创之作,《论语》主要记录孔子的言论和行动。由于孔子是以教师的权威地位和学生讲话,师生之间的地位是极不对等的,学生并不拥有和他同等对话和争辩的话语权力。孔子以智慧老人和百科全书的姿态出现,针对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无需严密的逻辑论证,直接给出简断和精辟的结论,学生无需辩驳欣然接受。长期影响着中国文论的诸多重要命题,如“思无邪”(《论语·为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等,都是孔子以这样的方式给出的。西方学者指出,“不同于欧洲和美国的大多数哲学家,孔子不依赖于演绎推理来使他的听众信服。而是使用诸如类比和格言警句等修辞手法来解释他的思想”(28)。《论语》、《孟子》、《朱子语类》、《二程遗书》和禅宗语录,直至“文革”期间的各种语录,语录体的话语方式贯穿了包括中国文论史在内的整个中国思想史,影响极为深远。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方式的特点之一,是喜用类比思维,往往采用比喻的方法说明问题,在这一点上《庄子》非常突出。用轮扁斫轮(《庄子·天道》)来比喻事物的精微之处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用“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庄子·骈拇》)来比喻仁义是不符合本然的多余的东西,用河伯见大海来阐述认识事物的相对性观点(《庄子·秋水》)。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得到广泛运用,“文若春华,思若涌泉”(曹植《王仲宣诔》),“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钟嵘《诗品》),以比喻和描述的方法,而不是理论演绎的展开来阐述文学观念,是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方式的典型特征。
佛教中国化以后产生的禅宗,与印度佛教在理论思维上有着显著差别。印度佛教卷帙浩繁,注重详细的逻辑论证和系统总结,某些经典如《大毗婆沙论》甚至带有经院哲学的繁琐特点(29)。唐代慧能创立的禅宗则高度简约化,标榜“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推行一套排斥语言文字、“以心传心”即直观思维的禅悟成佛方法(30),禅宗语录记录的是不加文字修饰的师徒问答,其特点是含蓄、简短、形象、直观。禅师教导门人时采用奇特的教学方法,对于初学者所问,多数情况下不作正面回答,而是采用棒打、脚踢、口喝、打耳光等,教人自己去体会和证悟。马祖道一法师原主坐禅,怀让以磨砖不能成镜为喻,说明成佛不必坐禅,使其顿然开悟(31)。宋代以后,“以禅喻诗”说盛行,严羽的《沧浪诗话》极具代表性,其中的“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等观点,都是强调创作思维和诗学知识的非理性与非逻辑。
姜广辉对中国古代思维模式特征作了这样的概括:“古人常常把形象相似、情境相关的事物,通过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办法,使之成为可以理喻的东西。我们称这种方法叫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32)。类比是一种较为形象直观的逻辑推理形式,它基于这样的假设,如果已知两个事物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那么它们在其它方面也一定是相似的。类比推理的优点是鲜明生动,它抓住两种事物的特征进行类比,容易化抽象为具体,增强说服力,比喻在本质上就是类比。正是类比思维的普遍运用,使中国古代文论擅长于化抽象为形象,能够把原本抽象的理论著述写得如同文学作品一般形象优美,生动感人。
但是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类比推理的弱点在于,逻辑上不够充分,是一种主观的不充分的似真推理,要确认其推理的正确性,还需要经过严格的逻辑论证(33),而这一点却往往为我们所忽略。当我们称颂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时,我们很少注意到,把天和人简单地加以类比,认为“天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夏秋冬之类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严格地说来,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取向比类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很普遍,但是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认识的一般过程应该由感觉、知觉、表象的感性阶段上升到概念、判断、推理的理性阶段。中国古人重视“象”,实际上是强调了思维过程中的表象作用,而概念思维却因此未能得到正常的发育。因此中国古人在认识过程中往往以表象代替概念,进行类比推理。……应该承认,人们有时会通过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所表现出的相似性、相关性,发现隐藏在其中的深刻规律。但是,如把类比推理当作思维的基本方法,就难免得出许多似是而非、牵强附会的结论。(34)
中国古代文论的许多名篇佳作,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杜甫《戏为六绝句》、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等,其共同特点在于,都是用优美的辞赋、骈文、诗歌写成,寓深刻的文学理论于浅显优美的铺陈和描写之中。如果说,亚里士多德《诗学》、康德《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美学》等西方文论经典更像是理论著作,那么,中国文论经典更像是文学作品。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更富中国民族特色,诗话也就是用漫谈和随笔的形式写成的关于诗的故事,诗歌理论即寓于其中。在大量的诗话和词话中,其点悟性、模糊性、经验性就更为突出。
中国古代文论这种诗意化的话语方式有一个显著特征,即缺乏明晰性与富于暗示性并存,“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35),“中国哲学所用的语言,富于暗示而不很明晰。它不很明晰,因为它并不表示任何演绎推理中的概念。哲学家不过是把他所见的告诉我们。正因为如此,他所说的也就文约义丰。正因为如此,他的话才富于暗示,不必明确”(36)。
中国古代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因此未能得到明确和自觉的区分,而是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比较接近的,在中国古代称之为“诗文评”,依据中国传统的古籍分类,“诗文评”附属于文学而没有取得独立地位。按照朱自清的说法,诗文评只有“一个附庸的地位和一个轻蔑的声音”(37),只是“集部(文学作品——引者注)的尾巴”(38)。中国古代文论确实给人以美的感受和多方面暗示,但是也鲜有精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不注重论证的过程,更多是经验的而不是理论的,更多是文学的而不是思辨的,通常是要言不烦,言简意赅,往往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随感而发,不成体系。正如赵汀阳所说:
尽管早就有许多深刻的问题摆出来了,但却没有由一个问题引出一些论证、由某种论证生成另一些问题这样一个明显的推进过程,结果2000年来的问题演变发展不大……不再面对问题,只在乎一些基本概念和教条的释义,这是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来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39)。
如果我们把中国古代思想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就会发现这种注经式话语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历史上不同的理论文本之间的联系,远胜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以哲学领域为例,先秦孔子在《礼记·檀弓下》中讲“苛政猛于虎”,汉代贾谊《过秦论》讲“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到唐代柳宗元《捕蛇者说》讲“赋敛之毒有甚于蛇”,讲的无非就要施仁政,至于如何通过程序正义的保证,真正迫使官员必须施行仁政,其核心问题即体制性的制约,则缺乏深刻的反思和实质性的理论推进,导致古代中国不管王朝如何更叠,始终是理论上空洞地倡导仁政而实际政治运作中难于实行,造成整个社会周期性的剧烈动荡而带来大规模的破坏。
从文论自身来看,先秦孔子的诗“可以怨”说,经汉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唐代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到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都是重视文艺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强调艺术创作主体对黑暗现实的怨愤激情和否定批判态度,要求作家创作出具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和深刻思想力量的文艺作品,这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够的,因为理论的实质性推进依然有限,顺向的理论传承远远大于逆向的创造性发展。由于面向现实提问和解答的能力不足,如果说在发展缓慢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不同理论之间的竞争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独裁所压抑,那么当置身于当今世界多种理论的飞速发展与剧烈竞争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文论的生存竞争和向异质文论辐射能力明显不足。
赵汀阳所论,不仅是制约中国传统哲学长期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着中国传统文论长期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在进入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互动的现代社会之后,这种制约性更加凸显。因为中国传统文论所面对的,主要是诗文正宗的经典文本,而现代中国的基础文类早已从小说戏剧转为影视文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概念“风骨”、“气韵”等和现代文艺基本绝缘。中国文论注经式的思维惯性妨碍了理论与现实文艺生活的源头活水之间相互流动,点悟性与模糊性的传统话语方式,又妨碍了作为思维之网的网上纽结即概念范畴的清晰性,这既不利于把现实文艺生活中产生的重大理论课题纳入研究视野,也不利于理论思维逻辑的积极展开和快速推进。如果说,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方式,和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及其文学样态是相适应的,但是对于深受西方影响而急剧变化的中国现代社会及其文艺样态,则是远远不够的了,我们必须赋予它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东西,积极推动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现代变革。
传统的中国社会本质上是宗法制农业社会,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所形成的强大家族意识,形成了中国社会宗教意识的普遍淡漠。类比推理的思维模式所产生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使封建帝王作为“真龙天子”的君权神授论得以合法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成为神权和政权合一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思想独裁和政治专制。专制社会中的思想独裁和政治高压给思想领域的影响,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智慧受到严重压抑而导致社会智力资源极度贫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浓厚的崇古和复古倾向,使得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滞重而缓慢。就汉字而言,我们并未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从象形文字进化到拼音文字,而是始终停留于象形文字阶段。作为表述思想的物质手段,汉字对中国古人的认知和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姜广辉认为:
由于中国文字具有象形意义,因而它的文字系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原来文字的内涵也随之扩大,有的名词甚至包含一两千年间不同的规定性,由此造成中国传统思维的概念(实为表象,这里姑且称之为概念)的流动性和模糊性。(40)
我们不妨对照西方文字,“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带有任何象形的意义,文字的意义完全是人主观加上去的。你提出一个概念并要人家能懂,就必须规定概念的确定意义。客观事物发展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就要重新界定概念,或创造新的概念,因而西方人的思维始终保持概念的确定性和对应性”(41)。如果说,中国文论传统的点悟式模糊话语,和中国文字的象形性自身带有意义相关,那么,西方文论严格遵循形式逻辑、“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42),则和拼音文字需要仔细规定概念的意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们从文字和多种艺术形式中,很容易感觉到中西思维样态的差别。有学者把传统的中国思维概括“朦胧意象思维”,认为“中国思维往往有些不确定的对象,如哲学概念的道、理、气、玄、禅、太极、元、亨、利、贞,都是很难描述清楚的……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烟雨蒙蒙,似有似无,中国人都喜欢沉浸在这种感觉中。相反,西方的文字、西方的油画,都以很清晰的方式传达信息”(43)。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就中国文论思维传统而言,在我们面对快速发展的现代文艺生活并自觉地建立中国现代文论体系时,就会感到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主体思维对客观现实及其映像的确认,不易对感知对象进行分析、整理、抽象、演绎”(4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这方面,西方文论话语方式恰恰对我们构成了有益的补充。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文论的特点在于,不是满足于提供现成的结论,而是重在正确地提问和论证过程的详细展开。《大希庇阿斯》篇是柏拉图为美下定义的最初尝试,文章的精彩之处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对“什么是美”这一中心问题所展开的有趣而深入的讨论,文章逐一考察了当时流行的关于美的定义和看法,却没有找到美的令人满意定义,最后仅以宣布“美是难的”而告结束。文章的功绩在于,第一次把“美本身”即美的本质和形形色色的美的现象加以区分,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正确提问,吸引着后代无数的美学家为此孜孜不倦地探索,从西方美学史上的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到当代中国的朱光潜、李泽厚、高尔泰等人莫不如此。
在前人理论思维的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对作为理论基本规则的形式逻辑进行了系统总结,确定了形式逻辑的基本内容,使之成为一门科学。他提出了形式逻辑的三大规律,即矛盾律、同一律和排中律,研究了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形式,研究了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强调思维形式的正确性,首创了三段论推理的格和规则的学说(45),亚里士多德把这些思维规则运用于他的文艺研究之中,这就是《诗学》。其实《诗学》篇幅不长,并非亚里士多德的完整著作,也未经作者认真润色,在多次传抄中文字也存在增删毁损。此书作为一部西方文论开创时期的经典之作,其中的话语方式比具体的思想观念更值得后人反复研习。
亚里士多德从摹仿艺术的区别性特征入手,研究了摹仿的媒介,划分了绘画与雕塑、音乐和诗歌等不同的艺术种类,接下来研究了摹仿的对象,区分了悲剧和喜剧摹仿的不同人物,然后讨论了摹仿的三种不同方式,作者又逐一探究了戏剧的起源、悲剧的定义、情节、诗与历史的不同,乃至人物性格、语言等,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古希腊戏剧及文艺理论的所有主要内容。它之所以能在西方文论史上享有崇高地位,除了得益于亚里士多德广博的学识外,与作者科学严谨的话语方式也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亚里士多德身为逻辑学家和科学家,秉承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等的科学传统,自觉采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冷静的科学分析来研究并解决文艺问题。事实上,建立理论体系的强烈和自觉意识始终是西方文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自觉寻找各种艺术门类的共同特征即摹仿,并把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看成是模仿的不同形式(46)。当传统的美的艺术在现代社会呈现衰败迹象时,现代西方文论又思考其历史起源和局限所在(47)。这和西方注重理论话语方式研究的传统紧密相关,造成了理论思维严格而明晰的特点。这种话语方式抽丝剥茧,不断展开,层层推进,成为西方文论的思维工具和牵领西方文论向前发展的火车头。
自鲁迅以来,国内学界往往将《文心雕龙》与《诗学》并称,这是中西文论史上的代表性著作,我们可以将二者的理论话语方式加以对照。其实《文心雕龙》尽管以“体大虑周”著称,但是依然带有中国文论所特有的意象思维的朦胧性,如其中的名篇《神思》,通篇并未给神思一个明确定义,从一开始把“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说成是“神思之谓也”,到“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再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都是直觉感悟式的话语方式,是一种形象性的富于感染力的文学描绘,不是理论逻辑的清晰说明。刘勰自己在结语处也承认:“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讲,《文心雕龙》远胜于《诗学》,但是从理性和清晰地把握文艺现象来讲,《诗学》则有过之。如果我们要想避免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的中的“以不甚了然对不甚了然”,试图以清晰的理论逻辑和强大的思辨能力,来展开与西方文论的对话并设法谋求我们在世界文论格局中的应有位置,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选择从《文心雕龙》话语方式到《诗学》话语方式的自觉转型。不管我们主观上是否愿意承认,事实上这一转型至少从王国维时代就已经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并仍将持续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就话语方式来讲,现在国内赞誉较多的王国维《人间词话》,追随和仿效者少,相反,现在国内批评较多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历来追随和仿效者甚众,后者援西释中的思路和精密论证的方式,被认为是开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方法即“阐发法”的先河。这意味着时下国内对于王国维的研究和评论,由于受到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和王国维的实际学术贡献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出入。
中西文论话语方式的确有着各自不同、特色鲜明的传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评估这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在承认文化差异现实存在的同时,又“不能把文化多样性视为一种一成不变的遗产……防止那些借文化差异之名把这些差异神圣化”(48),其实“抽象理论对中国并不是不可能的,只是不必要而已”(49),不必要的原因是古代农耕文明的中国不需要严格的精确化和逻辑化。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现代中国早已是今非昔比。西方文明向全球范围扩张的结果,从社会结构而言,中国从古代农业社会的农业文明,向着现代工业社会和商业文明急剧转型,在繁复的现代社会中,抽象的理论思辨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取代意象思维和类比思维,不仅必要,而且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文学样态而言,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础文类,即占据古代文学秩序中心的诗歌散文,已经被小说戏剧,后来是影视艺术所代替。中国古代与抒情短诗相适应的描述性、经验性、点悟性文论,无论是从研究对象还是话语方式来看,都已经不再适用。
从作为思维直接现实的汉语语言来讲,也发生了剧烈和深刻的变化,王力写道,“现代汉语曾经接受和正在接受西洋语言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包括语法在内,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50),在从古代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的过程中,汉语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古代汉语中占优势地位的单音节词已经让位于现代汉语里的双音节词,胡裕树指出,“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占绝大多数”(51),这种演变的结果是,“汉语里音节结构的单纯化促进了词汇双音化,词汇双音化又促使了词义和词性明确化,同时语法上词序的规则化也促使了词义和词性明确化”(52)。王力明确指出,“句法的严密化,和逻辑思维的发展是有密切联系的。所谓严密化,是指句子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53),“五四以后,汉语的句子结构,在严密性这一点上起了很大变化。……要求在语句的结构上严格地表现语言的逻辑性”(54)。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汉语所发生的这些显著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变化,或者说,已经构成了中国文论话语方式新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书面体的古代汉语被口语体的现代汉语所取代,以不确定性的单音节词为主和含意相对模糊的古代汉语,被以双音节词为主和更为严密精准的现代汉语所取代。这种变化,既是西方语言影响的结果,也是作为活着的汉语自身语言实践所做出的选择。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变化,古今汉语之间语法结构上的变化,意味着内在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这是包括文学在内的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结果。如果说古代汉语更适合于表达中国古代文论的弹性、模糊性、点悟性和诗意化特征,那么,现代汉语则无疑更适合于表达深受西方文论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论理论明晰化、逻辑化、精密化和确定性特征。如果我们承认实践优先的原则,承认实践总是先于理论上的先验设计而且优于理论上的先验设计,那么,合乎逻辑的结果是,我们就必须承认,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现代转型是中国文论研究实践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文论不可逆转的发展走向。
当代美国分析哲学家丹托(Arthur C.Danto)认为,“严格说来,分析哲学并不是一种哲学,而只是一套分析用于解决哲学问题的工具。可以推想,如果没有哲学问题,这些工具根本就不存在”(55),黑格尔有一句名言“手段比目的更长久”。从这个意义上讲,较之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在理论观念上产生的剧烈冲突,中国文论的话语方式作为解决现实中国文艺问题的思维工具,它所发生的深层次的变革,看起来波澜不惊,但是对于近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影响更为深远,更富革命性意义。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对于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关注,体现了中国文论研究领域问题意识的觉醒和对于文论思维工具的自觉,这对于中国文论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哲学史家郭齐勇认为,当今中国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面向世界的能力尚待加强……问题意识和理论深度还有待提升”(56),从哲学话语与文论话语在本质上的同一性而言,这也是当今中国文论亟待加强和提升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满腔义愤地抨击西方文论话语霸权,但是破中有立,以立为主,中国文论的发展还是应当在自我反思基础之上重在建设。努力把当今文艺生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纳入自己的学术视野,吸收异域文论话语中有益于自己的东西,与时俱进,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积极推动已经展开并且尚未完成的话语方式现代转型,才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文论之林的更为有效的途径。不怀偏见的人都不会无视这一点,那就是在近百年中国文论发展历程中,话语方式的自觉转型已经发挥了而且仍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杠杆作用。
注释;
①②③罗宗强、卢盛江:《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
④⑤⑥⑦⑧(27)(35)(36)(4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页,第365页,第365页,第366页,第367页,第14页,第14页,第29—30页,第13页。
⑨http://www.newworldencyclopedia.org/entry/Chinese_philosophy.
⑩(11)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页,第404页。
(12)See Daniel Kolak,Lovers of Wisdom: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with Integrated Readings,second edition,"introductio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2,p.xix.
(13)杨宪邦主编:《中国哲学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14)http://en.wikipedia.org/wiki/Western_Philosophy.
(15)See Daniel Kolak,Lovers of Wisdom: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with Integrated Readings,second edition,"introductio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2,p.xx.
(16)邬昆如:《西洋哲学史》,台湾“国立”编译馆1972年版,第150页。
(17)参阅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208页。
(18)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9页。
(19)(22)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第69页。
(20)(21)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页,第431页。宇文所安著《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3)G.W.F.Hegel,Aesthetics:lectures on Fine Art,Trans.by T.M.Knox,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p.41-43.
(24)参阅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25)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26)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28)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fucianism.
(29)(30)(31)方立天:《佛教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9页,第241页,第244页。
(32)(34)(40)(41)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397页,第397—398页,第396—397页,第397页。
(33)http://baike.baidu.com/view/441788.htm。
(37)(38)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0页,第539页。
(39)赵汀阳:《没有世界的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43)(44)王玉德:《文化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第147页。
(45)参阅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208页。
(46)(47)See Steven M.Cahn and Aaron Meskin,Aesthetics:A Comprehensive Anthology,Malden MA:Blackwell Publishing,2008.p.6.p.15.
(48)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71/127160m.pdf.
(49)陈汉生:《中国古代的语言和逻辑》,周云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50)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5页。
(51)(52)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第2页。
(53)(54)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5页,第479页。
(55)刘悦笛:《分析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56)郭齐勇:《中国哲学研究的七大缺失》,《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5日。
标签:哲学研究论文; 文化论文; 逻辑分析法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家论文; 沧浪诗话论文; 国学论文; 诗学论文; 冯友兰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