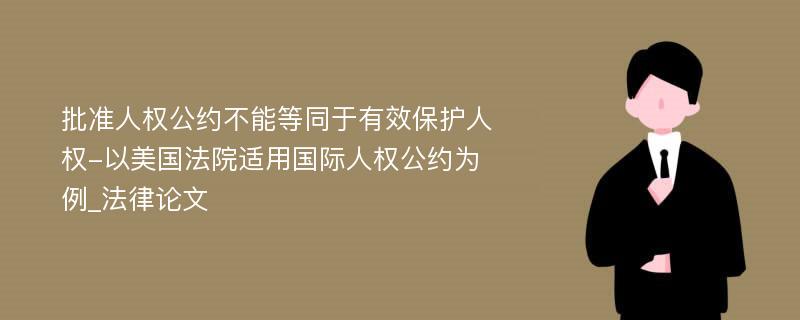
批准人权公约与切实保障人权不能等同——以美国法院对一项国际人权公约的适用为例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权论文,公约论文,例证论文,美国论文,切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于1992年9月8日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以下简称ICCPR)。ICCPR的缔约国有义务执行条约规定,在其管辖范围内通过立法确立ICCPR所承认的权利的效力。然而,美国在批准公约时提出了五项保留、五项理解和三项声明。保留的范围广泛,涉及死刑、酷刑、未成年罪犯的待遇等方面,①以至负责监督ICCPR的人权事务委员会失望地指出,这些保留、理解、声明加在一起,使“美国只接受已经成为美国法律的规定”。②本文以当事人援引ICCPR作为起诉依据的联邦案件为研究对象,意在审查美国法院是如何解释和适用本国缔结的人权条约的。
联邦法院在审理有关主张违反了ICCPR的案件时既审查程序问题,也审查实质问题。在许多案件中,对程序问题,如原告是否拥有起诉权、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当事人是否用尽了其他救济等因素的考虑可能排除对事实问题作进一步的审查。而所谓的实质问题,主要是指ICCPR对美国法院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的问题。尽管美国宪法规定,合众国缔结或将要缔结的条约与联邦宪法一样是美国的最高法律,③但是美国在批准ICCPR时声明,“公约第1条至第27条的规定是非自动执行的”,④这就要求参议院将公约的条款转化到国内法中,而至今尚没有全面转化公约的国内立法。因此,许多法院认为ICCPR对自己没有拘束力。此外,在当局的某些做法受到质疑时,法院尽量将它们解释得同公约的精神或规定相一致。
一、ICCPR案件中联邦法院对程序问题的审查
1.关于当事人是否拥有起诉权。一些法院认可当事人以违反ICCPR为由进行起诉。在Cabello v.Fernandez-Larios案⑤中,已故智利籍囚犯卡贝乐的家属指控前智利士兵犯有反人类罪,违反了ICCPR第6条,要求根据《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⑥获得赔偿。受案法院指出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依据《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能否使违反ICCPR行为的受害人获得救济。法院在说明这一问题时援引了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的结论,即根据《外国人侵权赔偿法案》法院可以为违反习惯国际法的受害者提供国内普通法上的救济。法院认为一条规则只有被“大部分”国家接受为“法律”时才构成习惯国际法,而ICCPR第6条就属于这样的规则,因此原告可以通过《外国人侵权赔偿法案》获得救济。法院补充道,由于ICCPR是非自动执行的条约,这就需要通过像《外国人侵权赔偿法案》这样的执行立法来使其在美国法院获得执行。法院最终认为卡贝乐的亲属有权根据《外国人侵权赔偿法案》起诉前智利士兵,提出其对卡贝乐法外执行死刑违反了ICCPR的主张。
不是所有的法院都支持当事人以违反ICCPR为由进行起诉。在Dickens V.Lewis案⑦中,原告是某机器制造厂的一名顾客,他请机器制造厂改造一些金属片,并告之改造后的金属片将用于组装机关枪。制造厂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美国酒精、烟草和火器管理局(ATF)。该局和制造厂一起没收了原告的金属片及武器组装说明书。于是原告起诉制造厂及管理局的代表侵犯了他依据ICCPR享有的权利,要求返还其财产。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均认为个人缺乏依据ICCPR提起诉讼的权利。类似的案件还有Thunderhorse v.Pierce案,⑧本案法院裁定声称监狱管理人员侵犯其根据ICCPR享有的自由进行宗教练习权的美国籍囚犯不具备依据该条约进行起诉的权利。法院认为ICCPR虽规定了政府的义务,但并没有授予个人提起诉讼的起诉权。
2.关于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在另一些案件中,法院讨论了自己是否对声称违反了ICCPR的案件的实质问题具有管辖权。
在Leinenbach v.Williamson案⑨中,原告质疑对他作出的多项涉毒指控的定罪和判决,认为对他的判决违反了最高法院在Apprendi v.New Jersey案⑩及Blakely v.Washington案(11)中确立的原则,同时也违反了ICCPR。法院注意到原告之前已经根据美国法相关条款提起过一次不成功的申诉,由于他不具备再次提起申诉的条件,所以法院以缺乏对实质问题的管辖权为由驳回了原告的第二次起诉。类似的案件还有Criffin v.Holt案,(12)本案的法院明确指出原告不能仅仅因为§2255对其连续起诉作出了程序上的限制就认为违反了条约。在Benitze v.FCI Phenix案(13)中,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也以同样的理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在Miller v.U.S.案(14)中,法院认为联邦索赔法院只对起诉美国要求金钱损害赔偿,或者基于合同、洗钱规定、美国宪法的某些条款,包括第五修正案中的征收条款提起的索赔享有管辖权。而原告则认为因为美国是ICCPR的缔约国,违反ICCPR即是违反了合同,对此法院应有管辖权。法院则澄清这种管辖权不包括美国行使主权权力的政府行为,而只涵盖政府以类似于私人主体的身份所进行的交易;另一方面,法院认为自己对合同索赔的管辖权仅指那些在事实上明示或默示的合同,不包括法律上默示的合同,后者产生于履行法律义务的承诺。因此法院以自己不具有对法律默示的合同的管辖权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3.关于当事人是否用尽了行政救济。法院在审理声称侵犯了ICCPR保护的权利,要求获得人身保护令的案件时,要审查申请人在提起申诉之前是否用尽了行政救济措施。
在Beharry v.Ashcroft案(15)中,法院就以申请人未能用尽行政救济措施为由拒绝了其人身保护令的请求。本案原告是特立尼达岛人,犯有二级抢劫罪,为避免被驱除出境,他试图寻求人身保护的救济。原告因抢劫罪被判处2.25至4.5年的监禁,根据实施抢劫时的《移民与国籍法案》(16)原告不属于加重犯(获5年以上刑期的犯人)的范围;但是在其认罪时,由于对加重犯的规定作了调整(获1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人),原告被归入了加重犯的范围。地区法院认为如果不经充分审理就把原告驱逐出境从而让他与女儿分离,将违反ICCPR。地区法院承认ICCPR不是自动执行的,但是它认为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已经声明美国法律与ICCPR在总体上是一致的,而且地区法院和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都有过适用非自动执行的条约条款的例子,因此,地区法院决定授予原告人身保护令并命令移民与归化局举行听证以决定原告是否可以留在美国。然而,上诉法院推翻了该决定,并要求发回重审,理由是原告在申请人身保护令之前未能用尽行政救济,因此法院对此申请缺乏管辖权。上诉法院认为申请人在申请人身保护令之前应当就自行豁免被驱逐出境的资格向移民法院和移民上诉委员会分别提出主张。
另一个类似的案件是AbimbolaAs v.hcroft案。(17)本案原告是尼日利亚人,在美国取得了永久居住的资格,因犯有银行诈骗罪,接到移民与归化局的搬迁令。移民法官和移民上诉委员会均确认了这一命令。原告以该命令违反了自己根据ICCPR享有的权利为由向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地区法院指出由于原告没有向移民法官申请取消该命令,因此没有用尽行政救济,致使法院不能审查该命令。原告又就此案向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了上诉,结果上诉法院确认了地区法院的裁定。
二、ICCPR案件中联邦法院对实质问题的审查
1.关于ICCPR对美国法院的约束效力。许多案件的法院均持有或承认ICCPR对美国法院没有拘束力这一主张。笔者以最高法院审理的Sosa v.Alvarez-Machain案为例说明美国法院是如何论证ICCPR对美国法院没有拘束力这一命题的。
在Sosa V.Alvarez-Machain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尽管ICCPR作为国际法对美国有拘束力,但是美国批准该公约时明确表示它属于非自动执行的条约,因此没有为联邦法院创设执行公约的义务。本案原告为墨西哥公民,因谋杀罪被用武力绑架、运送到美国接受起诉,后又被宣告无罪。于是原告根据《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等提起了针对美国、多位美国官员、以及多位墨西哥国民的诉讼,称在美国缉毒机构的授意下多名墨西哥国民将原告以武力绑架并强制运送到美国接受起诉,这么做违反了包括ICCPR在内的国际法。美国政府辩称:《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规定的是“地区法院对外国人提起的违反国际法或美国缔结的条约的民事侵权诉讼具有初始管辖权”,这一规定不能为本案原告提供救济,因为本法案只规定了联邦法院有管辖权,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并没有创设任何诉讼权利。最高法院承认联邦法院根据《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享有的管辖权,但是指出在法案于1789年生效时,联邦法院只被授权对国际法所规定的,并为普通法所承认的非常有限的案件进行管辖。原告主张法案为违反包括ICCPR在内的国际法的侵权案件创设了诉由。但最高法院认为原告对法案的解读有误,认为法案只涉及联邦法院的管辖权,没有创设任何新的诉由。不过过去法院的确为谨慎地利用法案对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提出索赔打开过大门,前提是被违反的国际法规范属于习惯国际法,而且要求规范的用语明确具体、足以支持联邦救济,类似于法案颁布时可受理的违反联邦普通法的情形。最高法院列举了三种符合这一标准的诉由,包括冒犯使节、侵犯安全通行权、个人盗版诉讼。法院指出,墨西哥国民只对原告进行了不到一天的短暂拘留,随后他即被运送到美国交给美国官员监控,并立刻进行了讯问,这些做法没有违反任何规定明确、足够得到联邦救济的习惯国际法规范。法院裁定ICCPR不包含任何规定明确的国际法规范因此不能被用来创设诉由,认为ICCPR虽然具有道德权威,但几乎没有实际效用,因为它是非自动执行的,没有创设可以在美国法院获得执行的义务。
2.关于ICCPR与国内法令的位阶关系。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审理的维尼西蒙诉移民与归化局案(18)中,收到搬迁命令的一位外国人申请人身保护令救济,但遭到了地区法院的拒绝。上诉法院认为,首先,由于该外国人犯有销售海洛因的罪行,无论他是否是美国常住居民,均不具备免除被驱逐的资格。其次,上诉法院认为地区法院裁定移民与归化局第212(h)条规定(19)优于ICCPR是正确的,因为当后来制定的法令同之前的条约不一致时,法令将使条约变得无效。上诉法院指出,国会于1996年修改了第212(h)条,如同本案申请人这样的加重犯不再具备申请取消搬迁命令的资格。于是上诉法院得出结论,1996年对第212(h)条的修正案使1992年对美国生效的ICCPR的相关规定变得无效。申请人不得依据ICCPR要求进行关于他不应该被驱逐出境的审理。在El Zoul诉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案(20)中,法院同样指出,尽管ICCPR与《移民与国籍法案》存在冲突,但是国会后制定的法案优于之前的条约义务。持相同观点的还有Castillo-Avavos诉Gonzales案(21)的法院。
三、联邦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ICCPR的解释
1.关于保护土著文化。美国法院认为ICCPR没有为美国施加保护土著文化的专门义务。在Inupiat Community of the Arctic Slope v.U.S.案(22)中,一个土著社区起诉要求制止对阿拉斯加北坡外土地的开发。地区法院作出了有利于美国政府的简易判决;土著社区提起了上诉,认为ICCPR为美国政府施加了保护土著文化的义务。上诉法院认为即使ICCPR适用于本案,由于原告不能举出该公约的哪个具体条款给美国政府施加的义务重于国内联邦法律为政府施加的义务,有鉴于政府已经履行了国内法上的义务,所以确认地区法院的决定,驳回了土著社区基于ICCPR的主张。
2.关于限制赴古巴旅行。在Freedom to Travel Campaign v.Newcomb案(23)中,法院认为限制赴古巴旅行的作法同ICCPR的规定并不矛盾。本案的案情是这样的:某组织拟组织一次赴古巴的教育之旅,但是受到了限制,于是该组织及希望赴古旅行的人们对《古巴资产管制条例》限制赴古旅行的规定提出了质疑。地区法院作出了支持条例、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原告提起了上诉。上诉法院首先指出《古巴资产管制条例》(24)是在肯尼迪总统于1962年颁布古巴贸易禁令(该禁令要求美国人未获许可不得同古巴进行任何经济交易)后不久颁布的,目前该条例通过禁止同古巴公民进行大部分经济交易来限制赴古巴旅行。上诉法院补充道,个别人可能有机会获得部分免除这些限制的一般许可;除此之外,所有人都必须从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获得专门许可,条件是他能够证明为了进行法律明确规定的教育活动迫切需要到古巴去。上诉法院认为该组织不具备获得一般许可的资格,也没有寻求专门许可。该组织辩称本案所涉条例与ICCPR第12条第3款相冲突,公约的条款规定只有在“保护国家安全所必需”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旅行限制。该组织认为即便古巴并没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条例仍然这么规定,它只不过是为了维持1977年关于禁止同古巴进行经济往来的祖父条款的禁令。上诉法院驳回了该组织的辩护理由,认为公约第12条第3款规定的国家安全条款仅适用于第12条的第一、第二节的情形。上诉法院进一步解释:第12条第一节称一国范围内的所有人都应享有在该国范围内迁移的权利,第二节规定人人享有离开任何国家,包括自己的祖国的自由。上诉法院指出,受到质疑的条例并没有提到在美国范围内旅行,因此第一节同本案无关,而第二节也只保证有离开美国的权利;它没有提到去某一特定的目的地的权利。因此,上诉法院认为受到质疑的条例并没有违反ICCPR,公约的第12条第3款同祖父条款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3.关于修建大屠杀纪念馆。魏斯诉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一案(25)讨论了大屠杀纪念馆的修建活动是否同ICCPR相一致。本案原告是在波兰Belzec集中营被杀害的犹太人的后代,他们要求法院向一家犹太组织颁发初步禁令,因为后者正在资助在集中营遗址上修建沟渠的活动。这个沟渠实际上是一个连接集中营地中心和纪念墙的走道。犹太人后代认为修建沟渠需要用大型机械挖掘,这违反了犹太法律,也将打搅和亵渎受害者的遗体。他们在纽约的一个州法院根据《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提起诉讼,声称存在违反国际法的侵权行为。但是涉案的犹太组织申请将案件移到联邦地区法院审理。地区法院首先指出,《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授予了地区法院对外国人提起的违反国际法或美国缔结的条约的民事侵权案件的初始管辖权,而这里所说的国际法仅指“习惯国际法”。本案原告声称侵权行为违反了ICCPR。地区法院认为原告所援引的ICCPR第17条(反对任意或非法干涉个人隐私或家庭)、第23条(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群体单位)和第27条(民族或宗教上的少数者享有自己的文化或宗教的权利)均不足以构成明确的习惯国际法规则。而从ICCPR目前的规定来看,它没有发现任何禁止现代文明国家挖掘沟渠的法律义务。因此,法院驳回了原告基于《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提出的主张,并将其根据州法律提出的故意和疏忽大意造成情感伤害的主张发回州法院重审。
4.关于在两个不同国家分别起诉同一犯罪行为。U.S.v.Duarte-Acero案(26)的被告已经就蓄意谋杀罪在本国接受了起诉,因此,原告主张ICCPR所规定的双重危害原则排除对他在美国地区法院再行起诉。上诉法院认为ICCPR第14条第7款的规定(27)只适用于“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而且只有当被告人根据同样的法律和刑事程序被再次起诉时才是不允许的,这种情况只有第一次起诉和第二次起诉发生在同一国家时才有可能发生。因此,上诉法院说ICCPR的一个缔约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审判某人,即便此人已经因为同样的行为被另一缔约国根据他自己的刑法典起诉过。上诉法院举出人权事务委员会对一份意大利公民的来文决定来证明自己的结论。在来文中,该意大利公民主张自己已因违法行为在瑞士受到过惩罚,意大利再次惩罚自己违反了ICCPR第14条第7款。而人权事务委员会则认可了意大利的做法,认为第14条第7款“禁止二次危险的原则只适用于某一缔约国范围内审理的案件”。
5.关于执行死刑。美国有法院认为ICCPR并不禁止政府处决已被宣告有罪的杀人犯。Sosa v.Dretke案(28)的申请人在得克萨斯州法院被宣告犯有谋杀罪,并被判处死刑。他向联邦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申请,声称设定多个执行日期、自己长时间停留在死亡名单上,以及政府在联邦地区法院不妨碍第一次联邦人身保护令申请的情况下驳回其请求后又设定执行日期的做法,违反了他根据宪法第八修正案、第十四修正案和ICCPR享有的权利。法院在驳回申请人关于准予上诉的申请后,指出没有一个美国法院曾认为ICCPR禁止对已宣告犯有最高罪行的谋杀犯执行死刑。另外,法院认为造成设定多个执行日期以及申请人长时间停留在死亡名单上的唯一障碍是申请人反复在州和联邦法院提起诉讼间接挑战对他的定罪和判刑的行为。
四、对联邦法院适用ICCPR的小结与思考
美国联邦法院解释和适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实践反映了美国司法系统对国际人权条约的认知状况和态度;从中也可以概括出ICCPR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就法院的态度而言,它们通常以当事人不是适格的起诉主体、法院不具备相应的管辖权、当事人没有用尽其它国内救济、后法优于先法等理由,尽量减少ICCPR的适用机会。难怪人权事务委员会感叹美国联邦、州、地方的各级司法人员并“没有充分觉悟到盟约规定的该缔约国的义务”。(29)就公约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而言,ICCPR在美国属于非自动执行的条约,因此需要通过适当的国会立法转化为国内法才可以适用,但是尚无全面转化公约的适当的国内立法,于是法院普遍认为该公约对美国法院没有直接的拘束力。目前《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赋予了联邦地区法院对违反习惯国际法的民事侵权案件的管辖权,当ICCPR的规定被证明具有习惯国际法的地位时,可以通过该法案予以适用,然而实践中难以找到成功的例子。法院一般将国内法的规定解释得同公约的精神或规定相一致。如果制定在后的法令同公约的内容存在明显冲突时,则后制定的法令有优于公约的地位。
联邦法院在上述案例中的裁判理由是否合法、合理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有关保护土著文化的案例中,上诉法院认为国家在国内法上的义务优先于其在人权条约下承担的义务,此外认为ICCPR没有明确要求国家保护土著人权利或文化。这种理解受到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质疑,并引起了后者的关切。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美国通过所谓的信托制度管理印第安和阿拉斯加土著部落的土地及其产权,实际上限制了土著群体的决策权,进而剥夺了后者依据公约享有的权利。委员会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采取措施,按照公约第1条和第27条保障所有土著人民的权利,使他们在影响其自然环境、生计及文化的决策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力。(30)另外,美国法院以后制定的国内法优于先缔结的ICCPR为由排除公约适用的案例不在少数。这么做显然与“约定必须信守”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存在冲突;这又让人联想到美国在批准ICCPR时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号召——“公约的缔约国应该尽一切可能避免对公约所承认和保护的权利予以限制,哪怕是公约所允许的限制。”(31)美国法院用后制定的国内法来废止公约认可的权利,难道不是在对公约进行限制,而且是做出公约所不允许的限制吗?再来看法院对执行死刑案件的解释。尽管美国在批准公约时提出保留对除孕妇之外的任何人,包括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依法执行死刑的权利,但是这一保留常常遭到攻击,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它与公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实践中每年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数目有增无减、宣判后的罪犯在死亡名单上长期煎熬等待处决,以及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等情况更是反复受到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诟病,但是美国当局并没有做出回应。
美国法院的事例表明,批准公约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个人是否可以依据公约主张权利,法院是否援引公约裁判案件,这不过是实现权利的若干途径;而距人人真正充分享有公约保障的人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美国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保留、理解和声明的具体内容可访问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ratification/4-1.htm。
②U.N.Doc.A/50/40,para.279.
③参见《美国宪法》第6条。
④同前注①。
⑤Estate of Cabello v.Fernandez-Larios,157 F.Supp.2d 1345 (S.D.Fla.2001).
⑥Alien Tort Claim Act,28 U.S.C.A.§ 1350 (ATCA).
⑦Dickens v.Lewis,750 F.2d 1251 (5th Cir.1984).
⑧Thunderhorse v.Pierce,2006 WL 359723 (E.D.Tex.2006).
⑨Leinenbach v.Williamson,152Fed.Appx.197 (3d Cir.2005).
⑩Apprendi v.New Jersey,530 U.S.466,120 S.Ct.2348,147 L.Ed.2d 435 (2000).
(11)Blakely v.Washington,542 U.S.296,124 S.Ct.2531,159 L.Ed.2d 403,6 A.L.R.Fed.2d 619 (2004).
(12)Criffin v.Holt,2005 WL 2230029 (M.D.Pa.2005).
(13)Benitez v.FCI Phoenix,27 Fed.Appx.917 (9th Cir.2001).
(14)Miller v.U.S.,67 Fed.Cl.1995 (2005).
(15)Beharry v.Ashcroft,329 F.3d 51 (2d Cir.2003).
(16)§101(a)(43)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INA).
(17)Abimbola v.Ashcroft,2002 WL 2003186 (E.D.N.Y.2002).
(18)Verissimo v,I.N.S.,71 Fed.Appx.859 (lst Cir.2003),cert.denied,540 U.S.1080,124 S.Ct.935,157 L.Ed.2d 754(2003).
(19)§212(h) of the INA,8U.S.C.A.§1182(h).
(20)El Zoul v.Bureau of Citizenship and hnmigrafian Services,2006 WL 526091 (2d Cir.2006).
(21)Castillo-Avalos v.Gonzales,136 Fed.Appx.629 (5th Cir.2005).
(22)Innpiat Community of the Arctic Slopev.U.S.,746F.2d570 (9th Cir.1984).
(23)Freedom to Travel Campaign v.Newcomb,82 F.3d 1431 (9th Cir.1996).
(24)Cuban Asset Control Regulations,31 C.F.R.§§ 515.101 et seq.
(25)Weiss v.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335 F.Supp.2d 469 (S.D.N.Y.2004).
(26)U.S.v.Duarte-Acero,296 F.3d 1277(11th Cir.2002).
(27)该款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
(28)Sosa v.Dretke,133 Fed.Appx.114(5th Cir.2005),cert.denied,126 S.Ct.619,163 L.Ed.2d 508(U.S.2005).
(29)U.N.Doc.A/50/40,Vol.1,para.280.
(30)U.N.Doc.A/61/40.Vol.1,para.84(37).
(31)关于美国在批准ICCPR时所作的第二项声明,可访问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ratification/4-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