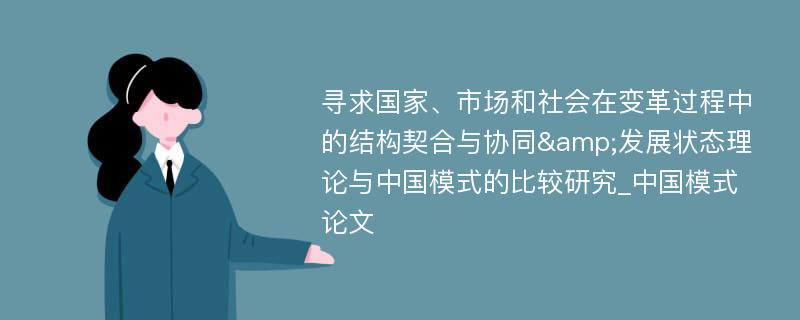
在变动中寻求国家、市场与社会的结构性契合与协同——对发展型国家理论及中国模式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结构性论文,中国论文,变动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14)03-0121-11 发展型国家是发展研究领域的一种经典模式。对发展型国家的理解,必须突破“国家”本身,对国家、市场和社会结构与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察,寻找它们之间所构成的结构性契合与协同,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发展动力机制。这种结构性契合与协同,也必须根据不断变动的国内国际局势进行调整和适应,其本身就是一个动态机制。各国国内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全球由冷战时代向全球化时代的变迁,都使得国家本身及发展模式必须进行自我调整。发展型国家模式本身所寓意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则使得它有机会在全球化时代重塑自身,构建新的结构性契合与协同。 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东亚资本主义新兴经济体的“前置性”发展经验的影响。它们在地缘上与中国的邻近性,文化上同属中华文化圈的相似性,以及初始经济发展阶段的滞后性,都使得它们的发展模式很自然地成为中国比照和模仿的对象,成为邓小平等改革政策制定者时常参考的样本。与政策制定时的比较和参照相伴生的另外一个现象,是在学术研究中,发展型国家理论也成为研究中国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式。发展型国家理论,一方面成为理论研究的参照系,用于与中国发展经验的比对分析;另一方面也成为一种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成为学者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 中国的发展经验并非完全是单向度的接受发展型国家模式的理论输入和政策影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所衍生出的“中国经验”,也提供了一个与发展型国家模式进行比照的新的生动案例,并为后发国家在全球化时期探索发展模式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参考。尤其在中国的发展模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暴露出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时候,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更应思考,中国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了发展型国家理论?中国经验在何种程度上验证了或者挑战了发展型国家理论?在全球化时代,发展型国家理论对于中国以及广大后发国家是否依然具有指导价值?发展型国家理论本身可否寻找到新的理论突破点?就这些问题,本文依据新的理论文献,尝试对发展型国家的经验模式和理论流变及其与中国模式的关系,进行比较和梳理。 一、二战后的“东亚奇迹”与发展型国家模式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东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为近代东亚唯一的工业化国家,日本战败并且经济近乎崩溃。中国虽然成为战胜国,但原本就薄弱的经济遭到重创,并很快陷入内战,导致大陆和台湾的分治。朝鲜半岛分裂为两个政权,并在随后爆发了朝鲜战争。而在全球冷战局势下,中国和朝鲜的分裂局面持续。当时,并无任何迹象表明,东亚能够很快地从战争和贫困中恢复过来。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日本连同“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Vogel,1979)却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并成为在全球极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这被称为“东亚奇迹”(World Bank,1993)。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已经发展成为“第二大最具生产力的开放经济体”(Johnson,1982),傅高义(Ezra Vogel)甚至提出“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的说法(Vogel,1979)。同时,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控制贫富差距和减少绝对贫困的目标(World Bank,1993),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拉丁美洲是不常见的。 在这些东亚新兴经济体中,除了香港之外,高度的国家规划、调节和干预都在它们的经济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Harvey,2005)。权赫周(Kwon Huck-Ju)指出,国家既是经济社会转型的客体,也是主体(Kwon,2009)。东亚威权国家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转型,也实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整体转型;他们所实施的国家干预不局限于经济政策,而是包括了“意识形态动员、全方位的政治控制和社会调控”(White & Wade,1988)。此外,东亚新兴经济体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文化特性:儒家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政治等级体系以及民族主义(White & Wade,1988)。因此,学者们试图寻找“东亚模式”,并探索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复制这种模式的可能性。 发展型国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理论正是发展研究中用于解释东亚奇迹的一个主流理论。它首先在对日本发展模式的研究中提炼出来,后来广泛应用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中。 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被公认为是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奠基人(Leftwich,1995)。他通过深入研究1925~1975年日本通产省的工业政策决策和执行机制,提出日本的经济奇迹是日本“发展型国家”的成果。日本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征包括:(1)一个小规模的、精英化的官僚体制,由日本最好的管理人才构成;(2)鼓励创新和效率的政治体制;(3)持续地追求政府对经济的理性化干预;(4)以通产省为代表的领导型中央机关(pilot central agency),能够监管一系列关键性的经济部门并进行产业协调(Johnson,1982、1987)。约翰逊提出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的目的,是在美国监管型模式和苏联指令型模式之外,提供第三种国家发展模式。他发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威权政体在二战后,充分利用了冷战及其所促发的战争工业作为自己的发展契机,并且掩护了自己的快速发展而长期不为外界所关注。在国内,政府与大财阀、工会和其他主要利益团体建立了具有统合主义色彩的互利关系,从而促成国家团结以实现发展目标。这一能力恰巧是战争动员或者革命运动所遗留的制度传统,但是威权主义与发展型国家并没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Johnson,1999)。 发展型国家理论原本是对战后日本发展模式的经验性归纳,但是在约翰逊之后的后续研究中,它逐渐被抽象化为一种描述和解释后发国家赶超式工业化发展模式的一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并通过对东亚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特征的描述和概括来定义这一理想类型。此类研究对发展型国家模式的特征都达成了如下的共识:(1)由于冷战局势和国内贫困落后,国家内忧外患;(2)由于殖民主义统治(主要是日本对朝鲜半岛和台湾的殖民统治)和国内革命运动或改革,地主等保守阶级的势力被极大削弱,奠定了比较合理的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关系和收入分配机制,劳动者的生产能力、组织纪律性较强且成本低廉;(3)政府以实现国家经济发展为最主要的合法性来源,并且就建设民族国家这一共同目标与国内各界达成广泛共识;(4)有精英化的国家官僚机构、对教育的持续投入和集体主义观念等儒家传统价值观;(5)实施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并进行持续的产业升级和多样化发展;(6)出于冷战的战略考虑,美国对这些国家提供军事保护和经济支援,或者至少向其开放美国市场作为出口渠道(Castells,1992;Vogel,1991)。 毫无疑问,发展型国家模式是国家间竞争背景下后发国家赶超式发展的一个经典模式,在二战后的东亚地区有集中的呈现。然而,类似的国家主导的“赶超式发展”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先例,而并非东亚所独有。比如禹贞恩(Meredith Woo-Cumings)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可以追溯到近代欧洲的重商主义,尤其是德国,其主要的国家干预手段包括,依靠人为控制的利率以操控金融业,通过国家指令的银行贷款以支持工业发展等(Meredith,1999)。而怀特和韦德则借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理论,提出发展型国家是一个给定国家“通过农业、工业和商业获得繁荣、文明和权力”的“政治经济学”(White & Wade,1988)。而肖恩·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则认为,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同样体现在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和亨利·克莱(Henry Clay)于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后为美国所设计的“美国体系”(the American System)中。这一体系使得美国政府有能力通过国家银行和信用体系支持产业发展协调及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高关税保护本国企业免受西欧强国的产品冲击。因此,当时的美国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Breslin,2009)。 二、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关于发展型国家模式的比较研究 国家政策的实施,必然与国内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关系密切相关。而国家政策作为一种配置生产性要素的手段,也常常与市场机制并行。因此,国家—社会关系与国家—市场关系,成为发展型国家研究不容忽视的议题。 为什么发展型国家模式在东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同时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东亚相距不远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并未实现同等水平的发展?对亚洲不同区域经济体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更清楚地说明了东亚发展型国家中国家—社会关系的特点。比如维维克·基伯(Vivek Chibber)对韩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提出,印度资产阶级对印度政府的发展政策有意识的抵制,是印度未能实现同样发展成效的关键原因。印度政府实施进口替代而非出口导向的策略,这使得印度资产阶级缺乏大规模扩大生产用于出口的动力,而且限制进口外国产品的政策,降低了印度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因而招致他们的普遍反对。印度政府因此未能与印度资产阶级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发展联盟,更无法对其投资行为进行有效引导以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Chibber,2003)。 对于发展型国家深深根植于本国社会利益关系结构,并与各主要社会群体广泛建立国家—社会利益同盟的能力,佩普尔(T.J.Pempel)提出“发展型政体”(the development regime)的概念。他把“政体”(regime)定义为“国家体制与社会经济秩序中的特定群体的持续融合,以及在公共政策导向中的特定偏好”。他进一步指出,尽管发展型政体保持较高的开放性,因而个人可以凭借能力进入国家体制,社会利益群体也可以将利益诉求通过国家体制进行表达,但是对于任何特殊主义和政治化的利益诉求,发展型政体都持明确的压制态度,因而保证了国家的自主性(Pempel,1999)。 如同发展型政体概念一样,琳达·韦斯(Linda Weiss)和约翰·M.霍布森(John M.Hobson)提出的“被治理的相互依赖”(governed interdependence),以及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提出的“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同样是对发展型国家这一特征的阐释,尤其是国家自主性转化为实施发展的国家能力的机制。他们特别强调,国内社会群体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合作不是自发形成的,因此,国家需要提出具有创新性的发展愿景,并且通过国家赞助的社会中间组织和政策咨询机制以及激励措施,积极引导社会群体对国家发展计划的参与及合作(Weiss,1994;Weiss & Hobson,1995)。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则是比较研究的另外一个着眼点。根据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程度,可以归纳出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两种制度传统,而发展型国家无疑属于后者。然而发展型国家又绝非国家对市场的完全替代,并且国家干预也要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这在东亚发展型国家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中显现出不同的发展成效。比如有学者认为,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很多政策选择上与东亚发展型国家有很高的相似性,比如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以及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高水平的国家投入,以及社会平等。相比之下,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用国家指令完全取代了市场机制,因此,面对国家指令的失误,就缺乏市场机制作为一种与国家指令互补的机制进行纠错。东亚发展型国家则将国家干预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成为经济发展中相互促进的双引擎(Antic,2003)。 三、后冷战时代全球化对发展型国家模式的挑战及其应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冷战格局结束,全球化时代来临,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也遭遇到普遍的困难、质疑乃至否定,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发展型国家弊病的集中爆发。一些研究者认为,发展型国家模式已经终结,监管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已经取代了发展型国家,成为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主导治国术(Kanishka,2005)。 仔细分析这些重大变化和危机的原因,有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 在外因方面,理查德·斯塔布斯(Richard Stubbs)认为,发展型国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冷战的产物。在后冷战时代,由于共产主义的外部威胁大大减小,东亚新兴经济体在国内基于国家生存的急迫需要而获得的国家自主性和动员能力都大大下降,而美国也要求它们进一步实施政治民主化改革;美国基于冷战战略所实施的经济援助,也逐渐被更为实用主义的跨国公司生产投资网络所取代,后者更倾向于在具备经济比较优势而非政治和军事战略意义的地区进行投资,并且投资流向变动更为迅速(Stubbs,2009)。 在内因方面,傅高义认为,东亚新兴经济体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使得过去出口导向型的大规模生产无法维持;而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多元化,也使得过去基于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这一共识的国家—社会发展共同体无力维持,民众在政治表达、社会福利等方面长期被压抑的需求越发强烈(Vogel,1979)。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同样指出,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嵌入式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工业家的联盟,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具有相当的排斥性。随着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劳工阶层对政治参与的要求越来越高涨,这种政—商联盟越来越难以维持,因而需要建立利益基础更为广泛和具有包容性的国家—社会联盟(Evans,1995)。 其实更为合理的分析方式,是将上述这些危机的内外因放在结构性的视角中进行综合审视。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以及Cho Hee-Yeon基于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发展经验的研究和对发展型国家理论的批判,提出进行“资本积累的政治社会学”,主张把国家—社会关系与国家—市场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国家干预是在社会结构和制度化的调节方式中发挥作用的,有效的发展模式并非国家的单一作用,而是市场机制、国家干预和社会结构三者契合与协同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化的动力机制的结果(Jessop & Cho,2001)。 而对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型国家所遭遇的危机,这两位作者认为,其根源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变了国内的社会阶级关系,旧有的结构性契合被打破。危机的最突出表现是社会抗争和阶级斗争的全面加剧,这些斗争指向社会不平等、大企业垄断、腐败、环境恶化、独裁政府、限制公民自由等各种问题,最终都发展为直接指向国家本身的政治斗争。国家逐渐成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的障碍,经济危机也使威权政府的合法性遭到质疑(Jessop & Cho,2001)。这些危机最终都导致国家本身的转型和资本积累体制的调整,而危机的最终解决,则依赖于国家—资本积累体制—社会阶级关系这三者之间在动态调整中找到新的结构性契合点。 发展型国家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是一套实用主义的政策适应机制,而非对任何特定政策范式的僵化的追求。因此,发展型国家并没有为自己设置制度性约束,而是具有高度的灵活性。面对经济自由化的挑战,发展型国家并非简单的走向解体,而是有机会、有能力进行适应性调整和转型,比如,驾驭跨国公司的投资以服务于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特定产业发展的目标(Kwon,2009;Wong,2004;Hayashi,2010)。有学者更是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并非发展型国家模式造成的,而恰恰是经济自由化削弱了发展型国家的经济规管能力,才导致这些国家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大打击(Weiss,2002)。 四、发展型国家模式与中国经验 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成为发展研究领域中继东亚新兴经济体之后的又一个热点研究领域。由于中国与东亚新兴经济体在地缘上的临近性和传统文化上的相似性,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以强大国家能力为重要特征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路径依赖,以及改革初期中国对日本、新加坡等发展型国家经验有意识的学习,都使得发展型国家模式很自然地成为研究中国改革经验的一个重要理论参照。 如果从经验层面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策略,确实在很多方面都与东亚发展型国家有高度的相似性,比如威权政治与经济自由化并行,国家对金融业的管控,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政策,以及居民的高储蓄率(Baek,2005)。 除了上述共性之外,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另一个特征是政府的企业化取向,也就是政府对盈利性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介入。国家通过政绩考核机制和越来越严格的预算约束机制,将官员的政治经济利益与市场化改革紧紧联系起来,使得经济增长成为一项持续的工程。而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家确保了国企掌握战略性的产业和资源,从而保证了国家对经济体系的有效掌控,并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So,2009;Shevchenko,2004;Pearson,2005;Lanteigne,2008)。国家通过企业家式的市场参与和国企运作所获得的收益,既可能用于在国家层面和地方社区提供公共产品,也可能服务于政府部门和官员自身的私人物质利益。此外,中国政府制定的很多政策,其最初都来源于灵活的地方试点,而非中央政府事先有意识的政策设计(So,2009)。这一点在改革初期的农村经济改革以及各地不同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涌现中表现最为明显。地方发展主义与地区间竞争,而非民族主义,是中国最主要的发展动力。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在财政、税收、金融和人事制度上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中央的宏观经济监管能力,有效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及其他扭曲市场机制的地方政府行为,改善了法律体系、技术质量监管体系。这些措施主要包括:(1)中央行政和财政能力的强化;(2)中央在基础设施等大型建设项目以及教育、研发方面的投资;(3)在意识形态话语和政策上开始关注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4)依靠巨额的外汇储备和巨大的经济规模对经济全球化实施趋利避害的政策选择,如引导跨国公司进行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投资(So,2009;Yang,2004a、b)。 然而,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很多制度设计的缺陷和问题,也都可以看作是对发展型国家模式的偏离,其主要原因包括政党—国家一体化的政治体制,中国巨大的幅员和区域差异性,以及地方分权化和地方主义。 肖恩·布雷斯林(Shaun G.Breslin)指出,中国行政、财政分权化以及区域发展水平和政策环境的显著差异,地方政府绕开中央政府吸纳外资的能力,以及地区间的竞争,都使得中央的发展政策在地方执行的过程中被扭曲乃至被抵制,因此全国性的经济协调难以有效实施(Breslin,1996)。中国的金融体制也受到批评,因为国有银行并未给极具活力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充足的融资保证,而是主要用来维持国有企业的运营,这也导致地下钱庄等为非国有部门服务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在某些地区的盛行(Tsai,2004)。另外,党政机关在历史上一直对非公有经济部门从业者持不信任态度,而且党政官员在教育等个人背景方面与私营企业主等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因此两者并未形成真正的信任和互惠的关系。与日本、韩国等发展型国家中国家与私营部门依托商会等高度组织化的制度平台进行协商沟通不同,中国的政商关系更多的是依赖个人化的、地方化的侍从主义关系(Howell,2006)。社会中间组织的低度发育,也意味着政府机关必须维持较大的规模以实施社会和经济治理,因而不同于日韩的小政府模式。另外,中国对外资一直持欢迎态度,而日韩曾经长期限制外资的进入。中国的劳资关系一直处于低度制度化状态,没有形成日本企业中雇员与企业长期稳定的共生关系和利益代表机制。而中国在转型期社会信任的普遍缺失,更是与日本有显著的差异(Calder,2004)。此类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可以说不胜枚举。 此外,发展型国家理论在运用于中国研究时也受到过批评。比如有学者指出,发展型国家理论的主要问题是:(1)以一种静态的、简单化的观念把国家看做是统一的、理性的行动者,而忽视了国家结构和政策制定中的复杂性;(2)低估了社会对国家的渗透能力,以及利用国家政策和制度服务于社会利益的能力(孙沛东、徐建牛,2009)。 总体来看,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既与东亚发展型国家有高度的相似性,又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时,国际局势总体趋向缓和,冷战格局向全球化格局演化。这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经济起飞时的全球冷战格局已经有很大差别。而且中国政府并未僵化地遵从任何一种发展模式(无论是发展型国家模式还是监管型国家模式),而是在不同情境下、面对不同的问题采取务实的态度,以寻求经济增长和维持政权稳定为目标,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因而,任何一种单一的发展模式,都无法完全概括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路径。此外,由于复杂的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各地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地方政府行为表现出更大的差异性,具有因时因地而变的特点,因而进行统一的判断和定性更为困难。地方发展模式中的许多有意无意的草根式的试验和探索,往往最终被国家认可并形成正式的制度而得到推广。 五、展望:全球化时代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选择 发展型国家理论系统阐述了后发国家以国家为主导的赶超式发展的独特模式选择。在二战后全球冷战格局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资本主义经济体面对共产主义国家直接的政治军事威胁,在美苏主导的全球冷战体系中处于岌岌可危的边缘地位和两极对抗的前沿阵地,加之威权国家本身政治合法性的薄弱和去殖民化浪潮中建设民族国家的任务,以及美国出于全球冷战的战略考虑而提供的经济援助和开放本国市场等历史性因素,发展型国家模式在二战后的东亚新兴经济体中得到最集中和典型的体现,因而成为发展型国家理论的缘起。而在发展型国家理论形成后,它又成为指导后发国家发展路径选择的重要的规范性概念,对其他后发国家具有普遍的参照价值。 对于任何后发国家来说,由于本国生产能力和市场体系的低度发展以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竞争压力,通过本国自由市场体系自发发展来实现工业化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后发国家势必要扮演比监管型国家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通过国家能力配置关键性资源和支持关键性产业的发展,以培养和保护本国企业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乃至国际竞争力,协助企业抵御短期市场波动造成的风险,并在研发等领域做长期风险投资。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互相配合,并且根据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不断调整。国家一方面要通过适度软预算约束和国家金融机构的倾斜性投资支持战略性国有企业的发展(Lo,2005),同时也要与本国私营部门进行合作,通过由国家管控的金融等制度杠杆引导其投资行为符合国家经济战略规划。国家宏观政治环境的稳定性本身也构成一种维持经济发展的预期,从而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企业在长期投资方面进行决策的重要支撑因素。国家与市场的合作,也切合查默斯·约翰逊提出发展型国家理论的最初动机,即提供在美国监管型国家和苏联指令经济之外的第三种发展模式。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显著的大国来说,基于行政和财政分权为特征的经济联邦主义体系,衍生出了多元化的地方发展模式,其中不乏具有发展型国家特征的所谓“地方发展型国家”模式(郁建兴、高翔,2012)。基于地方草根式试验、创新的自下而上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也值得广大后发国家进行进一步探索。 然而,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发展型国家模式本身也具有显著的阶段性。赶超式发展本身,就是后发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所采取的特殊的发展模式选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效的发展模式总是国家、市场、社会结构与国际秩序等多种因素达成的结构性契合与协同的结果,而非任何单一因素的作用。危机的产生源于旧的结构性契合被打破,而危机的化解则依赖于新的结构性契合的建构,而非否定、舍弃其中的任何一种因素(何子英,2011)。正如斯塔布斯所指出的,由于国家政策制定机制的路径依赖,以及发展型国家模式在过去取得的广为认可的发展成就,全球化时代国际国内局势的新变化,并不意味着发展型国家模式最终走向消亡。东亚国家历史上一直具有强大国家干预的传统,现在它们只是需要面对本国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的约束,然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可以是合作性的,而未必是对抗性的(Stubbs,2009)。 随着经济的起飞以及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发展型国家国内外的很多因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是标志着东亚新兴经济体发展阶段的转型,并进而要求其发展模式的转型。在国内,发展型国家应该更加注重国家监管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的建设;而在经济发展策略上,由于本国市场体系的逐渐完善,国家应该逐渐减少对生产投资行为的直接介入或者干预,而以间接的经济战略规划和引导为主。另外面对国内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政治参与要求的不断提高,国家如何进行民主化改革,如何维系一种对广大社会群体更具有包容性的、基于发展这一共同目标的国家—社会联盟,是更需要探索的问题。首先政府管理需要强化问责制、透明度和法制建设。而社会中间组织的发育,也无疑有利于促成国家与社会之间有组织、制度化的协商与合作。 全球化时代所造成的新的风险,无疑给后发国家的发展带来新的困难,比如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对后发国家的选择性贸易壁垒,以及跨国资本高速流动和本地化生产对本国企业造成的巨大竞争压力。对于早一步发展的后发国家如中国来说,它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具备相当的市场竞争能力的本国企业,也建成了相对合理的整体产业结构。而对于抵御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最为薄弱的最不发达国家来说,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毫无疑问,国家应该是唯一能够加以运用的制度性力量。尤其是在起步阶段,从国家长期发展目标出发,打破国内保守势力的阻挠和旧有社会结构的桎梏,启动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引导和制衡跨国资本,培育本国生产能力和市场体系,国家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感谢我的博士论文导师David A.Palmer(宗树人)对我的博士论文的悉心指导。同时感谢我的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张小劲教授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