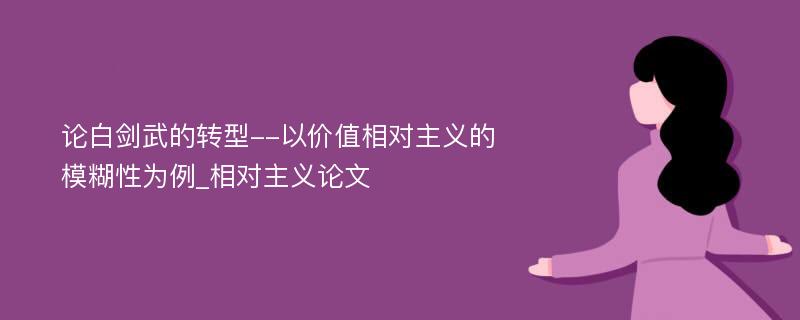
论白坚武的转变———个价值相对主义含混性的实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主义论文,含混论文,实例论文,价值论文,白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4-0396-06
白坚武,民国史上一个小人物。他之所以未被遗忘,主要是因为作为李大钊的同学和吴佩孚的幕僚,在历史大戏台上曾以配角身份登过场。不过,由于其身后留下了一部相对完备的日记,而且在日记中他有既记行踪又记思想的习惯,所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标本价值(注:《白坚武日记》,原名《知白堂日记》,自1915年12月23日始(在此以前的10余年系简单的追记),至1937年7月14日止(其中缺1924年9月28日—1927年9月6日,其间的经历,作者在1927年8月有简单的说明与追记)。日记手稿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本文即拟通过对《白坚武日记》所记思想状况的分析,探讨一下他从一个热血青年蜕变为可耻汉奸的思想历程,并希望借此反映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一种深层变迁(注:我认为由于大人物的思想具有超前性,所以像白坚武这类不太知名的人物往往更能代表当时社会的一般心态。)。
一、北洋“圈子”里的一个另类
白坚武(1886-1937),河北交河人,190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与李大钊同学,毕业后曾任黄钟报记者与内务部佥事,1917年以后分别在北洋军阀李纯和吴佩孚处做顾问,1937年9月,在冀南被属于冯玉祥旧部的国民党军队以“汉奸首领”罪处决。终其一生,白坚武都没有脱离北洋派的圈子,可以说他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任直隶督署秘书)与最顶点(任吴佩孚处总参议),都是在北洋派的圈子内实现的。
然而,年轻时的白坚武却对这个圈子颇为不满,对圈子内的人和事充满痛恨。这一点,倒与当时绝大多数受《新青年》影响的新派人物相通。譬如,1917年1月24日,他曾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入世以来,朴心未退,而社会机心日增;机心递演之结果,公之念日亡,私之念日焰。同一知交,大团之内有小团,大圈之内有小圈,对外无论矣;团与圈之内,无时不用其机心。所谓政团也、政治社会也,有如货币者然,只有恶货驱逐良货而已。”[1](第53页)
非但如此,作为圈内人的白坚武对所处“圈子”不仅愤慨,而且急切地想打破它,改变它。譬如,当他在上海听说北京的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上街游行,“焚卖国党曹汝霖宅,殴章宗祥几毙”,便在当晚的日记中表示强烈同情,认为此举“足征人心未死”[1](第194页);当他从一份报纸上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病死的假消息,便当即认为陈可称得上“中国之路得、卢梭”,斯人之死,“则人道之明星陨坠”[1](第216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他读过《新潮》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后,对文中流露的“根本改造”思想大表赞同,认为中国社会“亟有待于根本澄清,绝对不赞成调和,调和在本身为自灭,对客体为投降”[1](第202页)。当然,“根本改造”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种受到较多认同的思潮。据笔者所见,一个叫黄尊三的经历过辛亥革命的文人在1916年即提出此观点,他说:“以政治之为物,若不从根本谋改革,则人群之进化无望,人民狃于旧习不向上而苟安,……惟打破此循环之迹,而与国民以精神的根本改造,则新机勃发。”[2](第103页)不过,作为北洋派之一员的白坚武,对“旧社会”持如此决绝的态度,足以反映他对所处环境的不满。
打破或改造这个“圈子”从何入手?从白坚武的早年日记看,虽然他没有提供一个以新替旧的具体方案,但其倾向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即与当时大多数忧国忧民、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白坚武颇为看好社会主义。譬如,当他读过《新青年》6卷5号刊载的《马克思学说》一文后,立即感到“曙光在此”[1](第223页)。在1920年2月28日的日记中,他甚至写道:“余现觉宇宙间所有动止,俱由环境构成,物由心造,诚有此象。然展转以细索其因果,仍不出唯物关系。突然而有此内识,突然而有此外效,为世界所无之事。攻马克思唯物论者众矣,余不论其有充分理由。若以马克思所论演证据不充足则有之,强余绝对信仰唯心论现未能也。”[1](第228页)对唯物论的偏爱与对唯心论的怀疑,并由此而引发的为马克思学说的辩护,滥于笔端。
二、第一次思想转变:告别社会主义
白坚武思想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对社会主义由同情到怀疑的态度变化。
事实上,在民国初年,由于实施宪政并未带来预期效果,中国思想界陷入著名记者黄远庸所说的“人心枯窘”[3](第90页)的一个彷徨年代。如果说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同样混乱,那么晚清思想界起码还知道以一种共同认可的方式(宪政)去改变这种混乱,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一旦宪政这剂药方经过民初政治的检验证明失效后,包括白坚武在内的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这批年轻知识分子便不得不开始新的思想探索历程。
依照白坚武在1921年前所表现出的思想趋向,他极有可能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也是当时相当一批企图破旧立新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共同抉择。
除上一节中所列举的材料外,起码还有两点可以证明白坚武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
第一,他对宗教向来没有兴趣。民国初年,当“定孔教为国教运动”甚嚣尘上之际,白即“终不谓然”[1](第45页)。事实上,他不仅对定孔教为国教没有好感,甚至认为一切宗教都是无稽之谈。
第二,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1920年1月2日,当他读张东荪发表在《解放与改造》第7号上的一篇谈社会主义的文章时,发现作者所说的“如有建设必定依著社会主义的原则”,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在日记中写道:“是言实为我所欲言者。”[1](第229页)
一方面,白坚武在1917-1921年间追寻生命意义过程中,对彼岸世界的诱惑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他在此岸世界中对社会主义颇有兴趣,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实况来推演,白坚武转而信仰社会主义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事实上也是许多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思想轨迹。然而,1922年以后的白坚武的思想变化,并未沿正常轨道行驶,他非但没有从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变成信仰者,反而变成了一个反对者。
单凭笔者手头的资料,还不足以完全说明白坚武的这次思想转折,根据他留下的日记,笔者猜测可能有三种原因:
首先,可能与他在1922年人生际遇的改变有关。也就在这一年,他离开南京李纯的幕府,来到洛阳吴佩孚处参赞军政,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政治地位,都有了较大提升。从其日记看,也就是在这一年后,他对所处“圈子”的抱怨大为减少。
其次,可能与他对接触的苏俄代表的观感变化有关。在吴佩孚处,白坚武曾与来访的苏俄代表接触,发现对方在中东路和外蒙等关键问题上,“恍惚其辞,不肯为确定之答复”[1](第450页)。这一点可能使他对苏俄乃至社会主义都产生一种“厌”屋及乌的逆反心理。
最后,可能与他1917年的一次不佳的旅行经历有关。当年4月29日他乘国营的津浦线列车北上,发现该线的二等车尚不如京奉、沪宁、京汉线的三等车洁净舒适,便感喟道:“国家营业,乃如此乎?”[1](第67页)这次不愉快经历有可能长期定格在他的潜意识中。
这三点原因当然还限于理由并不十分充分的猜测,因为当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之初,有人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干多干少一个样,会妨碍个人的创造性,另有人则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劳动者当家作主,能刺激个人的创造性。但由于在世界范围内,计划经济刚刚起步,其利弊得失并非一目了然,所以双方还是处于各执一端的对峙状态。然而,不管怎样,从白坚武1922年之后的日记看,他对社会主义再也没有此前的热情和兴趣了,并且常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口吻谈及社会主义或计划经济。比如,1928年2月,他在读过一本书中关于烟酒归国家专有办理的论述后,即在日记中评论道:“(该论点)理论上诚然有据,然实行尚待讨论。即以北省言,业烧锅者甚多,一律令其完全丧业,殊非维持民生之道;且由国家为之,经官吏之手,亦不见其适宜得利。最好由国家提倡改良,维持其固有之业,而捐其相当之税,斯为酌量得中。凡政策须俯察实际,不可太涉空想也。”[1](第519页)
三、目标缺失后的漫游
白坚武在告别社会主义之后,其思想处于一种“目标缺失后的漫游”状态。由于没有一种价值体系,他在对政治人物或思想做判断时,便只能从“用”的角度出发来加以取舍。因此,他在1922年之后的政治思想带有较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的首要表现,就是否定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万灵丹,一切制度都要拿到环境中试验一番。譬如在1927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白坚武表露了类似的观点:“人类的政治与物质的机器不同,机器可以完全适用科学律,政治则须随时运用良明之人事支配确定之规模,方可相得益彰,若永久不敝之制度乃世所无也,道在因时制宜耳。”[1](第519页)
白坚武是否相信实用主义哲学,仅凭日记已不可考虑,但在日记中可以看出,每当提及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时,其笔端都流露出赞许同情之意;而且,对“永久不敝之制度”的否定,事实上也就是对真理客观性的否定,一切政治思想,在他看来,都只是“因时制宜”的产物。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其直接的外在表现便是价值相对主义——不承认固定恒一的价值观,一切以是否有用作为标准。
在这种价值相对主义的支配之下,人们不易被某一种意识形态俘虏。正因为如此,白坚武对于已成潮流的社会共识,往往也要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比如,对于20世纪30年代风靡中国思想界的以苏俄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思潮,白坚武即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不能苟同。他甚至认为苏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终为畸形发展”,因为“若处处为军事准备,就过程中或亦有相当便利,然终局总是害”[1](第891页)。另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白坚武的这种经济思想还是基于他对人性的一种根本认识。在1931年8月13日的一则日记中,他在论及公、私二字的关系时,感到“人类既不能无私,惟有以公调剂之耳”[1](第901页)。考虑到著名哲学家贺麟此后10年方提出“大公无私不过只是一完美邈远的理想,而假私济公才是切实有效的方法”[4](第65页),不能不承认白坚武的识见确实有独特之处。
一般而言,价值相对主义的长处在于分析——一切思想都可在是否有用的标准下被“去魅”,而其短处则在于综合——不可能形成一种能够整合社会的共同政治理想。如果白坚武在1927年下野后,在天津安安静静做寓公,凭着怀疑一切的价值相对主义眼光,他大可以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民间思想者”。但白一直是一个有很大政治抱负的人,这便促成了其思想的进一步转变。
作为一个冷眼旁观的“民间思想者”,白坚武尽可以将观察对象一一分解,而不用考虑这样做的社会后果。但作为一个政治参与者,他深知“旗号”(共同的政治理想)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换言之,以一种合情合理而非仅仅实用的政治目标来凝聚信徒,是任何政治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白坚武在民初政坛上摸爬滚打多年,自然深谙核心政治目标在动员群众方面的重要性。这在他1927年后的日记中有多方流露。比如,1928年12月14日,他曾与几个朋友预测国共相争的结局,白的观点是:“盖共党主张是非善恶,固另为一问题,而其澈头澈尾直捷了当予人以共见,则也所知也。……国党规定悉仿苏俄,而口头则称反共,其主张之方案,如平均地权等条目,又为准共产;迄无一明白贯澈之主张、脚踏实地以求实效,处处现傍徨歧路之象,此所以情见势绌也。天下有论而无行终归失败,何况并理论亦不能自完其说乎?”[1](第612-613页)
1928年,国民党尚处于上升期,白坚武能有如此预测,关键便在于他敏锐地发现国民党所宣示的理论不彻底,缺乏说服力。从后来的结局看,这一点也确实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白坚武不仅对夺取政权时的“共见”作用相当看重,而且也强调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同样应借助“信条”来整合社会。1929年9月27日的一则日记这样写道:“余谓国家有信条而后,群众心理对于政治始有准循。往昔皇帝一物,千百年纲纪修饬结果,构成一国家神圣信条,相率遵守而不敢渝;自皇帝倒而易民主,旧信条亡矣,必有可以代易之新信条,上乃有统治,下乃有遵循之道。惟民国以来,国家永无确定之信条,专凭当局一、二人之威权驱驭徒党;威权以势力而存,势力不能常具,而威权凌替矣。故政治变相仍其势然也。”[1](第690-691页)
不管是“共见”,还是“信条”,事实上在这里都是指一个社会中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与共同追求的政治目标。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白坚武对“共见”或“信条”在政治中的粘合剂作用有相当清醒的认识,那么,下野后仍不甘寂寞的他又应以何种思想作为自己动员群众的“共见”或“信条”呢?
四、第二次思想转变:南北畛域之见
通读日记,笔者发现白坚武选择的“共见”或“信条”是一种基于地域观念的思想,因为在其晚年思想中有一迥异于从前的变化:即对南、北畛域之见的强调。所谓南、北畛域之见,这里指的是将南北的地理差别引入政治斗争,认为北伐战争是南人对北人的侵凌,因此北人有必要起而反抗。
1933年夏,在与朋友的一次交谈中,白坚武即感觉到“蒋介石南北之见太深,以北为征服也,任其自然,惟有当亡国奴耳。非集合同志决心自救,无他途也”[1](第1117页)。此时已流露出以北方代表自居的意思。在稍后白坚武手订的《正义军军歌》中,这种强调南北对峙、复兴北方的观念更是表白无遗。军歌包括5首,其中第三首的歌名即是《强北》,歌中唱道:“泱泱东海,巍巍太行。惟人与士,王者北方。天如相中国,北在终不亡。燕赵好身手,切莫须臾忘。”[1](第1146页)
如同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对满汉民族差异的强调,白坚武此时对南北畛域之见的强调也有其社会背景。民国初年,由于南方和北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一些政治冲突便往往被简化为南北冲突。当时一个南方的革命党人曾从南方的角度表述过这种观点。他说:“中国古来南北之争,恒北方占优势,予作《革命杂诗》,有句曰:‘自古南都多短命,怕谈总统祭明陵’,所以纪实也。……孰知事至今日,愈出愈奇,以中原之人治中原,乃视南方等于被征服之士,派兵驻防,一如满州。”[5](第37页)南方对北方的不服与不满,跃然纸上。当时开战多称“南北战争”,议和则叫“南北妥协”,以致态度相对超脱的国民党领袖黄郛在1918年感叹道:“今北京命令,称西南曰南服;西南文电,名北京曰北庭;吾试问西南究为何国人,北京究为何国都。”[6](第287页)
北伐之后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尽管蒋介石在北伐之初即把三民主义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认为国民革命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不是以南方统一北方,但北伐战争毕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方发动、并取得成功的统一事例(第一次是元末朱元璋的北伐),这对北方民众的心理,应有较大刺激。而且,国民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一系列举措(如迁都南京),皆加剧了北方人对南方人的成见。青年党领袖李璜当时曾游走南北,对此有深切感受。他晚年回忆道:“国民党在北方未能深入民众去做基本诱导工夫,这已足造成南北彼此了解不够,易滋误会;何况……革命而要称之为‘北伐’,北京又定要改成‘北平’,更足使北人认为南人骄妄了。我初闻此种怨言于失意军人政客之口,并未加以重视,及询问同志们,乃知此一误解与怨言相当的普遍于北方社会,便令我不能不对国事有了隐忧。”[7](第249页)
值得注意的是,从白坚武的日记看,他并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大北方主义者”,换言之,他的南北畛域之见在早年并不强烈。譬如他很早即对南北两地人民有一种成见:即认为南方人“智忧而力不足”,北方人则“力不患不足,患见事之不明”[1](第150页),而且,这种成见基本贯穿始终。由此可见,他在能力方面并没有厚北薄南,充其量只是认为南人与北人在体力与智力上各有所长。不过,他在1927年之后,亲见中国政治中心南移后在北方造成的动荡与不满,于是便敏锐地抓住当时政治斗争的这一症结,迅即打出“强北”的政治旗号。这中间,从其前后态度的反差看,可能也有政治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作祟。
不管白坚武的南北畛域之见上是借题发挥,还是确实相信,这个借口或解释后来成为其政治行为的一种安魂丹,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第一节所述,白在青年时即持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观念,即使到晚年,这种起码的民族主义观念也并未完全丧失。譬如,面对日本的侵华活动,他在内心深处也有一定的防备,如其在1932年即认为:“现在日军横冲直撞,不啻向世界宣战,必步德国后尘。”[1](第961页)考虑到白写日记并无示人的动机,那么我们便不能认定他的这些言论完全出于作秀。事实上,白坚武一方面高谈救国爱国,另一方面为求政治发迹而与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其理由便是基于南北畛域之见的“强北”动机。正是这个虚构的“正当理由”,才使得他在内心深处将如此矛盾的政治行为统一起来,既为自己动员信众寻求理论工具,也为自己卖国求荣找到正当理由。
五、余论
综上所述,从青年到晚年的白坚武,一直处于价值相对主义的影响下。作为秀才出身的读书人,他对传统的儒学却并无好感与崇信;作为不满现实的愤世者,他又认为社会主义不合人性。白的思想在1922年之后即陷入完全以“用”做标准的彻底的价值相对主义。到1930年代,他在“用”的引导下,终于找到一种能解释自己行为的理论框架——南北畛域之见,他从一个爱国青年蜕变为可耻汉奸,便是在这个框架内获得心理平衡的。因为在这个框架内,可以用一种对北方的责任感取代对祖国的道德感。一般而言,基于地域或种族的思想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发动群众,但这种基于地域观念的情感诉求,并不成其为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没有回答“根本性问题”——如何构造一个能吸引受众的“人间天堂”,因此并不足以引人入胜,最终难免失败。
然而,白坚武的思想变化则反映了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新的价值系统的艰难历程。从五四以后的情形看,背弃传统的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且中国的重新统一,事实上也是建立在这种选择基础之上。但是,毕竟还有一些如同白坚武这类弃旧而又厌新的人物,在寻找思想之锚的过程中一直苦苦挣扎。直至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对“共同的理想或标准”的追求仍在困惑着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士。如一位学者在1946年仍呼吁中国要重建精神大厦,他的理由是:“本来所谓‘国于天地,必有以立’,这个‘有’原也不指武器,而是指某一社会中人群所同意信守的生活方式和原则——几颗思想上的大柱子,顶住了这个社会(或国家)的组织机构。一般人称这个机构为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这几颗大柱子有的时候叫作四维八德,有的地方叫作民治思想,有的地方叫作共产主义。不管叫它什么,重要的是在这个社会中的人群必须能同意支持这些柱子,这些原则,否则整个机构垮下来必酿成极大的灾祸。尤其重要的是同意支持,不是强迫支持。”[8](第10-19页)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一部中国现代史,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寻找“柱子”的历史。白坚武思想转变之频繁,正好反映了这些“柱子”的寻找之困难。
收稿日期:2003-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