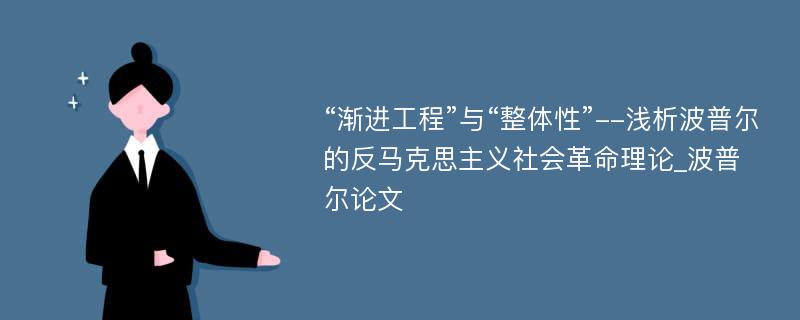
“渐进工程”对抗“整体主义”——波普尔反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主义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工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波普尔是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他采取先破后立的方法对历史决定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进行全面的批判。“破”,表现为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立”,表现为以“渐进的社会工程”理论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
由于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主要表现为“破”的过程,因而后人的研究也多半侧重于此。但对他的“渐进的社会工程”理论则研究不多、不深。而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以来,波普尔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在此情形下,对波普尔“渐进的社会工程”理论作一番探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波普尔不反对理论干预社会,而认为这种干预应该是渐进的尝试。他说,渐进观点“与历史决定论者的方法之间的区别,其标志与其说在于它是一种技术不如说它是一种渐进的技术。仅就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技术而论,它的方法不是渐进的而是‘整体主义的’”[1]。
波普尔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对社会进行彻底和总体改造的方法不同,他认为渐进工程与历史决定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有以下几种区别:
第一,在基础上,历史决定论承认历史规律的存在,而渐进工程只承认趋势的存在
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发现趋势,并尽量完善地解释趋势,而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他说:“我不相信历史规律,特别不相信进步的规律这类东西。事实上,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说,倒退比进步容易得多。”[2]他把历史规律和趋势作了严格的区分, 认为:“趋势是存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趋势的假定通常是一种很有用的统计方法。然而,趋势不是规律,断定某种趋势存在的命题是存在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断定在特定时间和空间有某种趋势存在的命题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而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这种逻辑情况的实际意义是值得考虑的。我们可以根据规律来作出科学预测,但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趋势的存在作出科学的预测。”[3]
我们认为,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历史规律,都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规律揭示的是现象的共性、本质性。规律作为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其表现形式也是多层面的,有适用于一切领域的普遍规律,有适用于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律,还有仅仅适用于个别领域的个别规律。即使是同一规律,在宏观领域里的表现形式与在微观领域、宏观领域里的表现形式就有很大的差别。这说明规律的存在是有条件的。波普尔把自然规律的特点搬到社会领域,从而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这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形而上学的做法。他只看到一个个相异的历史事件,看不到事件之间的共同性,因而只承认历史趋势的存在而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社会生产方式对社会性质起决定作用,在以棍棒、石块为工具的地方,其社会性质超不出原始公社制度,而资本主义制度要想产生、发展起来,就必须用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生产。
马克思主义认为,规律和趋势是两个不能等同的概念,但也不是绝对的对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规律常常表现为多种可能性在一定的历史的具体的条件下实现其中的某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是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波普尔完全否定历史的进步,认为“倒退比进步容易得多”,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历史的进步是不变的事实,是无可怀疑的,人类社会总是从原始、愚昧一步一步向文明、开化迈进的。尽管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可能出现倒退或挫折,但历史发展的总方向是前进的。
马克思通过对大量的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首先揭示了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即人们的物质资料、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进而揭示了社会生活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描画出人类社会各形态的演进过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
第二,在方法上,历史决定论因认定发现了客观的历史规律,坚信制定一整套关于彻底改造社会的正确计划是必然的和可能的;而渐进工程则在改革的范围中不抱成见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准备在尝试和错误中学习,通过批判逐步取得进展
对于历史决定论的整体主义,波普尔批判道:“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与渐进的社会工程相反,它绝不带有‘私人的’性质,而总是具有‘公众’的性质。它的目的在于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整个社会’;它的目的在于‘夺取关键地位’扩大‘国家权力……直到国家变成几乎与社会一样’,它的目的还在于从这关键地位上控制那些影响着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力量,或者阻碍社会发展,或者预见其过程并使社会与之相适应。”[5]
波普尔进一步指责:“整体主义者反对渐进方法,认为它太温和。然而,他们的反对和他们的实践并不相符;因为他们尽管是雄心勃勃的和无情的,但在实践中总是笨拙地随意应用基本上属于渐进的方法,只是不审慎和缺乏自我批评……实际上,乌托邦工程和渐进工程之间的区别,与其说在于规模和范围,其实不如说在于对不可避免的意外情况的审慎和准备。”[6]
从波普尔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渐进工程乃是他的试错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如果说对于局部的或小规模的改革还有点帮助的话,对于全面的或大规模的革命或变革则是有害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主张进行鲁莽的行动,而是进行仔细、审慎的革命,对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均作周密的考虑和安排。马克思主义者向来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方法和原则也为后来的各国革命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可见,波普尔批评马克思主义者“不审慎和缺乏自我批评”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知道,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这理应为波普尔所熟知,可波普尔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为了对抗整体主义,波普尔宣称,正是整体主义使历史决定论有可能与乌托邦的社会工程结成联盟,他的公式是:历史决定论=整体主义=乌托邦。我们认为,在上述三者之间划等号,是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诬陷,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事实就证明他的指责无效。波普尔主张一点一滴地改良,反对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改良主义,这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只允许局部的修修补补,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就要有长远的规划和整体的构想,没有这些,局部的改良就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一张可退可进的王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也将逐步丧失。当然,在社会革命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并不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拒绝社会改良,因为社会改良不同于改良主义,它可以成为社会革命的前奏,为革命作准备。
第三,在规模上,历史决定论主张整体上的变革,而波普尔认为变革只能是局部的和渐进的
波普尔认为,“在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主义的联盟中,最有力的因素无疑在于它们都是整体主义的”[7], “整体主义是要加以抨击的历史决定论的最关键性的论点之一”[8]。
波普尔否定整体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和其他学科一样,只能研究在对象中被选定的那些感兴趣的方面。他说:“整体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即表示‘整体社会有机体’或‘一个时代的全部社会历史事件’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这个思想来源于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广阔的发展长河这个直观看法。但这样的历史是无法写出来的。每一部写成文字的历史都是这个‘全部’发展的某些狭小的方面的历史,总是很不完全的历史,甚至是被选择出来的那个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的历史。”[9]
否定整体主义的历史观之后,波普尔从非整体主义的立场出发,否定人类有人类史。他认为,人类史是没有的,只有无数关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历史,如果有人类史的话,那应该是所有人的历史,也必然是人类的一切希望、斗争和灾难的历史。因为没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重要,那些被遗忘的无名人物的生活,他们的忧愁与欢乐,他们的苦难和死亡都是无数年来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然而,能包容所有这些内容的历史是无法写出来的。事实上,被称为世界史的历史,往往是在皇帝、将军和独裁者的监视下写出来的,它不过是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这种强权政治史只是一部国际罪恶和大量谋杀的历史,它既是有害的,也是肤浅的。说其有害,是因为它把某些罪大恶极的人物称颂为历史上的英雄;说其肤浅,是因为它只考虑一小撮大人物,而没有关心作为历史主流的更可贵的普通人。
不可否认,波普尔的历史观虽有很多偏激不妥之处,但他广泛关注普通人,反对强权政治史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他也感觉到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相通之处。他说:“在历史决定论中有着一些合理因素,它反对把政治历史仅仅说成是伟大的帝王将相的历史那种天真写法。”[10]
但是,波普尔断定历史决定论用整体主义的方式来研究和改造社会就必然导致乌托邦主义则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恰恰是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性质,它把现实社会的运动当作我们行动的出发点,因而从根本上扬弃了改造社会的空想性质。如果波普尔断定空想社会主义为乌托邦还不过分的话,那么他以此来指责马克思主义则是毫无道理的。相反地,从满足于现状和醉心于点滴改良的意义上,波普尔倒有些乌托邦式的幻想。
同时,我们认为,波普尔所批判的整体主义,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部分是整体的部分。把个别事物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取出来单独地加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忘记部分与整体以及整体中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抛开整体,就弄不清组成它的各个部分,而不了解一个个部分,也就不可能清晰地把握它的整体。整体不是各个部分的堆积,它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各部分之和,这完全取决于整体自身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把社会学说变成科学,就在于它从社会各方面现象的复杂的总联系中把握各个社会现象,它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它认为社会像人体一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像自然界一样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整体系统,具有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整个社会就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大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三大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使得社会发展表现为有规律的历史过程,这也就使得人们能够用相对比较精确的眼光去研究整个人类社会。
第四,在实际运行中,历史决定论往往导致“国家集权主义”,而渐进工程则保障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波普尔认为,整体的改造就要假定一套完善的计划,而计划的实施就需要集权,可是集权并不能导致社会按完善的计划运行。因为整个计划根本不可能符合现实,整体主义的变革越大,计划未预料到的和极不希望出现的情况也越多,这就可能迫使人们不断地修改计划,从而导致无计划的计划;也可能引起执行者进一步强化权力,强行实施计划,从而危及人们的自由。其结果必然是阻碍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以知识的进步为前提,权力的集中必然导致社会的停滞,“因为科学的进步有赖于思想的自由竞争,因而有赖于思想自由,归根结底有赖于政治自由”[11]。他接着说,“进步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因素;依赖于保障思想自由的政治建构,即有赖于民主”[12]。波普尔还公开声称,不要为了未来的理想而让现在的人做出牺牲,“每一代人都不必为将来的一代一代而牺牲,为一个可能永远实现不了的幸福理想而牺牲”[13],“同样,我们也不能说,一代人的苦难可仅仅看作是达致下一代或下几代永久幸福这个目的的一个手段……我们决不应该试图用牺牲某些人的幸福来补偿另一些人的苦难……一代代人都是匆匆而去的过客”[14]。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社会的进步与政治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政治本身就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问题在于波普尔把计划性等同于集权主义,把集中与自由完全对立起来,认为任何集中、计划都会扼杀人性自由,不能设想通过民主决策和民主参与制订、实施计划的可能性。试看当前的现实,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实行某种程度的计划,市场经济也需要宏观指导,没有任何计划就无异于盲目行事。波普尔关于理想与牺牲的思想,实际上是在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发出的呐喊,其目的不过是不致牺牲资产阶级的幸福来补偿无产阶级的苦难,要求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安于现状,放弃理想与斗争。
当然,波普尔认为强调计划将导致集权并非毫无意义,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与集中的结合在何种程度上最为有效,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波普尔在这里提了个醒,有助于我们重视它,并在现实当中进一步理顺计划与市场、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
第五,在过程上,历史决定论因主张彻底改造,必然导致割裂传统纽带的激进主义,而渐进工程则采取以传统为依托的稳健步骤
波普尔抨击历史决定论者想彻底“清洗”这个世界、“用崭新的理性世界把过去一笔勾销,一切从头开始”的观点是胡说八道,不可能实现。也没有理由相信重新构造的世界是一个幸福的世界,没有理由相信一个作为蓝图勾勒出来的世界会比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更好一些。他认为,在一个一无所有的世界里,在一个社会真空里,蓝图毫无意义,蓝图只有在像神话、诗歌和价值观这样的传统和制度的背景中才有意义。离开了这些,蓝图就毫无意义可言。因此,一旦我们毁灭了旧世界的传统,重新建造一个新世界的动机和愿望也必定随之消失。在科学中,如果说“我们取得的进步不大,让我们清除全部科学,重新开始”将是巨大的失策,合理的做法是去纠正它,进行革命的改造,而不是去清除。
应该说,波普尔对待传统有值得肯定的方面,但他机械地理解了革命与传统的关系,无法把继承与批判辩证地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不是割断历史,更不是否定一切,而是批判地继承,是扬弃。毁灭旧传统是使历史传统获得新生的动力,传统不能完全毁灭。因为毁灭了传统,文明也随之消失。可是,对于社会革命来说,毁灭旧传统与发展传统是完全一致的,正像科学的发展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样,无产阶级也必须站在传统的肩膀上,才能创造新社会。只要批判传统,传统就必然是我们的出发点,然而新理论的产生总是伴随着驳倒旧学说的过程,而新社会的建立也必然是破旧立新的过程。
注释:
[1][3][5][6][7][8][9][10][11][12]《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第91页,第52~53页,第53~54 页, 第58页,第60页,第64页,第118页,第71页,第123页。
[2][13][14]《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20页,第515页,第51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