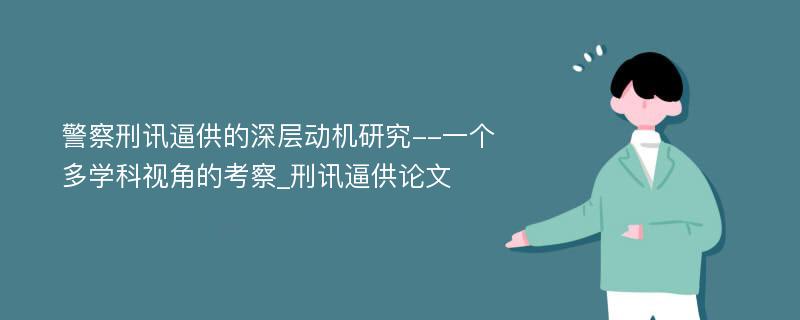
警察刑讯逼供的深层动因研究——多学科视角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讯逼供论文,动因论文,视角论文,多学科论文,警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285(2013)02—0006—05
2013年3月曝光的张高平、张辉叔侄冤案再次将刑讯逼供置于公共舆论的风口浪尖。这起所谓的张氏叔侄强奸致死案发生于2003年,昭雪于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的2013年。尽管一起发生于10年之前的冤案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并没有任何关联,但其在新《刑事诉讼法》颁行两月左右曝光,难免让公众发出刑讯逼供能否法到“病”除的疑问。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人们总结了诸多原因: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侦查人员素质水平的限制、法律制度规范的疏漏、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欠缺、外部监督力量的软弱等等。的确,上述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刑讯逼供在中国的消亡。但笔者认为,这些因素未能解释警察刑讯逼供更深层次的动因。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警察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刑讯逼供行为的施行者?这需要我们站在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更宽阔的学科视野去寻找答案。
一、经济学视角:警察刑讯逼供的成本收益分析
经济学理论认为,人是一种经济理性的动物,人的行为选择过程就是一个利弊权衡的过程,隐含着一种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在内)。犯罪人和普通人一样,都是谋求利益实现的“经济人”,获利与否决定行为与否,这是一切故意犯罪所考虑的根本问题。刑讯逼供作为一种延续多年的行为选择,体现了行为人的经济理性,是侦查人员所认为的在所有侦查资源配置方式中收益最大、成本最低的一种选择。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法学家边沁,提出并阐述了著名的“功利主义”原则,他指出:“该原则是指对某行为的肯定或否定,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具有增进涉及切身利益的当事人的幸福,或者说,是以能否促进幸福来评价行为。”而刑讯逼供最难驳斥的存在理由就是它的有用性。“有用性”给一些警察带来了显著收益,自然有助于增进警察的“幸福感”。
警察刑讯逼供最直接的收益是获取口供,最根本的收益是破案。人类对口供的青睐由来已久,口供之于破获案件的直接性、迅捷性、高效性远非其他证据形式所能相提并论,“一步到位”、“多快好省”、“及时方便”这些功利色彩极浓的词汇附身口供,使得口供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证据之王”。刑讯逼供所带来的“破一案带一串清一片”的意外收获使民警更深刻地感受到它不寻常的收益。口供帮助有效地破案,破案又能带来更大的收益——立功受奖。公安机关越是破了大案、要案、悬案、疑案、积案,警察个人和办案集体立功受奖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直接与间接的利益所增进的幸福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警察的行为选择。因此,在功利的驱动下,刑讯逼供难以禁止。
另一方面,刑讯逼供的成本极其低廉。刑讯逼供所利用的是人类对肉体痛感的最本能的恐惧。制造这种肉体的痛感和恐惧无论对侦查人员个体来说,还是对国家而言,都不需要投入太多的成本。省却了引进先进侦查技术手段及设备的支出,省却了培训侦查人员提升侦查技术水平的投入,忽略了警察连续作战、熬夜加班的付出(实践中警察熬夜已经成为习惯,被政府甚至警察自身所忽略),忽略了刑讯逼供使警察正常心理和心态受到的损伤(实际上这种隐形的损伤已被及时破案所带来的同行嘉许和社会认同所弥补),忽略了刑讯逼供对程序正义、公正理念、法治实现的破坏(国家和民众对实体正义的偏重使得这种社会成本只有在被发现的冤假错案中受到关注),加之刑讯逼供案件状告难、取证难、立案难、起诉难、判刑更难的特点所造就的低廉的惩罚成本,使得刑讯逼供成为一种收益明显大于支出的看似“理性”的行为选择,屡禁不止成为必然。
除了成本收益的权衡,刑讯逼供也是侦查人员在对案件实体正义的追求中看到“错”与“对”两种结果比例严重失调,进而做出自身行为选择的产物。实践证明,在以刑讯逼供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刑事案件中,错误地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只占极小一部分,因而在外部也相应地表现为:绝大部分案件还是“打对了”——犯罪嫌疑人罪有应得,极小部分案件遗憾地“打错了”——受害人令人同情,对这样的比例进行权衡之后,刑讯逼供这种最为原始但却不失为有效的方法自然而然地粉墨登场,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通向实体正义的程序牺牲品”。
二、管理学视角:“破案指标”对刑讯逼供的影响
“指标”是管理学中的常见概念。各行各业的管理者免不了同各式各样的指标打交道,除了公安机关的破案指标外,还有企业的利润指标、大学的科研指标等等。指标有软指标和硬指标之分,其划分标准在于硬指标可以定量,而软指标只能定性。在定量和定性的关系上,常常存在着隐含的冲突,即目的和手段的冲突。从更深层次看,其实质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这种冲突又被称为“指标陷阱”。①
人们对“破案指标”的质疑实质上反映的正是软硬指标的严重冲突。全国公安系统普遍存在的“破案指标”,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些地方的公安系统甚至以破案率排定各公安机关的座次,并凭此立功受奖。司法实践中,重大案件特别是命案发生后,上级机关、地方政府的领导会十分关注案件侦办情况,公安机关必须对这种关注予以积极的回应。尽管这种承诺本身并不符合刑侦工作的基本规律,但出于对部门政绩甚至个人政绩的追求,公安机关的这种追求带来的巨大压力自然会传递给每一个警察,使其甚至为了完成“破案指标”不惜动用刑讯逼供的方法寻求案件的快速侦破。
破案指标完成与否不仅与单位的评优和奖励密切联系,也与警察个人的福利休戚相关。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一个操作发生以后,接着呈现一个强化刺激,那么这个操作的强度就增强,所增强的不是S-R(刺激—反应)的联结,而是反应发生的概率。强化(reinforcement)即指增强某一反应发生概率的一种程序。因此,以指标完成与否为主导的赏罚机制无形中使刑讯逼供得以强化。当下一次审讯陷入僵局时,刑讯逼供就极有可能再次发生,这其中的强化物(凡能增强某一反应发生概率的刺激)近的是嫌疑人的口供,远的是办案人员的职务升迁、立功受奖。可见,破案指标本应为改善社会治安的目的而拟定,但有时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软硬指标的严重冲突:即不仅未能实现社会治安的好转,反而使警察因盲目追求完成硬性数字而增加了实施刑讯逼供的可能。
三、伦理学视角:警察刑讯逼供的道德宽宥
(一)警察刑讯逼供的“道德盲区”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体现在人是有理智的,具有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力,人的行为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即孟子所说的人人皆备的“恻隐之心”。警察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群体,肩负着惩恶扬善的社会职责,理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和人格。刑讯逼供显然是与警察应有形象格格不入的“恶行”。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恶行”为何没能得到道德的抵制?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对警察刑讯时的内心世界作以解读。一是刑讯目的的“高尚性”掩盖了“恶行”的本质。抛开公安队伍中个别败类以刑讯取乐的情形,刑讯逼供是警察执行公务时的一种“行为”,而非私人的复仇或妄为。警察与犯罪嫌疑人并无私仇,其如此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破获案件,维护秩序,实现正义,增进公共的福祉。这样一种“公”的性质,使得警察在刑讯逼供时“心安理得”和“理直气壮”,也使得刑讯逼供能够借助功利主义的道德获得宽宥乃至纵容。②二是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在道德层面上的不平等性。一方是维护社会正义、权力在握的警察,一方是涉案在身、低人一等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道德层面的优越感和权威感在讯问的情境中会急剧膨胀,进而引发不理智的行为。应该看到,在警察内心深处,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是有“道德基础”的。他们认为当一个人的行为与刑事犯罪有关时,要求其如实回答司法人员的提问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事实上,这种观念在社会大众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正如卡夫卡在《审判》中表达过这样的主题:因为你被控有罪,所以你有罪。因此,侦查人员很容易获得这样的心理暗示:在道德层面,犯罪嫌疑人是低人一等的,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被物化为刑事诉讼活动的“客体”,为了追求破案效果对其动用些非法的手段无伤大雅。
上述两方面原因为警察刑讯逼供扫除了心理障碍,使得这项“恶行”成为了一个“道德盲区”。不仅参与刑讯的警察“当局者迷”,就连其同行甚至公安机关的领导也很难做到“旁观者清”,相反,他们对于这样的现象“深表理解”。一旦遇有民警因刑讯逼供“东窗事发”而锒铛入狱,大多数同行表现出的都是深深的同情和不忍,很少有人对之深恶痛绝,更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对同行进行揭发。而如果因刑讯获得了口供进而侦破了大案,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则多会被忽略不计,上级领导和左右同事谁都不会有负罪感。
(二)警察对嫌疑人缺乏“恻隐之心”的思想根源
为什么人人皆备的“恻隐之心”在警察身上不起作用?应该指出,警察在刑讯逼供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麻木不仁”和“心安理得”并非因其道德品质败坏,而是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犯罪嫌疑人应该享有属于每一个“人”的权利保障,将其排除在自己的同类之外。究其本质,还是有罪推定的弦绷得太紧。
有罪推定是封建司法的遗毒,基本含义是: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罪犯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有的。③由于存在着把事实置于同调查官的假设相一致的倾向,因而就把被告推上了“普罗克汝斯特斯之床”:“法律折磨你,因为你是罪犯;因为你可能是罪犯;因为我想你是罪犯。”④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对犯罪嫌疑人的处境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刑事诉讼论证不是遵循非真即假的二元体系,而是遵循逐渐升级的原则。论证中的每一级都构成一定的罪责认定,从而涉及一定的惩罚。因此,疑犯总会受到一定惩罚。人若成为怀疑的对象就不可能是完全无辜的。怀疑就暗含着法官的论证因素,疑犯的某种程度的罪责及有限的刑事惩罚。一个疑犯如果始终受到怀疑,就不会被宣布无罪,而要受到部分的惩罚。当人们推理达到某种程度时,人们就完全有理由展开一种具有双重作用的活动:根据已收集的信息开始施加惩罚,同时利用这初步的惩罚以获得尚不清楚的事实真相。”⑤可见,在有罪推定思想的支撑下,刑讯逼供成为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被推定为有罪的人被讯问人员理所当然地视为异类,所有有关道德、良知、善良、仁慈等人类美好的品质在有罪推定面前均变得不堪一击。因此,这种思想不根除,一切为增强内部遏制力量所作的努力均无异于“形同虚设”。
四、犯罪学视角:“标定理论”对刑讯逼供成因的解读
道德宽宥为警察刑讯逼供扫除了心理障碍。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究:为什么一个人可能有罪就在道德层面上低人一等,成为脆弱而无助的“异类”?除了警察自身对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理解误区之外,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有些事后被证明无辜的人为什么也会显得底气不足?是什么主宰着讯问者与被讯问者地位的悬殊落差?我们可以借助犯罪学中的标定理论对问题作更为深入的分析。
标定理论(labeling theory,又译为“贴标签论”、“标签理论”、“标示论”等)是一组试图说明人们在初次的越轨或犯罪行为之后,为什么会继续进行越轨或犯罪行为,从而形成犯罪生涯的理论观点。⑥标定理论认为,尽管有很多人同样违反了法律,但是只有少数一些人因此而被逮捕拘留。犯罪行为本身并不能引起贴标签的过程,只有犯罪人在被刑事司法机关逮捕拘留时,才会引起贴标签的过程,从而对其心理产生莫大负担。若是被判有罪而服刑,对于家庭及个人更会产生巨大打击。服刑归来后,对其回归社会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同时,难免在服刑中感染一些不良恶习。
标定理论的研究对象虽然是越轨者,但为我们研究刑讯逼供中的犯罪嫌疑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管是不是真的有罪,只要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进入刑事司法领域,被拘留或逮捕,就会自然引起贴标签的过程,从而使犯罪嫌疑人在道德上或人格上受到来自国家、社会的质疑和歧视,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使其自信心受到毁灭性的打击。面对着代表国家公权力、咄咄逼人的讯问人员,犯罪嫌疑人自然会表现出畏惧、躲闪、不安等情绪,即便是无辜的人,其辩解也会在讯问的情境中变得越来越“有气无力”,成为引发刑讯逼供的刺激源。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不能仅仅归咎于讯问者与被讯问者权力、地位的悬殊差距,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来自社会的标定,这种标定给犯罪嫌疑人烙上了难以摆脱的印记,也使得警察的逼供行为看似有了强大的社会支撑。在这一标定过程中,国家、讯问人员、社会大众都难辞其咎。正因如此,现代法治国家在发动刑事强制措施和刑罚权时越来越慎重。
五、心理学视角:挫折—攻击理论对刑讯逼供成因的解读
笔者认为,促使警察刑讯逼供最大的心理动因是挫折。犯罪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挫折—攻击理论。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关系研究所心理学家约翰·米勒、伦纳德·杜布、霍巴特·莫勒和罗伯特·西尔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关于挫折与攻击的两条基本假设:(1)攻击发生时常预想挫折的存在;(2)挫折产生一些不同模式的行为反映,其中的一种是某种方式的攻击。多拉德等人认为,挫折是否引起攻击行为,取决于下列因素:(1)受挫折时产生的驱力的强弱;(2)受挫折时引起的驱力的范围;(3)以前所遭受的挫折的频率;(4)随着攻击反应的产生而可能受到惩罚的程度。多拉德等人关于挫折与攻击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说,为人们了解攻击行为产生的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从而也为解释攻击性犯罪行为的产生以及预防攻击性犯罪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⑦
刑讯逼供是一种典型的攻击性犯罪行为。一方面,警察扮演着如此重要的社会角色,总会想方设法地破获案件,满足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警察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面临着太多遭受挫折的机会:长期接触社会阴暗面、身处与犯罪分子殊死搏斗的第一线;每日被违法犯罪行为所包围、面对犯罪嫌疑人的对抗甚至挑衅;经常加班、熬夜,难以享受正常的社交和娱乐;时刻神经紧绷、压力重重、处于分辨真话与谎言的环境之中。⑧笔者在与警察座谈中发现,为数不少的警察认为“只讲道德不讲狠,公安机关就没有权威性和震慑力”,“对坏人的仁慈就是对好人的残忍”。有的警察谈到,想动手打嫌疑人时支配大脑的往往不是获取口供的强烈愿望,而是气愤难耐、想杀杀他们的嚣张气焰。因此,长期的受挫过程、高频的受挫频率引发强大的攻击趋力,加之刑讯逼供案件低廉的惩罚成本,使得警察很容易在受挫时选择攻击行为。因此,攻击行为是角色扮演受挫的反应。
六、社会学视角:角色理论对刑讯逼供成因的解读
为什么角色扮演受挫会产生攻击行为?我们需要借助社会学的角色理论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
角色理论(Role Theory)是与人的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角色理论的重要贡献者之一、美国人类学家林顿(R.Linton)认为,角色是由社会文化塑造的,角色表演是根据文化所规定的剧本进行的。⑨角色是人们行为的依据,是社会交往的基础,特定文化下的人们对于既定角色总是有某种期望,如果某人的行为有别于其所扮演的角色,社会就会视之为异类。
警察也不例外。社会赋予的期望与责任直接决定着其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的形成,使其在角色的扮演中不敢有丝毫倦怠。笔者在与民警座谈中了解到,很多民警认为“没有刑讯逼供的警察未必是好警察。实践中,刑讯逼供的警察有两类:一类是素质低下、容易冲动的警察,但现在愿意为‘公’冲动的警察越来越少了;还有一类是有责任感、事业心强的警察,他们比谁都清楚这样做可能会付出的代价,失去饭碗甚至失去自由,但是职业的荣誉感使他们不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想为破案做出努力。”可见,使用暴力(暂且不问程度)获取口供的行为与其说是个人道德的沦丧或行为的失范,毋宁说是在职业工作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反应方式、态度和习惯。刑讯逼供是讯问者“过度角色化”的一种表现。⑩除暴安良的角色扮演受阻是引发警察刑讯逼供的深层根源。从本质上讲,刑讯逼供是挫折引发的角色冲突的表现。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尽管新《刑事诉讼法》多项规定剑指刑讯逼供,但是仅仅凭借落实一部程序法很难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科学的制度设计必须与刑罚惩治力度的加大、考核指标体系的改革、无罪推定理念的深化、社会偏见的革除、警察心理压力的疏解、警察角色的理性定位等多项努力相配合,才能真正实现刑讯逼供“药”到病除。
注释:
①刘文瑞:《管理中的硬指标和软指标》,《管理学家》2006年4月。
②参见夏勇:《酷刑与功利主义》,载夏勇等主编:《如何根除酷刑——中国与丹麦酷刑问题合作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③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④[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⑤[法]米歇尔·福柯:《规戒与惩罚》,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6页。
⑥吴宗宪:《西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93页。
⑦同上书,第288—289页。
⑧刘昂:《遏制理论视野下的刑讯逼供成因及对策》,《法学杂志》2010年第6期。
⑨《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312页。
⑩吴丹红:《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法社会学视野中的刑讯逼供》,《中外法学》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