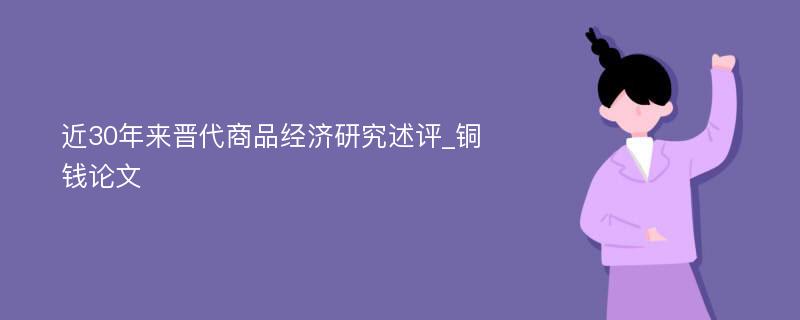
近三十年来金代商业经济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经济研究论文,近三十年论文,金代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朝统治的百余年间是中国北方地区商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史研究的蓬勃发展,金代商业史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有关金代商业的专著、论文陆续发表,一些有见地的学术观点逐渐得到金史界的认同。现将这些成果及其观点举要如下,以便我们对金代商业史的研究状况做系统考察。
一、关于金代商业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金代商业的发展植根于金代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的进步。近三十年来,金史学者在这些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第一,关于金代农业。在金代农业发展的总体状况方面,刘肃勇《试论金世宗恢复北方农业经济的措施》(《绥化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任蕾《金世宗完颜雍发展农业生产之管见》(《博物馆研究》2000年第2期)、禾女《金代农业技术初探》(《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等文,从政策、措施、技术等层面对金代的农业状况做了深入探讨。一些学者还结合考古发现对金代农业做了更加具体、细致的分析,刘景文在《从考古资料看金代农业的迅速发展》(《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中利用考古资料对金代使用的铁铧、铁镰、铁锄等农具做了细致分类,并对每种农具的形制、功能进行认真分析,得出了“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资料看,金代的农业都是我国北方古代农业发展史上速度最高的时代之一”的结论。
韩茂莉关于金代农业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近年来,她先后发表了《论金代猛安、谋克入迁中原与中原农业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古今农业》2000年第4期)、《金代主要农作物地理分布与种植制度》(《国学研究》第7卷,2000年)、《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核心区的转移与环境变迁》(《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4期)等论文,出版了《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三联书店,2006年)等著作。韩先生的上述论著详细研究了金朝本土、中原地区以及西辽河流域的农业状况,探索了金代主要农作物的地理分布与农业耕作方式,研究了人口迁移与各区域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金代农业区域史研究颇为活跃,金史学界对金代东北农业的研究尤为透彻,赵鸣岐《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朱国忱《略论金代黑龙江地区的农业发展》(《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王德忠《金朝建立前后金源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辽金史论集》第9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郝庆云、魏国忠《金代黑龙江地区的农田规模》(《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4期)等论文不同程度地探讨了金代发展东北农业的政策、农业技术水平以及农作物品种、农田面积、农业产量等问题。
第二,关于金代畜牧业。畜牧业是金代的重要经济部门,但由于史籍记载过于简略,很多史事已经淹没无传,给金代畜牧史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因此,与农业相比,近三十年来关于金代畜牧问题的论文数量很少。以刘浦江编著的《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为例,该书收入金代农业史论文计50篇,而收录的畜牧史论文只有6篇。有限的畜牧史论文中,张英在《略述金代畜牧业》(《求是学刊》1983年第2期)一文中对金代牧所的名称、数目及群牧布局进行了考证。程妮娜、史英平在《简论金代畜牧业》(《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一文中回顾了金代畜牧业的发展历史,并分析了女真畜牧由盛转衰的原因。乔幼梅在《金代的畜牧业》(《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中研究了金代畜牧业的饲养品种,分阶段探讨了金代畜牧业的发展状况,并就如何认识畜牧业在女真金国经济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第三,关于金代手工业。由于受史料等因素的限制,金代手工业研究一直是金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随着金代考古工作的进展,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金代手工作坊遗址及其产品,这为开展金代手工业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对出土金代文物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学术界发表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关于金代瓷器的探讨是金代手工业研究的一个热点。耀州窑、磁州窑、定窑是金代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窑场,学术界对上述窑场均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王长启的《金元时期的耀州瓷器》(《文博》1988年第2期),周丽丽的《耀州窑在五代、北宋、金三朝的历史地位》(《文博》1999年第4期),彭善国的《略论五代宋金耀瓷的流布》(《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段双印、王润合的《试论金元时期耀系瓷器的兴旺与普及》(《文博》1999年第4期),集中探讨了耀州瓷在五代宋金元时期的演变过程,分析了耀瓷的工艺特点和历史地位。李伟茹《金代磁州窑瓷器》(《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秦大树《金代磁州窑的繁荣及其原因探讨》(《考古学研究》五,文物出版社,2003年),对金代磁州窑的概况及繁荣原因做了认真分析。刘淼的《金代定窑瓷器的初步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第2期)以列表的方式详细统计了近年来金代纪年定窑瓷器及金、南宋非纪年定瓷的出土情况,并以这些实物为基础,对定窑瓷器中碗、盘、洗、钵等器物的形制进行了详细探讨。金代瓷器的整体研究方面,赵光林、张宁在《金代瓷器的初步探索》(《考古》1979年第5期)一文中详细开列了金代陶瓷制品的发现地点、器型及特征。冯永谦在《金代陶瓷摭谭》(《辽金史论集》第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7月)不仅对金代各窑场做了详细介绍,还提出了“金三彩”的概念。
关于金代的铁器制造业,李士良、田华著《黑龙江出土金代铁器的初步研究》(《黑河学刊》1990年第4期),对近年来黑龙江地区出土的金代铁器进行了认真考察。徐静波《小岭冶铁遗址和金代冶铁业》(《博物馆研究》1997年第3期)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对金代小岭冶铁遗址的状况进行了研究。张秀荣《简论女真的冶铁业与农业的发展》(《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1期)一文从各地发现的金代铁制农具入手,分析了金代黑龙江、吉林、辽东、中都等地的农业发展水平。胡绍增《冶铁业的发展与金代城堡的繁荣》(《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第17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回顾了金代冶铁业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冶铁业与金代城堡兴起之间的内在联系。黄秀纯、宋大川、陈亚州《北京金陵遗址出土铁器的金相学分析》(《北京文物与考古》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4年),使用现代仪器对北京金陵出土的铁器进行了科学分析。
关于金代的铜器制造业,目前学术界研究比较深入的是铜镜的工艺及款式问题。张英在《吉林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90年)一书中收录了吉林省出土的金代铜镜114面,那国安、王禹浪在《金上京百铜镜图录》(哈尔滨出版社,1995年)中收录了金上京出土的100面铜镜。学术界对这些铜镜进行了深入研究。王禹浪、李臣奇《金代铜镜初步研究》(《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吴顺平《金代铜镜纹饰》(《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2期),田华《金代铜镜的刻款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95年第3期),均对金代铜镜的纹饰、刻款、工艺做了深入探究。
二、关于金代货币
货币是建立发达商业的重要前提。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有金一代是令人关注的重要时期,其不分“界分”纸币的使用和法定银币的流通堪称中国货币史上的创举,同时,金代混乱的货币体系和金末的通货膨胀也为后代所诟病,基于这些原因,金代货币问题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系列对金代货币进行整体研究的论文问世,比较重要的有秦佩珩《金代货币史论略》(《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李世龙《试析金代币制特征》(《黑龙江民族丛刊》1999年第3期)、曾代伟《金朝金融立法述论》(《民族研究》1996年第5期)、吴剑华《金代通货膨胀略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乔幼梅《金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梁淑琴《试论金代的货币经济》(《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1期),不约而同地把金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同金代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极大地拓展了金代货币史的研究视野。特别是乔幼梅先生的论文,以翔实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研究了金朝120年间货币制度的演变过程,深入分析了货币制度对金代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堪称这一时期金代货币制度研究的代表作。
除此之外,学者们更多地开展了对金代货币的分类研究。
第一,金代铜钱研究。乔幼梅在《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一文中阐述了宋金双方争夺铜钱的手段和措施,分析了不同时期铜钱在宋金间的流向变化及产生这些变化的根源。乔文丰富了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中提出的“金人似乎有计划地吸收江南的铜钱”的观点。但也有一些学者对乔先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汪圣铎在《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以“关于铜钱争夺战”为题做了辨析,认为“所谓金朝争夺宋钱,大约主要是一些宋朝士大夫的主观猜测,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谓宋朝争夺金朝境内的铜钱,也主要是宋朝一些士大夫的设想,并没有成为宋朝的国策”。究竟这两种观点哪种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尚待学术界开展进一步研究。
近年来,关于发现金代窑藏铜钱的报道比较常见,大量金代窑藏铜钱的出现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王禹浪在《浅谈金代的窑藏铜钱及其货币制度》(《求是学刊》1984年第6期)一文中分析了金代窑藏特点,探讨了金代大量铜钱转入窑藏的原因。吴青云的《大连地区金代铜钱窑藏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1期)以大连地区金代窑藏铜钱为例,结合有关文献对金代窑藏铜钱的历史背景、原因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作了探讨。李东的《从吉林境内的金代窑藏铜钱谈当时的货币经济》(《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对吉林省金代窑藏铜钱的情况进行详细统计,并认为金代大量铜钱转入窑藏是当时货币经济乏力所致,其直接原因是政府推行限钱法。刘韫《金朝铜钱窑藏现象探析》(《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分析了金代窑藏铜钱的时代背景,总结了这些窑藏铜钱的分布、形式及内涵,探讨了金代铜钱转入窑藏的原因。
第二,金代交钞研究。虽然金朝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纸币的王朝,但却是最早使用不分“界分”纸币的王朝。金代的纸币——交钞以其在中国货币史上的特殊地位和繁杂的变化引起了金史学界的关注。刘森在《宋金纸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中对金朝纸币的种类、钞版及形制、纸币的禁伪与兑易、纸币的流通区域、纸币的发行、回笼及币值等问题做了详细考察,这是迄今为止对金代纸币进行的最完整研究。此外,穆鸿利在《关于金代交钞的产生和演变的初步探讨》(《中国钱币》1985年第1期)中分析了海陵王贞元年间产生交钞的原因,阐述了金代交钞的形制及演变。陈瑞台的《金代纸币制度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分析了金代发行纸币的历史条件,将交钞的演变划分为基本稳定期、膨胀初期和极度恶性通货膨胀期三个阶段。李跃的《对金朝流通纸币的一些看法》(《南方文物》2004年第1期)分析了产生交钞的社会背景,介绍了金代发行的几种主要纸币,认为交钞以其携带方便、流通灵活的特征促进了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尽管金代纸币在中国货币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但迄今尚未发现学术界公认的金代交钞实物,所幸传世交钞钞版弥补了这个缺憾,从而为研究交钞提供了可靠依据。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交钞钞版的论文主要有杨富斗的《山西新绛出土“贞祐宝券”铜版略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刘森的《金代小钞钞版初探》(《中国钱币》2006年第3期)、姚朔民的《金“圣旨回易交钞”版考》(《文物》2006年第6期),上述论文结合传世钞版深入研究了金代交钞的形制,有的还对钞版本身的真伪进行了考证,这对学术界进一步深化金代纸币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三,金代白银研究。金代的白银,史学界研究较多的一为银铤,一为“承安宝货”。近年来,黑龙江、内蒙古等地都发现了金代银铤实物。对此,李逸友著文《巴林左旗出土金代银铤浅释》(《中国钱币》1986年第1期),对内蒙古巴林左旗征集到的五件金代银铤进行了详细分析。周祥在《略谈金代银铤》(《钱币博览》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金代银锭根据铭文的不同分为贡银、税银、盐司税、地金银四种。王雪农在《有关宋金官铸银铤(锭)形制特点和等级标准的几个问题》(《中国钱币》2000年第1期)中认为金代的银铤除“承安宝货”以外,其形制完全与南宋银铤相同,其重量也与同时期宋朝的“五十两”银铤相同。
金代的“承安宝货”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第一次以白银为币材正式颁行的法定货币,是直接投入流通领域的白银。近年来“承安宝货”的出土与发现引起了史学界、钱币界的极大兴趣,董玉魁在《承安宝货五个档次划分的探讨》(《中国钱币》1986年第2期)一文中将“承安宝货”划分为一两、一两半、五两、七两半、十两五个档次,而月氏在《承安宝货五等之我见》(《中国钱币》1986年第2期)中将其划分为一两、一两半、二两半、五两、十两五个档次。王秀山的《试论金代“承安宝货”》(《辽宁金融》1987年第3期,“钱币专辑”)全面考察了金朝铸行“承安宝货”的历史背景,分析了“承安宝货”的形制和流通情况,并从“承安宝货”的发行过程中总结出金、银不可作为货币直接投入流通,单纯依靠币制改革不可能救经济危机的历史教训。
三、关于金代商业及其管理
金代是中国北方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有金120年间,商品交换日趋活跃,商业税收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国家对商业的管理日趋严密。近年来,一些学者撰文对金代商业及其管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武玉环的《金代商业述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4期)是较早对金代商业经济进行系统探讨的论文之一,她在该文中对金代的商业改革与商业管理进行了研究。王德厚在《金上京城市经济初探》(《北方文物》1993年第4期)中详细研究了金上京的商业发展状况,对上京地区的店铺街市、转运贸易、酒肆茶楼以及典当业进行了分析。林文益发表《金代的市场和商业及其与宋之间的互市》(《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对金代的市场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对金代的商业进行总体评价,认为金代的商业虽然有所恢复和发展,“但规模和水平远不如北宋时期”。岑家梧发表《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详细分析了金代女真人与汉、渤海、奚、回鹘等民族进行经济贸易往来的情况,强调了经济交流对促进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除了少数对金代商业经济进行综合研究的论文外,更多学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金代商业经济的某一侧面,它们包括:
第一,关于金代的度量衡。近年来,随着金代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陆续发现了一批金代权衡器,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对金代的度量衡进行了深入研究。高青山在《金代尺度试探》(《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第17册)中对目前已经发表,刻有确切年号的89方金代官印进行了详细测量,得出“金代的1尺长约合现在43厘米”的结论。刘俊勇、周家花在《金代自铭重量铜镜研究》(《北方文物》1998年第2期)中以目前所知的5面自铭重量铜镜为基础,对金代的重量标准进行了分析。阎万章在《辽东路转司三斤六两半刻款铜镜》(《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2期)中判定金代一两合38.165克,一斤则合610.64克。
第二,关于金代对外贸易。金代的对外贸易主要包括金与高丽、西夏、南宋的贸易。金与高丽的贸易方面,王崇时在《十至十二世纪初女真与高丽的关系》(《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中认为马匹、貂鼠、青鼠皮是女真与高丽贸易的主要品种。魏志江在《辽金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中认为金与高丽的贸易主要包括朝贡贸易、夹带贸易、榷场贸易、走私贸易四种形式。金与西夏的贸易方面,刘建丽、汤开建在《金夏关系述评》(《西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中谈到了金夏双方在经济上通过聘使往来,将各自名贵物资及土特产品作为贡品和贸易品输入对方的问题。刘建丽在《略论西夏与金朝的关系》(《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一文中谈到了金夏互市及使臣贸易的情况。
相比金与高丽、西夏贸易,史学界对金宋贸易的研究更为透彻。陈新权在《宋金榷场贸易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一文中详细分析了金宋双方榷场的建置情况,深入研究了榷场的兴废及职官设置,分析了金宋贸易的货物品种,考证了金宋榷场的收入情况。王则《宋金的经济文化交流》(《博物馆研究》1986年第3期)对宋金间的榷场贸易、走私贸易、使臣贸易进行了初步考察。靳华《宋金榷场贸易的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以宋金榷场贸易为核心,分析了双方设立榷场的目的,各处榷场建立的时间与地点、榷场管理机构及官员设置、榷场贸易中对物品的限制,进而指出政府强加给榷场的政治性始终制约着榷场的兴废,并使金宋榷场贸易呈现出不稳定性。靳华的另外一篇论文《试析宋往金界的走私》(《北方论丛》1993年第2期)则从宋朝的角度研究了宋金边界的走私原因、走私物品及走私途径和走私者的组成情况。
第三,关于金代的商业税收。刘浦江在《金代杂税论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中对金代的征榷税进行了分析,认为征榷税是金代财政的主要来源,其中尤以盐税为大宗,征榷税的缴纳方式则是均纳钱钞。此外,作者在论述金代杂税时,着重研究了商税、关税、市税、房税、地基钱以及金银之税的征收情况。吴树国在《试论金代的桑税》(《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金代的桑税来源于辽和北宋的桑税制度,金朝在辽宋基础上又提高了桑税在两税中的地位,并制定了专门的桑田制度。祁兵在《从金“茶课银锭”看金朝早期课税的发生》(《广西金融研究》1998年增刊)一文中分析了金代早期课税银产生的历史条件,介绍了金代早期“茶课银锭”的形制,认为“茶课银锭”是金代白银币制的先驱。
第四,关于金代的盐业经营与管理。郭正忠在《金代的盐使司与分司体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中首先对《金史·食货志》中关于盐使司的误记进行了考证,对大定年间盐使司机构变迁进行了详细梳理。其次,根据1974年陕西临潼出土的金代银铤,考证了安邑分司、滨州盐司、乐安盐司、辰渌盐司的设置情况。他的另外一篇论文《金代食盐业的经营体制》(《河北学刊》1997年第2期)还总结了金代的盐业经营体制。郭先生的这两篇论文,从盐业机构设置与盐业经营体制两个方面对金代盐务进行了详细研究,是金代盐政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王兴文发表的《金代盐业初探》(《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也对金代盐业资源、盐制、盐价、盐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金代盐课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年来,国外学者的金代商业经济研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日本学者高桥弘臣在《金末货币的混乱》(《史境》第19号,1989年10月)一文中分析了金末的纸币政策及其通货膨胀,并对铜钱减少,用银量猛增的情况进行了细致考察。另外一位日本学者井上孝范在《关于宋金榷场贸易的考察——盱眙榷场的榷场法与贸易》(《九州公立大学纪要》第18卷3号,1984年3月)一文中,着重分析了金宋双方在盱眙榷场进行贸易的情况。德国学者福赫伯在题为《金代的经济与财政》(《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2期)的学术演讲中分析了金代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状况,并对金代的税收与国家财政进行了初步研究。韩国学者金渭显在《高丽与女真的马贸易考》(《明知大论文集》第13辑,1982年)一文中对高丽与女真之间马匹贸易的数量、方式等进行了考察。
四、近三十年来金代商业经济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近三十年来,经过金史学界的不懈努力,金代商业经济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些进展集中地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金代商业发展的社会基础问题,学者们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并就金代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发表了一系列有颇有建树的学术成果,从而为我们从更深远、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研究金代商业经济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关于金代货币问题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在货币制度如何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乔幼梅的细致分析是这种突破的代表。在金代的具体币种方面,学术界对交钞的研究尤为深入,陈瑞台、刘森的相关论著引人注目,同时,刘森、郑恩淮等对交钞钞版的研究也颇具特色。在铜钱的研究方面,以东北学者对窑藏铜钱的研究最为深入。
第三,关于金代商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及管理方式问题,金史学界已经做了初步探讨,在金代商业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如榷场贸易、盐业管理等方面还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从而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近三十年来金代商业经济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明显,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在以往的研究中,“金代商业经济”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学者们只是把“金代商业”作为金代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而没有就金代商业自身的内容、特点、规律展开独立、系统的探讨,这就使得已有的研究远离金代商业的主题,显得过于分散和零乱。
第二,以往的研究着重对金代商业的宏观概括而缺乏对金代商业经济内部诸要素的细致分析,这就使得现有研究成果表面化有余而系统和深入性不足,至于根据金代商业不同时期发展的不同特点,进行定时、定量分析的著作和论文更为鲜见。
第三,以往关于金代商业经济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就商业论商业的水平上,而商业发展与金代政治变迁及社会进步的关系、商业发展与宋金对峙格局的演变等重大问题,学术界至今还未给予关注。
第四,以往的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学者完成的,因此,在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基本局限在史料考证与辨析等方面,研究方法比较单一。
基于上述认识,金代商业经济研究欲取得突破性进展,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深入开展金代商业经济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史料奇缺是学术界进行金史研究的最大障碍。在有限的金代史料中,商业经济史料更如凤毛麟角。因此,欲实现金代商业经济研究的突破,必须首先实现史料上的突破,这就要求金史学界进一步放宽视野,一方面从宋、金、元史籍中发掘更多的文字史料,另一方面,密切关注金代考古的新进展,力求从考古发现和传世金代文物中寻找新的线索。
第二,针对金代商业经济研究的薄弱环节重点突破。以往的金代商业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问题也相当明显,一些金代商业经济的核心问题,例如,商人群体的构成及作用、地位问题,商业组织内部的雇佣劳动关系问题,物价问题,政府的商业管理体系问题,或很少有人论及,或还处于空白状态。对此,金史学界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第三,借助经济学理论开展金代商业经济研究。近年来,借助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经济问题的佳作层出不穷,然而,金代商业经济研究还没有超越传统史学的治学方法,依然停留在史料排比和考辨的水平上,缺乏对商业经济内在规律的探索和把握。应该说,近年来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的许多进展,如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都为我们研究金代商业经济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金史学界如果能主动、自觉地学习这些新知识,以经济学视角对金代商业经济做重新审视,一定能够取得令人欣喜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