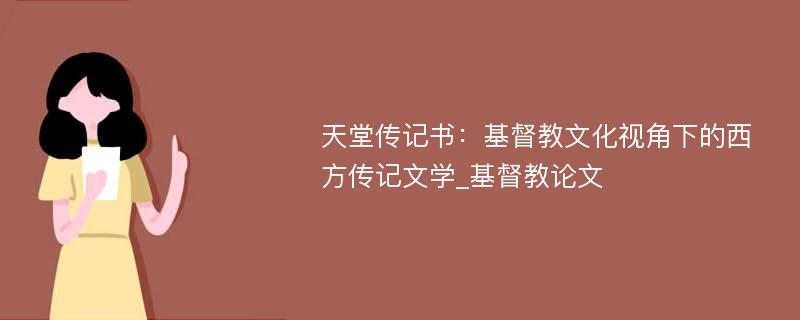
天上的“传记书”——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西方传记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记论文,基督教论文,视野论文,天上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10)06-0007-06
传记文学(auto/biography,或life writing)是古老而普遍的叙事类型。杨正润教授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古代的一些文类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以后就走向消亡”,而“今天传记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文类之一”;[1](P16)2001年出版的《传记文学百科全书》主编玛格瑞塔·乔利也发现:“现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神学、文化研究乃至生物学都在忙于对传记加以研究,试图解释人生为何变成了故事。”[2](Pix)在解释为何在我们这个时代传记如此重要时,乔利认为,这恰是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解释的焦虑”:
在现代之后的时代,人生故事需要以新的方式被加以解释。由资本所解放和重构的个人主义在沐浴了全球化和通讯革命的火焰之后,(传记)这种将个体生命塑造推向前台的文学写作似乎集中了这个时代的焦虑。……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对需要这种故事的需要进行探索,以确认或重新创造出已被生活过的人生指南。[2](Pix)
可以说,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对需要“传记”这种“人生故事”的需要进行探索,其深层动机正是来自于“人生”对“意义”进行解释的需要。对于这种解释,从传记实践与理论来说大体都可以辨认出两种方向:一种是基于世俗人性经验的自我解释、自我言说,或许可以不太恰当地称之为“自下而上”的解释。在这一方向上,传记作者通过“讲故事”(自己的故事和他人的故事)一方面“从经验建构意义”,不断拓展人生叙事形式的“库存”,另一方面也“将形式和秩序赋予经验”,①不断深化对于人生经验的理解。这一方向上的探索构成了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成就,也由此延伸出传记文学最重要的几个功能,如杨正润教授所概括的:人性的纪念、人生的示范和认知的快乐——传记“把人与人联系在一起,推动着人们的相互理解和人类之爱的实现”;传记“给读者一种示范和教训:人应当这样、而不应当那样去度过自己的一生”;传记所提供的是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全面的知识,这种认知“因为其充盈的人性而使读者感到温馨和满足”。[1](P191-218)
也正是在通往这一“自下而上”解释的边界处,另一方向即“自上而下”的解释的可能性出现了。②在自传《说吧,记忆》最后一章,纳博科夫甚至感到了这种“必须”的可能性:
每当我开始想到我对一个人的爱,我总是习惯性地立刻从我的爱——从我的心,一个人的温柔的核心——开始,到世界极其遥远的点之间画一根半径……我必须要让所有的空间和所有的时间都加入到我的感情中来,加入到我的尘世之爱中来,这样,爱的尘世边缘就会消散,就会帮助我去战胜十足的堕落、讥嘲与恐惧,在有限的存在中培养无限的感受和思想。[3](P8)
沿着纳博科夫所描画的那根延伸到“到世界极其遥远的点”的半径,我们或许能进入奥古斯丁这位西方自传传统的奠基者的视角,窥见他所看到的那卷“天上的传记”了。在《上帝之城》第二十卷,奥古斯丁解释了基督教《新约·启示录》。其中与本文的论题有关的是约翰的一段话:“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the book of life)。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新约·启示录:20:11-12》)
奥古斯丁注意到这段话中提到两类书卷,“另有一卷”是单独命名的。他接着以“天问”的形式对这段话进行了有趣而缜密的解释:
如果这本书是物质的书,谁能推算它有多厚多长?其中记载了所有人的整个生命,要用多少时间才能读?或者那时候是否有相当于人的数目的天使,每个人听到自己的天使唱诵他的生命?也许不是所有人共有一本书,而是每个人有一本书。……这本书应该理解为某种神力,使每个人回忆起自己做的事,无论好坏,让心志以惊人的速度浏览,知道后可以控诉或放过自己的良知,所有人中的每个人就可以同时被审判。[4](P196)
根据奥古斯丁的解释,这里的“生命册”也可以理解为“传记”(life),这一传记堪称“传记”的理想形式。每一个人都有一部这样的“传记”,可以是他传,可以是自传,也可以是“集合传记”中的一部。这样一部天上的“传记”被想象为包含着所有可能的人生经验,储存着所有的人生意义和形式、经验和教训;它是“某种神力”,又是可视可读的“书卷”,因此是名副其实的“生命之书”和“元传记”(“a life of all lives”或“The Life”)。虽然从理想悬设的角度来看,《圣经》是以“人言”的形式加以“符号化”了的或者“象征化”了的“神言”,但从基督教文化视角对西方传记文学进行探讨,作为“天上传记”之象征的《圣经》却是一个便利而自然的起点。
从传记史角度考察,西方传记文学虽然并非源于基督教,但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就与基督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成为基督教《圣经·旧约》的《希伯来圣经》中的“历史书”被认为“标志着传记的正式诞生”,[1](P2)而罗马后期出现的基督教更是“决定了西方文化、包括西方传记发展的方向。”[1](P66)《新约》开篇的“四福音书”与普鲁塔克、塔西坨和苏维托尼乌斯的传记作品一起标志着西方古典传记文学的最高成就,影响深远。在自传领域,基督教更对一种“深度主体性自传”(deep subjective autobiography)的发展有一种塑形作用。正如彼得·阿博斯所言:“与大部分古典作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旧约》常常表达一种激烈的个人渴望,这种渴望拒不接受任何世俗的调解和安慰。比如,《约伯书》和《诗篇》就表达了一种焦躁不安、源于灵魂内部的追求以及一种对于整全和拯救(wholeness and salvation)的热切渴望。在《新约》中对于心灵的关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和存在相关的期待和要求。在《新约》中,人对于生与死问题的急迫感赋予了以下问题以特殊的重要性:直接见证、直言不讳、外部行动的内部动机以及分享希望与狂喜的经验,这些都是在后世的自传中有待于发展出来的传统。”[5](P211)
《新约》的“四福音书”和保罗的书信在此应被特别提及。西方学者认为福音书可以看作是希腊罗马传记的一个亚类型即“辉煌行传”(aretalogy):叙述一个导师的事业,通常包括一系列奇迹故事,以此证明其超自然的能力,也被用于道德教诲,其叙述基调正是传统颂扬体传记(encomium biography)的赞美风格。[6](P104)传主的“死亡”对于他人的影响在这一类叙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福音书对于西方传记传统的推进也正体现在对传主“死亡”意义的深度推进。相对于苏格拉底的“我去死,你们去生。我们所去做的哪个事更好,谁也不知道,除非是神”,[7](142)耶稣“从死里复活”在福音书叙事里被确定为“更好”的“经验”和“知识”。这也决定了基督教的传记解释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自上而下”的视角。这一视角的确立对于西方传记文学的发展意味深长。
从对现代自传的回溯性理解来看,《新约》中保罗的书信可以说是最具有自传色彩的,也对西方自传叙事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他的书信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式的自我观念、自传冲动及深层动机都颇有启发。他在书信中“不仅详尽叙述了他的多次历险和遭遇,也揭示了他人格深层中的矛盾冲突的因素,一种身体需要和精神需要之间的分裂,这种冲突意志没有力量加以解决”,而且还显示出某种“远离外部形式的运动方向,以及伴随这一运动而来的对于忏悔和见证(confession and testimony)的坚持,就好像(或许有些矛盾地)没有这些外部的象征形式,那些内部的变化就失去了所有意义。在保罗这里,就好像自传行为本身即是(其精神意义)获得某种社会性证实的唯一方式”③。
此外,在自传叙事方面,我们在保罗书信中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某种“对比”模式,“这一模式显现在保罗被呼召之前和之后的生命之间的对比。这一模式和自传叙事的回溯模式很相近,在这一模式中,较早时期生命中的事件和活动的意义只有在回顾中才清晰地显示出来。”[6](P104)并非偶然的是,保罗的书信对奥古斯丁产生深刻影响并部分地促成了他最后的皈依,而正是奥古斯丁“将早期基督教所产生的自传冲动转变成如今许多学者公认的第一部重要的自传”。[5](P212)
随着基督教地位在西方社会的确立,“圣徒”成为新型“英雄”、“圣徒传记”成为中世纪西方传记文学的主要形式,并为世俗传记提供叙述规范。被称为“教会史”之父的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约260-339年)在其《教会史》[8]中勾勒了基督教在前三百年间的兴起状况,其中包含了耶稣、众使徒和殉道者的传记资料,和《圣经》中的相关记述一起,成为后世“圣徒传记”重要的叙事资源。亚历山大的阿塔纳修(Athanasius,约296-373年)写了被认为是“早期基督教圣徒传经典代表作”[9](P82)的《安东尼传》(Vita Antonii)。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历史学家比德(Bede,约673-735年)也是著名的圣徒传记作家,在其《英吉利教会史》中保留了不少生动的圣徒故事,他的《圣库斯伯特传》在欧洲家喻户晓,是典范的圣徒传。古英语基督教作家埃尔弗里克(Aelfric,约955-约1012)著有《圣徒传记》(Lives of the Saints,1002-1005),叙述了许多圣徒的事迹,传主范围覆盖英国和欧陆,还有一些是早期教会时期最古老的圣徒人物。
对西方圣徒传记及其对后世传记传统的影响,研究者一般都从现代“好”传记的标准出发给予负面评价,20世纪英国传记家哈罗德·尼科尔森就径直批评这一传记类型是“坏传记的源头”。[10](P17)稍后的唐纳德·斯塔弗尔也认为除了少数“伟大的例外”,如比德等人的作品(“在其最好的篇章里,圣徒融化在人里面”),大多数圣徒传记是“僵化的”,“由于原始材料的缺乏,少量的奇迹库存被一再重复,有时也对流行的传奇故事进行改编”,“和后世传记叙事的方法关系不大”。[11](P7)但他对自己的观点也有所保留:“在现代怀疑主义的视角和中世纪的轻信态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因此讨论圣徒传记若不能在一开始就先承认中世纪传记家的真诚,就会徒劳无获。”[11](P4-5)无论如何,圣徒传记发展出来的“模仿基督”的叙事模式一直延续到宗教改革时期的宗教传记,并为世俗传记的发展打上了鲜明的印记。圣徒传留给西方传记的文化遗产尚有待进一步解释和整理。在这一方面,威廉·詹姆斯对“圣徒性”的理解或可看作沟通中世纪传记和现代传记(或许也是中世纪人性和现代人性)的一个入口:“一切圣徒具备的人类慈善,以及有些圣徒的过度,都是真正创造性的社会力量,试图将原本只是可能的种种美德变为现实。圣徒是善良的创作者,是善良的添加者。人类灵魂的发展潜力深不可测。”[12](P257)有些吊诡的是,“在现代之后的时代”,圣徒传记传达出的人生意味竟像是“创新”的。
一般认为,从奥古斯丁《忏悔录》开始,忏悔成为“西方社会一个重要的价值准则和话语模式”,[1](P328)“忏悔录”则成为西方宗教自传或精神自传最重要的类型。据统计,奥古斯丁之后以“忏悔录”的名目出现的西方作品,“传世的估计在1 000种以上”,[1](P328)其中不乏名作。14世纪彼特拉克的自传性作品《秘密》(Secretum)采用了与奥古斯丁进行对话的形式。16世纪的特丽莎(Teresa of Avila,1515-1582)在其忏悔师的鼓动下写作了《忏悔录》。在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作家所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精神日记和自传叙述中,保罗和奥古斯丁的影响也很明显,其中以1666年出版的约翰·班扬的《大罪人沐浴神恩》(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最为重要。18世纪末的约翰·卫斯理推进了早些时候的清教传统,其追随者被要求定期写作日记,许多精神性自传自1778年就陆续在期刊《阿米尼乌斯杂志》(The Armianian Magazine,该刊在1798年更名为《卫斯理杂志》[Methodist Magazine])上发表。这些作品所塑造的“在世界内旅行、经受诱惑、追求神性、实现拯救”的“朝圣者”形象在其后乃至当代的精神自传和游记写作中仍若隐若现。[5](P212)
卢梭的自传沿用了奥古斯丁自传的书名,其《忏悔录》的开篇就大胆地站在了道德的至高处预想了末日审判的情形。颇有意味的是,他在此打算以自己写的这本“传记书”替代那部“天上的传记”:“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13](P1-2)从奥古斯丁到卢梭,西方自传“忏悔”基调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突转”,这种“突转”显得卢梭的《忏悔录》像是现代西方自传的一个寓言或缩影。
以鲍斯威尔《约翰生传》、卢梭《忏悔录》、歌德《诗与真》与富兰克林《自传》为标志,西方传记文学进入了现代阶段。现代西方传记文学的主体是世俗传记,注重真实性和对于传主个性的解释,基于卢梭式的自然人性观念的心理学在传记中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宗教改革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日渐世俗化的趋势相应和的是,传记中的宗教解释角度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述卢梭的《忏悔录》就是一例。这一点即便在“正统”的宗教传记领域也不例外。19世纪欧内斯特·勒南所著《耶稣的一生》就描绘了一个人性化的耶稣,此人笔下的耶稣会在十字架上可能想起“加利利那常使自己清新爽快的清泉、他憩息于其下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以及那些可能已答应了爱恋他的年轻处女们”,[14](P264)这一因“对事业的爱”而“受难”的“无可比拟的英雄、自由良心权利的奠基者”[14](P265)的耶稣形象看起来倒更像是罗曼·罗兰笔下的“名人”——或许在此就游荡着英国新传记作家斯特拉奇笔下“名人”的幽灵。
精神分析是推动20世纪西方传记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1910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达·芬奇及其童年的一个记忆》,精神分析心理学正式进驻西方传记。但在整体心理学框架内,基督教的符号/象征系统所提供的意义符号和象征仍为传记解释提供灵感,有时这种灵感反过来也会成为传记解释的结构性因素。比如,在弗洛伊德看来,在达·芬奇“秃鹫幻想”的背后有一个“圣母—基督”的幻想:在埃及神话中秃鹫只有雌性,他由此想像自己也没有父亲,母亲迎风受孕,生下自己,他借助这一幻想解释自己的神话般的命运;弗洛伊德有关摩西的传记研究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他要通过解释摩西来重新理解一神教及基督教,另一方面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他理解自己及精神分析命运的某种宗教解释框架:他将精神分析理论理解为一种新宗教——基督教的替代形式。再如,在埃里克森《青年路德》中,一方面传记家通过对传主心理历程的探索,用自我理想和身份危机解释传主,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使徒保罗的“皈依”模式在此一解释中的深度影响。又如,贯穿在艾德尔《亨利·詹姆斯》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兄弟竞争,传记家在此就借取了《圣经》中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大做文章,将基督教文化资源和精神分析结合起来,饶有趣味而不乏深度。此外,在现代传记和自传中,由《圣经》和基督教文化所构建的一些叙事类型或主题经由精神分析的整合也获得了更为细腻的表现效果,如“忏悔”叙事即是一例,在这一意义上又可以说,“宗教形式的忏悔发展出了我们今天一般称之为文学形式的自传,而在西方世界中那种不断被世俗化的、获得个人拯救的特殊欲望也演化出了今天对于发展个性的一般心理需要。”[5](P213)
在20世纪俄国著名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那里,和精神分析的传记解释框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看到了某种试图将心理学视角的传记解释纳入基督教总体框架中的努力。诚如刘小枫教授所说,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传记作品实际上是“圣灵降临”的叙事:“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主要著作大多是人物传记……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表现圣灵入驻人心时个体生命重生过程和灵魂斗争的痕印。传记实际就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神学论著——以象征主义手法描绘圣灵之国来临时的个体性痕印。”[15](P3)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一系列传记论著如《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路德与加尔文》、《诸神的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皆在“基督—敌基督”这一基督教神学总体视野中展开,既有对精神分析所关注的现代人性内部分裂这一共同主题的关注,又显示出迥异于精神分析传记的基于自然人性解释的解释路向和特殊深度。
但对于当代西方传记文学来说,基督教文化可以提供的更具启发性的资源或许来自当代神学解释学。经由后现代理论的冲击,传记的真实性问题、传记解释的限度问题、传记文类的边界问题、自传中再现自我的可能性问题都一再被追问,而如上所述,基督教文化中“天上的传记书”的悬设可能使得这些问题的深层结构被逼现出来。比如,奥尔森注意到,“有着优先权的、那个自传性自我的统一和连贯所需要的一个先决概念与圣经中那个统一和连续的上帝观念在结构上具有一致性,尤其当读者考虑到《创世纪》中上帝按(自我的)形象创造了人”,“这一有着特权的优先视角取得了某种有趣的效果,即赋予了某种话语以权威性,而无需对那种非如此接受就不能进入的经验进行证实和解释。正是由于这些共通性,先知和使徒的告白就承载了某种私密性的对于自我的揭示,这一自我是圣经与现代自我启示模式距离最近之处。”[6](P103)
但叙述角度的“同构”同时也彰显了叙述层次的差异,“最近”的距离也无法成为遮蔽最终“差异”的理由,这最终的“差异”就是“圣言”和“人言”的差异和分殊。由此而言,本体层面的“圣言”与作为圣言之符号化或象征的“圣经”有着差异,先知和使徒的告白与其所要揭示的“奥秘”之间有着差异,现代自我对其“私密”的解释与这个自我的“奥秘”之间也有着差异。在这诸多“差异”之间的空白处,神学解释学为自身也为人文学设定的任务恰是:“必须处理变化的语境对确定性意义的切近,必须找到理解的支点而无法逃向‘空白’”。[16](P240)
作为综合性的人文学科,传记应把“意义”置放在中心位置;作为现代传记/自传核心特征的“解释”,其深层“意义”也正在于恰如其分地“守护”传主/自我人生的“意义”。在这一命题中,“传记/自传的真实性”已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有意地淡化和刻意地强化或许都意味对“传记/人生(life)”边界的僭越。人对其自身而言始终是个“奥秘”,神学解释学要求“在确认人的有限性、语言的有限性和诠释本身的有限性的同时,确认‘奥秘’的真实性”。[16](P240)这也应是传记文学的追求。
注释:
①“从经验建构意义、并将形式和秩序赋予经验”的说法来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译文采自杨慧林《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建构”》一文,载《基督教文化学刊》第16辑·2006年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288-294页。
②杨正润教授在以司马迁为例论及“传记精神的极致”时对这一方向有所提示:“司马迁在悲天悯人,这是传记家‘究天人之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参看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74页。此处的“天人之际”就可以理解为“自上而下”的解释视角。
③Peter Abbs,'Christianity and Life Writing',Encyclopedia of Life Writing:Autobiographical and Biographical Forms.Londen/Chicago: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2001,p.212.保罗书信中的自传叙述这种近乎“强迫性”的“辉煌”行为在20世纪剧作家和小说家塞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那里可以找到一个对比性极强的“黯淡”版本:“他们全都同时说话,而且都跟自己说话。……他们谈他们的生活。光活着对他们说来不够。他们必须谈起它。”参看袁可嘉等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三册(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译文有改动。
标签:基督教论文; 奥古斯丁论文; 圣经论文; 自传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基督教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人物传记论文; 忏悔录论文; 圣徒论文; 新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