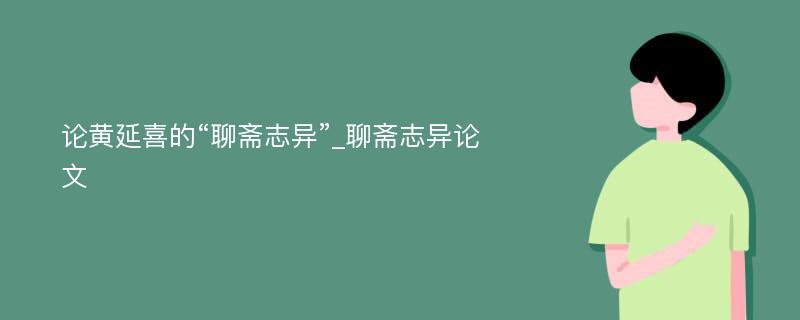
谈《聊斋志异》黄炎熙抄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聊斋志异论文,抄本论文,黄炎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02)03-0005-04
一
《聊斋志异》刊行前的传抄本今存数种,黄炎熙抄本是其中的一本。此抄本卷之一内封题“聊斋志异”,“榕城黄氏选尤”,各卷目录页均题“古闽黄炎熙斯辉氏订”。所以,现在学人称之为黄炎熙抄本。
此抄本原为成都刘氏所藏,后归华西大学,现藏四川大学图书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该校图书馆馆长赵卫邦教授惠赐此抄本之复印本一部,故得以目睹其书。多年来,我每次检阅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遥念赵先生惠助之恩泽。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林名均先生曾著文云:“全书既然在乾隆之末始有刻本,则此书必为尚无刊本之前抄写,因为全部抄录不易,故仅择其尤者。成都龚向农先生,博学耆旧也,尝鉴定本书所用之纸,确为雍正时物,是此书或当为雍正年间之所抄写。”[1]然按之其中文字,如《五通》“有赵弘者”,“弘在门外设典肆”,《齐天大圣》“穷极弘丽”,“弘”字均缺末笔;《辛十四娘》“漫检歷以待之”,“歷”字作“历”,是则避乾隆讳,当抄于乾隆年间或稍后,不可能是雍正年间抄本。
此抄本首卷无抄主题识,缺末卷亦不知有无跋语,难于考察抄主黄炎熙及其所据底本来源。兹检索《闽侯县志·选举志》“清贡生岁贡”栏中有黄炎熙之名,下注“侯官人”。紧跟其后者为蔡容,名下注:“俱乾隆年。”[2]据此可知黄炎熙为福建侯官人,乾隆间岁贡生,其《聊斋志异》选抄于乾隆年间,也当无疑问。又,《闽侯县志·文苑上》有蔡容小传,也提供了黄炎熙所据底本的信息。小传云:“蔡容字惟英,号于麓,成童读其家藏书,益从其邻陈县令家借读郑方坤所寄书,数万卷。”[3]郑方坤即《聊斋志异》青柯亭刊本卷首赵起杲《弁言》中所说郑荔芗,他编刊的《聊斋志异》所用底本,就是抄自郑方坤家藏所谓得自淄川蒲氏家的原稿。郑方坤,号荔芗,福建建安人,从乾隆四年(1739)年,先后官山东登州、武定州、兖州四州知府,长达十六年[4]。他性喜博览,留心诗学,著有《蔗尾集》、《经稗》、《五代诗话》等,《清史稿·文苑一》有传。他在山东做官期间,自然会听人说到蒲松龄写了《聊斋志异》一书,当时的王渔洋曾评点其书,他也会有兴趣、有条件从淄川蒲氏后裔家中抄录出一部来,只不过不会是蒲氏原稿本罢了。蔡容既可以从陈县令家借读郑方坤所寄放的许多书,那么,与之同时同里同为府学中人的黄炎熙,也是当或直接或间接地得读郑方坤的书。在青柯亭刻本刊行前的乾隆年间,福建恐怕只有郑方坤从山东带回的一部《聊斋志异》的全抄本。黄炎熙借得这部抄本进行选抄,是极合情合理的事情。这从后面对黄炎熙选抄本考察中,还会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二
要知道这部选抄本的性质及其所蕴含的价值,首先要做的是将它和蒲氏手稿做一番对照。现存蒲氏手稿本已残缺,仅有全书之半,不存者以直接据手稿本过录的康熙抄本代之,是理所当然的。应当说明的是,手稿本虽然已装订成册,却多数没有标明册次,现存四册之影印本的册次,是依据《聊斋志异》铸雪抄本排定,不代表原本的册次。康熙抄本也仅存四册,另有拆散的两小册。康熙抄本和手搞本互有存佚,两者共存者有两册,此有彼无者各两册,康熙抄本有一小册首行首格有“聊斋志异”四字,无疑为另一册之首,亦可供参照。所以,在与此分卷之选抄本一一对照时,只好以手稿本或康熙抄本各册之首篇题目表明是哪一册,两者并存的两册,仅出手稿本之名。
此选抄本原为十二卷,今卷之二、卷之十二已佚失,仅存十卷。下面依其卷次,一一对照其所收录篇目。
卷之一:篇目依次是手稿本《考城隍》册中的《考城隍》等十六篇,康熙抄本《董公子》册中《巩仙》等九篇,手稿本《刘海石》册中《驱怪》等十篇,共三十五篇。三个部分的篇目次第,与手稿本或康熙抄本中大体一致。
卷之三:居前的是康熙抄本《某公》册(小册)中《苏仙》等八篇,其后是手稿本、康熙抄本并佚的《西僧》等九篇,再后是手稿本《刘海石》册中的《青梅》等四篇,最后是手稿本《鸦头》册中《窦氏》等三篇,共二十四篇。四个部分的篇目次第,除《西僧》等九篇外,亦与手稿本或康熙抄本大体一致。
卷之四:居前的是手稿本《鸦头》册中《马介甫》等十八篇,篇目次第大体一致;后面的《吴门画工》、《仙人岛》、《乐仲》、《三仙》等八篇,系零散地选自不同的册次。共二十六篇。
卷之五:全部为手稿本《云萝公主》册中自《阿纤》以后的二十篇,顺序完全一致,没有弃而不录者。
卷之六:前面是手稿本《刘海石》册中自《狐谐》以后的十四篇,中间窜入已经证实的非蒲松龄所作《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三篇[5][6],其后为康熙抄本一小册中《侠女》三篇,最后是手稿本、康熙抄本均佚的《张诚》等四篇。实为二十一篇。
卷之七:从首篇《刑子仪》到《王生》,手搞本、康熙抄本均佚,最后《新郎》、《成仙》载康熙抄本《王者》册。共二十六篇。
卷之八:居前是的手稿本《刘海石》册开头的五篇,其后的《王桂庵》等二十一篇,手抄本、康熙抄本并佚而不存,共二十六篇。
卷之九:首篇为《云萝公主》,末篇为《胭脂》,正是手稿本《云萝公主》册的前面小半部分,中间仅缺《王货郎》、《牛同人》,凡二十篇,篇目顺序完全一样。缺《牛同人》事出有因,手稿本中此篇已残半页,此选抄本之底本,便大概没有抄录。
卷之十:全部为手抄本《鸦头》册之前三十三篇,篇目顺序完全一致。
卷之十一:主体是康熙抄本《董公子》册之后半部分,中间有未录入者,凡二十篇。此部分之前有《香玉》等五篇,之后有《僧术》第六篇,是手稿本、康熙抄本并佚而不存者,共计二十九篇。
通过上面所做的篇目组合情况的对照,对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此选抄本现存的十卷,不包括窜入的三篇非蒲氏之作,总计为二百六十篇(注:这263篇,包括《局诈》之《又》、《又》,和在其它抄本中作为《单父宰》之附则的《王生》。)。若假定已佚的两卷亦如其它卷的篇数,约共五十篇左右,此选抄本所录入的篇数约为三百多篇,相当于《聊斋志异》全书的五分之三。
此选抄本与手稿本和康熙抄本,在总体面貌上有较大的差异。此选抄本已做了卷次井然的分卷,各卷所录的篇目,有的是全为手稿本和康熙抄本某一册的篇目;有的则是分见于某二、三册里的篇目;有的两卷为手稿本或康熙抄本同一册的篇目,如卷之四、卷之十的篇目同为手稿本《鸦头》册(康熙抄本亦有此册)的篇目,是将其分作两截子分别装入两卷中,但卷之四收录的是《鸦头》册后半部分的篇目,卷之十收录的反倒是前半部分的篇目。此抄本扉页既然题作“榕城黄氏选尤”,那么分卷、篇目安排,也该是其人所为,而非其所据底本即如此。
此选抄本虽然其总体面貌与手稿本和康熙抄本大异,但各卷或整卷或局部的篇目次第,还基本上与手稿本和康熙抄本是一致的,只是有的有所遗而不录。这表明黄氏所做的不是像《聊斋志异》十八卷本那样,打乱全部篇章,另行以故事性质分类;也不是像青柯亭本那样,先选出精华,分作十二卷,尔后又觉得其余篇章弃之有“半豹得窥,全牛未睹”之憾,又增选了后四卷(注:鲍廷博《刻〈聊斋志异〉记事》:“初先生(赵起果)之梓是书也,与蓉裳(余集)悉心酌定,釐为十二卷,子第任雠校之役而已。今年正月,晤先生于吴山之片石居,酒阑闲话,顾谓余曰:‘兹刻甲乙去留,颇惬私意,然半豹得窥,全牛未睹,其如未厌嗜奇者之心何?取四卷重加釐定,续而成之,是在吾子矣。’予唯唯。后五月,十二卷始蒇事,而先生遽卒。未竟之绪,予竭蹶踵其后,一言之出,若有定数。”),而是不无随意性的剪截和重新拼合,从其中看不出黄氏有什么特别的用心和预定的体例。
三
此选抄本文字的情况,须要与手稿本进行校勘,方才能获得认知。那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情。我的学兄任笃行,曾经用了数年时间,汇集早期抄本、青柯亭刊本,与手稿本做了全面的校勘,“校记”附于其《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7]各篇之后。为了节省气力和行文方便,取其手稿本与此选抄本共有的四十篇之“校记”,做异文数目之统计,以看出此选抄本与其他几部抄本的差异。康熙抄本已确定系直接依据手稿本过录的,其优越性自不待言,这里就不列在其间。
此选抄本卷之一前十篇为《考城隍》、《瞳人语》、《山魈》、《咬鬼》、《王六郎》、《种梨》、《劳山道士》、《狐入瓶》、《妖术》、《叶生》,均载于手稿本第一册。持此十篇同易名异史的抄本(简称异史本),铸雪斋抄本(简称铸本),二十四卷抄本、青柯亭刻本(简称青本),与手稿本校勘异文分别是56处、55处、77处、40处、64处。
此选抄本卷之六前半之《狐谐》、《妾击贼》、《小猎犬》、《辛十四娘》、《白莲教》、《双灯》、《泥书生》、《寒月芙蕖》、《武技》、《秦生》,均载于手稿本《刘海石》册。将此十篇同异史本、铸本、二十四卷本、青本,与手稿本校勘,异文分别是31处、37处、125处、142处、37处。
此选抄本卷之十前半之《酒虫》、《狐梦》、《布客》、《农人》、《武孝廉》、《孝子》、《狮子》、《阎王》、《土偶》、《土地夫人》,均载于手稿本《鸦头》册。将此十篇和异史本、铸本、二十四卷本、青本,与手稿本校勘,异文分别是37处、31处、67处、55处、48处。
此选抄本卷之五后十篇为《葛巾》、《黄英》、《书痴》、《齐天大圣》、《青蛙神》、《青蛙神又》、《任秀》、《冯木匠》、《晚霞》、《白秋练》,亦为手稿本《云萝公主》册之最后十篇。将此十篇进行校勘,此选抄本、异史本、铸本、二十四卷本、青本,与手稿本的歧异,分别是69处、64处、158处、85处、64处。
这四组的情况虽稍有差异,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此选抄本、异史本与手稿本文字上较少异文;青本虽为经过重编的刻本,与手稿本文字上的差异仍然不算多;而二十四卷本、铸本则异文较多。还应当补充说明,铸本与手稿本文字上还不只是有字词的不同,有的一句或数句也经过删简,那就不是抄写中的脱、衍、误、倒,而是抄主自行删改了。
从任笃行先生的“校记”里,还发现了一种情况,就是这五种本子的异文,不少的是并非某本独家所有,而是为两三本所共有,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异史本、铸本、二十四卷本异文多一致,此选抄本,青本异文多相同。如《考城隍》校出异文有九条,其中异史本、铸本、二十四卷本异文一致者有三条,此选抄本、青本异文相同者二条;《种梨》校出异文有十二条,其中异史本、铸本、二十四卷本异文一致者四条,此选抄本、青本相同者三条;《叶生》校出异文凡二十五条,异史本、铸本、二十四卷本异文一致者六条,此选抄本、青本异文相同者八条。特别是有的篇目,如手稿本中作《妾击贼》、《驱怪》、《胡四相公》、《木雕美人》,异史本、铸本、二十四卷本均作《妾杖击贼》、《秀才驱怪》、《胡相公》、《木雕人》,此选抄本、青本与手稿本相同。由此可以推断,异史本、铸本、二十四卷本同出自某一现已不存的更早的抄本,此选抄本、青本则是同出自另一部抄本。现已知青本主要是依据郑方坤得自淄川蒲家的抄本编刻的,此选抄本之抄主黄炎熙与郑方坤同时同里,也有机会看到郑家的藏书,至此,便完全可以肯定此抄本是依据郑方坤的抄本选抄的。此选抄本何以文字上与手稿本异文较少,较其它三部抄本更接近原稿,由此也可以得到解释了。
四
此选抄本虽然在总体编次上与手稿本差异较大,但被拆开了的局部的篇次,大都还与手稿本保持着一定的一致性。所以,由此选抄本亦可以大体上返观其底本郑方坤抄本的情况,只是由于缺少了两卷,会有些看不到的地方。
从前面各卷所收篇目的情况看,卷之一是以手稿本《考城隍》册的篇目为主体,因为卷首有诸家序,故此选抄本一如其它抄本,置为首卷。卷之四和卷之十相合,即为手稿本《鸦头》册之主要篇目,只是前后部分颠倒了。卷之五和卷之九相合,即为手稿本《云萝公主》的主要篇目,前后部分也颠倒了。卷之六是以手稿本《刘海石》册的篇目为主体。卷之七和卷之八,除去部分篇目,合起来则为手稿本和康熙抄本并佚的、研究者断为《夜明》册的主要篇目。卷之十一是以康熙抄本《董公子》册后半部分篇目为主体。这种编排与青本前十二卷重在选优而过多的打乱了手稿本篇目次第的情况不同,它像似只就手稿本做了分割和重新组合。此选抄本与青本的不一致,可以认定两本的底本原非如此,而是各自的编选者所为。依此可以推想,如果作为底本的郑方坤抄本不是保存了手抄本的面貌,如分册而不分卷,有标明了“一卷”之《考城隍》册,还有以《鸦头》为首篇、以《云萝公主》为首篇的各册,此选抄本何以会是现在这样子?再具体一点的说,如果郑方坤抄本不像手稿本那种样子,此抄本何以会是卷之一、卷之八、卷之九、卷之十,都如手抄本那样分别以《考城隍》、《刘海石》、《云萝公主》、《鸦头》诸册之首篇为首篇,而且卷之九、卷之十竟全为《云萝公主》、《鸦头》册里的篇目,篇次也一致?此选抄本编定卷次之随意,岂不是正反映了郑方坤抄本亦如手稿本那样分装成册,却基本没有标明册次的情况,此选抄本卷之十一以康熙抄本《董公子》册后半部分篇目为主体,卷之一中又有《董公子》册的八篇,可推知郑方坤抄本必当有此一册,手稿本也当有此一册,只是佚失了而已。如果此选抄本没有佚失卷之二、卷之十二,那将还会看出一些问题,更有助反观郑方坤抄本,乃至手稿本已佚半部的状况。
此选抄本卷之六有《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三篇,为《聊斋志异》所有抄本、刻本所未收。现已经研究者考出,均系误置入的非蒲松龄的作品。《猪嘴道人》原载《夷坚志补》,《张牧》原载明《广艳异编》,《波斯人》原载宋濂《宋学士文集·录宾语》[5][6]。这三篇均未为青本所载,那么,十之八九是此本抄主自己误置入的。
收稿日期:2001-0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