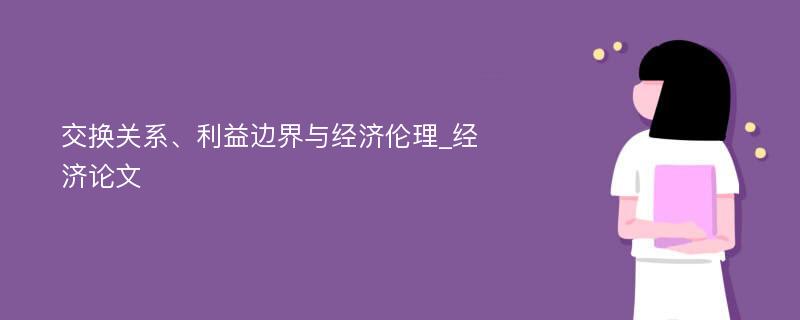
交换关系、利益边界与经济伦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界论文,伦理论文,利益论文,关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经济在体制上同计划经济相比,最大的差异性是建立在广泛分工基础上的交换关系。交换,首先是利益互换目的下两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契约。在交换过程中双方对自己的利益边界、成本费用、收益等都要进行小心的界定。然而当交换的市场制度被广泛地建立起来以后,交换就在双边乃至多边产生出外部效应,由此构成了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经济伦理冲突内容。
一、交换并不在任何时候都促成双边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增进
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交换方式配置资源替代了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的组织内部配置资源方式,这使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方式和利益安排上有了全新的意义:市场是一种利益契合机制,交换是一种利益组合过程。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颂扬市场交换制度时,有二个基本理论信念:第一,在交换中追求各自利益的经济主体可以达到双方利益的共同增进。因为交换使双方付出自己不太稀缺的物品,获得更为稀缺的物品,稀缺程度差异使交换活动产生,并使双方同时获益。第二,全社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都通过交换而得到增进,可以自然合成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增进结果。斯密的分析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进入交换和生产的经济主体都是自利的理性人,通过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每个人(或经济单位)都小心维护自己的利益边界不被侵害,或成本小于收益状况下的利益增进,那么社会总收益一定增进。如果要说存在某种公共利益的话,斯密认为社会总利益的增进就是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公共利益了。
然而斯密的信念受到了阿瑟·庇古的挑战。阿瑟·庇古在他的《福利经济学》(1920年)中提出两点对抗性看法:第一,斯密把交换看成是双方纯粹自愿状况下的行为,这种没有干扰和纯自由竞争的市场交换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交换双方在地位上可能不对等,某一方可能会利用某种垄断优势(信息、资本或规模经济等方面)对另一方进行利益侵害。第二,交换双方的私人利益增进也可能以损害第三方乃至整个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阿瑟·庇古的分析不仅指出了亚当·斯密颂扬的自由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更提出了在交换行为的同时,产生着一系列非道义的经济行为。诸如借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欺诈的交易行为,借助垄断压榨性交易行为,借助产权制度不明晰(林木起火的责任边界不清)的私人成本外溢性交易行为,都是一种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行为。
一般地说来,经济行为的目的性原则同伦理观念的价值判断原则有很大差异,经济学讲最大化为目的,讲效率、讲利益、讲最小投入获最大产出,伦理学讲仁义、讲善心、讲崇高奉献、讲公正廉明、克己奉公。经济学以人是“经济人”的假定为前提,进行理性选择,伦理学则以“社会人”的假定为前提,讲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体,人除经济利益倾向外,还有亲情、友谊,还有崇高感、仁义心。然而,事实上经济学的分析从来就没有完全彻底地抛弃伦理价值判断,没有排除利益与道义的协调性要求。正因为如此,亚当·斯密的信念基础仍然是不损人前提下利己,或交换双方乃至全社会在经济交换中利益增进。阿瑟·庇古对斯密的批驳也是指出斯密的这个道义性伦理学基础是不成立的,从而斯密经济学便有了重大的缺陷。因此经济学的分析都在寻求自己的伦理学基础,经济行为的合理性不仅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方面,还在于能否符合共同获益,至少不应损人利己的伦理学原则。例如著名的经济效率原则:帕累托最优境界,也是将边界界定为“每一个人的利益增进不得以减少他人利益当代价”的标准上。
二、界定利益边界:现代法制和经济伦理共同功能
现代市场经济交换是普遍的行为,显然外部效应也必然普遍存在。交换关系在增进人们利益的同时也在制造利益冲突,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非道义行为因交换而蔓延。
在自然经济时代,人口的稀少加上非交易性经济活动,人们对生产的需求十分有限,竭泽而渔、过渡放牧等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的情况并不多见,除非战争或自然灾害之后一般情况下人们少有无限扩大生产产量的动力。然而到商品交换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以后,以交换为目的生产,使生产的需求空间骤然放大,人们也被市场诱发了更多的贪婪,将一切可能进入交换的产品和资源都投入市场,换来可供自己享乐的产品和服务,甚至还在货币产生后期望积累一笔财富以供自己享用,作资本或供子孙享用。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交换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拓展,进入到交换关系最为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以后,产权观念、利益边界观念以及对交换行为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性的约束要求,都被呼唤而出。交换大大扩展了生产和消费的空间,从而大大增进了人类的福利,人们享用了远远超过自己所能制作、所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并且人们为了扩大交换,就必然扩大生产,而为扩大生产则努力改进技术,扩大分工,使劳动生产率因分工和技术进步而迅速、有效地提高,从而使生产产量和消费的使用价值量大大增加。当然社会在交换与分工的扩大同时,产量与消费量扩展也导致了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扩展,人们将不该进入商品的许多资源和物品等也拉进了商品范围,目的自然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及福利。奴隶买卖、假冒伪劣品,对他人侵害下的交换,甚至某些人际关系(亲情、友谊)也商品化、市场化了。
现代社会针对这些经济上非道义的交换行为自然不再会像以往的封建制那样去“抑商”,用取消交换的方式来消除经济领域的非伦理现象,而是发明了制度和法律。用制度来规范人们的交换行为,用法律界定人们在交换中应有的权利与义务。当人们有了交易规则和产权制度时,非道义行为和外部性效应会受到约束,人们的利益边界与权利边界得到有效的界定和保护。
很显然,人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离不开制度的约束和保护。尽管经济原则背后也有伦理的标准,“不损害他人利益前提下增进自我利益”是效率的标准,然而道义的约束是软约束,是有可能被甘愿堕落、良心泯灭之徒冲破的。人们发明了制度和法律,用强制方式将冲破道德樊篱的行为加以规范,将外溢的私人成本重新内部化,将被冲破的道德之网重新修补起来。可见,制度与法律的基础依然是道义,消除交换中的利益冲突,协调交换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克服外部效应,正是市场经济下最为重要的法律服务内容。
另一方面,道德规范的功用同法律制度一样,都在恪守某种契约,反对违约行为。一般说来,“舍己为人”、“克己奉公”被看作美德善行,“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被看作道德劣行。因此,即使法律制度还没有界定某种外部性行为是否违法时,其在道义上已经被判定为劣行了。所以,道义与伦理观念的建立,其目的也在于界定利益边界,将利益获得的边界和成本承担的边界对等起来。很显然,在道义上首先是反对外部性效应的,人们在一切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上或自己良心层面上订立着道德契约:自己在利益边界上是清晰的,即为人是清白、正直的,或是乐于助人、勇于奉献的等道义形象。这种形象不仅需要在自己内心树立,而且还希望得到公众社会的认可。每当人们陷入这种道德违约境地时,只能有以下三种选择:或尽快扭转这种不清晰的利益边界局面,修正自己的道德形象;或有意掩饰自己对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边界的侵害事实,以取得自我形象与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的一致性;或降低自我道义形象(良心泯灭、自甘堕落)来平衡这种已经发生的成本利益边界不对称。
由此看来,法律与道德的功用是一致的,只不过一个以强制方式出现,一个以软约束的意识形态出现。二者的作用是互相补充的,这是因为,虽然现实中经济活动的外部效应是普遍存在的,但消除外部效应的法律制度无法完全对等地存在。法律制度虽有强制性的优势,但显性的操作成本较高,倘若消除外部性的收益大于外部效应形成的社会成本时,相应的法律制度安排才会出现。这样也造成制度约束是有限的,而道义形象约束则是广泛的。
三、中国当前经济领域中的道德困惑及对策
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在经济增长上取得了明显的成就,改革,增进了资源配置效率,但利益矛盾与冲突也在加剧。经济领域中的道德规范一再被冲破,有人为了扩大自我利益边界不惜损害别人利益。这表现在多方面:商品制造中的假冒伪现象、企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经济活动中的欺诈行为、产品宣传上的虚假广告等。这些似乎都呈现着市场化改革与道德困境有着直接的负面关联性。
经济领域的道德失范行为不论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规模上都有蔓延的趋势,影响面显然也不止于经济领域,在社会人际关系上出现金钱化、交换化现象,在政治领域的寻租、受贿现象,以及冲破管理制度的贪污公款、挥霍性公款消费,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公害”。针对这些现象的判断,有“代价说”,认为市场经济取得的经济增长收益已大于道德失范给人们带来的损失,两者相抵收益是正值的,这是经济发展初期的代价(成本)之一。也有“双重效应说”,认为市场经济是双刃剑,市场制度把独立人格、自主、自由、权利等现代人的道德倾向带给社会时,也把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极端利己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种子播撒开来了;另一方面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体现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交易也因此得到广泛的拓展,市场由此而活跃起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同时带来了整个经济活动乃至社会活动的功利主义倾向,交换价值概念不断在外延上扩展,以至于排斥了社会伦理价值、人文道德精神应有的位置。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人们有一种把市场交换原则扩展到一切生活领域的倾向,不仅吞没了经济生活,而且在个人家庭生活、公共政治生活领域也充斥着交换价值的发掘行为。交换化、金钱化的泛市场行为不仅使整个社会陷入道德失范,而且在加速形成一个非伦理化的社会环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自我中心论使传统的道德是非观念在动摇,人们陷入“道德困惑”之中。
这种“道德困惑”其实正与人们在观念上和现实生活中的两个边界不清有关:第一,经济伦理与经济原则的混同。经济伦理应定义为在经济活动领域的伦理规范,特别是交换关系中的伦理准则。有一种观念上的误解,认为经济原则是同伦理原则相应的,经济原则讲功利性、讲利益、讲商业价值(交换价值);伦理原则讲精神价值、讲友善、讲仁义。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潮流下,经济发展必然迫使伦理原则让出空间,道德失范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代价的说法,便是这种观念误解下的推论。事实上并没有纯粹的不受任何伦理约束的经济原则,例如我们前面讲到斯密对交换关系中交换双方利益增进以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的信念,以及阿瑟·庇古对斯密信念的驳论,都是以“个人利益增进不得以他人利益减少为代价”的帕累托标准为基础的,而帕累托这种效率最优境界显然也是一种伦理规范。只不过经济伦理不可完全等同于社会伦理,它只是以不损人为前提来利己,这在社会伦理规范中是起点的范式,不是较高的范式,甚至不能是普遍的范式。如“不损人而利己”无法推及到亲友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的伦理关系上。第二,经济伦理与社会伦理的混同。倘如经济伦理是将经济领域的生产与交易活动进行利益边界界定,将交换的双边及多边利益边界加以约束,那么经济伦理与社会伦理有共同出发点。然而二者又有层次上与外延范围上的差异性,在经济领域讲求机会平等、效率优先、责任感、信誉开拓精神等,在社会领域则需要讲同情心、公益心、利他主义、奉献精神、高尚人格等。不应模糊这两个领域的边界,将经济领域的交换原则、金钱效率原则推行到社会领域是一种道德失范,也是一种经济原则的误用。但我们也要注意,把社会领域才适用的奉献精神、同情心等伦理标准拿出来对经济活动作价值判断,由此认定道德的失范,这种错位的价值判断不仅使思想上陷入困惑,也会延误了经济正常发展。准确的划分原则应当是,经济伦理是对“经济人”行为的一种道德规范,社会伦理是以“社会人”的道德规范,二者是不能互用的。
针对上述“道德困惑”除了将错位的观念纠正过来以外,还应当采取以下对策:
1.保障相关的法律制度供给与政府服务。经济领域的外部效应(私人成本社会的溢出转为社会成本),主要的对策应是将市场运行规则、交换规则法律化。法律制度与道德规范是共同防守向他人利益侵害的两个卫兵,倘如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那么势必给道德留下过重协调利益边界的负担,道德防线便也变得缺乏支撑,势单力薄,极易被突破。法律的供给者是政府,政府提供的法律服务正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在假冒伪劣产品面前,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是由政府提供技术准则和计量监督服务。因为私人要打“假”、“认假”不仅缺乏权威性,而且要让每一个消费者掌握市场上无数产品的技术性能标准显然是不现实的。对消费者来说,与其花费过多的“学习成本”(识假技术),不如纳税给政府聘用技术专家,提供公共“打假”服务,更经济合理。
当然,用制度来约束交换关系及经济行为中的利益边界派生的一个重要对策便是:对市场监督者的制度约束,否则会引发公共生活领域的非道义行为蔓延:寻租与受贿。
2、教育功能的泛化。一个社会越不成熟,文明程度越低,越会认为上学、读书是小学生的事情。而一个社会越文明有秩,受教育越成为一种全民族无论老少尊卑共同的行为,文明需要土壤,教养靠一种泛化的教育氛围熏陶。教育的功用不仅仅在职业技能的培养,教育人们去理解一种人文精神,一种文化价值,去感悟不同人生境界的差异,应该是更为本质的一面。
3、人格完善的价值追求。道德形象的完善应成为一种社会趋同的价值判断,人格高尚的寻求,完善的人格形象对人们行为模式应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对社会关系的协调会起到良好的效果。社会,特别是政府和社会团体,应营造一种氛围,熏陶一种思想,塑造一种道义形象,对社会将起到一种感召作用。50—60年代成长的人们难以忘怀像“保尔·柯察金”这样的人格形象,虽然人们做不到像保尔那样献身,但人们心目中保尔永远是个高尚的角色,想到他的名字便会发出“崇高感”。尽管人们在经济领域不会也不可能去实践这种崇高感,但这种崇高的人格感召力同样会让人们心灵深处筑起一道警戒线,决不轻易翻越道德的樊篱,即使在追求最大化利润时,也应恪守好自己与他人的利益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