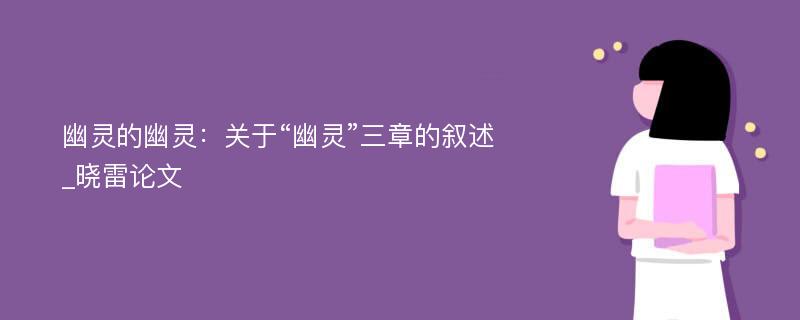
鬼子的“鬼”——说说鬼子三部中篇的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鬼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鬼子有些“鬼”。这有点像废话。鬼子不“鬼”,他就不是现在的鬼子了。在我的方言区域,说什么人“鬼”,没有丝毫的贬意,而是表达他有本事、有才华、有智慧等等诸如此类的意思。在这些字眼前面加上一个“鬼”字,说这个人有点儿鬼本事、鬼才华、鬼智慧,这些字眼的分量就被加强了,而且还显得亲切。
鬼子的才华和智慧表现在多方面。这里想说的,是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注:春风文艺出版社将鬼子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瓦城上空的麦田》收为一集,名为《瓦城上空的麦田》,2004年1月出版。)、他的三部中篇在叙事里所表现出来“鬼”劲儿,以及这种“鬼劲儿”与我们时代的深刻关联。
叙事动力与悲悯情怀
作家的出道,与潮流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你的创作与当时的文学潮流吻合了,你就可能受到关注,就可能成名。如果你在潮流之外,想要受到关注,就难了。于是,新时期的作家往往成“捆儿”的出现。用某个名目,把一批作家捆成一堆。这一堆作家可能就同时出名了。当然,成名之后,你还认不认那个“捆”、那个“堆”,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当然,也有例外。鬼子就是其中之一。鬼子的真正出道,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正不断吸引文坛眼球的时候。如果说鬼子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语境,那不太可能,因为鬼子在决心重新写作前,把近年来在中国有影响的作品全部找来看了一遍。他不可能不注意到正在影响中国文坛的新走势。但鬼子的“鬼”就在这里,他看所有人的作品,是为了不跟所有的人走,他对创作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追求。再说,鬼子不是七十年代人,他犯不着混在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堆里充时尚。于是,在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似乎要在文坛形成一个大漩涡的时候,在大江的回旋处,冒出了一点水花,这水花越来越大,竟变成了一个大的水柱,直向天上冲去,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发现,出现了一个独特的作家,他的名字叫鬼子!
这个叫“鬼子”的人有点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爱、性、欲,已经成为文学写作的最大亮点。而鬼子不靠爱情、不靠性,却能把故事写得十分有吸引力,写得精彩得让人放不下。这在五六十年代容易做到,在今天,却太难了。因为今天的读者不好侍候。人们都忙,你不能一下子抓住他,他早就把你的作品丢到一边去了。但鬼子却做到了。他是如何做到的?这是我对鬼子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
鬼子的故事,都有一个强大的叙事推动力。它推动着故事不断地走向高潮,也吸引着读者不由自主地攒紧着杂志或者书本。
大凡好作品,都会有较好的叙事动力。鬼子作品并不因为它有叙事动力就成了值得一说的佳作。重要的在于,他的叙事动力有其极具个人色彩的特色:它往往由一个小事件演变而成,或一小块脏肉,或一个未过成的生日。开始,你对这个小事件也许并不太在意,或者,你并不知道这个小事件,将来在故事中会发生那么大的作用,你会把它当做一般地事件去读。但读着读着,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小事件,不断地推动着故事发展,滚雪球一般把故事扩大,最后竟把故事推到你完全意想不到的、惊心动魄的程度!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就因为一小块脏肉,最后竟至于闹到家破人亡。《瓦城上空的麦田》就因为一个未过成的生日,最后让两家三口人撒手西去。《被雨淋湿的河》的主人公就因为想挣一点钱,钱没挣着却丢掉了性命。
把这些由小事件演变成的叙事动力稍作抽象,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是些小欲望,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小欲望,或物质的,或精神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里的母亲为了找到父亲,以解决生计问题,是物质欲望。《瓦城上空的麦田》里的乡村老汉李四为了让生活在城里的儿女记住自己的生日,是精神欲望。而《被雨淋湿的河》晓雷的言行里,既有物质欲望,也有精神欲望。
我需要在这里插一句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把欲望仅仅当成了物质欲望、肉体欲望。其实,人的欲望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肉体的,也有心灵的。欲望与需要相关,或者说,需要就是欲望。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多种层次,它们是:一、生理需要,也是生存需要,这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但它并不是需要的全部。在它之上或之外还有,二、安全需要;三、归属与爱的需要;四、尊重需要;五、自我实现的需要等等。这一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成了人们的常识,但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却将这一常识忘记了。我现在想提醒人们回忆这一常识。当然,我还想说,人们的物质欲望与精神欲望并不是一个层次满足了,才走向下一个层次的。处于生活底层的人们并不是没有精神欲望。
让我们回到鬼子,回到鬼子的叙事动力:挣扎在生活底层人们的小欲望。这些欲望都很小,但在这些人们那儿却无法得到满足。于是,鬼子的叙事动力便产生于这样一个机制:寻找/破灭。寻找欲望的满足——希望破灭;再寻找——再破灭,直至生命的消亡。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里“我”母亲因为失业、贫穷,偷了卖肉者的一小块脏肉,被人发现。这事儿一般来说,母亲当时受点辱骂也就过去了。没想到却导致了父亲的离家出走。家里出现了生计问题。当母亲听说父亲已经回来,并和一个妓女住在瓦城饭店的老楼里后,叙事就把母亲推向了一个更大的苦难之中:寻找父亲。终于,母亲的希望破灭。母亲第一次的希望破灭导致母亲的第一次自杀。母亲被救活后,生计出现更大的问题,逼着“我”天天去饭店守候父亲。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在饭店的美容屋里找了一份工作,这样既能守候父亲,又能有点收入。不想,“我”又被假意关心我的邻居马达诱奸怀孕。这件事导致母亲的第二次自杀。这次她成功了。第二次自杀是因为母亲的希望完全破灭。如果说,找不到父亲,女儿还能成为她将来的希望的话。那现在,连将来的希望也无望了。希望——破灭,再希望——再破灭,使母亲走完了她悲惨的一生。
《瓦城上空的麦田》里的李四,因为几个在城里工作的儿女忘记了他的生日,一怒之下进了城里,要让儿女们记住他的生日。他的要求并不高,只不过要求一点被儿女们尊重的权利。没想到,让儿女们记住他生日的目的没有达到,却让关心他、与他喝酒的胡来老汉丢了一条性命。而胡来的死却被李四弄成了李四自己的死。骨灰送回乡里,急死了老伴。当孩子们回家奔丧后返回城里,李四作再次努力,希望儿女们能记起他的生日的时候,儿女们竟把当成捡垃圾的胡来,认都不认他。李四连告状都告不进,只好撞车自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希望的反复破灭,终于让李四失去了生的意愿。
《被雨淋湿的河》里的晓雷,只希望到广东打工挣点钱,没想到却碰到了不给钱的不义老板,晓雷失手打死了他。转到一个服装厂,又碰到老板为一件衣服要全体工人下跪。晓雷反抗了。回到家里,他又为当地教师的工资被扣问题组织教师集体示威。事件之后,他进了一家煤厂。但煤厂老板与教育局长是亲戚。晓雷被人不动声色地害死了。
三个作品中,没有一个小人物的小欲望得到过满足,也没有一个小人物为寻找小欲望的满足而不丢掉性命。这样一个叙事动力、叙事机制不仅给鬼子的小说带来一个奇佳的艺术效果:故事线条清晰、简明,但吸引力特强。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叙事动力、叙事机制,是从社会底层人生里挖掘出来的。它是叙事手段,更是人生思考。它的叙事机制本身就揭示了底层人们苦难的生存方式。于是,鬼子就用一个个小的人物故事,写出了底层人物的大的人生境况。他在不断地追问:小人物的生存怎么就这么难?鬼子的此前的人生,有过诸多吃苦的经历。在创作的时候,他没有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没有背叛自己的人生经历、没有背叛自己的人生感受和思考,更没有背叛一直在底层生活的小人物。鬼子的叙事动力里,有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大的悲天悯人的叙事情怀。
双重叙述者与思想空间
让我们先看《上午打瞌睡的小女孩》里的一个细节。为了寻找父亲,母亲半夜把我拉到饭店。饭店竟没有父亲的住宿登记。于是母亲拉着我一个一个房间听父亲的呼噜声,没听出来。母亲又要以人梯的方式从天窗上审视房间。可怜母亲瘦小的身躯能经得起女儿的身体吗?但她硬是从地上挣扎了起来,把女儿送到了天窗。检查了几个房间之后,母亲还是不行了。但谁也没有想到,她会对女儿提出这样的要求:“露露,你蹲在下边可以吗?”一个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女儿呀!看到这里,我们对母亲的歇斯底里、对母女俩的悲苦,产生了深深地同情。我们体验到了一种无奈。在这样的无奈之中,除了同情,我们还能干什么?
现在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同情”是从叙述的什么地方传给我们的?这里的叙述者是女儿寒露——“我”。“同情”,不可能从她的叙述中传给我们。因为她是事件中人,此时她正在痛苦之中,正泪流满面。她没有可能跳出来,站在一个高处去同情自己和母亲。或者说,此时的叙述者“我”只在讲着一个正在进行着故事。
但是“同情”这种情感确实是从叙述中传给我们的。于是,我们发现,在显在的叙述者“我”的背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叙述者。是他,在真正左右着故事的发展,是他在将各种情感与情绪传达给我们。这样,我们在这样一段故事里,就看到了两个空间:一个故事的空间,一个情感与思想的空间。显在叙述人给了我们故事的空间,而隐藏叙述人却一直在给着我们情感与思想的空间。
鬼子的作品,在叙述人上一直较为讲究。他喜欢用一个独特的个人去讲述故事。这里三部作品的显在叙述人就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小男孩、一个成年女人。三人中,两个小孩是故事的参预者,而成年女人对故事的参预较少,更多的只是一个旁观者。不管怎样,个人叙述者给鬼子的作品带来某种色彩:不仅有故事,而且是一个独特眼光里出来的故事。有时,还因为这个眼光的独特,能对故事进行别样的剪裁,故事因而有了韵味。
但是,这不是鬼子安排叙事者的全部。
个人叙事者,是一种有限叙述者,他或她所叙述的故事,只能在他/她看到、听到的范围之内。有限叙述者的运用,是需要功力与经验的。事实上,鬼子对有限叙述者的运用,并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它经常出些小小的差错。比如,《瓦城上空的麦田》,李四六十岁生日那天在家里等儿女们回家祝寿的事儿,“我”一个十几岁在城里捡垃圾的小孩子是不知道的。我们在文本中也找不到后来他听说了这段事的有力证据。但是,“我”就这样理直气壮地把这些事儿给叙述下来了。同样,《被雨淋湿的河》一开始,晓雷父亲送晓雷上师范,一路上的情形,叙述者“我”是没有看到的。在文本中,我们也找不到她听到了这段事情的记录。于是,这段叙述就落空了。叙述者叙述了一段她无力或者说无权叙述的故事。这个作品的叙述小差错我们还可以提到一些。比如,服装厂老板要全体工人下跪一段,那叙述的语气基本上不是一个女人的。“老板像头张狂的野兽,朝混乱的人群凶猛地扑了过来”,“惊慌的情绪以狂风的姿态在人们的脸上变幻着”。这样的叙述句子,是这段故事叙述的主基调。要知道,叙述者“我”也是听晓雷说的,她听说后的转述,不太可能是这样的语气。那么,这语气是谁的?隐藏叙述人的。
指出鬼子作品在叙述上的小疵瑕,不是为了挑刺。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这些小裂缝,让我们窥见了鬼子作品叙述者设置的奥秘。鬼子在叙事方面最重要的力量,是他在显在叙事人背后,都有一个隐藏叙述人。隐藏叙述人安排着故事的进展,让显在叙事人讲述出来。而隐藏叙述人则在背后用一种听不到的声音,引导着读者的情感和思想。于是,我们的阅读便在故事和思想的两个空间里穿行。
鬼子作品显在叙述者的妙用人们已经谈得不少了。我不想多说。我在这里想做的是,看看鬼子的隐藏叙述者到底给我们开拓了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空间。
近年来,社会上有些人欲横流。这就产生了文化焦虑。在一般人眼中,欲望与文化成了一组二元对立,二者永远处于颠覆与被颠覆的关系之中。似乎不是欲望打败文化,就是文化打败欲望一般。其实文化与欲望的关系远不是这么简单。任何时代的文化创造都必须面对当时的欲望表现。不能对当代的欲望表现发言,谈什么文化创造?当然,放纵欲望,更没有文化创造。这就需要正确处理欲望与文化的关系。现在是重新认识欲望与文化关系的时候了。
鬼子作品的叙述在这一点上透露了他不同于人的认识。首先,他不否认欲望。如前所述,他作品的叙事动力就是欲望。《瓦城上空的麦田》里,那麦田,更是欲望的象征。因为麦田是人们满足生存欲望的资本。李四在瓦城城墙上的一段描写是多么富有诗意!李四想,任何一个孩子都是一块麦田。但别人的麦田都在乡里,而他的几块麦田却飘啊飘,都飘到了城里。那时,他是多么幸福!因为他的孩子都做了城里人,吃上城里饭啦。“做城里人”是鬼子作品里的一个重要意象。那是农村人的一个特别欲望,做城里人,过好日子。
但鬼子却看到了多种不同的欲望,看到了欲望与欲望之间的争斗。底层人们一点小小的欲望都得不到满足。而另外一些人却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他们可以像《被雨淋湿的河》里的采石场老板、教育局长等人一样,随意夺取别人的利益,以满足自己永不厌足的欲望。财富给社会带来了繁荣,也给社会带来了异化。于是这个社会就出现了不公、不义,出现了种种令人发指的罪恶,就出现了诸多苦难。鬼子的小说,始终关注着现实的社会苦难和人生的灵魂苦难,始终揭示着人间的不公,呼唤着人间正义。鬼子充分表现了今天时代的作家的良知。
但在今天,我们能用正义一下子将人间不公扫平吗?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苦难,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欲望表现,不同的社会也有不同的正义。鬼子的深刻正在于,他往往有意无意间写出了在这个欲望表现异常活跃的社会里,不同的正义(注意,都是正义!)却同时存在的复杂情况,你能用哪一种正义去否定另一种正义?《被雨淋湿的河》里,晓雷所做的一切,都是正义的。但他却碰到了另一种正义:法律。因为他失手打死了人。面对两种正义,我们的情感何等矛盾!但你不能不承认,晓雷的行为与法律行为二者都是正义的。聪明的作者没有在两种正义间作出选择。他把思考留给了我们。
既然今天的社会是异常复杂的社会,不同的欲望表现、不同的正义同时存在,我们怎么办?需要对话,需要不同欲望表现、不同正义间的对话,在对话中创造我们今天的文化。《瓦城上空的麦田》前半部分是表现了这种思考苗头的。李四要求儿女们记住他的生日,一点可怜的精神欲望。他并不想吃儿女们的一顿饭,他只是想得到儿女们的尊重。这要求显然是正义的。但儿女们忘记了父亲的生日,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城里人生活节奏紧张,大家都很忙。“可不忙行吗?不忙怎么活下去呢?你不忙,别人忙呀,别人就会当着你的面,把所有的好东西,一样一样地抢走,最后会把你碗里的饭也抢走,你说你不忙你怎么办?”李四,一个农村老汉,他不太懂这些。如果父亲与儿女们对上了话,一切误会都有可能消除。悲剧就有可能不发生。但他们终于没能对话。
其实这部作品在儿女们回家奔丧之后,叙述上是又出现了裂缝的。明明知道儿女们都为自己的“死”回家奔丧去了,李四为什么不回家?他如果立即赶回家,把事情说清楚,老伴不会气死,两代人的误会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但作者就是让李四在瓦城逗留着。到儿女们从农村回来,李四已经变成捡垃圾的胡来了。作品的后半部分有点荒诞色彩。那裂缝也是为这一荒诞安排的。于是作者得以继续他对城里人生异化的批判:他们只认“身份”不认人。即使是亲爹,如果“身份”不够,也是不能认的。人们都想进城,都想富裕。但进城之后、富裕之后,人、人性、社会,却被异化了。
两代人终于永远失去了对话的机会。今天的社会需要对话。但真正的对话却太难。别人怎么读这部作品是别人的事儿,我是这么解读这部作品的。在我看来,不管作者有意无意,这部作品蕴藏着今天时代的重要思想力量。
叙述语气与时代精神
该说说鬼子的叙述语气了。凡读过鬼子的人都知道,鬼子的叙述是平平淡淡的。不管他的显层叙述者是谁,那叙述一贯都是心态平静的。平平淡淡的叙述,却讲述着精彩十分甚至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使鬼子的叙述产生一种极耐咀嚼的张力。它使你产生一种阅读的异样感觉,这感觉吸引着你读下去。
这既是鬼子的叙事策略,也是鬼子的为人方式。他一贯是低调的,不想用抬高声音说话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身份或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他刚出版的一本书中有关自传性的文字里,他开宗明义就这么说:“一个人的心情很平静的时候,别人能不能听到他的呼吸?应该是听不到的。一个作家如果用一种正常的呼吸状态,叙述他的创作,叙述他的生活,结果会如何呢?我想这应该成为我的一种选择,我不希望别人在这些短小的随笔里,闻到什么不安的情绪,比如愤怒,比如埋怨,比如失落等等……那样对别人对自己都是没有益处的。大家活得挺不容易的。”(注:鬼子:《艰难的行走》,昆仑出版社,2002年9月。)
这里他说的是叙述他自己,其实他叙述故事的心态也是这样的。尽管他关注着人生苦难、灵魂苦难,他呼唤着社会良知和正义,但他并不是运用导师式的、精英式的方式,而是在一种正常的呼吸状态下说话。
这是他作为二十一世纪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文人的重要标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如果要表达鬼子式的思考,那一定会把精英状扮得十足,他要成为导师训导大众,他要用精英的深邃思想去震撼芸芸众生,去启蒙大众,带领大众从黑暗走向光明。
但是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突然发现大众开始远离了他们。他们不明白,这个社会没有成为大众导师的精英怎么行?终于,有人对知识分子的精英思想提出质疑了。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重要思想主题。谁来给启蒙者启蒙?谁来保证启蒙者言说的绝对正确性?精英与大众到底应是什么关系?精英能不能无视大众的创造?
思想的转型往往是最难的。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几场大的论争之后,启动了这个转型。人们终于开始明白,今天的社会并不是不要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而是需要知识分子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和说话方式。知识分子无权作大众的导师,他只能是社会、大众的对话者。他通过对话来进行自己的思考,为社会进行自己的精神创造。
鬼子似乎从来就没有把自己作为精英。他一开始就找准了自己的说话方式和位置。既使成名之后,他仍然追求“在正常的呼吸状态下说话”。他始终在与大地、与青草、与平民、与生活在人生最底层的小人物进行着对话。在对话时,他只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不是要作他们的精神领袖。他平平淡淡地叙述着他们的故事,却在思考着我们时代最深刻的问题。他的思想正在走向我们时代思想的最前列,体现着我们时代的思想力度。
我一直以为,对话,是二十一世纪的时代精神。鬼子在用他的作品与我们的时代对话。他的言说方式体现了二十一世纪知识分子的某些本质方面,体现了二十一世纪的时代精神。
鬼子,还有更大的“鬼”在后面。我想,这是一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