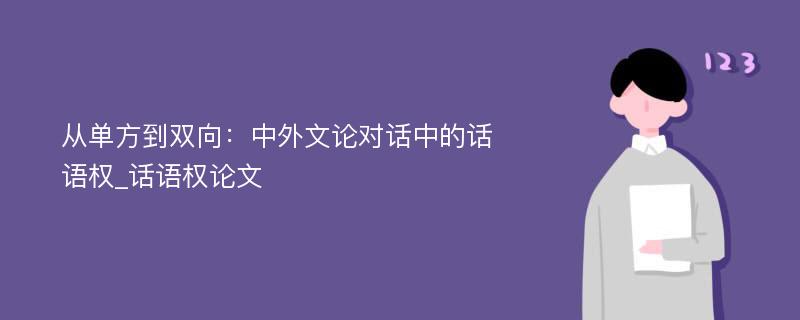
从单一到双向:中外文论对话中的话语权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一到论文,双向论文,话语权论文,中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界一直是十分开放的,学术气氛和理论争鸣也相对自由,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几乎对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每一种新的理论思潮或批评方法都十分关注,一旦了解一二便争相介绍到中国,或者自觉地运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对于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我们更是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前来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只要他们的发言稍稍对我们有所启发,都会安排他们在各大学或科研机构演讲,学术期刊的编辑们都会争相请人翻译他们的文章并予以发表。应该承认,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正是在与西方理论批评的交流和对话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文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在国际学术界的显示度又如何呢?我作为一个直接参与中西文学对话的探路者和推进者,对这种状况实在不敢恭维。正如一位期刊编辑愤愤不平地所抱怨的,在公认的国际权威数据库SSCI和A&HCI期刊目录中,“不仅国内很多‘权威期刊’、‘一流期刊’榜上无名,而且国内学术‘大腕’也鲜有在这些期刊发表大作的荣幸”①。可见这种文论交流和对话的“逆差”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所导致的结果确实令人汗颜。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果真是我们中国理论家水平太差以致我们的观点毫无借鉴价值吗?或者是因为我们无法用公认的国际学术语言——英语来表达所带来的后果呢?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面对这一严峻的事实,我们将采取何种对策,或者说,我们如何才能争得走向世界的话语权,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两个问题。
谁应掌握国际中国研究的话语权
任何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现状的人都不难发现,文革结束以来,由于我们不遗余力地将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思潮引进中国,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竟出现了所谓“尼采热”、“萨特热”和“弗洛伊德热”,在文学创作界及理论批评界也相应的出现了“方法论热”、“美学热”、“现代派热”和“后现代主义热”。一大批西方思想家和理论家的著作的不同译本,不管其质量如何,统统进入了中国的图书市场,强有力地影响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一时间,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大谈尼采和弗洛伊德竟成了一种时髦。作家和批评家在谈到创作和理论批评时,必然会提到现代派和后现代主义。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国内,不少带头译介西方理论思潮的学者从事的都是西方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而到了国外,他们的长项则体现在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会讲外语并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现状的中国学者,要想争得发言权,就只能就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现状发言。也就是说,在国际学术界,你的中国身份决定了你只能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内拥有有限的发言权,也即你只能就中国问题发言,或者就与中国问题相关的话题发言,否则你的权威性就大可怀疑。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而言,即使我们就某一个与中国文学创作或理论批评密切相关的论题发言,也显然不能掌握在这个话题上的主导权,而必须被纳入西方汉学界的体制内围绕他们所感兴趣的话题发言。换句话说,在国际场合,中国学者充其量只能充当某个国际性活动的点缀物。
回顾自己在这二十年的国际学术交流中所走过的道路,我深有体会:不管你在国内多么具有权威性和知名度,西方学术界总是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他们完全可以根据你在国际出版机构或期刊上发表的著述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内的一些学术体制内赫赫有名的“大腕”或“泰斗”级的人物到了国外,只能或者随团访问,或者通过探亲访友来进行有限的学术交流。倒是一些天资聪颖、外语基本功扎实并有一定学术实力的中青年学者,通过奋力拼搏以及与国际同行的激烈竞争,最后也能拿到国际研究机构的奖学金或研究基金。其中有些人凭着自己对国际学术前沿课题的了解和良好的外语写作训练,通过努力和竞争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这样的例子如果说在20世纪80、90年代尚属罕见的话,那么到现在已经逐渐多了起来,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研究者在国际学界不再“失语”了,一些知名学者还被国际学术期刊,尤其是中国研究期刊,聘请为编委或顾问,开始逐步掌握一点话语权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因为作为中国学者,即使就普遍的理论问题也许不拥有较多的话语权,但至少在中国研究方面,或在评价国际中国研究的成果的水平和质量方面,自然应是我们的长项,因此我们在这方面理所应当地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所掌握的话语权也是极其有限的。大多数在国内赫赫有名的中老年学者,为了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一点声音进而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把自己的成果推销出去,但效果往往是事倍功半。有的人则在默默地等待某个对自己研究课题感兴趣的汉学家来“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的价值,进而将其翻译成国际通用的学术语言——英语,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
与其相反的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现象则是,国外的大大小小的汉学家,尤其是来自西方的汉学家,有的只是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且尚未获得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却备受国内学界的青睐,甚至那些早先在国内学习外语后来为了便于得到奖学金而改学中国文学的“假洋鬼子”也摇身一变,成了掌握话语权的权威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国外发表了论文或出版了专著,就忘乎所以,假装外语太好故不便用母语写作,但国内的同行们却争相将他们的著述译成中文在国内期刊上发表。因为国内的这些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要想走向世界,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用西方通用的语言写出符合西方学术规范的论文,通过与国际同行的激烈竞争才得以发表,但这方面的成功者至今寥寥无几。不少人由于语言表达水平过差,辛辛苦苦写出或请人翻译出的论文通过不了同行评审而付诸东流;另一条路则是不得不借助于英文翻译的中介,等待某个汉学家的“发现”。这确实令国内同行汗颜!
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中西文化学术交流中的不平衡状态。一个开放的中国十分想了解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状况,但长期以来,外界却不那么热切地想了解中国,或者说,根本不屑去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更不屑于听中国学者在说什么。显然这一巨大的落差背后隐含着诸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当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经济上确实很落后,又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因而穷国是没有资格向世人输出自己的经验或研究成果的,也没有奢望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的对话。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由于中国高校的培养机制所致,绝大多数文学理论家或研究者不通外文,少数勤奋者至多只能掌握一门外语的阅读技能,通常是英语,因此他们的长项就是可以将西方学者的著述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却无法反过来用地道的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更无法通过与国际同行的竞争在英语学术出版界发表著述了。这就造成了中国学者在中外文论对话中的“失语”状态。
显然,中国学者长期在国际文论界陷入“失语”的状态是毫不奇怪的,这与美国的文化霸权和英语的强势地位不无关系。即使是德里达和哈贝马斯这样的大理论家如果没有美国名牌大学的邀请或英语出版界的推介,也很难成为蜚声世界的理论大师。而他们的一些国内同行,则因缺乏这样的中介而忍受着孤独和寂寞。同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汉学家的中介。应该承认,在西方的汉学界,确实出现了一大批学贯中西并对某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有着精深研究的大家,如早期的普实克(Jaroslav Prusek)、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高利克(Marian Galik)、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杜德桥(Glen Dudbridge)等,以及现在仍很活跃的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罗多弼(Torbjorn Loden)、顾彬(Wolfgang Kubin)、佛克马(Douwe Fokkema)、字文所安(Stephen Owen)、伊维德(Wilt Idema)、李欧梵、夏志清、王德威、孙康宜、苏源熙(Haun Saussy)、何谷理(Robert Hegel)、李夏德(Richard Trappl)等,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是在中国大陆或台湾长大然后到欧美去进一步深造的。他们的著述确实不亚于国内的同行,在某些方面甚至高过国内的同行。但是这样的大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另一方面,由于东方主义长期以来所导致的对中国的歪曲性报道和描写,西方汉学界的确有那么一些人,往往表现得十分傲慢,自以为来自第一世界,能够用流利的英文发言并写作,并能流利地使用汉语,因而掌握着中国研究的话语权。他们中的一些人竟然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就中国问题发言或著述,而来自国内的中国人则不具备这样的资格:不是理论话语陈旧就是表达的语言(英语)太差。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他们就中国问题说出或写出的东西往往建立在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一知半解或曲解之基础上,与中国的真实情况大相径庭。有些研究成果虽然对西方学界的外行也许还有些新意,但一旦译成中文之后,国内学者便觉得其中并没有什么惊人之语,与西方主流学界的水平相距甚远。当然,在那些封闭的年代,西方主流学界对他们还是比较相信的,但从本质上说来,由于他们与中国学者缺少交流和对话,因而其研究成果并不能代表国际学术界整体的中国研究水平。这也就是为什么汉学在西方主流学界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真正试图了解中国的西方理论大家则越过这些汉学家的中介,直接与中国国内的学者交流和对话。② 同样,一些西方的主流研究机构或学术基金会在评审汉学家就中国问题研究而提出的项目计划时,也破例地邀请中国学者进行评审,这充分说明,我们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在国际中国研究领域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了。③ 那么究竟谁才能代表中国研究的水平呢?或者说,谁应该掌握国际中国研究的话语权呢?答案仍然是不证自明的。
中外文论对话中的中国话语权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大国的国际地位再也不受任何怀疑了。全球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既交换自己的看法,同时也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切磋。在这方面,自然科学家在引领国人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方面确实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新兴的科技大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但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又如何呢?再具体一点说,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在国际理论界的地位如何呢?对此我们实在不敢恭维。我们对西方当代文论的关注确实十分密切,跟踪也很紧,几乎西方现当代的所有重要理论著作都可以很快地见到中译本,这样一批现当代西方理论大师,如于尔根·哈贝马斯、雅克·德里达、茨维坦·托多罗夫、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伊哈布·哈桑、特里·伊格尔顿、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等都来过中国,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和人文学界都受到很高的礼遇。而姗姗来迟的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罗伯特·扬等也自新世纪以来陆续来中国访问,并在中国的顶尖大学发表演讲。④ 而相比之下,能被西方一流大学邀请发表演讲的中国学者却寥寥无几,即使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位,大多也是顺访,很少有专门受到邀请前往演讲的。这应该就是中西文论交流和对话的不平衡的现状。
确实,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内,很少有中国学者能够在国际顶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这里仅以人文学科为例。在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流期刊上,中国学者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不用说与国际同行平等讨论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了。在文学理论界,迄今只有极少数中国理论家有幸在国际权威刊物,如《新文学史》和《批评探索》上发表论文⑤,能在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专著者更是凤毛麟角了。在讨论一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时,中国理论家总是对从亚里士多德到德里达等理论家的著作旁征博引,而国际同行们则几乎对中国理论家用中文发表的著述不去引用或讨论,似乎中国理论家从未提出过什么能够启发人的新观点,这确实是最令人沮丧的。我想,除了缺乏必要的符合专业水平的英语写作训练外,他们可能还缺乏理论思维和写作规范方面的训练。也即他们不掌握与国际同行进行讨论和对话的共同学术话语或基本的游戏规则。但即使如此,一些国际期刊,包括中国研究期刊的主编们仍抱有很大的同情心。在他们看来,在讨论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时,应该听到尽可能多的声音,而不管这种声音是来自西方学者还是东方学者。其中一些期刊主编甚至邀请一些主要的中国学者为他们的刊物编辑专辑,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邀请优秀的中国学者或国际中国研究的权威学者撰文,对于有些水平确实很高但自己不能用英文写作的学者,他们宁愿花钱去邀请人将其译成英文。⑥ 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听到中国学者对一些学术前沿问题以及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的观点和研究心得了。应该承认,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这些优秀的学术刊物真正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和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可惜这样的刊物在当今时代确实凤毛麟角,大多数刊物的主编们都愿意发表投稿者直接用外语撰写的论文,这样他们通过同行评审后就可以请作者在内容或形式上作出相应的修改,以力求完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一点确实与国内刊物的用稿原则和编辑程序大不相同。
国内从事比较文学或比较文论研究的学者,一般都热衷于追溯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学或文论如何对中国文学或文论产生影响的。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也许更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一个课题应该是中国文化和文学是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和被接受的,或者说,在中外文论交流和对话中中国文化和文论是如何影响或启发外国文学和文论的。当然,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难度或许更大,因为研究者不仅需要精通一、两门外语,最好还要有相当充足的时间在国外访学。因此相对于前者来说,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学者就如凤毛麟角,出版的著述自然就更少了。这无疑造成了中外文学关系以及中外文论交流中的不平衡状态,所导致的后果就是不少人竟认为,中国文论在国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中国文学在国外也几乎无人问津。对此,我们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自然感到问心有愧,因为我们在从事中外文学关系和中外文论的比较研究时,往往只是单向度地追踪外国文学或文论对中国文学或文论的影响,而很少去探讨中国文学或文论在国外的影响和接受。这无疑是一大缺憾。我认为,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这种文学交流和文论对话的单向路径应该改变,一种双向的乃至多元的理论对话之格局应该在中外文论对话中率先形成。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值得庆幸的是,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这种失衡的状况有了一些改变。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内率先出现了一个“东学转向”或“中国转向”,这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中外文学关系和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⑦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大量引进之后,中国学者也许最关心的是,如何使古老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如何使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走向世界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的声音。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地位得以确立。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对中国文化发生兴趣,因而努力向国外推介中国文化和学术思想便成了我们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者的一个义不容辞的义务。在这方面,自然科学学者又走到了我们的前头。而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国际上的声音则十分微弱。在公认的国际权威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目中,我们很难见到中国学者的外文著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权威学术刊物上,我们也很少见到中国学者的论文。当然,这其中的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霸权的因素是不可排除的,但我们中国学者的主观努力应该说也是远远不够的。
我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必须走向世界,中国的文学研究必须跻身国际主流文学研究界,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绝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向世界输出廉价商品和劳动力,还应该以一个文化大国的身份向世界输出思想观念和理论方法。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学者应该先行一步。我始终认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要走向世界,就要注重国际发表,也即在国际英文刊物上发表论文,从而使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跻身国际主流学术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在国内的学者中,有这种自觉意识者似乎还不多,他们常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说你要研究中国文化在国外的接受和传播,你首先要让国内的读者知道这一点,也即首先要在国内学界和出版界打破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的这种不平衡状态。⑧ 此外,在国际中国研究领域,中国学者也应当掌握更多的话语权,或主动提出一些出自中国文化土壤的、具有相对“原创性的”理论话题,引导国际同行去讨论甚至争鸣,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关起门来侈谈所谓“原创”问题。
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必要途径
也许有人会认为,中国经济的腾飞为中国文化的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广中国文化和学术。但这只是最基础的工作,在学术的层面上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则要靠我们学者自身的努力。作为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我们也许经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加快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国际化步伐?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才能使我国的文学研究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中国既然是一个文化大国,但为什么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发出的声音如此微弱?这究竟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仍在作祟呢,还是我们自身的水平确实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如果两方面原因都存在的话,那么如何才能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走出国门进而产生广泛的国际性影响?既然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因此中国不仅应当在全球经济的发展方面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而且更应当在包括世界文化和文学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做出自己的独特建树。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曾经在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大力鼓吹过在国际权威的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⑨,在国内及港台学界产生过一定的反响甚至争议。现在看来,这一初步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得以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而且一些由中国人主办的中英文期刊也进入了这两大权威的数据库。⑩ 但是若从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国际化着眼,单靠在SSCI和A&H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还远远不够,而且这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终极目标,只能作为我们的文学研究走向世界的必要途径之一。要想全方位地实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战略,则要从下面三个方面来共同努力:(1)组织学术造诣深厚且英文写作好的学者集体攻关,力争在公认的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数量可观的原创性论文,并使有分量的学术专著跻身国际权威出版社;(2)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学术翻译队伍,通过与国外学者的合作,将文学理论和研究的优秀成果译成英文,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在国际权威出版社出版;(3)努力打造中国文学理论和研究的精品刊物,绝不以盈利为目的,争取在今后的三年内,向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推荐一批高水平的A&HCI来源期刊。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至少说明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已经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或者说明我们掌握了部分话语权。
但是就目前的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现状而言,中国学者的声音确实是十分微弱,以至于竟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在国际学界处于“失语”的状态,在讨论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国际论坛上,中国学者的声音总是缺席或十分微弱。甚至在一些主流西方学者看来,中国有没有哲学还值得怀疑,中国的黑格尔、康德、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研究者基本上在国际学术界没有发言权。他们只能一味地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而不能和别人在同一层次上平等地对话,更谈不上对别人的错误观点提出批判性的讨论。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没有国际影响主要是因为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造成的,但我认为,这不能说完全是一个语言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是不是已经提出了目前国际文学理论领域里的前沿话题;第二,我们能不能把它准确流畅地用符合国际规范的学术话语表达出来。如果我们和国际同行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对话,那么这种对话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最后才涉及语言的问题。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汉语在全世界的普及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当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逐渐走向强势时,国际学术界也不得不设法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中国,甚至组织力量将中国学者的优秀著作翻译成主要的西方语言进而在国际权威出版社出版。(11) 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理论和学术研究水平也应当跟上。目前在中外文论对话中出现的一个悖论是:一方面,中国的理论研究者对现代主义以来的主要西方理论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真可谓如数家珍,连希利斯·米勒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都惊异地发现,他们在中国的知名度大大超过他们在美国的知名度。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内学界公认的“大师”或“泰斗”在国际学界甚至无人知晓,更不用说去讨论和研究他们的著作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中掌握的话语权极其有限,甚至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我们的学者也往往把主要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国外汉学家,甚至一厢情愿地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少数汉学家的“发现”和中介走向世界。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学者的一个误区。我认为,在国际学术界,至少就中国研究而言,中国学者应该掌握更多的主动权,或者说拥有主要的话语权,由我们来判断西方的汉学家的研究是否具有价值和意义,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应该根据当前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生产以及理论批评的实践提出一些理论话题,供我们的国际同行讨论甚至争论。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立足于本土经验和研究,提出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话题,用国际公认的学术话语加以表达。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有效地使得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真正走向世界进而产生较为广泛的国际影响。更具体地说来,探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首先要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尤其要发现那些被历史多年“尘封”的、未发表的资料,然后通过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析将其整理出来,最后再用公认的国际规范的学术话语加以表达。我想,只要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确实具有开拓性和首创性,那么即使我们现在用中文发表研究成果,将来通过翻译的中介也照样可以在国际上发表。当然,对于少数兼通中西并擅长于用中英文著述的学者,掌握话语权也应该体现于掌握世界公认的学术语言——英语,这样我们就可以瞄准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期刊,和国际同行平等地探讨一些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理论课题,并发出中国学者的强劲声音。
总之,中外文学理论的对话应该结束目前这种单向度的交流路径,拓展为双向的路径,也即我们在继续及时地将最新的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著述译介到中国的同时,花更大的气力把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成果推介到世界,具体说来,首先推介到英语世界。目前,在谈到全球化的时候,人们总喜欢说,全球化对于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西方化,而西方化本质上就是美国化。如果从经济和文化这两个纬度来看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们率先将中国文化及其研究成果推向英语世界,就等于走向了整个世界。因为历史证明,任何理论思潮要想具有普适的意义和影响,首先必须经过美国的中介,具体说来,在传播过程中则须经过英语的中介,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要想真正走向世界进而产生国际性的影响,也不得不通过这一中介来实现。如果我们的最终目标能实现,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这恐怕是我们当前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策略了。
注释:
① 参见朱剑《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② 实际上,应邀前来中国访问讲学的德里达、哈贝马斯、伊格尔顿、詹姆逊、米勒、科恩、托多罗夫等西方理论大师,都没有经过汉学家的中介,而是直接和中国学者进行交流的。
③ 就我本人而言,我最近几年就应邀参与了几个欧美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的评审,以及一些著名大学的讲席教授的评审。当然,这些项目或职位都与中国研究密切相关。
④ 应我本人的邀请,霍米·巴巴于2002年6月来中国访问,在清华大学发表2场演讲;斯皮瓦克于2006年3月来中国访问,分别在清华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发表3场演讲;罗伯特·扬于2009年3月来中国访问,分别在清华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天津外国语学院发表5场演讲。
⑤ 据统计,在这两家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学者除了我本人外,还包括张隆溪、钱中文、王逢振、丁尔苏、刘康、赵毅衡、张旭东以及一些在美国高校任教的华裔学者,但张隆溪和刘康是美籍,赵毅衡则是英籍,他们现在都在中国高校担任全职教授或讲座教授。
⑥ 坦率地说,只要我们能拿出相当质量的学术论文,不少国际期刊还是很愿意发表的,例如,钱中文的巴赫金研究论文“Problems of Bakhtin's Theory about‘Polyphony’”,发表于New Literary History,28.4(1997),pp.779~790;1997年发表在国际后现代主义研究的权威刊物boundary 2,24.3(1997)上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Postmodernism and China)专辑中的三篇文章就是特约编辑张旭东组织人将其译成中文并收录其中的。但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少。
⑦ 在我主编的专辑Beyond Thoreau:Literary Response to Nature,a special issue,Neohelicon,36.2(2009)中,就收录了三篇中美学者撰写的探讨梭罗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论文,这三篇论文都分别在2008年10月清华大学主办的“超越梭罗:文学对自然的反应”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
⑧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些出版机构开始关注“东学西渐”,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几套有一定影响的丛书:花城出版社推出了《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乐黛云、钱林森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东学西渐》丛书(季羡林、王宁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钱林森主编)等等,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西学东渐”的主导性趋向。
⑨ 这方面可参考葛涛对我本人的访谈《人文社科期刊怎样进入国际权威领域——王宁教授谈SSCI和A&HCI》,《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3日。
⑩ 例如,2005年,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中文刊物《外国文学研究》率先进入A&HCI;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英文刊物China and World Economy进入SSCI。
(11) 在这方面,比较热心于出版中国问题研究著作的国际著名出版机构有美国的哈佛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密西根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英国的路特利支(Routledge)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等,新加坡的马歇尔·卡文迪西出版社(Marshal Cavendish Academic)以及荷兰的布里尔出版社(Brill)。在这些出版社中,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布里尔出版社近来还约请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从中国学者用中文撰写的优秀著作中物色佳作,并组织翻译出版。
标签:话语权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中外文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国际文化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