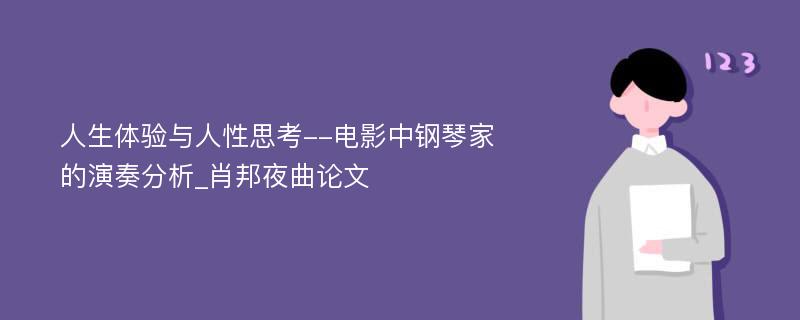
生命体验与人性思考——影片《钢琴师》的剧作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作论文,人性论文,影片论文,钢琴师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近代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犹太人一样,具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叫幸存;或许,这种幸存的民族经历使得今天的犹太民族更加懂得生存的需要,也更加容易获得世人的同情。于是,一边是以色列用坦克将巴勒斯坦人压制在加沙的集中营里,另一边是第75届奥斯卡奖的桂冠落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绝境求生的电影《钢琴师》身上。
历史当然不会原封不动地重演,但对于集中营里的被囚禁者来说,求生无疑是幸存者的共同语言。而且在二十一世纪之初,频繁的恐怖活动和危险的单边主义使得整个人类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在这个时候,反思一下,是什么使得人类在历史上屡次得以逃脱灾难,得以幸存?这或许是法籍波兰裔导演罗曼·波兰斯基要通过《钢琴师》传达给大家的一点人性思考。
幸存的故事
享誉波兰的钢琴演奏家的瓦瑞·斯皮曼每天在波兰的国家电台向世人演奏钢琴大师肖邦的作品,直到纳粹的炮火轰塌了电台演播室的墙壁,德军在昼夜之间占领了波兰。瓦瑞一家像大多数华沙的犹太人一样,即使在战争降临的时候,还希望恪守犹太人隐忍克制的处世原则;他们在片刻的惊恐之后,幻想着能够恢复往日的平静生活,他们将希望寄托于英国向德军宣战。
随着德军进驻华沙,犹太人的生活空间一步步地被缩小,瓦瑞一家亦步亦趋地遵守纳粹为犹太人制定的法规,用忍耐和顺从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瓦瑞失去了在国家电台的演奏工作,他们被禁止去餐馆和公园,被迫戴上大卫星的犹太袖标,甚至禁止在人行道上行走。直到最后,华沙三十六万犹太人无不遵守纳粹占领军发布的通告,主动按时赶到城中央一个特定区域,然后被高墙隔离。
包括瓦瑞一家在内的华沙犹太人,将全部被送上前往死亡集中营的火车。虽然这段犹太人殉难的历史在许多影片中都有展现,但是《钢琴师》却从此处将故事的发展引向了另一端。
瓦瑞在被押送上火车的关键时刻,被一名他所鄙视的犹奸所救,开始了他的逃生历程。求生的本能使得目睹了死亡的钢琴师开始背离自己在战争初期的处世原则,原本宁死也要一家人在一起的亲情观念被冷酷的现实所打破。逃得性命的钢琴师,从此与亲人生死相隔。瓦瑞加入了犹太劳工的行列,他暗地里开始帮助抵抗力量运送武器,最终伺机逃离了犹太隔离区。
瓦瑞在昔日的日尔曼朋友的帮助下不断地在市区辗转藏匿,直到隐藏到德国人的警察局旁边。透过窗户,瓦瑞仍能够清楚地看见犹太隔离区的大墙。在纳粹的眼皮底下,瓦瑞依靠朋友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的救济食物度过了艰难时刻。直到抵抗组织向警察局发动了进攻,德国坦克的炮火摧毁了他的隐蔽场所,瓦瑞不得不再次逃亡,这时的华沙已经满目疮痍,寥无人烟。瓦瑞躲过一个又一个劫难,终于藏身进了一个荒废的阁楼。现在他又要为食物发愁,就在他遍寻食物的时候,被一名德国高级将领发现。
故事至此到达了全片高潮,一路逃亡的瓦瑞已经筋疲力尽,摆在他面前的路也已别无选择;但意外的是,当德国军官得知他是名钢琴师时,命令他弹一首钢琴曲。瓦瑞的音乐在关键时刻战胜了这位纳粹军官,使他的人性得以萌发。大势已去的德国军官非但没有将他处死,反而帮助他获得食物和避寒的纳粹军服。
当苏军开进华沙的时候,曾经为钢琴师挡风避寒的纳粹军服险些要了他的命,人们诧异在华沙城内居然还有犹太人幸存。
幸存的瓦瑞战后重返了国家电台,而那名帮助他逃脱厄运的德国军官却死在战俘集中营里。
剧作主题的双重身影
影片的剧作主题是讲一名犹太钢琴师如何在纳粹迫害下绝处求生的故事。
剧本是根据波兰著名钢琴家瓦拉迪斯罗·斯皮曼(Wladyslaw Szpilman)的自传体回忆录改编而成。瓦拉迪斯罗于1946年将自己的经历写成自传体回忆录,末页还记录着那个曾救助他的德国军官的故事,并附了他的几页军中日记,日记中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纳粹的反省。瓦拉迪斯罗始终无法忘怀那些不惜冒险向他伸出援手的人们,不管那是犹太警察还是德国军官。在他的眼里,战争如同一部碾路机,虽然碾碎了生活中的一切,但无法泯灭人性的光芒。
的确,对比影片《钢琴师》的故事内容,影片毫无疑问是根据瓦拉迪斯罗的这部自传体回忆录改编而成的。虽然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有着和瓦拉迪斯罗类似的人生经历,但波兰斯基并没有将其拍成自己的“自传体”影片,波兰斯基对此的解释是:“我对这类影片从无兴趣”。
事实果真如此吗?
现年70岁的法籍波兰裔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一生经历极为坎坷。1933年,他生于法国巴黎,作为波兰犹太人和俄国移民的后代,波兰斯基在3岁的时候跟随父母返回波兰克拉科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纳粹把他全家关进了集中营,这时他才8岁。他的母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惨遭纳粹杀害,父亲则想尽办法使年幼的波兰斯基逃得生命,幼小的波兰斯基独自在乡村流浪,善良的天主教徒帮助了小波兰斯基顽强地逃过一次次搜捕。4年后,幸存下来的父亲走出了集中营。
这段惨痛的、梦魇般的童年经历在波兰斯基内心“潜意识”深处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创伤印迹,这段情感体验成为了波兰斯基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影响了他整个一生的价值观念。虽然波兰斯基否认这是一部关于自己的传记片,但是他童年时期的这段亲身经历被明显糅成了《钢琴师》中挥之不去的情感主题。这样影片剧作主题就显露出双重身影:钢琴师的故事和波兰斯基对自己深藏在内心中的童年记忆的寻找。波兰斯基说:“很明显,整部影片是关于生存的故事,对我而言,这是我从儿时到青少年时期不断萦绕的主题。”波兰斯基清晰地记得那个年代,那个令他童年痛苦的岁月。在影片前期准备阶段,波兰斯基焦躁难安,因为他必须再度面对儿时所经历的种种悲惨记忆。波兰斯基说,在指导上百名演员扮演奥斯威辛集中营难民时,“其真实的程度令我必须偷偷掐我自己,告诉自己‘这只是部电影’”。
波兰斯基非常尊重根据回忆录改编而成的剧本,影片基本上完全遵照回忆录的故事而完成,但在许多细节描写上,波兰斯基加入了自己童年的记忆,如:纳粹军官肆意在大和街上向队列中的犹太人开枪射击等暴力场景,又如主人公寻找父亲的过程,这些都宛如波兰斯基童年记忆的再现。犹太警察释放主人公的突转动作也是根据波兰斯基的童年经历设计完成的,当年幼小的波兰斯基曾因为饥饿请求看管集中营大门的犹太警察放他们回去吃点东西,这个在大人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要求,竟然获得了犹太警察的默许,当他们跑起来时,犹太警察压低了嗓门儿:“别跑!……”
波兰斯基回顾童年时的经历,常常会对那些无法用常理解释的人类行为所感动,这使得他在影片中所表现的思想主题上更倾向于人性的思考。影片中大量真实细节的描写,也使得影片剧作呈现出导演浓重的个人风格。由于波兰斯基独特的人生经历,加上深受超现实主义流派和荒诞戏剧、黑色电影的影响,使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电影风格:善于运用主观视点和畸变影像表现错乱、恐怖和死亡的主题,营造出悲怆的人性思考。影片《钢琴师》冷峻的叙事风格、凝重的纪实格调,常常会使人们忘却了这个故事的本身,而陷入对人性的深层思考中。
波兰斯基说:“让我讲一个人幸存下来的原因真是太难了,但某些人的幸存确实是人类的幸存!”
波兰斯基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人类幸存的希望是什么?
十年前,《辛德勒的名单》也提出了同一个问题,斯皮尔伯格对此的注解是英雄拯救世界,在这种美国式的英雄片中,小人物与英雄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在《钢琴师》中,波兰斯基将人类幸存的希望寄托在自身残存的人性上。瓦瑞的幸存是一系列小人物,甚至是敌人——纳粹军官帮助的结果,而如果瓦瑞不是人所景仰的艺术家,这些曾经救助过他的犹太警察和纳粹军官是否还会唤起已经泯灭了的人性良知?
从影片《钢琴师》里,观众看到了人类所面临的真正的危险。
钢琴曲与影片剧作结构
在影片《钢琴师》中,波兰斯基用音乐讲述了人性如何在人类杀戮中闪光的故事。音乐作为全片最为靓丽的剧作元素,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全片音乐主要取自波兰伟大的音乐家肖邦的钢琴作品,这和影片的历史背景、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以及故事的发展得以完美结合。钢琴曲在影片中不仅流露出钢琴师对生命的热爱,而且还成为影片起承转合的重要情节点。
影片开始,年轻的钢琴师瓦瑞在华沙的国家电台为听众演奏肖邦的升G小调夜曲,音乐声舒缓、祥和;突然演播室外传来德军的炮火声,钢琴师想坚持为收音机旁的听众演奏;但是,猛烈的炮火很快就摧毁了电台的播音间,瓦瑞的钢琴演奏被迫中断,波兰人的宁静生活被战争打乱,犹太人也逐步陷入了痛苦的深渊。波兰斯基在此用钢琴曲被打断作为全片开头,同时留下悬念。
影片发展,钢琴师瓦瑞一家为了生计卖掉了钢琴,遵照德国人的通告搬进了犹太隔离区,音乐从此离开了波兰犹太人的生活。瓦瑞由国家电台演奏家沦落到一家酒馆弹琴维生。这时候的音乐显着沉重而悲凉;隔离区中央铁道旁的犹太艺人在德国士兵的淫威下被迫弹奏出欢快的舞曲,而衣履褴衫等待回家的犹太囚禁者们被逼跳起了舞步,在欢快的音乐中,夹杂着纳粹士兵狂妄的笑声。
德军开始大规模的将华沙犹太人由隔离区押往集中营,这时,瓦瑞在一名犹太警察的帮助下逃离了纳粹魔掌,过起了东躲西藏、苟且偷生的日子。其间,瓦瑞在一幢劫后废弃的阁楼上看见一架尘封已久的钢琴,面对久违的钢琴,钢琴师瓦瑞的双手禁不住颤抖,他凌空悬指、紧闭双眼,仿佛听见往日的钢琴旋律如潮水般浸过心头,如同逃离了残酷的现实世界而沉入一个美好的心灵世界。无声的弹奏成为全片的一个转折点,也是钢琴师生命中最为悲惨的写照。
瓦瑞因为是波兰杰出的青年钢琴师,所以在生死关头,无论是犹太警察还是日耳曼演员都冒死向他伸出援手,所以说,钢琴师的身份使得瓦瑞不再是一名普通的犹太人,而是成为了一种整个人类美好希望的象征。而因钢琴艺术而幸存的钢琴师却不能够弹奏钢琴,这无疑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讽刺。
影片高潮极具戏剧化,而这戏剧化动作与钢琴曲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德军战败前夕,因饥饿寒冷而濒于死亡边缘的瓦瑞躲在一幢废弃的阁楼藏身,楼下却传来了德国人弹奏的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声音,《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柔板,旋律平静、祥和,与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形成巨大反差,流露出演奏人极为复杂、矛盾的心理。但是这个旋律对于饥饿中的瓦瑞来说,如同另一个世界的声音。许久,瓦瑞估计德国人已经离开,于是走出阁楼想方设法撬开好不容易找到的罐头,罐头不小心坠落到地上,滚落在一位德国军官的靴子旁,空气在瞬间凝滞了,濒临死亡的瓦瑞终于看见了死亡的光环!
德国军官把他带进一间房间,房间中央有一架钢琴!面对钢琴,瓦瑞沉默了,他慢慢的在钢琴前坐下,似乎考虑了一下什么,一段略显迟疑的开场白后,曲调变得流畅,于是肖邦的《第一号叙事曲》随着钢琴黑白琴键的跳跃飞快地洋溢出来,空洞洞的房间瞬间有了生机。在黑暗的世界里,音乐穿过黑幕,成为生命中的微光,它竭尽全力呼唤着人类已经泯灭的人性。
肖邦的G小调《第一号叙事曲》(OP23),是肖邦全部四首《叙事曲》中最为著名的第一首。钢琴曲取材于密茨凯维支的叙事诗《康拉德·华伦洛德》,这部长诗叙述了波兰民族抵抗条顿人的故事,是一部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颂歌。瓦瑞在死亡的面前弹奏起了波兰最伟大的钢琴家肖邦的作品,这与德国军官在战败前夕弹奏《月光奏鸣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德国军官走到一把椅子前坐下,开始聆听瓦瑞的演奏。短促的、忧郁的曲调过后,忧郁逐渐变成了暴风雨般的悲愤,这时候弥漫在空气中的是正邪之间激烈的人性较量。随着一段忧伤咏叹,月光洒满了荒无人烟的残垣断壁,逆光中的瓦瑞似乎在回忆过去美好宁静的生活。钢琴上的纳粹军帽暗示着潜在的危机,突然琴声展现出的灵敏的警觉,继而空气中又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悲愤之情,化成为势不可挡的滚滚波涛!
最后钢琴曲恢复到刚开始时的真挚、忧伤,但平静的旋律只延续了几小节,旋风般的尾声又重新卷入狂风暴雨般的激情和悲剧性冲突中!
坐在钢琴前的瓦瑞不再是先前的囚徒,而是坚强、自尊的钢琴师,是肖邦给与了他力量。德国军官显然被瓦瑞的钢琴声所打动,音乐的力量唤起了人性的苏醒,最终,肖邦战胜了希特勒。钢琴师与德国军官的地位对比在瞬间产生了变化。德国军官放了瓦瑞,甚至带给他食物与衣服。
影片结尾,在德国军官的协助下,瓦瑞坚持到了战争结束。年轻的钢琴师回到了国家电台继续为波兰听众演奏肖邦夜曲,宁静、祥和再次回到人们生活中。但是,瓦瑞并没有忘记那位救过自己的德国军官,他试图去寻找和帮助他,最终没有成功。
在肖邦辉煌的波兰舞曲中,观众知道了那位德国军官的名字威姆·豪森菲德上尉,他死于战俘集中营。
非传统的叙事策略
这部影片不同于波兰斯基以往作品的叙事风格,他用剧中人物主人公的主观视点贯穿全片,通过近乎纪实的手法平铺直叙的展现钢琴师个人的二战遭遇。影片似乎带有真实电影的美学意味,然而深入分析波兰斯基的创作动机,会发现其作品中的真实观念并非是一种创作方式,而是影片作者情感的真实再现。
波兰斯基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曾被问及在创作中是否考虑当代观众的观影习惯,他特别强调:“你身上发生的一切经历都会影响你创作,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而当代观众在电视的巨大影响下,已经习惯了快节奏,电影语言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我对时髦不感兴趣,我拍片就是拍我的片子,我希望自己满意,也希望观众能分享我的口味。”于是,波兰斯基惨痛的童年经历形成了他对二战影片的“潜意识”情结,用亲身经历再现波兰犹太人蒙难的历史成了影片极为深刻的情感特征。如何真实再现这段特殊的情感记忆,成为波兰斯基制定影片《钢琴师》叙事策略的基础。
波兰斯基的这部作品是继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之后又一部反映二战犹太人遭受大屠杀的巨片。同样是表现幸存这个概念,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在影像上追求黑白纪实风格,但在叙事上延续了传统的剧作手法;而波兰斯基的《钢琴师》正好与之相反,他在影像上极力还原童年记忆中的色彩,但在叙事结构、甚至在镜头语言上完全采取第三人称主观视点的纪实手法。
虽然《钢琴师》的拍摄剧本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而成,但波兰斯基规避了文学改编电影的许多特征。比如在剧作结构上,自传体回忆录及影片常常会选择倒叙的手法,随着主人公画外音娓娓道来,影片故事随之展开。波兰斯基并没有遵从常规叙事的办法,而是用顺时空方法展开历史的一段真实记忆。在影片视点上,波兰斯基也摒除了以我为叙事视点的外在主观视点方法,而是用第三人称视点的方式展现剧中人物的内心主观视点。这样,波兰斯基就可以与剧中人物主人公完全认同,主人公的眼睛宛如童年的波兰斯基,带着观众走入尘封已久的人类杀戮中去。影片中,一切外部冲突都是通过钢琴师的眼睛来观察的;影片开始,钢琴师作为上流社会的宠儿,对社会动荡明显带有一种冷眼旁观的高傲,这时观众看见全副武装的德军开进华沙的时候,有如在观看一段历史纪录片,并没有感觉到主人公内心的紧张感,对战争尚有一种间离感;但随着主人公不断地目睹犹太人的生命被纳粹所随意扼杀,主人公的内心压力越来越紧迫,直至影片的外部冲突直接威胁到主人公的生命时,观众就被完全融入影片的情境中了。视点外在距离的间离和心灵距离的拉近,成为《钢琴师》叙事风格的核心策略。这与布莱希特的戏剧间离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钢琴师》被贴上真实电影标签的原因之一。
影片对真实细节的追求也成为波兰斯基纪实风格的标志,影片中各种细节无不将历史的真实和作者的情感真实捆绑在一起。波兰斯基在研究大量二战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了纪录片的拍摄视角,无论是画面中的景物还是摄影机的拍片角度,都严格遵守二战纪录片资料还原而成。波兰斯基甚至在影片中加入了德国的纪录片工作者拍片的画面,这表示出一个电影人对电影纪录的美学思考。一方面,人类的各种行为被电影记录者冷静的客观记录着,不管记录者的意识形态如何,真实场景的再现总能够唤起人类复杂的情感记忆。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电影的作者总是在试图将自己的真实情感“还原”成历史的“原貌”,是历史成为带有个人“情感特征”的历史。
《钢琴师》不仅摈弃了传统电影的叙事策略,而且还超越了传统的冲突观念,波兰斯基将戏剧性冲突集中在面对“生与死”的人性思考上。他在写实风格的基础上,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和强烈情绪,使得观众在清醒的意识中对那个时代人们经历的感受得以与作者、剧中人物认同,超越了电影剧作结构上假定性的局限。
波兰斯基选择了这种难度非常大的非传统叙事策略。《钢琴师》在剧作结构上有几种划分办法,第一种分法是前文所讲的传统结构,按钢琴师与钢琴曲的命运分为四个段落;第二种分法,就是按照钢琴师逃亡的过程划分,可分为三个到五个段落,即从钢琴师被犹太警察拉下火车开始,之前为开端,逃亡为叙事核心,结尾是逃亡成功;第三种分法,就是按照核心人物冲突来划分影片的剧作结构,这样的情况下,核心冲突双方建立冲突之前都被称作是影片开端,于是整个影片百分之九十的片长都是开头,冲突的发展、高潮、结尾总共只占到全片的百分之十。
在第二种和第三种结构法的开头部分,波兰斯基在形式上不仅完全摒弃了对观众的主观引导,甚至没有为之建立对立人物和女主人公,大量纪实性的平铺直叙,仿佛是主人公生活的流水帐。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由影片作者在开头部分建立的影片主题反而由观众自主地完成了,观众在冷静、理智中建立起对人性的思考,所以在片尾一旦当核心冲突建立的时候,观众会感觉到眼前一亮,更加主动的缝合进作者的叙事中了。
无论是第二种结构法还是第三种剧作结构,《钢琴师》的成功足以说明波兰斯基非传统叙事策略的成功,而这种成功较之传统剧作法更为杰出。无独有偶,华人导演李安在《饮食男女》中也选择了类似的剧作结构,同样引起了巨大的艺术效果。
人物设置及隐含主题
影片《钢琴师》的人物设置是与波兰斯基的叙事策略完全吻合的,基本上是以散点的办法勾勒出为数众多的次要人物和背景人物,然而停留在线性叙事上的主人公似乎只有一个:钢琴师。没有与之情感纠葛的女主人公,也没有从头至尾贯穿的对立人物,这在一般的影片剧作中是很难想像的,更不用说在长达三个小时的叙事中始终把握住观众的脉搏了。
波兰斯基在影片人物的设置技巧上,完全保持了史诗性传记片的特点,在设置态度上也保持着重述历史的冷峻严肃,不仅让观众与剧中人物时刻保持着一种距离感,而且让人物之间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在整部影片的拍摄中不仅隐忍克制着自己的情感,而且还在强烈的抑制着剧中人物之间的情感。这种情感的抑制并不是忽略情感,而是令观众更加冷峻的看待人情冷暖和生存问题。饶有趣味的是,在整部影片里,那些真心帮助钢琴师逃亡的人物外表都极为冷漠,甚至故意令观众对他们产生怀疑的心理,然而就是他们真正的帮助了钢琴师;相反,有一名表情丰富的、外表和蔼的地下抵抗成员,却打着帮助华沙犹太人的名义,筹集大量资金潜逃。令观众对人物情感产生更多的思考。在那个年代,犹太人无论是逆来顺受、还是奋起反抗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活下去。
正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亲身体验,在波兰斯基的眼里,影片中人物之间是靠生存关系来联系的,而这些联系又透露出主人公戏剧性的命运转折。
如果说,这部影片中有一个核心对立人物的话,那就是片尾的德国纳粹军官,虽然他只出现了几场戏,但是他对整部影片所起的意义远远地超出了这个人物的本身,从而引起观众对战争、对人性的更多思考。
这名德国纳粹军官没有明显的个人特征,这让观众常常会产生幻觉,似乎音乐代表着尚未泯灭的人性,而这名德国纳粹军官则是人性尚存的德国军人的群像缩写,他们的人性深处也酝酿着不安与恐惧。如果波兰斯基的创作意识中真有这样痕迹的话,那么战争带来的痛苦就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那些处于人性煎熬中的德国军人!如果这种解读成立,那么影片主要对立人物也就成立了,与钢琴师始终纠葛在一起的德国侵略者也就可以理解成对立人物的群像。那么纳粹对犹太人施暴就成为对全人类的犯罪,片尾那些集中营里的德国军人同样也成为这场杀戮的受害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影片《钢琴师》就显露出人性宽容的隐含主题,它超越了个人幸存的思考,上升到对人类生存的一种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