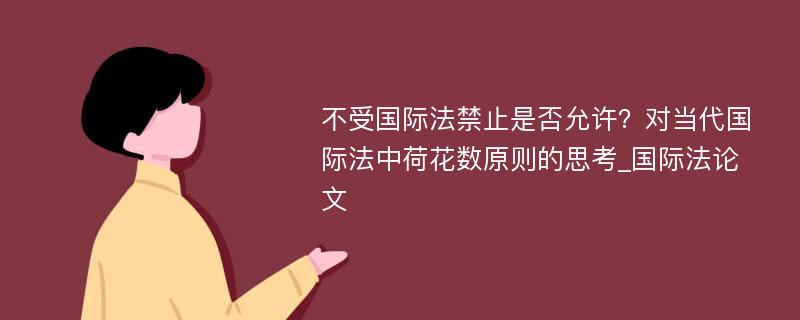
国际法不禁止即为允许吗?——“荷花号”原则的当代国际法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法论文,即为论文,当代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国际法不禁止即为允许”是最经常援引的一个论断。国家主张其行为的合法性往往不是依据国际法的积极授权,而是依赖于国际法上不存在相反规定。例如,在2010年“科索沃宣告独立”咨询意见案中,国际法院认为,一般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1244(1999)号决议都没有禁止科索沃宣布独立,因此科索沃单方面宣告独立的行为本身并不违反国际法。①
上述实践涉及国际法上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在国际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是否存在一个基本假定,可以初步判断有关行为或情势合法与否。事实上,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如何判断一个行为或情势的合法性,是任何法律体系都要解决的问题。在公法领域,行政机构的权力一般限于宪法或法律的明文授权,“法无授权即禁止”;而在私法领域,公民的自由则以法律不禁止为边界,“法无禁止即自由”。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假定体现了不同的法律政策和价值取向:在公法领域限制公权力的自我扩张,在私法领域则尽可能保护个人自由。
国际法不禁止即为允许这一原则又称“荷花号”原则,源于国际常设法院在“荷花号”案中的判决。法院在该案中提出了国际法的一个基本论断,即对独立国家的限制是不能假定的。根据“荷花号”原则,国际法是由禁止性规范构成的法律体系,在国际法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下,国家享有主权和自由。因此,“荷花号”原则可以说是国际法高度实证化的一个经典表述。与此同时,“荷花号”原则间接支持了国际法体系是一个私法体系的观点:国际社会中的国家类似于国内法上的个人,国际社会不存在高于国家主权、超越国家同意之外的公共秩序。
然而,“荷花号”原则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其强烈的实在主义导向经常受到国际法学者的批判,“荷花号”原则已经过时的主张也不绝于耳。如何看待“荷花号”原则,恐怕是每个国际法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荷花号”原则的争议何在,又该如何解决?在国际法从共存法向合作法演进的过程中,特别是保护人权原则受到高度重视的今天,“荷花号”原则是否依然是当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自身是否已经受到修正?本文将结合国际实践和学者学说,分析“荷花号”原则涉及的若干争议问题,以求揭示当代国际法的基本结构及其最新动向。
一 “荷花号”原则的产生
1926年8月2日,法国邮船“荷花号”在地中海的公海与土耳其船只“博兹—库特号”碰撞,“博兹—库特号”被撞沉,8名土耳其人死亡。在“荷花号”抵达伊斯坦布尔港之后,土耳其当局对这起事件进行了调查,以过失杀人罪逮捕了“荷花号”大副、法国海军上尉戴蒙(Demons)和“博兹—库特号”船长、土耳其人哈森·贝(Hassan Bey),并提起刑事诉讼。1926年9月15日,土耳其法院判决戴蒙80天监禁和22英镑罚款。法国对此提出抗议,要求释放戴蒙,或者将该案移交法国法院审理。随后两国达成一项特别协定,同意将此案提交国际常设法院,请求法院裁判土耳其对法国公民戴蒙的审判是否违反国际法原则。②
法国主张,公海碰撞案件的刑事管辖权专属于船旗国,因此法国享有对戴蒙的排他管辖权,作为遇难船员国籍国的土耳其对法国公民采取刑事措施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③土耳其则主张,土耳其是对其本国船舶“博兹—库特号”船长哈森·贝行使刑事管辖权,而戴蒙是因为关联犯罪而被起诉,这符合各国的实践。此外,土耳其还主张,并无任何国际法原则禁止土耳其行使刑事管辖权。④法院最后支持了土耳其的主张,认为其行为并不违反国际法。
在判决的主文部分,法院就法律适用问题做出了一个经典表述:“国际法支配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国家有拘束力的法律规则产生自国家本身的自由意志,这种意志体现在公约或者……惯例。因此,对独立国家的限制是不能假定的。”⑤该表述在此后的公法学说和国家实践中被反复引用,“荷花号”案也由此成为国际司法实践中最重要的经典案例之一。
“荷花号”原则涉及不少具有根本性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问题,⑥但其最核心的论断是:国际法源于国家意志,除非国家自愿接受国际法约束,否则国家享有绝对主权和行动自由。不少国际法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更是把这一论断夸大或简化为“国际法不禁止即为允许”。“荷花号”原则看似简单明了,非此即彼,但在实践中却往往是国际争端的焦点所在,理论界对此的态度也是高度对立。本文第二部分将试图澄清“荷花号”原则的争议。
二 “荷花号”原则的理论争议及其解释
恐怕没有哪个国际法原则比“荷花号”原则更具争议性。在六票对六票的情况下,国际常设法院院长马克斯·胡伯(Max Huber)法官投出决定票通过了判决。六名法官对该案发表了反对意见,其中洛德(Loder)、魏斯(Weiss)、芬利(Finlay)和尼霍姆(Nyholm)四位法官明确反对“荷花号”原则。例如洛德法官就批评说,这个原则将国家自由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不利于国际法的发展。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少国际法院法官⑧和知名国际法学者⑨都认为“荷花号”原则已经过时,不适用于当代的国际法实践与发展。尽管如此,实践中“荷花号”原则却仍是被各国援引最多的国际法原则。国际法院的态度则是暧昧不明,其在若干案件中都直接或者间接涉及“荷花号”原则,但却从未引用或依据该原则来裁判案件。
实际上,关于“荷花号”原则的争议一定程度上源于国际法学者自身的职业偏好,因为绝对主权一直以来都被国际法学者视为对国际法的最大威胁。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则在于学者将“荷花号”原则脱离其上下文和案件具体情况,忽视判决表述本身的自我限定,从而将之扩大为抽象的绝对原则。
因此,在这里有必要重读“荷花号”案的判决。在法律适用部分,国际常设法院首先陈述了“荷花号”原则,紧接着就限定说,国际法对主权国家的基本和首要的限制在于,一国不能在他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在此意义上,管辖是领土性的;除非基于国际习惯或者条约的许可性规范,否则一国不得在其领土范围外行使管辖权。”⑩简言之,一国在行使领土管辖权的时候,也要尊重他国的领土管辖权;但在领土管辖范围内,国家的管辖则不依赖于国际法的许可性规则。“在此情况下,能要求国家的仅仅是它不得越过国际法对其管辖的限制;在这些限制内,行使管辖的权利基于其主权。”(11)可见,法院在“荷花号”原则中对主权国家管辖权的肯定是以领土管辖为基础的,因此在事实上限定了“荷花号”原则的适用范围。
借鉴米歇尔·拜尔斯的研究,以领土管辖为标准,国际法规则可以大致分为内部规则、详见本文第四部分。分界规则和外部规则三类。(12)内部规则是指涉及一国在领土管辖范围内处理内外事务的主权权利的国际法规则,例如外国国家和财产豁免规则、市场准入要求、进出口产品公共卫生与检疫等;分界规则是指涉及划定主权国家领土和管辖范围的国际法规则,例如领海宽度、基线方法、大陆架划界等;外部规则是指涉及一国在其自身领土管辖之外——例如在国际公共区域或者他国领土范围内——行使特定权力的国际法规则,例如保护环境和人权、打击海盗、公海登临检查等。(13)
具体来说,“荷花号”原则适用于内部规则。换言之,除非有条约或者习惯法的限制,否则国家可以在其领土管辖范围内自由处理内外事务,国家的权利不依赖于国际法的许可性规则。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一国对其本国国民的属人管辖。在这两个领域内,如果一国质疑他国行为的合法性,那么质疑国有义务证明他国违反了特定国际法义务。因此,“荷花号”原则的有效性是基于自我限定,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把“荷花号”原则解释为“国际法不禁止即为允许”这样一个没有限定的绝对论断本身就是错误的。
“荷花号”原则不适用于分界规则。这类规则涉及对国家管辖权边界的限定,无法适用“荷花号”原则,因为每个国家都可以主张其国家主权自由,最终裁判必须依赖于特定国际法规则。例如,在1949年“英挪渔业案”中,挪威就采取了“荷花号”原则的策略,请求国际法院判定其渔业划界法案不违反国际法,而不是有国际法的授权或许可。但法院认为,虽然挪威的基线方法并不违反国际法,但“海洋划界必然有其国际方面;它不能仅仅依据沿海国表达在国内法中的意愿……其划界行为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有效性取决于国际法。”(14)换言之,一国对其领土管辖的划定需要有其他利益相关国家的同意或者默认,或者明确的国际法依据,而不能仅仅依据“荷花号”原则。
“荷花号”原则也不适用于外部规则。关于这一点,国际常设法院在“荷花号”案中有明确表述:“除非基于国际习惯或者条约的许可性规范,否则一国不得在其领土范围外行使管辖权。”(15)主权平等意味着主权的相互尊重和不干涉,一国不得因主张自身主权而损害他国主权,非经国际法规则特别许可不得在他国领土管辖范围内行使管辖权。
总之,在涉及分界规则和外部规则的情况下,“荷花号”原则所能起到的作用仅仅在于一国可以将之作为法律基础来主张权利,但这种主张并不当然具有国际法上的合法性。这种权利主张的合法性的最终判定必须要有明确的国际法依据:或者是特定国际法规则的授权,或者是其他国家明示或者暗示的同意或承认。
三 二战后国际实践对“荷花号”原则的影响和修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法调整范围不断扩大并且向纵深发展,从国家间外交和国际政治等传统领域扩展至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涵盖交通、通讯、贸易、劳工保护、货币政策、投资、物价、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把越来越多原本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吸纳进来。(16)一般认为,国际法已经从共存法阶段走向合作法阶段,“合作法”或者“合作国际法”的概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接受。通过在上述领域内大量缔结国际条约,国家承担了广泛的合作义务,使得“荷花号”原则的适用范围在实体法层面进一步缩小,即使是在领土管辖范围内,主权国家的行动自由也日益受到国际法的限制。
(一)国际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对“荷花号”原则的影响
国际组织广泛建立并成为国际社会重要成员,是二战以后国际法最为显著的发展之一。自1949年国际法院发表“赔偿案”咨询意见之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得到了广泛承认,(17)国际组织成为有限的国际法主体,相对于其成员国拥有一定的独立性。
国际组织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暗含权力,即国际组织享有的权力并不以其组织文件明文授权为限。关于暗含权力的法律基础,国际法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明示权力基础说,以哈克沃斯(Hackworth)在“赔偿案”中发表的反对意见为代表。他认为:“该组织享有一种源自授权和明文列举的权力,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以假定成员国意图授予该组织的权力规定在宪章或者成员国缔结的补充协议中,但不能轻易假定没有被明确授予的权力。暗含权力来源于明示权力,并且限于为行使已经授予的明示权力而有必要享有的权力。”(18)根据这种观点,暗含权力应当以组织文件明确授予的权力为基础,在行使该明示权力所必需的范围内,国际组织可以享有有限的暗含权力。因此,从根本上说,国际组织的权力必须基于国家明示或者暗示的同意。
另一种观点是职能说,认为国际组织可以在其职能范围内广泛和一般地享有暗含权力。国际法院在“赔偿案”咨询意见中就持此种立场:“在国际法上,该组织必须被认为享有那些虽未明文规定在宪章中,但可通过必要推论得出的、对于履行其义务至关重要的权力。”(19)以国际组织的职能作为暗含权力的基础,要比以明示权力作为基础宽泛得多,但法院的解释从根本上背离乃至否定了传统的“荷花号”原则在国际组织框架下的可适用性:暗含权力的推论过程并不等同于探寻当事方的真实意图,当事方的意图甚至被认为与此无关。(20)虽然有观点认为国际法院在该案中对暗含权力的广泛解释仅适用于联合国,但实践表明暗含权力说在此后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其适用范围并不仅限于联合国。(21)
国际组织虽然是依据国家间的条约而成立,但必须承认,“一个机构一旦成立,就独立于产生它的因素而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必须依据国际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创立者的意见来发展”。(22)国际组织的权力扩张对“荷花号”原则构成了第一次实质性冲击。国际组织可以履行其宗旨和目的为由,在缺乏成员国明示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进行权力的自我扩张,从而实质性地扩展国家在章程下承担的义务。换言之,在国际组织与成员国关系问题上,“荷花号”原则并不适用。
(二)人权人道原则对“荷花号”原则的修正
人权法和人道法的蓬勃发展构成二战后国际法发展最重要的方面,人权人道原则对于荷花号原则的影响更为根本。
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同样的措辞在序言中载明,“确认此种权利是源于天赋人格尊严”,(23)亦即人权是人所固有的。奥斯卡·沙赫特分析说,这个假定意义重大,它意味着人的权利不来自于国家或者任何其他外在权威。(24)这个论断从根本上否定了国际法的实在主义基础。从国际法的内容和调整对象来看,国际法不但调整国家间关系,赋予国家权利,而且赋予个人权利。这种个人权利具有一定客观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人权义务的对世性。从法律渊源的角度来看,在国际人权法的形成和确认过程中,国家意志仅仅是一个辅助性要素。(25)这表明,随着人权的兴起,当代国际法不再是“荷花号”原则所说的纯粹的国家间法,国家也不再能垄断国际社会的造法活动。
更重要的是,人权人道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法的基本假定。首先,在国际法的价值导向方面,人权成为和主权相竞争的价值因素,此消彼长,相互博弈。(26)其次,在人权人道事务方面,在缺乏特定实在法规则的情况下,国家有义务善意行使国家权力,避免侵害人权。“荷花号”原则的假定是在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内法不禁止则属国家自由,但当涉及人权人道事务时却要优先推定个人权利而非国家自由,国家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限制必须有正当理由。这方面的典型是《〈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条第2款,即所谓“马顿斯条款”(Martens Clause)。该条款规定:“在本议定书和其他国际法律协定所未包括的情况下,平民和战斗员仍受来源于既定习惯、人道原则和公众良心要求的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支配。”(27)
因此,人权法和人道法的发展使得“荷花号”原则的可适用性进一步缩小。即使是在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内,当涉及个人自由与权利时国家的自由也不是无限制的。国家首先要遵守和履行有关条约和习惯下的义务;即使不存在相关条约或习惯,国家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限制也必须有正当理由。这意味着当代国际法并不假定国家在人权和人道领域享有任意自由。换言之,即使是在主权国家领土管辖范围内,“荷花号”原则也仅仅适用于不涉及人权和人道事务的事项。
(三)全球化对“荷花号”原则的影响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研究的基本社会背景。全球化的首要特征就是“非国家化”,在此意义上与国际化有着根本区别。(28)在国际法层面,全球化对领土原则构成严峻挑战,以领土边界为管辖边界的传统国际法体制受到日益广泛的质疑。
环境污染、国际犯罪、恐怖主义、传染病和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危害和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行为发生地国家,其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也无法通过单个国家的行动来实现。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体系并不能充分满足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治理需要,因此全球化促使各国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生活的组织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生活的这种需要。(29)在此意义上,全球化进程定义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但这只是全球化的一面。全球化的另一面是单边主义。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国家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从贸易和投资扩展到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此情况下,很少有什么主权行为能够真正被认为是纯国内的,一国在其领土管辖范围内的主权行为往往会发生一定域外效果。而且,除领土管辖外,国家还可以依据属人原则、保护性原则和普遍管辖原则行使管辖权,从而扩张自身利益。很多时候,一国并不是要求其他国家积极从事特定行为或承担特定义务,而是要求后者承认或者默认一国领土管辖内主权行为的域外效果。例如,美国经常以违反美国国内法为由对其他国家的公司和个人进行制裁。这在本质上是管辖权冲突问题:在国际法上,各国有权依据其各自的法律连接点来进行管辖,但国际法缺乏相应规则来解决管辖权的冲突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解释“荷花号”案。该案同时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土耳其在国际法上是否有管辖权,二是法国作为船旗国是否享有专属管辖权从而能够排除土耳其的管辖。这本质上也是管辖权的冲突问题。国际常设法院仅仅用“荷花号”原则肯定了土耳其在国际法上的刑事管辖权,但并未用此原则来解决管辖权的冲突问题。“荷花号”原则仅仅是管辖权的基础,并不能解决管辖权的冲突问题。换言之,冲突的解决需要明确的条约或习惯规则。此后的1958年《公海公约》第11条和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97条均规定,在公海上发生碰撞或任何其他航行事故,在追究船长或任何其他为船舶服务的人员的刑事责任时,船旗国享有专属管辖权。
可见,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领土范围对不涉及人权和人道事务的事项行使管辖权也有可能受到其他国家或组织的挑战和影响。“荷花号”原则仅仅是管辖权的法律基础,并不必然能够保证管辖的有效性得到其他国家承认,也不能保证主权国家有效对抗他国的长臂管辖。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主权扩张往往建立在牺牲或削弱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荷花号”原则往往成为大国、强国扩张自身权力和管辖范围的借口。
四 与“荷花号”原则有关的国际法基本问题
“荷花号”原则至少涉及如下几个国际法核心问题:
首先,用菲茨莫里斯的话来说,到底是国家权利源自国际法,还是说国家权利原则上是无限的,仅仅受到国际法的限制?(30)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触及国际法的根本,涉及国家权利的基础、国家主权与国际法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法治化。倘若国家权利来源于国际法,那么一国行为的合法性就需要有国际法规则的依据;换言之,国家权利来自于国际法的授权。而倘若国际法仅仅构成国家主权的限制,那么国家就是无限自由的,除非受到特定国际法规则的禁止。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国际法的一个核心假定,即承认国家的自由意志还是坚持国际社会的法治。总体来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家主权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法授权的权利。
其次,在国际关系和国际诉讼中,国家行为的合法性是取决于国际法的许可性规则,还是说国际法不禁止即为允许?在“荷花号”案中,法国和土耳其提交法院的特别协议中请求法院裁定土耳其的管辖是否违反了国际法。(31)法院认为,当事方的提问方式(是否违反国际法)是由国际法的性质和当时条件所决定的。(32)在“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案中,“荷花号”原则也是一个争议焦点。不少国家主张,法院应该回答的是国际法是否禁止使用核武器,而非其是否允许使用核武器。法院认为没有必要介入措辞上的争论,关键是在国际法上判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33)但在事实上,禁止和许可的两分法支配着法院的整个推理过程。(34)在作者看来,在分界规则和外部规则中,法院不能简单通过许可或禁止来判决案件,因为案件本质上涉及的是利益的平衡和管辖权的分配,有必要赋予法院一定自由裁量权,而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法律裁判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法院有效履行司法职能。事实上,在判断一国行为的合法性时,如果该行为纯属国内管辖事项,那么该国只需要主张“荷花号”原则即可证明合法性;但若该行为涉及管辖权冲突和划界,或者属于外部规则,那么不论是否有确定的可适用的条约或习惯法规则,其合法性都来源于具体的国际法规则。
再次,“荷花号”案涉及国际诉讼中的举证问题。如果假定国家权利除了国际法约束之外是无限的,那么原告就负有举证义务证明被告违反了国际法规则;但若假定国家权利来源于国际法,那么被告就有责任证明本国规则合乎国际法或者得到国际法授权。这样在特定国际法规则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诉讼结果将取决于当事人的原告或被告身份。对此国际法院的态度是:“法院作为一个国际司法机构,被要求对国际法加以司法认知,因此对于有关《国际法院规约》第53条的案件,与其他任何案件一样,由法院依职权考虑所有可能与争端解决有关的国际法规则。在案件的特定情况下确定和适用有关法律规则是法院自身的义务,确立或证明国际法规则的责任不能施加给当事方,因为法律属于法院的司法知识。”(35)但在实践中,如果一国在内部规则所涉事项上受到他国指控,那么其他国家有责任证明这个国家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相反,在涉及边界规则和外部规则的情况下,主张权利的一方有责任证明其行为拥有国际法的授权或许可。
最后,“荷花号”案涉及法律不明时如何处理的问题。尽管国际法院原则上不承认存在法律不明的情况,但在涉及边界规则和外部规则时,事实上经常存在无法可依的情况。这方面最经典的案例是“北海大陆架”案,国际法院认为1958年《大陆架公约》规定的等距离中间线原则并没有成为习惯法,因为德国虽然签署但尚未批准该公约,所以等距离中间线原则不能适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可依,仍然有规则可以适用,那就是公平原则。法院认为公平原则并非抽象的正义,也并非《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2)款所称的“依公允及善良裁断”,而是一项确定的国际法规则。(36)这恰恰表明,边界规则往往涉及利益的平衡与分配,以及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对此国际法往往缺乏具体规则,因而日益依赖于公平原则。
五 结论
正是基于其根本重要性,“荷花号”原则最能体现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与变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国际人权运动的兴起,“荷花号”原则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荷花号”的沉没意味着民族国家已经不足以作为全球化时代下国际治理的充分条件,意味着人类生活有了更多的国际性或全球性话题与事务,也意味着国际法学者在国家法治建设和全球化进程中的话语权正在增加。但这仅仅只是表明过分简单化的“荷花号”原则已经无法满足全球化条件下高度复杂的社会生活,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拥有超越“荷花号”原则的新的立法技术和制约霸权强权的技术,也不意味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性法律的出现。相反,在“荷花号”原则走向衰落的同时却没有出现充分的国际法规则来规范和调整国家间关系,使得国际法对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缺乏制约。在一定意义上,对公平原则和人权原则的高度依赖恰恰也意味着国际法的确定性和规范性在日益降低。我们没有理由对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法治盲目乐观。
“荷花号”原则的弱化同时也意味着实在法学说的衰落。传统国际法对于法律的理解不过是国内法上法律的概念在国际法层面的延伸。实在法学说的经典代表是奥斯汀,他认为法律主要是指一个具有政治优势者角色特征的最高统治者或者主权者主体所作的直接或者间接命令。(37)如果将实在主义理论引申到国际法,那么国际法就是主权国家之间意志协调的产物,或者说是共同同意。(38)“荷花号”原则正是在国际法层面体现了这种实在法的理念。实在国际法的社会基础是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由这个中央化的权力对其他社会主体制定法律。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民族国家的权力正在削弱,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权力则在扩大,传统的实在法模式的立法形式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国际社会生活需求。“荷花号”原则的衰落正说明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权力和知识生产模式无法充分满足全球化的国际生活,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国际社会治理的职能。
对“荷花号”原则的分析还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国际法不成体系的问题。(39)国际法的不成体系,其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国际法规则的大量产生,而在于各个相对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国际法部门及其对应的国际机构有着各自的内在价值偏好。例如,人权机构强调人权的优先性,而世界贸易组织则强调贸易与投资自由。虽然这些法律部门和机构的有效运作并不能完全脱离其他部门的国际法,但是每个机构都有其独立的目的和宗旨,因此其他部门的规则是由这些机构在其自身偏好的基础上解释和适用。正如科斯肯涅米教授指出的,最好将这些机构比作主权国家。(40)每个机构都有自身的运作逻辑,每个机构都在创建自身的法律秩序,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荷花号”。在这个意义上,一般国际法的重要性在下降,学者的理论正在逐步让位于机构的实践。
注释:
①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n,Advisory Opinion (22 July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41/15987.pdf,last visited on 30 April 2011.
②Lotus case,P.I.C.J.,Ser.A.,No.10,pp.10-12.
③同上,第7-8页。
④同上,第9页。
⑤同上,第18页。
⑥详见本文第四部分。
⑦Lotus case,p.34。
⑧参见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Alvarez,Fisheries case,Judgment of December 18th,1951:IC J Reports 1951,p.152。例如,威拉曼德里法官认为没有特别的禁止性规则并不等于国家有绝对自由,并且认为荷花号原则只适用于平时法,而不适用于人道法,参见Dissenting Opinion of Judge Weeramantry,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Advisory Opinion,pp.492-496。
⑨参见Gerald Fitzmaurice,"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1951-54:General Principles and Sources of Law",30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10(1953)。
⑩Lotus ease,pp.18-19.
(11)Id.,p.19.
(12)参见Michael Byers,"Custom,Power and the Power of Rules: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17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9,149-155(1995-1996)。
(13)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对这三类规则的解说与米歇尔·拜尔斯的原文略有不同,所举例子也不尽然是拜尔斯原文中所列。
(14)Fisheries case,Judgment of December 18th,I951:ICJ Reports 1951,p.152.
(15)Lotus case,pp.18-19.
(16)参见W.Friedmann,"Some Impac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on International Law",50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75,476(1956)。
(17)参见饶戈平,《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中外法学》,2003年第3期。
(18)Dissenting Opinion by Judge Hackworth,Reparation for the injuries suffer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Advisory Opinion:ICJ Report 1949,p.198.
(19)Reparation for the injuries suffer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Advisory Opinion:ICJ Report 1949,p.182.
(20)参见Krzysztof Skubiszewski,"Implied Power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in Yoram Dinstein (ed.),International Law in a Time of Perplexity:Essays in Honour of Shabtai Rosenne (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9),pp.860-861。
(21)参见饶戈平,蔡文海:《国际组织的暗含权力探析》,《中国法学》1993年第4期。
(22)Dissenting Opinion by Mr.Alvarez,Admission of a St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Art.4),Advisory Opinion:ICJ Reports 1948,p.68.
(23)王铁崖、田如萱:《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166页。
(24)参见Oscar Schachter,"Human Dignity as a Normative Concept",7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48,853(1983)。
(25)这在人权习惯法领域表现为,只要有充分的法律确信,国家实践所需要达到的标准就不那么严格。有关理论参见Anthea Elizabeth Roberts,"Traditional and Modern Approaches to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A Reconciliation",95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57 (2001); Frederic L.Kirgis,"Custom on a Sliding Scale",81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46 (1987)。
(26)参见李鸣:《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人权定向对主权定向》,2009年中国国际法年会主题发言。
(27)《〈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条第2款,载白桂梅、李红云主编:《国际法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页。
(28)参见Jost Delbrück,"Globalization of Law,Politics,and Markets-Implications for Domestic Law-A European Perspective",1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9,10-11(1993-1994)。
(29)参见饶戈平、黄瑶:《论全球化进程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关系》,《法学评论》2002年第2期。
(30)参见Gerald Fitzmaurice,"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1951-54:General Principles and Sources of Law",p.8。
(31)有意思的是,芬利法官在反对意见中认为,法院应当回答的问题是国际法原则是否授权土耳其行使刑事管辖权,而并非国际法是否禁止土耳其行使管辖权。参见Lotus case,p.52。
(32)Lotus case,p.18.
(33)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Advisory Opinion,pp.238-239.
(34)法院首先考察了国际法上的授权性规则,结论是不存在授权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法规则的结论;随后考察了禁止性规则,结论是不存在全面和普遍禁止使用核武器的规则。之后,通过考察国际人道法的发展,法院认为使用核武器一般而言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原则和规则的,但其无法判定一国在生死存亡关头进行自卫的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
(35)Fisheries Jurisdiction (United Kingdom v.Zeeland),Merits,Judgment,ICJ Reports 1974,p.181.
(36)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Judgment,ICJ Reports 1969,pp.46-48.
(37)参见(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页。
(38)《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即认为国际法的效力依据是共同同意,参见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王铁崖等译,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8-10页。但是奥斯汀本人认为国际法不是真正的法律,而只是实在道德,参见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第148页。
(39)参见Martti Koskenniemi,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UN Document A/CN.4/L.682,13 April 2006。
(40)参见Martti Koskenniemi,"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w-20 Years Later",20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7(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