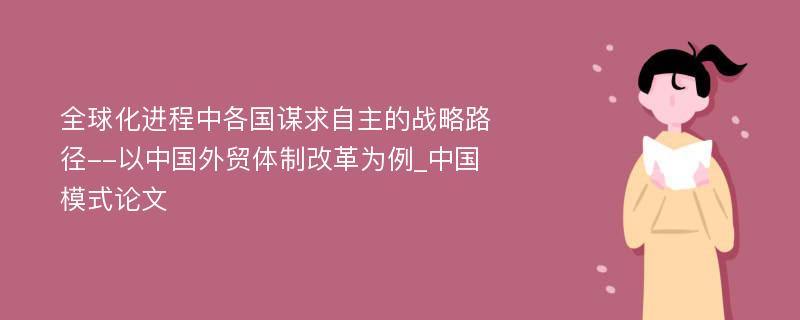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寻求自主性的战略路径——以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体制改革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自主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的来说,改革开放的过程包含着三个彼此联系却又相互区分的进程,即发展的进程、市场化的进程及经济自由化的进程。①发展的进程指的是中国在二十多年间,启动和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实现了经济起飞,是继东亚“后发展型”国家或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之后的又一“经济奇迹”。市场化的进程则是指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也是在这一点上,很多学者将中国的改革描述为“渐进式”改革,以与前苏联及东欧的“大爆炸式”改革相对照。而经济自由化的进程涉及的是各经济部门对世界市场的开放程度。经济自由化(economic liberalization)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的主题与核心内容。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经济自由化表现为贸易自由化、金融开放以及政府对各经济部门管制的解除(deregulation)。而在中国,这一进程则与市场机制的建立几乎同步而行。作为一个处于贸易与金融全球化浪潮中的“后发展”国家,一个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国家,中国为研究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及其背后的逻辑提供了一个全新和独特的经验平台。
在有关国家与经济发展的学术议题上,国家主义者通常认为,国家干预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联性。②这一论点往往假定,一个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发展型”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模式必然与市场导向的模式相异。在经验层面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的增长经验,似乎为这种论点提供了实证支持。
不过,这些成功案例多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那时,冷战的政治需要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使它们能够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对国内市场维持一定程度的保护。而随着后冷战时期全球化浪潮的兴起,这些国家先后走上了经济自由化的道路,可供国家主义者分析的经验样本越来越少。③那么,国家主义者所推崇的后发展国家的增长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些国家一旦走上了市场导向的经济自由化道路,是否就意味着其政府已经放弃了发展战略,在全球市场力量面前退却和让步?
此外,有关干预型增长模式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s),而很少涉及转型经济中的国家与市场关系。前一类发展型国家的政府面对的是成熟的市场和界限清晰的私营部门。而转型经济中,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干预市场与否,而是如何建立市场机制。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恰恰包含了“发展型国家”研究在经验层面的缺失之处。中国案例本身并不能推翻国家主义者关于国家干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设,研究中国经验的目的也并不在此,而在于展示负有发展使命的发展型国家处理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性选择,即国家可能通过市场导向的经济自由化实现其发展战略。解读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演变及路径选择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解答国家为什么选择如此处理与市场的关系的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已有研究的解释
西方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解读主要来源于中国问题专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是谢淑丽(Susan Shirk)的“官僚政治”解释。谢淑丽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中认为,中国改革遵循的不是经济逻辑而是政治逻辑。改革的顺序和制度变革的方式是由政治领袖及各种官僚利益之间的竞争决定的。改革措施的采纳并不完全是以提高经济收益和效率为前提,而是政治协调和妥协的结果。她认为,中国改革将会是部分的、不完全的改革;全面的市场化与经济自由化不会是中国改革的可能结果。④
另外一种观点将中国改革描绘成顺畅平缓的渐进过程,认为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与帕累托累进的方向相一致。持这种观点的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认为,中国改革初期在很多领域采用的双轨制确保了整个经济体系不会在瞬间倾覆,而是让市场因素随时间逐步增长,迫使国有部门逐步加入竞争的行列。这种过程与发达国家曾经历的“解除管制”(deregulation)改革类似,当时这种改革也是有选择性地向一些经济部门引入竞争,逐步推广至整体经济,以确保改革的平稳推进。中国改革也正是在这种经济逻辑下,“从计划中成长”,走向自由的市场经济。⑤
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者之间。魏德安(Andrew Wedeman)认为,中国的改革的确是渐进型的,但其过程却不是一个均匀平缓的演进历程。改革一度如谢淑丽所描述的那样,引发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但也恰恰是这些行为和现象,削弱了国家统一控制价格的能力,从而在实际上推动了价格改革,瓦解了计划经济的制度基础。⑥
诺顿的“从计划中成长”论实质上是对渐进式改革理想化的经济学解释。在诺顿看来,双轨制和表面上看来不完整的改革都是精心设计的策略,以获取最理想的经济结果。然而,这种解释却只考虑了理性决策者的理想选择,而没有探究改革的每一个步骤可能引发的制度效应及制度内各方主体之间的互动。
与之相对,谢淑丽完全是以政治的逻辑解释改革的过程,认为改革的渐进性和局部性不完全是精心设计的结果,而往往是不同政治主体之间妥协的产物。谢淑丽所认定的改革逻辑与分权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某种契合之处,但是这一套逻辑却无法解释1992年以后中国政府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努力。谢淑丽本人也承认其理论的局限性,并试图从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跨国力量等层面解释中国政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决定。不过,这些解释引入的却都是一些临时变量,缺乏理论上和逻辑上的连贯性。⑦
魏德安的理论既顾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动态,又对市场化改革做出了解释。但是在他看来,分权化改革所引发的问题反而促进了市场化进程,而中央政府在新一轮改革中只是“使国家政策跟上经济现实变化的脚步”。从本质上来说,他的解释是纯粹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解释,认为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功也就是供需推动价格走向均衡点的过程。然而,这种以价格改革为核心的解释却低估了市场化进程的复杂性。1992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包括一系列目标和措施,价格改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地方间的竞争的确为变革提供了动力。但是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主动推进和有力措施,统一的全国市场及更加开放的经济很难从地区之间相互隔离和竞争的状态中“自我实现”。
在上述三种观点中,诺顿注重描述制度的构建,却疏于考虑制度变化本身的政治经济效应。谢淑丽和魏德安的分析从本质上来说都把制度看作理性主体互动时的游戏规则。而本文认为,要深入解释改革路径背后的逻辑,探究现时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成因,要求我们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式,将国家看作具有历史渊源的制度体,并关注改革发生和演进的历史和制度情境。在这种分析框架下,中国改革不仅仅是政治主体在既定利益条件下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还涉及国家内部结构和组织方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自主性(state autonomy),并部分地决定了其后的改革路径以及国家对待市场的方式。
现代化与发展进程中的国家与市场关系: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新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应该由市场引领,国家在其间只应起到制度维持的基本作用。⑧将此种假定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学者,倾向于将国家描绘成市场活动和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因素。在他们看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为寻租行为提供了温床,扭曲了市场运行,阻碍了经济发展。这种观点在本质上把国家当成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众多个体的集合,认为政治体系中关心自我利益的政客和官僚往往会通过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或对市场活动的某些定向干预奖励其支持者。这样做的代价是破坏了经济效率和市场的正常运行。⑨另一方面,持国家主义观点的学者将国家看作一套超越社会利益的制度,强调国家干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全力关注和引领经济发展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对于国家、特别是后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国家主义学者如查尔姆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等人在研究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奇迹时认为,所谓东亚模式就是指国家通过产业规划、对具体经济部门的选择性干预及对国际经济交往的谨慎控制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发展模式。⑩
虽然这两种观点对国家在市场活动中的作用的评价大相径庭,却都倾向于将国家与市场对立起来:国家自主性的行为一定与市场活动的取向不一致乃至相反;而一旦经济活动由市场规律所主导,则意味着国家在市场力量面前做出让步、甚至丧失部分自主性。
然而,这种对国家和市场关系的定位却存在逻辑和实证上的漏洞。如果国家真如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只是个体寻租者的集合,那么这种观点所推崇的“最低限度的国家”(minimal state)就成为逻辑上不可实现的目标,因为这些寻租者不会听凭可供其寻租的地盘缩小。这还不只是一个逻辑问题。在现实中存在很多国家主导的经济自由化和解除政府管制的例子。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与结果就对上述观点构成了现实上的挑战。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多多少少可以用中央和地方之间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来解释,那么,第二个十年中的市场化改革则是新自由主义所预期的国家行为模式无法解释的。
另一方面,国家主义者有关国家干预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也遭遇到诸多现实的挑战。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评论者将亚洲经济中的非市场因素如政府管制及不必要、不健康的政企合作关系视作危机发生的重要根源,原本被用来解释经济奇迹的东亚模式成了危机的罪魁祸首。当然,国家干预是否引起或加重了金融危机仍有待探讨。但显然,所谓东亚模式并不能解释所有成功的经济增长案例。在中国的成功经验中,政府就更倾向于利用国家现有的比较优势,参与自由贸易,而不是寻求积极的产业规划和干预性政策。
事实上,上述两种观点都把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作为自变量,论述这一变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然而它们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由具体的“历史情境”(historical context)所塑造的,因此本身也是有待解释的结果。
实际上,对现代化和发展型国家的早期研究者如亚历山大·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和阿尔波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格申克隆和赫希曼都认为,国家对待市场的方式,即国家与市场的相对关系,首先是由“后发展国家”工业化之前的具体历史和制度条件决定的。处于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国家,对于经济的促进方式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政治制度结构,与工业化进程的不同时机相结合,导致了这些国家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11)
较新的一些研究也触及不同类型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成因和逻辑。例如,加里·汉密尔顿(Gary Hamilton)和尼科尔·比加尔特(Nicole Biggart)通过比较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对国家主义者所描述的“东亚模式”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在这几个东亚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各不相同,而并非遵循“国家强力干预”的单一路径。汉密尔顿和比加尔特将国家与市场关系作为解释对象,并将其放在国家组织形式的文化历史渊源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进行解读。(12)
与之相应的,是对国家自主性的认识。国家自主性的概念来源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认为现代文官制国家(bureaucratic state)与传统国家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超越个人利益,具有“自主性”。职责清晰化、专业化的文官视完成其工作职责为己任。(13)韦伯之后,很多学者对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做了探讨,认为国家自主性是以国家制度结构的连贯性(coherence)和凝聚力(cohesiveness)为基础的,表现为国家相对于各种特殊利益保持独立性的能力。(14)东亚增长模式的研究者往往将国家自主性当成初始条件,在此基础上论证国家干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现实中的国家结构与韦伯的理想国家之间存有差异。例如,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在《嵌入式的自主性》一书中,探索了国家结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塑造作用。埃文斯认为,韦伯所设想的具有内部连贯性和凝聚力的自主性国家并不是在任何现实条件下都可能存在的。根据国家组织形式及国家与社会联系的程度与方式的不同,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会有所不同,国家自主性的强弱也会有所区别。(15)阿图尔·科里(Atul Kohli)关于“边缘带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则更明确地探究了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制度基础。科里认为,国家的自主性以及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能力,来源于集中而有效的政体结构以及国家机构渗透并掌控社会的能力。(16)对于埃文斯和科里来说,他们的研究重点不在于韦伯式国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而在于对比现实中不同国家在国家内部结构的差异,并评估这些差异对国家自主性及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影响。
埃文斯、科里以及汉密尔顿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看待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新视角,即通过对国家的内部结构的历史观察与分析,评估其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解释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不同形态。本文便试图借助这一视角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将国家看作具有历史根基的制度体系,观察制度结构的变化对国家利益和国家行为产生的相应影响,并探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成因。
从地方分权到市场化与经济自由化:国家寻求自主性的历程
审视中国的国家结构及其在改革时期的演变,有助于解读“国家引领下的经济自由化”这一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特殊形态。前述各项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研究采取的是对不同国家制度结构之间的横向比较方式。而本文则对不同时期国内制度结构特点做纵向对比和观察,其间的关键点是结构的变化。
人们普遍将改革前的中国国家(the Chinese state)视作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soci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按照科里的定义,发展型国家具有集权化和目标明确的权威结构,而同时这种结构体制又能渗透和深植于社会之中。(17)总的来说,中国改革前的国家结构符合这一标准。国家意志通过各级党政机构的纵向制度渠道,从中央贯彻到地方和基层。不过,一些学者曾指出,在中国的国家制度结构中,一直存在一体性和区隔性两种特征。许惠文(Vivienne Shue)在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放权和重新集权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直达社会基层的国家各部门的纵向机制常常遇到地方权威和利益的横向拦截。(18)
在改革时代的行政性地方分权阶段,这一特征则凸显出来。80年代初期开始的地方分权并不是中央政府首次将经济计划权下放到地方政府,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轮改革对中央和地方的收益分配做了明确的规定,且分配的方式与比例存在地区性差异。产权和财政权力的下放促使地方政府不断扩充其组织机构和人员设置。(19)许惠文所提及的与中央政策执行机制的纵向管道相交的横向网络进一步加强。
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由于国家在很多产业和经济部门中引入了双轨制,市场机制开始在经济的计划外区域初步运行。然而,分权制下地区差异性的财政安排又强化了经济的地区区隔,导致了市场的割裂和地方保护主义。
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促使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为本地区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尽管在本地区内,地方政府仍然履行着其“发展型”政府的责任,但是在国家层面上,它们的角色从中央政府的政策贯彻机构日益向地方利益的维护者转化。可以说,行政性地区分权措施在大大搞活中国经济的同时,也为中国的国内制度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许惠文所描述的旧体制下“高度的集权与管理下的地方主义相互补充的局面”,已经为强化的地方权力和受到削弱的中央财政权威所代替。横向的地方权力网络拦截、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阻断了从中央下达到基层的纵向政策贯彻管道。其结果是,国家制度结构的连贯性和凝聚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进而削弱了国家行使其发展型职能所必需的自主性,使得国家执行其发展和增长战略的能力受到影响。(20)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央政府没有采取行政上的重新集权,而是进一步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推动经济的全面市场化以及与世界市场的融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国家的行政部门从微观经济活动中剥离出来,并弥合行政分权时代各地区的政策差异,从而消除地方政府和地方利益寻租活动的根源,重塑国家制度结构的连贯性和凝聚力,以使国家获得有效管理经济所必需的自主性。因此,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过程并不是国家让位于市场力量的过程,而是中央政府通过建立市场体制再造发展型国家的过程。
以下本文便对中国外贸体制改革做历吏情境下的回顾。在众多经济部门的改革中,外贸体制的改革贯穿了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经历了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完整变化,适合用作相对独立的分析单元,来观察制度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果以及对其后改革路径的影响。(21)此外,外贸体制的改革处于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交汇点,也处在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的交叉点。分析这一领域内国家、社会和市场力量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把握改革开放时期政策选择的整体动态与逻辑。在本文中,外贸体制改革作为单一案例,并非用来证明前述观点,而是在前文理论探讨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示前述分析框架在经验问题上的解释力。
国家引领下的经济自由化:以外贸体制改革为例
当我们以国家内部结构的特征和变化为基础来理解中国改革时,国家引领下的经济自由化这一看似异常的现象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市场导向的改革和经济自由化的具体措施,并不是政治主体寻租行为和互动妥协的副产品,也不意味着国家臣服于市场力量,而反映的是国家寻求自主性的努力。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外贸领域无疑是变化最显著、最深刻的经济部门。在改革之前,外贸经营权完全集中在12家国有进出口公司手中。中国的经济处于半自给自足状态,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足10%。中国在世界贸易国中排名第36位,进出口总额不足世界贸易总额的1%。(22)而自从1979年外贸体制改革开始以来,整个外贸部门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全面的变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间,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长率都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贸易依存度达到67%,远远高于世界主要贸易国如美国、日本的贸易依存度。(2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24)与中国在外贸领域的不凡表现相关联的是国家外汇储备的增长,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超过14000亿美元。(25)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很容易令人联想到20世纪日本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如韩国、台湾地区的经济起飞模式,即以出口导向战略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然而,事实上中国在对外贸易领域的实践和表现与前述东亚国家或经济体的情况不尽相同。所谓东亚经验的特征是国家为促进出口有选择地对一些经济部门进行干预,并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联系起来进行战略规划。(26)而中国在改革期间的外贸政策制定权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部门,且外贸政策与产业政策没有系统性的联系。(27)与东亚式的出口导向战略不同,中国的进口与出口一直同步增长,在某些年份,甚至还出现贸易赤字的情况。(28)此外,与其东亚邻居相比,中国的高贸易依存度显示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期具有比前者更为开放的经济。
中国外贸改革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作为一个具有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中国为什么选择了“自由贸易”的方式而非东亚新兴发展国家的干预市场型发展方式?
已有的研究在解释中国外贸改革的政策选择时,往往强调外部压力的作用,如争取成为世贸组织缔约国的需要,摆脱美国对最惠国待遇年度审查的政治约束的需要,等等。(29)然而,这些解释倾向于将中国政府的改革决策看作短期政治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把它放在持久的国内改革的历史情境下进行分析。
本文试图从外贸体制改革的历史和制度情境出发,解释外贸自由化背后的逻辑。一般认为,外贸改革遵循的是渐进式模式。但事实上,这一领域的改革并不像渐进一词所暗示的那样呈均匀和累积的态势进行。外贸改革最初并不是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而是简单的行政分权。分权的目的是在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和各部门之间重新分配外贸管理和经营权。在这一阶段,指导中国外贸实践的基本方针并没有大的变化,出口仍然被看做换汇的主要途径,而换汇的目的是支援国内经济建设。曾有学者预测,这样以行政分权为基础而且存在地区差异的外贸改革,会使中央和地方权威之间的利益分割永久化,从而导致改革无法进行到底。(30)显然,事实的发展与这种预测大相径庭:全面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已获实施,取代了早期部分性的、有地区选择性的改革。
在这一过程中关键的是地方分权对国家内部结构的影响。在分权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具有双重身份,即一方面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另一方面又是地方利益的维护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横向的权力网络阻截了中央政府垂直的政策贯彻机制,国家制度结构的连贯性和凝聚力受到了行政分权的削弱,国家(中央政府)的自主性减弱。而为了重获中央权威和政策自主性,中央政府选择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将国家机制从微观经济活动中剥离出来。与此同时,地方分权也为外贸自由化做了制度准备——对外贸经营权以及外汇留成的地区差异性安排在地方政府之间造成了竞争效应,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期望获得更多的外贸经营权和自由度,而这正契合了外贸自由化的改革方向。贸易自由化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社会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一)地方分权第一阶段
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从总体上来说是为了辅助内部发展,改革的重点旨在使农业部门重新焕发活力,使进口替代的工业部门获得增长的动力。改革的主要目的不是彻底打破计划体制,而是要改善其运行的效率。改革前的外贸体制完全由中央统一控制,外贸活动由国家的外贸部门独家垄断经营。所有的进出口活动都严格遵循国家计划。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与国际市场的供需情况完全不接轨。国家从国内生产商手中统一收购出口商品,在对外贸易部的统一领导下由12家国有外贸公司出口到国外。地方的外贸局和国家外贸公司的分支机构负责执行国家外贸行政机构和国有外贸公司的计划和指令,它们本身却没有外贸自主权,因为外贸计划的任何微小改变都需要获得上级机关的批准。出口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换取外汇,以支持战略商品如粮食和工业原料的进口。外贸整体规模很小。而人民币估值过高也使得外贸活动以进口而不是以出口为导向。
1979年以后,外贸改革作为对外开放举措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通过出口换汇,以购买先进的技术设备,为国内经济建设做出有益的补充。外贸分权制从本质上来说并非全新的政策。早在1959年大跃进时期,中央政府就曾经把外贸计划权下放到地方;而各地方政府竞相提高外贸计划的目标导致国家整体外贸计划失控,国家不得不在1963年和1965年间收回了这一权限。(31)新时期的分权制和50年代的分权举措相似的地方在于,都是对行政权限的再分配。外贸计划和经营权下放到地方政府,而不是下放给生产型企业。计划机制仍然得以完整保留。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有选择地在一些地区“实验性”地展开分权,分权的重点在于中央和地方的收益共享,使地方政府能够以更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外贸计划和经营活动。(32)
这一新机制并非以市场为导向:国内绝大多数的生产型企业仍然不能直接参与国际贸易,进出口活动仍遵循中央和地方的外贸计划。然而,这种安排无疑给经济特区及其所在省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促使它们扩大外贸活动的范围和规模。而经济特区及其所属省份通过外贸、投资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获得的经济收益也引起了其他省份的羡慕,推动中央政府进一步实施分权计划。(33)1984年,中国开放14个沿海城市,并开始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表明了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进一步走下去的决心。在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地方外贸公司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或者从国有外贸公司中分离出去。而主管各个产业部门的政府部委也纷纷建立各自专属的外贸公司。仅仅从1984年到1985年两年间,就有400家新外贸公司获准建立。国家也将外贸经营权下放到一些特殊的生产单位,从而打破了国有外贸公司垄断进出口活动的局面。(34)
虽然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产业部门及其下属的外贸公司争相进入外贸领域,但是它们的关注点却仅仅在于通过出口获得外汇留成,而对于出口活动的利润和损失却不甚关注。因为在这一阶段,国家仍然会对出口活动中的亏损做出补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在1984年实行了外贸代理制,旨在促成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之间的联合,使进出口活动更好地反映国内生产商的成本,从而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然而,这一机制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对各自的成本信息都倾向于保留而非共享。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在外贸分权和外汇留成体制下,外汇成为稀有资源,外贸公司和生产型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主体,在外贸活动中获取最大收益的需要使它们的利益相互抵触。事实上,很多外贸公司仍坚持从厂家购买产品后自主出口,而不是和生产型企业实现产销联合。(35)
总的来说,在分权制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国家对外贸业务的垄断经营被打破,全国范围内经批准成立的专业、部委及地方外贸公司达到2200多家。(36)但是,这种本质上以行政分权为基础的出口激励,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社会经济效果。地方及部门外贸企业为了获得出口换汇的机会,争抢可供出口的产品,引发国内产品价格的上涨。而在国际市场中,情况却恰恰相反,外贸公司和具有外贸经营权的生产型企业拼抢出口渠道,竞相削价出售自己的商品。结果是出口利润外流,而由于所有外贸公司的亏损都由国家来补贴,最终受损失的是国家。仅1986年,中央政府为补贴外贸公司损失的支出就达到250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37)
在出口总量增加的同时,国家的外汇储备并没有显著增加,反而在某些年度呈负增长。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进行出口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换取外汇,出口品大部分是低附加值产品和原料,而不是像当时国家希望的那样,将出口计划与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相联系。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官方汇率过高,而外汇方面的管制又较前放松,国内的需求造成进口激增。而有选择的地区性分权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经济特区和享有外贸优惠政策的省份借助外贸特权进口消费品并在国内市场上转卖。这样一来,一方面国家在为出口的亏损埋单,另一方面,经济特区和沿海省份的外贸公司通过“内部进口”赚取利润。(38)
面对这种状况,中央政府的一个可能选择就是冻结外汇留成制,这一举措一旦实施,便意味着地方分权改革的结束。而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外贸经营权的下放既是对外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也是其重要象征。以重新集权的方式收回外贸经营权从现实上来说不可行,而且也会削弱改革计划的可信度以及公众及社会信心。中央政府的实际做法是进一步深化外贸分权制改革。而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一套机制,既能继续为外贸公司和政府组织提供扩大出口的动力,又避免国家继续遭受损失。这就引来了外贸分权制改革的第二阶段。
(二)外贸分权第二阶段
在第一阶段的外贸分权改革中,企业、外贸公司和地方政府组织并未把外贸活动的成本效益和获利能力摆在重要的位置上。相反,分权机制在实际外贸活动中往往起到鼓励亏损的效果。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的地方分权改革,其制度基础在于将地方政府看作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以及贯彻中央政府意志的重要环节。但实质上,分权化的结果是国家机构的地方制度结构本身发生了变化,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由国家政策的实施者向地方利益的维护者转变。如何重新定义地方政府的角色,使国家意志在执行中不打折扣,使国家利益不会受到地方利益的侵蚀,是第二阶段改革的重点所在。中央政府试图建立一套机制,使地方利益成为合法化的诉求,同时又明确地方政府对中央的责任。为此,中央政府在外贸领域引入了外贸承包制。在这一举措下,外贸改革仍然不是市场导向的改革,而是沿着行政分权的轨道继续深化。不过承包制本身引入了更多的经济激励,以期重塑中央、外贸公司及地方政府间的动态关系。
承包制的改革从“条条承包”开始。1987年中央政府在外贸体制内部引入了承包制,在外经贸部及其下属外贸公司和其他工贸公司之间建立承包机制。由于这套机制是在不同部门的上下级之间垂直承包,因此被称为条条承包。在这一机制下,外经贸部成为外贸的总承包人,与国家签订承包合同,就外汇收入、出口成本以及国家对人民币损失的补贴上限确定目标。外经贸部再与各外贸公司和工贸企业的总部订立合同,规定每个公司的具体目标。而后者再与其各分公司签订承包合同。这一承包机制并不包括省级地方政府及其新建立的地方外贸公司。但是国有外贸公司的地方分公司却被纳入其中。国家建立这一承包制的目的在于,使外贸体制内的核心企业组织能够通过利润共享机制对企业行为负责。
同时,中央政府还将出口退税制引入了外贸体制。此前中国政府对出口采取直接的财政补贴方式。而出口退税则将补贴与具体出口企业及出口产品挂钩。这样做旨在改变前一时期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利益盲目出口初级产品的情形,改进出口商品的构成。
条条承包对中国外贸体制的业绩表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87年,进出口总额比前一年度增长了11.9%,出口总额增长28.5%,而进口总额则减少了1.5%。出口成本降低了2.6%。(39)国家的外汇储备情况和出口利润率都得到了改善。
然而,在地方分权制继续实施的总形势下,外贸条条承包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由于外贸领域的承包与现行的地方利益板块呈纵横交错的态势,“条”与“条”之间的正常商业往来和合作受到地区因素的阻隔。同时,由于对可供出口商品的争抢并未停止,而且往往发生在地方外贸公司和国有外贸公司的地方分公司之间;外贸企业为了实现其承包目标,仍然将在价格上打败其竞争对手作为主要目标,由此造成基于短期利益的外贸采购行为。而这一切,都不利于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40)
为了纠正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在1988年以块块承包代替了条条承包。这一新的承包机制重点在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承包责任制。外经贸部与各省级行政部门签订承包合同,确定出口创汇、外汇上缴以及政府补贴等方面的指标。而各地区的具体指标,则由外经贸部、财政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不同地区的财政状况以及在国家经济战略中所处的位置做出差别化的规定。各省级地方政府在上缴指标规定的外汇金额后,超过指标的大部分外汇收入可供本省留成。
国家还放松了对进出口的控制,只将少数战略产品和资源归入指令性计划,由指定的国有外贸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经营,另外少数“重要商品”则归入国家指导性计划,其他大部分商品的经营对各级外贸公司开放。
在条条承包期间推行的出口退税制得以保留和推广。退税的范围扩大到价值链的各个部分,包括产品税、销售税,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增值税。
上述种种措施都是为了使地方政府和各级外贸公司成为利益共同体,同时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更加以出口为导向,在外贸活动中以利润为驱动力而不是依赖国家的补贴。而差别化的地方外汇留成体制旨在使出口激励机制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相统一。也就是说,承包制承载着外贸政策上的地区战略。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的外贸政策从本质上来说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政府干预模式有某种相似之处。
承包制对国家的外贸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从1998年到1990年间,进出口总额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平均每年增长超过1000亿人民币。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提高到13.7%,成为世界第14大出口国。(41)
然而,无论是条条承包还是块块承包,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外贸分权制给中央和地方关系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首先,虽然中央政府希望通过承包制把外贸企业变成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但是承包制却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提供了一个新平台。由于中央政府继续在各地区出口成本估算的基础上以财政补贴形式为地方政府提供补贴,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经济获得宽松的财政环境,自然会争取将这一部分收益最大化。而这一诉求使地方政府在有意无意之间鼓励当地企业提高出口成本,以期获得更多的国家补贴,而不是改进经营效率,降低出口成本。1988年,国家的出口补贴总额达到70亿人民币,相当于出口总额的4%。(42)在这一问题上,地方政府和代表中央利益的外经贸部实际上处在零和游戏之中——前者的收益恰恰来源于后者的损失。
此外,以地区为单位的承包制加剧了地方分权制改革以来的某些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外贸企业进入外贸领域,在出口商品的采购市场中竞争越发激烈。由于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签订了承包合同,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保护本地商业利益。地方保护主义进一步蔓延,一些地方保护型政策阻止了外地采购企业进入本地市场。而在各种外贸企业的争抢下,出口商品的收购价格仍居高不下。
更严重的问题是“内部进口”现象屡禁不止。在80年代后期,人民币的官方价格仍然过高。而购买外汇的实际成本,即外汇调剂价,要高于官方价格。当企业通过进口许可证进口商品时,国家会补足其进口成本和官价之间的差额,以及进口产品按人民币官价折算的价格与国内价格之间的差额。这样,国家实际上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了进口补贴。享有高外汇留成率以及更多进口许可权的地方和企业很快认识到,现行的地区差异正是套利的机会。进口商品,特别是进口消费品通过这些省份和经济特区进入国内,再转卖到内地其他市场上去。而在这一过程中,获利的是进行“内部进口”活动的地方和企业,而受损失的仍是国家。中央政府实际上在提供双向补贴,即出口和进口补贴。
在承包制下,地方外贸企业的出口活动仍以获取硬通货为主要目标,而非基于成本利润分析。同时,进口活动由于其套利可能性而对外贸企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其结果是,虽然这一时期国家的目标是发展出口导向的经济,但是整个体系的回报却仍然偏向进口。在1987年到1990年这四年中,有三年进口总额超过出口总额。(43)
此外,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仍得不到根本改善。如前所述,由于地方政府和外贸公司的外贸经营活动是基于短期经济利益,以简单换取外汇为目标,因此往往倾向于出口资源性产品和初级产品,而不是根据国家的沿海发展战略,发展轻工产品及加工型产品的出口。在进口方面,内部进口现象使得国家实施进口控制的外国制成品涌入国内市场。甚至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国家刚刚对某一类产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地方进口政策便反其道而行之,大量产品零部件和原料从国外进口到国内,经过组装后在国内市场上再次销售。(44)
(三)外贸自由化
长达十年的外贸分权制改革使得外贸部门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焕发了活力,但是也造成了上述的种种问题。然而,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却不是简单地重新集权或者继续推进分权制就可以做到的。如其他经济领域在分权时代的情况相似,外贸领域也面临着“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困境。在地方分权制全面展开、中央和地方利益重新划分的情况下,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地方政府遏制不合法的进出口行为收效并不明显。另一方面,继续推行行政分权制也不是现实的选择。分权制削弱了国家的政策执行能力,导致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利益和发展目标上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发生冲突。
有趣的是,重新提升中央权威的一种可能途径就是通过进一步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将国家行政机构从微观经济活动中剥离出来,减少其与地方和社会商业利益的纠葛,从而使国家重新获得政策自主性。自1991年中国政府强化了重返关贸总协定的努力以后,中央政府的各项举措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1991年至1993年间,为推行全面的外贸体制市场化改革,中央政府做了一系列铺垫性努力,包括取消出口补贴、取消外汇留成的地区差异、将地方外贸与中央财政脱钩,以及规范进出口控制、降低关税及减少许可证控制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央政府的这些举措谨慎而又有效地移除了前一阶段改革的某些制度效应。过去以地区差别性为基础的分权和承包机制本来旨在调动地方积极性,同时又保持国家对经济发展布局的设计能力以及对开放进程的控制能力。然而,这种安排的结果却是中央的计划和监督能力被削弱。中央政府在听任中央权威进一步受损和中止改革计划这两个选择之外,开辟了第三条路,即通过进一步放宽对外贸领域的控制,重新获得对全局的把握能力。
在这一系列准备性措施实施以后,外贸体制中尚待解决的两大问题就是外汇留成制和事实上的汇率双轨制。这两项制度都是外贸分权时期的创新。中国在1985年取消了汇率双轨制。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仍然存在双重汇率。到1993年,官方汇率已历经几次调整,却仍然高估了人民币的价值。同时,获得授权的企业可以将其部分外汇留成收入在外汇调剂中心以调剂价进行交易。尽管外汇留成的地区差异已被取消,但是根据企业所处产业及其经营项目的不同,企业仍享有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因此,对不同企业而言,同样的外汇收入兑换为人民币后,数额上便有了差异。1994年初,中央政府正式统一了双重汇率。与之相应的是,中央政府取消了外汇留成制。企业从此可以直接向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结汇及合法购汇。(45)
双重汇率制和外汇留成制的取消结束了中央和地方在外贸领域的承包制。中央不再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制定外汇收入指标,而是以指导性方式管理进出口活动。其主要措施包括:建立出口退税制,对少数重要的和战略性的产品采取许可证及配额制,并建立政策银行,为机电产品及成套设备的交易提供政策性信贷支持。
然而,虽然中央政府采取了这些指导性措施,其改革重点却不在于建立以产业政策为先导的进出口体系,而是努力建立符合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规范的自由贸易体制。
为此,中国政府在1994年初降低了2989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占中国海关全部税目商品的45%。主要耐用消费品如汽车的关税下调了36%,1995年,烟、酒、音像制品等消费品的税率平均下调了35.5%。1996年,政府对4997类商品进行了新的一轮关税下调,关税总水平降至23%。至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前,关税总水平已降至15%。(46)
此外,虽然削减非关税壁垒并不在加入世贸组织所要求的范畴之内,中国政府仍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努力。从1995年起,中国政府逐步减少了受配额限制的进口产品类别以及进口商品特别目录上的产品种类,以使大多数商品能够自由进出口。1995年至1997年间,国家取消了对18种产品类别和368个商品税目的进口许可证,分别占其各自总量的32%和52%。(47)
在出口方面,除了16种最重要商品由国家统一经营,约95种产品受到配额管制或需要出口许可证之外,其他商品都可以由具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直接出口。而即使在政府干预仍然存在的商品领域,国家也倾向于以市场机制而非行政命令进行协调。例如,1994年,中国政府对几种主要商品如原木、纺织原料和某些化工品实施出口配额有偿招标的办法。(48)在改革的上一阶段,这些产品曾引发激烈的价格战,为外贸公司造成严重的损失。而对出口配额的使用采取有偿竞标的办法,把企业置于相对平等的竞争位置上,迫使它们对出口行为的利润前景以及运营中的成本效益进行评估。
与汇率体制和进出口体制方面的改革相呼应的,是外贸经营权的进一步下放。而这一轮放权,不再是行政权的下放,而是通过放宽外贸经营权的资格限制和审批程序,将外贸经营权落实到企业。到1997年,8000多家生产型企业获得了产品出口和原料及零件进口的权利。到2000年底,又有16000多家外资企业和3000多家国内生产型企业获得了此项权利。(49)
在中国加入世贸后的三年间,中国政府彻底将外贸经营权下放到企业层面。除了原油、烟草、粮食等产品继续由指定外贸公司专门经营,其他产品的交易都可以由企业个体直接操作。外贸活动的授权和审批程序大大简化,企业经营项目的范围也较前扩大。至此,中国外贸领域基本实现自由化。
外贸自由化的逻辑:制度结构、国家自主性和发展战略
1991年开始的外贸自由化是国家引领下的中国全面市场化改革和经济自由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中国外贸部门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经历了根本的变化。从表面上看,这些变化是按照“对外开放战略”呈渐进式展开的。但是,对外贸改革进程的深入研究提示我们,外贸改革的进程及方向是由几次范式性的变化决定的。从外贸改革开始至今,中国对外贸易的目的发生了几次关键性战略转变,即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及由出口导向战略到自由贸易的转变。由于中国有很长的计划经济历史,并与以国家干预著称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人们倾向于认为中国会采取以国家干预和积极的产业政策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战略。事实上,中国在外贸改革开始后几年曾推行过这样的战略,然而其效果却不像在其他东亚发展型国家中那样显著。而随着中国加快人世的步伐,外贸改革也向全面市场化和自由化推进。
通过回顾外贸改革的历程,观察国家制度结构在各阶段的特点及变化,本文认为,决定中国外贸改革方向和轨迹的关键因素,是国家制度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央政府对此种变化做出的反应。中央政府进一步减少对外贸活动的控制,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正是为了重新获得国家自主性,加强宏观控制能力。
在外贸体制改革的地方分权阶段,中央政府试图赋予地方更多的经济自主权,推动国有外贸公司和生产型企业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向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国家却仍然依靠旧的国家政策贯彻机制执行外贸计划。而作为这一机制上重要环节的地方政府,却因为获得了新的经济激励而日益扮演起双重角色,其作为国家政策贯彻者的功能受到削弱。地方分权的制度后果促使中央政府重新考虑其对经济的干预方式。最初,国家试图通过将分权制与具有约束性的承包制结合起来,然而这一举措却强化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功能上的错位,国家的政策贯彻能力进一步被削弱。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央政府采取了市场导向的经济自由化,通过将国家机构从微观经济活动中剥离出来,去除由于行政原因造成的地区经济差异及种种不规范的经济现象,以使国家重新获得宏观控制能力和政策自主性。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机构的作用也部分地发生了变化。2003年,原外经贸部与国家经贸委及国家计委的部分职能合并组成了商务部,其职能从过去的行政规划向监督与协调职能转变。
外贸领域的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经济部门的改革经历折射出过去三十年间国家制度的变化动态,并为研究中央、地方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相对完整的历史情境。
外贸改革这一案例所揭示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演变背后的逻辑,与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现有的解释既有区别,又相互补充。本文与谢淑丽的研究相一致的地方是注重观察经济决策背后的政治基础。而在关注改革开放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及互动造成的影响方面,又与魏德安的研究相似。但是,谢淑丽和魏德安的分析从本质上来说采用的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将政策结果看作自利个体或利益集团之间交易或妥协的结果,而制度仅仅是理性主体互动时的游戏规则。本文却把制度看成具有历史渊源的结构,通过对国家内部结构和组织方式的变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来探索国家政治经济决策背后的动因。而与诺顿的“从计划中成长”及魏德安的“均衡价格”这类遵从经济学逻辑的解释不同的是,本文试图探寻国家发展战略范式性转变背后的政治动力。
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鲜的经验研究的平台,以供研究者观察在发展、市场化和全球化潮流交汇下的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经济部门改革的过程,展示了国家制度结构在地方分权政策下的变化如何影响到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以及如何决定了其后的改革与发展路径。当然,中国案例本身并不能推翻国家主义者所推崇的国家干预型的增长模式,但中国经验本身却展示了国家实现发展目标的另一种战略可能性,即国家积极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与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相兼容。市场导向的经济自由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全球市场力量面前的退却和萎缩,反而可以是发展型国家为实现其发展目标的主动选择。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汇聚了三个相互关联并正在进行的进程——发展、市场化与经济自由化。对中国改革经验的回顾与研究仅仅是一个起点。在这三个进程中选择任何一个进程,将对中国一国的观察扩展到更系统的跨国比较研究,都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索后发展、转型与经济自由化这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课题。
注释:
①本段下文对“经济自由化”给出了明确定义。这一概念涵盖了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国家普遍面临的贸易自由化、金融开放及政府解除对经济部门的管制等进程。在中国,这一进程包括政府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市场的全面开放。本文用国际通行的概念“经济自由化”描述这一进程,而将“市场化”定义为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两个进程在中国交织进行,但从进程的本质以及研究层面的可比对象来看,二者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②具体研究的例子见:Chalme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Robert Wade,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Alice Amsden,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Frederic Deyo,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zation,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③例如,阿图尔·科里在其关于发展型国家的研究中,就明确地将其分析时段限定在“新自由主义”浪潮开始以前,详见Atul Kohli,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3。
④Susan Shirk,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⑤Barry Naughton,Growing Out of the Plan: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⑥Andrew Wedeman,From Mao to Market:Rent Seeking,Local Protectionism and Market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⑦2005年,谢淑丽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讲座时,承认了她旧有的分析模式的局限性并介绍了她的新研究导向。
⑧对此种观点的描述,见 Douglass 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Norton,1981,p.20?
⑨Anne Krueg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 Seeking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No.64 1974,p.293.
⑩详见 Chalmers Johnson,1982; Robert Wade,1990; Alice Amsden,1989。
(11)Alexander Gers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12—22; Albert Hirschman,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pp.35—36.
(12)Gary Hamilton and Nicole Biggart,"Market,Culture and Authority: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4 (Supplement),S52—S94,1988.
(13)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New York:Bedminster Press,1968,p.54.
(14)Adrian Leftwich,"Bringing Politics Back in:Towards a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Studies,Vol.31,No.3,1995,p.408; Eric Nordlinger,"Taking the State Seriously" ,in M.Weiner and S.P.Huntington,eds.,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Little Brown Co.,1987,p.361.
(15)Peter Evans,The Embedded Autonomy: Stat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16)Atul Kohli,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17)Atul Kohli,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p.10.
(18)Vivienne 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53—56.
(19)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hevchenko,"The State of the State,"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eds.,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334—335.
(20)有关分权制下国家制度结构在地方层面与地方社会利益甚至结合,见 Christine Wong,"Material Alloc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in Elizabeth Perry and Christina Wong,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Jean Oi,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
(21)与之相比,其他一些经济部门如对外直接投资,是改革开放后新引入的经济成分。这一经济部门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而非改革的对象。因此,作为案例,这类经济部门不具备对外贸易领域所能提供的制度情境。
(22)David Wall,Jiang Boke and Yin Xiangshuo,China's Opening Door,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7,pp.110—111。
(23)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学会网站,http://tjxh.mofcom.gov.cn。
(24)美国和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在20%左右。有些学者认为,由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被低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中国近年来的贸易依存度被高估了。但即便去除这些因素的影响,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对于一个国内市场较庞大的国家来说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
(25)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储备2007年统计数字。
(26)Robert Wade,"East Asia's Economic Success:Conflicting Perspective,Partial Insights,Shaky Evidence",World Politics,Vol.44,No.2,1992,pp.270—320.
(27)China:Foreign Trade Reform,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1994,pp.133—134.
(28)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1979-2003年统计数字。
(29)Susan Shirk,How China Opened Its Door,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4,pp.70—72.
(30)Susan Shirk,How China Opened Its Door,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94,pp.53—54.
(31)尹集庆主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20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2)例如,除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外,经济特区的留成比例为100%,广东、福建等享受特殊政策的地区留成比例为30%,其他地区25%。
(33)关于差别性地区分权所引起的地区间竞争,见Dali Yang,Beyond Beijing:Liberalizations and the Regions in China,London:Routledge,1997?
(34)尹翔硕:《中国对外贸易改革的进程和效果》,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35)David Wall et al,China's Opening Door;刘向东:《中国对外经贸政策与改革纵览》,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36)尹集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20年》,第39页。
(37)China:Foreign Trade Reform,p.26.
(38)Susan Shirk,"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Reform",in Elizabeth Perry and Christine Wong,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211—213.
(39)尹集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20年》,第53页。
(40)同上,第52—53页。
(41)外经贸部(商务部)进出口统计数字。
(42)China:Foreign Trade Reform,p.27.
(43)外经贸部(商务部)进出口统计数字。
(44)尹集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20年》,第64页。
(45)1996年12月起,中国正式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规定的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46)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字。
(47)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海关总署关于调整进口许可证管理商品目录及发证机关的通知(1996)。
(48)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对原木等出口商品配额试行有偿招标的公告(1994)。
(49)外经贸部(商务部)统计数字。
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全球化论文; 分权管理论文; 贸易结构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经济学论文; 外贸推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