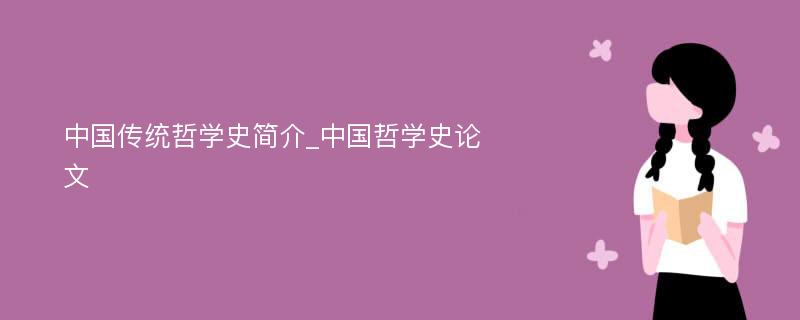
中国传统哲学史方法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史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哲学史方法 批判方法 考辨方法
提要 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有待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进步。考察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是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研究的重要前提。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主要表现为:秦汉时期的批判方法和明清时期的考辨方法。
方法是科学的灵魂。任何一门学科的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与这门学科相应的方法,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是如此。对中国传统的哲学史方法作一些回顾和思考,将有助于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完善和发展,也将有益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创新。
一、中国哲学史方法应当是它自己的方法
在我们加深对中国哲学史方法探讨的时候,黑格尔关于“方法就是对于自己内部自己运动形式的觉识”;“哲学方法应当是它自己的方法”[①]的论断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依照黑格尔的理解,方法实际上是人们对事物内在运动形式的理解和运用,方法的内容应当同对象自身的运动形式关联。人们认识事物,理解事物内在的矛盾运动有程度、层次的不同,由此而形成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是,人们认识事物的系统性差别和有效性差别,并不能否定黑格尔对方法的事理方面的根据的肯定。黑格尔正是出于对方法的事理根据的理解,才认定“哲学方法应当是它自己的方法”,强调科学方法的具体性和特殊性。黑格尔的这种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思考中国哲学史方法,首先必须肯定中国哲学史方法是它自己的方法,在探讨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发展时,应当以考察中国传统的哲学史方法为前提和基础。
考察中国传统的哲学史方法,必须克服在哲学史方法探究中轻视传统的倾向。当今学术界议论哲学史方法,大都离不开结构、系统、解释之类的话题,视线多在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历来是不注意方法的。其实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实际来看,中国哲学不仅有其内在的理论系统,而且有其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方法传统。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重视“立德”,但并不否定“立言”。注意“立言”,不可能不注意“立言”方法。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方法的概念是出现得很早的:“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度量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是以圆与不圆者可得而和也。此者故何?则圆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度量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方者谓之方,不中吾方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②]这种量度方形之法当是方法的本义。后来方法被引伸演绎出一般的办法之义仍与方法的本义相关。在中国文字中,方与法是可以通用的。方字不仅可表示方向、区域、品类,而且可以表示义理、定规。方法作为人们认识事物、解决矛盾的办法,本身应有事理的根据。哲学史研究所依凭的定准、原则,正是哲学史的方法。
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于具体的“立言”方法也是很重视的。孟子提倡“知言”。主张对于偏激的言论弄清其不全面,对过头的言论弄清其失误,对邪恶的言论弄清其所背之理,对于隐讳的言论弄清其理屈之处。这种“知言”,实际上讲到了“知言”的方法。从方法概念的形成和孟子一类古代思想家对“知言”方法的论释,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哲人的方法意识。那种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领域轻视传统的观念是背离史实的。我们只有依据历史本身,肯定和清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历史形态,才有可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发展。
二、秦汉时期的批判方法
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方法在历史上都是以非独立的形态存在的,中国哲学史同一般学术思想史混而未分,中国哲学史方法也同一般学术思想史方法混而未分。但是,混存于一般学术思想史中的中国哲学史和混存于一般学术思想史方法中的中国哲学史方法仍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先秦时期的哲学史方法主要是以荀况“解蔽”方法为代表的批判方法。这种方法反对学术思想的片面性,以批判否定对立的学术观念来确立自己的思想理论为特征。荀况认为事物是多样的,事物之间的差异常常会使得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产生片面,这种片面实即是“蔽”。荀况将形式多样的认识片面性视为“心术之公患”,反对在学术上“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况曾“非十二子”,评析先秦诸子之学,评析方法即是指斥诸子学术思想上的片面性。
在荀况看来,“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③]其要害都在于片面性。荀况将学术上的片面视为“天下之害”,主张“息十二子之说”。哲学的本性即是求真。为了真实,必须批判违背真实的各种思想学说。荀况“非十二子”的批判方法不仅使他在一个较高的认知层面上总结了先秦的诸子之学,也使他的《非十二子》之类的著作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哲学史性质的著作,使他的批判方法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哲学方法和哲学史方法。
在荀况之后,以“解蔽”为目的和内容的学术批判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韩非子》中评析儒、墨二家,批判“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具体地指斥了儒墨之学的矛盾和儒家后学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并得出了“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④]的结论。《韩非子》一书对儒墨之学的批判,正是其用以建立法家理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在《韩非子》的《显学》《五蠹》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而使《韩非子》中的这两篇文章也具有哲学史著作的性质。《庄子·天下》也是一篇具有哲学史性质的著作。从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天下》篇明确地提出了“方术”与“道术”的观念。“方术”是一般具体的学问,“道术”是具有普遍意义洞悉本原的学问。《天下》篇正是以“方术”和“道术”的观念辨析先秦时期不同思想系统的旨趣,批判各家之学的片面性。认为由于“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各家之学囿于“一察”而失之全面,使“道术”由于各家的“一察”而遭到了支解。
在《天下》篇的作者看来,墨家钦羡追求“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但是墨家立意虽好,其言行却不符合多数人的愿望,因而并不合于“道术”。彭蒙、田骈、慎道追求“公而不当,易而无私”,主张“弃知去己”,以求解脱。但慎到之道被人认为是“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也不合于古之“道术”。名家一派的理论在《天下》篇的作者看来,“惠施多方,……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公孙龙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弱于德,强于物”,也不合于“道术”。在《天下》篇的作者看来,唯老庄之学博大精深。因为老庄之学“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在学术上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以道观物本是庄学的方法。庄周“齐物”“逍遥”的观念即是以道观物的方法确立起来的。《天下》篇中以“道术”“方术”的观念评断诸家学术得失,这是将庄周的观物之法转换为学术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确立一种原则的前提下,辨析各家学说,肯定老庄之学,仍不失批判与否定的方法特征。尤为可贵的是《天下》篇中为批判各家,还保留引述了不少学派具体的思想资料,这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古人的学术方法,而且在哲学史体例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范式。
中国学术到汉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研探学术问题的方法意识更强了。从哲学史方法的角度来看汉代典籍,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尤其是其中的《要略》篇。《要略》篇的主旨是要对《淮南子》全书内容进行概略的评述。这种评述实际上论及了学术方法问题。《淮南子》中有《倜真训》。倜是开始,真是真实。《要略》篇论及《倜真训》时说:“倜真者穷逐终始之化,嬴埒有无之精,离别万物之变,合同生死之形。”使人“观至德之统,知变化之纪。”这种评述,不止是对“倜真”的诠释,实际上也论及了“倜真”的方法。《淮南子》的《汜论训》是“博说世间古今得失”,《诠言训》则是“就万物之指以言其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汜论”和“诠言”本身即是方法。《要略》中说“汜论者……接径直施,以推本朴,而兆见得失之变”;“诠言者……善择微言之眇,诠以至理之文”。这不仅指出了《汜论训》与《诠言训》学术旨趣的差别,实际上也指出了二者方法的不同。可以说《淮南子·要略》中论及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方法,在方法上推重系统性、多样性。特别是《要略》中说《齐俗训》“通古今之论”的观念透露了一种强烈的史学意识,“通古今之论”的重要途径即是研究学术思想史、哲学史。这对于我们理解哲学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是有启发的。
从哲学史方法的角度来看,汉人的另一成就是明确地形成了“六家”的观念。司马迁为先秦诸子列传时,将孟荀合传,老庄申韩合传,即不仅记述了各家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而且留意到了各家学说总的风貌与特征,表明了他对“六家”之学旨趣的理解,也表明了他对其父司马谈在学术研究中的归类方法的领悟和运用。
总的讲,秦汉时期哲学史虽未独立成科,但人们研探不同学术思想流派的同异、旨趣、思路,评断各家学说的得失,已开始注意和形成研究学术思想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对不同学术思想的批判和归类。批判的方法中蕴含有分析,归类的方法则蕴含着综合。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治学主张究天人之究,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学术方法上不排斥对不同思想理论的贬斥和批判。刘向、刘歆校书,其方法也是“论其指归,辨其讹谬”[⑤]。实际上也非常注重学术批判方法。应当说秦汉时期人们所注重的学术批判方法,是最具哲学和哲学史方法特色的学术方法,因而也是对于我们现实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最具借鉴价值的学术方法。
三、明清时期的考辨方法
中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到宋明时期出现了新的气象和格局,这种新气象新格局的标志即是由儒、释、道三家融合而成的道学的兴起,在道学内部形成了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以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为代表的气学。儒、释、道三家合流而成道学并非一蹴而就,其间有一个漫长的学术交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释、道三家之学相互对立、辩难以求自身的发展。这种追求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曾经影响和促进中国佛教的宗门意识、儒家道统、学统观念的形成。而宗门意识、道统、学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秦汉时期人们曾注意的学术归类方法和批判方法的发展。唐代韩愈作《原道》,批判佛道,维护儒家的道统,认为对佛道之学“不塞”“不止”不行,只有对佛道之学“塞”“止”,才会使儒学“流”“行”。在《原道》中,韩愈甚至主张对佛道之学采取“人其人,火其书”这种激进的批判方式。宗密则站在佛教中华严宗的立场来批判儒学和道教以及佛教中的其他宗派。在《原人论》中,宗密不仅指斥儒道之学迷执,同时也指斥佛学中其他的宗派偏浅。道学兴起之后,道学内部的各派学说虽然都自认为承袭了儒学传统,攻击佛老之学,但对于道学内部与自己对立的学说在理论上同样取否定的态度,十分注意维系自己的学派系统,关注自己的学脉源流。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考察“伊洛渊源”,实即是要清理理学一派的学术系统和思想源流。唐宋以来学统观念的不断强化和学术上归类批判方法的不断发展,终于使明清时期以《学案》形式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也使历史上传统的哲学史方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前者的代表是《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学术著作,后者的标志则是人们在《学案》研究中所形成和使用的考辨方法。
由黄宗羲始撰、全祖望续撰才完成的《宋元学案》共100卷,写了90多家学案,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学术著作。《明儒学案》是黄宗羲独立完成的,全书62卷,共写了19家学案。从方法上来看,明清时期形成的学案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考订、辨析、比较的方法。黄宗羲的两部学案都从论释一家学案入手,详细地考辨案主的学说主旨,思想源流,后学传递,并录有案主的思想资料及有关学者的评述。学案次序的编排则顾及学术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线索。《宋元学案》首案为《安定学案》,即是顾及案主胡瑗乃宋代学术思想发展中早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之一。全祖望在《宋元学案》的《序录》中说:“宋代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即是肯定胡瑗、孙复等人的学术活动对于宋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从方法上讲,这可以说是从历史的角度对案主的学说进行定位,而将案主的后学,同门关联在一起,则是从学术的角度对案主进行定位,这都属于考订。学案中对各个案主思想的评说,如学案中说“安定沈潜,泰山笃实”,说张载“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于伊洛”等,都是对胡瑗、孙复、张载学说与别家之学比较之后作出的评断。《明儒学案》的写作方法也大体如此。可贵的是由于《明儒学案》成书于《宋元学案》之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更具体地讲到了学案的写作方法。
在黄宗羲写成《明儒学案》之前,考辨理学学脉源流的著作已有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和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但黄氏对二书都不甚满意。在黄氏看来,周、孙二氏的著作不论在研究方法、材料搜求方面还是在学术评断方面都存在“疏略”。周著对各家思想搜罗不广,加之周氏从禅学的立场评析诸家,对各家学术的旨趣不能实际地评断,所以黄宗羲说周氏之书“见闻狭陋”。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之不足也在于资料的利用和学术的评断方面。这就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讲到的:“钟元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其闻见亦犹之海门也。”周、孙之著的不足实有相同之处。黄宗羲在总结周、孙之作得失的基础上,更注意学术史研究的方法。黄氏认为研究学术史首先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博大的学术胸怀。在黄氏看来,思想家们学术观念的差别源于其对事理的不同理解。“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⑥]事理不同,人心万殊,这是正常的。对于不同学术观念,在总体上不宜“好同恶异”,拘泥于一种学术标准。黄氏十分反感那种在学术研究中对诸家之学“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畔道”[⑦]的学术风气。其次黄宗羲主张在对某一家学术思想资料的抉择中要能了解“去取之意”,对某一思想家的理论“纂要钩玄”,真正把这一家家学中的精华发掘整理出来。再其次则是要对各家之学真正“分其宗旨,别其源流”[⑧]。显示研究者自身的学识和见解。黄氏曾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⑨]在学术上有真知灼见是自成一家之言的条件,对学者的真知自得之见进行独立的辨析,以见其得失,是学术史研究中应有的追求。只有提倡真知自得,反对人云亦云,才有学术的发展,才有学术史研究的发展。黄宗羲的学术史研究主张具体操作起来,即是他在《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中使用的考辨方法。黄宗羲之所以在学术史研究领域也取得巨大成就,在很大的层面上应归功于他所主张和使用的学术研究方法。
在黄宗羲的两部学案之外,清代还出现过《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之类的著作,乃至于民国时期还有《清儒学案》的问世。这些著作的学术价值及研究方法都未能超越黄氏的两部学案。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研探一般的史学研究方法。章氏在唐人刘知几的史学观念基础上提倡史识、史学、史才、史德并重,在方法上讲“道器合一”、“六经皆史”,主张理论与史料一致,反对治史中“空言著述”。章氏在他的《校雠通义》中还主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氏的史论对于我们独立地开展中国哲学史研究,也有方法方面的启示和意义。但仅从学术史研究方法的角度看,章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张并未超越黄宗羲曾使用过的考辨方法的范围。中国传统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发展到晚清梁启超的史学方法时才有了新的进步。
在晚清学者中梁启超是学贯中西的人物。梁氏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是学术史著作中的经典之作。梁氏也曾论释过学术史方法问题。在梁氏看来,晚清学术方法有今古文之别,这种差别实是研究精神的不同。前者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后者能够在学术问题上大胆怀疑解放,是“创作的先驱”,这两种精神各有自身的价值。梁启超由总结晚清的学术思想而谈到了学术研究的方法。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顾炎武时说:“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新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顾炎武之在‘清学派’,即其人也。”梁启超将顾炎武的学术成就归功于顾氏的治学方法,并将顾炎武的治学方法“约举”为“贵创”“博证”“致用”加以辨析。梁氏对顾氏治学方法的推崇,表明了他自己对学术方法的看重。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的最后所讲的数种“感想”,实即是他理解的治学方法。梁氏认为治中学首先应正确处理好古今中西的关系,尽量吸收外来文化,又不妄自菲薄,轻视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要学习古人的“学者人格”,专志于学问,深入领悟到学问的价值在“善疑”“求真”“创获”,同时也要善于客观地评断古人学术上的片面,用新的学术方法对中国固有文化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
同时,梁启超认为随着文化的发展,治学不宜象古人那样包罗万象,只有有所割弃才会有所专精,在学术研究中应“分地自治,分业自治”。学问非某一领域可以尽涵,治学不能只求“思想统一”,而应不厌辩难,“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这样才有学术的繁荣发展。梁氏的这些见解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都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后来梁启超又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和《补中国历史研究法》,系统地诠释史学的意义、范围、价值,以及史料的鉴别考校方法。梁启超治史反对“强史就我”,提倡客观科学地研究历史,主张史学研究应有益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有价值的。梁氏主张对中国文化分科整治,却未能写成独立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梁氏主张的学术方法虽可归属于传统的哲学史方法范围,毕竟不是独立的中国哲学史方法。独立的中国哲学史方法是随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历史上以批判方法和考辨方法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史方法仍然是独立的中国哲学史方法中的基本内容。当我们探索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建设时,决不能忽略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历史形态和历史传统。
注释:
① 列宁:《哲学笔记》,第94—95页。
② 《墨子·天志》
③ 《荀子·解蔽》
④ 《韩非子·显学》
⑤ 阮孝绪:《七录序》
⑥⑦⑧ 黄宗羲:《明儒学案序》
⑨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
标签:中国哲学史论文; 黄宗羲论文; 儒家论文; 哲学史论文; 淮南子论文; 天下论文; 宋元学案论文; 韩非子论文; 哲学家论文; 经世致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