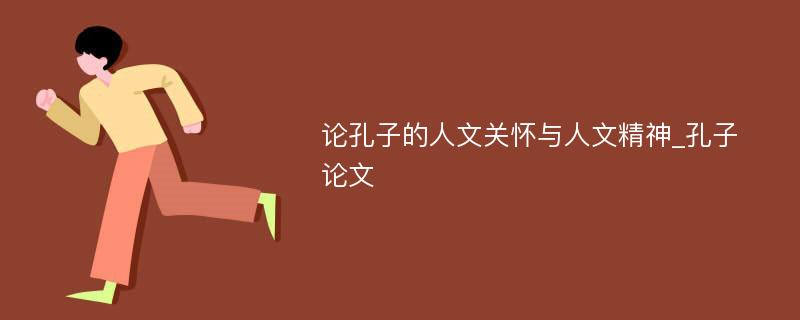
试论孔子的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试论论文,人文精神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1)02-0021-06
孔子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从他一生的人文实践以及思想中的人文主义倾向可以得到证明。当然,严格意义上的“人文主义”(Humanism),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Humanists)用来反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统治的思想武器。但是,远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时代,孔子就在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倾注了种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与浓厚的人文精神。正是这一点,孔子学说才延续数千年而不衰,时至今日,一些国家还视其为治国兴业之圭臬。对此,如果单纯从孔学为历代统治者所需要这一点来说明它存在的价值的话,那就显得过于幼稚、简单。
一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产生首先是从人文学科的分类,并从经院神学中别出开始,随后伴随着人文教育的普及以及借复兴古典文化的名义而逐步形成、发展。这一过程,在孔子那个时代也有类似状况。
首先,孔子删定“六经”,确定了中国传统人文学科的基本格局。在孔子以前,几乎没有人文科学,更没有人文学科的分类,所有的内容几乎都是以“礼”、“乐”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制礼作乐”成为了三代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虽然西周的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隐含了某些人文气息和人文关注,但是这种早期的民本主义却是一种政治理念。只有到了孔子删定“六经”,才将哲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从“礼乐文化”中分类出来,使它们具有了比较精确和专门的意义。“六经”的分类是很有意思的:《易》是哲学;《书》是古代的历史;《春秋》是当代史;《礼》是由哲学派生出来的政治学;《诗》是文学;《乐》是音乐艺术。“六经”的删定使中国从此有了人文科学的分类,也有了人文学科的教育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孔子的贡献还不仅如此,他在疏通整理前代文化遗产的同时,还充分利用哲学、文学、历史等重要学科来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思想。如他作《易》,借用记述古代卜筮之术来阐述其“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从而使《易》这本卜筮之书提升为一部以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哲学著作[1];又如作《春秋》,运用一些隐含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表达自己对当时社会的事和人或褒或贬的态度,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至于他对《周礼》的崇敬与向往,以及“克己复礼”的主张,则主要在于进一步阐发自己的“仁”学思想。这样,孔子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他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也首先是从对人文学科的关注开始。
其次,孔子删定“六经”,其目的在于推进人文教育。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打破了三代以来“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的教育传统,使西周主要针对贵族子弟的“礼乐”政治教育下放到民间。所谓“有教无类”,就是代之以人文学科的内容来进行教育。孔子教学的科目主要是“六经”中的内容,有诗、书、礼、乐、射、御(另一说为礼、乐、射、御、书、数),称之“六艺”。《论语·述而》说:“子有四数:文、行、忠、信。”虽然在孔子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中,不乏政治和道德的思想,但他将人文学科推向教育,又扩充到民间,这无疑比西周的贵族教育要进步得多,也有利于人文科学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有人认为孔子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家、道德家;他所创办的学校是政治学校。对于这种观点我们不敢苟同。首先,孔子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所关注的对象是人与人类社会,而政治恰恰是其中心领域,所以孔子关注政治,并注重对于古今政治历史的总结和理论概括,恰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理性所在。至于道德,更是人文主义者所强调的内容,表现出他们对于“人”的一种终极关怀。因此,与其说孔子是一个政治家或道德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人文主义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第二,孔子教学的内容也不是以政治为主,在“六艺”中,真正属于政治内容的只有“礼”、“乐”两种,仅占三分之一;而“四教”中,除了“忠”为政治学的内容,其余皆属一个“士”立人做事的技能与原则。因此,把孔子从一个人文主义者硬给套上政治家的帽子,把孔子创办的人文学校硬说成是培养从政者的政治学校显然是欠思考的。他们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孔子的人文主义倾向以及他对那个时代的人文关怀。
再次,孔子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解为保守主义者,这是因为他曾宣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加之在其政治主张上崇尚西周的礼乐制度,并要求人们从自己做起,恢复西周的礼乐文化。的确,孔子的思想情感是向着过去的,尤其是他的“复礼”主张,很容易让人对他产生“保守复古”的错觉。其实,孔子的这种思想情感倾向正是一个早期人文主义者在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必由之路。
第一,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面临我国古代社会第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此时旧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已被打乱,趋于崩溃,即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而新的社会变革还在进行之中,其表现尤呈残酷,其形态不够彰显,给人一种道德驰坏,理性不张的感觉。至于未来如何更难预料。面对这种状况,可以说任何人都感到茫然,自然滋生出一种对古代的向往。而且相对孔子同时代的思想家老子的怀旧情感来说,他对于西周的向往,还算是现实的。
第二,孔子作为一个人文主义的思想家,由于他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和人类社会,因而不像当时的政治家那样有功利心,他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具体事件的一般意义,而呈现出一个思想家的理性分析与整体追求。孔子推崇“礼”,是他比较了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历史以后得出的。孔子发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比较的结论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在这里,孔子不仅把夏、商、周的政治文化来了一次大检索和比较,发现它们之间的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特点,而且认为,经过“损益”之后,周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所以他用“郁郁乎文哉”对此加以赞叹、褒美(注:孔子在这句赞美词中所用的“文”,历来依朱熹《论语集注》中的释义:“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实际上,孔子的“文”还有“文雅”、“美善”等人文含义。)。这就是说,孔子从西周那种带有宗法血缘色彩的“温和”统治体制中感受到了一种浓郁的人文气息(注:西周的“敬德保民”思想中,有“修德”、“惠民”、“慎罚”等内容,且包含着一种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这些东西几乎充斥于《尚书》,而且成为西周政治之大纲。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说:周人“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所以他产生出了对于“礼”的认同与赞美。
第三,历来的人文主义者几乎都有“复古”情结,他们受古代文化的熏陶,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对古代社会的认同与向往,甚至还企图使它再度恢复。这种情况,直至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者,还有类似倾向;他们的文艺复兴运动,不就是以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为表征的吗!当然,这种复兴,并非简单的恢复,而在于借复兴古代文化的名义,来阐发自己的新思想,其实质在于一种思想的创新。孔子对于“礼”的崇尚以及他要求“复礼”的主张也主要是围绕他思想的中心范畴“仁”而进行的。简言之“礼”是为“仁”服务的;前者是因循,后者才是创造。孔子为阐发自己的人文精神——“仁”,并对当时的社会寄予充分的人文关怀,必然要从古代的文化中去吸取宝贵的养料,寻找一个基本出发点和理论的依据,而这些,只有在西周的“礼乐文化”中才有其端倪。孔子正是抓住了西周“礼”制中所隐含的人文主义气息,来进一步阐发自己的人文主义的。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孔子思想中的“礼”与“仁”的关系,应该要正确处理,千万不可本末倒置。
二
关于孔子的“仁”,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中心议题,其研究已十分深入、透彻,对此,本文不再赘述。这里主要谈一个问题,即孔子“仁”学缘起的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
几乎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但“仁”的缘起到底是哲学内容还是政治内容却仍未搞清楚。这是因为,孔子关于“仁”的阐述既宽泛又多变,既有哲学的,如“仁者,人也”[4];又有政治的,如“克己复礼为仁”[5];还有伦理学的,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6]。而且始终没有一个囊括一切“仁”的内涵的定义性的结论。或许孔子本人并不想去定义,而有意让后世的人们去讨论,因为孔子知道,他所讨论的“仁”,是人类永恒的思想主题。然而,不管怎样,孔子确是世界上第一个把“人”作为一种类概念来进行系统哲学思考的思想家,单凭这一点,孔子思想的价值就足矣。在孔子之前,中国的思想家们有许多关于“民”的论述,其中不乏人文气息与人文关注,但这些“民为本”的思想显然还停留在政治学领域。如《尚书》中就保留了许多这样的材料。《皋陶谟》中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民,自我民自畏。”《泰誓》中也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人的“敬德保民”思想亦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所谓“今王惟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王曰:‘欲至千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7]这就是说,孔子以前的“民”学思想,主要阐述的是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并用“天命”——“敬德”——“保民”三者统一的图式加以统括。春秋时期,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从破除三代“天命”观出发,开始了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产生了最早的人文主义的概念:“人”和“人道”。如郑国的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8]齐国管仲曾对齐恒公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9]但是,这时的所谓“人”,仍然具有“民”的含义,还没有完全挣脱政治学的意义。尽管当时的人们已隐约发现了人的价值和作用,并产生了轻“天道”,重“人道”的思想倾向。只有到了春秋末的孔子,才在吸取、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发挥,率先在世界上把“人”作为一个类概念来进行思考,这就是他的“仁”的提出。在孔子“仁”学思想体系里,“人”已不再是政治学的“民”,而是天地之间大写的“人类”。这种思维的理性显然比以前提升了一个层次,它开启了人类对自身的全面思考与认识。
当我们面对《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的“仁”字以及孔子从不同角度释“仁”的众多含义时,确实会感到无从解说。孔子的“仁”到底是什么?然而,当我们用“人文主义”的范畴来概观孔子一生的人文实践以后,似乎又不难发现,孔子的“仁”,原来是一个从“仁者,人也”出发,到“仁者,爱人”为终结点的“人”学思想体系。
首先孔子的“仁”学,以“人”为研究内容。《中庸》中的“仁者,人也”[10]的解释,就已经告诉我们,“仁”是以“人”为运思对象的。孔子的后学孟子亦有类似释义,《孟子·尽心上》:“仁也者,人也。”东汉许慎的《说文》也释之:“仁,亲也,从人,从二。”这样,不论是孔子的初衷,或后世的理解,“仁”的确是从“关注”人开始的。
第二,关注“人”,必须先肯定“人”,也就是破除三代以来把“人”混同在政治学的“民”学里的传统,而将“人”以一个类概念来作为思维的本体。于是孔子开始思考“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与作用,终于发现了人的重要性。《孝经》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同时,孔子很少谈到天道鬼神。《论语》记载说:“子不语怪、力、乱、神”[11];又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2]。甚至他还轻慢鬼神,所谓“敬鬼神而远之”[13];“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14]。可见他的这种人文关怀是现实的,而非天命的。从而使他从三代的原始宗教和天命观的影响中挣脱出来,且自然而然引发出对人及人世间的尊重与热情。孔子也曾谈到过“天”,但他的“天”似乎已很少人格神的成分,而更多的是自然的现象。如《论语·阳货》中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至于他提出的“畏天命”的思想,历来认为是他思想中的矛盾部分,但能不能说这是孔子对于自己的“仁”学在形而上学方面关注不足的一种补救呢?!其实类似情况在近代西方人文主义者那里也有:当时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斯的著名哲学家中,不少人就是一方面反对经院神学和教会;可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摒弃宗教精神和宗教信仰,相反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宗教信仰,并从基督教的信仰中找到关于人的尊严、人权等形而上学的依据和认可。象洛伦佐·瓦拉、马尔西利奥·费奇诺等就是典型的代表[15]。或许我们的这种类比会存在某些不妥之处,但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即孔子之前已经有了极其丰富的“天命”思想,发展到周人的“天命”——“敬德”——“保民”公式,已经融进了许多“天意即民心”的内容。孔子重人道,但又不排除“天命”,这正是孔子“仁”学缘起的巧妙所在。
第三,孔子的“仁”对人的关怀是全方位的,是一种由个人到社会,由家庭到国家,由政治到道德的整体模式。众所周知,“仁”的最初提出是一种宗法血缘关系的道德总结,主要指血亲之爱,早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国语·晋语》中明确指出:“爱亲之谓仁”。对此,孔子继承之,他的“仁”也是以“爱亲”为基本内涵的。《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孔子的学生有子加以总结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16]如果参以孟子的“亲亲,仁也”[17];“仁之实,事亲是也”[18]就更加清晰了。然而,孔子的“仁”,还不仅限于此,而要求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前述《学而》中孔子所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其中“泛爱众”的提出,说明“仁”的意义是超越了“孝弟”亲情,而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对此,孔子多次强调。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要求“仁”行天下:“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甚至其适用范围还超越了民族、种族,而发展到对整个人类的关怀。如《子路》中说:“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秋,不可弃也。’”《子罕》中也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在孔子看来,“仁”是全人类的精神,自然也包括华夏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而且所有具有“仁”的精神的人,都有义务将其推广到“夷狄”之中去。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仁”,是由对“人”的肯定开始,到“亲亲”之爱,最终发展到对整个人类之爱,即所谓“仁者,爱人”。这恐怕才是“仁”的总的精神和终结点。
既然孔子的精神是现实的,那么这种现实的人文主义必然将“仁”引入对于当时政治状况的关注与阐说。对于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现实,孔子的评估是不高的,他用“礼崩乐坏”以概括之,反映了他对古代“礼”制社会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所以他提出“克已复礼”的政治主张,并把它作为推进“仁”的一个具体内容。在孔子看来,西周的“礼”是相对三代以来发展最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其中关于社会伦理秩序的内容以及“保民”、“惠民”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仁”的精神,是“仁”的依据和历史存在,所以他用极大的热情歌颂文武周公,赞美“礼乐”文化。但是,孔子的“礼”始终是在其“仁”学框架里的东西,是说明“仁”的内容。譬如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孔子曾对管仲的“僭越”行为表示极为不满,多次斥责他不懂“礼”,但对他辅佐齐桓公称霸一事却予以肯定,并许以“仁”。《论语·宪问》中记载:“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在回答子贡同一问题的孔子进一步阐述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区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9]在这里,孔子的“仁”显然已大大超越了一个单纯的道德家的眼界,而上升到了维护华夏民族团结和文化传统承继发展的高度,其中蕴含的种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可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而只有对人、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充满着无限的爱,并且这种爱已不再关乎个人利益,甚至群体利益;已不受个人政治主张、家族甚至民族政治倾向影响,才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人类的“博爱”精神。如果说孔子的“克己复礼”具有某些保守主义倾向的话,那么,在这种政治主张之上所环绕的“绝对精神”——“仁”,则以它“爱人”的光辉,将他思想中的一丝灰色消弥得干干净净。
三
孔子的人文关怀是进取的,其表现就是他的“仁”学思想不仅仅是一个设计出来的理想境界,而且是必须付诸行动加以推进实施的。
首先,孔子从“仁者,人也”出发,最终阐发出“仁者,爱人”的人类博爱精神,其中一个重要的伦理学前提就是“人——仁——爱人”,即人皆有的道德属性。在孔子的思想里,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道德自觉,有德性,也就是人应以“仁”为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论语·微子》中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为政》中亦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参以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20]的命题,孔子实际上是在阐述一种对“人”的道德要求过程,即人必须以“仁”为出发点,“行仁”、“成仁”,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最后依归,否则就与鸟兽一般。
第二,孔子为了推进“仁”,曾经把人分成“君子”与“小人”,试图通过“君子有仁”,而“小人无仁”的命题设计来寄托对“君子”行仁的希望。对此,学术界不少人认为孔子的“仁”是有等差的,反映了他落后的等级观念。实际上孔子的这一分类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孔子的划分只不过是一种事实的描写罢了。众所周知,春秋时期社会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西周以来的宗法等级制仍然是主要形态。社会中的等级分野十分清晰,当时各国的执政仍然是贵族等级(君子)支配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而广大的平民、奴隶等级(小人)也仍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卑贱地位。这一事实孔子是亲眼所见,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如“苛政猛于虎”等等。然而,孔子又肯定了这一社会存在,因为只有肯定“君子”存在,才能通过对“君子”的怀仁、行仁、成仁的要求,来实现“仁”的从上自下的推进。在孔子的“仁”学中,对统治阶级的要求甚多,如“仁”的五德之一“惠”,就包括“富之”、“教之”[21];“使民以时”[22];“敛从其薄”[23]等等内容。还有“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而成谓之暴”[24]的警示,也提出了对于统治阶级“行仁”的标准。二是孔子的这一分类还是一种理想人格的设计。这就是将社会中的“人”,划分为“君子”与“小人”,其标准是“仁”。所谓“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25];“君子上达,小人下达”[26];“君子怀德,小人怀土”[27];“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8]。诸如此类在《论语》中还有很多,都可以看出,孔子的所谓“君子”,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等级分类了,而上升到对于人的整体理想要求,这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怀仁、行仁,那么你就是“君子”,否则你就是一个“小人”。由此可知,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已经超越了阶级、等级的意义。孔子这一设计意图很明显,就是想通过这一图式,使人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定位在“君子”范畴里,而去实现“仁”。而且,这种“定位”,似乎还存在某种道德的强迫性:非“君子”,即“小人”。应该指出,孔子关于“君子”的设计仅仅是一个理想模式,是不可能存在和实现的,这一点孔子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论语·宪问》中记载子路问“君子”,孔子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标:“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可他最后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可见他是很明智的。他之所以推出一系列“君子”论,主要在于推进“仁”,使人们朝“君子”靠拢,从而实现“仁”的企望。
第三,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除了西行不到秦,几乎奔走天下,目的在于宣传自己的“仁”学;他也谋求做官,但他是带着自己理想和学术走进庙堂的,所以他并不在乎统治者需要什么,而只要求他们应该怎么做。他的这一出发点注定了他必然会到处碰壁。于是到了晚年,他开始设帐授徒,将传播“仁”学,实现“仁”的任务交给了包括他的学生在内的“士”。这就是他提出的所谓的“士志于道”。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兴起及其作用,学术界已讨论已久,无须再述。仅引余英时先生关于“士志于道”的精彩阐释:“所以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29]至于“道”的内容,孔子的学生曾参已明确领会就是“仁”。《论语·泰伯》中记载:“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的这种由个人对于人类和社会的人文关怀转而要求“士”的群体关怀,不失为其人文精神中最为光辉的一面。
当我们的学术界仍在盛赞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的精神时,我们不妨也回头看看孔子为后世留下的古代人文主义的丰厚遗产。而当我们的社会人文精神日渐失落之时,我们不妨记起孔子的厚望:“士志于道”;“君子忧道不忧贫”。
收稿日期:2000-10-07
标签:孔子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人文关怀论文; 国学论文; 天道论文; 君子论文; 礼乐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