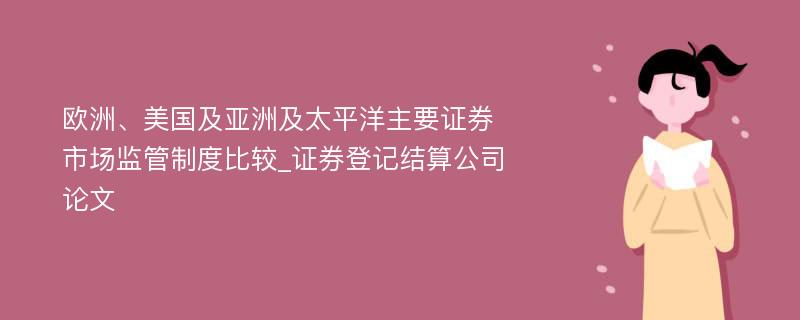
欧美及亚太主要证券市场监管制度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证券市场论文,亚太论文,欧美论文,监管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行政与司法救济并重的美国证券监管制度
美国证券市场发展早期,自发形成的市场使得交易只通过熟人的关系进行,小范围的群体关系就可以使经纪人自觉地遵循公认的规则,进而形成共同遵守的交易惯例与信用维护体系,证券交易能够在缺乏政府机构监管的情况下依靠自律规则而得到有序运行。但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华尔街市场作为美国证券交易中心地位的形成,大量外来经纪商参与到交易过程中。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经纪人通过欺诈、误导的成本变得极低,收益却极大,以散布虚假消息、不转移所有权的自我交易和操纵市场(通过无限制的买空、卖空)为特点的交易泛滥于华尔街的各个角落。而在罗斯福新政前,美国所秉行的是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主义,政府从不干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所谓“自由交易”,这也使得“买者自负”(caveat emptor)成为政府对待证券欺诈行为的默认准则。在这样的监管认知背景下,以获取博弈利益的欺诈行为在证券市场层出不穷。
随着20世纪初经济大萧条时代的到来,1929年那场著名的股市崩盘成为美国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转折点:在美国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委托费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 Pecora)进行了一个名为“皮科拉听证会”的调查后,皮科拉听证会对证券市场欺诈、误导行为的揭示内容激发了广大民众对于联邦政府直接管理股市做法的支持。因此,在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立法机构通过了以贯彻“披露原则”为主的《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这两部法律连同随后几年的《1935年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1940年投资顾问法》构成了美国证券监管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个新建立起来的监管体系以“卖者负责”哲学代替早先“买者自负”原则,要求卖者必须为其出售的证券按照法定的要求向买方或市场做出披露,否则即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授权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得以组建并替代先前的联邦贸易委员会行使对公开发行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职权,美国证券市场由此走向了以登记、披露为主导要求的监管模式。随后几年,《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1978年破产改革法》、《1995年证券私人诉讼改革法》、《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和SEC一系列配套的规章(regulations)和规则(rules),补充并完善了整个美国证券监管制度。
美国监管制度显著特征就是始终以“披露至上”以作为证券监管的原则和监管底线,其所秉承的理论基础在于,通过政府介入市场主体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披露监管,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博弈失衡。在此理念下,就监管责任而言,SEC仅在法律授权范围内,通过颁布法规、法令或登记的方式,就买卖双方如何进行信息披露提出要求,它对市场主体如何参与市场活动,或者以什么方式参与市场交易并不多做干涉。因此,美国的证券监管并不是以行政审批作为其监管特点,主要还是通过对存在法定披露要求信息的登记备案,来实现保证市场交易公平与合理的监管目标。在司法实践中,除如实披露(包括及时、全面、公平披露)的监管要求外,SEC在交易的实体或程序方面并无过多的要求,它只是忠实充当保障市场信息得到有效披露的“看门狗”(watch-dog);而从监管职责上看,SEC不负有维持市场信心或其他直接干预市场交易的监管义务,最近的一次例子就是在2008年爆发堪比1929年股灾的金融危机中,SEC仍秉承不直接干预市场的传统,没有对基于流动性短缺造成的信用恐慌采取证券监管层面的调节与干预。同时,SEC也没有因为金融危机对市场的冲击而放松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相反其加强了对受影响的金融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强化其金融衍生产品数量、交易信息及坏账拨备的信息披露。
总体而言,美国证券监管一直遵循着尊重市场主体交易自主原则,以保护交易信息对称的方式进行证券监管,任何主体若违反法定披露义务或要求,则因其行为的违法性而可在刑事、民事及行政三个层面分别被司法部、交易对手及SEC追诉,从而以设置高昂违法成本的方式来阻却市场主体的违法动机。在监管责任划分上,由证券交易所依照上市契约与交易所章程负责日常的交易监管,SEC只是负责对各市场主体信息披露合法性、合规性的监管,对具体交易活动介入不深。
二、英国证券市场自律监管的特点
18世纪20世纪初,英国以南海公司为代表的一批贸易公司以编制各种海市蜃楼般的利润前景诱骗投资者从事股票交易。1720年6月,为制止各类“泡沫公司”的膨胀,英国国会通过了《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即著名的《泡沫法案》,the Bubble Act),开始以政府管制方式对内幕交易与投机行为进行规制,并最终挤破南海公司的股市神话。以南海事件为代表的股市泡沫的破灭使“神圣”的政府信用随之破灭,英国自此整整100年没有发行过股票。
随着以蒸汽机车为代表的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18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的发展重新刺激商人对资金融通的需求,从而再次掀起股票发行与交易热潮。为防止重蹈南海泡沫覆辙,英国国会在1844年的《公司法》里首次规定了公司公开招股时对发布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要求,由此建立了现代证券发行披露报告制度雏形。但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除招股书的披露要求外,英国并没有在成文的法律层面规定对应的证券监管机关(作为市场组织者的交易所除外)。相反,如同对银行、保险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那样,其证券监管多采用“自我管理”方式,通过“道义劝说”对市场参与主体的业务活动与经营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并由此形成大量具有实质管理作用和影响力的行业自律组织。
至少在1986年《金融服务法案》(Financial Service Act)以前,英国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通过司法介入的“纯法院”模式予以解决,其监管理念是将证券交易等同于其他商品交易一样,由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各负其责,政府不作任何干预。若发生相关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案件,受害方可依据成文法和判例法寻求民法和刑法保护。证券市场的约束只是依靠诚信、合同法以及交易所与证券公司自律维护交易,同时法院按照判例法精神在实践中不断造法,以判例形式给市场树立规则。1986年作为“金融大爆炸”(big-bang)的改革产物,《金融服务法》(Financial Service Act)获得英国议会的通过。金融服务法整合了对所有涉及金融领域投资活动的监管要求,对投资业务的业务许可做出了法律上的要求。为此,英国成立了拥有管理证券市场权限的证券和投资委员会(SIB)。在SIB的授权下,不同行业的自律性组织(Self Regulation Organizations,SROs)承担对行业直接、日常的授权和监察工作,每一个自律组织负责管理金融服务业中的一个特别领域。1991年,证券协会和期货经纪商与交易商协会在合并后创建了证券与期货管理局(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 Authority,SFA),也成为一个法定的证券行业监管机构,从而形成对证券业多头管理的金融监管体制。在此过程中,英国制定了包括1995年《向社会公众发行证券的规定》(简称POSR)、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简称FS-MA)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法律、法规。其中,《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整合了先前关于金融监管(包括证券监管)的所有法律,成为英国规范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而依据《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设立的英国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FSA),整合了先前全部金融监管机关,成为金融行业的统一监管机构(仍是一种公司制组织而非政府机构)。
综观英国证券监管制度,虽没有专门立法体系,却有较为完善的证券市场自我管理体系,强调“自律原则”多过政府监管。它的监管特色在于没有专门的“证券法”,有关证券发行与交易的监管制度散落于财产法、公司法及有关证券代理方面(经纪人监管)的法律。这源于英国立法和司法传统上一直将证券视为一种新的财产类型,从而沿用普通法和衡平法项下的商品交易裁决规则,并以“法院造法”和“法院释法”的形式进行证券交易行为的事后监管。因此,可以说法院的判例造法和议会立法,是英国证券市场在200年无“英国证监会”情况下得以不断发展并成为欧洲最大的金融中心的秘诀。最近20年来,为顺应证券市场发展和国际化需要,英国也在判例法基础上,结合证券市场特点,在实现监管体制集中化的同时,实现证券市场立法的成文化和体系化。
三、德国证券市场的三层监管架构
德国证券市场产生于16世纪,到现在已有400多年历史,但德国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历史尚不久远,证券监管在德国被认为是最年轻的监管领域。在1994年以前,德国证券市场没有建立统一的证券法体系,没有一个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中央性机构,自律管理成为市场管理的基本形式。
1994年后,德国依据《第二部金融市场促进法案》颁布了《有价证券交易法》,并设立联邦证券交易监管局(BaFin)对内幕交易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等行为进行联邦监管。2002年,德国为适应对金融混业经营的监管,成立联邦金融监管局,负责对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市场以及政府资产进行监管。随后,市场操纵等原本由各州自行监管的监管职责被上升至联邦金融监管局。
德国现行证券监管机构和监管体系存在三重监管结构,除联邦金融监管局外,各州也都设有各自的监管机构,加上在证券交易所内设置的监管办公室,形成了德国证券市场监管的三层构架。这三个层次监管机构的职权范围彼此有别,又相互合作。交易所的监管办公室处于证券监管体制的最前端,是一线监管者,负责管理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等具体业务,履行对证券交易的一线监管职能;州政府交易所监管机关负责监管本州辖区内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行为,对交易所实施法律监督,对辖区内的交易、结算和其他证券活动进行监管;联邦金融监管局是联邦直属的公法上的行政机关,履行对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国家监管职能。联邦金监局与各州政府交易所监管机关之间不是隶属关系,而是相互合作、密切配合的关系。
四、“护航式”的日本证券监管制度
日本证券交易来源于明治初年的大米商品交易。由于战前的交易是以股票的投机买卖为中心,因此对证券市场的管理主要以对流通市场和流通业者进行规范为中心。所以,在1941年移交大藏省管理之前,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是农畜务省和工商省。二战后,日本建立了一种以利率限制、业务活动领域限制以及国内外金融市场分离为主要内容,并以间接融资优势为主要特征的限制性金融体制。在证券监管领域,日本参照美国的证券监管模式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为证券行政的中枢机关。1948年日本模仿美国证券法体制制定了《证券交易法》,作为证券法制的核心法律。在监管主体层面,作为金融业行政主管机关的大藏省不仅负责对包括证券业在内的整个金融业的监管,还承担对金融机构经营的限制、管理、监督和检查。它既是金融体系中的政策制定者,又是政策执行者,还是政策实施的监管者。
在日本,证券市场作为“应该被保持和强化的重要的国家财产”的观念影响深远,通过管制使资金流向政府优先支持的相关产业是政府控制证券市场以实现政策意图的基本手段之一。20世纪80年代前,日本的证券监管属于政府高度管制的“过度规制”(excessive regulation)状态,这与日本作为西方发达国家融入“金融自由一体化”的进程格格不入,证券监管难度和成本越来越高。1991年,由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主导的“证券舞弊案”激化了市场及投资者对政府证券过度监管的责难。为此,日本大藏省在1992年不得不重设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作为分管有关证券交易以及金融期货交易的监督机构。随后,为适应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提高日本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东京国际金融市场地位,日本政府对金融体制进行了放松管制、加速金融自由化、重组金融机构等多方面的改革。1998年,证券监管部门从大藏省独立出来成为总理府直接管辖的金融监督厅。2000年7月,在金融监督厅的基础上成立金融厅。金融厅承接了原大藏省对证券市场进行检查、监督和审批备案的全部职能。2001年1月,金融厅升格为内阁府外设局,成为日本金融监管最高机构,独立行使并全面负责金融业监管。至此,日本金融监管有了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
日本证券监管体制的特点是一种“护航式”的监管。“在监管机构的护卫下,以航速最慢的船只即效率最差的金融机构为标准,制定各种市场管制措施,维持不破产神话。”在日本,从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到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规范都在监管之列,连金融服务价格和金融机构日常经营活动也由一只高高在上的“看得见的手”操纵。政府的行政指导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府事先划定的游戏范围成为一种软约束,它能与管制对象进行充分协商,但缺乏统一规范,从而使管制存在不透明性和无规则性。日本证券监管的这种监管特点有其两面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证券机构资金来源短缺,证券机构往往选择服从政府指导,监管当局的行政命令就易于贯彻,监管效率能够得以体现;其弊端则是当证券机构资金短缺得到缓解,监管当局对经营机构的奖励意义逐步减缓之后,当局监管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五、香港证券市场的“轻度监管”传统
香港证券经纪协会在1891年成立(1941年改名为香港股票交易所)。20世纪70年代之前,因港英政府奉行对经济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加之受英国对证券市场进行自律性监管理念的影响,香港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采取由市场自我调节的监管政策。但随着1973-1974年股市震荡及内幕交易丑闻的频发,香港当局为保护投资者而被迫采取措施监管股市。为此,香港颁布了《证券条例》、《商品交易条例》和《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建立起相应的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商品交易事务监察委员会和相应的监理专员办事处。1989年,为进一步适应证券市场监管需要,香港立法局依据戴维森报告(the Davison Report.27 May 1988)的建议通过了《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条例》,该条例正式指出证券监管的目标是“使市场有足够的流通量,并公平、有秩序和有效率地运作;控制和减低交易系统风险,避免市场失灵和适当地管理风险,以确保一个市场的危机不致影响其他的金融范畴;保护投资者;促进一个有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经济环境的设立。”为此,一个独立的法定监管机构——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证监会,SFC)于1989年5月1日成立。
在SFC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从监管分工的实践而言,作为证券上市及交易撮合主体的交易所仍承担着对证券监管的更多监管权限。1991年11月,SFC与联合交易所签订《谅解备忘录》,把对《上市规则》的日常管理及监管上市公司的直接责任移交给联交所。因此,香港的交易所(1997年前以香港联合交易所为主)拥有多项监管职能,更多地承担一个类似于“俱乐部”性质的自律性组织的管理职能,而证监会只承担对交易所、金融中介人、监管投资产品的销售、收购及合并活动的监管职责。为进一步弥补自律组织监管的不足,在1999年3月,香港财政司公布了香港证券与期货市场的全面市场改革计划。此后不久,在完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期货交易所有限公司和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合并后,交易所对券商监管的工作正式移交香港证监会。2003年4月1日,两部在香港证券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法规《证券及期货条例》和《证券及期货(在证券市场上市)规则》同时生效,这两部法规重新确定了证监会与交易所对上市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双重存档”制,由此重新构建了目前香港证券市场“双重监管”的主要制度框架。
从总体而言,香港证券监管的特点仍遵从“自行规管”和“轻度监管”的监管方式。如同“戴维森报告”所阐述的:“我们仍推荐采用一个以从业员为本的自行规管制度,这是能够实现我们为香港订下的目标的最佳途径。我们作出这个决定则希望极力避免以严厉的法定制度来约束证券市场,这样的一个制度很容易会使市场过分受到反应缓慢或运作不灵的管制方式限制……我们不能单单因为有人不当地使用或严重滥用这个制度而完全将它摒弃。”因此,香港的证券监管仍然体现了高度的自律监管性质:监管机构只对专业机构的资格准入、信息披露等小部分市场行为实现直接监管,其他方面的监管多通过对交易所与专业机构的监管实现间接监管。
借鉴英国传统,香港没有综合性的证券法例对证券监管进行统筹监管,调节证券市场的各种规定及监管要求散见于《公司条例》、《收购与合并守则》、《证券(权益披露)条例》、《证券(内幕交易)条例》及交易所上市规则之中,而且监管手段多为警戒、谴责等道德监管手段,行政或法定监管的约束力较弱,缺乏罚款、刑责等法律诉讼历史传统。
六、结论
就主要证券市场的监管历史及监管经验而言,监管制度的形成具有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特点。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美国、英国还是上述其他国家的监管制度存在多大区别,都是在市场变迁驱动下完成对监管制度的设立与改革,是一种典型的“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在我国证券市场属于“强制性变迁”路径的背景下,借鉴与学习虽是我国证券市场监管路径选择与完善的“捷径”,但经验告诉我们,“选择经常服从于实用色彩的研究,选择必须由实际可观察的产权选择的有效性所决定。”因此,就学习借鉴的角度而言,在我国“市场加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证券市场的监管提升之道应该是在分析、总结上述国家和地区先进监管制度的历史轨迹、监管特点、监管背景,“去粗存精”、“去害存益”,借鉴先进市场监管经验来完善我国证券监管的改革之路。
标签: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监管机构论文; 证券论文; 金融论文; 证券交易论文; 法律论文; 交易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