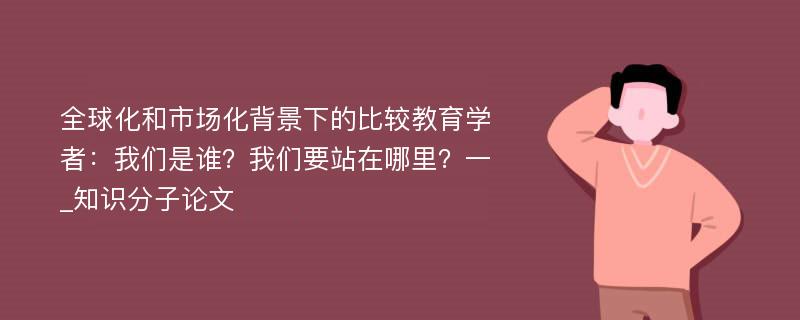
全球化和市场化背景下的比较教育学者:我们是谁?我们的立场何在?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者论文,立场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209(2006)03—0021—07
关于比较教育以及比较教育学者身份和使命问题的讨论,已经在该领域存在了大概有一百多年之久。其身份与使命的表现方式也随着不同的地区和背景而有所不同。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分析了在全球化时代和教育市场化背景下比较教育学者的角色问题。(众所周知),全球化时代和教育市场化给比较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我主要分析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 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 的著作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观点和理论。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对英语世界国家里的比较教育学者对自身角色的认识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其中尤其关注他/她们对自身和比较教育领域的期望以及他/她们的担忧之处。最后,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我反思了全球化和教育市场化对比较教育工作、学者身份以及目标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一、知识分子
葛兰西对各种“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概念进行了评述。他反对传统的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一个界限清晰的社会群体,因此反对把知识分子定义为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或者是那些只与文字打交道而脱离经济政治生活以及历史进程的群体。不过他同时也指出,有些群体自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比如他的话语体系中的“神职人员”以及他所认为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某些群体。他认为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保守并往往向统治阶层妥协。[3](P132)他也反对有些人是知识分子而有些人不是知识分子的论调,认为即使是体力劳动者,也具有对这个世界独特的概念,也具有道德意识,同样也为新知识的产生作出了贡献。不过,葛兰西也承认,在对社会的作用中,有些人智力上的影响力的确比另外一些人要大。
在葛兰西的著作中,他认为每个社会阶级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就是对其所在的社会群体进行同质化影响以及帮助该群体理解自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角色。这些知识分子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该社会群体的,因此葛兰西把他/她们称为“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于是资产阶级就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且还包括具有各种专家知识的知识分子,比如技术知识、政治经济学知识、法律知识等等。同时,在各个社会阶级内部,知识分子也有分层的现象。比如有些知识分子提供专家知识,而有些知识分子则担任内部成员组织者的角色。
葛兰西注意到,那些处于统治地位或者是寻求成为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往往不断地扩展并精心设计内部知识分子的分层现象,同时不断地将其他社会阶级的知识分子笼络到自己的阵营中来。这些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扮演着统治阶级“代理人”的角色,并保证维持统治阶级的霸权地位,以及保证大众默许由统治阶级所确认的社会生活秩序。
学校在知识分子的生产和制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葛兰西指出,教育体制的范围越广阔,知识分子多样性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那些掌握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基础教育扩展的民主过程(即“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为满足统治阶级对专业知识分子的要求提供了便利条件。
葛兰西在他1926年入狱到1937年去世期间详细阐述了其有关知识分子的观点。在当今被称为后现代社会的世界中,我们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我们可以将他关于社会群体的概念扩展到性别、种族和其他社会群体,这里的社会群体不同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阶级的概念。于是我们可以认为所有的社会群体——不管其是否建立在阶级、性别、种族或是其他类的性质上——都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创造和维持该社会群体的身份以及理解该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的社会地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第二,葛兰西为我们指出了学校在生产不同种类的知识分子以及促进理智主义中的作用。他还警告我们,学校往往服务于统治阶层对智力知识分子的要求,而以牺牲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为代价。
与葛兰西类似,福柯也对知识分子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在葛兰西去世40年后,福柯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欧洲“左派”知识分子(left intellectuals)的减少。工人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的概念)已经变得更像“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倾向于寻求关于公平、公正以及法律的永恒、普遍的真理,“他(工人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声称要成为宇宙的代言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就意味着像是社会的良心/良知……就像无产阶级一样,由于它的历史地位,要成为世界的信使……因此知识分子期望通过自己的道德、理论和实践选择,成为普遍性的表达者”。
然而,福柯认为,欧洲知识分子从二战以后变得越来越与实践相连,越来越与社会的某些专门领域相连。因此他/她们获得了一种“对斗争更及时和具体的认识”。这些专业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大众或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候也不一定与大众或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和大众一起面对着共同的对手,比如“跨国公司、司法和警察机构、投机商等等”,他/她们因此与大众的距离拉近了很多。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学术工作关注的焦点,从试图表达普适性的真理或价值,转移到了专门部门以及学者知识之间的政治参与中来。福柯还举了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Oppenheimer)的例子,认为这位科学家不再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也不再是一个“试图寻找普遍价值观念,甚至希望死后流芳百世”的人。相反,这位科学家所拥有的尖端知识“既可以用来为国家服务,也可以用来反对该国家;既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
尽管这些知识分子拥有高深的专门知识以及与之相连的权力,但是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危险。第一,尽管这些领域是相互联系和依存的,不过他/她们的工作领域基本上还是限于专业之内。第二,这些专业知识分子有可能会被地方群体比如某些协会或是政治团体所利用。第三,这些知识分子在其自身领域之外缺乏全球性的视野,而这有可能会限制其解决地方问题的有效性。在第一种情况下,地区性斗争/工作可能是很重要的,比如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第二种情况下,即使在为国家、协会或是政治团体服务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也有可能带来战略性的变化。
根据福柯的观点,专业知识分子无论其所属的阶级地位或生活、工作条件如何,他/她们都不可避免地与真理相关。用政治的术语说,这并不是指将真理与谬误分开,也不是去发现或接受什么是真理,而是关于理解权力与真理之间关系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关于“与真理相关的所有权力规则”以及“真理的地位及其所扮演的经济和政治角色”的斗争。
布莱克尔[4](P348—367) 提出了专业知识分子的两条实践原则:第一, 他认为,专业知识分子可以通过限制活动的范围来提高其效率,这样的话他/她们就能获得更深广的影响。第二,专业知识分子内部可以达成某种“诚实和正直”,这样才能保证其对自身工作可能带来的影响持续保持关注。在上文提到的核物理家的例子中,他们的工作是非常高效的,但是他们缺乏某种正直感,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缺乏清醒的认识。
总的说来,葛兰西认为:
“传统的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错误地把自己看作脱离政治、经济或历史背景的知识分子。
“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是指从属于某个社会阶层,并与阶层之间的知识斗争相连的知识分子。
福柯认为:
“左派的知识分子”(left intellectuals)是工人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倾向于寻求某些普适性的真理。
“专业/专门的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s)具有可能产生广泛影响的专门知识,有被各种团体利用的危险。由于其地位能够产生战略性的影响,他/她们尤其具有发现和识别真理的能力,他/她们应当对自己的工作可能产生的政治、社会和其他影响有更清醒的认识。
接下来我们将主要分析英语世界国家的比较教育学者对自身身份、角色和特征的认识。
二、比较教育和比较教育学者
因为比较教育是一个专门的领域,很多比较教育学者很自然地都把自己看作专家。在福柯的概念中,即他/她们认为自己是“专门的知识分子”。关于比较教育是否是教育领域中的一个专门领域的讨论发生在二战以后,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那个时代正是传统知识分子向专业知识分子转变的时代。在西方比较教育学领域,很多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纽约大学举行的比较教育大会上。在那次会议上,学者们所关心的是他/她们的工作既应当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应当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5](P88—96)[6][7](P30—34)后来的比较教育学者同样有类似的担心。[8](P1—6)[9][10][11]作为专门知识分子,这些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福柯所提到的危险,即专业的限制有可能会影响学者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生作用。
除此之外,很多学者还表现出了保护学科疆域的期望。尤其20世纪50年代,在比较教育学界发生了一种忧虑,即害怕没有受过专门学科训练的外行人会对教育政策产生影响。这种忧虑主要表现在对业余爱好者、门外汉、非正规的学者以及新上任的所谓权威等这些外行人的担忧上。[7](P30—34)[12](P116—125)[13]
尽管西方的比较教育学者期望对教育政策产生影响,但是他/她们很少明确地表示有可能会被政府、政党或其他社会团体利用的危险。相反,早期的比较教育学者把自身的角色定位为通过促进(本国)教育体制的发展来帮助国家打败竞争对手,[14]而康德尔[15] 和格雷斯[16] 则明确地表示比较教育的目的是作为民主的保卫者和极权主义的对立者。不过也有两个例外,一个例子是贝雷迪,[6]在苏联卫星上天给美国社会带来的一片哗然中,他曾担心比较教育可能会因此受到抑制和警告;另一个例子是布劳德福特,[17]他反对某些带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政府和国际组织所倡导的教育商品化。
福柯认为专门知识分子的一种危险是可能缺乏全球性的眼光。总体说来,对于比较教育学者来说,这种危险是不存在的。相反,在某些情况下他/她们过分夸大了比较教育对于社会和世界的影响。比如,很多学者曾希望比较教育能阻止战争的发生[14][18][19](P8—11)[20] 或者是解放被压迫者。[21][22](P25—49)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打算详细地讨论比较教育学者所属的社会阶层,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许多被认为是西方比较教育奠基人的学者(或教育官员)都与统治阶级有明确的关联,因此用葛兰西的话说,这些早期的比较教育学者是统治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在这篇文章中,我也不打算探寻布莱克尔[4](P348—367) 所描绘的专门知识分子的正直和可信程度。在其他的文章中,我曾经讨论过比较教育学者对“学科边界警察”的现象缺乏关注,并分析过比较教育学者试图定义和规定学科领域而带来的后果。[23][24]不过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我将回到关于比较教育学者正直和诚实性的讨论中。同时,下面还将对比较教育学者中的“传统知识分子”(葛兰西的概念)和“左派知识分子”(福柯的概念)作两点说明。
第一,虽然比较教育学者很少把自己看作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但是很多比较教育学者都试图把历史上的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圣职人员)拉进比较教育名人的万神殿中。在这些先人中,我们可以发现的例子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尼、西塞罗、尤里斯·凯撒、塔西佗、圣保罗、马可·波罗、神圣罗马教皇四世、阿卜杜拉—拉赫曼·哈路德(Abd-al-Rhamam Ibn Khalud)、马太·阿诺德。[25][5][26][27](P220)[28](P150—158)[29][30](P85—97)
第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比较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当福柯认为20世纪的欧洲左派知识分子向专门知识分子转向时,比较教育学领域的专门知识分子较之左派知识分子占据更优势的地位,并且前者很可能繁荣起来而后者则逐渐衰落。
三、全球化和市场化
在最近10年中,很多对教育和全球化进行研究的学者对全球化的定义都比较狭窄。比如,麦克金[31] 将全球化等同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如教育管理与决策的分权化趋势。斯特姆奎斯特和孟曼,[32](P3—25)瑞威和林茄德[33] 以及西恩[34] 主要从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维度对全球化进行了研究。当我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虑全球化时,很显然,作为一种现象,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会、地理和文化环境中对全球化的体验都有所不同。[34]全球化,尤其是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全球性的合作,能够促进民主观念、人权和环境意识。[34][35]全球化还能为人们提供不同于自身背景的各种文化资源,使人们得到不同的文化体验,感受到不同的文化活动和文化身份,同时全球化也是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深入挖掘。因此全球化能够促进文化的异质化,不过政府对于这种异质化的反应有可能是反面的。[36]同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带来文化类型、教育政策、经济政策等的同质化,而在世界范围内,由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分配是很不均衡的。[33]正如瑞威和林茄德[33] 指出的那样, 全球市场的增长以及政府对此的放任,导致对“民族国家作为国家经济、公共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管理者”的角色重新定位。但是,全球市场的增长以及跨国公司的控制对民族国家角色的再定位有重要的影响,比如对重要药品的专利控制以及所谓的“自由贸易”有可能会对地方经济产生毁灭性的打击。也就是说,对于世界上大部分人口来说,全球化不仅仅是一套理论、一种现象或一种态度,[34]它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
在全球化所带来的矛盾性、复杂性和双面性中,我们能从葛兰西和福柯对知识分子的理论中获得怎样的启示呢?葛兰西70年前关于“传统知识分子是一种幻想”的说法在今天依然是相当中肯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相关联。这也就是说,不管比较教育学者自身的社会阶层、性别、文化或其他社会地位如何,他/她们都需要确定自己的忠诚对象,并决定到底服务于谁的利益。葛兰西提出的一种可能性就是“成为统治阶层的‘代理人’……社会霸权和国家统治的组成部分”[1]。
至于成为追寻普遍伦理的“左派知识分子”的可能性,正如福柯提到的那样,这种普适性的想法是有问题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提法就更有问题。因为其一,全球化是一个矛盾体,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即他/她们不可能寻求普适性的真理);其二,对于有些人的生活来说,全球化给他/她们带来了真实的不利影响,而左派知识分子揭露和反对压迫行为的传统,在全球化带来的不均衡影响中尽管是很重要的,但他/她们不可能为所有人代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比较教育学者来说,专门知识分子的提法依然是合适的,但同时也是具有危险性的。之所以称它是合适的,是因为全球化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领域需要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分子,比如经济学家、会计师、咨询师、国际教育专家、企业家等等。之所以称它是危险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教育专家很容易被拉入统治阶层的阵营。用葛兰西的话说,即危险在于我们间接地成为专门知识分子,在具有专业知识的同时,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了某种政治意味。第二,用布莱克尔[4](P348—367) 的话说, 我们的工作可能产生不诚实和不正直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对自身工作可能带来的无意识影响缺乏持续的关注。比如,如果我们为一个旨在促进“全民教育”的国际组织工作的话,我们就需要牢记让所有的孩子都接受基础教育这种想法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我们需要关注它的实现方式,注意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谁的知识,谁的知识被排除在外了?究竟是谁从中获益?对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和文化影响?第三,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专门知识分子面临的危险还有,我们缺乏理解全球化的理论、态度和现象所需要具备的宽广知识基础[34]。另外,由全球化所带来的知识爆炸也同样是一个强大的阻碍。为了深刻理解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全球化,我们需要阅读经济学、发展学、历史学、后殖民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传媒研究、社会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如果我们对教育和全球化感兴趣的话,我们还必须阅读关于以上提到的各个领域与教育的关系的著作。除此之外,还必须关注当代的焦点问题,比如教育公平、教育管理、性别问题、多元文化教育、教育的国际化、合作办学、政策研究、教育人类学,等等。如果我们认为在以上提到的所有领域都有深入研究是不可能的话,那么,作为专门知识分子,我们就需要寻求研究全球化问题的新策略和新方法。
在全球化和研究全球化的过程中,专门知识分子需要对专业领域有深入的研究。不过为了对全球化以及它的有利和不利影响进行更透彻的研究,正直的专门知识分子可以采取的策略是与其他相关领域的联合。这种联合可以是暂时性的,只在研究项目或咨询中存在,并且旨在解决地区性或本土问题(在性别研究中也有类似的讨论[37])。在这种联合中的专门知识分子,能够将具有各种学科知识的知识分子以及各个部门的人联合起来,共同解决某些本土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成为来自本土社会群体的专门知识分子。通过这种类型的合作,以及在全球化的研究中选择可行的和正直的立场,专门知识分子就能避免上文提到的各种危险,比如被统治阶层利用、给社会带来无意的负面影响、知识面过于狭窄,等等。
收稿日期:2005—11—10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葛兰西论文; 全球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福柯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