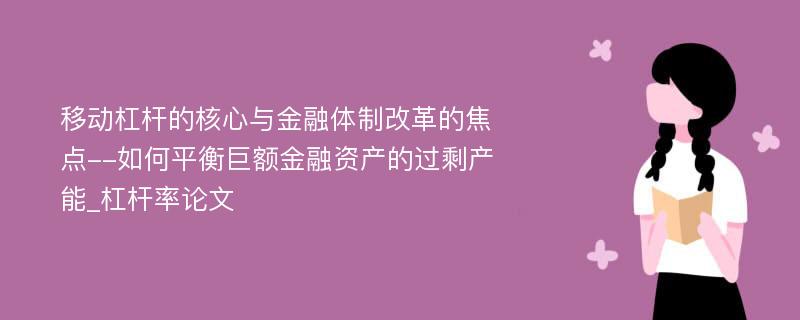
移动杠杆率的核心与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如何平衡过剩产能和巨额金融资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杠杆论文,产能论文,巨额论文,金融体系论文,金融资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5年年中出现“股灾”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它并不是一次偶发性的股票市场价格的急剧波动事件,也不是金融监管部门没有能够有效地对股票市场实施监管的结果,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产规模扩大和金融资产快速增长之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路径来扩大总需求的必然现象。因而,对于下一步金融改革的方向和重点的讨论,应该跳出股票市场本身的监管思路,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和新的发展特征的梳理上入手,明确什么样的融资体系才能更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和促进经济增长。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当前中国经济有两大新特征:一是产能过剩使得工业产品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而经济政策的重点仍然聚焦在为企业提供更多资金的供给观点;二是已积累起的庞大的金融资产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寻求一种日益高涨的资产回报率,而产能过剩的经济体并不能通过金融市场提供这样的机会,于是,过多的金融资产都去追逐有限供给的金融产品。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解决过剩产能和巨额金融资产之间的矛盾,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将会经历频繁的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 需求相对不足的产能过剩压力 计划经济的特点是短缺经济,产能过剩则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工业产品从供给短缺到过剩是最近十年的事情,2002-2014年工业产品的增长率不仅是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工业史上罕见的绝唱,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从2000年大约6.3%到2014年的22.7%,只用了14年的时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回眸过去十年,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经历了一次爆发性增长,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惊人的,可以用工业产品的实物增长率来测定这一时期中国工业革命的成就,下述的数据是有说服力的:其一,2001-2014年,钢材产量从1.61亿吨增加到11.50亿吨,增长十倍。其二,发电量从14808亿千瓦小时增加到53976亿千瓦小时,增长四倍。其三,制造业资产从10万亿元增加到100万亿元,增长十倍。在许多国家为十年能够增长一倍而欢欣鼓舞时,中国工业增长的步伐则是一次又一次创造了新的纪录。 显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过巨大的投资所形成的工业生产能力,一旦遇到总需求下降就迅速变成了“过剩”,它已经变成了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一大难题。2012年以来,国内外需求增长的相对不足使得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已经连续三年半是负数了;最终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也受到抑制,2012年和2013年的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只有2.6%,2014年下降为2.0%,2015年上半年的消费物价指数处于“一字头”:1.2%。 为了应对通货紧缩的风险,2014年11月以来的四次下调存贷款利率的货币政策做了适时的调整,同时适度增加了社会融资量。政策本意是释放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积极推动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然而,释放的货币流动性会促使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生产性企业吗?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在于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的背景下,企业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积压的库存,如果银行向生产性企业提供贷款,则企业利用新增贷款来增加生产的必然结果是更多的库存。越来越多的库存吸收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和物质资源,却无法找到一个需求旺盛的最终消费市场,各种资源就沉淀在库存的产品上,从而使商业银行不得不面对更多的企业坏账。资不抵债的企业并不是没有资产,而是有着找不到市场需求的库存。2015年第一季度,工业利润是负增长4.2%。当前,讨论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恐怕只是一种空泛的议论,企业需要消化库存才是政策的重点,而大多数企业正是在一个产能普遍过剩的市场环境下,进行生产和经营的。 因此,要使经济能够顺畅运行,政策调整的核心应是扩大总需求为企业创造一个更大的市场。由于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7500美元的水平,创造和扩大总需求就不是低水平的发展需求了,不是吃饱和穿暖的需求,它需要借助于金融体系为更大的市场需求提供资金,要创造更高水平的市场需求。 提高金融体系在物质财富创造中的配置作用 金融体系的最基本功能是促进一个国家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它不是为少数人发财致富提供的场所。倘若金融体系仅仅以“低进高出”的利息运用方式,来为各种金融机构创造丰厚利润,这样的做法不仅没有发挥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而且导致了金融资源的错误配置,即生产企业的低利润与金融行业的高利润同时并存,生产企业成为金融机构的“打工者”。 进入21世纪后,人均收入增长的真正基础是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中国金融体系已累积起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当社会财富被不断创造出来时,它就需要以货币等金融资产的方式来表明其价值。下述数例即可说明金融资产的快速膨胀:其一,2002-2014年,居民储蓄从8.69万亿元增加到50万亿元,增长5.7倍;其二,货币供应量M2从18.50万亿元增加到122.8万亿元,增长5.75倍;其三,社会融资规模从2万亿元增加到17.32万亿元,增长7.66倍。中国的金融资产增长是伴随着物质资产的增长而来的,是真实的金融资产。然而,与储蓄资产相比较,股市的市值波动则可以看作“虚拟”值了。比如,大家熟知的上证综指,以全年的平均数来看,2002年是1358,2007年攀升到5262,2008年下跌至1821,2015年6月初又上升到5100,2015年8月21日再度下跌到3500。指数的上下波动,其反映的是市场预期导致的资金流入数量的变化,并不是经济增长率的高低。 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环境下,“过度繁荣”的股市变成了各种金融资产追求更高回报率的理想场所:在股市的市值上涨时会吸收大量资金,在股市的市值下跌时,既消蚀了股票的市值,也促使大量资金离市。那么,股灾之后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使金融资源流向能够提供稳定回报率的实体经济部门? 面对工业产能过剩性和金融资产流动性的双重压力,当务之急应是扩大有真实需求的市场,积极推动金融资源向物质财富的创造部门流动,如此,金融资源的(高)回报才有变成现实的可能。如果宏观政策调整重点从单纯的资金流动性管理转向总需求管理,以更加积极的政策明确人均收入要从2014年的7500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1.5万美元,则需要有更大规模的物质财富来支撑,而创造稳定上升的实际需求就是必然的选择。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的风险,也会随着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大规模的资本形成而逐渐消退。 以移动杠杆率来扩大总需求 当前,经济增长率下行的挑战是严峻的。2015年第1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增长率分别只有14.5%和10.6%,比2014年的15.3%和10.9%更低,出口则受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影响,使得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是下降的。2009-2013年,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在48%左右,居民消费占36.17%,合计为84%;而政府消费占GDP比率在2013年为13.63%,仅仅依靠政府支出的增加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总需求的。要防止经济增长率的继续下滑,就必须在提高资本形成和扩大居民消费支出方面提出新的对策。 怎样来减轻当前经济增长率放缓的压力?中央政府的政策重点仍然强调改变供给结构方面。今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两条指导性意见:一是“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二是“把发展实体经济和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 那么,谁来选择和决定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从流行的做法来看,应由政府部门来主导金融资源的配置。但企业的投资方向是由企业本身决定的,如果企业投资决策失误,期望和理想中的投资项目变成了亏损,企业的负债率也就上升了。如此,政策的重点能否转换一下呢?即把扩大总需求的政策从增加供给的角度向增加需求的角度转换,尤其是向居民的投资与消费需求转换,使居民成为投资主体之一。因为,中央政府无论是促使商业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还是发挥资本市场作用,以企业上市的方式提供资金,均在短期内难以解决产能过剩下的工业利润增长率下降的颓势。 怎样的政策才能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呢?笔者以为,可以考虑移动杠杆率的办法来提高居民的投资与消费率,以最终需求端的扩大带动总需求的增长。杠杆率是负债与收入的比例,宏观经济的杠杆率可以用负债与国民收入的比例来衡量。移动杠杆率就是在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之间,通过调整负债率的方法来提高总需求。而中国移动杠杆率的空间非常大,是未来几年宏观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理想工具。 第一,与其他经济大国相比较,中国经济的杠杆率并不高,非金融企业则有较高的杠杆风险。以2013年债务占GDP比率统计,非金融企业为130%,居民家庭为23%,政府为57%。由于各国杠杆率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经济增长率也不同,因而很难用统一的指标来评论杠杆率的高低。如果以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的德国为参照坐标,德国的杠杆率是非金融企业为49%,居民家庭为55%,政府为77%,杠杆率的结构性差异一目了然。中国的非金融企业主要还是工业企业杠杆率太高,这是2002-2012年间的大规模投资导致的,工业产值占GDP40%的比率反映了我国工业化的特征。不管以什么标准来说,非金融企业130%的杠杆率确实太高了。而从外源融资为主迅速向内源融资为主转变,通过需求的持续增加来消化库存,是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有效途径。杠杆率的数据显示,供给层面的政策支持有可能使已经很高的企业杠杆率变得更高,中央政府需要作出一个新的政策考虑:是继续支持企业的融资,还是把贷款的很大一部分转向居民家庭,逐步提高居民家庭杠杆率从而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第二,中国居民家庭的杠杆率仅为23%,说明居民的负债率相对较低。而家庭部门的债务通常选择住户贷款这一指标,以贷款额与GDP比率来衡量家庭部门杠杆率水平,因此,要提高居民家庭杠杆率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居民储蓄率仍然非常高,2014年的居民储蓄额为50万亿元,是当年GDP的79%。2012-2014年,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居民储蓄/GDP比率则温和上升,2012年和2013年分别是76.92%和78.69%。在这么高的储蓄率背景下去讨论增加居民杠杆率,可能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但必须看到,一个较高的居民储蓄/GDP比率表明需要加大投资力度,逐步降低居民储蓄/GDP比率和提高居民负债率是并行不悖的政策。而居民家庭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上升,在消化过剩产能的同时又能够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化解部分企业的债务风险。居民家庭储蓄率的下降和负债率的上升,则取决于居民对投资的需求。由于我国家庭部门负债主要为银行贷款,其中购房贷款占一半以上,居民对住宅的需求直接带动了家庭部门负债的扩张。换言之,将居民家庭的住宅需求列为提高居民负债杠杆率的主要途径,也是由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决定的。 二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是什么?哪些投资和消费领域会成为居民家庭愿意负债的重点?笔者以2013年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比率为例,来说明怎样找准扩大总需求的方向。居民支出的各项比率如下:食品(35.0%)、衣着(10.6%)、居住(9.7%)、家庭用品(6.7%)、交通通信(15.2%)、文教娱乐(12.7%)、医疗保健(6.2%)和其他(3.9%)。随着人均收入上升,食品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恩格尔系数)是持续下降的,传统耐用消费品如彩电、冰箱和新一代信息产品如笔记本电脑、手机、无线上网的普及率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了。未来家庭支出比重大幅度上升主要还是居住类方面,当前9.7%的比重是同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居住条件相对较低的状况有关的。可以预见,未来这一比重上升不会是原有居住条件不变而只是物价上升带来的结果,而应当是居住条件的普遍改善,才会带来居住开支占居民消费结构较高的比率,如20%或30%。因此,住房仍然是居民家庭负债的主要原因,这也是高收入国家的普遍现象。 上述两个方面均说明,移动杠杆率的重点是要激发居民对高质量住房的需求。但我国居民家庭利用银行贷款来购房的需求还有多大呢?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居民的储蓄率不降反升,通过企业负债率的上升来增加供给只会带来产品库存的增加,扩大总供给的政策在产能过剩的条件下不会创造新的需求,只是增加更多的无效供给,经济增长率仍可能继续下滑。 第三,为了说明通过适度提高居民家庭杠杆率来扩大总需求的思路可行性,有必要统计城镇新建住宅总量。1995-2014年,城镇新建住宅总量是136.51亿平方米。以55%的城镇化率计算城镇人口为7.48亿人,新建人均住宅的面积为18平方米。如果要将人均居住面积提高到36平方米,需要翻一番的新建住宅量。对原有低质量住宅的改造、更新也会激发出新的需求。当城镇化率达到75%时,城镇人口将达到10亿以上,其显示对城镇住宅的需求仍然是强劲的。 提高居民家庭的杠杆率无疑需要银行体系的融资政策的支持。当中国储蓄率高于投资率时,增加投资就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有效举措,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提高住宅建造标准来扩大居民家庭对新住宅的需求。更高质量的居民住宅建造,既是消费,也是投资,是居民家庭的投资与消费高度融合的社会财富。政府应当颁布各种激励政策来促进居民家庭用贷款来改善居住水平,如此,以居民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换也找到了落脚点。提高发展标准不仅开启了总需求扩大的大门,投资产生的财富效应也会激励更多的投资。因此,提高包括改善居住水平的发展政策就是创造新的需求。 概言之,当前移动杠杆率的核心,是将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重点,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资金支持转到扩大居民投资与消费需求的总需求扩大方面。与之相对应的金融体系的改革重点,是使金融体系从主要为企业融资转变到企业和居民家庭并重的融资结构,这也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