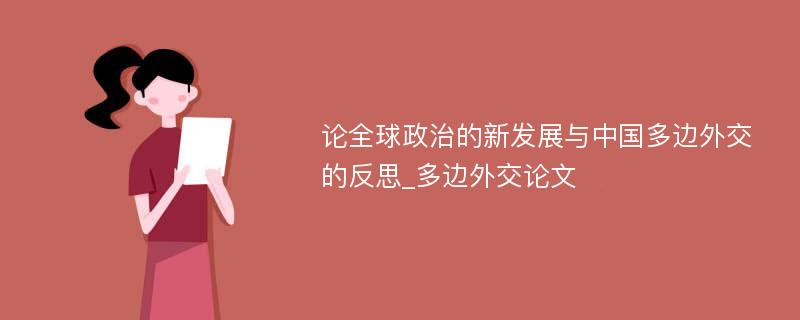
试论全球政治的新发展和中国多边外交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新发展论文,外交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在过去的30年里,多边外交为提高我国外交能力和国家形象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增加了我国处理国际热点问题的有效手段,并日益发展成为中国参与建设国际体系转型的制度性平台。在新的历史时期,全球政治的新发展与全球治理能力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国际多边机制发展的不平衡与全球化背景下要求全球参与、合作共治的需求之间矛盾加剧,改革国际多边机制的呼声持续高涨。同时,在参与国际体系改革过程中,中国多边外交的定位和角色面临不断变化的环境压力。中国外交应当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原则上,积极争取更大作为,努力谋划和塑造有利于捍卫和拓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地区和全球机制,推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民主、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多边外交需要不断丰富、发展其战略和政策的规划。
一、全球治理机制的“能力赤字”日趋严重
当前全球政治新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全局性影响。一是全球政治中涉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重大问题已经上升到各国议程的前列,合作、协调、共进等理念从观念层面提升到政策和战略层面,但与此相反的是全球治理机制的“能力赤字”也在同步提升。
人类面临生存的全球性重大问题不是一个新话题,例如冷战时期的核对峙与核毁灭的危机,以及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等。但新世纪以来,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与全球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行为的联系,全球化中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发展鸿沟”的扩大,边缘国家的“实际的主权能力”严重不足导致的大规模的人道危机和地区不稳定,气候变化的加速发展及其灾难性的环境后果,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等,都对现有国际体系乃至人类家园的生存环境构成严重破坏甚至毁灭性打击。新的国际关系议程要求国际社会成员,尤其是核心成员更关注“代际因素”,即具备“更关注未来影响”,而不仅仅是“眼前发展”的战略意识。①由此,国际体系中合作、特别是大国之间协调合作的空间得以扩展,合作共赢的思想、大国合作共治的理念更具吸引力和生命力。
在全球化以及全球性的人类生存问题的冲击下,现行的多边国际治理机制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发展严重失衡。现行许多国际制度创制时的目的、功能、观念,都无法适应全球化的狂飙突进及其所产生的问题,全球化导致的许多问题无法在现行的国际制度框架中得到充分解决。例如,作为二战后诞生的管理全球政治和安全的联合国,其初衷在于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通过大国一致原则处理国家间的传统冲突。到了60年后的今天,联合国需要应对的国际安全威胁的范畴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对国家之间的传统安全关切已经扩大为关注整个人类的发展、生存等“大安全”议题,但联合国的体制和机制更新步伐尚无法跟上“大安全”议题的变化节奏。②在国际经济领域,以布雷顿森林机构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机制的不充分性矛盾同样突出。例如1997东亚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金融制度在预警、防范以及危机处理和相互协调上的匮乏。同样,2008年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再次暴露了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严重缺乏对国际金融全球化的监督能力和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应对能力。③
有效性不足问题同样日益严重,它首先与一些全球多边机制的实际能力和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脱节有关。例如,长久以来联合国在安全和经济社会问题上的集体多边行动存在效率低、反应迟缓、授权不明、缺乏权威和资源等缺陷,甚至被认为是“最复杂、费时、费事的多边外交形式”。④又例如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各种安排和运行机制,沿袭了二战后初期制定的推进自由化的政策,完全依赖市场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提供短期资金帮助,这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国际发展援助机制的困境则在于缺乏约束性和政治中立性,使得以世界银行为首的国际发展援助机制的援助效果大打折扣。有效性不足的问题还经常涉及主权国家和国际制度权力来源之间的关系。当前,有效性问题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霸权国存在把国际制度视为“私产”的倾向,当国际制度有助于扩展其权益时就加以支持,甚至强制它国跟从参与;而当制度规范不利于其权益,或成为其实现国家利益的障碍时,它们往往采取单边行动,置国际制度于无效。⑤二是一些主权国家的实际主权能力严重不足,存在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以及严重影响地区甚至全球稳定的现实威胁和隐患,但国际社会集体介入并提供合法、有效援助的机制和手段尚不充分。⑥
全球政治发展中的另外两个全局性的影响是国际权势中心从跨大西洋国家(美欧)向其他地区转移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活跃/兴奋”,进一步加剧了当前国际治理机制能力不足的矛盾,其中尤以合法性不足最为尖锐。
美国在“9·11”后的一系列军事、外交和战略失误,尤其是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美国经济发展体制、国际领导力、乃至国家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削弱了其掌控全球事务的能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整体崛起正在改变国际力量格局,促使大国关系发生重大量变,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多极化格局日趋明朗。各类大国更加重视在国际体系的构建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与竞争,以及在未来发展模式和全球政治议题话语权上的合作与竞争。
“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活跃/兴奋”不是新生事物,但现代信息技术的突破全面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活跃和兴奋的范围和程度,促使各种政治、宗教和宗族认同的人群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互动,共同挑战所谓人类社会的“不公平”等“非正义”现状。其表现形式既有相对和平温和的,如全球公民社会与主权国家政府在全球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环境等议题上的矛盾;也有更加极端和暴力的,如各种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总之,全球范围内日益强烈的“不平等”感也促使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尊重多元文化,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解以及和谐共处。⑦
国际权势中心的转移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活跃/兴奋”,加剧了人们对现有国际多边治理机制的合法性置疑。国际多边机制的合法性问题突出表现为机制决策过程和决策内容的代表性不足。由于代表性不充分,所以合法性也受到置疑。合法性不足在不同的国际制度中有程度差异,其外在表现也各有不同。在联合国框架内,合法性发展的不平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表现为贡献与能力相对较高的大国成员对于“一国一票”决策制的“不公正性”的不满;⑧另一方面,它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试图绕开联合国安理会的集体决议(如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或者以“意愿者联盟”形式将联合国作用边缘化(如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后初期的国家重建政策),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忧虑。此外,联合国框架内合法性不平衡问题还表现为包括安理会改革、人权理事会创制过程中的“代表性不足”的不满,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增加在安理会决策中的发言权,成为联合国机构改革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代表性的不足同样深刻地反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内,即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比例,长期无法反映它们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内的实际地位和作用。
合法性发展不平衡还源于国际社会成员对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机制运行规范的不同的利益取向。例如联合国成员内部围绕“不干涉内政”、“主权责任”、“反恐形势下的武力使用和预防性打击”、“恐怖主义界定”等问题仍存较大分歧。而随着全球化和全球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公民社会部门参与国际多边机制的需求、能力和作用同步上升,使得传统上主权国家主导国际多边机制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国家利益主导下的多边机制能否代表全球公民社会的利益,尤其是国家内部处于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越来越受到质疑。在全球层次上起始于基层公民社会的复杂而多元利益诉求开始削弱传统多边机制的合法性基础。⑨
总之,全球政治的新发展以及全球合作共治的新需求,既为未来国际多边机制的演变设定了发展方向,同时也不断凝聚新一轮国际多边机制的改革动力。
二、“中国领导”及“国际责任”的挑战上升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在改革开放30年内的迅速提升,以及全面参与当前国际体系内的各种多边机制,中国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究竟在各种国际多边机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确立怎样的身份定位,发挥怎样的作用,提供怎样的国际公共产品,已经成为国内外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领导”和“中国责任论”成为持续的国际热门话题。⑩如何平衡国际责任与自身发展战略的关系成为考验中国多边外交的新课题。
首先,国内外对中国国际责任的内涵既有一定的共识,又有不同理解,对中国在多边国际机制的作用和角色有着不同的期待和需求,从而增加了中国在多边外交上的协调难度。加之中国国内对于自己在国际体系和多边机制中的身份角色定位、利益判断、战略需要也存在认识分歧,更增加了中国平衡国际责任与自身发展战略关系的难度。
国际责任是国际社会成员为维护国际体系的正常运行所承担的成本,应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持现有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规避、分摊国际责任的趋势在加强,一方面回避西方殖民和侵略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道承担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汇率稳定、贸易平衡等国际责任。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主动承担、争取国际责任的态势也在同步强化。总体上,非西方力量的集体崛起加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国际体系的掌控能力下降,不得不由过去“排他式领导”逐步向“合作式领导”转变,强调“多伙伴合作”,增强体制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通过规范约束新兴力量,并力图在新一轮的多边机制规制制定中保持其主导地位。(11)当前国际社会热议“中国国际责任”,正是国际体系力量对比和进程不断演变的集中反映。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的要求和期待各不相同。美国希望中国能分担其霸权治理的成本,欧洲要求中国在非洲发展、人权、能源、环境领域增强与欧盟的合作,但两者都要求中国在国内民主法治建设上向西方模式靠拢。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期待中国能在国际多边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中维护它们的权益。但同时新兴发展中大国与弱小贫穷国家对中国责任的要求也存在较大差异。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一方面积极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要求中国明确表态支持;另一方面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提升中国等少数国家的投票权表示出失望和不满。部分发展中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或刻意夸大中国的国际作用和责任,或质疑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属性。凡此种种,都增加了中国在国际多边机制的改革和建设中协调各方利益的难度。
第二,“中国国际责任”的兴起是外部压力和内生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考验着中国政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政策规划和实施能力。国际社会对中国责任的讨论直接源于中国在国际体系内部地位和实力的上升,中国对于维护现有体系的稳定正起着战略性的作用。以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为例,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之一,但同时中国又是全球能源和各种原材料进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国家,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也导致了中国与许多国家的贸易纠纷不断上升。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关乎全球生态环境能否良性变化,也关系到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关系的健康与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社会体系改革速度,导致内部不和谐因素日益凸显。(12)中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经验看,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不断加快,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利益日趋多样化,今后一段时间内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13)就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而言,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加快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14)这是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和中国自身发展的共同需求,也是中国维护全球经济体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责任”。这对转型中国的机制、法制、体制改革和创新提出了新要求,形成了新压力。
第三,国际关系中行为体多元化和分散化趋势加剧了“中国责任论”的实施难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全球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日益多元和分散,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都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责任的行为主体既有传统的宏观主体(如政府),也有微观主体(如企业)。由于两者的运行机制和对两者的约束条件不同,责任的界定要求也不同,从而出现责任分化甚至责任不清的倾向,但是两者对于共同承担国际责任的目标又相互关联,彼此呼应。从中国政府的视角看,“负责任国家”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核心是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中国责任在世界经济领域具体表现为促进相互合作、优势互补,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同时,在完善和促进国际多边经济机制建设上,中国应当继续按照通行的国际规则,扩大市场准入,依法保护合作者权益,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通过磋商协作处理经贸摩擦。(15)就中国企业而言,它们一方面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主要行为者,又是中国新时期“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主体,同时在中国“走出去”战略中肩负着维护中国在海外国家形象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实现非营利性目标的社会责任加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参与到政府、非政府组织的协作或联盟中,为社会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上述发展变化要求中国企业转变经营战略,把更多的社会性目标纳入其经营核算体系内,更加深入地理解盈利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之间的紧密联系,实现“强企业”与“好企业”的相互兼容。无论从管理体制还是经营理念而言,中国企业距离此目标尚有相当距离和困难。一些研究指出,由于西方国家公司捷足先登,中国企业参与的许多项目都位于政治不稳定或缺乏有效实施环境和劳工法律的发展中国家,导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的政治、社会和环境风险加大。西方国家则经常指责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时不遵守国际劳工标准、国际环境标准和财务透明度标准等等,并与整个“中国责任”问题挂钩。因此,如何把提升企业竞争力与互利共赢理念有机结合,从而使得企业的海外经营能够促进而不是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成为新时期中国开放战略的重要课题和难点。
第四,中国面临自身的国际战略和国际责任定位的挑战,在外交战略规划和制度建设上面临着化解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中国在外交战略布局上适应新的全球政治的发展,统筹内外两个大局,在政策实施上保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平衡难度增加。新时期外交内容日益丰富,出现了经济外交、体育外交、文化外交、公共外交、学术外交等外交新形式;多边外交继续发展,呈现“多个行为体、多项议题、多重角色、多元价值”的复合特征,这些都需要中国加大在高级多边人才培养上的长远规划和机制保障,提升在国际多边外交议题上设置权能力,增强推进多边机制“软法”向“硬法”转变的主导能力。
从国内角度看,承担国际责任,提供国际公关产品的战略要求与我国多边外交目前的战略规划及实施之间存在不小差距。中国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多边战略,尚缺乏一整套指导我国参与多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利益取向、协调具体领域和地区多边外交的细则及路线图。(16)多边战略具有全局性,随着我国外交参与单位的多元乃至分散,更需要外交部门能够发挥战略指导和政策统筹的功能,确保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否则将不利于中国总体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的推行。
三、新时期中国多边外交的战略思考和政策重点
作为塑造未来国际体系的核心国家之一,中国需要构建“和平渐进、多边协商、互利共赢、尊重多样、合作共进”为内涵的新国际秩序,在此过程中丰富多边外交理论内涵,拓展多边外交的战略布局,充实中国多边外交的政策手段。
首先,中国在长期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不动摇的前提下,需要主动适应“发展中大国”的身份调整,以此来界定我们在全球和地区多边舞台不断变换发展的利益范畴、价值取向和责任边界,指导我们多边外交的目标和政策。
在可预见的未来,多元、重合的国家身份仍是我国在国际舞台上角色定位的一个突出特征。其中,长期坚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是我国外交的出发点之一。它既符合我国国家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属性和能力,又有助于界定我国家利益的基本范畴,也有助于国际社会识别并认同中国在国际力量组合中的归属,从而能为我们合理地承担国际事务中的责任和义务确立原则。同时,长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取政治、发展和安全利益,符合我国外交的核心价值。更重要的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总体处于不利地位,它们作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生力军,是我国建设性参与国际多边机制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变革的主要依靠力量。
但是,无论是中国综合国力(经济、军事实力和国际议题的规制权力)发展趋势,还是国内外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和责任的期待或者要求,都要求我们在坚持传统定位的基础上,更加自觉、主动地适应“发展中大国”,即日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调整。这种调整符合我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全球影响力扩大和国际责任增加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也适应我国新时期外交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战略原则。在兼顾我国长期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延续性同时,为我国日益扩展的利益范畴和不断提升的外交能力提供空间。总之,长期坚持作为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其核心就是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避免锋芒毕露,防止引火烧身,承担超越自身能力和利益的所谓“领导”。而主动适应“发展中大国”的定位调整,对内是为了培育国内适应发展中大国所需的大国责任意识和胸怀,提升大国外交内外统筹的机制和能力建设。对外则意味着中国在多边外交战略中需更积极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以及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改革,更加旗帜鲜明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更坚决和广泛地参与涉及我国核心及重大利益的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
其次,在战略规划和布局上统筹推进地域性和领域性多边机制的改革和塑造,把握长期目标和短期突破相结合的原则。当前阶段,抓住国际金融危机提供的特殊机遇,把提高国际金融体制应对金融国际化能力,提高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和参与权作为提升中国参与制订国际规则制定的首要领域。同时在推进与发展中大国的机制性合作中创造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和制度保障,在深化亚太地区金融、经济合作中提升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改革的能力及影响。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中的特殊阶段。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成为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内容。因此,中国在全球层面上应更主动积极倡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为突破口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增加其可利用的金融资源,扩大其发挥作用的范围。同时中国应当旗帜鲜明地强调,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的作用需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为前提,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机制等方面需要根本性的变革,包括加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相关规则的制订过程之中。
同时我们要对中国参与改革的基本态势有现实和清晰的认识。国际金融危机为二十国集团的崛起创造了机遇,但其能否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核心治理机制尚有诸多不确定性。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发达国家在现有的主要国际金融、经济组织中的主导地位仍难以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仍然存在,美元作为国际基础货币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其经济修复能力仍非常强劲。新兴市场大国尽管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但是发展阶段仍然较低,在主要世界经济领域(例如金融、贸易、科技、跨国公司等)的竞争力仍然和发达国家差距甚大。“金砖四国”峰会以及发展中五国的磋商显示发展中大国通过集体力量发挥更大作用的意图和决心,其能否成为重要的全球治理机制取决于发展中大国对该机制的战略定位,以及能否拓展它们之间在重大领域的合作,增进对外政策的协调和积累共同的战略意识。只要新兴发展中大国不能在某个经济领域享有足够的控制力,就难以推动现有主要国际金融、经济组织的根本改革。
为配合和支撑我国在全球层面参与国际金融机制乃至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加大了多边外交的力度,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地区合作战略思维。中国一直是亚洲金融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积极推动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一个根本的考虑是维护地区稳定和持续发展,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区域内其他国家。从地缘政治经济因素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立足于亚洲,保持亚洲金融环境的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同意设立区域外汇储备库,并就占总金额的32%出资份额作出承诺。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对于促进中日合作、改善中日关系来说也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亚洲区域合作的整体进程。在这种地区性的机制安排中,中国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将与中国的贡献和作用相匹配。中国在与多个亚洲国家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时,增加了人民币作为双边贸易结算货币的功能,为人民币从区域化走向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从更宏观视野看,我们应当进一步提升地区战略思维,加强地区各个领域的合作筹划。中国地区合作的重点在亚洲,应更进一步提升为“泛亚”合作。中国的跨区域合作应同领域合作更加衔接。在地区层次上,一是重点运筹好大国关系,特别是推动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包括以尊重各自核心利益为前提,以协作推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地区和全球秩序为主要动力,以承担与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为保障为主要内涵,发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不断拓展两国协调合作的全局意义。二是积极构筑小多边的大国合作框架,作为提升中国外交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它包括与新兴大国俄、印等协调合作框架,加强三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意识,建立三国战略沟通机制,发挥在欧亚大陆合作中的集体领导作用。同时,中国应着力构筑利益互惠、功能互补的亚太协调合作机制,重点是推动中、美、日三边对话机制,作为中美、中日双边关系的重要延伸,培育三方在重大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协调合作思维和习惯。三是着力从亚洲整体发展框架中提升次区域的合作,包括推进东盟+3机制一体化步伐,推进东亚、南亚、中亚等地区合作的兼容性(如东亚峰会成员的扩大)和同质性(全面发展政治、经济、人文、环境气候等合作),为最终实现亚洲区域合作机制化做好铺垫。
此外,丰富和充实新兴大国合作中的重点是在已有机制基础上加强“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在官方层面,应当规划考虑举行更加机制化、更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首脑会议、外长和财长会议等机制。在非官方方面,应大力推动建立“发展中大国智库网络”、“发展中大国金融论坛”、“发展中大国发展论坛”等。以新兴大国集体倡议的方式向世界展示我国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尽快在聚焦重点、细化任务、整合机制、根据不同任务确定核心成员等议题上形成可操作的共识。
第三,把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思想、尤其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作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多边外交的核心理念;把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对世界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作为塑造中国同世界关系的必要保障。(17)胡锦涛主席对和谐世界理念基本原则及内涵已经作出了全面和完整的概括,其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等五个领域,涵盖了中国特色的“新世界观”的原则性框架。因此需要着力思考如何通过各种多边外交的努力,丰富发展该理念。
一是要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努力打破历史目的“一元论”的主流叙述,强调多元和谐共存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从观念上看,历史目的“一元”论的宏大叙事仍然占据国际政治意识形态叙述的主流,所谓“亚伯拉罕主义”就认为历史有一种单一的本原性的目标,(18)这与我们“和谐世界”理念中强调各种本原价值多元共存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和哲学意义上的思维差异。在当前阶段,由于美国对外战略中对我倚重加强和自我约束增强,显性的对立也许暂时能够控制,但不代表这些本原价值观的矛盾不存在。“民主和平论”是西方国家或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国家的主导理念,布什政府期间,“民主强行扩张论”虽然严重受挫,但“民主和平论”内含的“国内民主体制决定对外行为”的思维根深蒂固。美国和西方坚持对我采取“融合加防范”的战略正典型地表明了西方的心态。
二是要丰富和强化和谐世界理念中“主权的责任”的内涵,从而有助于与当今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合理思想对接。和谐世界包含了对各国(主权国家)的责任要求(对外行为)的基本原则,而且隐含了对“强权和霸权政治”危害性的批评。但这一理念并没有点出当前国际安全问题存在的另一个重要挑战:国家主权的能力缺失导致的对国际社会的外部性危害。要充分认识到,国际社会对“主权责任”的认识快速接近,并对“不干涉”等问题的讨论进入更加实质性阶段。和谐世界理念应该适时地反映这一变化,在坚持“不干涉内政”的政治原则基础上,在实践中更主动积极地朝着“建设性接触和说服”的方向努力,(19)以争取在国际交往的话语体系中赢得更多的共鸣。
三是在理念构建和丰富过程中,与建立中国“核心价值”有机结合起来。当代中国应着眼于思考如何对世界历史根本进程/思想潮流作出贡献,它们包括提供我们对人类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国民信仰、体制功效、社会面貌、行为方式的思想指导和核心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间对世界主要的现代价值观,特别是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对世界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仍缺乏创造性贡献。未来之关键仍在于注重国家软实力的国内培育,确立文化自觉性,完成中华文明的新生和复兴。未来的中华文明应该是在传统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吸收世界所有其它文明的精华,并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成功实践而创造出的一种崭新文明。
注释:
①[美]布鲁斯·琼斯等:《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秦亚青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②参见联合国改革高级别名人小组2004年12月提交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享的责任》,A/59/565;安南秘书长2005年3月提交联合国的秘书长报告《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A/59/2005。
③诺贝尔经济学家、联合国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主席斯蒂格利兹认为强行推动的金融“去规制化”(imposed financial deregulation)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之一,参见Joseph E.Stiglitz,"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Global Crisis",Project Syndicate,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tiglitz111,"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Systemic Failures and Multilateral Remedies",Report by the UNCTAD Secretariat Task Force on Systemic Issues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2009,p.iii.
④Thomas G.Weiss,What's Wrong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How to Fix It,Malden,MA:Polity Press,2008,pp.107-124.
⑤陈东晓等:《联合国:新议程和新挑战》,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107-110页。
⑥[美]布鲁斯·琼斯等:《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秦亚青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⑦本文中的“全球政治兴奋/活跃”的提法参照了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全球政治觉醒”的概念,参见[美]布热津斯基:《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陈东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3-168页;另见Zbigniew Brzezinski and Brent Scowcroft,America and the World,NY:Basic Books,2008,pp229-230。
⑧参见Joseph S Nye,Jr,"Globalization's Democratic Deficit:How to Mak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ore Accountabl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2001.
⑨关于新多边主义与传统多边机制的互动与矛盾,可参见Robert Cox (ed.),The New Realism: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St.Martin's Press/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1997。
⑩例如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September 21,2005,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Commission of European Union,"EU-China:Closer Partner,Growing Responsibilities",Oct.24,2006。
(11)美国奥巴马总统上台后,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为首的外交团队大力倡导“多伙伴合作”理念,见希拉里2009年7月15日在美国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上的演讲,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july/126071.htm:同时参见李杰:“从责任论透视国际体系转型”,《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第36-37页。
(12)阎学通:“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政策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15页。
(13)“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第1版。
(14)“把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四论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精神”,《人民日报》(网络版),2008年12月24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GB/40604/8568109.html。
(1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48页。
(16)王逸舟教授在论述中国外交与提供国际公关产品关系时提出要处理好“大与小”、“远与近”、“破与立”三对关系。见王逸舟:《中国外交新高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9-64页。
(17)2009年7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强调,要不断提高中国外交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7/20/content_11740850_1.htm。
(18)Walter Russell Mead,God and Gold:Britain and Americ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NY:Alfred A.Knopf,2008,pp271-296.
(19)关于“建设性接触和说服”概念,请参见陈东晓等:《建设合作共进的新亚洲:面向2020年的中国亚洲战略》,2008年10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出版。
标签:多边外交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全球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际金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