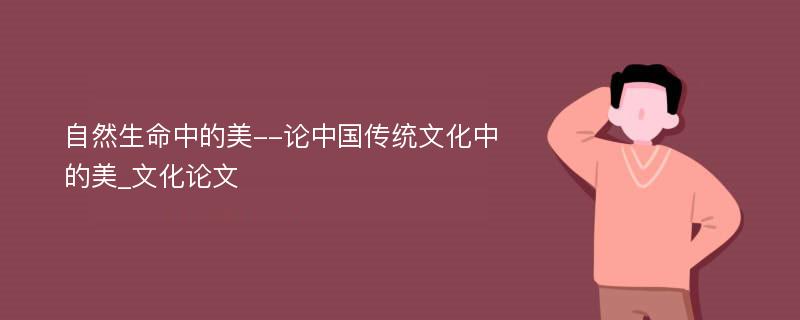
美在自然生命——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美的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美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自然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学思想是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因而不同的民族、乃至不同的时代,只要具有不同质的文化,就会对美有不同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美是什么就有自己特殊的理解。
庄子认为,宇宙生命就是最高的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这是他的名言。“大美”者,真美与至美也。《田子方》那段“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的描述,是他“游心于物之初”、即心游天地之所见所得。有曰“请问游是”,他便回答:“夫得是,至美至乐也。”他还说,天道虽“视乎冥冥,听乎无声”,但“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天地》)就是说在深邃浩淼的大化流行之中,仿佛可以看见鲜明的形象,仿佛可以听到和谐的乐声。王夫之尝云:“诗者,幽明之际者也。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抟而不可得之象。霏微蜿蜒,漠而灵,虚而实。”(《诗广传·卷五》)在庄子的心目中,宇宙生命就是这样的诗。《乐记》论乐,是这样说的:“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乐礼》)这段话,前面完全是复述《周易》,讲天地如何化生万物;最后却突然提出“乐者,天地之和也”。其间的联系,只有简单的两个字:“如此”。在《乐记》的作者看来,似乎天地化生万物当然就是最高的美,故当然就是音乐的本原,这是不需要解释的自明之理。庄子与《乐记》的这些言论是否表明:对于美与文艺,或曰无论自然之美还是文艺之美,中国古代都是从宇宙生命出发去理解的?
一、和
中国古代以“和”为美,此人所共知而共言也。但尚需再思再言的是:中国古代何以会以“和”为美?或者说“和”在中国古代何以会成为美?这就涉及“和”与“生”的关系了。
且看那些较早地提倡“和”的言论。史伯认为,周朝之弊,乃因于周幽王喜同而恶异,亲小人而远贤臣。他以“生物”比拟政事,认为不同事物的结合谓之“和”,同类事物的会聚谓之“同”;只有不同事物的结合,才能使万物生长,万事兴旺;若以同类事物相补凑,则物尽事败,国将以亡。总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可见“和”之可贵,即在于“生物”。伶州鸠论乐与政,谓“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平”指每音之合律适中,即所谓“细大不逾”;“和”指众音之协调相应,即所谓“声应相保”。每音适中,众音始和,故谓“和从平”。他认为这样的音乐可使天下风气顺畅(“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国语·周语下》)“嘉生繁祉”,言美好的生物得以繁殖而造福。“物备而乐成”,言物产丰盛而音乐始收到应有的功效。音乐之和呼应着天地阴阳之和,使万物生长,人民富足。“和”之义,仍在于“生物”也。“和”不仅关系着物之生,而且关系着人之生。如下面两段话:“伶州鸠曰……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窈,大者不袴,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亿,安也)则乐。窈则不咸,袴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单穆公曰……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国语·周语下》)第一段,“小者不窈,大者不袴”指乐器与乐音,乐器不过小过大而适度,乐音则不过弱过强而适中。乐音适中也属于“和”的范畴,前引“和从平”即此意。这段话就在“和于物”之后又着重指出,“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可使人安适而快乐;反之,若乐音过弱或过强,则会使人听不清(“不咸”)或难承受(“不容”),导致感而生疾。第二段更进而从生理过渡到思想、政治,认为“听和而视正”则耳聪目明,耳聪目明则能闻善言、见美德,闻善言、见美德则可使思想纯正而坚定,使人民诚服而归心;反之,若声、色过强而失和,就会使人耳失聪而目失明,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患莫甚焉”。在宇宙统一的生命大家庭中,物与人、身与心、乃至自然与社会,原是一“生”之所贯穿;“和实生物”,当然“和”也就可以“生”人。
“和实生物”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观念。故言“生”者多以“和”为“生”之前提。如庄子之所谓“合则成体”,荀子之所谓“天地合而万物生”。而言“和”者亦多以“生”为“和”之结果。如《乐记》云:“和,故百物不失。”“和,故百物皆化。”《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观念在《周易》中有十分突出的表现。如前引《系辞下》曰:“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又如《说卦》云:“水火相逮(相及、相合),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除《易传》的这些论述外,“和”还是《周易》判断吉凶的一项重要标准。“和实生物”,“生物”则吉。故大致而言,《周易》诸卦,凡体现“和”者,多涵吉意;而凡体现“分”或“同”者,多涵凶意。
“和”实“生”人的思想也得到了后人的发展。秦代《吕氏春秋》本伶州鸠“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及单穆公“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的言论,继云:“夫音亦有适。太巨则志荡,以荡听巨则耳不容,耳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太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不詹则窈。太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溪极,溪极则不鉴,不鉴则竭。太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耳不收,不收则不抟,不抟则怒。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仲夏纪·适音》)“心必和平然后乐。”(同上)“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同上《大乐》)根据人的生理与心理反应,把音之平和适度概括为“适”,又称“心必和平然后乐”,这就把“和”同人心之“适”与“乐”联系起来了。至明代袁宏道,又从《吕氏春秋》“声出于和,和出于适”的说法出发,而摆脱了道德、政治的牵扯,把“和”完全落实到了生命的欢乐。袁氏著文《和者乐之所由生》,纯粹以性情论乐,认为乐之产生,乃“本人心自有之和”;乐之目的,乃“用以宣天地之郁,而适万物之情”;而“和者,人心畅适之一念”尔。“和”就是人心与万物的“畅适”,就是个体生命的欢乐。
可以说,“和”之一字,无往而不与生命相关。它是生命诞生的根本前提,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生命全体的共存共荣。盖“和”者,生之本也;有“和”则有生,无“和”则无生。故贵“和”者,贵生也;爱“和”者,爱生也。知“和”之为美而不知“和”之何以为美,可谓造其门而不入者也。
二、文
《易传》曰:“物相杂,故曰文。”(《系辞下》)《说文》注:“错画也,象交文。”(《卷九上》)“文”的一个基本涵义,就是交错的线条。《文心雕龙》复曰:“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声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情采》)这就又将“文”扩展为多样而统一、变化而有序的形式,美术、音乐、文学等诸般文艺无所不包了。那么,这多样而统一、变化而有序的形式又是怎样产生的?在古人看来,文产生于宇宙生命,文是生命的表现形式。
古人论画,皆以造化生物为本。或云“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唐·王维《山水诀》),或云“凡赋形出象,发于生意,得之自然”(宋·董卣《广川画跋》)。不仅人物动植物等有生命者,须捕捉其活动的生命情态,所谓“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即山水云石等今人以为无生命者,亦“非以按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描摹外形而已,仍须“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使“孤岩郁秀,若吐云兮。横变纵化,故动生焉”(南朝宋·王微《叙画》),表现出它们作为宇宙生命的产物所具有的那种气象万千的生命精神。至清中叶郑板桥犹云:“古之善画者,大都以造物为师。天之所生,即吾之所画,总须一块元气团结而成。”(《题兰竹石二十七则》)“一块元气”者,宇宙生命也。这可以说是中国画论的总结。
书法依于文字。而古以为文字始于八卦,八卦乃概括天地众生的形象符号,故文字亦如此,书法亦如此。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论文字之始,即从庖牺作八卦说到仓颉之造书,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沆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后人亦据此论书法。如唐代张怀谓:“昔庖牺氏画卦以立象,轩辕氏造字以设教”,“春秋则寒暑之滥觞,爻画乃文字之兆朕。”(《书断》)元代刘有定谓:“天地之理,其妙在图书(指河图洛书)。圣人法天,其用在八卦。六书,八卦之变也。”(《衍极》注)因而《易传》的下面这段话:“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虽非以论书法,却可以说是一篇书法指南。仰观、俯察、近取、远取,即取法天地人物等宇宙万有。“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即体现生化无穷的宇宙生机和千姿百态的生命情状。这种取法天地、体现众生的思想,就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本质。
论书之作,云:“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隋·虞世南《笔髓论》)“至哉!圣人之造书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盈虚消长之理,奇雄雅异之观,静而思之,漠然无朕;散而观之,万物纷错。书之义大矣哉!自秦以来,知书者不少,知造书之妙者为独少;无他,有师法之不传也。”(《元·郑杓《衍极·造书》)
论书之势,云:“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立矣。”(东汉·蔡邕《九势》)“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举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婀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字势》)
论书之形,云:“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蔡邕《笔论》)
论书之体,云:“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苏轼《论书》)“筋、骨、血、肉、精、神、气、脉,八者全具,而后可为人,书亦犹是。”(清·翁方刚《竹云题跋·卷三·欧阳率更醴泉铭》)
至于书法鉴赏,更每每以人与物的生命情态为比拟。如“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均见宋·袁昂《古今书评》)之类,可谓不胜枚举。生命,抽象而鲜活的生命,跃然纸上、迎面扑来的生命,这就是观赏书法之所得,也就是书法艺术之精髓。
“乐者,天地之和”的说法,已经把音乐同宇宙生命联在了一起。前引论“和”之语,即多为论乐。古人云:“昔者,伏羲氏既画八卦,又制雅琴。卦所以推天地之象,琴所以考天地之声也。”(宋·朱长文《琴史·莹律》)传说古琴出于伏羲时。此虽言琴,实亦论乐。如此,则同雅琴相连的音乐,就获得了与同八卦相连的书法一样的资格,即体现宇宙生命;不过后者推其象,前者考其声而已。音乐如何“考天地之声”?古以为,音乐作为声音的律动,体现着宇宙生机的律动。天地之气,动而生风;而“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汉《淮南子·主术训》)。每月风不同,律亦异,故有十二律以应十二月。所谓“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吕氏春秋·季夏纪》)“吹葭飞灰”以测节气的习俗,就生动地反映了这样的观念。据载:将苇膜烧成灰,放在律管内,到某一节气,相应律管内的灰就会自行飞出。此“律”之所以通于“历”,古昔往往合而言之曰“历律”也。有云:“圣人之制律也,其用通之于历,历有定数,律有定声。”(清·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一》)既然音乐体现着宇宙生机的律动,那么反过来,音乐也就具有了应天开物、赞育群生的意义。《国语·晋语》云:“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乐记·乐礼》云:“圣人作乐以应天”。此即所谓“候气”与“召气”也。“乐律可以候气,可以召气。气已至而律辨之,主其候者也。气未至而律迎之,主其召者也。武王伐纣,吹律听声,自孟春至季秋,役气相并;师旷吹律,而知南风不竞,多死声;此非用律以候气乎?幽谷无黍,邹子吹律暖之;师旷清角,而悲风急雨骤至;此非用律以召气乎?”(明·庄元臣《叔且子·内篇卷三》)
于此亦可知,这“候气”、“召气”的“气”,并不仅限于自然界的气节之气,还包括人世的治乱兴衰之气。在宇宙统一的生命大家庭中,这原是一“气”贯穿的。西晋阮籍的《乐论》,对上述音乐观念有一个全面的理论概括:“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气。故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欢,九州一其节,奏之圜丘而天神下,奏之方泽而地祉上,天地合其德,则万物合其生,刑赏不用而民自安矣。”乐乃“天地之体,万物之性”,即宇宙之生机,万物之生命。作乐乃“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即一方面顺应宇宙生机之律动,一方面赞育天下万有之生长,直至国泰民安,神人以和。总之,音乐就是宇宙生命的声音对应物。
诗文亦然。有曰:“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清·黄宗羲《斜皋羽年谱游录注序》)“夫诗本天地元音,有定而无定,到恰好处,自成音节,此中微妙,口不能言。”(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四》)这都是说,诗文禀赋着天地的自然生机。还有更为形象的说法:“圣人文章自深,与学为文者不同。……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为之者,或有绘画为之者,看之虽似相类,然终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宋·程颐《二程遗书·卷十八》)“文要得神气。且试看死人活人,生花剪花,活鸡木鸡,若何形状,若何神气。”(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文》)“诗有造物。……造物之妙,悟者得之。譬诸产一婴儿,形体虽具,不可无啼声也。”(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或如“生花”,或如“活鸡”,或如呱呱坠地的婴儿,一句话,诗文也要象活物,也要有生命。但诗文的生命是指什么?书、画有形,音乐有声,固此类“形文”、“声文”尚可仿象万物,呈现众生;而诗文乃语言艺术,其直接呈现的只是书面语言,而不是物。当然,诗文可言志抒情,故应表现出作者的精神生命;诗文亦需以言状物,故亦应体现出物的生命。但古人之强调生命,并不是就作品所写的具体内容而言,而是就作品的整体、作品之作为一物而言。因而他们所强调的生命不是具体的人或物的生命,而是一种抽象的、超越性的生命,一种只能以心感知、而不能目视耳听的生命,只能说是一种生机、生气、生命活力,或曰生命精神,或简称为“生意”。而这一点,也许更能反映中国古代的以“生”为宇宙本体的生命意识,因为“盎然宇宙之中,浑是一团生意”。其实,即使是“形文”、“声文”,中国古代所追求的,主要也不是具体的“生物”,而是这种“生意”。
对于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戏曲小说,中国古代也是这样看的。试举一例。明代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写道:“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即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古执也,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如此等人,皆若士元空中增减朽塑,而以毫风吹气生活之者也。”“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即从其生命内部把握其种种生动的情态。而这些人物的生命,又都是汤显祖所赋予的。评论之精,几令今人千言万语都成秽物。而所论之旨,即在创造人物的生命。
总之,无论天文、人文,亦无论绘画、书法、音乐、诗文,以及戏曲小说,诸般文与文艺无不被视为生命的显现。若谓“和”为生之本,则“文”乃生之象也。
三、神
古人衡文,讲究“神”、“气”、“韵”,以及由这三个词两两组合而成的“神气”、“神韵”、“气韵”。
“神”、“神气”、“神韵”:——“作画形易而神难。形者,其形体也。神者,其神采也。凡人之形体,学画者往往皆能;至于神采,自非胸中过人,有不能为者。”(宋·袁文《翁牖闲评》)“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南朝齐·王僧虔《笔意赞》)“晋明帝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亦有齐观。”(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顾骏之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微谨细,有过往哲。”(同上)“矜持于句格,则面目可憎;架叠于篇章,则神韵都绝。”(明·胡应麟《诗薮》)
“气”、“气韵”:——“虽不该备形妙,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谢赫《古画品录》)“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五代·荆浩《笔法记》)“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
“韵”:——“葫芦依样不胜揩,能如造化掘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明·徐渭《画百花卷与史生》)“今人见画,不谙先观其韵,往往以形似求之。此画工鉴耳,非古人意趣。岂可同日语哉?”(明·俞弁《逸老堂诗话》)
这些不同的概念,却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就是与“形”相对。上述诸例就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所有这些概念都是在与“形”相对的意义上被使用、被强调的。因而它们之间也往往可以互训,如:“谓虽曰画而非画者,盖只能传其形不能传其神也。故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宋·邓椿《画继·卷九》)“论画之高下者,有传形,有传神。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元·杨维桢《图画宝鉴序》)可知“神”即“气韵”,“气韵”即“神”。在这种与“形”相对的意义上,也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个范畴。故这些概念,分而言之,涵义各别;合而言之,可通谓之“神”。
关于“神”,《庄子·德充符》有曰:一群小猪在刚死的母猪身上吃奶,一会儿都惊慌地抛开母猪逃走了,因为它们发现母猪已经死了。可见“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就是指支配“形”的“神”。在这里,“神”就是生命,就是使形体活着的生命。有“神”则生,无“神”即死。故庄子谓:“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在宥》)。施之文艺,东晋顾恺之云:“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趣失矣。”(《论画》)把绘画视为“以形写神”,又以“传神”与“荃生”并举,则“传神”亦即“荃生”,“神”即“生”也。明代徐渭又云:“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题画梅》)“东风吹着便成春”者,乃活树,具有内在之生命者也。
关于“气”,实际上前文已论及。阴阳,即气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所以生物者也。“气”乃宇宙产生万物的动力,因而也具有生命的意义。故庄子谓:“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清人王夫之亦谓:“气者,生气也,即嗥天之和气也。”(《庄子解·人间世》)施于文艺,如郑板桥“总须一块元气团结而成”,王思任“以毫风吹气生活之者也”,董其昌“文要得神气”,等等,皆是指内在的生命活力。那么“气”与“神”有何区别?《淮南子·原道训》云:“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充”即充沛,指生命活力。“制”即“使”,即统摄。就是说,“形”、“气”、“神”是凝成具体的生命物的三种要素,而“形”只是生命的居舍,“气”是生命的活力,“神”是生命的灵魂。因而,“形”是外在的,虽亦为生命物所不可缺少,却还不是生命本身,生命本身是“气”与“神”;而“气”与“神”虽然都是内在的生命,但气作为生命的活力仍较为显露而实在,而“神”作为生命的灵魂则更为幽隐而虚灵。
关于“韵”,徐渭“不求形似求生韵”的话,已经表明了它与生命的联系,“生韵”就是某种生命情趣,或生命情调。但“韵”与“气”和“神”都有微妙的区别。有人把它同“气”作了如下的比较:“文章之无气,虽知视听言动,而血气不充于内,手足不卫于外,若奄奄病人,支离憔悴,生意消削。文章之无韵,譬之壮夫,其躯干枵然,骨强气盛,而神色昏瞢,言动凡浊,则庸俗鄙人而已。”(宋·王正德《余师录》)据此,则“气”似强盛的体魄,“韵”如清雅的神情;“气”偏于壮而“韵”偏于婉。的确,古之言“气”者,多与“壮”或“力”相联,前引诸例即有。金人元好问诗曰:“邺下曹刘气仅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自题中州集后》)亦足为证。因而,“韵”亦较为幽微。“有余意之谓韵。……尝闻之撞钟,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宛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也。”(宋·范温《潜溪诗眼》)“画家之妙,全在烟云变灭中。……山水中当著意生云,不可用拘染,当以墨渍出,令如气蒸,冉冉欲堕,乃可称生动之韵。”(明·莫是龙《画说》)这就接近于“神”了。但谓之“余音复来,悠扬宛转”,谓之“令如气蒸,冉冉欲堕”,究意还是一种似有若无的存在,不象“神”那样虚。再参之以“韵者,生动之趣”(明·李日华《六砚斋笔记》)、“韵者,态度风致也”(清·方东澍《昭昧詹言》)之类的说法,这点区别就更明显了。正因为与“气”和“神”有这样的区别,“韵”就更具有了美的意义。壮“气”须加上一点含蓄,虚“神”须带上一点风仪,才成为美;而“韵”可以说就是含蓄的风仪。所以“气”和“神”都同时、甚至首先是哲学概念,而“韵”则是个纯粹的美学概念。
可见,在与“形”相对的意义上,“神”、“气”、“韵”都是指内在的生命精神。施之于文艺,当然都是通过形象焕发出来的生命精神。不过仔细分辨起来,“神”泛指各种生命精神,亦偏于最为内在的生命之魂;“气”较为显露,偏于生命之力,指豪壮的生命精神;“韵”在显隐方面处于二者之间,偏于生命之美,指温婉的生命精神。
还有个涵义似更为宽泛的概念,曰“意”。说到“意”,人们往往仅理解为一般之所谓意思、内容。而其实,它与“神”、“气”、“韵”一样,也是同生命联系着的。这样的例证很多。如:
“古来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欧阳修《盘车图》)
“清苑田景延善写真,不唯极其形似,并与东坡所谓意思,朱文公所谓风神气韵之天者而得之。夫画,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与天者,必至于形似之极,而后可以心会焉。”(元·刘因《田景延写诗序》)
“画虽状形,主乎意;意不足谓之非形可也。虽然,意在形,舍形何所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于形;失其形者,形乎哉!”(明·王履《华山图序》)
在这些言论里,“意”与“形”相对,而与“风神气韵”相联,其内在生命之意义极为明显。此亦可见,中国传统文论之所谓“写意”与“传神”,虽概念为二,而实质则一也。再举一例。《列子·说符》载——
伯乐年长,秦穆公问他后代中有无可以继承其相马之才者,“伯乐对曰:‘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弭辙。臣之子皆不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马也。’于是推荐了九方皋。穆公使行,三月而得。穆公问:‘何马也?’九方皋答:‘牝而黄。’使人往视之,乃‘牡而骊(黑)’。穆公谓伯乐曰:‘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伤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叹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胜臣千万而不可量)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所谓“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就是超其形而得其神,专注其内在的生命活力、生命精神。因而,这个本与文艺毫不相干的故事,后来却成了文艺创作的楷模。宋人陈与义就此写了两句著名的咏画诗:“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说的正是“意足”。“意足”者,生命精神之充盈饱满也。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意”,在很多情况下是指“生意”,而不是一般所谓意思、内容。
实际上,“生意”一词,已屡见于前面的引文中。如罗汝芳:“盎然宇宙之中,浑是一团生意”。程颐:“终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董卣:“凡赋形出象,发于生意”。
且不仅“意”为“生意”,即“神”、“气”、“韵”以及“神气”、“神韵”、“气韵”,何者而非“生意”?内在的生命精神,或曰生命意蕴,或简称为“生意”,就是这些中国古代用以衡文的主要概念的基本涵义。
四、美与生
“和”者生之本,亦美之本;“文”者生之象,亦美之象;“神”者生之意,亦美之意。这样,美就相当全面地被归结于生命,被归结于通天人、合物我的自然生命了。
关于美是什么的问题,古希腊人从他们的文化思想出发,强调形式。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柏拉图的“理式”,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作为构造万物的模式,既是世界的本质,也被视为美的本质。虽然这些概念往往具有形而上的涵义,但毕竟还是形式。毕达哥拉斯学派作为美的规律提出的“黄金分割律”,可以说是他们的一项美学代表作。而且按照西方美学的基本思路,美是非实用、超功利的,既然是非实用、超功利的,就与物的质料无关,那么美之为美,也就只在于物的形式了。所以就基本倾向而言,西方美学是重形式的。
而中国古代则更强调生命,更强调内在的生命情韵。因此,中国古代也不象亚里士多德那样,把事物分析为“质料”与“形式”两方面,而是一般区分为“形”与“神”。“形”指外在的形体,“神”指内在的生命。而“质”是被视为形体,并入“形”之中的。如王夫之谓:“物生而形形焉,形者质也。”(《尚书引义·毕命》)宋范成大诗云:“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四时田园杂兴》)“鬼质”即指采菱人的枯瘦如鬼的形体。故论文艺亦往往“形”、“质”并列,而与“神彩”、“情性”相对。如前引王僧虔所谓“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形质次之”,清包世臣所谓“书之形体如人之五官四体,书之情性如人之作止语默”(《答熙载九问》)。有“形”而无“神”的死物,在中国古代看来是断然不美的。
西方人的观点自有其不可低估的正确性。但如果审美是人的确实存在的心灵需要和心灵体验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说:只有生命才能感召生命,只有生命才能抚慰生命。不仅那深邃的审美意蕴可以满足人的精神生命的渴求,即使那纯粹的审美形式也是因为它应和了人的生理生命的律动,才被感受为美的。有的西方人后来也认识到:“死人的脸庞和活人的脸庞,就物质的对称性来说还没有变形,然而活人的脸庞上却闪耀着美的光,死人的脸庞上只有一点美的痕迹。还有,比较栩栩如生的雕像即使没有别的雕像对称,也仍然要比别的雕像更美一些。”(普罗提诺《九章集》)世界把生命意识赋于了人类,人类又以自己的生命意识感应着世界。“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陶渊明《读山海经》)就在这生命与生命的交流中,人体验到了诗意的栖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