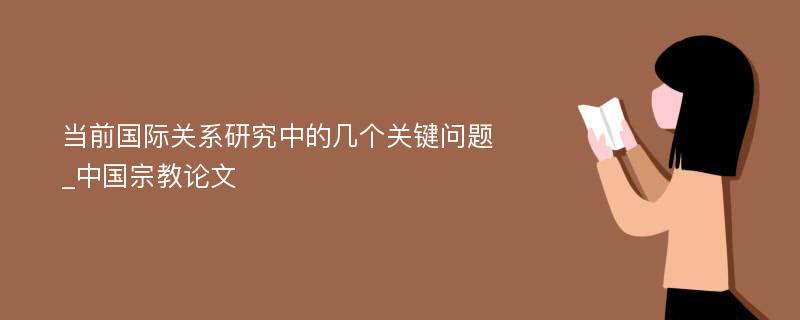
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重点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重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再来北大,专门参加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建院5 周年及她的前身国际政治系建立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在研究工作特别是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上,做到“不惑”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今天不想对国际关系做详细介绍,因为大家对此都很熟悉。我只想提出一些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供大家思考。当前我们所处的世界日新月异,变化非常快。要跟上这个形势的发展,有自己深刻的理解、认识,作出正确的判断,确实是不容易的。搞外交也好,搞国际问题研究也好,都要考虑到这种不断变化的形势。
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做研究工作的同志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个方面,现在是信息社会。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数量和它的覆盖面,比过去是大得多了。古人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那时候说这个话有些不切实际,有些吹牛。但现在,如果我们多加注意,完全可以同步跟踪天下大事,及时地掌握形势,这一点并不夸大。甚至可以说,现在人们遇到的问题经常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真实的信息、被歪曲的信息,以及各种误传、误导都会有。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对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反而增加了困难:不是材料少了,而是材料太多。新的形势对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们能够作出快速反应。要很快地了解情况、很快进行研究并得出应有的结论,及时作出反应。由于处在信息社会,任何事件发生以后的第一时间内,公众都能够得到大量的有关信息。所以做研究工作、外交工作的同志,如果反应迟钝,就很可能会陷入被动。另外,现在的整个信息是开放的,所以对外事务的社会性也增强了。也就是说,在信息时代客观上人人都可参与,外交的事情和内政交叉在一起。所以我们作出各种判断、反应时,不仅要考虑到国外的反应,也要考虑到国内的反应。换句话讲,我们的外交行动也要能够得到国内广大公众的支持。不仅仅要考虑能否在国际上得分,而且也要考虑是否能在国内得分。当然外交是国家的行为,有许多暂时不能公开的内部活动需要保密。但是能公开的就必须让人了解。现在有人提问时,我们经常回答说无可奉告。这也是个办法,但从根本上来讲,现在“无可奉告”不能解决问题了。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上,现在标准要大大提高。研究要有材料,但正如我刚才谈到过的那样,如果说过去信息匮乏,没有办法进行研究,现在则是信息爆炸,材料非常的多。这就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抓住要害。就要求我们研究工作人员具有真正的高水平、高素质。特别是要看到信息中也有各种假新闻、假材料,对人会起到一种误导、诱导的作用。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制造谣言。现在就有专门制造谣言的报刊和信息来源。过去说“谣言可以杀人”:它虽没有直接杀人,但是如果谣言多了,就可以起这个作用。德国法西斯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可以成为真理”。你不相信吗?但为什么人人都在说。说到最后曾参的母亲也会相信她儿子杀了人。所以我们要借助信息来了解情况,但对信息又需要分析。实际上现在信息也还是有垄断的:虽然表面上是自由地发布、自由地接受的,但终究是谁的钱多,谁就有更大的能力来发布自己的信息。它整合了发布的网络,当然它的发言权就大,声音就高,听到的人多,它的影响就大,所以信息也有霸权。美国现在对比尔·盖茨起诉,说他垄断,这是从技术上来讲。但人们为什么不注意到信息的内容也可以垄断这一事实呢?只要能快,能先入为主,能做到铺天盖地,就会形成一种巨大可怕的力量。大家开始会有些怀疑,慢慢地也就人云亦云了。这就是潜移默化,就是主导媒体、塑造舆论,就是渗透、影响,就是抢占先机。所以谈到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当前的外交,我觉得信息社会这一点是当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方面是经济的全球化。目前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冲击,对世界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冲击。对此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考察:首先,跨国公司、跨国企业的运行超越了国界,跨国公司的总产值现在已经大体上占到了世界总产值的40%。而境外投资的90%、内外贸易的60%也是由跨国公司来进行的。这个新情况说明跨国公司的运作、经营超越了国界。其次,世界市场的容量和范围比以前有空前的扩大。如果20年前每天的世界外汇交易量大概是100亿美元的话, 那么现在每天是15000亿美元。1970年时, 全球的出口量大约占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4%,现在则达到了24%。所以可以看到在世界的范围内,不管是进出口贸易的市场还是外汇交易的市场、投资的市场都大大地扩大了。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对经济信息资源的推动更为资本和货物在全球的流动创造了条件。另外,经济运作的规则,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许多规范,都趋向于统一。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也使得整个世界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应该说美国率先进入了新经济,它现在在世界经济中明显地处于一种主导的、领先的地位。美国的经济有109个月或者说110个月一直维持着景气的状态,这大体上就是10年。与此同时,欧洲、日本也在加速内部调整,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来争夺新兴市场。一些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也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但是在这个进程中有不少的发展中国家落在了后面,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使他们的国家面临边缘化的危险。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而这种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也会导致政治的不平衡发展,使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受到冲击。
第三个方面是宗教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冷战后,宗教、民族问题突出起来。许多热点问题差不多都与宗教、民族问题分不开。我认为宗教、民族问题并不是新问题,是古已有之的,只是在当前又热起来了。有人这样分析:历史上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在中世纪,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大力向外传播,经常发动圣战;然后基督教组织十字军东征,从欧洲一直打到西亚。这次高潮持续了很长时间,造成了国家间关系的动荡与战乱。第二次高潮是近代亚非国家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借助本土国教反抗传教的殖民主义者。而现在是第三次。波黑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斗争;科索沃危机的起源是东正教的塞族和穆斯林阿族的斗争。其他如车臣问题、东帝汶问题、斯里兰卡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内战、中东问题、北爱尔兰问题等等的冲突都和宗教背景有关。所以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将来世界上注定会发生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三大宗教、三大文明的冲突。当然,我们难以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宗教问题也好,文明不同也好,如果处理得法是可以妥善解决的。但是无论如何现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宗教经常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二是宗教自由经常与人权联系在一起;三是宗教经常与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四是宗教经常与国家的政局、民族的分裂或统一联系在一起;五是宗教的认同往往跨越了国界和民族的界限。这种跨越国界、民族的感情有时起的作用会相当大。宗教的影响是各方面的,我们看到印度教徒会反对美国在印度搞麦当劳快餐店。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国际关系中,当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宗教的矛盾、民族的矛盾往往使得原来得到控制的、得到处理的、得到解决的问题重新爆发,宗教、民族问题会突然变得重要、敏感起来。但宗教问题就像潘多拉盒子,打开容易,关上很难,没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办不到。再加上有的国家以宗教自由、人权等为口号干涉别国内政,也使矛盾更加激化。经济的贫困、政局的不稳也可以成为宗教矛盾的温床。应该说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然现象,现在经常讲2000年到来了,世界新的第三个千年开始了,这就是从宗教概念上说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当然不止两千年,要长得多。人类的一切事物都会变化,都要经历发生、生长、扩展一直到灭亡这个过程。但是相对于国家来讲,宗教的历史应该说是更长的。所以宗教问题是我们必须注意研究的一个问题。最近教皇对罗马教会两千年间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忏悔,请上帝宽恕。他说罗马教会犯了七大罪状:第一是强迫教徒忏悔;第二是十字军东征并设立宗教裁判所;第三是导致基督教的分裂;第四是敌视犹太教;第五是强行传教;第六是歧视妇女;第七是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教皇承认这七大错误并进行忏悔,这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他并没有提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宗教所起的帮凶作用。他也没有提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主办教会,选出来的神父、主教请梵蒂冈认可,梵蒂冈采取的态度是罚绝,绝对不承认而且还要处罚,处罚到断绝关系。这是梵蒂冈的一个错误,但他们没有提到这一点。当然罗马教会可能不止犯了这些错误,还有其他错误。实际上教皇承认错误的目的是希望保持基督教的统一,加强梵蒂冈的地位。
第四个方面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权问题以及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主权是与国家的出现同时产生的,互相尊重主权和主权平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当代世界史中,主权原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联合国时制定的一项基本的国际关系原则。不能认为因为重视人权,这个原则就过时了,就不需要继续坚持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倾向。这次联合国召开千年首脑会议,肯定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人权是主要的,国家主权是次要的。应该首先尊重人权,可以不顾国家主权。但如果整个世界都这样做,联合国也这样做的话,那就会天下大乱。联合国的基础就是180多个主权的国家都是平等的成员。 她有宪章,她不能不制定国家之间关系的确定准则,这是天经地义的。当然你可以谈人权问题,可以谈安全问题及其他问题。但是联合国成立的初衷,她的宗旨、章程,她所制定的一些准则,都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的总结。应该说没有这些,就没有二战后半个世纪的和平。
谈到人权高于其他原则的问题,我们可以举些例子。首先是科索沃问题,这是以人道主义为名使用武力,结果造成了“人道主义的灾难”,至今没有解决问题。现在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反思。其次是国际贸易问题。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是正常的,世界贸易组织通过一些规定,大家按照这些规定来进行贸易,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也在积极要求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美国众议院刚刚通过了的并不是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案,因为这件事不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首肯。刚刚通过的是取消在正常贸易关系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限制。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正常贸易关系一开始叫做最惠国待遇。但实际上这个最惠国待遇并不是一种恩惠。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为进口商品制订的税率应适应于所有国家,不能为不同的国家制定出不同的章程,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税率。那么怎么会出来一个给不给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呢?这个问题的起源是美国国会70年代通过的一项法律,杰克逊·瓦尼克(Jackson—Vanik)法。这个法律最初的目标是苏联,他们要求苏联允许犹太居民自由移民离开苏联,否则美国就不给你最惠国待遇,即可以在贸易中采取歧视措施。那么这个问题怎么会用到中国来了呢?中国没有犹太居民,当然也没有犹太人移民的问题。这就是这项法律的引申:凡是美国不愿意给予正常待遇的国家,他就说你适用于这条法律,就每年审议。中美是1979年建交的,当时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因为中美贸易很少,中美关系较好。后来贸易量越来越大,中美关系方面出现了些摩擦,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美国政府每年总需要向国会提出准备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以一年为限,要求国会审议。通过了就给一年,不通过就不给。实际上每年都能通过,但每年都要有一番争斗。有人主张给,有人主张不给,多年来是每年吵架一次,每年都能通过。克林顿总统执政以后继续这个方针,每年搞一次,每年吵一次,每年都能通过。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正常贸易关系,有两点是中美之间有分歧的。第一个是最惠国待遇的名称,我们说这不是最惠国待遇,中国也不要求什么“最惠”,我们只是要求正常。既然中美间有贸易协定,那么贸易就应该正常。最后,用了七八年时间终于把这个最惠国待遇改名了,原来叫MFN,现在叫NTR。第二个我们主张每年审议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正常贸易关系的。所以这次作出了决定要给中国PNTR,就是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在我们看这本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实际上却费了很大劲。应该承认,克林顿总统做了很大努力,把它作为卸任之前最大的外交目标。从另一方面看,美国也是自找麻烦。搞了这么个东西是完全不在理的,要取消它还挺困难,还得做各种各样的动员。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把什么问题都和人权联系起来有很大的危险性。要做贸易还要看你人权怎么样,你这里有犹太人要看你是不是放他们出国。你这里没有犹太人,就要看看别的方面做得怎么样。没有这个问题,还有别的问题,总之可以找出问题来,说我不能和你做贸易。但不做贸易又赚不了钱,所以还要做。然后一年审议一次,每年我给你找点儿麻烦,实际上是他们自找麻烦。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现在费了很大的劲,通过了PNTR,但又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审议中国的人权状况,但又不作为条件,审议归审议,贸易还是照做。这又是新的自找麻烦,类似这样的问题以后还少不了,但是越来越不得人心。
下面谈谈台湾问题。从3月18 日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大选中当选到5月20日他发表施政演说整整是两个月。现在台湾的局势究竟如何? 应该说民进党人上台使台湾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也使两岸关系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从投票的结果来看,39%的人选了民进党的陈水扁,60%的人没有投他的票。这后一部分人又分为两派,就是国民党候选人的支持者和从国民党分离出来的候选人的支持者,这两部分人加起来投票率是60%。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没有达到半数票的候选人当选为总统。对前一部分选票还应作进一步的分析:民进党在纲领中是明确地提出要搞台独的,但在39%支持陈水扁的选民中,支持这个纲领的大概不过半数。还有半数陈水扁的选民投的票是要反对国民党的“黑金政治”即腐败。在3月18日到5月20日这两个月之间,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再次宣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从台湾岛内来讲,社会各界也都期待打破僵局,改善两岸的关系。工商界更希望进一步发展两岸的经贸关系。从我们国内来讲,大家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是一贯的。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当选总统实际上准备不足,基础脆弱。所以为缓解内外的压力,他由“明独”转为了“暗独”。出于稳定内部、巩固政权的需要,在两岸关系上采取缓兵之计,以争取喘息的机会。他在讲话中摆出一副和解、善意、务实的姿态,比较明确地提出“四不”的承诺,不宣布台湾独立,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进行统独公投,不改国号,再加上宣布没有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问题,但却拒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他对“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关键问题是既不承认,但也不强硬对抗,采取回避和模糊的态度。在台湾摆出缓和两岸关系的姿态、又拒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时,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在原则立场上不会做任何的退让,同时我们也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陈水扁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我们要对他保持压力;同时我们要采取行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争取国际舆论,争取台湾民心。这就是我们对待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对陈水扁回避“一个中国”原则的真实意图和改善两岸关系的空洞承诺要揭露,对他做出的“四不”的承诺要迫使他落实。同时我们对两岸对话、两岸“三通”等重大问题要提出我们的主张,保持主动。应该说台湾问题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邓小平同志过去说过,解决台湾问题要用“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解决,因为右手力量大一点儿。但实在不行只好用左手即军事力量。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如果说有什么灵活性,那就是我们可以等待。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变,可以有自己一定规模的军队,现行的政策可以不变,可以继续同外国进行贸易、商业与民间交流,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台湾人民的收入不会减少,只会增加。但是这一切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我们总的要求只有一条:是“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邓小平还说过,两岸实现“三通”没有先决条件,“三通”就是说先来往,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增加人民间的了解,这是促进谈判的一种方式。所有国际朋友如果真是要促进中国统一的我们欢迎,但中国统一这件事要由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决定。希望两岸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做这件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我们希望台湾的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邓小平还讲到,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个月就能解决的,需要时间。我们并不想屈人之兵,我们绝不是要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位。邓小平的这些话,现在仍然代表了我们的立场。
在我们看来,台湾问题从实质上讲是中美关系问题。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内容主要都是谈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实际上就是干预了中国内政,给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造成了障碍。如果美国国会坚持干涉中国内政,将会使中美关系发生波动。总而言之,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基本的方针并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