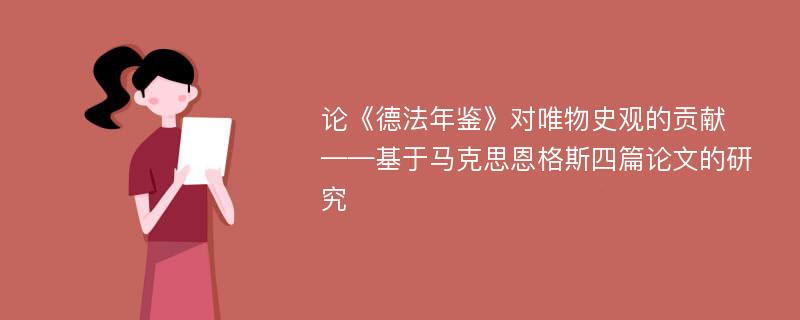
[摘 要]《德法年鉴》时期,通过“走在时代前沿”的德国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露了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后,“实践”性的哲学就该出场了。获得了自身解放的政治国家,却不得不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被赋予平等权利的现实的人,却在犹太精神的宰制下深陷竞争的囹圄,政治解放远没有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未竟的解放事业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唯有以“批判的武器”武装“武器的批判”,才能在血与火的革命中,迎来新世界的曙光。至此,两位创始人循着不同的路径,却殊途同归,都完成了两个转变。思想进程的不谋而合,奠定了他们后来矢志不渝的伟大合作与伟大事业。
[关键词]《德法年鉴》;新宗教观;市民社会;人的解放;殊途同归
《德法年鉴》仅在1844年3月出了一期合刊,却不可否认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在这期合刊上,马克思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以下简称《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恩格斯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以下简称《英国状况》)。列宁曾指出,这四篇论文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两个重大转变,即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当下,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西方“马克思学”蓄意制造马恩之间的对立,面对纷乱的社会思潮,重温《德法年鉴》,以经典文本为依据,探寻其中潜藏的历史唯物主义萌芽,厘清马恩思想的发展进程,对于我们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觉得“缴学费”这种说法很新鲜。讲到坐车不付钱,他兴致来了。“几年前,有三个年轻人搭我的车,路程很短,只有15元。到了之后,三人说:‘老子坐车从来不付钱,坐你的车算给你面子。’我把车子往路边一停,随手抄了一个长长的铁扳手,下车就把那个带头的人往死里打,打得他满头满脸是血。第二个拿木棍朝我打,我扬左手挡,手上骨头全碎。我也朝他的膝盖用力一挥,他立刻倒地哀号。第三个看了,吓得在旁边发抖。”
一、新宗教观的出场:宗教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
德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宗教批判的历史意义。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后,罗马教皇加强了对德国的宗教控制,实行高压政策,人民的生活愈发困苦。在当时的德国,基督教作为国教,在社会政治、宗教生活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而犹太人被斥为异端、“天生的贱种”和“社会的祸根”。1841年,普鲁士国王颁布“内阁敕令”,提议恢复同业公会制度,拒绝犹太人服兵役和参与公职,意图把犹太人与基督教社会隔绝。这一法令使德国本就很严重的排犹现象变本加厉。一时间,“犹太人问题”在社会上引发了大讨论。
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认为,“犹太人问题”的症结在于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宗教对立,因而,解决问题的锁钥就是化解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宗教矛盾,而化解宗教矛盾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消灭宗教。至于如何消灭宗教,鲍威尔找到了一条从头脑中改造世界的方式。他认为,只要消除了头脑中的宗教意识,宗教本身就不复存在了。具体说来,鲍威尔企图通过改造人们的宗教观念,即犹太人和基督徒把他们各自的宗教信仰,看作人的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看作一定历史时期蜕去的蛇皮,以消除两大宗教的敌对状态,实现犹太人放弃犹太教、基督徒放弃基督教、一般人放弃宗教,最终实现所有人作为公民得到解放的美好构想。
马克思反对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看成纯粹的宗教问题,并指出鲍威尔的思维误区在于,他始终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1](第25页)。而马克思看到,在“犹太人问题”这一共像之下,宗教问题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德国的犹太人问题是纯粹神学问题,法国的犹太人问题是立宪制问题,北美的犹太人问题是真正的世俗问题。马克思还提出,“完成了的政治解放怎样对待宗教?”[1](第27页)宗教问题在民主制国家就销声匿迹了吗?令人惊奇的是,宗教不仅存在,而且“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1](第27页)。可见,宗教消亡绝非易事,宗教问题并不构成世俗局限性的原因,相反,它只是作为表征映射着潜藏在深处的社会矛盾。
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获得了各自独立,那么这二者之间是何种关系呢?当时德国理论界比较权威的理论解释当属黑格尔的有机国家观。黑格尔认为,作为特殊性的存在,市民社会总是无止境地引起新的欲望,每个活跃的个体为了达成“利己的目的”,总是尽情发挥“一切癖性、一切禀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3](第225页)。在纵横交错的关系罗网下,市民社会成为“个人私利的战场”[3](第351页)。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3](第224页)。混乱无序的状态,只有通过有权控制它的国家才能调和。国家是“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是“绝对的不受推动的自身目的”[3](第288-289页),是扬弃了各种中介和假象的真实基础,是普遍存在的地上的精神。只有国家,才能扬弃市民社会原子化的“分裂态”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伦理颓废。
马克思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第3页)。宗教批判是要撕碎锁链上虚幻的花朵,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追求现实的幸福。恩格斯同样也直指宗教的欺骗性,认为一切谎言和伪善都源于宗教。马克思还形象地把宗教表述为“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其主要功能是为“颠倒的世界”提供“包罗万象的纲要”、“通俗形式的逻辑”和“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1](第3页)。
宗教之后,人不再毫无自知地拜倒在神的脚下,然而,发现了自身价值的人,似乎并没有过上预想的幸福生活。在无限膨胀的欲望下,人们受到金钱势力的奴役,陷入了意义的失落,跌入了无家可归的困境,整个人类社会呈现出涣散、空虚和无灵魂的状态。那么,人的解放的现实出路,到底在何方?
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思想贯彻到对政治国家的批判中,指出“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1](第30页)政治国家实际上是同人们的世俗生活相对立的另一个“上天”。马克思洞察到,尽管国家宣告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宣告私有财产资格限制无效,宣告人人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但是,“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1](第30页)。事实上,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所谓的平等天国。平等的外观恰恰是为了维系和巩固实质上的不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恰恰是为了遮蔽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
从“犹太人问题”开始,马克思和鲍威尔公开决裂。鲍威尔认为,犹太人不自由,根源在于宗教信仰,主张直接废除宗教,以获得自我意识的完全自由。他是诉诸思想改造现实的唯心主义路径。马克思则认为,产生社会压迫的根源不在虚幻的天国,而在粗糙的尘世中。自由并不需要以舍弃宗教信仰为前提,关键在于摆脱隐匿在宗教矛盾背后真实存在着的现实羁绊。马克思恩格斯都意识到,仅仅寄希望于宗教批判来消除宗教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宗教批判,既无法真正实现宗教解放,更无法解放现实中的人。由此看来,马克思恩格斯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物主义路径——透过表层的宗教问题,走向现实矛盾的深处。
3.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爱国主义。她已经深深地融入我们这个民族的意识、品格和气质之中,成为56个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精神支柱和价值取向。勇于探索的果敢精神和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思想源泉,也是推进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二、新历史观的萌芽: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
马克思指出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1](第26页)。所谓“政治解放”,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消灭宗教特权、废除国教,使国家以国家自身来行使职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力图解决也完全能够解决的任务。法国和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极为充分的例证。而“普遍的人的解放”要求在一切领域中消除人的异化态、人的孤立状态,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归还给人自己。因此,政治解放远不是真正的人的解放。那么,如何才能推进这未竟的解放事业呢?
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疾风骤雨变革了世界的原有图景。在政治革命爆发之前,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浑然一体,每个人都从属于一定等级的职业团体,都被纳入等级制度中确定的一环,社会生活等同于政治生活。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1](第45页),伴随着政治国家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市民社会同时也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意义。政治革命将原本浑然一体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剥离开来,原先的同一状态被打破:公共的、政治的生活属于政治国家;物质的、经济的生活属于市民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只能是人类社会中的现实问题决定宗教领域的神学问题,而不能把神学问题当作现实问题的根源。固然,“犹太人问题”有其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还是深深扎根于粗糙的尘世生活之中。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宗教的礼拜生活中,而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人的真正自由无需以抛弃宗教信仰为前提,关键是要摆脱压迫他们的社会关系的束缚。表皮上的细小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有机国家观,指出政治国家只是一种幻想:政治国家在精神上的优越性,不过是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观念上的优势;政治国家在外表上具有的普遍性,不过是有名无实的“非现实的普遍性”。在马克思看来,即便是民主制国家,也仅仅只是在形式上代表人民的利益,“普遍事务的被意识到的真正的现实性只是形式的”[2](第80页),而就其实质来说,不过是脱离了市民社会的抽象存在。“正如基督徒在天国是平等的,而在尘世则不平等一样”[2](第100页),在尘世生活中,曾经作为中介作用的基督,这样一个身份让渡给了政治国家,曾经用来解释自身所遭受的种种局限的逻辑,从宗教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
MRCP检查采用GE光纤磁共振MR360,检查前常规禁食、禁水8h,患者取仰卧位,首先完成轴位呼吸触发自旋回波序列(FSE)T2WI、屏气快速成像稳态采集序列(FIESTA)扫描、脂肪抑制扫描,然后完成MRCP二维和三维薄层扫描。二维扫描参数:层厚60mm,每隔17°扫描1层,一共扫描6层。采用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序列(SSFSE),扫描参数:TR为6000ms,TE为1354ms,FOV为32cm×32cm,带宽为31.25k Hz。三维扫描参数:层厚1.6mm,无间隔扫描,FOV为36cm×36cm,带宽为41.67k Hz。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露了宗教对现实问题的粉饰作用,而且极富战斗性地提出,“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1](第6页)。要撕碎宗教的虚幻面纱,“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使耻辱更加耻辱”,使“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以唤醒沉睡中的人,激起人民的勇气,起而争取现世的幸福。马克思高声呐喊,“向德国制度开火”恩格斯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宣战,“我们惟一迫切的任务归根结底就是同它进行斗争,使我们摆脱它,使世界摆脱它”[2](第518页)。只有彻底解决了世俗生活中的矛盾,宗教问题才会如淡淡的烟雾自然散去。宗教批判不是要否定宗教存在的意义,而是要批判那需要宗教幻想的处境,使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摆脱幻想,重新作为有理性的人去思想、去行动,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现实性。
这种施工方法主要利用的是重锤自重法来进行地基与填方部分施工的夯击处理,从而可以加速沉降以达到路基的强度指标要求,该设备比较简单、工期较短、成本也比较低,所以通常会应用到碎石地基与细粒土的工程中。
和Y o u n g面对面说话我只经历过一次。之后和他交流时都是网上。他跟我坦白过,他说、写中文其实不怎么样,但是有键盘就不同了,都不会有人意识到他是美国人。
第三,职业技能。具体包括语言运用技能和技巧、人际交往技能和技巧、组织协调技能和技巧、游客安全保护能力、快速计算技能和应变能力等一般技能,还有,一定的外语交际技能和心理咨询技能。
总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看清,“虽然在观念上,政治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奴隶”[1](第51页),国家生活是违反本质和通则的外观,政治权力是金钱势力的奴隶。获得了解放的政治国家,不得不重新承认市民社会、恢复市民社会、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
“向管理要活力,要绩效。”他介绍,2010年,恰逢全国医疗机构“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启动,盛京医院临床护理专业成功挂牌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这两件大事,成为护理工作整体提升的重要契机。”
三、经济批判的滥觞:犹太精神和竞争规律
NIH希望通过最近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大量资助吸引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多年来,患者权益倡导者一直在提出这个问题:随着美国人口的老龄化,阿尔茨海默病正在造成越来越大的伤害,治疗成本迅速上升。这些预测和“到2025年有效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目标促使国会在3年内将NIH给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症的资助预算增加到原来的3倍,达到19亿美元。这种猛增的趋势并未结束,2019年的两份NIH支出草案会为该病的研究带来总数为23亿美元的资助——超过了NIH总预算的5%。
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恰恰相反,政治国家不得不服从市民社会。厘清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后,历史的任务就是要继续深入到矛盾的内核,即市民社会中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市民社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培育得日渐充分。市民社会是丧失了相互的精神关联的零散的孤立的各个人构成的非人性的世界,是缺乏共同性的内在必然性的各原子的集合态而否定地来理解的世界,是在物质经济活动层面由自私自利的各个人构成的分裂世界。[4](第171页)市民社会的成员没有超出狭隘的私人利益,始终以自我为中心,需要和私人利益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
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是以“犹太人问题”为切入点展开的。自私自利,缺乏社会性,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是市民社会成员的真实图鉴。这与把实际需要、自私自利奉为圭臬的犹太精神并无二致,“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1](第52页),犹太人是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现实载体,他们将自私自利、崇尚金钱、唯利是图等市民社会的庸俗习性发挥到了极致。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生意人,世俗上帝是金钱。“金钱通过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人而成了世界势力”[1](第50页),犹太精神是真正与市民社会相适应的普遍的社会意识。
如果说,马克思还只是从“犹太人问题”窥见了经济社会,那么,此时的恩格斯,因身处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比马克思更早地直观到了市民社会的状况。正如恩格斯所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5](第202页)。可见,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洞见到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了。
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学,恩格斯认为,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主要范畴。“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1](第72页)。就连作为竞争对立面的垄断,也无法给极速旋转的竞争漩涡摁下“暂停键”。“垄断是重商主义者战斗时的呐喊,竞争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厮打时的吼叫。”[1](第73页)表面上,二者处于截然对立的两极,但在显而易见的对立中,却蕴藏着深层的统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不回荡着竞争的主旋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无不臣服于金钱势力的统治。
恩格斯指出,竞争在土地、资本、劳动这三大主要生产要素之间发挥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刺激着每一要素的所有者,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与另外的两方博弈。在弱肉强食的游戏中,资本和土地,因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再加之科技,这一在当时还不受重视的生产要素地夹持,劳动无疑成了最卑微的一极。恩格斯还指出,竞争不仅在生产要素间制造紧张,而且在同一生产要素内部,也无时无刻不在诱发着极为激烈的角逐。随着竞争加剧,人与人之间的蚕食愈演愈烈,“丛林法则”一次次应验,竞争的结果越发触目惊心。
以极其敏锐的经济嗅觉,恩格斯作出预判:不可遏制的激烈竞争势必引爆社会革命。在竞争涡旋的驱使下,财产积聚是必然趋势。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纯自然的规律”[1](第74页)。财产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多的中间阶级被吞并,并被抛入工人阶级行列,于是,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必定显著增加,“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1](第84页)。恩格斯还预见到,“这是一个产生革命的规律” 。在“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1](第74页)的危机面前,在与日俱增的失业、贫困等社会矛盾面前,每一次接踵而来的更普遍、更严重的商业危机,都有可能成为引燃社会矛盾的导火索。“最后,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1](第75页),而这场革命将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1](第63页)。
总的来看,马克思通过探讨“犹太人问题”转向对市民社会的思考,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直观经济社会,他们都关注到了社会生活中人的真实境遇,即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每个人身上都携带有犹太精神的基因,在普遍地追逐私利的过程中,整个经济社会呈现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图景。
四、人的解放理论的初步奠基:“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
式中,E(r)为入射光在焦平面上的光场分布,Fi(r)为少模光纤不同模式下的模场,ds为焦平面处面元.
“理论”层面的宗教批判结束后,“实践”性的哲学就该出场了。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后,要做的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第4页),以宗教批判结束的地方为起点,马克思展开了新的批判。
参照《中国矿产地质志(江西卷)》(2015)[1]:区内基底地层主要有青白口系周潭岩组(Pt31bz.),南华系万源岩组(Nh1w.)、上施组(Nh1s)、洪山组(Nh2Z1h)。周潭岩组为一套次深中深变质海泥砂质浊积岩建造,南华系为一套浅海-次深海中深变质火山碎屑岩-泥砂质夹硅铁质-碳酸盐岩建造,均受区域变质作用形成低绿片岩相,主要岩性有变粒岩、片岩、千枚岩、片麻岩等。区域盖层较新,有白垩系石溪组(K2s)、茅店组(K2m)、周田组(K2z)、河口组(K2h)及第三系新余组和头陂组,均为内陆盆地砾岩、砂砾岩、砂岩与粉砂岩、泥岩沉积。第四系为现代河流冲积相及残坡堆积。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解放的实际可能就在于形成特殊的阶级。“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1](第12页)。不同于鲍威尔和卡莱尔把解放事业寄希望于“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贵族已经日暮途穷,对任何进步都不闻不问。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2](第497页)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是不带偏见的可造之材,拯救人类的进步事业只能靠他们,尽管他们粗野、道德堕落、文化程度低。
马克思恩格斯透过纷繁的现象,走向历史的深处,找到了尚不成熟但潜藏着无限可能的现实力量,即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不实现一切阶级的解放就不能解放自身的阶级——无产阶级,来打碎这个普遍隔绝的旧世界。无产阶级是自身异化的极端产物,其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一切属人的东西都丧失了。正因为一无所有,他们最有可能迸发出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最彻底的革命行动,炸毁资本主义社会,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而这个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反对一切领域中违反人性的现象,只有普遍地解放了其他阶级,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完全回复人本身。
但仅凭“武器的批判”能完成历史使命吗?从十九世纪初工人运动的现实状况来看,答案是否定的。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无产阶级很迷茫:他们知道有敌人,但不知道敌人是谁或者是什么;他们知道有盟友,但不知道盟友在哪里。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科学理论对工人的革命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第11页)过去的宗教改革从僧侣的头脑开始,现在的革命运动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马克思指出,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以来的德国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1](第9页)。恩格斯同样也显示出对德国哲学的“自负心”[4](第97页),他认为,德国高水准的哲学已使它当之无愧地处于社会变革的理论先导的位置,彻底的宗教批判使它形成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进而,“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这样一个绝对命令将成为德国哲学接下来的理论任务。[1](第11页)
马克思明确提出,只有实现“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深度融合,普遍的人的解放才能不断推进。“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第17页)。当“走在时代前沿”的哲学掌握了代表着“人的完全丧失”的阶级,当“彻底的理论”说服了这个“带着锁链的阶级”起而为“人的完全回复”反抗,当“思想的闪电”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的时候,便能在血与火的革命中,与旧的世界做最彻底的决裂,从而开辟出一举达至世界史最前端的变革道路,迎来新世界的曙光。
五、《德法年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毋庸置疑,《德法年鉴》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进程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依托文本的真实语境,我们能够更为真切地感知,这一时期两位创始人的思想转变,即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首先,通过“走在时代前沿”的德国哲学,马克思恩格斯不再用神的眼光,而是用人的眼光,来透视社会的现实问题,表现出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马克思明确说道:“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1](第49页)“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1](第3页)恩格斯同样也有类似的表述,“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2](第520页),历史的内容“不是神的内容,而是人的内容,整个归还过程就是唤起自我意识”[2](第519页)。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都深刻认识到了宗教的世俗基础,都透过宗教问题,来审视现实世界中的客观矛盾。同时,他们还认为只有根本消灭宗教的物质基础、消灭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世俗要素,才能使“颠倒的世界观”烟消云散。这初步崭露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具有解释世界的理论价值,更具有改造世界的实践属性,显示出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鲜明的战斗性。“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涉及这个内容的批判是搏斗式的批判”[1](第6页),等等,从这些铿锵有力的词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两位创始人已经吹响了战斗的号角,表露出鲜明的阶级性和战斗性。
其次,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有关涉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经济生活领域。从马克思的两篇文本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研究重心的转向,即从宗教批判着手,经由政治批判,走到了经济批判的入口处。以谋求人的真正解放为主线,从探讨犹太人的解放出发,经由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实现了从对“副本”批判到对“原本”批判的转变。恩格斯因身处在当时大机器生产最为发达的英国,先于马克思开始了经济研究,而恩格斯的研究成果无疑对马克思的思想转变,甚至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山之内靖提到了这样两个事实: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和经济学研究的第二阶段,至少两次研究了恩格斯的《大纲》,而且,在包含马克思独自展开的思想的《李嘉图笔记》和《穆勒笔记》之前,马克思重新阅读了《大纲》。[4](第210页)可见,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献,作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6](第3-4页),恩格斯的这篇著作,对马克思研究重心的转移、《资本论》的创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都初步形成了要通过社会革命,打碎相互隔绝的旧世界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远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要彻底实现具有人的高度的解放,就必须“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1](第33页),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继续将解放事业推向前进。而完成解放事业的主体,要靠代表“人的完全丧失”的无产阶级,打破人们之间封闭孤立的状态,才能在谋求本阶级解放的同时,完成普遍的人的解放。恩格斯面对生产过剩、财富过剩同人口过剩、贫穷过剩同时并存的英国社会,预见性地指出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的特征,并指出社会革命爆发的必然性。而要克服这种极具破坏性的状况,唯有将生产要素联合起来,使人作为有意识的人,进行有组织地生产。由此看来,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现存社会的“原子态”所潜藏的问题,只有通过人与人的联合才能克服,这为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自由人联合体”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然,必须承认,“哲学家也有自己的青年时代”[7](第49页)。《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还在形成与发展中,尚没有准确、系统地阐明或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还处于酝酿阶段,我们只能在他们的文本中发现一些蕴藏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零星片段。但是,任何成熟的思想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有一个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我们同样也不能苛求。
六、结 语
重温《德法年鉴》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四篇著述,我们可以看出,两位创始人在研究初期是循着完全不同的路径启程的。马克思以德国问题为研究对象,恩格斯以英国社会为研究对象;马克思注重文献研究,恩格斯注重实践调查;马克思是从天国的批判到尘世的批判、从“副本”的批判转向“原本”的批判,恩格斯是直接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批判进入、以当时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为考察背景;马克思是从批判宗教、国家和法着手,层层深入到背后的物质根源,是从现象层面的“果”逐层析出本质层面的“因”、从上层建筑逐步推进到经济基础的思维进路;恩格斯由于置身于当时机器大生产高歌猛进的英国,直接接触到了火热的经济生活,因而研究路径相对更为直接,他把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批判和同经济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致思理路。
尽管研究路径不同,但英雄所见略同,殊途同归,马克思恩格斯在诸多方面已潜在地形成了诸多共识,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结论。他们都看到了宗教问题的根源在于世俗世界,而要破解现实社会中的难题,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关键在市民社会。一场打破旧世界的社会革命必不可少,而社会革命需要诉诸“武器的批判”,无产阶级是最有希望来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人选。唯有打碎不平等的旧世界,才能让经济生活中的价值、地租、工资等回归于本身,才能避免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才能使市民社会中的社会成员复归于政治生活中的公民,才能不给宗教神学留有空间,才能使人的关系复归于人自身。
这样,我们看到科学共产主义的两位创始人,各自依靠独立的研究,在《德法年鉴》时期都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如果说,马克思是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那么,恩格斯则是通过观察英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实际状况走向社会主义的。正如恩格斯回忆道:“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5](第202-20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观点上的不谋而合,为他们后来矢志不渝的伟大合作和伟大事业奠定了坚不可摧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山之内靖:受苦者的目光:马克思的复兴[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作者简介]黄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 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5-3980.2019.03.002
[文章编号]1005-3980(2019)03-0011-07
收稿日期:2019-03-11
[责任编辑邓念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