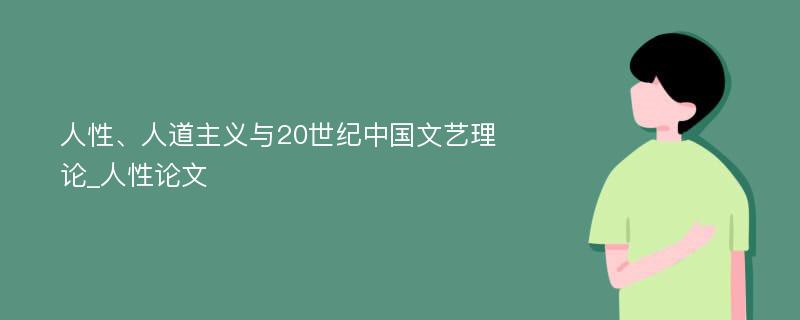
人性、人道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人道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文艺理论界那些在即将过去的世纪中曾经艰难跋涉过的人来说,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是不免会有别样的滋味的。在回首往事,对这踬蹶的来路作思辨的清理时,像人性、人道主义这类曾引起过理论界普遍关注,使一些人吃尽苦头的论题是不可能从人们的记忆中轻易消失的。
一
世纪之初,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依然被儒家的道统观念牢牢地把持着。儒家学说所倡扬的礼仪伦常,在价值取向上,重君父、轻臣子,重天理、轻人欲。它公开张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人的个性存在,人的生命需要和情感需要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封建的社会秩序。在这种思想的统制下,儒家文论也便隐隐地包含着这么一种观念:即人的一切都是君父赐予的,他的生活质量与生活要求是不值得重视的。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性、人道主义成分的稀薄,其肇因盖出于此。封建社会的文学不可能正常地表现人的感情、人的需要和人的价值存在。例如,爱情一般被认为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但在我国的古代文学中就没有得到健康的和富有创意的挖掘。庙堂文学是有意回避爱情的表现的。民间文学在表现爱情时,也受儒家文论的影响,要么将其与因果节烈之类的陈腐现象联系在一起,要么将爱情描写得十分拙劣十分淫亵,视妇女为玩物。
如果说封建文学在一个封闭的国度里,尚能维持其权威的统治的话,那么,随着国门洞开、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包含民主传统的异域文化的输入和一大批新人的诞生,这种灭绝人性的文化观便日益显示出它的背谬。它之受到接受思想自由原则,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五四”新人的激烈攻讦也便显得十分自然。“五四”新文学的功绩正是在于经过它的倡扬,人性、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开始获得承认,成了维护人的生命存在和个性要求的不可小觑的精神力量。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很久,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便已开始了思想启蒙的活动。在文艺思想方面,黄遵宪以“我手写我口”张扬审美个性,认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力图突破儒家道统观念对艺术创作的限制,排除非审美因素的干扰,将个人情致的表达视为艺术审美的灵魂。他的这种观点振聋发聩,受到了文坛的重视。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称自己“夙不喜桐城古文”,不受古诗文的束缚,“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追求一种“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的美学风格。这些美学思想无疑都成了“五四”新人张扬个性自由、力摒礼教束缚的思想前提。
鲁迅最初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所秉持的也是人道主义的立场。《狂人日记》以吃人的礼教作批判的鹄的,多方挖掘,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的背谬。《孔乙己》则怀着深切的人道同情,刻画了一位受封建的思想意识腐蚀与戕害的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他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等也清晰地昭示了其时鲁迅对封建社会中人之命运的文化思考与美学思考。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关于情感的思辨,也抓住了载道文学拘于理义伦常而扼杀人之性灵的要害。胡适认为,情感是文学的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载道文学为理义伦常所束缚,使本为情感驱动具有极强抒情特性的文学创作,成了某种道德观念的传声筒。质言之,情感的解放实质是人的解放,人性的解放。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向载道文学大胆开战,并热情推荐符合他的审美理想、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平民文学”,在这一视野中,卢梭、雨果、左拉、狄更斯等外国作家都受到他充分的肯定。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尽情地发挥了他的人道主义的美学观点。周文强调作家的创作态度,认为作家的创作应以人作为思维中心,以人的生活为是,以非人的生活为非。该文还对中国的旧文学的非人的特性作了系统的解析,对西方文学的人道主义的传统作了全面的介绍。周文关于人道主义的文学态度与旧文学观念的对立是一目了然的。
我们注意到,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理想中,也一样包含了人道主义的因子。李大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1 〕从“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的纪录”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他将18世纪的法国革命与20世纪俄国革命都无一例外地看作是“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必须指出的是,该文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因此,李氏将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表明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同等程度的概念,信仰社会主义也必信仰人道主义。事实上,拿当时的中国的国情看,宣传社会主义与进行人道主义的思想启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确实是互为补充的。在关于文学的思辨中,李大钊张扬“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2〕,其人道主义的美学趣味了然可见。
20年代初期,中国新文学承“五四”人道主义宣传的惯性,继续在各个方面表达文学新人的人道主义的美学理想。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宣言表达了研究会同人服务人生的美学旨趣。茅盾以朗损的笔名发表《社会背景与创作》,提倡“怨以怒”的文学,即“于同情于被损害者外,把人类共同的弱点也抉露出来”〔3〕, 这一文学宗旨的人道主义性质我们是不难发现的。郑振铎以西谛的笔名发表的《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在表述其文学主张时,也把人道主义作为主要的思想参照,他说:“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泻于文字上的。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诗人把他的锐敏的观察,强烈的感觉,热烘烘的同情,用文字表示出来,读者便也会同样的发生出这种情绪来。”〔4〕
创造社是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但在创造社同人的文学主张中,我们照样也看到了执著用世的人道立场。例如,成仿吾阐述创造社文学宗旨的《新文学之使命》认为,文学应对社会的“不公的组织与因袭的罪恶”加以严厉的声讨,并把这视为文学家的责任。他说:“一个文学家,爱慕之情要比人强,憎恶之心也要比人大。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在我们这种良心病了的社会,文学家尤其是任重而道远。”在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势时,成仿吾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有强权无公理的时代,一个良心枯萎,廉耻丧尽的时代,一个竞于物利,冷酷残忍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的组织,既于这样的时代相宜,我们的教育又是虚有其表,所以文学家在这一方面的使命,不仅是重大,而且是独任的。我们要在冰冷而麻痹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摇摇的激震。”又说:“对于时代的虚伪与它的罪孽,我们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我们要是真与善的勇士,犹如我们是美的传道者。”〔5〕
总起来看,“五四”时期关于人道主义的宣扬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不加区分的,即宣传社会主义也必宣传人道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出现了合流的现象,社会主义者如果没有公开宣传人道主义,至少也对人道主义持中立的立场。而“五四”时期虽持进步立场但不赞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与社会主义者取得共识。第二,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的思想启蒙中,理论与创作是互相配合的。即它不仅有理论的诠解,而且有数量众多、极具创意的作品作为这种宣传的形象铺垫,因而形成了相当的声势。前面提到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便以对封建制度的猛烈批判与对被压迫者的人道同情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冰心“五四”时期的创作则着力表现作者爱与美的社会理想与美学理想;此外,像乡土文学也都浓浓地含着作家对人物的人道同情。第三,“五四”时期中国的革命者所面对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人道主义思潮的崛起,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斗争,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
20年代末,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由被冷落到受批判,在主流文论中开始失势。其后的遭际颇值得深思。
如众所周知,20年代,经过“五四”的广泛的思想启蒙,在中国出现了革命的形势。北伐战争势如破竹,革命在中国老百姓面前显示了创造历史的巨大能量,但是当战争正轰轰烈烈地向前推进的时候,即发生了国民党的叛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地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重任。置身在这样的形势中的一部分革命文艺家举起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旗帜,用文艺这个武器同国民党的恐怖统治作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革命文艺家必得要突出无产阶级文艺的个性,以此来为无产阶级的文艺争得生存和发展的地盘,阶级论与人性论也因此而发生龃龉,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合作也不再可能。生活活动于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很自然地会形成一种思维惯性:革命文学与人道主义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要革命就不能讲人道。人道主义是革命的负累。由于受到反动统治的巨大压迫,左翼文艺家失去了从容思考文学阶级性的条件和耐心,其持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不免于偏激。例如,在这一论辩中,出现了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6 〕不少人往往满足于阶级口号的叫喊,而不是对阶级社会中文学阶级性作具体的分析。而对那些虽然无意革命,但却尚有社会良心,对艺术情有独钟且继续坚持人道主义立场的文学观点则往往缺乏兼容的气度。因此当梁实秋等人公开出来向阶级论的文艺观点发起挑战时,也就更容易引起左翼文艺界的更为强烈的情绪反弹。二三十年代对人性论人道主义文艺观的批判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梁实秋关于人性论文学观的宣传存在不少问题。在他的理论主张中,有文艺是为少数人的,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文艺的观点。这种论点既然一笔勾销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人群的文艺欣赏和文艺创作的权利(从梁实秋的实际论述看,他主要否认的是人民群众的创作能力),也就失去了起码的人道主义的意味,因而清晰地暴露了这位主张人性论的理论家自己的人性中的阶级性。在表明新月派文学观点的《新月的态度》一文中,梁实秋以“健康”与“尊严”相号召,认为“社会的纪纲靠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的社会的天秤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7 〕在稍后所写的《文学与革命》一文中,他反复申述了他的人性论的文学观点,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普遍的人性,从人性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是忠实,——忠实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断定“文学一概以人性为本,绝无阶级的分别”。〔8 〕在与左翼文艺界发生争论以后,梁实秋写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进行答辩,他首先对阶级观念作了充满鄙夷的解释,进而对文学的阶级性提出质疑,他说:“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在对文学的阶级性作了否定之后,他认为,资本家和劳动者在人性上是没有两样的,而文学就是要表现这基本的人性。他进一步分析说:“无产阶级的生活苦痛固然值得描写,但是这痛苦如其是深刻的,必不是属于一阶级的”。他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阶级的。”在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加以辨析时,他对左翼文艺界对文学的斗争功能和宣传功能的理解发出了尖刻的嘘声。〔9〕客观地讲, 梁实秋确实抓到了左翼文艺界在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上的某些狭隘僵硬的论点(后者正好为梁实秋提供了恣意嘲弄的口舌),并提出了一些值得加以研究的东西,例如共同人性的问题,人性的超阶级性的问题。但是正如上述,其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恐怖统治和血腥屠杀之中,左翼文艺界尽管也要求文艺家应当对民生痛苦表现出人道的同情,但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文艺作为武器,来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进行斗争。而梁实秋的关于人性论文学观的鼓吹,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只能发生消解人民群众的反抗意识的作用,因此迅即遭到左翼文艺界的驳斥。这种驳斥很快便演变为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全面的批判,表明左翼文艺界至此已放弃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所有对梁的反击中,几乎无一例外地用阶级论来抵制人性论。彭康《什么是“健康”与“尊严”?》〔10〕一文否认有超阶级的“情爱”,他说:“我们对于同一阶级自然会‘互助’,会‘情爱’,而对于敌对的阶级一定要‘仇恨’,要斗争。”冯乃超《冷静的头脑——评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认为:“在阶级社会的里面,阶级的独占性适用到生活一般的上面,言语,礼仪,衣食住,学术,技艺,乃至一切的生活内容。”对于梁实秋,冯文着意揭示他“晓得‘不能强制没有革命经验的人写革命的文学’,却不能明白没有生活全人类的生活的人绝对不会写全人类的人性”的背谬。认为梁犯了在抽象的过程中空想“人性”的过失。
鲁迅的论析对文学的阶级性作了较为全面的说明。鲁迅认为,人的性格感情因受经济的支配,而不免于阶级性,但是鲁迅认为即便是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性格感情也只是都带而非只有阶级性。〔11〕但鲁迅对左翼文艺界所张扬的文学的武器功能和宣传功能,也作了肯定的回应。这一事实说明,无产阶级文艺当时面对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来进行斗争,过分纠缠于共同人性,只会消泯无产阶级文艺的斗志,只能有利于反动派维持其旧有统治。
批梁之后,左翼文艺界随后还发动了对第三种人、自由人的所谓死抱住文学不放的文学观的清算。左翼人士对“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的主张的反感,其出发点依然是阶级论的文学观。所以与第三种人、自由人的争论,实质是同新月派人性论文学思想斗争的继续。
在这两次颇为热闹的公开的论战之后,理论界在建国前再不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有影响的讨论。但我们不能因此说,这些问题就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界之外。要不然的话,40年代,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不会有一段关于人性论的论述。毛泽东当时是从否定方面来论析人性问题的,他认为不存在抽象的人性。1976年何其芳在回忆毛泽东的文艺观时,说毛泽东后来还曾有过正面肯定人性存在的见解。
建国后,中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审美需要和文化品位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争时期以阶级斗争和政权更迭为依归的充满火药味的作品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人们的美学趣味与欣赏要求。于是,意识到这一变化情势的理论界的有识之士大胆地讨论起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巴人的《论人情》将“人情味”普泛化,以此作为他的文学表现人性的主张的突破口,他说:“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在解释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时,他认为阶级斗争的出现,是因为有人试图“阻止或妨害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爱和希望”,这样就有了阶级斗争。他机智地将阶级斗争说成是争取“人性解放的斗争”。于是在他看来,“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这种作品大都是鼓励人要从阶级束缚中解放出来。或悲忿大多数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或反对社会的不合理、束缚人的才能智慧的发展,或希望有合理的人去生活,足以发扬人类本性。这种作品一送到阶级社会里去,就成为捣乱阶级社会秩序的武器。但正是这些东西是最通达人情的。人情也就是人道主义。”〔12〕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13〕一文的主旨是要将人作为文学思维的中心,认为人即是文学的目的,反对将人当作某种政治斗争的工具。他说:“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伟大的诗人,都是本着这样的理想来从事写作的。要改善人的生活,必须先改善人自己,必须清除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培养和提高人的坚毅、勇敢的战斗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50年代中期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人们之所以能有这样大胆的揳入,一方面诚如上述,是同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的新变有关,另一方面更同当时较为宽松的文化氛围有联系。因此一旦政治空气发生逆转,出现了反右这样的新事变时,艺术思维亦必沿袭其惯性的运作,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不仅不会出现什么积极的结果,相反,它们必将遭到更为猛烈的批判。宣传人性论人道主义文学观点的这部分理论家在反右斗争中不少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60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周扬在其所作报告中是这样来表述文艺的特性的,他说:“文学艺术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阶级斗争的神经器官。”他还以阶级划线,说“革命的文艺从属于革命的政治,反动的文艺从属于反动的政治”,于是,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文学观点在这个报告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周扬说:“目前修正主义者正在拼命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等谬论,来调和阶级斗争和革命,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以达到他们保护资本主义旧世界和破坏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周扬认为:“‘人性论’是修正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武器。他们以抽象的共同人性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以人性或‘人道主义’来作为道德和艺术的标准,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该报告还将50年代国内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文学观的正常讨论与苏联东欧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蜕变联系起来分析,将人性论人道主义描绘成一种十分危险的文艺思潮。在周扬发表这篇报告的前后,文艺理论界展开了颇有声势的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伐。
现在看来,巴人论人情,出发点依旧是阶级论的。他肯定文艺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但却由此推导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文艺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但其终极目的则为解放全人类,解放人类本性。”他认为:“描写阶级斗争为的是叫人明白阶级存在的可恶,不仅要唤起同阶级的人去斗争,也应该让敌对阶级的人,看了发抖或愧死,瓦解他们的精神。这就必须以人人相通的东西做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情,也就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本来所谓阶级性,那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而我们要使文艺服务于阶级斗争,正是要使人在阶级消灭后‘自我归化’——即回复到人类本性,并且发展这人类本性而且日趋丰富。”像这样持平的观点不能获得认可,这也足以说明当时的文化氛围是何等的凝重、压抑。
三
总起来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性、人道主义是被当作革命文艺的对立物受到批判受到责难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初,一部分曾长期对人性人道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也终于在对新中国文艺实践的曲折经历的反思中意识到人性、人道主义的美学价值。但文艺思维稍一出现“异动”,便立即遭到了思维惯性的阻遏,一度趋于活跃的讨论也便无疾而终。其中周扬的遭际尤其让人为之惋惜。周扬在新时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思想解放,敢于负责,积极领导了对庸俗社会学的清算,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他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猛醒,表达了迥异于前论的观点,却因此受到了相当严厉的诘问。经历过文革劫难的周扬,居然在文学的春天里挺不过这骤然来临的批评! 令人高兴的是, 80 年代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得到理论界的普遍的认同, 到了90年代,当西方文艺界反理性、反艺术、宗教化的趋向逐渐得势,暴力、色情等丑陋的东西被当作有趣把玩、展示、炫耀,中国的文艺界中也有不少人以此为时髦的时候,文艺界开始认识到了人性、人道主义在抵制这类不仅反艺术而且还反人类的所谓文艺思潮时的价值。在即将告别20世纪的时候,文艺界在人性人道主义文学观念上再一次形成广泛的共识,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在世纪之交学术讨论更趋于平静、理性的时候,我们已经具备了就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作一严肃的论辩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否真的如某些人所说,是水火不相容的?此外,我们还想讨论一下20世纪中国文艺界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批判的经验教训。
我们知道,近年来,有不少人把马克思主义指称为一种只讲斗争和暴力、面目狰狞的理论,而声称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庸俗社会学恰恰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核心的面目全非的解释,迎合了这些指责,仿佛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的是一种不关心人的与人的尘世生活无关,只是为了获得政治权力和建立某种抽象的正义的思辨体系。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看,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都是受到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启蒙的学人,康德毫不犹豫地宣称“人自身便是目的”,并将这一信念作为他的最高的实践原则。黑格尔虽然有观念吞没人的思维取向,但他承认“各人是他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并在辨析他的自由观时,说:“自由乃是于他物中发现自己的存在,自己依赖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意思。”〔14〕费尔巴哈要建立爱的宗教,认为“爱可以使人从中找到自己感情的满足,解开自己生命的谜,达到自己生命的终极目的,从而,在爱中获得那些基督教徒在爱之外的信仰中所寻求的东西”〔15〕。一般认为,费尔巴哈的理论充任了马克思恩格斯由黑格尔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介,显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随便地与无所用心地越过这一中介的,他们携着人类古代文化遗产的积极因子,吸取了费尔巴哈具有浓重民主色彩的人本主义理论而达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此外,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也构成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另一个前提。诚然,马恩对空想社会主义有许多批评,甚至认为它的进步意义与历史的发展成反比。但马恩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受苦大众所表达的人道同情还是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马恩还说:“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16〕
若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从事理论活动之初,就坦言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是承载着历史创造着历史的人,并藉此与德国各种官方哲学划清界限。无论人们给马克思所讲的人加上什么定语,人总是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不是人以外的什么东西。马克思希望人能够获得幸福的生活,人能够获得发展的自由、创造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人的生活,力图改善人的生活,致力于人在社会关系与物种关系方面的二重提升,这些都足以证明,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维中心。
如果说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中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追求才能得以体现的话,那么在精神文化领域中,特别是在与实际需要拉开了较大距离且更多地反映出个性要求的美学领域,人道主义的诉求便被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成为对扼杀人的情感被金钱亵渎的所谓艺术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美学理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在文学艺术中更多地表现被压迫阶级的生活状况,他们认为这种表现将有助于“社会关注所有无产阶级的状况”〔17〕,至于表现工人阶级对他们所生活的压迫环境的反抗,那更是马恩所欢迎的。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激赏那些表现了真正人类感情的作品。他们深切地感到,“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被破坏得差不多了”〔18〕,因此怀着欣喜对当时以性爱为旋转轴心的诗歌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19〕第三,在评判文学作品时,他们舍弃了党派的道德的标准而选择了包含人道主义因素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如前所述,进入90年代以后,文艺论坛不大能听到反对人道主义的声音,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进步。我认为,面对世纪末甚嚣尘上的反理性、反艺术、宗教化思维取向和解构主义的挑战,如果我们不得不要为捍卫文艺的价值、捍卫人的价值进行斗争的话,那么,人道主义将会给我们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持。
从上面的简要回顾中,我们知道,人性人道主义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经历了由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我们从这一经历中又可以获得哪些经验教训呢?我认为二三十年代以后人性人道主义受到一次比一次严厉的批判,是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的。
从客观原因讲,世纪之初,思想界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封建主义对人性的扭曲与戕害在觉醒了的先进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反弹,在缺少理论参照的情况下,曾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过重要启蒙作用的人道主义思想遂成为反对封建专制,文化蕴涵深厚的精神力量。但当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实行恐怖统治的时候,人道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便显得相当的乏力,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与黑暗势力妥协的遁词,宣扬人道主义只能表明宣扬者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正是因为如此,我认为当时革命文艺界有意与人性人道主义拉开距离的立场是合理的。然而建国以后,当社会恢复了常态,文艺也有了向审美回归的要求的时候,却因政治上的失误,而丧失了实现这一回归的有利时机。当阶级斗争被认为异常的激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被认为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张扬人道主义将被看作是自拆心防,向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投降。
从主观原因讲,首先,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与人道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人为地制造了阶级论与人性论的对抗,理论界视讨论人道主义问题为危途,人性、人道主义实际上成了极易引爆的雷区。其次,对文艺的特征认识不清也是理论失误的重要原因。诚然,在阶级社会中的文艺,能够表现作家艺术家的政治意识,甚至可以为政治服务,但就文艺发生的终极根源说,文艺是因人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它的主要作用在于陶冶情感、扩展与提升人的感觉机能、创设和谐的生活氛围。文艺具有提升精神改良人性的人道主义的性质是不容怀疑的。反对人道主义的美学原则,在文艺审美领域刻意追求审美以外的东西,就会使文艺失去其存在的根据。因此尽管在人类生活的一些特殊阶段,文艺的人道主义性质被客观情势所抑制,但这种抑制的合理性也只是阶段的合理性,一旦社会生活进入正常状态,便应适时地恢复文艺的正常机能,使其发挥改良社会改良人生的积极作用。从坚持文学艺术的进步取向和人学特征着眼,从西方思想文化领域所弥漫的反理性、反艺术、反人道主义的文化思潮和人们对这一文化思潮的极大反感的实际着眼,即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立者在艺术审美领域真的如人所说是排斥人性人道主义的(这是一种虚拟的假设,事实完全不是这样),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者,在新的形势下,为了文艺的健康发展也应对人性、人道主义的美学思想作出自己本于良知的肯定。
注释:
〔1〕《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载《新青年》1918年11月15 日第五卷第五号。
〔2〕《什么是新文学》。载1919年12月8日《星期日》社会问题号。
〔3〕《小说月报》1921年7月10日第十二卷第七号。
〔4〕《文学旬刊》1922年5月11日第三十七期。
〔5〕《创造周报》1923年5月20日第二号。
〔6〕《中国青年》1923年12月22日。
〔7〕载《新月》第一卷第一号1928年3月10日。
〔8〕《文学与革命》,载《新月》第一卷第四期1928年6月10日。
〔9〕《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1929年9月10日。
〔10〕载《创造》第一卷第十二期1928年7月10日。
〔11〕《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载《语丝》1928年8 月20日第四卷第三十四期。
〔12〕载《新港》1957年1月号。
〔13〕《文艺月报》,1957年(5)。
〔14〕《小逻辑》,44页。
〔15〕《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24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7页。
〔17〕恩格斯:《大陆上的运动》。
〔18〕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9〕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标签:人性论文; 文学论文; 人性论论文; 梁实秋论文; 文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