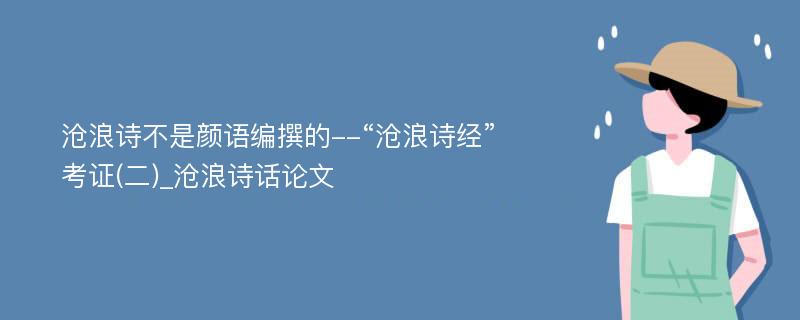
《沧浪诗话》非严羽所编——《沧浪诗话》成书问题考辨(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成书论文,之二论文,非严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从单行本之版本源流看《沧浪诗话》成书及得名之由来:明正德胡瓊刻本始有《沧浪诗话》之名
《沧浪诗话》除见于《沧浪吟卷》一书外,还以单行本流传。学术界一般认为,严羽的《沧浪诗话》原来是单行的,只是到后来才被收入《沧浪吟卷》中。这种观点实际上渊源于《四库全书总目》。该书卷一六三《沧浪集》提要说:
其《诗话》一卷,旧本别行,此本为明正德中淮阳胡仲器所编,置之诗集之前,作第一卷,意在标明宗旨,殊乖体例。今惟以诗二卷著录别集类,其《诗话》别入诗文评类,以还其旧焉。
又卷一九五《沧浪诗话》提要云:
此书或称《沧浪吟卷》,盖闽中刊本,以《诗话》置诗集前,为第一卷,故袭其诗集之名,而实非本名也。
依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沧浪诗话》原本是以单行本行世的,只是到明正德间胡重器刻本才将《沧浪诗话》置于诗集之前。当代学者多从其说。但这个说法乃是错误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明正德胡重器刻本之前,还有一个元刻本,也是将严羽的论诗著作列在诗作之前。而胡重器的刻本恰恰是从元刻本来的。所以单就这一点而言,这个说法就不可为据。
1.元代曾有论诗著作单行本
前面说过,黄清老之前不可能有《沧浪诗话》一书。郭绍虞先生所谓有宋刻本《沧浪诗话》的说法是不足为据的。[2] (《试测〈沧浪诗话〉的本来面貌》)正是黄清老汇辑了严羽的论诗著作,即是张以宁所说的“裒严氏诗法”。黄清老所汇辑的严羽论诗著作在元代也有单行本。明代怀悦刻本的诗法汇编《诗家一指》及杨成刊本《诗法》中在《严沧浪诗体》前都有一段题记:
《严沧浪先生诗法》,亦有印本。所论多出《诗家一指》中。盖此公于晚宋诸公石屏辈同时,此公独得《一指》之说,所以制作非诸人所及也。自家立论处,依旧有好处。今摘写于此中,其余出《一指》者,兹不再编矣。然诸家论诗多论病而不处方,卒无下手处。
笔者曾考证怀悦编集本诗法汇编《诗家一指》及杨成本诗法汇编《诗法》的初编当在元末,此处的编者题记也当在元末。但是这则题记有个错误,那就是题记者因《诗家一指》“三造”部分中引有严羽论诗语,而误认为《诗家一指》的年代早于严羽,严羽受《诗家一指》的影响。[8](P31)不过这则题记表明,元末曾有《严沧浪先生诗法》的刻本,这个刻本与张以宁所说的黄清老“裒严氏诗法”的说法相合。因而这个《严沧浪先生诗法》应就是黄清老所汇辑的严羽论诗著作的单刻本。以上两部诗法汇编本所收入的《严沧浪诗体》,编入了《诗体》、《诗评》部分的内容,已经被严重地窜改。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把严羽原著中的“本朝诸公”改成“宋”,又把所引《诗评》部分的内容冠以“总论”之名。
2.明正德以前没有《沧浪诗话》之名
《唐诗品汇》在《历代名公叙论》中所引《沧浪诗话》的内容之后,分别标明“已上见《诗辩》”、“已上见《诗评》”、“见《诗法》”,没有提《沧浪诗话》之名。在《引用诸书》中标有“严沧浪云”,并注:“《诗辩》、《诗评》、《考证》。”也没有提《沧浪诗话》之名。这表明在明代初年,尚没有《沧浪诗话》之名。
就我们目前所知,明代最早的单行本是明正德二年(1507)刊的《沧浪严先生诗谈》。黄丕烈跋明抄本《沧浪严先生吟卷》云:
余向得《严沧浪先生吟卷》有二,皆樵川陈士元编次、进士黄清老校正者。……此外,又有《沧浪严先生诗谈》,系正德二年本,但有《诗辩》等,无《答吴景仙书》及五言绝句以下诗。盖专论诗法,不称《吟卷》矣。
黄丕烈所得的两种《严沧浪先生吟卷》都是胡重器刻本。他所说的《沧浪严先生诗谈》这个本子,笔者未曾寓目。而阮元文选楼刻《天一阁书目》曾著录《沧浪严先生诗谈》一册,应就是这个本子。黄丕烈在跋语中将它与胡重器刻本相比较,认为《沧浪严先生诗谈》只是缺少《答吴景仙书》及诗歌作品,可见《诗谈》这个本子与胡刻本的《诗辩》等五篇是相同的。据此,则《诗谈》乃是从《沧浪吟卷》中将《诗辩》等五篇独立出来而自成一书的。并且,这个本子也并不称“《沧浪诗话》”,而是称“《沧浪严先生诗谈》”,可见正德刻本的刻者也并没有见过有《沧浪诗话》,因为如果这个本子所据的是一个叫《沧浪诗话》的单行本的话,他不应把书名中的关键字“诗话”改成“诗谈”。
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十八著录《严沧浪诗谈》一卷,解题云:
宋莒溪严羽仪卿著。列诗辨、诗体、诗注(按当作“法”)、诗评、诗考证,定诗宗旨正变得失,议论痛快,识高格当。
这个本子也只有《诗辩》等五篇,而没有《答吴景仙书》,与黄丕烈所叙的正德二年本相同。虽然在关键字“诗谈”的前面一是“沧浪严先生”,一是“严沧浪”,但这很可能是著录者的略称。比如《沧浪严先生吟卷》或被称为《严沧浪吟卷》,或被称为《沧浪吟卷》。所以这里著录的《严沧浪诗谈》应就是正德二年刻本。又,《万卷堂书目》卷四杂文类著录《诗谈》一卷,题严羽著。这里略去了严沧浪或沧浪严先生几个字,所指的也应就是正德二年刊本。
3.正德十一年刻本始有诗话之名,命名者为胡瓊
最早将《诗辩》等五篇论诗著作命名为诗话的是正德丙子(十一年,1516)序刊本《严沧浪诗话》(阮元《天一阁书目》中著录为《沧浪诗话》)。此本卷首有胡瓊序云:
国朝少师西涯李公,尝称严沧浪所论诗法,谓其超离尘俗,真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说,未尝有失。余因取其集读之,信然。虽然,在宋儒已称其诗宗盛唐,自风骚而下,讲究精到,而近时河阴和君亦谓其《诗辩》等作,其识精,其论奇,其语峻,其旨远,断自一心,议定千古,至于指妙悟为入门,取上乘为准则,陋诸子为声闻,评辩考证,种种诣极,则又知沧浪之深者乎。余窃爱其“诗有别材”一段,尤为知作诗之妙,得性情之本,其他则前辈或多异同,未之敢复辩也。余愚且陋,学诗数年,病未知其要,晚于沧浪之论,欲取则焉。因意海内学诗之士或有同情者,迺独取其《诗辩》、《体》、《法》、《评》、《证》诸篇,正其讹而传之,总其名曰诗话。若夫全集,则已梓之开封郡斋云。时皇明正德丙子岁孟春望赐同进士出身知慈溪县事延平胡瓊序。
胡瓊,字国华,福建延平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由慈溪知县入为御史,历按贵州、浙江。其序刻严羽论诗著作,即是在慈溪知县任上。胡瓊在序中所提到的开封郡斋刻本就是正德八年王蒙溪刻本。这个刻本有和春序,胡瓊序中所说的“近时河阴和君亦谓其《诗辩》等作”云云正是和春序中语。胡瓊在序中说,“迺独取其《诗辩》、《体》、《法》、《评》、《证》诸篇,正其讹而传之”,这清楚地表明,他所序刻的《严沧浪诗话》是从全集本中分离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从《沧浪吟卷》中分离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一个单行本。在这篇序文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总其名曰诗话”一句,这句话表明,是胡瓊把《诗辩》等五篇给予了一个总名叫《严沧浪诗话》。这正表明,在胡瓊刊本之前,没有一本题名《沧浪诗话》的本子的。因为如果胡瓊之前,本来就有《沧浪诗话》,他不可能会说自己名之曰诗话的。胡瓊的这段话正可以与张以宁序黄清老诗集中称严羽论诗著作为“诗法”、杨成刊本《诗法》的编者称《严沧浪先生诗法》相印证。
自正德胡瓊刻本之后,题名为《沧浪诗话》的单行本就多了起来。最著名的有毛晋《津逮秘书》本《沧浪诗话》,以及《说郛》本《沧浪诗话》。从此以后,《沧浪诗话》遂成定名。
五、关于《沧浪诗话》的一些问题的重新认识
1.对《诗人玉屑》本与通行本两个文本价值的评估
关于《沧浪诗话》的文本,在《诗人玉屑》本与通行本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在郭绍虞先生《沧浪诗话校释》中已经被清楚地揭示了出来。根据郭绍虞先生的说法,《沧浪诗话》原本有个宋刻本,即是所谓的咸淳四年序刻本,这个刻本已不得见。现在的通行本都是源自于明刻本,但明刻本“经过窜改,错误较多”[2] (《试测〈沧浪诗话〉的本来面貌》),而《诗人玉屑》本作为《沧浪诗话》的宋刻本,保存了《沧浪诗话》的原貌。所以郭先生校释《沧浪诗话》,特重《诗人玉屑》本,称其在“先后排次及各条分合之间,亦以《玉屑》为主,正今传各本之误”。[1](《宋诗话考·沧浪诗话》)但是,根据笔者的考定,并不存在郭先生所谓的《沧浪诗话》的宋刻本,而元刻本的《沧浪诗话》他也没有见过,他不知道明刻本乃是从元刻本而来,其所谓明刻本的“窜改”“错误”之说就只是臆测,不可据信。(注:黄景进先生已经据元刻本指出郭说的问题。见《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第38—39页。)这样,就存在着一个问题:《诗人玉屑》所收录的文本与通行本的文本究竟哪一个更可靠呢?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和评价严羽的诗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诗人玉屑》本与通行本的差异主要是在《诗辩》,两者不仅文字上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而且在结构顺序上也有着重大的不同。这两个本子何以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沧浪诗话》为严羽生前所撰定,既然为严羽生前所定,那么,《沧浪诗话》的文本就应该是唯一的,就是严羽《沧浪诗话》定稿时的文本。但是,严羽本人生前并没有作《沧浪诗话》一书,并不存在《沧浪诗话》的定稿。这样,文本的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
据笔者考察,《诗辩》篇还不止以上两个文本,还有第三个文本,那就是《夜语》所引用的文本。我们在前面说过,范晞文《夜语》曾引用过《诗辩》的文字。《对床夜语》成书虽晚于《诗人玉屑》近二十年,但却大大早于通行本,其所引的文字对我们考察《诗辩》的文本情况具有特殊的意义。这里将《对床夜语》所引的文字抄录如下,并与《诗人玉屑》及通行本对勘。
严沧浪羽云: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玉屑》及通行本此处有“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三句,盖为《夜语》略去)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之悟(通行本无“之悟”二字),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陶、谢至盛唐诸公(“陶、谢”,《玉屑》及通行本皆作“谢灵运”),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严沧浪又云:诗有别才(“才”,《玉屑》及通行本作“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而古人”二句,通行本作“然非多读数,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诠者(诠,《玉屑》作“鉴”),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诗人,通行本作“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寻,《玉屑》、通行本作“求”)。故其妙处,莹徹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影,《玉屑》及通行本作“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通行本于“诸公”后有“乃”字),以文字为诗(通行本“以”前有“遂”字),以议论为诗(通行本此句在“以才学为诗”后),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通行本无此句),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玉屑》及通行本于此句后尚有“且其作多务使事”一段,盖范氏此处为节引之故)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
通过将《对床夜语》所引的两段文字与《诗人玉屑》、通行本对勘,我们发现,这两段文字更接近于《诗人玉屑》,而与通行本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那么,《对床夜语》所依据的文本是不是直接抄录《诗人玉屑》而来呢?也不是。因为《对床夜语》的文字与《诗人玉屑》本也存在着差异,比如《夜语》“诗有别才”,《玉屑》及通行本作“材”;《夜语》中“陶、谢至盛唐诸公”一句,《玉屑》本和通行本就作“谢灵运至盛唐诸公”;《玉屑》本“镜中之像”,在《夜语》中作“镜中之影”;《玉屑》本“无迹可求”,在《夜语》中作“无迹可寻”。其中,“陶、谢至盛唐诸公”一句,与《诗人玉屑》及通行本差异甚大,关系到对陶渊明的评价问题,不是一般的文字歧异。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对床夜语》所引的文本不是直接抄录《诗人玉屑》而来,而是来自其所见到的《诗辩》的另一文本。
由于《对床夜语》只引以上两段文字,所以我们无法对《对床夜语》所引文本的总体情况作出判断,但是就以上两段在文字上更接近《诗人玉屑》本来看,我们应该可以推断,《对床夜语》所引的《诗辩》的文本应非常接近《诗人玉屑》本。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流传在宋末的严羽论诗著作的文本可能就是《诗人玉屑》及《对床夜语》所依据的文本系统。
对于通行本所源自的黄清老校正本的文本来源,现在已不能确切地考知。这一文本是否得自其师严斗岩呢?我们固然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十分大。严斗岩本人并没有完整保存严羽的著作,甚至并没有保存严羽的著作。如果严斗岩保存了严羽的著作的话,何以李南叔录本仅存什一于千百呢?何以黄清老校本并没有更多地增补呢?如果严斗岩藏有严羽全部的论诗著作的话,黄清老何以还要“裒严氏诗法呢”,从其师那里直接刊印不就可以了吗?所以我们认为严斗岩顶多藏有严羽部分的论诗著作,或者根本没有保存。黄清老所得的文本有可能得自于当时流传的抄本。
由于黄清老搜集刊刻严羽著作的时代距离《诗人玉屑》的刊行已经有八、九十年时间,严羽的著作在传抄的过程中有被改动的可能,所以通行本的文本很有可能是被改动过的本子。而《诗人玉屑》本由于早于通行本,而且有《对床夜语》的印证,其可信度要大大高于通行本。
2.关于《诗辩》中结构顺序问题
在《诗人玉屑》所编入的《诗辩》中,是以“学诗者以识为主”一段开始的,而通行本以“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开端。这两种文本在结构顺序上的差异表面看起来无关紧要,实际上结构顺序不同,强调的重点就有所不同。如果以“学诗者以识为主”开端的话,那么全篇的中心在“识”字,郭绍虞先生作《沧浪诗话校释》,《诗辩》篇的结构顺序依据的是《诗人玉屑》,所以郭先生认为,《沧浪诗话》一书论诗,“关键在一‘识’字。《诗辩》开端第一句,‘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开宗明义,已极明显”[1] (《宋诗话考·沧浪诗话》)。如果是以“禅家者流”一段开始的话,则全篇的重心就是诗禅说。如果我们认定《诗人玉屑》的文本更加可靠的话,则关于《诗辩》的结构顺序就应以《玉屑》本为准。
3.关于严羽不知禅的问题
严羽以禅喻诗,但钱谦益、冯班等人则指责其不知禅。其最引起非议的是下面一段话:
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
钱谦益、冯班认为,声闻、辟支果就是小乘禅,而严羽把大历以还之诗比作小乘禅,而又把晚唐诗比作声闻辟支果,等于说声闻、辟支果不如小乘禅,这样就把声闻、辟支果独立于小乘禅之外。钱、冯二人据此认为严羽不懂禅。
但以上这段话与《玉屑》本在文字上有差异。在《诗人玉屑》中,“大历以还之诗”后无“小乘禅也”四字,根据这种文本,并不存在将声闻、辟支果置于小乘禅之外的问题。郭绍虞先生校《沧浪诗话》就指出了这一点,称“据《玉屑》则沧浪原不误”。元人诗法《诗家一指》曾引述《诗辩》谓“大历以还已落第二义,晚唐则声闻、辟支”,同于《诗人玉屑》。据我们对两个文本的考察,《诗人玉屑》更为可信,通行本的文本可能为传抄者所加。
4.关于“有分限之悟”的问题
《诗人玉屑》本有“然悟有浅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一段,其中“有分限之悟”一句,在通行本中作“有分限”,没有“之悟”二字。郭绍虞先生《沧浪诗话校释》从通行本,以为“之悟”二字为衍字,当代研究者皆从其说。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床夜语》所引的文字与《诗人玉屑》相同,这表明“之悟”二字并不是《诗人玉屑》本所衍,而是原本如此。根据通行本,悟的深浅有两种:一种是透彻之悟,一种是但得一知半解之悟。前者是严羽肯定的,后者是其所否定的。但是,依《诗人玉屑》及《对床夜语》的文本,悟的深浅就有三种:一是“分限之悟”,乃是有限度的悟,悟到一定的程度,但还不透彻;二是“透彻之悟”,乃是最高的境界;三是“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这种悟低于“分限之悟”。三者之中,“透彻之悟”最高,“分限之悟”虽低于“透彻之悟”,但高于“一知半解之悟”,严羽对其肯定的程度高于“一知半解之悟”。元人《诗家一指》引述《沧浪诗话》云:“禅在妙悟,诗道亦然。悟有三:有透彻,有分解,有一知半解。”这里所引在文字上并不准确,其所谓“分解”就是上文所谓“分限”,但是其所谓“悟有三”,正与《诗人玉屑》本相合。
以上文字《诗人玉屑》本与通行本哪一个更合理呢?一般都认为通行本为正确。但笔者却认为《诗人玉屑》本更合理。这不仅是因为《诗人玉屑》的文本有《对床夜语》及《诗家一指》的旁证,而且从文意上来说,也以《诗人玉屑》本更合理。严羽论唐诗,盛唐高于大历,大历高于晚唐,则唐诗至少有三个等级。如果悟的等级只有两个即透彻之悟与一知半解之悟的话,要么是“透彻之悟”,要么是“一知半解之悟”,只有两个层级,这样就不能用来说明唐诗的三个层级。而照《诗人玉屑》本,则可以说盛唐是透彻之悟,大历是分限之悟,而晚唐是一知半解之悟。所以《玉屑》本当更合理可信。
5.关于“透彻之悟”的问题
《诗人玉屑》本及通行本有“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一句,但在《对床夜语》中却作“陶、谢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照前者,透彻之悟不包括陶渊明,而依后者,则包括陶渊明。这个差异关涉到对陶诗的评价,特别值得注意。《诗评》说:“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句。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根据这种说法,晋以后诗与汉魏诗有着明确的分界。正是因为汉魏古诗气象混沌,所以《诗辩》说:“汉魏尚矣,不假悟也。”在他看来,陶渊明诗已不属于气象混沌一类,所以不属于“不假悟也”的一类。如果他说谢灵运至盛唐诸公诗是透彻之悟,那么陶渊明既不属于“不假悟也”的一类,也不属于“透彻之悟”的一类。而在他看来陶诗又高于谢诗,所以更不属于第二义之悟。那么,陶诗在他的诗禅说中就无处安身。如果按照《对床夜语》的文本,则陶渊明与谢灵运都属于透彻之悟的一类。所以在笔者看来,此处《对床夜语》的文本更合理。
6.关于《考证》是否为严羽作的问题
《沧浪诗话》中有《考证》篇,此篇在元刻本的目录中作“诗证”,而在卷内则作“考证”。此篇在《诗人玉屑》中并没有标明为严羽作。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沧浪诗话》为严羽生前编定,《考证》篇既然收入通行本的《沧浪诗话》中,则其为严羽作是无疑的。但是,现在我们考定《沧浪诗话》汇辑于元代,那么就有一个问题:黄清老所编入的《考证》篇是否为严羽所作呢?由于汇辑者黄清老是严羽的再传弟子,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黄清老把《考证》作为严羽的著作是有根据的。但是,也不能绝对排除《考证》篇是来自于《诗人玉屑》的可能性。如果其文本确实是来自《诗人玉屑》而又没有直接的证据,那么《考证》是否为严羽作还需要进一步确证。
7.关于《沧浪诗话》的地位及影响问题
《沧浪诗话》在诗歌批评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地位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其所提出的问题的理论价值及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在诗话发展史上的地位。学术界认为,诗话体发展到《沧浪诗话》,从以资闲谈的笔记体发展成为严肃而有体系的理论专著。学者们论证《诗辩》等五篇如何互相关联,构成一个严密的系统。但是,原本并不存在一部《沧浪诗话》,《诗辩》等作五篇原来只是单篇的著作。这五篇著作中唯一可以认定为严羽亲定的只有《诗辩》一篇,而从体裁上说《诗辩》乃是论辩体,而不是诗话体。像《诗法》、《诗评》原本是否独立成篇也还不能确定,也许是严羽与其门弟子谈诗的记录,为其门弟子分类汇集成篇。由于严羽本人并没有作诗话的意识,由于原本并不存在《沧浪诗话》这部诗话著作,因而我们就不能把后人汇辑而成的《沧浪诗话》放到诗话体的发展史中来评价。这就像《带经堂诗话》为王士祯弟子所编,我们不能说这部诗话如何有体系性,在诗话发展史上应占什么地位,因为王士祯并没有作这部诗话。如果后人汇辑前人论诗著作而成的诗话也可以放到诗话发展史中来评价,那么我们今天辑苏轼论诗语编成《东坡诗话》也就可以放到诗话史中去评价。这样的话,诗话史就成为一笔糊涂账。事实上,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元人并没有把《诗辩》等五篇视为诗话,而是将这五篇论诗著作当作诗法来看待的。黄清老的密友张以宁称这些著作为“诗法”,就是如此。张以宁是个进士,又是个有相当名气的诗人,他的看法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元代汇编诗法的人也称“严沧浪先生诗法”,而不称诗话,也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到了明代,人们才将这些著作视为诗话著作。根据以上所说,笔者认为,学术界所谓《沧浪诗话》是一部有严密理论体系的诗话著作的论断就不能成立,所谓《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发展的总结及高峰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这样以来,诗话发展史就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现在一般认为,严羽《沧浪诗话》自产生以后对后来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上在宋元时代,严羽的影响并不很大。当时尽管有上官伟长、吴梦易、朱叔大等人继承其诗学,但影响只局限于邵武一带。魏庆之《诗人玉屑》收录严羽著作,但这并不表明严羽在宋末诗坛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因为魏庆之是福建人,而其《诗人玉屑》对闽人的著作收录独多,方回在《桐江集》卷七《诗人玉屑考》中批评说“闽人有非大家数者,亦特书之,似有乡曲之见”。《诗人玉屑》收录严羽诗学著作,在相当的程度上也与这种地缘关系有关。尽管《对床夜语》也引述了其诗论,但这也并不能证明他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著作在宋末就已经散佚得很严重了,《宋史》中也没有为他立传。在元代,虽有邵武诗人陈士元、黄清老诸人继承严羽的倾向,搜集严羽的作品,但就总体而言,严羽的影响并没有扩展到整个诗坛。从现存的元代的诗学文献看,除了福建诗人以外,元代诗人引论严羽诗学的人极少。只是到了明初,闽中十子继承严羽诗学,尤其是高棅的《唐诗品汇》,宗严羽之说,论唐诗分初、盛、中、晚,并大量引述严羽诗论,而此书为有明一代馆阁所宗,严羽的诗学才走出福建而影响整个诗坛。
本文蒙业师张少康教授审阅并提出重要修改意见,日本九州大学合山究教授、台湾政治大学黄景进教授曾在资料方面给予帮助,谨致谢忱。
收稿日期:1999-0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