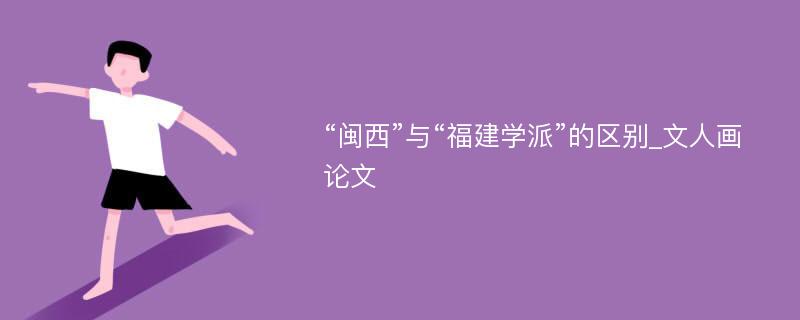
“闽习”与“闽派”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闽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福建绘画历史上有无“闽派”?文献上说有。但是,若认真追究,问题便接踵而至。如问,闽中画派,何人开派?何人传承?有何特征?流布状态又如何?这些都必须一一加以澄清,方可成一说法。
现有三则资料可供分析。
(1)《闽杂记》,成书于18世纪后半叶, 为从幕闽中的浙江人施鸿保所著。其文有曰:
闽中人才辈出,能诗能书能画,各有名家,惟各有派别。诗自徐兴公与曹能狎主词盟,后进奉为金科玉律,至今犹称“兴公诗派”。书以林处士宠为模楷,学书者千腕一律。而闽画亦然。写人物则用粗笔画居多;写山水则偏锋,粗则以墨水涂之,细则只求工致,毫无皴法。故以两浙三吴之派求之,闽中百不得一(注:清·施鸿保《闽杂记》(12卷),小方壶斋与地丛书抄第九帙,1878年。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
显然,施鸿保以为明清之际,闽中诗、书与画都各具地方特色,且异于浙派、吴派而自成一派。随后,他又谈到何泓(字郢生,福清人,生活在康熙、雍正年间)的山水画学董源,“气韵生动,皴法浑厚”。何泓曾游艺江南,访宋元书画名迹,“下笔俱能神似,是非奉闽派为圭臬者”(注:清·施鸿保《闽杂记》(12卷),小方壶斋与地丛书抄第九帙,1878年。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这是游离于闽派之外的闽籍画家。我们从上文中对何泓画风的归类性描述,亦可将其视为对“闽派”的反证之例。
(2)《山静居画论》,成书约在1795年前后, 作者为浙江石门(今崇德县)人方薰。书中有言曰:
人知浙、吴两派,不知尚有江西派、闽派、云间派。大都闽中好奇骋怪,笔霸墨悍,与浙派相似。(注:清·方薰《山静居画论》。)
以上两家说法出现的时间很接近,虽言称闽派,均未提开派及传派人物,只用一种模糊的大致分类法,与浙、吴两派在品味上进行排比区分。施鸿保对闽中画派讲得具体些,也不可能象他言及诗坛与书坛那样,举出象徐囗(1570—1642,字惟起,又字兴公,闽县人)与林宠(字异卿,闽倒人,生活在清初)等人作为诗派与闽书派的旗帜,也举出闽画派的领袖人物。闽中画坛“闽派”的提出,以施鸿保为先。在他之前,有张庚对闽中绘画总体特征的评述,他归纳为“闽习”。
(3)张庚,字浦山,浙江秀水人,通文史,擅画。 其有关闽画的论述有两处,分别见于《国朝画征录》与《浦山论画》。《国朝画征录》,初刊于1735年,对闽籍画家上官周有几句评语,如“有笔无墨,尚未脱闽习也;人物工夫老到,亦未超逸”。(注:清·张庚《国朝画征录》。)张庚此书以亲见作品为据,执论以华亭派为正宗,对“闽习”也未展开论述。但在《浦山论画》中,谈论明末清初华亭派以外的诸地方流派时,以浙派和松江派为主座标,其余参之,论之较详,对闽中绘画的风格也给予定位。如,
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是派也,始于戴进,成于蓝瑛。其失盖有四焉:曰硬,曰板,曰秃,曰拙。松江派,国朝始有,盖沿董文敏、赵文度之习,渐即于纤、甜、赖矣。金陵之派有二:一类浙,一类松江。新安自渐师以云村见长,人多趋之,不失之洁,即失之疏,是亦一派也。罗汉中崛起宁都,挟所能而游省会,名动卿士夫,学者于是多宗之,近谓之西江派,盖失在易而滑,闽人失之浓浊,北地失之重拙。之数者,其初未常不各自名家,而传仿渐陵夷耳此。(注:清·张庚《浦山论画》。)
此文对他方画家以“派”名目,而对闽中画家只说“闽人失之浓浊”。此“失”与谁相比?当然参照的标尺是董其昌倡导的文人画。这“失”,说透了就是文人画家常言的习气问题。所谓习气,是与士气相对的批评术语。士气者,体现为干笔俭墨,属文人画的审美品格;习气者,体现为工笔重色,属画人画的审美品格。
张庚的《国朝画征录》与《浦山论画》先于施鸿保的《闽杂记》和方薰的《山静居画论》约半个世纪。可见,“闽习”之说在前,“闽派”之说在后。闽习,在当时就有两种说法:一在品鉴趣味层面上使用,如习气;二在画家类群的区分层面上使用,相同于闽派,或者,更确切些,指的是一个区域性的画家群,有相同创作倾向或共同拥有一个传统的画家群。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那种地方宗派。在“闽习”与“闽派”两个概念出现的时间差中,我们必须注意到黄慎的存在。黄慎之前,闽习所指的是福建绘画的泛传统。雍正年间(1723—1735)黄慎在扬州求诗、书、画的统一发展,为文而脱俗,批评界仍有人说他“未脱闽习”。若干年之后,黄慎成了一位大师,后者相继仿之。闽中画坛的风气也有了改变,“闽习”便不见有人再用,而用“闽派”。这个“派”就有了“school”的定义。
二
何谓福建绘画上的泛传统?
我们可试图将其描述为一个具有两极反向作用的精神实体,在一个共有的价值标杆上运行。两极,即温和宽厚的写实面与奇崛愤抑的纵情面都各有一个活动的原点,它们相逆相构。那么,共有的价值标杆上则是技艺与情思的双刻度。因是两极,它们有不兼容的特点,又因为拥有共同的价值标杆,它们又被包容在一起,在共同地域的历史文化作用下,具有一种协调性能。这种精神实体的图式,是揭露现象事实背后的东西,即本质的描述。回到历史现象的表层,我们就能看到泛化的结果。
泛化,指称传统作为实体之外部边缘的模糊与散漫。它的内部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轴,就是两个活动原点的位置也时常变换,且各自的作用力不等。尤其在历史的运动过程中,两个原点的周围均会出现外抛的离心现象。两者碰撞在一起时,运行的线纹就会出现因干扰产生的波动与紊乱,运行物就会偏离原有的线路而进入他方的运作场或因两者的相互作用力另寻途径。因此,边缘是最活跃的,时常会有新的结合或分化。经过一定的时间,这种泛化的离散的表现也会影响运动中心区的结构状态。
以上关于泛传统的图式描述,基本上沿用“太极图式”的思路,它很能说明从宋代直至清初福建画坛的主流现象,也能说明其中蕴涵的一种独有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取向。历史上,福建绘画比其他发达地区要晚整整一大截。唐代,中国画的写实一面已发展到高峰,而福建的绘画才进入准备阶段。宋代,国内出现僧人与文人的写意画并迅速地发展,出现了好几位大家,而福建的文人此时也以最积极的姿态参与绘画。许多著名的福建文人和诗家,或直接作画或点评画作,甚至著述书画谱录。这在福建的历史上仅此一例。如僧惠崇、陈容与入元的南宋遗民郑思肖,在历史上都是名家。朱熹、刘克庄都有画评或题跋,蔡京则参与主持编撰《宣和画谱》。宋代的福建职业画家也不少,有的还召入画院,如大观年中的费道宁,宣和年间的徐知常。宋代的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各有特色又相互影响。如对“形似”的好尚(宋代文人画家都尊重写实技艺。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来看待宋代文人绘画)与对“人意”的追求,是两者相通的一面,此见《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之言:……有以兴起人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注:宋·蔡京等编纂《宣和画谱》。)
这种“夺造化”与“移精神”正是福建绘画传统的精神内容,在表现形态上,福建绘画过于多样。有细工妍丽的,有平淡天真的,有率情恣意的,有绵延遒劲的,不一而足。
明代是福建绘画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是福建职业画家大展身手的时期,也是文人画家分道扬镳的时期。福建的绘画是在明代成熟的,它的那种泛传统的特征也是在明代形成的。宋代是一个铺垫——“文”的铺垫。随后,明代是“艺”的成熟。这个成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皇家办了绍兴画院。宋亡,皇族南逃福建,是否亦有众多宫廷画家与民间职业画家避难于闽?(注:聂崇正《明代宫廷中何以浙闽籍画家居多》,《美术观察》1997年第4期,第48页。)尔后,薪火相传,在福建民间将宋代院体的写实画风传播开来?这仅仅是一种推论。事实是,明朝初年,征召画家供奉内廷,浙江与福建籍的画家就是特别多。据现有资料统计,明太祖洪武至神宗万历年间,福建值殿供奉的画家有22人(注:穆益勤《明人院体浙派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8月版。)。而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5 )有边景昭、边楚芳、边楚善、上官伯达、方昌龄、解秀; 至宣德十年(1426 —1435),则有李在、周文靖、周鼎、黄济、林景时、郑时敏、郑克刚等7人。其中,边景昭、李在、周文靖、黄济等都有相当高的水平, 但各自的风格取向差异也大。边景昭主“静”,为花鸟画家;黄济主“动”,为人物画家。静者,线卧墨寂,平铺直叙;动者,线形飞扬,曲折变化。李在与周文靖都擅墨笔,善写善皴兼备水墨,承南宋院画马远、夏圭的路数。李在特别灵巧,特别善变。以山水论,就有细润与豪放之二格体,分别宗以郭熙与夏圭、马远;画人物,也法梁楷或贯休。(注:穆益勤《明人院体浙派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8 月版,第31—32页。)所以,尽管他们技艺高超,终因在中国画坛上未能独树一帜,而无法成为一代宗师。正是因为如此,闽中诸多大家,各有承继,各领风骚,形成一个多元共存的泛传统局面。
泛传统也是传统,也存在着一个共同规范的问题,那就是突出“用笔”,讲究笔线、笔力、笔味。水墨画出现后,“用墨”异军突起,又逐渐与“用色”的观念并置,甚而超乎其上,但“用笔”仍占主位。中国画的分类,有一流行的说法,即“工笔”与“墨笔”之分。工笔者,当是唐宋之传统,也是历代画家相承而完善的旧模式;墨笔者,或称意笔者,是唐宋时代的产物,是禅宗与文人参与绘画的结果,历元而至明,成为一新传统;再至明末,经董其昌提倡后,又变成近现代画坛上中国画的正统。明代的院体画家和职业画家也画意笔,尤以戴进等人著名。因戴进是浙江人,史称浙派。闽中诸家,因风格相近,多被归入此派。浙派的画,到明末被一些批评家贬为“习气”,即作家气,也因为这用笔的问题。什么问题?一则笔刚且率意,不柔;二则重线,重勾斫皴擦,不重墨染,前者被认为不具平和之气,后者被认为有笔无墨。明末福建几位有影响的画家,如万历年间入画院的吴彬,职业画家郑文林,流寓金陵的肖像画家曾鲸,都以工笔见长。有的虽也画一点意笔,也以墨染,但均有一定限度。从其留存于世的作品中,确能印证上述特征。
明代福建也有文人画家,但不如宋代那般突出。如明永乐初以布衣召入翰林为待诏的高秉礼,号称闽中十才子之一,为诗人兼画家。还有林鸿诗派的诗人赵迪,《闽吕十子诗》的编者袁表等人都擅画。诗人郑善夫(1485—1524)的山水松石之画。被人评为“师法古人,不落画家蹊径”。评者徐囗是诗人也是书家兼画家,他还著有《闽画记》,这是对福建绘画进行全面论述的第一部著作,是一部史录与品评相结合的著作。其成书于17世纪初,今已失传,原文多见录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的《闽中书画录》(黄锡蕃编撰)和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闽画纪》(林汾贻、林家溱编撰)。徐囗对书画的看法自然与其重振风雅的诗文主张相近,与文人玩味笔墨,追求清婉的审美趣味相谐。如记叙文人画家的画风来源时,总不时地说某某人“学董北苑、米南宫”或“摹仿文待诏”等。他以学沈石田、高房山为不俗,评画之语常用“天趣”二字。但是,上述文人画家的作品均未见传世,故无法多言;只有晚明的张瑞图与黄道周尚有作品留存,尚可对证。张瑞图和黄道周的书名更为显著,画不多,均是墨笔写之。以画风辨,绝不同于职业画家。若论闽习,此类画家应当排除。
闽习,是在明代福建职业画家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普遍的风格,是一种地域性的历史沉积,其中蕴含着较为浓厚的人文品质。它既有民间职业画家对“技艺”的执着,又有海边人的开阔胸襟和山地人的倔强个性。闽习,很难用某种规范的术语加以标定。只有当我们回到福建绘画自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回到明末国内各个地方画派蓬勃兴起的历史格局上,一纵看一横比,我们才能把握福建绘画的传统所在,才能言说“闽习”。
三
为什么说黄慎是闽派的旗帜?
从明亡到清代康熙年初期,即浙江人施鸿保与方薰分别都提出“闽派”之前,时间不过几十年。这期间,福建绘画相对沉寂,或者说是高峰前的过渡时期。虽然文人画家仍聚集在福州,如许友介等人;但职业画家依然十分活跃,如福州地区的谢天游、郭鼎京,莆田人郭巩,漳州人陈惟邦,闽西人李森、李良佐等人。据说,李森在清顺治年间廷试得第二(注:《宁化县志》)。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福建绘画出现了又一个高峰,许多职业画家工写兼顾,诗文相通,尤以闽西三杰为最。这三杰便是上官周、华喦和黄慎。
上官周(1660—1750?),清代前期闽西画家的代表,也是福建画史上很有代表性的画家。但他还不足以作为闽派的开派人物。他的画基本上延续福建职业画家工笔绘画的传统,特别是工笔人物,其线延绵遒劲,将人物的类型特征把握得相当好,神亦好,可以说是集大成者。他的山水画上承明代李在一路;晚年的写意人物画与黄慎相似,但略为简疏。他的工笔画成就是黄慎所不及的,一本《晚笑堂画传》足资证明。上官周的活动多在闽西一带,晚年出游广州,名声传播岭南。
华喦(1682—1756),也年长于黄慎。他于1703年离家,寓居杭州,又游历诸多名山,往返扬州、杭州之间,最后客死他乡。华喦号新罗山人、白沙道人、布衣生、离垢居士等,他善写诗文,对人物、山水、花鸟与走兽等诸画种皆通;画法远师李公麟、马和之,近及陈洪绶、恽寿平与石涛。他的画多见意笔,常以水墨淡彩涂之,松秀明丽,空灵骀荡,但又非大写意、大泼墨之类,实属笔致秀婉一路,颇具文人画风。有的论者认为他的画与恽寿平可并驾齐驱,尤其是他的花鸟画,对清中叶以后的画坛影响甚大。华喦的画。比之上官周更靠近文人画,这一点也是黄慎所不及的。他的创作实践突出体现了“职业画家文人化”这一时尚。查慎行说:“上官山人今虎头(顾恺之)”,张庚评华为“脱去时习,而力追古法,不求妍媚,诚为近日空谷足音”(注:清·张庚《浦山论画》。)。
黄慎(1687—1770?),号瘿瓢子、东海布衣等。黄慎早年学画于家乡,受上官周影响很大。尤其是工笔人物,画神仙故事、历史传说与文苑逸事等,也学作诗文。乾隆时,浙江德清徐氏,号清凉道人,其《听雨轩笔记》(成书于1791年)中有一段趣话,言及黄慎师从上官周。文中先说黄慎学人物、花鸟山水、楼台等,尽得师传。但与师之作相比,自觉难以与师争名。故自勉自励,废寝忘食又作画累月,出新作。“其画初视如草稿,寥寥数笔,形模难辨,及离丈余视之,则精神骨力出焉”(注:清·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这里谈到黄慎前后两个阶段的画风变化。尽管变化的原因不是由于吴人的歧视(如谓之“闽习”),而是自己想超越上官周。黄慎的超越点也是他的蜕变点,以书入画,变工为写。这个变至关重要,它使黄慎跻身中国画坛大家之列,为时人所认可,也因之将福建绘画推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完成了职业绘画和文人绘画在题材内容、笔墨形式及表达个人情感诸方面的融合,或者说是完成了文人画风对职业绘画的改造。在此,我们暂不追究黄慎与上官周是否为师徒关系(注:参见丘幼宣《“黄慎少学画于上官周”质疑》,《美术研究》1 985年第4期。)。尽管清凉道人说此事系听沈益川游闽归后所述,可其对黄慎笔法画风的变化,阐述相当到位。历史上对黄慎或褒或贬的评价都集中在这一点。黄慎笔法的变化是一个交界点,黄慎因为这点成为两面性的人物。清代的批评家们往往站在文人绘画的立场来贬斥黄慎绘画中的“作家习气”,而肯定黄慎变工为写之举,使其名满天下(注:清·钱湄寿《潜堂诗集》卷6。)。 历史却还给黄慎一个公道,我们不仅看到黄慎的画在当时能“雅俗共赏”,而且以“变革”言,黄慎至少在福建的画坛上开启一代新风,为后辈所师法。
黄慎画风之变与闽派的开创关系十分密切。首先在时间上,黄慎成名于扬州,时为雍正年间,“登莱间人极重其画”(注:清·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52。)。我们再对现存的落有年款的黄慎书画作品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在雍正年之前,未见粗笔写意,也未见草书。作于雍正四年(1726)的《花果册》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意笔画(注:参见陈勤宁编《黄慎书画传世作品简目》(初稿),《宁化文史资料》 第 8 辑,1987年10月,第96—125页。),黄慎的人物大写意出现得更迟。 雍正期间是黄慎变法的时期。施鸿保有关闽派的说法,当在雍正之后的乾隆年间,按理说,他应当知道黄慎的书画成就,为什么不能象他谈论闽诗派与闽书派均言开派人物那样,也推举黄慎为闽画坛的主盟者呢?我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在福建的诗界与书坛,对领袖人物都有定论,画界没有,他不便擅言。二是因“闽派”之义近于闽习,贬意甚之,闽中名家唯恐避之不及,谁愿担纲或为头目?黄慎纵然画名显著,影响甚广,习者亦众,他不敢也不愿意别人将他奉为闽派之首。三是施鸿保“以两浙三吴之派求之,闽中百不得一”,当然他无所发现,只见流风所及。我们现在谈“闽派”,是接过这一历史的话题,理清福建绘画历史发展的脉络。我们会发现雍正朝不仅是黄慎绘画历程的一个转折,也是福建职业画家整体风格转向的一个重要时期。
其次,在这场变革中,黄慎个人的努力和成就奠定了他在闽中画坛的地位。关于他这“变”的努力,有嘉庆、道光年间的扬州人谢坤之言:“(黄慎)初至扬郡,仿萧晨、韩范辈工笔人物,书法钟繇,以至模山范水,其道不行。于是闭户三年,变楷为行,变工为写,于是稍出有一倩托者。又三年,变书为大起,变人物为泼墨大写,于是道之行矣。”(注:清·谢坤《书画见闻录》。)显然,当时变工为写是一个大问题,它关系到“道”之行与不行。谢坤对黄慎画风之变的看法固然有其文人的局限性与片面性,也许在个别时间概念上,如“三年”之说可能会有出入。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谢坤的说法。因为他的批评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标准;而无论怎样,黄慎的创作也不可能无视时代的风尚。他走出闽山闽水,先变书法,再变画法是必然的。可他早年的工笔造型基础及闽人固有的文化心态必然导致着这种变化的方向与特定的性质,即职业绘画与文人绘画在审美趣味和笔墨形式上相融合的性质。这在黄慎的写意画中表现得很具体,尤其是山水与人物,既不用大泼墨,也不用淡墨轻轻地罩衬着一种很平和的线;而是跌宕起伏,粗笔重墨,极讲技巧,极为率意。至晚年,黄慎以狂草笔法作衣褶,画树石点苔,“横涂直抹气穹窿,不与人间较拙工”(注:清·黄慎《(米点山水图)题画诗》。此画现藏福建省宁化县文化馆。)。黄慎画风之变根本上是笔法之变。由工而写,亦笔亦墨。关于他的用笔,胡松年和窦慎都说得十分贴切到位。邵氏在《古缘萃录》中说他“用笔奇峭,取境古逸,虽非正宗,自写一种幽僻之境。”窦氏在《国朝书画家笔录》中说黄慎“笔法纵横排奡,气象雄伟,为时推重”。黄慎写意笔法与他的草书笔法十分一致,很具个性特征,后学者不少。
再其次,便是黄慎变法成功之后,回闽周游各地,对福建画坛产生了直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乾隆初年(约1737—1750),黄慎从扬州挈妇奉母,返回家乡。回乡后,又在闽省内地漫游鬻画,并授徒传艺,足迹遍及长汀、沙县、南平、福州、古田、建阳、崇安、龙岩、南安、厦门等地(注:参见丘幼宣《瘿瓢山人生平梗概》,《宁化文史资料》第8辑,1987年10月。),收有门徒吴馨等人。这期间, 黄慎就是作画、卖画和交友,画作相当可观。据现存资料统计,有年款的作品为扇面三、册页五(其中有一为写生山水、诗书合册)、图轴二十七、横披一,总计36件。其中,以人物画居多,为16件,山水画10件,花鸟画10件(注:参见陈勤宁编《黄慎书画传世作品简目》(初稿),《宁化文史资料》第8辑,1987年10月。)。这不包括尚未发现者, 或无年款难以考订年代的作品,更不包括那些已失传的作品。黄慎靠他的画影响福建各地的画家,而影响最深的是他的意笔人物画与山水画。施鸿保说的那些“偏锋粗笔”和“粗笔钩画”就属这一类。生活在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康瑞,字喜子,铜山县(今属山东县)人,擅花鸟、山水、人物,画法超绝,笔格遒劲,一抹而就(注:参见《铜山志》和《诏安县志》。)。其画未见传世,从文字叙述来看,似为黄慎一路的画风。在他之后的沈瑶池,字古松,诏安人,生活在乾隆年间,善人物、花鸟,曾征召不至,以书画终,享年七十余。他的画有传于世,早年师同邑沈锦州,后学黄慎,特别是人物画,其笔墨极似黄慎。沈瑶池的画又影响了闽西南一带的画家。而近两百年后,仙游画家李霞与李耕又力追黄慎。李霞(1871—1938),字云仙,人物画家,仿效黄慎,以狂草笔法入画。李耕(1885—1964),字砚农,祖上两代均为民间画家,至李耕方大成。李耕的人物和山水画,笔墨奇拙直率,极似黄慎。徐悲鸿见之亦言:“有奇拙胜者,首推李耕君;挥毫恣肆,可追宗瘿瓢”。李霞、李耕的门生不少,有人称承此风气者为“仙游画派”,李耕是最主要的代表。李耕一度也曾自称为“闽中画派”(注:李耕曾落款自称“闽中画派”。闽中不是指闽省中部,而是指闽省。身为闽西人的黄慎,也曾在画面上自题“闽中黄慎”。),这不仅有地域之声明,也有画风师承之声明,声明自己为宗法黄慎的福建画家,声明有闽派的存在。
四
为什么闽派的问题在中国绘画批评史上总是不为人所重?原因有二。
一是在明末清初“文人画家职业化,职业画家文人化”的风潮中,福建绘画的整体发展水平滞后。个别有才分的画家多取向外发展的道路,游历他乡。如郑文林,被人视为“吴伟传派”(注:穆益勤《明人院体浙派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8月版。); 黄慎是众所周知的“扬州八怪”之一。这又使福建绘画的整体形象被肢解。明代福建绘画的主要成就在职业画家。明前期尚为人所重;明中期以后,随着文人画家地位的提升就被贬斥一旁;明末,情况就更糟。董其昌建立了一套文人画的批评标准,导致一场热闹又单调的讨论,所谓热闹,是今天说这派,明天道那派,大多标以地名,是中国绘画批评史上关于地方画派问题讨论的热点时期;说其单调是指绘画批评标准的单一与理论上的苍白。在这种形势下,福建画坛的“行家作派”就被贬为“闽习”。当历史推进到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文人画的理论和实践又有了发展,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裂变。特别是黄慎立足画坛的“扬州时期”,中国画坛正是经验性的个体精神展开对先验性的集体意识的批判。一时求奇、求拙、求险、求放成风,甚而求俗,此俗,非流俗与庸俗,乃不避技艺,直面人生,不矫情,不做作,敢言“画之润格”,撕破文人“雅”的面纱。职业绘画中的许多可贵的品格被重新确认。黄慎作为闽地画家的代表跨出变革的重要一步,为福建画家扯起一面旗帜。但是,对地方画派的批评已不再是理论的焦点。闽派之说,虽被人提起(如前述施鸿保等人),因不是时候,再无人进一步详加评说。史家多注意雍正间黄慎的“扬州时期”,而不注意乾隆初黄慎的“闽游时期”,将黄慎从福建画坛剥离出去。我们可以认为黄慎不只是一位地方性的画家,同时他也是国内画坛的大师。但是,为什么忽视他对福建画坛的影响呢?其实,这是中心区的权力话语作用,是淡漠边缘地区,无视非主流现象的必然结果。
二是清代中期以后福建绘画自身发展的多元性,使理论上“闽派”的认识产生歧义。本文之所以抓住黄慎这一历史性的人物,正因为他开创的一代画风使福建的绘画在那时期中国画坛上占一席之地,使之有别于其他地方画派。如果忽视了黄慎,我们很容易被其他纷乱繁杂的现象所迷惑。与黄慎同时或在他之后,承袭福建工笔画传统或接受省外其他地方画派影响的画家大有人在,而且发展的势头也不弱。他们足以混淆视听,形成一个驳杂的发展局面。福建绘画的多元性正是福建文化的边缘性使然,福建文化在历史上容易对汉文化中心区的各种文化现象作出反应,这是边缘文化向心力的一种表现。历史上的福建画家同样缺乏自信心,对本土有创意的画家也缺乏认同,甚而引援他方的画风以标异相抗。故而史家要确认一种独立的单元优势就显得十分困难。对清代福建画家的各种画风作综合判断,也不外三种:文人画风、职业画风与中庸道者。各方都有佼佼者。例如,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我们就要面对上官周、华喦和黄慎这三者。前两者对后辈画家都有很深的影响。另外,清后期“海派”对福建画家的影响又是一例。
因此,本文无意用黄慎和“闽派”涵盖清代的福建画坛,也无意褒扬一家而贬抑他家,也不想开展对文人画批评标准的批判;只力图通过历史的分析,对“闽习”与“闽派”的说法重新认识,并藉此考察福建绘画中文化品格的历史形成过程。我们可以认为福建绘画是一种亚文化现象,先天中有许多非精英的东西,但又被人放在中国精英文化的话语谱系中加以解读,就显出它的难堪、被动与不相合。这似乎注定福建绘画的自立会很艰难。黄慎的可贵就在于他把握了蜕变与自立关系中合适的度,独出一家;而谈论闽派的意义,也就在于寻找区域文化的特性和地方绘画历史发展的歧向性,在多维的向度中确认一种边缘地区的主流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