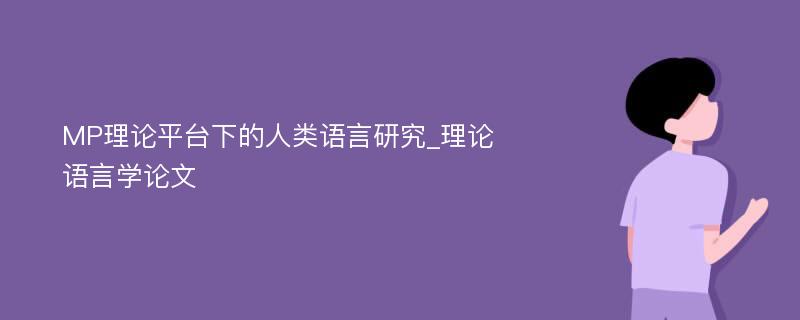
在MP理论平台上的人类语言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论文,理论论文,语言论文,平台上论文,M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MP的理论基础
以Chomsky为代表的生成语法学派探索人类语言的生物遗传属性(即普遍语法,以下简称UG)已有半个多世纪。“最简方案”(简称MP)在凝炼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为实现“Lenneberg科学梦想①”的科学事业开设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平台。之所以叫做平台,是因为Chomsky像一位负责任的科学老人一样,不厌其烦地告诫有志于在探究UG的漫漫长路上下求索的后生们,要实现这个科学理想,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MP没有关于UG现成的答案,只有一些可能的科学假想和线索,以及需要重新提出的研究课题。那么,Chomsky搭设这个研究平台的理论思想是什么呢?
用一句话讲,就是Chomsky的“本体最简主义”(substantive minimalism)的自然科学观。所谓“本体最简主义”就是把一切自然之物(如雪花、脊柱等)都看成是“完美的”,并把此作为一个科学信念和科学公理。从这个科学信念出发,科学研究的本质任务是回答为什么雪花、脊柱这些自然之物是完美的。比如,在回答雪花为什么是完美的问题上,Kepler(1611)这样回答:水分子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形成结晶体,众多结晶体的汇聚便是雪花。但是,在回答为什么作为自然之物的脊柱是完美的时候,情况要比雪花复杂多了。从脊柱的承重和支撑动物躯体的功能上看,自然这个造物主选用的是胶原纤维、粘多糖等有机材料和钙、磷等无机材料,而没有选用更为坚硬的金属材料。就此而言,脊柱这个自然之物是不完美的。如果坚持一切自然之物都是完美的科学公理,脊柱势必有使用这些不完美材料的完美理由。这就是,从脊柱和其他相关躯体系统相处的接口关系上看,用这些比金属松软的材料构成的脊柱是完美的。就是说,造物主在制造脊柱的时候让它满足了脊柱同其他系统的接口条件。
如果要把“一切自然之物都是完美的”这一科学公理运用到语言研究上,那么人类语言作为一种自然进化之物,其完美性也应表现在满足同其他系统的接口条件上,即使语言在交际功能上表现出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宁春岩2002)。因此,在MP理论平台上研究人类语言这个自然之物,就是要找到语言系统同其他相关系统的接口条件。Chomsky在他的MP中提出的许多具体设想都是关于自然万物完美这一科学公理的发挥和展示。我们应该从这个公理的角度认识语言系统的接口条件问题,在MP平台上参与生物语言学研究。
构成MP研究平台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是Chomsky(1986,1988)关于语言研究问题的五问:人类的语言知识是什么?这种语言知识是如何获得的?语言知识是如何运用的?人类的语言系统和其他生物系统有什么共同之处②?人类语言系统是如何进化来的?
这五个问题中的前三个问题是人们所熟悉的“柏拉图问题”。最后两问构成MP理论研究平台的核心课题,因此,也是认识、改造及批评Chomsky某些具体理论的根据和出发点。在MP之前(如“管约论”,简称GB),生成语法学派主要是在语言层次上寻找“普遍语法”,提出了一些具有强烈普遍语法色彩的UG原则(如“X-杠理论、比邻原则、空范畴原则、约束论、格理论、提取域条件、局部原则”等)。由于这些原则大多数基于“语言构件”本身,有点“不识语言真面目,只缘身在语言中”的味道。所以,Chomsky在MP这个平台上提出了要从语言“之下”层次上,即从第四问中所说的同其他生物系统的共同之处上寻找(Chomsky 2007)。为此,Chomsky并没有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而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假说。比如,在MP中最基本甚至是唯一句法操作“合并、经济性原则、计算上的效率”等都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初步回答。我们只能从Chomsky五问的意义上认识、使用、质疑这些系统概念,而不能把“合并、特征核查”等理论概念看成简单的技术操作,更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看成描写语言现象的新奇工具。
和其他科学领域研究相比,MP平台是一个很具有研究特色的地方。这就像Chomsky多次声明的那样,这里只有关于生物语言学的问题,没有关于生物语言学的最终回答。总之,MP平台是挑战人类认识智慧,发挥自我认识才能,尤其是“实现认识人类语言生物遗传属性”这一梦想的一个十分值得尝试的好去处。
二、MP平台上的研究课题
既然MP是一个研究人类语言生物遗传属性的平台,那么究竟有哪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应该在这个平台上开展研究呢?这里,我们不妨列举一些笔者认为是带有根本性的研究课题。关于语言系统同其他认知系统的接口条件问题。MP继承了GB关于句法系统有PF(phonetic form,语音式)和LF(logical form,逻辑式)这两接口的传统,继而认为MP句法也有两个接口,一个是同主司意义的“概念-意图系统”(简称“思维系统”)相接的SEM(语义),一个是同主司发音的“语音-运动系统”(简称“语音系统”)相接的PHON(语音)。由此而产生的第一个重要的语言学理论问题是关于这两个接口之间的关系问题。从逻辑上的可能性上讲,有三种:(1)像GB里的LF和PF是平行并列的一样,MP中SEM和PHON也是平行并列的。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占大多数,Chomsky也持这种看法。(2)PHON先同“语音系统”相接,SEM随后再同“思维系统”相接。持有这种看法的有Hinzen(2006)等。(3)SEM先和思维系统相连,后由PHON同语音系统相连。不同的处理方法,会引起众多相关操作技术上的不同。比如,什么是“语段”(phase)?什么是可以“拼读”(spellout)的单位?什么时候实行“拼读”?究竟有没有“短语”(phrase)?为什么“合并”的产物是“无序集合”(unordered set),而不是“有序的”?还有,为什么一定要先合并出无序的集合,再使用Kayne(1994)的“线性对应公理”,把无序集合线性排列出发音顺序,而不直接合并出有序的语音形态?
实际上,在两个接口的关系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在平行并列存在着的SEM和PHON两个接口的背后,是否有Descatres的二元论在作怪?可是,如果认为语言中的意义像“物种进化论”中的“威尼斯拱肩拱”③,就会摆脱本体二元论的困惑,就不会存在与一个声音系统平起平坐的意义系统,也不会有一个什么并列于任何具体人类语言之外的“思维语”(mentalese)的存在。由此,Chomsky关于“先验概念”(innate concepts)的说法可能要遭到质疑,至少应该给予重新定义。和这个哲学性的问题相关的句法操作问题是,在Chomsky的MP句法中CP和vP这两个“语段”的定义是基于命题的。这里似乎把命题看成是先于句法语段的概念。如果像Hinzen(2006)所说的那样“没有句法,则没有命题”,把句子看成是和命题共存的概念,Chomsky确定的语段依据也就不存在了。命题和意义一样也是依附于句子之上的“拱肩拱”了(Ning 2009)。
关于LF或SEM的表达样式问题,即什么样的句法输出才能满足语音系统,特别是什么样的句法输出能够满足思维系统的接口条件。GB中的LF表达式的确立,源于人们所熟悉的May(1977)关于量化成分的解释域的研究和Huang(1982)关于英汉特殊疑问词的解释域的研究。在May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抽象的“量化词提升”(quantifier raising,简称QR),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多个量词解释领域的歧义多解问题。而在Huang(1982)的研究中,看到汉语中原位不动的疑问词和英语中显性移动的疑问词在解释域上是相同的,且两种语言中的疑问词的解释域都可以用QR形式实现,因此推断出由抽象移动推导出来的LF表达式的存在。问题是,假设语言中没有量词解释域歧义的存在,而都遵循那种称作“同构”(isomorphism)④的解释原则的话,QR还有必要存在吗?如果QR不存在了,LF上的抽象操作还有必要吗?基于Huang(1982)的理由确立起来的LF还存在吗?如果,MP继续维持雷同于GB中LF的SEM,SEM需要重新定义吗?如果解释域歧义属于“边缘现象”,而不再是“核心语法”应该关注的现象,那么MP的SEM还要延续GB中的LF吗?有没有理由和可能把所有解释性的抽象隐性移动从整个句法操作系统中去掉呢?
关于词项及词项特征的问题。和GB中的词项一样,MP中的词项也是词项特征的集合。因此,这就涉及究竟有哪些词项特征问题。按照Chomsky的词项特征的描写,词项仍旧分成实体词项和功能词项两大类。功能词项在早期的MP中包括C,v,T,AGRs,AGRo,D。在现有的MP研究中,只剩下C,v,T和D了。Chomsky本人这个思辨过程本身就说明,究竟应该有多少功能词项,仍旧是MP平台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早期的AGRo是依据像巴斯克语(Basque)中有动词-宾语之间一致性标记这种显性现象而提出的。AGRs是根据英语等语言有主-谓之间时态、人称、数等语法特征一致性形态标记而确定的。可是在近期MP中,AGRs和AGRo这些成分消失了。这究竟是技术上的调整还是理论原则上的变化?再看现有模型中的v,这原本是基于Larson(1988)“VP壳形结构假说”提出的,显然又是基于短语结构确定功能词项的方法。因此,确定功能词项的原则到底是什么,一直是个大问题。第一种方法认为,功能词项具有UG性质,为所有语言所共有。如果一种语言中没有而其他语言中有,则可允许在没有的语言中是“抽象”的存在。AGRo对于英语来说就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种认为,功能词项有多少因具体语言的具体情况而定,没有必要追求语言之间的共有性。在基于形态词法的MP句法中,似乎应该采用后一种方法。当然,一种语言中源于形态词法特征的功能性词项(如英语的T),可否对应于另外一种语言中源于词汇的功能词项(如汉语中的“了”),也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在词项特征的描写上,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研究。这就是人们常用的N、V等符号所标注的到底是词项的什么特征:形态词法特征?句法特征?还是语义特征?如果像Baker(2003)等人所说的那样,这些我们十分熟悉的符号本来就是“彻头彻尾假定的”,那么我们习惯用了几十年的V、N等符号画出来的句法结构树到底变成什么东西了呢?由此引发出来的语言研究的根本问题也就太多了。
再就是涉及Chomsky所提及过和仍在使用的一些词项特征问题。比如,“语义有解特征、语义无解特征、强特征、弱特征”这些在早期MP研发阶段还常见的特征,在近期却被统一的“特征赋值”(valued/unvalued features)所取代,即“赋格特征([Assign Case])、结构格(structural case)、形态格(case)、语法特征(phifeatures,Gender,Number,Singularity/Plurality)”等。尤其在GB中起到巨大作用的“结构格”是不是词项的固有特征?Chomsky不止一次还用“人造之物”(artifact)这样的术语刻画词项特征。为什么?不得其意。如果真的引入这类词项特征,恐怕会对句法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再就是,动词小类(如与格动词、非宾格动词、作格动词等)、名词的可数/不可数、量化词等影响句法操作的特征需不需要纳入词项特征刻画的范围之内?还有,为什么Chomsky把时态和名词身上的语法特征看成是“语义有解特征”,而把与之相应的动词身上的语法特征看成是“语义无解特征”?区分有解、无解的清晰原则究竟是什么?某种特征一旦计入词项特征,是不是不能成为无效特征,而必须成为合并的条件?另外,关于有没有Chomsky所说的作为各种语言词项特征源泉的普遍语法词项特征库,这是不是无法证明或无需证明的假说呢?如果它是各种具体语言词项特征的累加和,这种假说还有什么普遍语法意义呢?
三、关于合并及其相关的问题
Chomsky提出的合并除了具有语言进化的假说意义外,当然具有句法操作上的技术意义。这里涉及在词项与合并之间的“操作算式”或“词项矩阵”、“合并”(外合并及内合并、序偶合并及集合合并)的产物是什么以及加标(label)在句法中起什么作用的等问题。
按照Chomsky在句法运算上的考虑,“操作算式”规避反复运算的“参考坐标”(reference set),“词汇矩阵”中加入了功能词项及某些词法特征(如动词的时态标记)使某些可以预测的有规律的形态变化在这里实现,以减轻词库的负担。这些做法看起来好像清晰明了,但是词库里哪些词项可以进到“词项矩阵”里接受运算?是随机任意的还是有条件的?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应该有哪些条件?对此,大多数MP研究者默认地把原GB中的语义选择、句法选择甚至赋格关系等作为进入操作的条件。但是,无论怎样,用来构成条件的特征都必须是固有的词项特征,不能随机定义,也不能循环定义。
还有合并的结果问题。按Chomsky的做法,合并是将两个词项合并成无序集合,然后把合并在一起的新成分用其中一个成分的特征加标。循环使用合并便得出一些加了标的、有句法层级的词项无序集合,然后施用Kayne的“线性对应公理”,以语段为单位拼读出去,形成语音的线性排列顺序,向PHON输出。对Chomsky的这些做法,在MP的平台出现了热烈的讨论。所讨论的问题,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在总的推导原则上,Epstein和Seely(2002,2006),Nunes(2004)和Fernandez-Salgueiro(2007)等人提出“全然推导观”(strong derivational thesis)。这种做法的突出特点是彻底放弃GB中的所有句法短语结构,取消了Chomsky关于CP、vP的语段以及依赖于句法短语结构的操作(包括“线性对应公理”)。而以Chomsky为代表的大多数MP句法研究者认为,虽然从词库到PHON和SEM之间没有任何中间句法结构性的表达式,但短语结构仍是推导过程中的基本单位。还有,近期兴起的Halle和Marantz(1993)的“分布式词法(distributed morphology)”句法模型、Borer(2005)和Di Sciullo(2005)的“并列词法”句法模型以及Beard(1995)的“项素-词素词法”句法模型对MP句法的整个系统做了重大的改变。
在合并操作上,Chomsky等大多数研究者始终坚持外合并产生的结果是无序的集合,然后通过“线性对应公理”,再把无序的集合(短语结构)展开排列成线性终端序列。在加标问题上,目前主流的做法是用N、v、V等传统符号。可是在MP的句法平台,这些符号究竟代表什么,是句法意义上的,还是语义意义上的,还是形态词法意义上的,十分值得讨论。Collins(2002)提出了一个“无标加标法”(to label without label),试图缓解在加标符号问题上遇到的困难。Boeckx(2008)认为加标的目的是实现参与合并的两个词项的非对称性,以保证其中一个的未赋值的词项特征(uF)进一步得到赋值。并把一切词项关系归并为同一“探针和目标关系”(probe-goal relation)。
和句法操作关系十分密切的还有关于什么是语段的问题,也就是推导到什么阶段执行拼读的问题。大多人认同Chomsky的做法,把CP和vP看成是句法中仅有的两个语段,在推导出vP和CP时,就像PHON输出推导结果。也有人(Femandez-Salgueiro 2007)认为不必依赖语段,可以随时合并,合并后即刻拼读出去。
关于限制条件问题。在MP的句法平台上,合并(包括内合并,即移动)既然是句法演算的基本操作,限制条件自然应该主要是关于外合并和内合并的限制。Chomsky为此提出的总的限制条件是遵循计算上的最大效率原则。世界万物无一不在计算,而计算无一不在遵循最大效率原则。运动的物体都会“算出”最省时省力的路线,人类语言中的符号运算也遵循这一法则。比如,词项的特征就像物理世界一样要能量守恒,在句法推导中不增加也不减少,移动遵循省时省力原则,遵循“局部性(locality)原则”等⑤。但是这些原则在语言中的句法操作中究竟是怎样实现的,仍旧是人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大多数关于外合并的限制源于GB句法中的选择性限制,有句法上的,也有语义上的。语义上的限制,比如“语义角色理论”,似乎问题不大。但是,句法上的限制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因为在MP的句法中,在词项插入之前并没有可用于句法选择的句法结构参考。另外,按照Chomsky(1995)的做法,经济性原则还体现在同一运算列式中的词项间不同合并结果间的竞争关系。外合并的结果要比内合并的结果要经济,需满足接口条件。全然推导论者认为,句法操作应该给出唯一的也是合乎经济原则的结果,不应该允许几个推导式间的竞争。总之,句法操作的限制条件在GB中是研究的中心课题,在MP这个平台上更是如此。
关于GB的UG原则和MP的UG的关系问题。GB句法研究中曾提出一些颇具普遍语法意义的UG原则。比如,有名的“比邻原则、空范畴原则”等。由于这些原则过于依赖语言结构自身,在MP中已经只具有描写上的意义(Chomsky 2004),属于现象学的概念。所以,在MP平台上探索人类语言的生物学属性,应该充分利用但不局限于GB中UG原则所触及的语言现象。“去伪存真”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了。GB的UG原则的“真”,首先在于它使用了形式句法的概念工具,在生成语法的框架中概括了众多人类语言的语言事实;可能存在的“伪”,是在各种复杂的语言事实面前表现出描写上的不充分性⑥。究其原因,除了这些GB的UG原则过于依赖语言结构,作为元语言没能和目标语言拉开足够的距离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UG原则的提出主要基于词法有形态变化的语言,而没能充分照顾到像汉语这样没有词法形态的语言的情况。
此外,由于GB中的UG原则参数同具体的UG原则相关,如,“中心词在前、在后”的参数和“映射原则”相关。而这些UG原则以及与其相关的参数都是和句法结构层次相关。而MP句法中不再有句法内部的结构层次,深层结构没有了,表层结构也没有了。在同样的句法操作中,表现语言间差异的参数只归依到不同语言不同的词项特征和功能词项上。因此,在MP平台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就是要重新按着这种参数的归属提出UG原则。
当然,在MP平台上,人类语言的进化问题是理所当然要回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主要有:Chomsky(2000)、Lenneberg(1967)、Bickerton(1998)、Donald(1991)等人的“内变异语言进化观”和Pinker和Bloom(1990)、Dunbar(1993)、Jackendoff(2002)等人的“外适应语言进化观”。他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进化观的代表⑦。孰是孰非,难以判断。
四、MP平台上的生物语言学的实证研究
MP平台的方法论基调虽然是形式主义的,但也为开展生物语言学的经验实证性研究提供了场所。这好像和GB时期的基调有明显的不同。主要原因是,Chomsky认识到人类语言的生物语言学属性不能仅限于语言自身上的寻找,而必须在和“低于”人类语言的其他生物系统共同的属性上寻找。因此,提出了“合并”这个既有生物进化意义又有和其他生物系统通约意义的概念。Hauser,Chomsky和Fitch(2002)的研究就是一个经验性研究的实例。更值得注意的是,Chomsky提出的“合并”虽说是形式系统中的操作工具,但是,如果像他那样把合并看成是生物基因突变的结果,那么基于合并的MP句法就不再像GB句法那样只具有形式主义的意义,而是具有心理学和生物学上的真实性,至少出现了主动向心理现实性靠近的苗头。Chomsky(2000)在GB时期,始终批评从心理现实性方面认识生成语法,批评用实验方法验证“X-杠规则”和短语结构的心理现实性的做法。但是,MP中的合并不只是元语言形式系统中的概念,而是具有物理学(至少是生物学)现实意义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合并分成Chomsky“窄式句法”意义上的合并以及“宽式句法”意义上的合并,或者Boeckx在“生物语言学宣言”中所说的“弱势生物语言学”意义上的合并以及“强势生物语言学”⑧意义上的合并,从这两种合并的共性和差别上寻找多学科的通约项,寻找形式主义研究和经验主义研究实践的交集,语言学研究和其他领域的科学研究便不再是只停留在哲学层面的沟通,而是实实在在的合作了。
儿童语言习得的实证研究。GB中的儿童语言习得研究是以“柏拉图问题”为语言习得研究的逻辑问题,取得了不少成就。GB的“柏拉图问题”在MP中变成了“Chomsky五问”。如果五问是MP儿童语言习得的逻辑问题,那么,围绕“五问”的习得研究势必和围绕着“柏拉图问题”的习得研究有重大的不同。其本质上的差别是:GB习得研究是关于语言本身的习得,充其量涉及到人类认知问题,较少触及语言底层的生物语言学的遗传学问题。而MP的习得研究则会迫使人们在习得研究中有意识地触及语言和认知的深层次遗传基因问题。在这方面,Wexler(2009)等人的“成熟理论”和“普遍语段要求”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些尝试使用了Chomsky的“语段不可穿透性条件”等,同时把MP句法、语言习得和语言障碍实证研究结合了起来。
生成语法本来就是关于儿童语言习得的理论,在MP这个理论平台上研究儿童语言习得问题,势必得围绕着MP的基本理论假想进行。为此笔者认为以下理论问题值得研究:(1)Chomsky的MP始终认为,命题先于语句,这和他先前提出的“先验概念”相通。那么,婴儿在习得句法之前是否有命题意识?是否有可记述成为句法范畴中的[+N,+V]?这些问题为传统习得研究中的“语义引导”还是“句法引导”赋予了新的理论意义。(2)合并既然是MP句法的唯一操作,我们自然会推断婴儿先验地具有循环使用合并的本领,这个本领是通过人类基因遗传下来的。而一个婴儿凭借这种遗传固定下来的本领习得语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课题就应该是考察婴儿是否显现出天然合并的能力。由于合并是通过加标连续进行的,我们不妨考察婴儿什么时候开始感知并使用加标标注、继续合并,或者用MP的合并思想重新解释已有的习得数据。
五、MP平台上的汉语研究
在生成语言学框架中的汉语研究,和其他任何语言的研究一样,都是要回答人类语言的生物遗传属性问题,这是和一般汉语研究的根本性差别。在GB研究时期是这样,在MP平台上更是如此。GB时期汉语研究曾对探讨当时发展水平上的UG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主要表现为Huang(1982)为确立LF层次的存在和认定ECP等重要UG原则的研究上。在当今这个MP平台上汉语研究也势必会做出自己的贡献。由于GB使用的是“推导式词法”,而MP使用的是“屈折式词法”,而汉语一个显著的词法特征是没有形态变化。无形态词法的语言如何纳入基于形态词法的句法系统中,这是本来在GB时期就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在基于形变词法的MP句法时期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了。因此,用汉语这类没有形态词法的语言在MP平台上提出并回答生物语言学问题,相对于有形态词法的语言有着难以预见的意义。在此,笔者为在MP平台上的汉语研究提出以下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语言“不完美性”在汉语中的表现是什么?汉语的“核心语法”应该限制到什么程度?话题化结构属于“核心语法”吗?没有形态词法的汉语究竟有哪些词项特征,又如何用元语言表达?汉语中的合并如何标注?常见的N,V,P,A等句法元语言符号联系到汉语究竟是什么意义?词法意义?句法意义?语义意义?汉语对应于英语等语言中的T,v,C等功能性范畴是什么?尤其T在汉语中是什么?汉语中的“合成动词”是一个词项还是多个词项的合并结果?如果是一个词项,如何刻画这种词项的特征?如果是多个词项合并的结果,什么时候且如何进行合并?“分布式词法”模型可否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较好的答案?
六、GB研究的经验教训
GB给予我们语言研究的基本经验是坚持“原则-参数”立论法则。这一点已为人们所熟知。普遍语法的原则是什么,一时没有找到,或者找得不准,参数定义得过多或者过于任意,都不会影响“原则-参数”的真理性。实际上,这个立论法则不但适用于语言研究,也会对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产生影响。当然,GB研究也给我们留下了立论上珍贵的教训。
(一)GB给我们的第一个重大的教训——GB寻找UG原则或语言的生物遗传属性,过分依赖语言自身的结构。因此,用GB理论工具发现和描写的各种语言事实突破了UG本应具有的普遍语法解释力。这说明人类语言本身不是语言生物学属性最低的、有意义的表达层次,这个层次应该“低于”语言的表达层次,因此要在同其他生物系统共享的层次上寻找UG⑨。所谓人们长期追求的语言中的“原始项”(primitives)好像没有真正找到。在MP平台上应该找到比GB的UG原则更为抽象的、不再局限于语言自身的、更普遍的原理。进而有可能找到语言学同其他自然科学相通的“通约项”,最后使语言学家、生物学家、神经学家等在MP平台上有共同的语言,这样生物语言学才能成为成熟的科学。
(二)切记避免循环论证。这在研究语言的时候尤其需要防备。GB中循环论证的主要表现在,用X-杠生成的句法结构树上的节点符号(如N,V等)本来源于形态词法的词类形态,而词项插入的凭证也是形态词法的词类形态符号。这好比我们复印了张三的身份证,再把它贴在一个坐席上,然后规定一个入座条件说只有持有张三身份证的张三才能坐到那个席位上。显然,这样既冗余又循环。GB中句法内部多个表达层次也是造成循环论证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正像Lasnik等(2005)说的那样:“如果一个理论有冗余和循环论证现象,无需任何经验性的证明,这个理论肯定是有问题的理论。”
除了上面的经验教训外,笔者还认为有一点在MP平台从事语言研究所应该牢记的,特别是汉语研究。这是应该坚持被称为“所见即所得”(WYSWYG,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的语言学立论法则。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语言A中看到了显性标记X,而在语言B中没有看到X,则不能说语言B中有什么“抽象的、隐性的”的X。比如,汉语中有显性的量词是我们在汉语中的“所见”,但不能由此推断英语中有“隐性”的量词。同理,英语中有显性词法形态的“数、时态”等语法特征,但不能依此推断说汉语中有“抽象的、隐性的”的“数、时态”标记。也不能根据巴斯克语的动-宾语法特征一致的显性标记,为英语和汉语等语言确立一个通用的AGRo结构来。
(三)应该把握住各种语言的“核心语法”范围。虽然,尚没有明晰的方法可以用来确定一种语言的“核心语法”界限到底在哪里,但总的原则是,当某一理论原则在一种语言的事实面前遇到挑战的时候,首先考虑这种语言事实是不是该种语言“核心语法”应该囊括的现象,不能轻易地断定这种语言事实是某个理论原则的反例。这对在MP平台上的汉语研究尤为重要。应该说,GB和MP涉及语言事实是极为有限的,GB和MP所研究的语法本来就是“儿童语法”,GB句法和MP句法本来就是关于儿童语言习得的理论,而不是成人、文人们的“华彩语法”。所以,把“核心语法”恰当地控制在“句子语法”而不是“篇章语法”的范围内,对维系GB和MP的理论目标很有必要。更不能把语用因素引进MP句法的建设中。比如说,汉语中的“吃食堂、桔子剥了皮”可能就不为汉语“核心语法”所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把所有语言现象都覆盖在内的语法肯定不是“核心语法”。总之,不宜过分地追求描写上的满足,而忽略解释上的充分性,偏离探寻人类语言生物遗传属性的MP理论追求。
注释:
①Lenneberg(1967)在他的《语言的生物学基础》(Th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一书中对人类语言的生物学基础从理论和经验角度做了很详尽的描写,被看作是生物语言学经验性研究的奠基之作。从而产生了“Lenneberg梦想”这个词语,表述探索人类语言生物遗传属性的科学理想。
②Boeckx和Grohmann(2007)在他们为《生物语言学》(Biolinguistics)期刊所撰写的“生物语言学宣言”(Biolinguistics Manifesto)中把这个问题表述为“人类语言知识是如何在人脑中实现的?”
③拱肩拱(Spandrel)原指威尼斯圣马可(San Marco)大教堂方形门上角和镶嵌于其中的圆形拱门之间形成的拱形空间。艺术家把拱肩拱当成进行艺术创造的背景,在上面做出一些精美的浮雕或壁画。显然,这种拱肩拱的形状和功能不在建筑设计之中,是建筑之外的副产品。生物学家Gould和Lewontin(1979)用这个拱肩拱的比喻说法,认为生物进化属性不是出于功能性的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先前物种属性自身进化的副产品。Chomsky把这个比喻用到人类语言的进化上,认为人类语言也是物种基因突变的偶然结果,是语言器官之外的其他器官进化的副产品。笔者把这个比喻用到了认识语言的意义上,认为语言中的意义是语言声音符号系统的副产品,意义系统是寄生在声音系统之上的副产品。
④句子表层结构中量化词的位置本身,就决定了量化词间的解释域关系。
⑤Lasnik等(2005)详细地类比了MP句法所遵循的法则和物理世界中的基本法则。
⑥汉语生成语法研究的许多文献表明,“约束论”关于反身代词的规定,不能充分描写像汉语这类语言的反身代词用法。
⑦“内变异语言进化观”的要点是:人类语言是人类前身某个(些)个体基因突变的偶发结果,是人类其他器官进化的副产品。“外适应语言进化观”认为,语言进化是更适应语言交际功能缓慢的适应结果。“内变异语言进化论”和“外适应语言进化论”的关键差别在以下几点。语言的本质功能上,语言的主要功能是社会交际,还是心智表达和用语言思维;进化驱动力上,是社会交际压力,还是自身的偶发个体突变;进化过程,是连续的渐变,还是突变。两种观点都有各自在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神经解剖学等方面的支持,孰是孰非,难以判断。
⑧“弱势生物语言学”指关于语言系统本身相对独立的研究。“强势生物语言学”在更紧密的意义上从多学科(生物遗传学、神经科学等)角度在MP平台上回答生物语言学问题。
⑨至于说低到哪个层次,则取决于科学认识的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原子、量子这些粒子层次不会是对人类语言有意义的层次。这就和我们不能期待在原子、光子、量子呈现的层次上找到疼痛和恐惧的相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