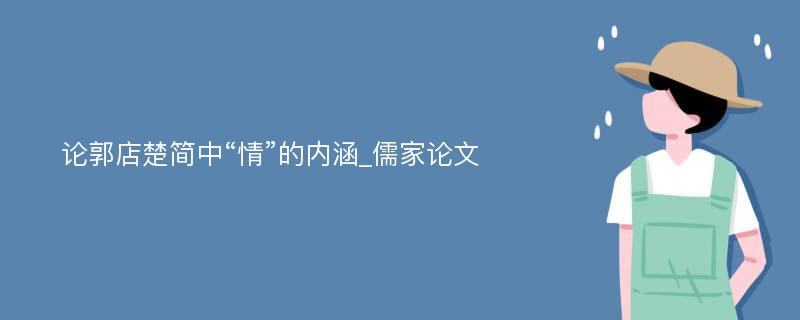
论郭店楚简“情”的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论郭店楚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3)04-0061-08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篇,有关“情”的内容颇为丰富,思想十分深入。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郭店楚简尤其是《性自命出》篇颇为重“情”。但是此“情”到底为何义?学者们的回答并非完全一致,绝大部分学者将其直接理解为情感之情,或说此“情”与情感之情密切相关。我以为,这些见解是值得商榷的。另外,目前对郭店简与“情”相关观念的理解,学界尚不免于片面与驳杂,有待于做更加深入的辨析和贯通理解的工作。
一、由《性自命出》、《语丛二》反思“情”与“性”的关系
郭店楚简论“性”、“情”颇为丰富,所以有些学者主张将郭店简《性自命出》命名为《性情》篇,[1](P58)这一观点得到了上博楚简编者的响应,他们径直将其整理的竹简称为《性情论》。[2]但是“情”与“性”到底是什么关系?则是我们需要切实回答的问题。
对于性与情的关系,宋儒有明确的理解。朱熹说:“有这性,便发出这情;因这情,便见得这性。”[3]《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朱熹《集注》云:“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4]显然,在朱熹的哲学架构中,性与情是完全对应的。在朱熹之后,他的弟子陈淳对他有关性情关系的理论解释得至为明确:[5]
情与性相对。情者,性之动也。在心里面未发动底是性,事物触着便发动出来是情。寂然不动是性,感而遂通是情。这动底只是就性中发出来,不是别物,其大目则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中庸》只言喜怒哀乐四个,孟子又指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性中有仁,动出为恻隐;性中有义,动出为羞恶;性中有礼智,动出为辞逊、是非。端是端绪,里面有这物,其端绪便发出从外来。若内无仁义礼智,则其发也,安得有此四端?大概心是个物,贮此性,发出底便是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云云。恻隐、羞恶等以情言,仁义等以性言。必又言心在其中者,所以统情性而为之主也。孟子此处说得却备。又如《大学》所谓忧患、好乐及亲爱、畏敬等,皆是情。
从朱熹和陈淳的论述来看,宋明儒关于性情关系的基本思维框架当来自《中庸》关于“已发”、“未发”的陈述,他们并以此来理解《孟子》等书;反过来,通过对《孟子》、《乐记》,乃至《易传》的相关论述和阐释,加深和扩展了对儒家性情论的理解。这便是“心统性情”论的提出。从陈淳等人的论述来看,仁、义、礼、智四看为性,四端七情(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喜、怒、哀、惧、爱、恶、欲)及忧患、好乐、亲爱、畏敬等,皆是“情”。显而易见,“情”是相对于“性”之发,从“已发”言其无所不具的一个概念;同时从其外延来看,宋儒所理解的“情”又重在情感上面。无可否认,这些观念已经构成了我们理解郭店楚简的“先见”(preunderstandings),但是这些“先见”是否符合郭店楚简论“情”的实际,则当然需要我们做出一番审慎的辨析与考察。
《性自命出》第2-5简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人之。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6](P224)所善所不善,势也。”“情”是从何物生出的?根据简文,“情”是由“性”生出的。但是,“情”是什么,是“喜怒哀悲之气”吗?《性自命出》并没有直接的文本回答。如是有的学者根据宋儒的理解,除了将“性”理解为“喜怒哀悲之气”,即《中庸》所说的“未发之中”的状态外,还径直将其“已发”的状态,如喜、怒、哀、悲,断定为所谓的“情”。[7]在此,我认为这一论断是需要受到严格的反思和怀疑的。
根据上引简文,我们可以对《性自命出》中由性所生之物列举如下:
[1]喜怒哀悲之气,性也。
[2]情生于性。
[3]好恶,性也。
[4]善不善,性也。
另外,第39至40简也有两个相关的陈述:
[5]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
[6]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
由上面所列出的6条引文来看,可以推断这些由性所生之物呈现出并列的关系,也即是说,喜怒哀悲之气、情、好恶、善不善、仁皆由性生出。如果我们还不能进一步断定它们必定如此,那么至少在陈述方式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逻辑关系是平行、并列的,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任何从属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观察和陈述,还可以在《语丛二》中得到更为显豁的证明。
《语丛二》有关性生诸物的陈述是这样的:[8](PP.203-204)
[7]情生于性,礼生于情,严生于礼,敬生于严……(简1-4)
[8]爱生于性,亲生于爱,忠生于亲。(简8-9)
[9]欲生于性,虑生于欲,倍(悖)生于虑,争生于悖,党生于争。(简10-12)
[10]智生于性,卯生于智,悦生于卯,好生于悦,从生于好。(简20-22)
[11]子(慈)生于性,易生于子,肆生于易,容生于肆。(简23-23)
[12]恶生于性,怒生于恶,乘生于怒,惎生于乘,恻生于惎。(简25-27)
[13]喜生于性,乐生于喜,悲生于乐。(简28-29)
[14]愠生于性,优生于愠,哀生于忧。(简30-31)
[15]瞿生于性,监生于瞿,望生于监。(简32-33)
[16]强生于性,立生于强,断生于立。
[17]弱生于性,疑生于弱,北生于疑。(简36-37)
比较《语丛二》与《性自命出》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二者有异有同。其所同者,皆是平铺地列出由“性”所生或所由以出的概念系列,且“情”并不囊括其他诸种概念,与“性”完全对应、对称。其所不同者,《语丛二》比《性自命出》所言性之生的系列更为丰富,但《性自命出》由于自身文本的重要特性,使其相关的论说显得更为深刻。我认为,有如下几点是值得密切注意的:
其一,这两篇简文都有情生于性和恶生于性,及礼生于情的说法,表明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情”是由性所生之情,同时是礼乐之作的直接来源。但是此“情”的具体内涵指什么,是值得引起深切关注的问题。
其二,在《性自命出》中以“气”陈述出来的喜怒哀悲者是性,而在《语丛二》中则说爱、慈、喜、愠出于性,显然已不是所谓“气”者。这种差别似乎表明,当人的情感尚处于“气”的存在状态时,就是所谓涵于中的“性”,反之就是表现出来的各种具体感情。而《性自命出》说“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又说“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似乎“好恶”、“善不善”都有《中庸》“未发”、“已发”的问题,显然逸出了“情”、“性”一一相对应的宋儒理解框架。
其三,《语丛二》对众多的名词、概念之间的相生关系进行了探索和连接,这与<性自命出》区别较为明显,但仍是《性自命出》在相关内容上的继续和发展。
其四,《性自命出》与《语丛二》在陈述性之生的系列时,互有差异。如前者说“性生仁”,后者说“智生于性”。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的“性”中涵有仁、智之根,也就是说有善根。这样,当然有向“性”中追问仁、智之根的必要。而孟子的哲学,显然沿着这个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另外,郭店简《性自命出》“心取性出”的思想,为孟子通过“心”来体认人性必定内涵仁、义、礼、智之端的思想准备了最基本的原理;同时仁、智出于性的论说,也为孟子人性善的主张开了先导。而宋儒直接以仁、义、礼、智为“性”来理解孟子的人性论,虽是这一路线的继续发展,但毕竟与《孟子》文本,尤其与郭店楚简不尽相同。此外,《语丛二》的作者还说到了人的意志力的“强”、“弱”,及人的天赋机能(“瞿”)皆出于性。这一点,后儒的解释比较婉曲,多从气质上言之。
其五,《性自命出》说“好恶,性也”,可是在《语丛二》中却说“恶生于性,怒生于恶,乘生于怒,惎生于乘,侧生于惎”。前者是从“未发”言,但“好恶”似乎不应归属于情感范畴;而后者则与情感紧密相连,似乎应将“恶”归入人的情感之列。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其六,“情”与“欲”、“欲”与“好恶”的关系问题。《性自命出》、《语丛二》没有文本说明“情”与“欲”具有紧密的联系,两处文本都是平铺着的,也即是说“情”是“情”、“欲”是“欲”。当然,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情”、“欲”在简文中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欲”与“好恶”,在简文中并不具备生发关系,特别是在《语丛二》中由“欲”所生的名词、概念众多,可就是没有文字说明“好”、“恶”生于“欲”;相反却有”恶生于性”的叙述,在《性自命出》中更说“好恶,性也”。可见在简文的作者那里,“好恶”是一个概念,“欲”则是另外的一个概念。如此,就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到底什么是简文所说之“欲”?
总之,可以肯定,“性”是一个更根本的概念,而人人具有此性,且“四海之内其性一也”。[9]具体说来好恶、善不善及喜、怒、哀、悲之气,皆是性;由性而生,就有所谓的情、欲、强弱、瞿及喜、怒、哀、悲诸物。前者可以说是“未发”,后者可以说是“已发”,与《中庸》在理解结构上有相同的地方。尽管如此,这与宋儒所理解的《中庸》思想及性情观是有较大区别的。朱熹说,“未发”之物皆是“性”,“已发”之物皆是“情”,“性”与“情”在此完全是对应关系,所以“情”在外延上可以包括人的各种欲望及情感等等。可是在楚简中,“情”只是”性”已发之一物,而“欲”与喜、怒、哀、乐等,似难直接将其判定为所谓的“情”。另外,仁,智不属于未发之性,而属于已发之物;好恶属于未发之性,而不属于已发之物,更不属于所谓的“欲”,这大概是远后的儒者们闻所未闻、想所未想到的。因此应当把先奏儒学与宋明儒学,朱熹《集注》与《四书》本身,特别是将二者的心性内容努力分开,用心去探寻先秦儒家心性之学的真实内涵和真正本质。
二、由《性自命出》等篇理解“情”的概念内涵
郭店楚简论“情”颇为丰富,根据我的计数有27个“情”字,《缁衣》、《唐虞之道》、《语丛》四篇共7字,《性自命出》则高达20字,后者因此自然成为我的重点考察的对象。而“情”是什么?是情感,是情实,是质实,还是像Chad Hansen所说的是“对实在的回馈”(reality feedback)?[10](P196)这是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
1.楚简《性自命出》篇的“情”字义分析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包含“情”字的文本如下:
[1]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乏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人之。 《性自命出》简3-4
[2]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宜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 《性自命出》简16-18
[3]礼作于情,或兴之也。 《性自命出》简18-19
[4]君于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 《性自命出》简20-21
[5]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 《性自命出》简23
[6]凡古乐龙心,益乐龙指,皆教其人者也。《赉》,《武》乐取,《韶》、《夏》乐情。 《性自命出》简28
[7]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乐,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 《性自命出》简29-30
[8]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求其心有伪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以伪也,可知也。[不]过十举,[11](P265)其心必在焉。察其见者,情焉失哉? 《性自命出》简37-38
[9]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 《性自命出》简39-40
[10]凡用心之躁者,思为甚。用智之疾者,患为甚。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用身之忭者,[12](P114)悦为甚。用力之尽者,利为甚。 《性自命出》简42-43
[11]人之巧言利词者,不有夫诎诎之心则流;人之悦然可与和安者,不有夫奋作之情则侮。 《性自命出》简44-48
[12]凡人情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之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 《性自命出》简50-51
第[1]条之“情”,无疑是性情之情。这个“情”由“性”而生,且是“道”所由以发端者,这说明它一方面是由中出的,另一方面对“道”的建构与理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推论,如果我们把“道”的语义理解成道路、规律或人在此世界中所通由的规定性的话,那么“情”相对于“道”来说,就有“端绪”之义,这个端绪生发出来就是“道”。不过,此“端绪”当然已不属于“性”中之物,而是即“已发”以言人所具的最直接、最初始的现实性。
第[2]、[3]、[4]三条引文,都处在一个文本脉络里,着重讲“情”与“道”,尤其是与“礼”的关系问题,涵义应该是相同的。第[2]条在理解上有些困难,主要是其中的“其”指代什么,这一问题有些难以回答。上文说“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第15-16简),因此我认为这里的“其”字就是指“人”。[13](PP.41-43)整句话是说,圣人通过排比人之类、观察人之先后、体会人之宜及条理人之情的手段,而制作出诗、书、礼、乐;然后又以其来教化老百姓。这里的“情”当然是指人情,而不是指《乐》之情。第[4]条的“情”,显然是指人情,而且从“美其情”来看,此“情”是嵌在“人”自身的。第[3]条“礼作于情”,与《语丛二》第1简可以互证,所以此“情”也是性情之情;相对于礼而言,它更为根本,是与人的根源(性)更紧密相关的真实生命。
第[5]、[6]、[7]三条引文,也处在相同的文本脉络里,着重讲“声”,尤其是“乐”与“情”的关系问题,而且它是由“道”与“情”的关系这一问题演绎出来的,所以其中的“情”字涵义应该相同,也是人情、性情之情。但是,由于这里“情”与“声”、“乐”紧密关联在一起,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了,因为“声”和“乐”不仅表达了人的感情,而且着重是要表达人的感情。如是,“情”和感情(或情感)的关系在此必须得到更准确、深入的说明。第[6]条说《赉》、《武》之乐,以周革殷命,取得天下为乐;《韶》、《夏》之乐,以抒发人本真、自然的生命为乐。这个“情”,很显然并不就是情感之情。第[5]条说“凡声,其出于情也信”句,表明“声”由“情”出,而“情”是“声”的本源,“信”则表明“声”与“情”二者之间确实具有深切的生化和印证关系。这再次说明,“情”是人所本据的自然而真实的生命。说它是自然的,因为它不是人为的;说它是真实的,因为它是由“性”直接呈现的,但不是由“信”加以判断、肯定的产物。“声”,如果排除其内在包涵、传达的“情”,那么就纯粹是一种物理的现象;可是“声”,在此毕竟要传达它所本应该传达的“情”,这里就有所谓的“信实”问题。“信实”首先是一种事实判断:“情”以本源的方式在“声”中绽放它的真实。其次,它同时又是一种价值判断:所有的“声”都应该如实地传达本体“情”的真实。正是“情”使“声”成其为“声”,使“乐”成其为“乐”,“情”的内在丰富性随着“声”、“乐”一起绽放,转变为具体的丰富性。这个具体的丰富性,是通过各种具体的情感表现和心理反馈作用演绎出来的。第[7]条说“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正是表达了此一思想。“至乐必悲”是极端之例,“哭亦悲”则是寻常之例,皆是用来表达人之“情”的。在此,这个“情”就是情感之义吗?我认为不是。“至乐”是致生“悲”者,“哭”则是呈现”“悲”的现象物,它们表达的是一种“情”,这种“情”具体指悲哀的感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感情并不就是“情”本身,它也不过是用来呈现“情”的内在特性的。哀与喜、怒、乐、优等等,是通过“情感的样式”来呈现“情”的多样性和本体性的。设想,如果“情”没有内在的内敛的多样性,就不会有情感的多样性,如喜、怒、哀、乐的分别;但是必须指出,这两种“多样性”只有相应性,而无同一性。如果没有“情”所生发的本体性作用,喜不成其为喜,怒不成其为怒,哀不成其为哀,乐不成其为乐,人类所有的声音、动作和反应都只会是物理现象,根本不会有情感这种心理现象发生。另外,第[10]条说:“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情”在这里是被用者,“哀乐”则是用之者。哀乐最能够“用情之至”,即最能利用“情”之至真至实者而充盈于情感自身而已。显然这里的“情”非情感之情,尽管它与情感之情似乎具有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
第[8]至第[12]条,都在《性自命出》的下篇。下篇讨论的主题是“修身”问题。第[10]条已论述过,第[11]条有些特殊,其他几条的“情”字义则明显颇为接近。第[11]条“巧言利词”、“悦然和安”分别从言、貌而言,是密切相关的;“诎诎之心”、“奋作之情”分别从心、情而言,关系也当是对等的,因此我认为这个“情”与情实、性情之义也有紧密的关系。
第[8]、[9]、[12]三条,其中的“情”都有情实之义,而且与“信”、“伪”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第[8]条说“求心”不能以“伪”,以“伪”求心,则心弗得。这个“心”,当是指人的真实之心。真实之心,只能以“信”求得。另外,人的真实之心存在于他的行为活动中;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其真实之“情”就不会丧失,一定会被洞察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心”与“情”相关,心之所在,实际上是由“情”来确定和规定的。这说明“情”在“心”中之“在”是本真性的存在:得其“情”,则知其心之所在,同时亦得其心之实体。第[9]条说“信”是致“情”之方,而“忠”是致“信”之方。忠、信、情,一个概念比一个概念更为深入,而情出于性,因此这里的“情”无疑是性情之情。第[12]条指明“情”即“人情”,也是情实之义,与情感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本条特别强调“情”的本源性作用,无“情”也就无所谓“信”。
2.楚简《性自命出》“情”字义的内在关联
通过以上分析,《性自命出》的“情”在不同的语境里的确具有不同的内涵。有偏从主观而言的真实义,相当于“诚”;有偏从客观而言的真实义,指人本然的真实的生命,或呈现为实在的外在事物。另外,“情”还与情感有紧密关联。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这些不同含义,或者在不同语境中含义有所偏重的“情”,它们之间到底是分散、隔离的呢,还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相互依赖、贯通在一起的?我认为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统一性。
前面已指出,《性自命出》上篇第[2]条中的“情”是指人情,它是诗、书、礼、乐的制作来源之一,与第[3]条中所说“礼作于情”之“情”相一致。第[4]条中的“情”承接上文而来,与第[3]条中的“情”属同一概念。不过第[2]条说“理其情”,说明“情”是有头绪、有脉络的,与作为混沌体的“性”不同;第[4]条说“美其情”,说明“情”是十分素朴的,所以才需要节文之。第[5]、[6]、[7]条中的“情”,都与“声”、“乐”有紧密的关系。而从第18简末至上篇末尾(第35简),都是论述礼乐的,且礼乐为“一术”。由此可以推论,第[5]、[6]、[7]条中的“情”应与上文论礼的文本中的“情”字,具有同一性。《礼记·乐记》也有类似“乐作于情”的论述,[14]与《性自命出》论乐的部分比较契合。第[6]、[7]条,及下篇的第[10]条的论“情”,皆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一原则。第[5]条论及“情”与“信”的关系,完全可以与下篇论“情”结合起来看,与第[9]条的论说是相互配合的。
下篇主要是在修养论上谈“情”与“信”的关系,这些“情”,除了第[10]、[11]条外,其他的“情”字义显然是统一的。第[10]条,上面已指出与第[6]、[7]同例,而第[11]条的“情”与悦然和安之意相对,是指人所具有的为了维护人的尊严的振作、威严之气,此“情”显然是从生命本体中贯通下来的,应该是礼的直接根源。
总之,《性自命出》中的“情”分别以上、下篇为中心分成两组,每组意义相近或基本相同。下篇第[9]条说“信,情之方也;情出于性”,由此我们全可以断言与下篇相关联的一组“情”字,是性情之情。上篇第[3]条说“礼作于情”,第[2]条说“情生于性”,更有力的旁证是《语丛二》第1简“情生于性,礼生于情”两句,完全可以断言与上篇相关联的一组“情”字,也是性情之情。另外,我们还可以就《语丛》、《唐虞之道》和《缁衣》简中的“情”字义的统一性问题,同样给出必要的说明。因此,整部郭店简的“情”字义,实际上都是统一的。而所有的“情”在不同的语境中所侧重出来的意义,都应该在性情论的思想统系中得到说明,同时也是性情之情的内涵向不同语境中的“情”字义贯注的结果。
3.对郭店楚简“情”的内涵的进—步分析
上面,我们已根据郭店楚简分析了“情”在不同文本中分解的含义,并对这些解析了的“情”字义做了贯通的理解,指出不同“情”字义的最终来源乃维系在性情之“情”上。另外,我们还可以指出,郭店楚简的“情”字皆为褒义,如“脂肤血气”在许多先秦文本中常被当作致恶的因素而加以否定,可是在《唐虞之道》中则要“顺乎脂肤血气之情”。而为什么要顺之?不是因为“脂肤血气”不可能没有致恶的因素,而是因为此“情”为性情之情,有真实,乃至中正(无所偏倚)之义,是对“脂肤血气”的内在限定,惟其如此,故要顺此脂肤血气之中正、真实者,而完成一己圆满的生命。
既然郭店楚简的“情”,是由性已发的本然的生命,那么它的由中出,则必然要求所发之物在用心和结果上都是真实的。从本质上来说,如果生命活动纯粹是一种无心的现象,那么真实与否的判断并无来源;但是,如人,则是一种有心的生命体,其活动就有用心的不同和信伪之分。注意,郭店楚简中的信伪概念,不是直接言“情”之信伪:“情”本身是真实之质,无可怀疑的,无所谓信伪;信伪的产生,乃根源于在人的不同用心及由此用心而产生的行为、结果中,“情”丧失了其本真的特性与否。《性自命出》下篇讲心术,讲修养,讲信伪,都是要显发以“情”为根基产生出来的此一方面的思想。由此,那种常用“信情”、“伪情”来论说郭店楚简“情”的内涵的说法,是不恰当的。
《性自命出》下篇除着重论述“信”与“情”的关系外,还对“欲”做了大段的论述。《性自命出》的作者对“欲”的态度如何?第62-65简说:“凡忧患之事欲任,乐事欲后。身欲静而勿羡;虑欲渊而毋伪,行欲勇而必至,貌欲庄而毋伐,[心]欲柔齐(济)而泊,喜欲智而无末,乐欲怿而有志,忧欲敛而毋昏,怒欲盈而毋希(肆),进欲逊而毋巧,退欲肃而毋轻,——欲皆敏(文)而毋伪。”“欲”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在修身、节文的过程中指向结果的“应该”,这个应然性的规定自然有适度、适中之义,同时“欲”也是人心之“想要”。“想要”和“应该”之义相结合,就是《性自命出》中“欲”这一概念的内涵。这与荀子之后,中国哲学中“欲”的概念不一样。荀子之后基本认为“欲”是恶的,需要人“伪”节制之、遏止之和起化之。《性自命出》不但没有遏制“欲”,而且实际上是在宣扬“欲”,通过修身之“欲”以端正其心。第67简说“君子身以为主心”,“身”作动词,是修身之义,“主”则有主持、端正之义。整句话是说,君子修身乃是为了端正其心。不过,“欲”既然有应该之义,那么《性自命出》的作者不会反对对“欲”自身作适当的节制;但真正重要的是,需要理解“欲皆文而毋伪”这一命题的内涵;“文”有繁饰、节文、美化之义,《性自命出》的作者主张“欲”都应该得到节文,得到实现,但“欲”不应该在“文”的过程或结果中变得虚伪、不可信起来。可见真信,是节文“欲”的核心标准。而崇尚真信这一点,似乎也是从“情”的内在特质贯通下来的。也因此,“情”虽然不是“欲”,但是它毕竟对“欲”发出了本真的要求。
在《语丛二》中,从第10-19简谈到了大量由“欲”所生之概念,而这些概念,一般具有贬义、否定的意味,属于所谓恶者。这与《性自命出》很不一样,而与荀子之后的中国思想家对“欲”的认识和态度,几乎如出一辙。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现象。
“情”和诸种“情感”,尽管二者之间具有“已发”、“未发”的关系,但是喜、怒、哀、悲的情感在当时是否属于“情”,则是需要严加讨论的。在《性自命出》上篇的下半部分,谈到礼乐的制成问题。简文认为礼乐皆作于情,[15]但是礼乐的制成却在现实的层面上比这一原则远为复杂,有“当事因方而制之”的原因,[16]还与人的情感等因素密切相关。《性自命出》第20-21简说“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显然这里的“乐”、“悦”等感情,与“情”是分开的:一个是讲人的情感心理表现,一个是讲制定礼的真实根据和本源。第22-23简的“笑,礼之浅泽也;乐,礼之深泽也”,其中的“笑”、“乐”表达了人的情感,不过这两种情感反应都是受到礼的影响而作出的。它们不但不是“情”本身,反而证明了“情”正是使心理发生情感反应的本源和价值所在。第23-27简,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声”或“乐”,如果出于“情”非常信实的话,那么反过来就能深深地打动人心。所谓打动人心,简文随后从情感反应等方面加以说明。第29-35简继续前面的话题,论述了不同的“声”、“乐”现象,反映了不同的情感反应;还论述了“情感反应”打动他人之心,及“心思”在情感反应中的作用问题。其中“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致)其情也”句,说明了无论悲或乐这些情感反应,还是由情感反应产生出来的“声”、“乐”现象,皆是为了表达人之“情”,是为了表达从人的生命中流露出来的至真至实者。这段简文还谈到了“其声变,则[其心从之];其心变,则其声亦然”的思想,不过“声”是具有情感之声,“心”是具有情感反应特性的“忧思”、“乐思”。这一思想,深入地阐明了“心”与“声”交互作用的理论。总之,人们或喜或悲,或乐或哀,都是人们用心对“情”反应的结果。情感确实是一种反应,不过不仅仅是通过对“实在”的反应,而更主要的是通过心对事物(如“声”、“乐”)内涵的真实之“情”的反应,并且这种反应的程度与事物所含“情”的程度成正比。可见感情是通过心的作用开显出来,不过它的真实力量和存在的根源却是以“情”为基础的。
如是,我们可以得出另外两个结论。第一,喜、怒、哀、悲之气从“性”发为喜、怒、哀、乐的具体情感,是由“心”面对外物反应、作用出来的。第二,在郭店楚简中“情”是由“性”而出,它是已发的至真至实者,是事物本来既有、本来应有的内在规定,而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也不是心面对外物产生的心理反应;当然从“[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的原理来看,[17]“情”之所以能出于“性”也是“心取”的结果。所以“情”与情感之情,在概念上本无混淆,但情感的存在根据与它的感动力量之源却是由“情”提供的。
三、略论“情”义内涵的转化问题
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先秦儒家文献对“情”的概念内涵的理解,从字义上来说基本上是统一的,都有“实”的意思,A.C.Graham的见解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18](PP.59-65)也同于中国古典研究的学者,像阮元等人的意见。[19]但是仅从字义上并不能完全揭示这一概念,尤其是它的哲学意蕴的内涵。它虽然有质实、情实、真诚之义,同时即已发而言也有端绪、中正和原初的多样性、现实性之义,但是“情”的最深沉、最内在的含义,乃根源于它与“性”所具有的紧密关联,其规定性的本源皆在于“性”:无“性”则无所谓“情”。而Chad Hansen认为早期中国古典文献中的“情”是指“对实在的回馈”(reality feedback或reality reaction)的看法,[20](PP.196-197)就先秦的“情”不是“情感”义来说,这是正确的;但是他给出的定义显然没有把“情”着重看作“出于性”的结果,从而断绝了从本原(“性”)上来思考“情”的内涵的真实通路,这必然导致他的定义仍然落入西方心理学的理解结构中,而得不出正确的意见。
我同意,即使在郭店楚简那里,“性”是“未发”、“情”是“已发”的观点仍然是有效的。但是,必须指出,《中庸》只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尚无明确的文字指出“性”、“情”对应“中”、“和”。因此,在当时,乃至整个先秦,“未发之性”与“已发之情”并不具备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样,朱熹对《中庸》的注释只能看作宋明理学有关性情论的基本理论论说,而不能看成先秦的性情论思想,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另一方面,从外延来看,有所谓“六情”、“七情”、“五性”之说。“六情”包括喜、怒、哀、乐、好、恶,[21]“七情”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22]“五性”(“五情”)包括喜、怒、欲、惧、忧,[23]它们大体是好恶、情感、欲的混合物,当然可以用“心里实在”来概括它们。这一点,与《性自命出》明显不同:在《性自命出》中,欲是欲,好恶是好恶,情是情,根本不相混。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即以人情为自然之情。这一传统,在《庄子》和《荀子》写作的时代仍在继续。不过,庄子及其后学着重分辨了人情和自然之情的区别,他们反对把是非、好恶及情感等看作是“性命之情”,批判把“人情”看作是“自然之情”的儒家性情论。当然,我们反思在庄子及其后学的时代,可以得出“情”的外延进一步被当时的儒者扩大了。荀子以好恶喜怒哀乐为“情”,并在耳目声色之欲上来理解“情”,认为人情甚不美。[24]在此,“情”和“欲”非常接近,且都有恶的意味。
由“情”在先秦的这一历史变迁来看,它的外延主要是通过人各种后天所具有和生而即有的东西,不断得到补充的。“情”的外延在不断发展变化、不断丰富的这一事实,为先秦儒学和宋明儒学的性情论,即《礼记》、《孟子》的相关说法与朱熹解释之间的贯通提供了文献上的可能性。同时,在内涵上“情”的最基本的字义“实”,及作为哲学根基的性命之“情”,为“情”的外延的灵活变化提供了内在的方便和可靠的基础。[25](P195)也即是说,正是性情之“情”及其“真实”之义,为这一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的确定和展开,打开了富有张力的解释和重构的前景。另外也说明,“情”虽然在外延上最终容纳了喜、怒、爱、悲的情感内容,但是它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情感”是可以肯定的。而人们动辄以“情感”来解释宋明儒的“情”,其实不仅不合乎先秦性情论的大统,恐怕也不符合宋明儒思想的实际。[26](P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