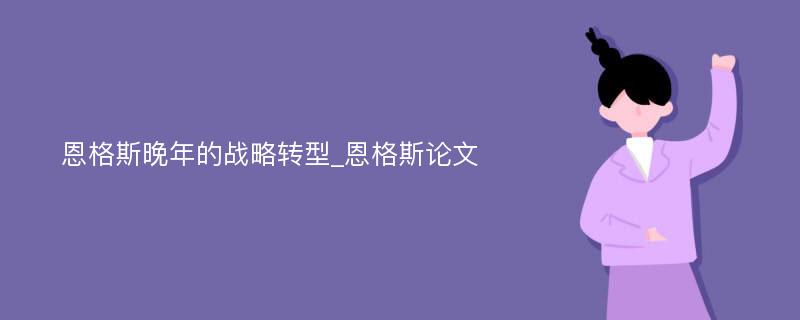
恩格斯晚年的战略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晚年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722 [文献标识码]A
无产阶级通过什么样的道路取得政权,是恩格斯晚年一直十分关注并花费大量精力加 以思考的问题。有关论述散见于《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草案批判》、《卡尔·马克思<1 848年—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等著作以及大量的书信 之中。恩格斯逝世以后,其有关思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 时至今日,仍未取得共识。在这些争论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恩格斯晚年一直坚持 暴力革命与合法斗争两手,其中以暴力革命为主的策略。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则认 为,恩格斯晚年虽然仍然坚持暴力革命与合法斗争两手策略,但侧重点已发生了变化, 即以合法斗争为主,暴力革命为辅。笔者认为,恩格斯晚年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在对他 和马克思早期的暴力革命思想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合法斗争的战略。
一、暴力革命不再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最适宜的手段
综观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著作,除1847年恩格斯在其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表 述过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方式实现变革所有制的愿望以外,他们的大量论述都认为暴力 革命是无产阶级唯一的正确道路。
1842年恩格斯指出:“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 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1](p.550-551) 。1845年恩格斯又说,工人阶级要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 ”[2](p.548)。1846年,恩格斯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要消灭私有制并代之以公有制,“ 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它手段”[3](p.319)。18 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也提出了与恩格斯相同的结论。1848年,马克思、恩格 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 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4](p.285)。
在上述引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暴力革命”前面冠以“唯一”、“除了”、“只 有”等排他性的限制词。这表明,他们当时认为暴力革命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1895年,恩格斯在《导言》中回忆这段历史时,从主客观两方面说明了发生“迷误” 的原因。
就主观方面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 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5](p.594)。资产阶级的历史表明,正是暴力革命产 生了资产阶级政权。没有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不 可能在这些国家实现从封建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飞跃。马克思、恩格斯从总结英 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历史所反映的社会革命的规律中得到应有的启迪:一种私 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尚且需要运用暴力,将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产阶级私有制也 必然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达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是通过 揭示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发展规律来论证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就 客观方面来讲,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认为,资产阶级社会“ 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它已经受到这种关 系的阻碍。”这种认识辅之以接踵而至的巴黎、维也纳、米兰、柏林的起义,尤其是6 月间在巴黎发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大搏斗,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毫不怀疑 :“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其结局必然是无产阶级的胜利。对此,恩格斯在《导言》 中反思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 ,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 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 奥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 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 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正因为这样,“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 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甚至“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 是不可能的。”[5](p.597-600)
与40年代相比较,19世纪最后三十年是欧美各国生产突飞猛进的高涨年代。在完成第 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又涌现出石油和电力等新能源,钢铁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 业等先后崛起,整个西方进入“钢铁时代”和“电力时代”。世界工业产值加速增长, 1850—1870年间世界工业产值增长1倍,而1870—1900年间则增长2.2倍。生产力的发展 又引起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结构的变化,即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这期间虽 然发生数次经济危机,但经济从整体上是向前发展的。当“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 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革命。” [6](p.11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针对当时的经济状况所讲的这段话,无疑同样适用 于19世纪末期的资本主义。不仅如此,19世纪两次工人起义失败及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 也使恩格斯对暴力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产生怀疑,他明确指出:“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 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5](p.600)。19世纪工人运动曾出现 两次低潮,第一次是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开始了马克思所说的“难忘的十 年时代”。在法国,路易·波拿巴废除共和,恢复帝制,把军事官僚机构发展到空前的 规模,疯狂摧残人民的民主权利,禁止和取缔工人群众组织。在德国,反动派不仅公然 地把1849年宪法视如废纸,抛在一边,重建和强化君主专制统治,而且肆无忌惮地迫害 工人和民主派,取消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一切新思想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就是以资 产阶级自由主义标榜的英国,自由党和保守党也愈益趋向联合,握手言欢,建立起大资 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寡头政治体制,共同对付人民群众。恩格斯在《一八五八年的欧洲 》一文中对这种情形作过深刻地描述:“从1851年12月2日到今年年中,就政治方面来 说,欧洲大陆好像裹上了一件尸衣。统治者由于依靠自己的军队在巨大的革命冲突中取 得了胜利,就有可能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地颁布和取消法令,遵守或者破坏法令。各地 的代议机关都变成了空架子,几乎任何地方的议会反对派都不能存在下去,报刊堵上了 嘴。”“到处都认为军事专制和君主专制制度是唯一适当政体。甚至英国政治改革气氛 也日益低落。”[7](p.695)第二次是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形势都发 生了急剧变化。在公社时期曾吓得丧魂失魄的各国统治阶级,现在为了向无产阶级进行 报复,而对第一国际会员和第一国际组织进行了疯狂的迫害。至1872年,几乎欧洲所有 的国家,国际的活动实际上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禁止。而对于法国的工人阶级来讲,损 失尤为严重。工人组织完全遭到了破坏,并且受到严酷的法律追究。对公社参加者的诉 讼案,从1871年8月起,一直延续了好几年。军事法庭提出的判决书共达五万多份。187 2年通过了杜弗尔法,根据这一法律规定,凡第一国际会员即被判处两年监禁,并剥夺 公民权;而对国际的积极活动家的监禁期限则可长达五年。结果,法国无产阶级的元气 大伤,其精华丧失殆尽。对于这两次失败所引起的工人运动的严重损失,恩格斯一直耿 耿于怀,并多次劝告工人领袖切忌采取不合时宜的暴力行动。1885年6月3日,恩格斯在 给左尔格的信中谈到5月24日巴黎举行纪念巴黎公社战士的示威游行中警察进行挑衅发 生冲突这一事件时说:“由于没有国民自卫军,就不可能获得武器,因此任何暴乱注定 要失败。”[8](p.323)同年12月19日,恩格斯写信给荷兰的纽文胡斯,也谈到制止暴力 行为问题。他说:“您在荷兰制止一切暴力的爆炸,是完全对的。那只会招致无益的牺 牲使运动倒退几十年。”[8](p.400)这年他写给倍倍尔的信当谈到德国的形势时表达了 同样的心情:“我们绝不能希望发生大的灾难。它会使我们的运动退居次要地位好多年 ,然后我们大概又得像1850年以后那样耽误很久,一切又要从头开始。”[8](p.381)
另外,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也越来越造成使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成为不可能 的形势。对此,恩格斯做了较详细的考察:“城市街道变得又宽、又直、又长,使新式 枪炮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力;街垒越发难以构筑,巷战更加困难;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 军队的集结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军队数量成倍增长,武器装备得到改进,先进的火器 和枪弹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因此,“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 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5](p.603)“如果军队作战,进行抵抗就是发疯。” [9](p.505)
由上可见,恩格斯基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顽强扩展力、无产阶级失败的历史教训以 及新时期武装起义条件的恶化,基本上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二、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逐步成为战略手段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道路越走越狭窄时, 在她的旁边却敞开着一扇充满诱惑与希望的大门——合法斗争。只要我们回顾一下马克 思、恩格斯关于革命道路思想的发展进程,便不难看出他们是如何从反对合法斗争到赞 成合法斗争以致恩格斯晚年在此基础上最终确立合法斗争战略的。
1842年11月30日,恩格斯写的《国内危机》一文在分析英国的宪章运动时指出:“在 工人和宪章派心目中唯一的指导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原来就是宪章派的——就是合法 革命的思想。这种思想……,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他想要实现这种思想才遭 到失败。……‘合法革命’把一切都搞糟了。”[1](p.550)恩格斯写于1844年9月—184 5年3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 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 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问题的任何希望。”[2](p.548)与此同时,马克思在1847年上半 年写成的《哲学的贫困》里,也做出了类似的论断:“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 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 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 此。”[4](p.161)
在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谈到了普选权对于英国的意义。“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 ,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它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 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10](p.3 90-391)“普选权在英国所产生的效果同它在法国所产生的效果相反,正像这两个国家 的城市和农村的情况一样。”[11](p.300)这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有了英国可以 和平取得政权的思想,只不过还没有作为一种论断明确提出。
到了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表明他们赞成和平过渡的道路,同时强调暴力方式 不可避免。1871年9月12日,马克思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的发言时指出:“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 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12](p.700)1872年9月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 的演讲中又说:“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推翻维 护旧制度的旧政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 的手段。……,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 还可以加上波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 必须承认,在大陆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的杠杆。”[13](p.179)马克思不 仅提出了两种斗争方式,同时还明确地界定了如何运用两种方式的标准,这就是,“凡 是利用和平宣传更快更可靠地达到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12](p.683 )这说明,除非不得以,马克思更赞同使用和平方式。
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也就是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更多地谈到和平方式,尤其是 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非常法”的节节胜利,促使恩格斯逐渐将合法斗争视为一种战略 加以强调。1878年,在俾斯麦的指示下,帝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反社会党人法” ,企图以此搞垮德国社会民主党。然而,俾斯麦的如意算盘落空了。1884年10月28日举 行的帝国国会选举以及随后于11月举行的重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到24个议席,5499 90张选票,使社会民主党党团第一次获得了提出法案的权力。这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破 天荒的大事,恩格斯从此更加重视党的合法斗争的研究,主张党团在国会中除了批判揭 露反人民的政策外,还应提出积极的法案。这是马克思议会思想的一大转变:由消极的 变为积极的。1890年2月的国会选举,社会民主党人以取得140多万张选票(将近总票数 的20%)来庆祝自己的胜利和“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它成为恩格斯确立议会战略的转 折点。他开始看到,通过选举争取农民的多数,争取军队的多数是可能的。在这样的情 况下,应当坚持合法斗争,决不能去搞暴力活动给敌人以借口重新宣布党为非法或借此 机会趁党还不够强大时把党镇压下去。这期间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阐述了这一观点。
1893年3月7日,恩格斯给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我们目前应该宣布进行合法斗 争,而不要理睬别人对我们的种种挑衅。”[14](p.359)两天之后,在给李卜克内西的 信中又说:“我们不应当在胜利的道路上受人迷惑,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危害,我们不应 当妨碍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因此,我同意你的意见:在当前,我们应当尽可能以和 平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避免可以引起冲突的任何借口。”[14](p.362)工人领袖不 仅要保持头脑冷静,而且还应当约束不理智的群众。4月12日给左尔格的信就谈到这一 点:“选举的胜利使群众,特别是不久前站到我们这边来的群众冲昏了头脑,他们以为 用冲击就可以取得一切。如果对他们不加约束,那就将做出不少蠢事来。”[14](p.378 )
1892年5月在法国市镇参议会的选举中,法国工人党在22个市镇参议会中获得了多数, 取得了600个席位。恩格斯对这次胜利给予这样评价:“这对于使工人们懂得普选权赋 予他们的行动以多大力量,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9](p.344)他还告诉左尔格:“法 国人日益走上德国人开辟的道路,并在学习如何使用普选权,而不是谩骂它。”[9](p.435)同年11月12日,他又对拉法格说:“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四十年来,只要善于利用 ,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这要比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9] (p.513)
1893年6月,在德国帝国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又获得了巨大胜利。他们得到178万张 选票、44个议席,所占席位比1890年增加1倍还多。这次胜利使德国、英国的资产阶级 舆论大为震惊,同时也对恩格斯产生重大影响。他说:“一个政党这样持续不断地一往 直前,在任何国家都还没有见过。……1893年的增长意味着……在下次普选中肯定将有 更大得多的增长。”[15](p.83-84)他甚至认为,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德国社会民 主党在1900年或1910年就能获得政权[5](p.636)。
到了1895年,恩格斯在《导言》中则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对 工人阶级利用普选权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很高评价,最终确立了合法斗争的战略。在《导 言》中,恩格斯写道,德国工人阶级自从把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倍倍尔选进了帝国议会以 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普选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 国工人效法的模范。……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 ”[5](p.602)恩格斯已经完全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对普选权的作用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第一,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每隔几年检验和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第二,无产阶级政党 所得选票数目的增长是最好的宣传手段,一方面会更受尊重,另一方面也会使人害怕。 即是说,既能增强工人阶级的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第三,各个政党之间所得选票 的比例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它是无产阶级政党估计行动的比例尺。恩格斯曾经 根据德国党1890年的得票情况指出:“有百分之二十的选票投给了党,这是一个非常可 观的数字,然而这同时也表明,还有百分之八十的选票投给了联合在一起的敌人。”[5 ](p.91)在这种情况下举行暴动,无疑是自不量力,自投罗网。第四,竞选鼓动是无产 阶级政党感染群众的最佳手段。无产阶级政党可以深入群众、宣传群众,从而维护自己 的观点和行动,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无产阶级政党的进攻。第五,议会 讲坛比报刊和集会的作用更大。无产阶级的代表可以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地多地向自己在 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扩大和增强党的影响。第六,利用普选权虽然比号 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10倍。它可以使无产阶级逐步地、有成效地占领敌人的 阵地,“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 害怕选举的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5](p.603)总之,恩格斯认为:“世界历史的 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比采 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 革有利的”;通过合法斗争,社会民主党“却长得肌肉结实,面颊红润,好像长生不老 似地繁荣滋长。”[5](p.610)
由上可见,如果恩格斯不是实现了战略上的转变,怎能如此重视合法斗争呢?
三、暴力革命从主要的斗争方式转变成服务于议会斗争的工具
不可否认,恩格斯晚年的确多次讲过不能放弃“暴力革命”的话。例如:1890年3月9 日,恩格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指出:“毫无疑问,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 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14](p.362)1892年,恩格斯在《答可尊敬 的卓万尼·博维奥》一文中声明:“我根本没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将取 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之前,就会使用 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14](p.327)1 895年3月8日,恩格斯致理查·费舍的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 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 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15](p.401 )甚至在《导言》中,恩格斯也提到了“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 革命权”这样的话。许多人正是依据以上论述认为恩格斯晚年仍然坚持暴力革命与合法 斗争两手策略,而没有实现战略上的转变。恩格斯所谓的“暴力”、“革命权”是否指 本来意义上的“暴力革命”即武装起义呢?早在1884年,恩格斯致劳·拉法格的信中对 此问题就已做了初步的回答。他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当武装力量还在反对我们的时 候,我们不会去同军队发生战斗。我们可以等待,直到武装力量本身不再成为反对我们 的力量。在此之前发生的任何革命,即使取得了胜利,也不会使我们掌握政权。”[8]( p.241)1890年非常法废除后,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读者告别信》中指出,如果 新政府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把党再次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这就不得不使德国社会民 主党重新走上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但是即使如此,也决不意 味着进行武装斗争。恩格斯接着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将怎样呢?党将修筑 街垒,诉诸武力吗?党一定不会使自己的敌人得到这种满足。党对历届帝国国会普选所 赋予它的力量的认识,使它不会这样做。有百分之二十的选票投给了党,这是一个非常 可观的数字,然而这同时也表明,还有百分之八十的选票投给了联合在一起的敌人。如 果我们的党在这时候看到,投给它的选票在最近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并且在下届选举时 还能期望选票有更大的增长,那么,除非它失掉理智,否则不会在今天百分之二十对百 分之八十,而且面对军队的情况下进行暴动,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二十五年 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5](pp.91-92)由此可见,恩格斯认为在社会民主党没有取 得人民多数的支持时,即使敌人首先使用非法手段,党也不能诉诸武力,否则将会丧失 掉以前所占领的一切阵地。
然而,社会民主党在取得人民的多数时,能否和平取得政权呢?这正是恩格斯多年来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他虽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的确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在《导言》中,恩格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 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 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 流血牺牲。”[5](p.607)恩格斯在这里表达了一种避免流血,希望通过争取人民的多数 ,比较和平地获得政权的愿望。那么如何才能争取人民的多数呢?
恩格斯首先注意到农民问题。他说:“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已经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 。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该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 ”[5](p.566)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甚至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当易北河以东 地区的农业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5](p.586)
恩格斯也注意到了社会民主党通过议会选举活动争取政府军队中士兵的工作,并赋予 这项工作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在现代军事技术装备(速射枪等等)的水平下,革命应该 在军队里开始。至少在我国,革命会这样开始。”[8](p.254)他估计,“当我们有350 万张选票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远了),整个军队就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当我们取 得多数时,我们的军队将自觉地做法国军队曾经本能地做过的事情,拒绝向人民开枪。 ”[5](p.629)在《导言》的最后,恩格斯还用基督教怎样从备受压迫、禁止的不合法的 “变革党”,经过17年的积蓄力量,使军队中绝大多数士兵成了基督教徒,终于被继任 的君士坦丁大帝宣布为国教这个事实来暗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途。联系到恩格斯多次 说过的如果军队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感染将从统治阶级手中“滑走”这样的思想来看, 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既然恩格斯认为可以和平取得政权,既然认为不能诉诸暴力——武装起义,这岂不与 他自己在90年代多次讲过的不能放弃暴力的话自相矛盾吗?当然不矛盾。恩格斯所讲的 “不合法道路”、“革命权”、“暴力”之类的话,并非意味着真的要诉诸武力,因为 斗争条件的变化使武装起义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换言之,“革命权”主要侧重于“ 权利”而并非“革命”(即武装起义)。恩格斯晚年主要是坚持“暴力革命”的权利而并 非诉诸武力,这一点,也正是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某些机会主义分子的主要区别之所 在。因为像福尔马尔之流甚至连“革命”权利都放弃了,主张在德国这样的专制的国家 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种做法”,恩格斯指出,“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 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它一切机 会主义更危险。”[5](p.274)坚持“革命”的权利之所以仍然十分重要,在恩格斯看来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任何一个政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在内,都不曾否认过在 一定的情况下有进行武装反抗的权利,从来没有一个政党会放弃这种非常的权利。在无 产阶级政党不断面临被宣布为非法的情况下,要求这个政党做出无条件放弃“革命”权 利的声明,“简直是荒谬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已经表明:采取对敌对者顺从 和让步的办法,工人政党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坚持“革命”的权利,才能迫使敌人尊重 我们[8](pp.240-241)。第二,在议会斗争中,“革命权”能够作为筹码和敌人讨价还 价,以便首先把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然后再逐步将其 改造成为民主共和国。在恩格斯看来,“勿庸置疑……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 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5 ](p.274)如果这点能够做到,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旦取得人民多数的支持,就完全有 可能避免流血,和平取得政权。由此可见,“革命权”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无条件 地放弃“革命”的权利,敌人当然会大喜过望,而工人阶级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四、美、英、法等国“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恩格斯认为,“德意志帝国宪法,以交给人民及其代议机关的权力来衡量,不过是185 0年普鲁士宪法的抄本,而1850年宪法在条文里反映了极端反动的东西,根据这个宪法 ,政府握有全部实权,议院连否决税收的权力也没有,正如在宪法冲突时期所证明的, 政府可以对它为所欲为。”[5](p.272)因此,在这样的国家,社会民主党在坚持合法斗 争战略的同时,必须坚持“暴力革命”的权利,社会民主党如果无条件地放弃“革命” 的权利,“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5](p.273)
但恩格斯并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于德国,他也注意到了情况不同于德国的英国、法国 、美国等民主国家。
英国通过1832、1867、1885年三次选举法的改革,议会的权力不断扩大。有人甚至宣 称英国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和把女人变成男人外,可以办到任何事情。”这 虽是夸大之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议会在国家权力中处于较高的地位。早在19世纪50 年代,恩格斯就指出了普选权在英国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意义。他说:“普选权在工业 无产阶级占2/3的英国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单独的政治和一切与此密切相联的社会制度 的各种革命变革。”[6](p.285)马克思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在英国,普选权的实 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它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 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10](p .391)到了70年代,马克思更是满怀希望地指出:“英国是唯一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 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是能够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为本身谋利益。”[12](p.4 68)
马克思在70年代初曾把法国作为必须采用暴力方式的典型国家,而恩格斯则于1884年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把法国纳入“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之列 。这是因为,马克思所说的法国指的是第二帝国和梯也尔政府(1871—1873年),那时法 国的议会民主制只是徒具形式。1875年,国民议会通过了第三共和国宪法,规定:立法 权由众、参两院行使。总统由众、参两院联合而成的国民议会依绝对多数票选出。1884 年又做了重要的补充,规定:政府的共和形式不得成为修改提议的对象;凡曾统治过法 国的家族成员不得当选为共和国的总统。这就从法律上进一步巩固了法国的民主共和宪 政。
对于美国而言,它不仅是美州第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个长期 稳定存在并且逐步得到发展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1581年 建立的荷兰共和国,1649年建立的英吉利共和国,都如昙花一现,只存在几年就消失了 ,都出现过封建专制的复辟,最后都变成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唯独美利坚合众国自17 76年建国以来,国体和政体都没有发生变化。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的国家,行政权赋 予总统,立法权属于国会。美国总统不同于英国的首相,不对国会负责,于是乎人们一 般都把美国总统作为一个权力极大的行政首脑来评价。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事实上, 从立国一直到19世纪后期,美国几乎一直是国会的权力大于总统的权力,有人称之为国 会制政府时期。最重要的是,总统由普选产生,而且不拥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这是它与 当时德国君主制的显著区别。
正因为注意到上述这些区别,恩格斯晚年才没有把针对专制德国的“暴力”论当作暴 力一般套用到其它国家身上。相反,一俟把目光转移到民主比较发达的国家,恩格斯则 几乎完全放弃了“暴力”论,做出了超越以往的崭新论断:“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 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 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 样的君主国。”[5](p.273)这说明,就当时多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合法斗争 应当成为一种普遍的方式,成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战略手段。
恩格斯根据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敢于正视过去的“迷 误”,毅然实现了战略转变,体现了革命导师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锐意进取精神。这 一点正是共产党人永远值得学习的宝贵财富,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永葆生机的源泉。
收稿日期:2001-10-20
标签:恩格斯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哲学的贫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