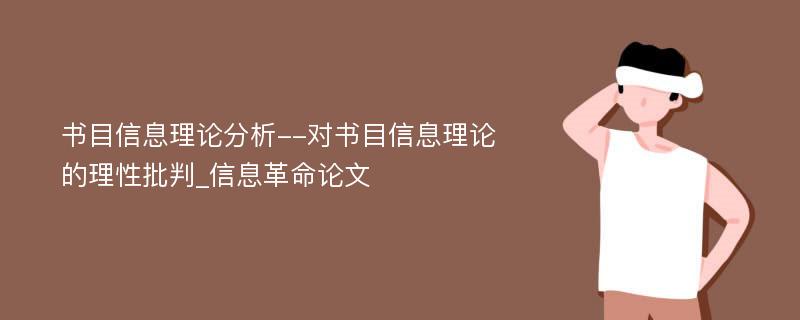
剖析书目情报理论——对书目情报理论的理性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目论文,情报论文,理论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近十余年来,中国目录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新概念莫过于“书目情报”。新近出版的《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1](以下简称《管理》)一书为5位作者的力作,其中不乏成就与建树,是当今我国“书目情报理论”的最新成就与集大成之作,但我们对“书目情报”及其有关理论实在不敢苟同。在此,仅就《管理》一书中所展示的较为成熟、系统的“书目情报理论”以及与当代中国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有关的问题,作一理性的批判,并求教于各位同仁。
2 “书目情报”与“书目情报理论”
《管理》告诉我们,“书目情报”是一“新的术语”,围绕这一术语,“创造”了一系列理论,主要有:“书目情报”之“引入”、“创造”论,“抽象”、“上升”论;目录学“基点”论;“书目的一般理论”与“书目情报理论”等同论;矛盾说“升华”论;“坚持书目情报与书目控制相结合”论;“书目情报系统”论等。其中,“书目情报系统”论中又包括“四种系统”论;“书目情报系统”包含“二次情报系统”论;“书目情报系统”类型划分论以及“结构”、“要素”论等较为丰富的内涵。
2.1 “书目情报”与“引入”、“创造”“书目情报”这一概念究竟从何而来?何时而来?《管理》中提出:“我们曾身体力行,引进了‘书目情报’的概念”。“书目情报理论……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50年代谢拉和伊根的社会认识论,经过前苏联60年代科学交流思想的改造,70年代发展成型,80年AI写作进了高等学校目录学教科书。书目情报理论是传统书目工作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新思想,它的出现被认为是目录学理论的彻底革命,结束了国外目录学以具体书目成果为核心的历史。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创造了‘书目情报’这一新的术语,更重要的是寻找目录学新的基点,动摇了传统目录学的思想体系”。“书目情报的概念80年代中期被引入我国”。
上述引文中提出了“引进”、“引入”、“创造”等三个概念,其中“引进”、“引入”的含义差不多,表示其来源于境外。那么,我国的“书目情报”的概念究竟是“引进”还是“创造”?是一种什么样的“创造”呢?
早在1959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赵继生同志在其一篇文章中一般地使用了“书目情报”[2]这一概念。可谓名副其实的“创造”,但他的这一“创造”受到了中国目录学家们多年不应有的冷落。
1986年和1987年,《目录学》和《目录学普通教程》(中央电大)相继出版,“书目情报”的概念也由此在我国流行起来,近十多年来,几乎成了不少目录学家们理论宝库中的瑰宝,“书目情报”及其“新理论”令人眼花缭乱。以“书目情报”为“基点”开展当代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形成小的“理论流派”,人们私下称之为“书目情报学派”、“珞珈学派”。正是由于该“流派”不少人多年的努力,并对“书目情报”这一“新的术语”进行了再“创造”,遂成今日之小气候。
2.2 “书目情报”与“抽象”、“上升”、“区别”、“高度”、“深度”。十多年来,“书目情报”的宣传者们对这一神秘莫测的概念作过多次定义,叫人莫衷一是[3]。所幸的是,《管理》一书两次对这一概念作了同样的定义:“目录学界正达成一种共识,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区别于表示事物的二次文献概念,是书目文献这种具体概念基础上的抽象概念,是书目文献中关于文献及其识别的情报,是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这样,我们对“书目情报”这一概念的认识终于有了一个权威的版本和依据。
——首先,我们应指出,上述对“书目情报”的定义仅仅是5位作者今天的“一种共识”,而不是5位作者之外的“书目情报”宣传者的“共识”,更不是我国“目录学界”的“一种共识”。中国目录学界从未在任何会议、活动中对“书目情报”达成“一种共识”。中国目录学界“研究基点的不同”历程早已开始。在此,我们提出迥然不同的“共识”。
·依据概念间的外延关系理论,概念间外延关系主要有全同关系、真包含关系、真包含于关系、交叉关系、全异关系、矛盾与反对关系。那么“书目情报”定义中的主要概念之间表现的又是哪一种关系呢?①“书目文献”、“二次文献”之间的全同关系,并用于“表示事物”,是“基础”、“具体概念”。②“书目情报”“是书目文献中关于文献及其识别的情报”,即“书目文献”中含有“书目情报”,“书目文献”概念大于或包含“书目情报”。③“书目情报”“区别于表示具体事物的二次文献概念”——具体概念,即经“上升”、“抽象”、“创造”、“彻底革命”后成为有一定“高度”、“深度”的“书目情报”——“效用信息”;“书目情报”与“书目文献”、“二次文献”的关系即为“具体概念”与“抽象概念”的关系,亦即反对关系。“书目情报”定义之精华亦为“抽象”、“上升”、“区别”、“高义”、“深度”、“彻底革命”等。
依据情报学的理论,“文献是用于固定情报以及传递和使用情报的物质客体”[5],即“文献”与“情报”两者是“物质客体”与“有用知识”、“知识和智慧”的关系。我国国家标准对文献的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即认为文献概念的内涵包括“载体”——“物质客体”与“知识”——“有用知识”、“知识与智慧”——“情报”等两大方面,亦即文献概念包含“情报”内涵。尽管上述两种看法不尽一致,但都不能说明“文献”与“情报”两者之间的“上升”、“创造”的关系。如在我国大量流行“文献情报”概念这一事实就说明文献与情报并不是两个截然“区别”的概念。同理,“书目文献”与“书目情报”两者之间也不是“上升”、“创造”的关系,依据逻辑学观点分析,两者有包含关系、交叉关系,而不是矛盾关系或反对关系。我国至今流行“书目文献情报”、“书目文献信息”等概念这一事实也证明两者之间的交叉关系,而不存在严格的“区别”、“基础”、“上升”、“深度”、“高度”、“革命”等关系。
——为完善“书目情报”的定义,《管理》中还告诉我们说:“书目情报服务作为书目文献具体概念上的抽象,将书目文献上升到效用信息的高度”。这里,作者们认为“书目情报”与“书目情报服务”可共同“作为书目文献具体概念上的抽象”。那么,依此标准,“书目情报”与“书目情报服务”是同一概念吗?
2.3 “书目情报”与“书目”。《管理》一书毫不掩饰“书目情报”与“书目”、“书目成果”、“书目文献”、“书目工具”、“书目信息”、“书目情报信息”等概念的密切关系。但他们从未正式在理论上指出书目文献与文献概念之间的属种关系:书目文献是文献中的一种——书目,即并未正式在理论上正式确立“书目”、“目录”的关系。该书虽说“一些基本概念如目录、书目、二次文献、二次情报服务等是理解书目情报系统的基础”。却并没有进一步指引我们如何对“目录”、“书目”这些基本概念进行“理解”。我们知道,“70年代发展于苏联”的“书目情报理论”曾认为:“苏联目录学家建立了书目在文献交流体系中的功能模型,由文献、书目(包括书目情报)、需求者三部分组成”[6]。“科尔舒洛夫认为书目比书目情报要复杂(具体)得多”,即苏联“书目情报理论”“70年代成型”时,“书目”包括“书目情报”,并比“书目情报要复杂(具体)得多”——书目概念包括和大于“书目情报”的这一概念,两者是真包含关系。
但是,到了“80年代书目情报理论写进了高等学校的目录学教科书之后”,“书目情报”这一概念经过作者们的“彻底革命”和重新“成型”,突然反过来对“书目”概念进行反包括,两者间形成了“基础”、“上升”、“区别”、与“高度”、“深度”等全新的逻辑关系——沧桑巨变,换了人间。
对此,我们的理解是:“书目情报”这一概念中的“书目”概念具有与“目录”概念不可替代的地位,即不能运用目录情报替代“书目情报”,“书目情报”概念中的“书目”已与表示具体“书目成果”中“书目”、“目录”划清了界限——“书目”在此已具有概括具体的目录、索引、文摘的功能[7],即本身就是“抽象概念”。在完成了上述理解后,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书目情报”乃至“书目文献”是在规范、抽象后的“书目”这一“抽象概念”的基础上再次抽象后的“抽象概念”,即“书目情报”概念的本质、本来面貌就是书目[8]。因此,运用形式逻辑理论观察“书目文献”、“书目情报”以及“书目”等概念都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和思维形式。
我们知道,“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4]和思维形式,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是词、词组。概念的这一根本特征决定了不论是“具体概念”还是“抽象概念”,都具有“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的职能,《管理》的作者们轻易断言“书目情报”是“抽象概念”,有什么起码的逻辑依据呢?
2.4 “书目情报”与目录学研究“基点”《管理》认为:“走向未来的跨世纪目录学”应当以“书目情报”为“研究基点”,并对“基点”及“基点”的选择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但我们不敢苟同,并认为“走向未来的跨世纪”的任何一门传统学科,都不能“随心所欲”地“重新选择”和“确立”自己的“基点”。这是因为:我国所有“走向未来跨世纪”的学科大多并没有“重新选择”自己的“基点”,这一个“历史过程”决不能轻易地“因时代而异”。重新选择“基点”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意味着一切从头开始,即至少必须考虑到一门学科的“基点”是否具有某种属概念的功能并能派生出若干种概念?学科“基点”与学科名称之间是何种逻辑关系?学科“基点”与学科基本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是何种关系?学科“基点”与学科领域内诸分支学科的关系等重大问题。
——在信息学、情报学领域,以“信息”、“情报”为“基点”和作为属概念,派生出一次信息、一次情报、二次信息、二次情报等若干种概念。“书目情报”作为“基点”和属概念能否派生出若干种概念呢?迄今为止,“书目情报理论”的研究告诉我们:“书目情报”不具备这种派生出种概念的功能,即使勉强派生出来,也很难说明其概念间的逻辑关系。
——以“抽象概念”——“信息”、“情报”为“基点”的学科主要有“信息学”、“情报学”,其显著特点是学科“基点”自然而然地包括在学科名称之中。与此同时,以“文献信息”、“信息管理”、“科技情报”等为“基点”开展科学研究的学科分别有“文献信息学”、“信息管理学”、“科技情报学”等。其中,“文献信息学”与传统的“文献学”就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其主要区别是学科的基点不同,学科名称也不同。目录学要“彻底革命”,还必须考虑其自身学科名称是否要随之改名?以“书目情报”为“基点”的“创造”首先应考虑是否能构成“书目情报——书目情报工作——书目情报学”这一新的学科核心概念体系的可能[9]?即将传统的目录学以目录为“基点”,并形成“目录——目录工作——目录学”这一传统的学科核心概念体系,再加以“彻底革命”,即彻底引入情报的概念与机制,并将目录学最终改名为“书目情报学”——情报学的亚学科,才是“以书目情报为基点”的“创造”的真正归宿,除此,就是目录学、“书目情报”两者概念与义域之间的矛盾[10]和“混乱不堪”,从而无法开展有效的“创造”与“革命”。这是因为,“目录学”中之“目录”这一“具体概念”、“基础”尚未经“上升”到“效用信息”的“高度”,怎能概括“书目情报”这一“抽象概念”?目录学又怎能成为“书目情报”这一“效用信息”之“高度”之学呢?
其次,尚需指出,一门学科要“彻底革命”不能简单地取决于是否轻易地在原有学科“基点”上后缀“情报”两字。这是因为:①与目录学关系密切的档案学在信息化社会条件下,并没有简单地在其原有“基点”——“档案”后加上“情报”——档案情报,该学科一样具有活力。由此可见,原有学科“基点”后加“情报”一词,并不是文献工作领域内原有学科“彻底革命”的唯一选择,“书目”加“情报”这一模式没有普遍意义。②“书目情报”这一“基点”的“选择”必然导致“情报”、“信息”之间相互解释过程中的麻烦以及与英语"information"对译[11]——目录学国际交往与国际接轨的麻烦。③十余年来,“书目情报”及其理论的研究始终没有摆脱上述问题的困扰,至今仍处在极度混乱之中而不能自拔[12]。如《管理》中先后出现的“书目情报”、“书目信息”这两个概念,实际上都是一种“效用信息”和“高度”、“深度”,但这两个概念的混用,最终将导致“书目情报”概念不能明确与确立。
——“以书目情报为逻辑起点”的《管理》是否提出一套经“彻底革命”后的学科基本概念体系呢?翻阅《管理》全书,并稍经归类后,我们可得到以下一些重要概念(均不包括该书引用的文献):
·“书目”、“书目文献”、“书目系统”、“书目情报”、“书目信息”、“书目情报信息”、“书目情报产品”、“书目工具”、“文献书目线索”、“国际书目产品”、“国际畅销书目产品”、“书目情报产业”、“书目情报系统”、“书目数据库”、“书目数据库系统”、“书目情报数据库”、“文献检索体系”、“联机书目系统”、“北美四大书目服务社”等。
·“二次文献”、“二次文献系统”、“二次文献资料”、“二次文献产业化”、“二次情报系统”等。
·“书目工作”、“书目实践”、“书目情报服务”、“国家书目情报社会关系”、“书目事业”、“书目工作系统”、“书目情报事业”、“书目工作现代化”、“书目工作服务”、“书目情报工作系统”、“书目情报工作”等。
·“书目员”、“书目工作者”、“书目情报人员”等。
·“书目情报理论”、“书目的一般理论”等。
·“书目控制”、“国家书目控制中心”、“全国书目情报中心”、“国家书目情报控制系统”等。
·“书目标准”、“书目文献情报标准化”等。
·“书目分类法”、“书目编纂学”、“书目编制法”等。
上列8组名词中,除最后一组为单纯的“书目”系列外,余均为“书目”与“书目情报”混合的系列。此外,“二次文献”内缺二次情报一项,即《管理》并没有在实践中真正做到“以书目情报为起点”的“彻底革命”——建立以“书目情报”为基点的学科基本概念体系并进行科学论证,也并没有真正“结束了国外目录学以具体书目成果为核心的历史”。根据“什么样的学科基点便会产生什么样的理论体系”原理,我们即可明白,在这种“基点”与非“基点”的任意混合的前提下,“书目情报理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体系”了。为此,我们将在下面继续加以讨论。
——“书目情报”这一“基点”对目录学学科领域内诸分支学科有什么影响与作用呢?具体来说,对专科目录学、目录学史、图书馆目录学[13]、文献编目、文献分类、档案编目、档案检索[14]、档案目录学[15]、比较目录学、文献检索学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什么普遍的意义呢?能衍生出专科“书目情报”、专科“书目情报”学等系列关系密切的概念及相应的理论体系吗?事实是,所谓“书目情报理论在目录学中的核心地位”之说纯系杜撰——它对自己各分支学科的建设至今没有任何影响和作用。
2.5 “书目情报”与“书目的一般理论”、“书目情报理论”在“书目情报”这一“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作者们为我们进一步展示了其丰富的“书目情报理论”,并认为“书目情报理论50年代产生于美国,70年代发展于苏联”,“苏美书目情报理论并非尽善尽美。美国70年代后更注重书目情报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没有确立书目情报理论在目录学中的核心地位,前苏联虽然发展了书目情报理论,但缺乏计算机书目情报实践的探索,特别是没有将书目情报与书目控制结合起来研究,导致应用理论的贫乏”。
在上面的一段理论中,作者们为我们“理解”“书目情报理论”的产生、发展、完善及重大意义等提供了帮助。但是我们认为:
——迄今为止,我们还并不明确“书目情报理论”50年代在美国如何产生及“70年代”如何地“深入研究”?我们注意到:“五十年代谢拉”仅仅是多次运用"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这一术语,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书目控制”理论,并坚持使用书目,而不是使用“书目情报”和提出什么“书目情报理论”;1997年运行的联合国书目信息系统(UnitedNations BibliographicInformation System),仅仅是实践中出现的一个专门概念。其中的"Information"可译成“信息”,也可译成“情报”,即并非国外有严格的“书目情报”概念存在;其次是“在这些文献中并没有阐明书目情报的概念”——即连最起码的概念阐明都没有。因此,完全谈不上什么“书目情报理论”50年代产生于美国和70年代的“深入研究”,即在国外,并未形成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书目情报理论”。
——《管理》一书中提供的理论依据大都源于苏联的科尔舒洛夫。巴尔苏科和科尔舒洛夫的“书目情报理论”中一个最基本的结论是:“就这个概念而言,书目的一般理论就是书目情报理论”[16],即书目与“书目情报”、“微观的书目研究”与“宏观的书目情报研究”、“书目的一般理论”与“书目情报理论”等数者之间并不是什么“抽象”、“上升”关系,而是全同关系。而科氏的上述理论经作者们的“创造”、再次“成型”和与“书目控制”相结合、“迎接新技术革命”后,则变为一种“尽善尽美”的理论,是一种道地的国产货。
那么,由作者们“创造”的“书目情报理论”何以能“结束了国外目录学以具体书目成果为核心的历史”呢?况且,“书目情报”学派迄今在我国还只是一部分人,反对这一理论的还大有人在。如在“书目情报”十分走红的情况下,“书目资料”、“书目信息”[17]、“书目文献信息”[18]、“二次文献”等概念与之相对立地提出。其中,南京大学郑建明先生早在1994年就明确指出:“‘书目情报’术语正在为‘书目信息’所替代”,并以“书目信息”为基点“构筑起自己的学科框架”。
2.6 “书目情报”与“矛盾说”《管理》说,“以‘书目情报’作为跨世纪目录学研究的基点,是矛盾说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升华,体现了信息时代目录学的本质特征”。是为矛盾说“升华”论。
1959年,陈光祚先生试图将马列主义的观点,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一门科学的对象”[19]的论断引入目录学的研究,提出了目录学正是“由于人类巨大的图书财富和读者对图书的一定的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和解决这个矛盾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20],此即我国目录学研究对象“矛盾说”的真正源头。之后,经《目录学概论》、(中央电大)《目录学》等著述的广为宣传并几经修定,“矛盾说”遂成为一种似乎权威、正统的理论而被某些人沿袭下来。陈光祚先生的主要贡献在于:在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引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方法和在这一研究中引入读者用户需求这个过去被忽视的重要方面[21]。数十年后,陈先生修正了自己过去的理论,提出了“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的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22]的新论断。与此同时,杨沛超、张治江、纪晓萍等人多次严肃地指出:“科学研究的对象应是具体的社会或自然现象,而不是什么抽象的矛盾”[23]。但陈先生的合理内涵及杨沛超等人的正确主张并没有引起我国目录学界的足够注意。相反,陈光祚先生最早提出的并经多人修改、补充的“矛盾说”在《管理》中以全新面貌出现:“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导图书资料(文献的信息)与人们对图书资料(文献信息)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并认为“书目情报”概念就是这一学说的“升华”。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
——“矛盾说”最新版本中使用的“图书资料”、“文献信息”、“文献的信息”等概念,本身就不够规范,仅以《管理》一书的惯例及“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情报”等理论,即应分别称之为“文献情报”、“文献情报资源”和“文献的情报”等。
——依据形式逻辑原理分析,“科学地揭示与报导图书资料(文献的信息)”与“人们对图书资料(文献信息)的特定需要”两者均为正概念。两者的负概念为:非“科学地揭示与报导图书资料(文献的信息)”、“人们对图书资料(文献信息)”的非“特定需要”。上述两个正概念之间不存在对立统一关系,亦不能相互转化。两个正概念经拼凑后怎能轻易地成为“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呢?依据陈光祚先生“文献流整序、测度和导向”的思想和哲学、形式逻辑的有关原理可以认定:“目录学领域里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是文献的无序(混沌)与有序的矛盾。
——在“矛盾说”这一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学说基础上“升华”、“创造”出的“书目情报”及其理论有什么科学性和生命力呢?
2.7 “书目情报”与“书目控制”《管理》宣称:“坚持书目情报与书目控制相结合,最新理论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
“书目情报”这一“抽象概念”如何能同“书目控制”中未经“上升”、“彻底革命”的“具体概念”——“书目”、“书目控制”相结合呢?“基点”与非“基点”可任意“结合”吗?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所谓“书目控制”即以“书目”为基础、为工具的控制[24];以“书目(bibliography)”为“基点”的书目学(bibliography)的基本概念包括:书目控制(BC)、国家书目控制(NBC)、国际书目控制(UBC)等,它与“国家书目情报控制系统”、“全国书目情报中心”等概念不属同一个“高度”、体系,两者很难“结合”。纵观《管理》全书,满篇尽为“书目情报”、“书目情报服务”、“书目情报系统”等章节与字眼,“书目控制”则作为一个陪衬,时而又写作“书目情报控制”。我们不知作者们所“坚持”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结合”?
至于“最新理论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之说,也很难让人“理解”,如:①“矛盾说”是旧时代的旧理论,如何能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②我国书目控制现代化相对地落后,如何能“创造”出高于国外的“最新理论”?它的实践土壤、环境是什么?
3 “书目情报”与“书目情报系统”理论
中国“书目情报理论”宝库中还有一重要理论支柱——“书目情报系统”理论。我们对此亦应注意“理解”。
3.1 “书目情报”与狭义的“书目情报系统”“书目情报系统”即“系统”概念的限定——“系统”概念外延缩小,“书目情报”概念外延的扩大,是一种极常见的概念相加,其目的应是以系统的观点去解释、看待“书目情报”——将“书目情报”这一“效用信息”看作一个系统——“书目情报”、“效用信息”系统,离开了“书目情报”这一“基点”,即不存在“书目情报系统”。从这一点看,即为狭义的“书目情报系统”。遗憾的是,《管理》并未提出狭义的“书目情报系统”概念及其包含的子系统。
3.2 “书目情报”与“广义的书目情报系统”构成《管理》在未对狭义的“书目情报系统”作出解释的情况下,便仓促地向我们提出了“广义的书目情报系统”的概念,并认为“广义的书目情报系统是以书目情报为逻辑起点”的包括“书目系统”、“书目工作系统”、“书目数据库系统”和“二次情报系统”四种系统的一个大系统。对此,我们的“理解”是:
——“书目情报系统”的系统构成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概念划分问题,依据逻辑学理论,概念每次划分只能依据一个标准进行,否则就会使划分结果交叉重叠、混淆不清,达不到明确概念的目的,而上述“四种系统”理论的矛盾、错误正在于划分结果交叉重叠、混淆不清。如:①“书目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系统”——“书目系统”;②“书目工作系统”包括了“书目系统”;③“书目工作系统”本身就包括了“机读系统”、“光盘系统”;④“书目数据库系统”即“机读系统”、“光盘系统”,并早已被包含于“书目工作系统”内,但却又单列为一系统;⑤“二次情报系统”包括“二次出版物(书目、索引、目次页等)和可检索的数据库”,与上述三系统形成交叉关系;⑥“二次情报系统也叫二次情报服务”这一理论有什么根据?“系统”与“服务”是同一个概念吗?同理,“书目情报系统”也能叫“书目情报服务”吗?
——依据《管理》中有关“上升”的理论进行考察,“书目情报”与“书目文献”、“书目”之间是“基础”、“区别”、“上升”、“高度”、“深度”的关系——矛盾关系或反对关系,上述概念后加上“系统”两字后,“书目情报系统”与“书目系统”之间就能形成了包含关系吗?
“以书目情报为逻辑起点”的“书目系统”、“书目工作系统”、“书目数据库系统”是否应首先“彻底革命”并“上升”为“书目情报系统”、“书目情报工作系统”、“书目情报数据库”系统后,才能归入“书目情报系统”?反之,传统的“书目系统”、“书目工作系统”、“书目数据库系统”是否不需要“彻底革命”、“上升”即可合格地归入“书目情报系统”?其次,诸如文摘系统、索引系统、文献情报系统、索引情报系统等相关概念到底属于“书目系统”,还是属于“书目情报系统”?我们应作何种“理解”?
3.3 “书目情报系统”与“二次情报系统”《管理》对“书目情报系统”(包括“二次情报系统”)还提出了以下全新的理论依据:“从书目情报服务的发展看,二次情报系统无疑是书目情报系统的主流和方向,但将二次情报系统的概念等同于书目情报系统,则忽略了二次情报系统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根本特点,这类系统主要生产文摘、索引,其二次文献的范畴并未包举无余,不少人将图书馆目录系统、国家书目系统、书业目录系统等排斥在二次情报系统之外,这就使‘二次情报系统’的概念范围仍然是狭义的”。我们对上述理论很难苟同,这是因为:
——对于两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采取形式逻辑的方法,来判别其概念的限定、延伸、全同、异同等。比如依据《管理》提出的“书目文献”、“二次文献”是全同关系,“书目文献”应“上升”为“书目情报”、“书目情报系统”,则“二次文献”同样可以“上升”为二次情报、“二次情报系统”,即“书目情报系统”与“二次情报系统”也是全同关系,而不应任意断言“书目情报系统”包含“二次情报系统”。同理,“二次情报系统也叫二次情报服务”,则“书目情报系统”也可叫“书目情报服务”。那么,《管理》的“书目情报系统”和“书目情报服务”两章也可合为一章。
——判定两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还应依据有关国际、国家标准进行,这是我国当代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国际接轨、向国际标准靠拢的要求所决定的。事实是,在ISO的文件中,“二次文献”概念大于“书目”[25],实际上也就是大于“书目文献”、“书目情报”。我国国家标准认为二次文献是“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整理而成的具有报道性与检索性的文献”,即“二次文献”与《管理》中的“书目文献”的内涵大体一致。依上述标准,“二次情报系统”与“书目情报系统”两者系真包含或全同关系,而不可能得出“书目情报系统”“包括二次情报系统”的结论。
——《管理》对“书目情报系统”包括“二次情报系统”理论所提出的依据是“从书目情报服务的发展看”——即以实践为依据,这固然是应该和值得提倡的,但应以全面、客观和从本质上加以考察为准。为此,我们认为:即使“从书目情报服务的发展看”,“二次情报系统以科学技术情报为中心”并不是其“根本特点”,即其“根本特点”是“二次情报”,至于“不少人”将某些系统“排斥”在外,但也有“不少人”未将这些系统“排斥”在外,作者们又怎能轻易地以偏概全呢?难道我们没有见到中国社会科学信息学会等组织正在开展以社会科学“情报为中心”的“二次情报服务”吗?“二次情报系统”这一概念之下难道不是可以包括科技“二次情报系统”和哲学、社会科学“二次情报系统”这两个概念吗?
3.4 “书目情报系统”与“书目情报工作系统”
——《管理》一方面提出了“书目情报系统”这一概念,一方面又提出了“(我国)书目情报工作系统”这一全新的未经严格定义的新概念。我们不知道这一“书目情报工作系统”与“书目情报系统”、“书目工作系统”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包含?还是“全同”?
——在“(我国)书目情报工作系统”下,《管理》仅为我们列举了“图书馆书目情报系统”、“科技情报系统”这两种概念。在此之前,我们对《管理》在列举概念的方式方面提出过质疑,这里仍须指出:与“图书馆书目情报系统”概念相并列的应为档案馆“书目情报系统”、出版商“书目情报系统”等;与“科技情报系统”概念并列的应为“社科情报系统”。遗憾的是,该书未规范地提出上述有关概念,也未从上述方面加以论证。
——在上述较模糊的概念基础上,《管理》又提出了“确立书目情报工作的社会地位”问题。我们不知道“书目情报工作”与“书目工作系统”、“书目情报系统”、“书目情报工作系统”等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究竟要“树立书目情报系统观”,还是要“确立书目情报工作”观?依据《管理》的“书目情报系统”理论,我们应确立“书目工作系统”观,即只有“书目工作系统”才是“书目情报系统”的合法子系统,但依据“书目情报理论”,“书目情报工作”、“书目情报系统”、“书目情报工作系统”与“书目情报”概念的关系最为密切,即全都因经过严格的“上升”、“彻底革命”,而带有较强的“情报”色彩。我们究竟应“树立”什么“观”呢?
3.5 “书目情报系统”与其类型划分《管理》“按服务对象”将“书目情报系统”划分为公共书目情报系统、科学书目情报系统和咨询书目情报系统三个类型,但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划分的逻辑依据何在。这是因为:①“公共书目情报系统”的并列概念是非“公共书目情报系统”;②“科学书目情报系统”的并列概念是非“科学书目情报系统”——哲学、社会科学“书目情报系统”;③“咨询书目情报系统”的并列概念则应是非“非咨询书目情报系统”或图书馆、文献中心“书目情报系统”、档案馆“书目情报系统”,出版、发行部门“书目情报系统”。所谓的“公共书目情报系统”这一概念为何能同另外两个性质、标准完全不同的概念并列在一起呢?
3.6 “书目情报系统”与其“结构”、“要素”《管理》认为,“书目情报系统”是“多功能的复杂系统”,其“结构”、“要素”为:“书目情报人员、书目情报过程、书目情报数据库”,并认为,“书目情报数据库”包括“书目数据库”、“指示数据库”、“全文数据库”等。《管理》还认为“书目数据库从技术说,是将一个个文献目录记录转换成二进制代码,能够用于计算机阅读和运算的资料档,通常有顺排和倒排两种方法。通常的目录、索引、文摘是数据库的主要产品”[43]。对此,我们质疑如下:
——“书目情报系统”之“结构”、“要素”理论中称之为“书目情报数据库”;“书目情报系统”之“四种系统”理论中称之为“书目系统”、“书目数据库系统”,两者相互抵触,“上升”与不“上升”相互矛盾。如“书目情报数据库”为什么始终未能构成系统——“书目情报数据库”系统?为什么不能进入所谓的“书目情报系统”?
——具有“抽象概念”特征且不能成为系统的“书目情报数据库”,包含有“具体概念”特征的可成为系统的“书目数据库系统”,这有什么理论依据?
——《管理》一书的作者们认为“通常的目录、索引、文摘是数据库的主要产品”,但究竟是“书目情报数据库”还是“书目数据库”的“主要产品”呢?事实上,在我国,“通常的目录、索引、文摘”是“书目数据库”的主要依据,即“通常的目录、索引、文摘”生产在先,转换成“书目数据库”在后,而其作为“数据库的主要产品”则仅仅是开始,尚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对此,《管理》在后面章节中也承认:“计算机在书目工具的编制中尚只能充当辅助角色,也就是说,书目、索引、文摘等书目工具编制的完全自动化尚不能实现”[44]。
——“书目情报数据库”的本质是“书目情报”的一种载体形态——机读型“书目情报”,与其相并列的即为书本型的“书目情报”——“通常的目录、索引、文摘”,两者是平行、并列关系的概念,不存在相互包含关系。
——纵观以上“书目情报系统”理论,“书目情报”仅仅作为一种“逻辑起点”出现在“书目情报系统”内,但运用系统的观点分析,这种“逻辑起点”对系统的构成、作用、功能等并没有什么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及各个层次系统——子系统,“书目情报”对于系统甚至不能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要素”、子系统,又怎能构成“书目情报系统”及“广义的书目情报系统”呢?
4 “书目情报”与“书目情报行业组织结构”
《管理》中还提出了“书目情报行业组织结构”这一概念,并认为“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科学院图书情报中心三大系统,它们是图书情报行业的主要成员,它们之中书目情报服务活动共同构成书目情报行业”。我们不知道“科学院图书情报中心”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简称还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两者共同的简称?亦或是科研图书馆的别称?这三个概念怎能并列而论呢?
5 “书目情报理论”与我国书目工作实践
任何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新理论”的产生、发展,都必须依赖其实践,从实践中产生,并用以指导实践和接受实践的检验。“书目情报理论”作为一种“新理论”、“新思想”,也必须用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严格检验。那么,实践又是如何呢?
《目录学》(中央电大)曾倡导“图书馆和情报单位都应当设置独立的‘书目情报服务部’”。迄今为止,我们未见任何文献工作部门采纳这一建议,没有任何一个“书目情报服务部”建立。
作为“最新理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中关村地区“中国教育与科学研究示范网(NCFC)”,网上运行的“中关村地区书目文献信息共享系统”所使用的是“书目文献信息”,而不是什么“书目情报”、“书目情报系统”等概念。
至于对“书目情报服务”研究中所调查的对象——用户或读者,绝大多数人(甚至是全部)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书目情报”、“书目情报服务”。此外,对目录学各分支学科建设的影响问题前已涉及,在此不赘述。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书目情报理论”的主要特点是:①以“书目情报”这一“抽象概念”为所谓的“基点”和以“书目信息”、“书目文献”、“书目工具”、“书目”等“具体概念”等同时为“基点”;②以某种抽象的矛盾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③“书目文献”需要“上升”、“革命”到“书目情报”——“效用信息”的“高度”、“深度”,而“目录”、“目录学”则不需要同时“上升”、“革命”到目录情报、目录情报学、“效用信息”的“高度”、“深度”;④不需要逻辑方法的推理与思维;⑤以大量管理、组织理论相辅助。
“科学,是理性的事业”而不是少数人的主观“创造”。所谓的“书目情报理论”凭借某些复杂的历史因素堂而皇之地代表了我国“目录学界”某些人的“共识”,但它并不是依靠民主讨论、科学研究而形成的科学理论。尽管它还可能要在我国继续流行、存在一段时间,并取得某些荣誉,但“‘书目情报’术语正在为‘书目信息’替代”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书目情报理论”的终结也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