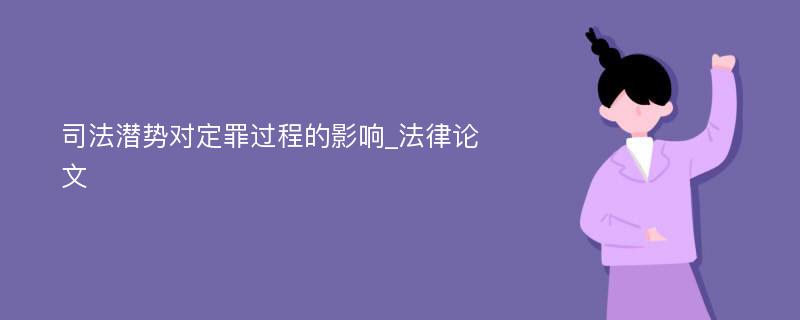
司法潜见对定罪过程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司法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无罪判决并不常见。但罕见不等于没有,且小概率事件背后往往蕴含着大问题。说它背后可能有大问题,首先是因为一直以来,无罪问题在学界就没能成为一个像样的问题。从权威期刊检索结果不难看出,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从正面回答什么是犯罪,很少有研究专注于对什么不是犯罪的考察,集中研究司法实践中无罪判决的论著更是寥寥无几。然而,如果放弃对无罪判决问题的系统研究,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和法律社会学将失去一次极佳的合作机会。①更重要的是,实体定罪条件以外的某种司法潜见,②既是某些案件最终无罪的原因,也是某些有罪判决的原因之一。司法潜见的存在,不仅引发对某些有罪判决可靠性的担心,而且意味着,有法律、法学,并不等于就有法治。
一、如何理解无罪率
法院的无罪判决,通常会引起两个不同方向的关注。一方面,每当出现佘祥林这样的错判案件,③人们便会思考,这种没有把握定罪的案件当初为什么没有作出无罪判决?无罪判决为何凤毛麟角?④许多国外学者往往从这个视角研究无罪问题。2005年,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的《刑法和犯罪学杂志》发表了萨缪尔·格罗斯等人的研究报告。该研究选取从1989—2003年间美国的无罪裁决共340个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其中,绝大部分是由于证据不足,或借助DNA技术发现新的无罪证据而裁决无罪的。作者承认,这些无罪裁决并非美国这一时期无罪裁决的全部,司法事故的范围很可能不止于此。⑤实际上,早在1986年,纽约市立大学的几位教授就基于500个错判案例样本的调查,研究过错案的普遍性、形成原因和相应对策。⑥比较晚近的研究是旧金山大学法学院的理查德·A.利奥等人以《错判研究:以社会科学为视角》为题发表的一篇论文。该文指出,近十年来错判问题研究呈爆炸式增长,说明法学界越来越重视刑事司法中实际上无罪却被定罪的现象。然而,在这个领域,缺乏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与犯罪学的合作研究。⑦无罪判决是错案发生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错判研究是无罪研究的重要视角。
与此不同,对无罪问题的另一种关注来自相反方向。一般来说,无罪判决意味着有罪指控的失败。而问题是,到底该如何理解控方的这种失败?失败是否意味着失误?这里所说的控方,显然主要是指公诉方,因为自诉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毕竟不多。在本研究的样本库中,自诉案件只占所有样本的0.2%,其余99.8%的案件都是公诉案件。因此,这个追问及其回答对检察机关的意义显而易见。目前各级检察机关已经将无罪率设为评价检控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只要出现了无罪判决,相关公诉人员就会在绩效考核中承担不利后果。⑧进一步看,旁观者也想知道,既然无罪,为什么当初被司法机关认为有罪?既浪费了司法资源,又给被指控有罪的人带来各种负面影响。
对无罪问题的上述两种关注都与无罪判决有关,然而,从错判研究角度关注无罪问题,出发点是被告合法权益和人权的有效保护。而从公诉成功率的角度关注无罪问题,出发点是打击犯罪和保卫社会。从这两个出发点提出的问题恰好又由无罪问题关联在一起,揭示了无罪问题研究的真正意义:对无罪问题的深入观察和思考,使“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护人权”这个话语模式不得不面对某种实际上的紧张关系:无罪率过高,会被指打击犯罪不利;无罪率太低,又会担心人权风险被掩盖起来。
其实,“为什么本来无罪却被判有罪”和“为什么实际上有罪却被判无罪”这两个问题可以合并为一个问题:到底该如何解释无罪判决?无罪判决与有罪判决到底有何不同?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检法两家的证据标准不同,法律解释的精准性要求也不同,法律适用对审判机关有着更高更严的要求。这个解释暗示着,指控犯罪可以粗一点,审理刑事案件要细一点。这种关于控审关系的概括显然也站不住脚,因为不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执行的是同一部刑法,同一部刑事诉讼法,说执法标准只是“粗”与“细”的不同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也是对现代司法制度的肤浅误解。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无罪判决意味着控方把本来不是犯罪的行为当成犯罪来指控。这个解释似乎暗含着某种指责:控方对案件的误读或对法律的误解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应该说,这个解释也让人难以接受。其一,即使让法官与检察官的位置调过来,仍然会有无罪判决。更何况,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检法两大群体的人员组成和知识结构已经大体相当,没有太明显的制度性差异。其二,为了考察司法实践中罪与非罪界限的实际操作,我们还在北京市几家基层检察院进行调研,收集了大约200多件不捕不诉案件样本。仔细观察这些样本不难看出,在审判阶段之前,一个案件是否逮捕、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已经投入了大量司法资源。检察官通常不愿意看到一个案件的最终结局是捕了不诉,或者诉了无罪。没有十分的把握,检察官不会轻易把决定一个案件无罪的机会留给法官。这说明,检察官不大可能以牺牲公诉成功率相对降低为代价,换取公诉成功绝对数量的提高。其三,如果认为公诉失败等于工作失误,无异于鼓励检察机关为了降低无罪率而尝试检法之间的私下运作。这种运作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对法院可能宣判无罪的案件作出提前撤案处理。这样,无罪率也许真的得到了控制,可被控有罪的人却被剥夺了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作出无罪判决的权利和机会。
这两种解释尽管让人无法接受,但还是蕴含着某种合理性:从定义犯罪的主体和过程角度,而不是从定义对象本身去寻找无罪现象的解释。当然,沿着这个理论方向进行的考察到底能让我们走多远,还要看无罪判决的大样本经验研究能带给我们多少新的发现。
二、潜见的形成及其对判决的影响
观察发现,法官之所以形成某个案件事实不符合实体定罪条件的判断,很可能与案件处理过程中的某种思维过程有关。比如,“某人实施盗窃一犯再犯,和某个体面人同时被发现在某个失窃现场,于是,窃贼肯定是这个惯窃而不是那个体面人”。这个关于无罪的判断即使结论很可能正确,但仍然不能直接据此得出结论。美国学者布莱克较早注意到类似因素对司法的影响。他指出,即使案件的社会性质是完全一致的,它们所包含的社会信息仍然会使他们变得不一样,并且导致处理差异的产生。⑨在《法与现代精神》一书中,弗兰克认为,传统的概念法学就像那些坚信父亲全知全能的儿童一样不成熟。在审判实践中,决定判决内容的,既不是法律规范,也不是逻辑,更不是概念,而是“跟着感觉(hunch)走”!换言之,要先根据感觉大胆得出结论,然后到法律和学说中去小心求证。⑩
在此类观察的启发下,我们的假设是,某些案件之所以被认为不符合定罪条件,原因之一是司法潜见的影响。司法潜见形成于尚未结案之前,一旦形成某种司法潜见,司法人员会主动地寻找、组织甚至裁剪案件事实和法律根据,有意无意地去支持这种潜见。
从司法潜见与以下几个概念的区别,可以看出其独特性。其一,司法潜见来自于某些刑事诉讼相关的背景信息,如控辩力量是否悬殊,而不是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文化、身份地位等所有信息。因此,司法潜见比社会偏见、社会歧视等概念更接近刑事诉讼过程本身。其二,由于入罪并非司法运作的唯一功能,因此,司法潜见不同于具有负面影响的司法惯性,(11)而是既可能不利于被告,又可能有利于被告。例如,在美国,最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是一名黑人杀死一名白人,其次是一名白人杀死一名白人,再次是一名黑人杀死一名黑人,最后是一名白人杀死一名黑人。(12)这里,司法潜见对黑人而言是负面的,对白人而言则是正面的。其三,与潜见更相近的术语是前见,两者常有交叉重合,但前见的含义更广泛深刻。在哲学诠释学上,前见又称前结构,是伽达默尔定义的一种人们头脑中预先存在的观念及思考方式。(13)在法学研究中,人们也从不同角度注意到前见的存在。(14)而潜见与刑事司法的自身结构以及运作规律有关,因而,具有大体相同前见的个体被分派到不同的司法机关,处于不同的诉讼环节,就可能对同一案件形成不同的潜见。其四,司法潜见对判决结果的影响具有某种潜在性,是在某些案件背景信息渗透下形成的案件处理的隐性推定,而非明确的思维定势或先入为主的判断倾向。导致司法潜见的案件背景信息与案件基本法律事实有关,但并非基本法律事实本身,更谈不上对案件基本事实的采信取舍。因此,司法潜见也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有别。其实,潜在性意味着不规范性,而刑事司法的功效之一正是过滤非规范性影响,这也是关注司法潜见的意义所在。其五,作为思维定势的一种特殊形式,司法潜见还与法律经验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潜见其实是概率现象的主观反映。因此,司法潜见可能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但经验是实践理性,潜见也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在一个反扒专家眼中,匆匆路人只有两类,小偷和常人。但是,反扒专家一旦失手,就不能归咎于经验太多,而应归因于潜见的影响。经验越多越好,丰富的经验使人更加关注对象的特定性、丰富性和唯一性,从而减少误判的可能。相反,潜见越多越容易使人陷入某种归类陷阱而忽略某种不该简化的信息,增加误判的可能。至于哪些司法潜见,如何促成了法官对案件罪与非罪的判断,是接下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三、研究样本及分析
通常,研究无罪判决的常规方法是对无罪判决与有罪判决的判决理由进行直接比较。在这方面学界已有成熟研究,(15)然而,先不说实践中判决理由的说理水平参差不齐,就是这种解释方法本身的客观性和可信性,不可能不因判决书中当然的“自圆其说”有所折扣。在有罪判决中,法官会将所有证据、法律规则组织起来,论证其有罪判决的合法性。同理,在无罪判决中,法官为了证明无罪结果,也会穷其证据和法律根据,支持无罪的判决。将这两种判决理由放在一起比较,将毫无悬念地发现差异,并据此说明罪与非罪的不同。如果某些案件另有隐情,有罪与否的判断实际上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法官便不会将其写进判决书。一些连法官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又的确存在的某种影响因素对判断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就更不可能出现在判决理由中。既然判决书中没有,比较就没有根据;既然无法直接比较,猜测、想象便在所难免。为了避免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本文以判决结果是否有罪为因变量,以大约几十个判决理由以外的其他案件信息为自变量,利用量化分析手段透视它们之间的关系,揭示判决书背后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提炼一般性理论。
本研究的检验逻辑是,如果对有罪样本与无罪样本的比较,没有发现除被告人基本行为事实以外的其他任何显著差异,那么,有罪与无罪的判决结果就只能归因于被告人的基本行为事实。只有当研究发现,有罪无罪两组样本之间的确存在基本行为事实以外的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对理解罪与非罪的不同才有意义,也才能进一步发现这些不同与司法潜见有无关联,进而解释为什么对有些案件做无罪处理。还应说明,这种开放性研究策略对样本的规模、跨度、多样性也有较高的要求。为满足这种要求,本研究的经验材料来自北京大学实证法务研究所从全国各地各级法院收集的刑事判决书数据库。
1.该样本库到目前为止的总规模为32万生效刑事判决。应该交代的是,一个刑事案件中可能有若干犯罪人,一个犯罪人可能被控多项罪名。其中,每项罪名的法律后果才是罪刑关系的最小单位。不论是研究有罪无罪还是罪轻罪重,都应该聚焦这个最小分析单位。这个样本库中的32万刑事判决的分析单位就不是判决书的份数,也不是犯罪人的个数,而是从二十几万刑事判决书中逐一拆分出来的被控罪名及其相应法律后果的罪刑关系个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个无罪判决其实不是指某个案件无罪,也不是说某个被告人无罪,而是指某个具体行为的有罪指控不成立。
2.这个样本库中,无罪判决仅有586个,约占样本总量的0.2%。这个数据是否意味着司法实践中的无罪率,还要看该样本库本身的代表性。需要说明,样本库中还有4395个样本,是根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由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而免予刑事处罚,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的非刑罚性处置措施样本。由于本研究的问题定位在无罪问题,因此,这四千多个免予刑事处罚的样本还是归人有罪样本。
3.这32万样本的空间分布大体上是,东部沿海地区占41.1%,中部内陆地区占50.6%,西部边远地区不到5%,其余样本的地区信息不详。可见,本研究结论将对东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有一定可推论性,但基本无法用于说明西部边远地区的实况。
4.时间上,样本库中97%以上的样本为2000年及以后判决的案件。其中,所占比例较大的几个年份依次是,2010年案例占28.5%,2011年案例占22.1%,2009年案例占21.7%,2008年案例占5.8%,2006年案例占4.5%,2007年案例占4.1%。可见,所研究的样本基本上都是近年来根据1997年《刑法》作出的裁判,具有一定的鲜活性和时效性。
5.从作出裁判的法院层级看,这些样本裁判,76.7%由基层法院作出,20.3%由中级法院作出,2.8%由高级法院作出,0.2%由最高法院作出。四级法院的无罪率顺序与其样本规模的顺序正好相反,分别是:0.1%、0.5%、0.8%和1.5%。就是说,基层法院虽然受理案件最多,但每百个案件中的无罪判决仅有0.1个,而最高法院裁判的案件虽然最少,但每百个案件中的无罪样本就有1.5个。应该说,这基本上反映了受理案件的实际规模以及案件疑难性程度与无罪率之间的关系。
四、四类背景信息下的司法潜见
尽管我们已经说明,司法潜见不等于偏见、歧视,但我们还是对以下几个变量与无罪结果的关系进行了观察。结果证实,在我们的样本库中,无罪率的高低基本上与被告人的某些社会身份特征无关。第一,在样本库中,有13.3%的样本涉及外来人口被告人。而这些样本与其他非外来人口样本两组样本相比,其无罪率都是0.2%。而且,在全部五百多个无罪样本中,有15.2%的样本是外来人口被告人的样本,略高于外来人口样本在总样本中的比例。这至少说明,本地被告人并不比外来人口被告人有更高的机会得到本地法院的无罪处理。第二,样本总数中有将近5%的案件属于少数民族被告人,而在无罪样本中,有8%的少数民族被告人。可以认为,少数民族被告人在无罪样本中的比重略高于少数民族被告人在样本总数中的比重,说明对其是否有罪的判断,司法机关是比较审慎的。第三,从性别差异来看,样本总数中有7%左右的案件属于女性被告人,而在无罪样本中,有9%左右的女性被告人。至少可以认为,女性被告人被判无罪的机会与男性被告人被判无罪的机会大体上相当。当然,户籍、民族、性别并非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我们只能说,在这些有限的观察中,未见无罪率的明显归因。
至此,我们可以着手司法潜见的测量了。我们认为,证据与事实的关系、事实与法律的关系、控辩关系、控审关系,是刑事司法中的四大元素。如果现实生活中真的存在司法潜见,应该在这四大元素中寻找。
(一)证据信息不对称与司法潜见
证据与事实的关系是刑事司法中第一对基本关系,也是发现司法潜见的第一条线索。证据不等于案件事实本身,甚至,证据永远都无法百分之百地还原案件事实本身。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距离的大小,与证据提供者与案件之间的利害关系有关。(16)从这个意义上说,证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直接利害关系的证据,包括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这些证据的大部分提供者至少在形式上与案件中的冲突双方之间保持中立客观的立场。所以,无直接利害关系的证据又可称为中立证据。另一类是无法排除利害关系的证据,包括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这两种证据。与中立证据不同,这两种证据的共性在于,其提供者与案件之间的利害关系明确,不可能具有绝对的中立立场,都希望所提供的证据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方。不同的只是,被害人陈述更可能导致案件处理朝有罪或罪重的方向发展,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更可能导致案件处理朝无罪或罪轻的方向发展。由非中立立场所决定,这类证据往往会掩饰、夸大甚至改编案件事实。
基于证据与案件处理结果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样本进行了两次划分:首先将样本中包含中立证据且包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但不包含被害人陈述的样本提取出来,作为证据更有利于辩方的一组样本;然后,将样本中包含中立证据且包含被害人陈述但不包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样本提取出来,作为证据更有利于控方的一组样本。完成这一操作后,我们对两组样本的无罪机会加以比较。结果发现,非中立证据仅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而没有被害人陈述的样本,在所有样本中的比重为29%,但在无罪案件中,这种证据明显有利被告的样本就占到61.6%,是前者的两倍还多。而非中立证据仅为被害人陈述而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样本,在所有样本中的比重为23.6%,但在无罪案件中,这种证据明显不利被告的样本只占到了0.5%,是前者的几十分之一。就是说,在无罪案件中,有利被告的证据至少在数量上绝对压倒不利被告的证据:绝大部分非中立性证据都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有很小一部分有利于被害人的证据。应该说,无罪案件中这种证据取向的明显倾斜,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案件最终结果有较大的概率有利于被告。(17)因为不对称的证据信息更容易在法官头脑中形成某种有利被告的背景信息,而这种背景信息很可能在法官头脑中形成某种潜见,其直接逻辑结果就可能是被告无罪。至少在证据与事实的关系中,我们无法排除或证否这一司法潜见的存在。
这个发现的意义并不在于证明,何种证据将导致何种判断。这个发现的真正意义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案件中的非中立证据只有利被告,而有的案件中的非中立证据只有利被害人?或者说,为什么会出现证据信息的不对称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刑事诉讼中,将被害人陈述作为一种与证人证言相区别的独立证据种类,本来就是比较特殊的分类方式。其实,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国家,被害人陈述均属于证人证言。因此,无罪案件中证据信息的不对称现象,可能是由于有些被害人陈述被归入了证人证言的范围。如果是这样,上述证据信息不对称的说法就不能成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陈述毕竟仍是一种法定的与口供并列的独立证据种类。况且,它是否应该被归入证人证言的范围尚存争议。一些学者坚持认为,被害人陈述应被视为一种独立证据。(18)因此,一个建设性的追问是,是否应该要求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中只要包含非中立性证据,就应当尽可能追求其对称性、对等性?(19)其实,这种追问本身也是无罪现象的某种解释:除了案件中构成要件事实本身是否违反刑法、该当某罪以外,如何借助证据体系还原、再现这些事实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有些被控有罪的案件最终走到无罪判决。
(二)实体性暗示与司法潜见
对证据清楚的案件,接下来的问题是,有证据证明的某个案件事实,是否符合实体刑法的相关规定而构成某个犯罪。因此,事实与法律的关系是刑事司法中第二对基本关系,也是发现司法潜见的第二条线索。然而,针对某个案件事实的实体性判断不只发生在庭审阶段,还发生在庭审之前的许多个环节。问题是,这些庭审前的实体性判断是否会形成某种司法潜见,对最终的定罪过程构成影响?观察发现,某些司法潜见实际上以一些实体性暗示的形式存在着。在其影响下,一些案件在最终判决结果作出前其实已经没了悬念。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8条,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从字面意义看,所谓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该既包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有罪案件,又包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无罪案件。但实际上,人们很可能将这个条件理解为有罪的案件事实和证据。在我们的样本库中,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占所有案件的40.9%,而在样本库的无罪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只占2%。这两个数据证明,在相当多数人的理解中,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主要是指构成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这种理解不一定是对法律的误解。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8条,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不仅包括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还包括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案件。不同之处只是,后者是被告人自己认为有罪,前者可能是司法人员认为被告人有罪。在样本库中,在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罪的样本中,无一例无罪判决,全部被判有罪。无论怎样,这些先于有罪判决的有罪判断,都意味着某种实体性有罪暗示,而且都在案件正式审理前就已降低了无罪机会。因此,有学者已经注意到简易程序适用中可能存在的风险。(20)理论上说,简易程序的设计理念来自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假定。但其中的效率不应仅指案件快审快决,还应指轻微犯罪行为是否按犯罪处理。然而,在简易程序中,面对定罪还是刑法但书的适用,似乎更多地选择了定罪。
我们发现的另一种实体性暗示是,在有罪判决中,曾犯过罪的人员比例占12.4%,相比之下,在无罪判决中,只有2%的样本涉及曾犯过罪的人员。在有罪判决中,曾被劳教的人员比例占2%,而在无罪判决中,无一例曾被劳教的人员。在有罪判决中,有其他行政前科的人员比例占5%,而在无罪判决中,只有0.3%。可以认为,如果面临刑事审判,曾经犯过罪的人、曾被劳教的人以及有其他行政前科的人,比其他人有更大的机会被判有罪。(21)应该指出,这与累犯制度截然不同。从原因上看,曾犯过罪的人可能构成累犯,也可能不构成累犯,而行政前科和劳教都与累犯构成条件无关。从结果上看,累犯只涉及刑罚轻重,不涉及罪与非罪问题。更明显的是,累犯重罚有法律根据,而上述几类人是否应该有小于常人的无罪机会,不可能有任何法律根据。尽管如此,这几类刑法现象之间还是有一个共性:它们都是法律事实以外的其他因素,明示或暗示着对被告人不利的案件处理结果。
除被告人自身因素外,被告人以外的其他同案被告人也可能成为某种实体性参照物。观察发现,无罪样本中只有3.6%的案例是案件审理时同案其他被告人已经被判刑的样本。而在有罪样本中,则有10.2%的案例属于案件审理时同案其他被告人已经被判刑的样本。即,如果法官知道某被告人的同案被告人已被定罪,那么,就更可能对本案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也许,由于同案的某甲有罪,所以某乙也有罪,这一逻辑是客观事实的某种反映。但如果将这一事实逻辑直接取代刑事司法的定罪逻辑,就意味着,由于经法定程序审理认定的某甲有罪,所以,未经法定程序审理认定的同案被告人某乙也就一定有罪。归谬的结果,事实逻辑当然不能直接取代法律逻辑,但刑事司法中一定不存在这种取代现象?不一定。一些相互印证的证据是,在样本库中,涉黑社会样本的无罪率几乎为零。而且,无罪样本中只有2.6%的案例是案件审理时同案其他被告人因脱逃不在案的样本。而在有罪样本中,则有5.5%的案例属于案件审理时同案其他被告人因脱逃不在案的样本。就是说,如果法官知道,某被告的同案被告人在押中脱逃,那么,就更可能对本案被告人作出有罪认定。尽管影视作品中不乏因蒙冤而脱逃的个案,但人们还是更容易相信,实际生活中多半的在押犯脱逃属于畏罪脱逃。一般认为,分化瓦解,区别对待,是法官常用的策略技巧。对同案不同犯罪人作出的刑事反应有轻有重,有宽有严,将有助于案件的处理。但是,上述证据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当下案件作出无罪认定,已经不大可能对已经定罪或脱逃的同案被告是否与司法机关合作构成积极的策略性影响。在这个前提下,与其作出无罪决定,不如有罪决定来得更加符合常理。
的确,上述几个观察结果都在说明这样一个事实:那些被司法机关认为案件(有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或者被告人自己都承认有罪的案件,或者那些曾经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或者同案其他被告人有罪或很可能有罪的人,的确有更大的可能实施了犯罪。相比而言,不具备这些背景信息的被告人,就有相对较大的机会被认为无罪。至少,此类判断所冒的犯错误的风险的确较小。这就是为什么会形成司法潜见的一个解释,无论有罪判断还是无罪判断,判断失误的风险越小,先前反复出现的概率事件对当下的判断就越可能形成有影响力的司法潜见。尽管如此,任何司法官员都不太会确认,自己的某个具体判断是基于某种潜见作出的。
(三)法律服务市场与司法潜见
对一个案件基本法律性质的判断来说,控辩关系是一个案件能否生成高质量法律问题的关键。几乎所有刑事案件中都有至少一个焦点问题,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实际上可以视为刑事司法对这种焦点问题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无罪判决应该从这些判决中的焦点问题开始。当然,大部分聚焦是否有罪问题的案件最终还是走到有罪判决的结果。同时,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没有集中讨论是否有罪问题的案件就一定有罪。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看到,本研究的意义之一恰好在于提出问题:为什么在有些案件中,是否有罪的问题未被提出?法庭上这类问题的缺席,对案件处理有何影响?
高质量焦点问题的提出不一定导致无罪判决,但没有高质量问题的提出,甚至没有提出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法庭作出无罪判决的可能更是微乎其微。既然焦点问题的质量如此重要,那么,谁更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庭上,被告人一方的各种角色中,最关心诉讼结果的显然是被告人本人,而最熟悉相关业务的应该是职业律师。然而,我们不敢肯定,一个关键性的高质量焦点问题更可能出自被告人本人还是职业律师。被告人为自己所作的辩解可能因为不够专业而无法切中要害,而律师所作的辩护又可能基于成功率的考虑而放弃无罪辩护,只做罪轻辩护。相比之下,除少量自诉案件外,控方是检察机关的公诉人员,不仅业务上训练有素,背后有强大的国家检察机关背景,而且在侦查、批捕、审查起诉等多个环节已有充分准备。在这三者之中,被告人和控方在任何案件中都是必备元素,而职业律师不是每个案件都会出现。于是,我们可以假定,案件中是否存在职业律师为被告提供专业法律服务,意味着控辩双方在力量对比上的两种可能:如果没有职业律师的法律服务,则被告方的力量相对较弱;如果有职业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被告人的境况将相对好于没有律师服务的案件。
具体到无罪案件,这个假设可以转换为:有职业律师参与案件的无罪率应该高于其他案件的无罪率。为此,我们对32万多样本进行观察,结果发现:在全部无罪样本中,有365个样本中有职业律师为被告人提供辩护,占无罪案件的62.3%;只有221个样本中没有职业律师的出现,占无罪案件的37.7%。相比而言,在有罪样本中,只有26.8%的样本中可见职业律师的身影,其余73.2%的有罪判决都没有看到职业律师的辩护活动。就是说,绝大部分无罪判决中都有职业律师的出现,而绝大部分有罪判决中都没有职业律师的出现。换个角度观察,有职业律师辩护的无罪案件占有职业律师辩护案件总数的0.4%,没有职业律师辩护的无罪案件仅占没有职业律师辩护案件总数的0.1%,而无罪案件占总体样本的0.2%。这三个微小的百分比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样一个判断:只要有职业律师的参与,案件审理出现无罪结果的概率就显著高于没有律师参与的案件。(22)反之,职业律师的缺席大大增加了案件有罪判决出现的机会。
一个更细致的观察是,在有职业律师参与的无罪案件中,又可以分为被告人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这两种情况。观察发现,律师参与的无罪案件中,大约90%的案件是被告委托律师,指定辩护只占极小部分。这两种情况对无罪结果的贡献率也存在不同:如果律师的出现是被告人出钱委托的,则有0.5%的机会得到无罪结果;如果律师是由法庭指定的,则只有0.2%的机会看到无罪判决。如果被告人自行辩护,无罪结果的机会只有0.1%。这个差异的显著值也符合小于0.05的要求。换个角度观察,在样本库中,所有案件的委托辩护与自行辩护的比例分别为24%和73%,但在无罪样本库中,委托辩护与自行辩护的比例则调过来,为59.7%和37.7%。可以说,职业律师的出现与否对无罪案件的显著影响,应主要归因于委托辩护,而指定辩护的影响很小。一般而言,委托律师比指定的律师可以得到更高的律师费用。因此,从这个数据分布中最可能推出的认识是,不仅要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介入,而且要有更高费用支付的介入,才会有更大的机会出现无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辩方力量越强越可能出现无罪结果,就是指辩方的法律知识越专业,并且,辩方因辩护服务所得到的收益越高,案件才越可能走向无罪判决。(23)
总之,法律服务市场对有罪无罪的界分也有显著影响。雇不到好的律师,就可能提不出有质量的法律问题,结果,无罪判决出现的机会就随之降低。这是因为,焦点法律问题是连接案件事实与相应法律规定之间的重要纽带。如果这条纽带的发现出自训练有素的律师,显然会有利于被告。因此,有无有利被告的高质量法律问题的提出,在法官心目中会形成完全不同的关于案件的心理准备状态。如果这种心理准备状态事实上对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构成影响,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司法潜见的存在。尽管对无罪案件而言,这种潜见的作用无可厚非,但是,从这个视角观察我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反倒引人思考。有学者发现,我国东部西部之间存在法律职业分布的严重不平衡。(24)而且,由于种种原因,(25)有些律师对刑事辩护采取回避态度。结果,70%的刑事案件中没有律师辩护。(26)从这个视角观察司法潜见与刑事司法的关系,真正引发人们思考的,也许不是无罪判决的解释,而是有罪判决的原因。
(四)控审关系与司法潜见
除了上述三对关系以外,控审关系也会对案件处理结果构成直接影响。在这条线索上我们注意到,案件提起公诉之前,如果检察官相信某个案件构成犯罪,便会对其进行另一种筛选。其中,最常见的选择性操作就是逮捕还是取保候审。在样本库中,逮捕率约为63.6%,取保候审率约为19.3%,说明这是两种最常用的强制措施。除一些信息不详的样本外,拘传和监视居住两项加起来还不足3%。由于逮捕和取保候审决定很可能反映检察官对案件的某种预知,因此,如果要了解检察官的这种预知会不会对法官的决定构成影响,就要比较这两种强制措施最终的无罪机会有无显著差异。观察发现,在203604个采取逮捕措施的样本中,有0.1%的样本最终无罪;而61862个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样本中,有0.3%的样本最终无罪。这两个数据看似差距不大,但相对全库中的无罪率0.2%的水平,两者的差异则意味着,逮捕案件的无罪机会低于平均水平,而取保候审案件的无罪机会高于平均水平。这个检验的显著性水平p=0.00,说明差异显著。可以说,取保候审案件比逮捕案件有更大的可能性最终走向无罪。
这个现象看似细枝末节,却很有意义。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法官面对一个案件时清楚地知道,经过侦查、批捕、公诉等多道工序,案件已经被层层过滤,先后被做过两次划分:第一次划分是罪与非罪的划分,不构成犯罪或者不按犯罪处理的案件被检察机关剔除,其法律形式是存疑不起诉、绝对不起诉或相对不起诉。第二次划分是重罪与轻罪、危险性大与小的划分,法官所能见到的案件其实只是被第二次划分过的这两类案件。那么,这种先于审判阶段对犯罪的分类,会不会形成审前程序的某种潜见对法官的判断构成影响?换句话说,在所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案件中,较重或较危险的犯罪被突出显示,是否在向法官暗示此类案件应该有更高的定罪机会?在上述观察中,检察官对案件的初选主要体现在各类强制措施的选用上。根据《刑事诉讼法》,取保候审的对象包括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或者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等(第65条)。相比而言,逮捕的对象则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第79条)。可以看出,管制、拘役等可能适用的刑罚轻于有期徒刑等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比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嫌疑人、被告人的危险性要小。应该承认,审判之前对案件的这种划分,是法律赋予检察官的一种权力。尽管下一道工序中的法官会想,罪与非罪的问题还没最终判定,何来轻罪重罪?但是,法官不大可能彻底无视检察官对案件的这种初选。至少,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链条:被检察官认为较重或较危险的犯罪案件,更可能采取逮捕措施,而逮捕后起诉到法院的刑事案件则更可能被判有罪,无罪的机会相对较小。相比而言,被检察官认为较轻或危险较小的犯罪案件,则更可能被取保候审,而取保候审后起诉到法院的刑事案件则有相对较大的机会被判无罪。(27)总之,统计结果表明,法官的最终决定并非完全独立于之前检察官对案件的初步筛选。(28)
问题是,应怎样理解之前轻与重或危险性不等的初选,对之后有罪与无罪判断的影响?尽管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这种初选的影响不应该是一种有意而为,但我们还是应该承认,逮捕后被判无罪的案件可能导致国家赔偿乃至一系列紧随其后的负面评价,很可能引发检法之间关系的紧张,对检方而言构成一定压力。捕后无罪率较低这一现象,也许正是避免这种紧张、回避上述压力的某种结果。(29)相比之下,取保候审后被法院判决无罪就显得相对容易接受一些。对控审之间这些微妙的博弈过程,除了用刑罚资源的透支或者逮捕的实体化来说明外,还可以用司法潜见来解释。对一个案件的处理将会给司法机关内部带来何种影响的预见,也会作为某种心理准备状态或者背景信息对案件审理构成影响。
至此,我们完成了四类案件背景信息及其影响的观察,但在得出结论之前还应审慎回应一种可能的质疑:也许正是由于案件本来的确无罪,所以证据信息才不对称,所以才有律师愿意提供法律服务而作出无罪辩护。所以,所谓司法潜见的发现和证实就变得没有意义。笔者认为,绝大多数案件处理结果的确都是因为案件原本就无罪或有罪。但在逻辑上,我们不能反过来用结果推导原因,这无异于否认错判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谁能保证这种错判只是将有罪错判为无罪而不可能将无罪错判为有罪?只要部分案件处理结果可能部分地归因于司法潜见的非规范性影响,只要这部分案件没有少到不符合统计规律上的显著性要求,我们去挖掘这部分案件背后的真实定案原因就是有意义的。至此,我们可以说,用司法潜见解释无罪判决的理论假设得到了证实,司法潜见是无罪判决的影响因素之一。司法潜见源于四种有利被告的案件背景信息,使面对这些案件的司法人员无形中对无罪结果早有心理准备乃至预期,因而提高了这些案件的无罪机会。这四种有利被告的背景信息分别是:向被告倾斜的证据信息,实体性无罪暗示,高质量的辩方法律意见,控方附加给案件的宽宥属性。对每天都会面对大量有罪案件的司法人员来说,这四种背景信息一旦集中出现在某个案件中,无罪几乎就是顺理成章的高概率选项。至少,在这种心理准备状态下,司法人员基本上不会拒绝无罪结论。
五、从无罪看有罪
完成了上述假设检验,我们不可避免地联想,司法潜见的解释力是否仅限于无罪判决?其实,如果换个角度理解四种背景信息,无罪也许不一定是司法潜见的唯一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把向被告倾斜的证据信息表述为证据信息不对称,把实体性无罪暗示表述为实体性暗示,把高质量的辩方法律意见表述为控辩力量对比悬殊,把控方附加给案件的宽宥属性表述为控方对案件的初选。与此前不同,重新表述的背景信息由仅仅有利被告人变为中性信息,既可能有利被告人,也可以不利被告人。问题是,如果案件背景信息是中性的,相应的司法潜见是不是也可能具有双重属性?如果司法潜见既可能导致无罪也可能是某些有罪判决的解释,我们到底该怎样理解有罪与无罪之间的真正界分?
首先看证据信息不对称。在无罪案件中,很多案件没有被害人陈述而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因而更可能形成有利被告人的司法潜见。据此可以推断,在有罪案件中,很可能存在只有被害人陈述而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案件。回看上述样本观察可见,样本库中有23.6%的样本确属此类。对这些案例而言,证据信息不对称实际上表现为不利被告的证据信息。既然有利被告的证据信息可以导致相应的司法潜见,因而导致无罪结果,那么,这百分之二十几的案件之所以有罪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不利被告的证据信息及相应的司法潜见来解释?然后看实体性暗示。与证据信息不对称一样,实体性暗示也不可能只有一个方向。既然有实体性无罪暗示,也应该有实体性有罪暗示。既然无罪案件可以归因于实体性无罪暗示以及相应的司法潜见,那么,实体性有罪暗示也应该可以用来解释某些有罪判决。事实上,在我们的样本观察中,有30%—40%的简易程序和独任审判案件,其无罪率几乎为零。可以认为,这些案件在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无法绝对排除实体性有罪暗示的影响了。加之被告本人有不良记录和同案被告已被定罪等背景信息的作用,司法潜见的负面影响有可能已有相当规模。再来看控辩力量对比悬殊。既然专业律师提出的高质量法律问题可以扭转案件的控辩力量,营造出明显有利被告人的司法潜见因而提高无罪的概率,那么,有些有罪判决是不是可以部分地归因于高水平法律服务的缺席呢?尽管法律说,每个被告人都有权平等地获得法律服务,但是,有人付得起昂贵的律师费,有人只能靠法律援助得到律师服务,有人又出于各种原因而选择自行辩护。于是我们看到,势均力敌的控辩力量对比其实是偶然的,而控辩双方力量悬殊、失衡才是常见现象。这时,我们还有多大把握说,一个案件之所以有罪,完全是由于被告人的行为本身的确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最后来看控方对案件的初选。既然取保候审案件的无罪率高于总体的无罪率水平,原因之一可能是控方认为案件可能被判处较轻的刑罚或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小,那么,逮捕案件的有罪率较高,也应该可以部分归因于控方一开始就认为被告人应该判处较重刑罚或者被告人身危险性较大。尽管一个案件最终是否有罪不是因为犯罪较重所以是犯罪,也不是因为被告人很危险所以应该定罪,但我们还是没能从现有诉讼制度中发现某种有效的阻断机制,使控方有意无意营造的这种不利于被告人的背景信息不至于在法官心中形成某种有罪潜见。
根据以上分析,与案件基本法律事实有关的背景信息既可能有利于被告人又可能不利于被告人,于是,司法潜见也相应地有无罪潜见和有罪潜见之分。我们在证实无罪潜见是无罪判决的一种解释的同时,实际上也一并证实,有罪潜见也会让有些案件比其他案件有更多的可能性走向有罪判决。于是,这些有罪案件的可靠性其实是令人担心的。起初,我们只是假定,司法潜见是无罪判决的原因之一。现在,它的自身逻辑已经把我们从无罪判决的观察带进了有罪判决的分析,发现其真正的理论潜力。
(一)司法潜见位于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二元分析框架的盲区
本研究的知识增量不在于提出实体定罪条件的新解释,而在于发现现有定罪条件的实际运作规律,了解定罪条件是如何与司法潜见交织在一起影响案件处理的。在刑法学中,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是刑法解释论中两种相对权威和前沿的理论概括。坚持形式理性的一方认为,形式解释论基于罪刑法定原则所倡导的形式理性,通过形式要件,将实质上值得科处刑罚但缺乏刑法规定的行为排斥在犯罪范围之外。(30)坚持实质理性的一方则认为,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不能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义上,必须以保护法益为指导,使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可以作出扩大解释,以实现处罚的妥当性。(31)应该说,这一论争为刑法解释论提供了一个穿透力很强的分析框架,绝大多数刑法学问题都能在这个框架中得到深刻把握。然而,司法潜见的发现和证实意味着,司法潜见现象恰好位于这个分析框架的盲区中。
根据我们对司法潜见的观察,司法潜见以潜在的、隐性推定的方式对定罪过程构成影响。所以一方面,尽管法益保护是实质理性说的基本追求,但不排除实践中被扩大解释而与有罪潜见混杂在一起的可能。结果,有些有罪潜见会以法益保护为名无形中挤压无罪判决的空间。另一方面,不论是有罪潜见还是无罪潜见,都可能从刑事法的形式要件中找到支持。一个因有罪潜见而指控乃至定罪的案件,也可能符合形式要件的要求。同理,一个符合定罪形式要件的行为,也可能因实质上不应处罚而出罪。因此,坚持形式理性不必然通向人权保护。司法潜见的存在证明,有些非规范的人为因素,正是借助规范刑事法律制度的形式化运作影响案件处理过程的。当这种影响的结果是有罪判决时,就意味着被告人并不完全是因为符合实体法的定罪条件并依照法定刑事诉讼程序而最终承担刑事责任,而是部分地受到司法潜见的非规范性影响。可见,法的形式要件不仅不是人权保护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且还可能掩盖某些有罪判决中的实质非理性,使其看上去具有相当的妥当性。因此,只有在坚持形式理性的过程中,自觉控制司法潜见的影响,才能更贴近刑事法治的要义。
(二)刑事法治意味着刑事法权利的平等保护和犯罪控制
既然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不是刑事法治问题的终极概括,那么,我们至少有理由从其他角度寻求刑事法治内涵的不同理解。通过上述考察不难看出,证据信息不对称意味着被告人与被害人刑法权利的不平等,实体性有罪暗示意味着行为人之间刑法权利的不平等,法律服务市场的不平衡意味着被告人之间刑法权利的不平等,控审关系中对不同案件的审前筛选意味着当事人刑法权利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发生在刑事司法的不同环节,是司法潜见的不同侧面,所以,刑事司法潜见的要害在于,它把一种看不见的不平等悄悄植入罪与非罪的判断过程乃至结果,并使其获得合法性身份。这就是为什么刑事司法中有法律、有法学,却不等于有法治的一种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刑事法权利的平等保护应是刑事法治的内涵之一。
不过,如果用平等保护解读刑事法治,那么,实现这个意义上刑事法治的最大障碍也许并不来自犯罪现象,而是来自犯罪控制本身。因为从理论上看,司法潜见可以理解为一种犯罪定义学现象。(32)有罪判决其实是法定犯罪条件与司法潜见的综合产物。作为犯罪定义的一种文书形式,有罪判决既无法彻底还原为犯罪定义的对象本身,也无法彻底还原为定义者自身的主体性。这种不可还原性又一次证实了犯罪定义学的一个基本理念:犯罪(有罪)是按照一定主观图式组织建构起来的事实,而不是纯客观自在的对象。(33)组织建构犯罪的这些主观图式除了法定形式要件和诉讼程序以及精美的犯罪论体系以外,还有司法潜见。与规范因素一起,司法潜见也参与了对某些行为的筛选、分类、排序,赋予这些行为犯罪的属性和意义,从而制作出有罪判决。司法潜见的客观存在意味着,即使不存在歧视、偏见因素,司法潜见也不可避免地将犯罪定义者自身的某种属性投射、粘贴到对象身上,在诠释、适用实体刑法的同时,也无意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因此,某些案件所以有罪或者无罪,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案件事实符合或不符合定罪条件,还应当承认定罪条件在被解释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掺入某些主体自身的元素。如果说,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只是一种技术性较强的选择的话,那么,对犯罪定义者来说,是否将刑法平等确定为法治的目标,是一个难度更大的选择。
正如美国学者吉尔兹所说: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是社会的产物。(34)所以,有效控制人为因素对刑事司法的负面影响,自觉控制犯罪控制,才能相对接近刑事法治的理想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犯罪控制的对象不只是犯罪行为,还包括犯罪控制本身。只有当犯罪控制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犯罪行为才可能得到规范、有效的控制。
(三)回到无罪率
由司法潜见的角度质疑有些有罪案件的真实原因,其实践意义之一在于使人们理解司法潜见的不可避免性,进而理解无罪判决的不可避免性。无罪判决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有罪指控错了;同理,有罪判决也不绝对意味着其中的无罪辩解全都无理。因为我们有理由怀疑,有些有罪判决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有罪潜见。与其质疑无罪率太高,不如质疑有罪率是不是真的这么高。零无罪率的提法不仅流露出对现代诉讼规律的无知,甚至有容忍错案、掩饰错案之嫌。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分追求低无罪率是一个可怕的想法。而保持一定水平的无罪率,可以适当调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控方乃至整个犯罪定义系统而言都将利大于弊。至于为什么会提出零无罪率问题,可能已经超出了法学本身力所能及的范围。但可以肯定的是,本研究中0.2%的无罪率水平只低不高,实际上的无罪案件应该高过这个水平。
最后,既然某些无罪案件被掩埋在有罪判决中不能归咎于执法水平失衡或社会偏见歧视,也不能说现行实体、诉讼法律制度本身就蕴含着这种必然性,那么,就应尝试一些建设性的对策建议,积极消减有罪潜见的负面影响。其中,除了要求证据信息对称、鼓励而不是压制律师依法从事刑事辩护等措施之外,在案例指导的实践中建立无罪案例库也许是个可行的尝试。而且,根据同案同判原理,这里所说的无罪案例不应该是经各级法院层层筛选仅限于最高法院发布的所谓精品无罪案例,而应该是全部依法经法庭审理并发生法律效力的无罪判决。作为指导性案例,一个质量有瑕疵的无罪判决,总比一个有问题的有罪判决更加安全。如果这样的无罪案例库实现全面公开,相信对定义犯罪的各方都是个好消息。
*写作过程中,得到苗生明、王平、王新、陈浩、黑静洁、高原等人的支持和建议,特此感谢。
注释:
①储槐植教授提出“刑事一体化”思想(参见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论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页),但一直以来,口头认同这一思想的多,践行这一理念的少。
②司法潜见并非规范法学的术语,而是对司法实际进行考察所发现的一种司法社会学现象。所谓潜见,是由一定背景信息、思维惯性的影响而形成的某种心理准备和行为倾向;司法潜见,是指在一定案件背景信息和长期职业习惯的影响下,司法人员在尚未结案之前对案件处理结果形成的某种定型化的心理准备和行为倾向。关于司法潜见与相关概念的区别,详见后文论述。
③1994年4月11日,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发现一具无名女尸,被认定是佘祥林失踪的妻子。当月,佘因涉嫌杀妻而被捕。同年10月,湖北省原荆州地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死刑。1995年1月,佘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发回重审。1998年6月,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有期徒刑15年。1998年9月,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佘上诉,维持原判,佘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2005年3月28日,佘“死亡”11年的妻子突然出现。2005年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宣判佘无罪(参见《特别策划:佘祥林案——冤案为何办成了“铁案”?》,2005年4月7日,http://www.people.com.cn/GB/news/25064/3300177.html,2012年10月16日;《佘祥林案今日再审 “杀妻者”被当庭宣判无罪》,2005年4月13日,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58116,2012年10月16日)。
④葛琳:《无罪判决为何凤毛麟角》,《南方周末》2005年6月16日,第A5版。
⑤萨缪尔·格罗斯等:《美国的无罪裁决——从1989年到2003年》,刘静坤译,《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6期。
⑥C.Ronald Huff,Arye Rattner,Edward Sagarin and Donal E.J.MacNamara,"Guilty until Proved Innocent:Wrongful Conviction and Public Policy",Crime & Delinquency,vol.32,no.4(October 1986),pp.518-544.
⑦Richard A.Leo and Jon B.Gould,"Studying Wrongful Convictions:Learning from Social Science",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vol.7,no.1(Fall 2009),pp.7-30.
⑧仇新华:《对待无罪判决应持宽容态度》,《检察日报》2009年8月11日,第3版。
⑨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⑩转引自季卫东:《法律解释的真谛(上)——探索实用法学的第三道路》,《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
(11)姜保忠:《刑事司法错误与司法惯性》,《河北法学》2010年第8期。
(12)唐·布菜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第66页。
(13)参见刘星:《法学“科学主义”的困境——法学知识如何成为法律实践的组成部分》,《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14)参见冯亚东:《违法性认识与刑法认同》,《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许发民:《论前见、法律事实与刑法解释》,《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5)参见陈兴良:《对68起无罪案件的实证分析》,《刑事法评论》第1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5页。
(16)参见赵旭光:《刑事被害人陈述的证据学思考》,《证据科学》2011年第1期。
(17)应当承认,我国司法实践中往往更看重被告人供述,甚至夸大口供的作用,而轻其辩解。理论上,这种重供述轻辩解的证据很可能不利辩方,以至于更多地成为有罪的关键证据。然而,这与多数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案件还是被判有罪,以及只有此类证据的案件无罪率高于只有被害人陈述案件的事实之间并不矛盾。
(18)龙宗智:《证据分类制度及其改革》,《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
(19)的确,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处理必须证据确实充分(第53条),但没有规定一个案件的证据必须由全部证据种类构成。相关法条规定的司法人员收集的证据种类,是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第50条)。既然是“或者”而不是“和”的关系,那么,就不是在收集有罪证据的同时,又必须收集无罪证据。
(20)杨宇冠、刘晓彤:《刑事诉讼简易程序改革研究》,《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6期。
(21)有学者指出,在某些案件中,如果被告人的犯罪记录(一种规范的信息)被法官及陪审团预先得知了,那么这些被告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参见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第69页)。
(22)这里所谓“显著”,是指交互分析的显著值p<0.05。
(23)当然,不绝对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被告人不出钱聘请律师是因为确信自己有罪,而舍得出钱聘请律师是因为确信自己无罪。然而,我们也无法排除另一种可能,即被告人聘请律师的目的是为自己减轻罪责。而不论被告人出于何种目的聘用或不聘用律师,法律服务市场与刑事案件判决结果之间的高度相关性,的确是一个引发人们深入思考的现象。
(24)朱景文:《中国法律工作者的职业化分析》,《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
(25)其中,律师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无罪辩护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原因之一(参见成安:《无罪辩护实证研究——以无罪辩护率为考察对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26)谢佑平等:《律师角色的理论定位与实证分析》,《中国司法》2004年第10期。
(27)有学者通过对146个法院无罪判决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在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司法实践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这反过来正好证明,取保候审与无罪判决之间的确存在更紧密的关联(参见陈轶:《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从无罪判决的实证分析入手》,《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2期)。
(28)陈瑞华也发现,在中国,由于逮捕的条件接近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所需要的证据条件,也由于逮捕与未决羁押在程序和理由上都没有发生分离,因此,逮捕决定一旦作出,往往被视为定罪、科刑的预演(参见陈瑞华:《未决羁押制度的理论反思》,《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
(29)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反映就是关于附条件逮捕制度的讨论。尽管许多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但还是有学者发现,实施附条件逮捕后,捕后无罪率提高了,实际上对逮捕条件几乎等同于定罪条件的现象有所改观(参见陈光中等:《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权衡》,《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30)参见陈兴良:《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31)参见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32)参见白建军:《关系犯罪学》,第六章“犯罪定义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33)白建军:《从中国犯罪率数据看罪因、罪行与刑罚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34)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 解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