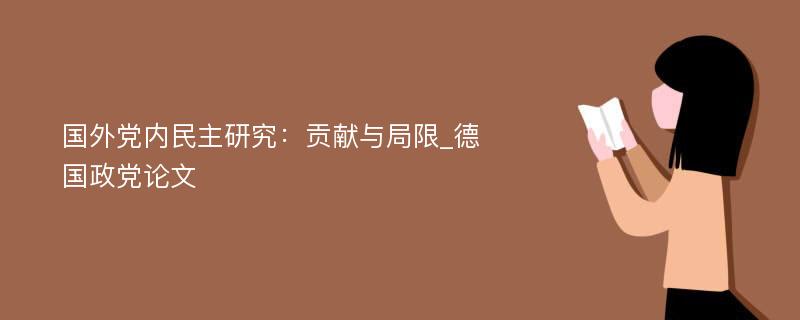
国外党内民主研究:贡献和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民主论文,贡献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5
早在20世纪初,党内民主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外政党研究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比较偏重于方法论的创新,所以他们积累了一些比较新颖的分析视角,但也表现出一些不足。本文试图归纳几种颇有代表性的分析视角,谨供学者们参考和指正。
一、政党组织的视角
政党组织不仅是党内民主研究的重要视角,也是研究其他一切有关政党问题的重要方法。其根本原因是,政党本身是个组织体,组织体的特征和结构影响着政党的行为、制度以及其他政党现象。研究政党的经典作家奥斯特洛戈尔斯基(M.Y.Ostrogorski)、韦伯(M.Weber)、米歇尔斯(R.Michels)都是首先把政党看做是一个组织来进行研究的。他们提出,要想理解和解释政党的活动和嬗变,就必须分析政党的组织内核。从政党组织入手研究党内民主,主要涉及组织结构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因为,只从组织内部讨论党内民主,往往忽略了组织外部因素对党内民主的影响,因此,往往对党内民主得出比较悲观的结论。
1902年,俄国人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出版《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一书,阐述了英美两国政党组织的起因和后果。他不无见地地指出,组织与政治活动的理想相互矛盾,组织是对个人主义的淹没。组织用被操纵的大众意向来取代深思熟虑的个人行动,从而侵蚀个人主义。组织对个人意志的过滤,导致组织意志与个人意见的差异,结果是民主的畸变。如果选举得到了良好的组织,就会使选民投票所反映的不是负责任且又明智的公民们通达的想法,而是反映了协商一致的安排。公众代表的独立见解受制于纪律严明的政党组织的控制,而政党本身又处于政党核心集团的控制之下。因此,选民代表越来越多地为政党领袖的利益所操纵和控制,政党领袖则通过表面上民主的大众支持者组织的活动掩饰他们的权力。民主的允诺使虚假民主得以建立,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换取的却只是一种民众权力的表象。总之,组织是民主走向专制的通道。①
韦伯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利益分化和社会分层加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这样,社会就需要对各阶层、各部门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行协调,行政管理事务迅速扩大。这适应了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趋势,满足了资本主义对效率的追求,官僚制便应运而生,且以技术方面的优势,在社会组织中全面迅速扩展。政府、学校、军队、企业等大型组织毫无例外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官僚体制。为顺应这种趋势,官僚制也在不断地入侵各国的政党组织。韦伯经过研究发现,“在最近几十年中,随着竞选斗争技术的日益理性化,所有的政党按其内部的结构,都向着官僚体制的组织过渡。”②与米歇尔斯相同,韦伯也深知官僚制对政党组织的渗透所具有的潜在危险。不过,他对官僚制的态度却并不像马克思那样激进,也不似米歇尔斯那么悲观,“而是在考察了取代官僚制的其他各种可能的选择,如社团的原则、非专业的行政、分权以及直接民主制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自由议会和由选举产生的责任领导才是现代条件下可以期待的最佳制衡方式。”③
米歇尔斯指出,民主制的理想之所以堕落为寡头制,原因有两个:一是民主自身的缺陷,一是人的内趋本能。他通过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亲身经历发现,那些政党的寡头化倾向丝毫不亚于保守派政党。为什么会如此呢?米歇尔斯解释说,那是因为民主本身的内在局限。民主本身包含着某种寡头制的内核。社会民主党虽然具有民主的理想,但是没有组织,民主是无法想象的。而组织又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所以,即使是革命劳工党也无法摆脱这种政党的困境。由此,米歇尔斯对政党和民主陷入了极度的绝望,“在现代政党活动中,贵族制俨然以民主的面目出现,而民主制则往往渗透着贵族制度的某些成分。一方面,存在着以民主制形式出现的贵族制,而另一方面又有本质上属于贵族制的民主制。”④总之,无论如何,人类也无法避免寡头制的厄运。⑤“‘寡头统治铁律’说明党内民主仅仅是个幻想,因而米歇尔斯认为政治系统的民主也是毫无希望的、脆弱的。他把党内民主看做是国家民主的一个前提。”⑥显然,米歇尔斯政党研究的入口是组织。“事实上,组织是保守逆流滋生的温床,它漫过民主的平原,有时泛滥成灾,并将这一平原冲刷得满目疮痍。”⑦由此得出结论:“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⑧正是政党的组织本质推动其官僚化的进程,从而走向民主的反面。这就是寡头统治铁律的一般原理。
当然,米歇尔斯的观点过于极端了。他的寡头统治铁律的最大弱点是只从政党组织的内部来看待政党,而没有考虑到外部环境对政党组织的影响。因为,“政党组织之间的竞争和议会内政党之间的竞争本身具有寡头特色,同时它也阻止政党官僚在政党组织中把持的统治角色。”⑨在民主体制下,政党之间的竞争性势必推动政党的民主改革,从而抑制政党组织内部的寡头倾向。而且,在成熟的民主政体下,政党组织本身面临着来自宪法和法律的制约,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政党组织向寡头化方向发展。
二、民主理论的视角
民主理论的视角把注意力转移到党内民主与民主政体的关系上来,主要涉及党内民主对于民主政体的必要性、民主政体对党内民主的影响、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的关系、党内民主和审议民主的关系等问题。但是,因为对民主的理解不同,学者们在分析党内民主和民主政体的关系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会给予党内民主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
赖特(William E.Wright)提出的“理性效能政党”,类似于竞争性经济市场的运作。正如商业公司为顾客而竞争一样,政党为选民而竞争。那么,公司应该向顾客负责,而不是向员工负责。同样,政党也应该向选民负责,而不是向其成员负责。⑩因此,政党组织内部的民主并不是民主政体的必要条件。政党和其成员之间不存在民主的逻辑。反之,在民主政体下,政党为了获取竞争性选举的胜利,反而应该通过寡头统治提高效率和团结。寡头统治不仅不会危及民主政体,相反,它是民主政体得以完善的必要条件。正如赖特所言,为获得选举或政府成功,政党必须建立联合阵线来面对反对党和大众。因而在赖特看来,寡头统治是必需的。(11)与赖特的观点大致相似,迪韦尔热(Duverger)认为,民主的决策过程是低效的,它会削弱政党与其对手竞争的能力。“民主的原则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都经由选举产生,要求他们经常更替,具有集体性质,并受到权力约束。但根据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党却不利于进行政治斗争。”(12)他也认为,党内民主不利于政党竞争,会削弱竞争性政党体制下的政党能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有萨茨斯耐德(E.E.Schattschneider)和麦克肯兹(R.McKenzie)。萨茨斯耐德认为,“民主不会在政党内部而只会在政党之间发现。”(13)麦克肯兹认为,党内民主“是与民主政府的运作不协调的”。他说,议会外政党机构控制立法和行政是极权政治体制的显著特征。“政党组织被政党领导人寡头控制,是独立于民主政体的良性运作的。”(14)萨茨斯耐德和麦克肯兹认为,在民主政体下,政党组织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和控制,党内民主和民主政体没有必然关系。政党组织的运作模式是否民主,对民主政体没有负面的影响。政党组织的寡头统治和民主政治的制度运作没有冲突。
与以上学者观点不同,韦尔(A.Ware)和梯瑞尔(Teorell)则认为,党内民主与民主政体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党内民主和民主政体是相互联系的。党内民主不仅不会削弱民主政体,反而会促进政党之间的公平竞争。韦尔赞成根植于竞争模式的党内民主观点。他认为,政党竞争体制不会削弱公正的偏好积聚功能。通过让政党领导人向其成员负责,政党竞争体制可以使政党更加清楚地了解选举人的利益。(15)韦尔认为,党内民主可以促进党内权力的良性竞争,使政党领导人接受其成员的监督,从而避免政党竞争中的一些与民主不一致的现象。而且,党内民主可以促使政党与选举人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有利于政党对选举人的利益进行综合和表达。总之,党内民主不仅不会削弱竞争性政党体制,反而有助于竞争性政党体制为民主服务,是对民主政体下竞争性政党体制的补充。
梯瑞尔从民主理论出发,检视了以往的党内民主理论。他认为,党内民主和审议民主是相符的。“首先,可以将党内民主看做是一种机制,通过选举使立法机构能够对公共舆论反应灵敏。政党可以为公民社会的审议提供联结,使它穿越公众进入政治领域……其次,政党被赋予审议联结的重任是基于问题和组织之间的特殊关系……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政党不仅仅促进和转移论点,也形成观点……审议民主的逻辑要求党内行为与党外行为的一致。只要政党官员同公众审议,那么也有理由要求他们和其党员审议。”(16)再次,“政党不仅仅鼓动和转移争论。舆论不仅在党内形成,政党也形成舆论。最明显的是,政党对公共领域问题解决日程表有巨大的影响。”那么,政党组织内部是否民主自然会影响到公共领域问题日程表的设定是否民主,这就涉及政体民主问题了。最后,“即使党内民主不被看做是审议民主的必要条件,它也很难说服那些与之相反的观点。审议民主的逻辑要求党内行为和党外行为的一致性。只要政党领导人和公众审议,那就有强有力的理由要求他们和其党员审议。否则,可以坦率地讲,如果他们对自己党员的意见都视而不见,我们怎么会相信他们会考虑公共领域中敌对团体提出来的观点呢?”(17)梯瑞尔认为,党内民主可以有助于政党发挥其政治联结功能,也可以实现在民意基础上党内公共舆论的形成,可以对解决公共领域中的问题施加有力的影响,并且党内民主是更大范围的审议民主的基础。所以,党内民主与审议民主是一致的,是审议民主的补充和必要条件。
三、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
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是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借用于分析党内民主问题。以此视角研究党内民主的学者认为,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虽然最初是分析集团问题的,但是用它来分析政党组织问题也适用,因为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所提出的理论假设也符合政党组织的特性。
巴尼斯(Barnes)把政党研究的理论分为三类。一类是规范的。这类理论把政党标示为利益积聚的首要工具。第二类是归纳的。这类理论通过尽可能多的数据来验证一个经验的命题。它从特殊案例中总结出普遍性的结论:政党的目标在于获取公共职位。巴尼斯把第三类称为形式的。这种理论根源于理性人的经济观念,吸收了博弈理论和决策理论的最近成果,与前两类理论有较大的差异。集体行动理论是这类理论的一个典型。
从集体行动理论出发,以意大利社会党为案例,巴尼斯对意大利社会党的内部民主进行了研究,认为,虽然集体行动理论本来是为理解压力集团活动而设计的,但是它也非常适合解释有关意大利社会党的问题。他发现,奥尔森对大组织和小组织的区分是很有用的。显然,包括一些地方领导人在内,许多政党成员并没有从他们的政治活动中获取物质利益。但是,他们未必没有获取非物质利益。除了在政党选举中投票外,政党普通成员没有时间和能力为政党发挥重要作用。大多数组织工作都是由一小部分积极分子和领导承担的。这一核心集团会因为他们的努力而获得非集体性利益。巴尼斯在对意大利社会党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政党目标的设定,来自于政党领导人之间的竞争和联邦组织与地方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政党竞争的另一种形式。在民主的政党内部,领导人为赢得党员支持而竞争,大多数普通党员的非理性动机要求领导人从集体的角度重新阐释他们的主张。简而言之,吸引政党成员的必要性迫使领导人把竞争的非集体性的一面升华为对集体目标的追求——也许只是副产品,并以牺牲他们自己的特殊目标为代价。我要重申:我不否定政党领导人意识形态和利他主义动机的重要性,而是要指出这会限制它对精英行为的解释。”(18)巴尼斯认为,从集体行动理论角度研究意大利社会党可以发现,政党内部的选举和竞争本质上是政党领导人为获取特殊利益的结果,它只是在客观上使党内形成了党内民主的幻象。
巴尼斯认为,政党组织领导人宣传的集体目标只不过是他们获取普通党员支持的手段,政党领导人之间的竞争性选举并不意味着党内民主的存在,它只是政党精英为获取非集体性利益的行为。在政党组织内部,政党精英垄断权力的情况在各个政党组织内部是普遍存在的。“吸引普通党员的必要性是精英冲突的非集体方面升华的基本原因。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党内民主的存在。政党精英联合起来,以抵抗外敌、确定继任者、有效垄断所有精英职位和完全控制政党选举,是可能的。实际上,这种模式在政党组织中是普遍存在的,它也是许多有关寡头制争论的基本原因。因此,他们认为政党选举是必需的,但并不是党内民主存在的充分条件。”(19)巴尼斯认为,政党精英的本性也是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但他们在追求特殊利益过程中却形成了一些民主的特征。然而,政党组织内部在本质上是集权和专断的,“正如集体行动逻辑所暗示的,所研究的这一案例中的政党民主不过是各个领导人追求他们个人非集体利益的副产品。”(20)他指出,集体行动理论对建立分析意大利社会党民主基础的框架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意大利社会党内部两个派系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差异,也可以理解他们的特殊的、非集体利益。它使我们可以理解精英的理性行为与党员的非理性行为之间的差异。
四、议会内外政党关系的视角
自从大众政党兴起以来,如何处理议会内政党和议会外政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各国政党必须面对的难题。这一问题也影响到各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是否可能。因为,议会内政党和议会外政党面临的不同环境会对它们产生不同的影响。议会内政党面临着议会的竞争,并要遵守议会的规则,这往往需要效率和自主性;议会外政党则会直接面对基层党员、支持者和选民,这往往需要民主和代表性。议会内政党和议会外政党的这种差异,会直接影响到政党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和政治运行,因而涉及大众政党的党内民主问题。
霍夫曼(David Hoffman)考察了当党内民主引发政党的议会部分和大众部分之间的冲突时,安大略湖联合农民党组织所面临的困难。那些议会外起源的政党较早地经历了议会党团与大众组织观点的分歧。在许多极端情况下,大众政党对政党政策的极端责任性都是以党内民主原则表现出来的,根据此原则,政党政策是由大众组织的多数票决的,议会党团只是作为其中的成员作出行动。但是,通过竞选成功的议会内政党也许偶尔会迫于压力而向非常复杂的政治现实让步,从而没有严格按照草根组织的原则行事,甚至也许会采取被大众组织理解为与政党政策对立的政治路线。在这一点上,党内民主原则也许会带来真正的困难,正如安大略湖联合农民党那样。在一定条件下,大众政党部分所坚持的政党政策应该优先于议会内政党意愿的观点,也许会导致政党两部分之间的严重冲突。这一冲突实际上对议会代表制和责任内阁制形成了挑战。政党的这一分裂的反作用是非常深远的:不团结会严重影响到政党在选举投票中的成功。(21)除非从政治领域撤离,每一个议会外起源的大众政党都必须面对固有的两难境地:要么仍然真正保留政党发展初期的党内民主,要么改变自己,以适应议会内政党的严酷规则。党内民主原则和责任内阁制政府之间的冲突也许大多被认为是与政党具有较少的民主制而具有较多的寡头制有关。其实,寡头统治铁律为解决两者之间的尖锐冲突提供了一个权力架构。(22)
卡茨(Richard S.Katz)所研究的主题和研究方法与霍夫曼大致相同。他以卡特尔政党为案例讨论了议会内政党与议会外政党之间的冲突。认为,候选人的选举对于政党是非常重要的,但它是一个两难选择。这种两难来源于担任公职的政党成员和草根政党代表之间的冲突,这在卡特尔政党里表现得异常突出。政党领导人对这种两难的回应,是在形式上使候选人选举民主化,而实际上加强中央集权。卡特尔政党通过具有包容性但又非组织化的政党代表选举团创造出民主的假象,而实际上候选人的选举是不民主的。(23)具体而言,在卡特尔政党模式中,政党领导人采用了一种策略,确保他们获得必要的自主性,以有效地参与超政党的事务。这种策略,就是他们在形式上授权给普通党员或者更广范围的政党支持者。它名义上增强了基层党员的权力或影响,但却牺牲了可能有效挑战顶层领导人权力的中层政党分子,而没有牺牲顶层领导人的权力。通过这种策略,卡特尔政党形成了多层级的内部权力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中央领导将在国家层面上赢得自主性,而放弃了地方支部的自主性以及他们对地方事务的了解。这样,一方面议会内政党成员摆脱了基层政党,拥有了自主性;另一方面,候选人(未来的议会内政党成员)的选举表面上处于基层政党的控制之中。(24)
五、最新进展和简要评述
在国外,党内民主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方法已经相当成熟。近年来,人们把眼光更多地投注到社会转型中的党内民主问题。卡杰达·普瑞塞(Khagendra Prasai)非常关注党内民主与政治转型问题。他认为,只有那些在思想、行为和工作风格都民主的领导人才会有助于政党、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化。民主的领导人会在政党的领导人与其他成员之间建立和发展互惠和平等的关系,而非民主的领导人则维护基于不平等的单边关系。(25)换言之,政党领导人的个性也是导致党内民主能否实现的重要原因。捷恩·米恩本(J.Mimpen)从民主化的角度观察党内民主问题。他认为,基于特定的政治举措以及各政党的政治环境,党内民主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在激烈动荡的政治局势中,党内民主面临诸多挑战,甚至不利于民主政体的建立。(26)罗克斯伯(K.Loxbo)以社会变迁为主线,分析了瑞典社会民主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过程中党内领导人自主性和积极分子影响力的变化。他发现了瑞典社会民主党民主化加强的趋势,这种趋势是社会转型的结果。(27)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国外党内民主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第一,西方民主中心论。国外学者对党内民主的研究,其民主概念都是建立在西方的价值观之上的。他们对党内民主的研究也是以西方政党为分析对象。在研究党内民主问题时,很少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和文化,也很少把发展中国家的政党纳入党内民主研究的范围。所以,在西方政党民主研究中,对发展中国家党内民主的研究尚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第二,批判性重于建设性。在西方许多国家,政体民主已经建立和比较完善,党内民主显得可有可无。他们的党内民主研究大多是从政体民主的角度来俯视党内民主问题,因此引起了学者对党内民主的非议和争论。他们在研究党内民主之前就确立了一个前提假设:政体民主高于党内民主(即使肯定党内民主的学者,也是从党内民主对政体民主的意义出发的)。这样,国外党内民主研究很容易形成一种倾向,即忽视党内民主建设问题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很少深入讨论党内民主如何建设。我们在国外党内民主研究的著作中也就很少见到专门讨论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文献。所以,如何从政党本身出发研究党内民主的发展,显得尤其重要。
第三,宣称政体民主和党内民主的独立性。国外党内民主研究大多坚持党内民主独立于政体民主。他们认为,政体民主是国家体系的民主,党内民主是独立于政体民主之外的次国家层次的民主制度。二者是不同层次的民主,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实际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政体民主尚未完善的国家,党内民主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些国家而言,党内民主本质上也是政体民主的重要内容,是政体民主的重要财产,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党内民主比政体民主更重要。
注释:
①[英]戴维·米勒、韦农·皮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49页。
②[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763页。
③[英]戴维·米勒、韦农·皮格丹诺,2002年,第81页。
④[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⑤孔凡义:《组织本质和政党官僚化》,《二十一世纪》(香港),2006年2月号。
⑥Jan Teorell,A Deliberative Defence of Intra-party Democracy,Party Politics,Vol.5,No.3,1999,pp.363-382.
⑦[德]米歇尔斯,2003年,第19页。
⑧同上,第28页。
⑨Klaus Von Beyme,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1985,p.238.
⑩William E.Wright,Comparative Party Models:Rational-Efficient and Party Democracy,in Wright(ed.),Columbus,OH:Charles Merrill Publishing,1971,pp.50-51.
(11)William E.Wright,Party Processes:Leaders and Followers,in Wright(ed.),Columbus,OH:Charles Merrill Publishing,1971,p.446.
(12)M.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Methuen,1954,p.134.
(13)E.E.Schattschneider,Party Government,New York:Rinehart and Company,1942,p.60.
(14)R.McKenzie,Power in the Labour Party:The Issue of Intra-Party Democracy,in Dennis Kavanagh(ed.),The Politics of the Labour Party,London:Allen and Unwin,1982,pp.194-198.
(15)A.Ware,The Logic of Party Democracy,London:Macmillan,1979,p.78.
(16)Jan Teorell,A Deliberative Defence of Intra-party Democracy,Party Politics,Vol.5,No.3,1999,pp.363-382.
(17)Ibid.
(18)Samuel H.Barnes,Party Democracy and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Allyn and Bacon,Inc.p.136.
(19)Ibid.,p.137.
(20)Ibid.,p.138.
(21)David Hoffman,Intra-Party Democracy:A Case Study,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Revue Canadienne d'Economique et de Science Politique,Vol.27,No.2,1961,pp.223-235.
(22)Ibid.
(23)Richard S.Katz,The Problem of Candidate Selection and Models of Party Democracy,Party Politics,Vol.7,No.3,2001,pp.277-296.
(24)Ibid.
(25)Khagendra Prasai,Inner Party Democracy,Conference Paper,2007.
(26)Jeroen Mimpen,Intra-party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Democratization in a Volatile Political Landscape,Conference Paper,2007.
(27)Karl Loxbo,The Fate of Intra-party Democracy:Leadership Autonomy and Activist Influence in the Mass Party and the Cartel Party,Party Politics,Vol.7,No.3,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