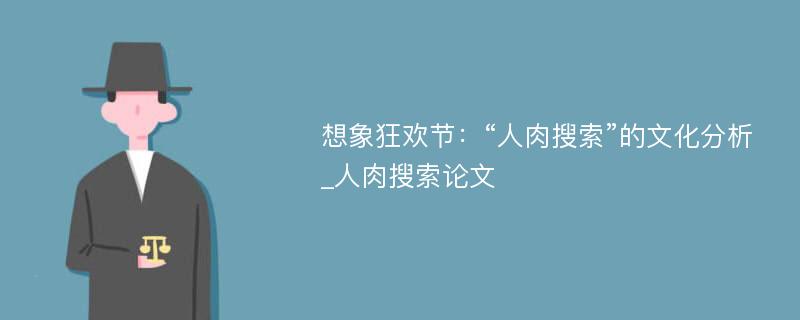
想象的狂欢:“人肉搜索”的文化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学论文,人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你爱一个人,把他放到人肉搜索上去,你很快会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你恨一个人,把他放到人肉搜索上去,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样一句显然是模仿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警句,最近一个时期被人们以一种充满快意并且意味深长的方式一再提起。事实上,从“虐猫事件”到“铜须事件”,从“卖身救母”、“最毒后妈”到“正龙拍虎”,再到最近的“自杀博客”、“真假范晓华事件”、“奥运冠军寻父”等等,作为一种利用人工参与来提纯搜索引擎所提供的信息的机制,“人肉搜索”不仅在网络世界波澜壮阔,更搅动得现实生活风生水起。
互联网上的“百度百科”对“人肉搜索”是这样解释的:
人肉搜索就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变枯燥乏味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声呼唤惊醒万颗真心的人性化搜索体验。人肉搜索不仅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揭露某某门背后的真相,为某三某七找到大众认可的道德定位,还可以在网络无法触及的地方,探寻并发现最美丽的丛林少女,最感人的高山牧民,最神秘的荒漠洞窟,最浪漫的终极邂逅……人肉搜索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肉。
这段解释浪漫而充满豪情,显然出自“人肉搜索”的某位积极拥趸者之手。可以看到,“人肉搜索”不仅可能穿越时空,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大范围内的线索、智慧和力量聚集起来,向着同一个“革命目标”奋勇前进,而且能够打通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的界限,让虚拟世界汇聚起来的智慧和力量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
有关“人肉搜索”所涉及的隐私权问题,以及由此派生的网络民主和网络暴力的问题,线上线下已是众说纷纭。结合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和拉康的镜像理论,我认为,作为网民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的极端形式,“人肉搜索”借助虚拟空间的广场特征,以道德狂欢的方式侵入现实。由于虚拟社区的区位化和同质化特点,对话的可能性被降低了。从根本上讲,“人肉搜索”与狂欢无关。就“人肉搜索”的自我建构而言,“人肉搜索”是一个将异己的群体性的无意识幻象误认为是自我化的过程,占领道德制高点的自信使其表现出强烈的自恋性质。
一、作为网络集群行为的“人肉搜索”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人肉搜索”的具体特征,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近期的例子:
2008年5月20日,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出现了一段长达4分40秒的视频。在这段引起轩然大波的视频当中,一名身穿彩色条纹T恤的女子身处网吧,脚翘在桌上,用轻蔑和幸灾乐祸的言辞大谈对四川地震和震区灾民的看法,其中充斥着激烈和肮脏的字眼。而导致她抱怨和咒骂的全部原因仅仅在于,在为汶川大地震而设置的全国哀悼日里,她的娱乐生活受到了影响:互联网上无处不有关于地震的报道,几乎所有的网页都变成了黑白两色,尤其是她所钟爱的一款名叫“劲舞团”的在线游戏也因为全国哀悼日而临时关闭。
一个小时以后,该视频被网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链接和介绍到了天涯、猫扑等影响广泛的国内论坛,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无以计数的网民震怒了,各种声讨和反击的帖子潮水般涌现。很快,一个号召“13亿人一起动手把她找出来”的“网络通缉令”在天涯社区发起。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由线上到线下,由线下到线上,一场声势浩大的通过网络社区活动寻找视频当事人的“人肉搜索”在整个互联网上迅速蔓延开来。
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通过其上网的IP地址,网友发现该女子上网的具体地点是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的一个网吧。“辽宁女”这个更加简明易记的代号更加快了“人肉搜索”活动的进程。随即,“辽宁女”的QQ号码以及存储于QQ空间中的该女子的年龄、血型、居住地等资料被网友公开在天涯网上。初战告捷,网友们乘胜追击,又以极快的速度对这些资料的真实性进行了核实,更大范围的搜索得以展开——该女子的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家庭成员、具体住址、工作地点,甚至父母亲和哥哥的电话也一应俱全地被“挖”了出来。
“SB”、“无耻”、“脑残”、“智障”、“没人性”等讨伐之词以及越来越多的肮脏字眼开始铺天盖地在互联网上蔓延,针对该女子的各种极端言论也频频出现。甚至,义愤填膺的“四川女”、“北京女”也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自己录制的视频以对骂的方式回敬“辽宁女”。
21日下午1时,沈阳市公安机关根据网上提供的“辽宁女”的信息,在一家网吧将其抓获。警方称,该女因对网吧停止游戏娱乐活动不满而录制了辱骂视频,目前她已对自己的言论表示忏悔和道歉。几天之后,“辽宁女”的父母(?)发帖“向全国人民道歉”。
但网络上的“声讨战”远没有结束。尽管这段辱骂视频虽大部分已不能观看,过激的网友评论也被屏蔽,各贴吧和私人博客却随即成了新的战场,该女子行为是否违法以及如何处理成了新的讨论热点。不仅如此,有人开始怀疑“辽宁女”的行为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商业炒作,而这场商业炒作的幕后黑手正是经营“劲舞团”的那家在线游戏公司。一时间,要求政府封杀“劲舞团”的声音在互联网上此起彼伏。“劲舞团”则发表声明,称与此事无关。
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伴随着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当然更可能是既无“是”也无“非”,互联网就以这样的方式奉献给人们一次又一次“精神大餐”。通过这个实例,我们可以看到,“人肉搜索”起码具有这样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人肉搜索”是一个网络集群行为。在社会学中,集群行为指形成群体的两个人以上的类似行为。一般认为,集群行为具有以下特征:1.自发性,即不是事先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行为,而是受到某种刺激后自发形成的行为;2.狂热性,即行为的方向目标不清,缺乏理智的思考,完全被激情所支配;3.非常规性,即行为不受一般的社会规范约束;4.短暂性,即行为由一时的情绪冲动产生,难于持久。一旦集群解散,成员的归属感和一体感就消失。集群行为的发生是在高度刺激和暗示的情况下产生情绪感染,最终导致情绪爆发。情绪感染和模仿是集群行为形成的主要心理机制①。“人肉搜索”显然符合以上特征。不同于一般集群行为,“人肉搜索”是一个发端于互联网并以互联网为主要场所的集群行为。
第二、智慧叠加是“人肉搜索”的基本方式。互联网不仅体现出信息传递的优势,更体现出智慧叠加的奇异效应。在“辽宁女”事件中,获取当事人的网络IP地址,破译其QQ号码及其QQ空间密码,进而获得当事人及其家人的详细的个人资料,所有的一切既不是某个人独自完成的,也不是有组织进行的,而是在前人智慧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许多人的反复试错和相互修正逐步完成的。而在著名的“虎照事件”中,网友们从不同角度你一言我一语对“华南虎照片”展开质疑,自然和人文科学中的诸多学问、技术纷纷登场亮相,使得“挺虎派”在“打虎派”强大的“智慧攻势”下节节败退;而“华南虎年画”的发现,同样是全国各地网友智慧叠加的结果。不仅如此,在这场网络剧中,网友还创造出一些有意思的成果,除了出现“顶片叶子”等新网络词汇外,还创造出一个新的“成语”:正龙拍虎。网友给出的注释是:1.意指某人或某集团为利益驱动做假,被揭穿后还抵死不认;2.社会公信力缺失。这就使得智慧叠加不仅具有拨乱反正、查明真相的“侦查”意义,而且同时显现出具有强烈反讽特征的社会喜剧意义。正如有媒体所指出的,华南虎事件告诉我们,互联网正在将越来越多的个体智慧联结成更大的集体智慧。
第三、“人肉搜索”的参与者包括三类:侠客、哄客和看客。侠客是“人肉搜索”的主要作战兵力,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不遗余力地积极投入到各种线索的搜集与核实中,他们的每一个成果都不仅使“人肉搜索”的战场捷报频传,而且极大提高了自己在网络社区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看客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人群,他们有的对“人肉搜索”充满憧憬,有的则持保留态度,也有的可能持反对意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只浏览网页而不进行公开发言。当然,不论持何种立场,对“人肉搜索”的关注、好奇甚至难以名状的窥视欲望,可能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哄客,则是“人肉搜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喜欢凑热闹,习惯跟风,发现公共场合的人事纠缠,不论事情大小,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飞奔赶到,组成如墙如堵的庞大观众圈子,形成唇枪舌剑的观战之师;他们爱打老虎,自我感觉良好,在“人肉搜索”展开的虚拟空间中,他们各个化身为道德景阳冈上的武松,恨不能有三头六臂,拳打脚踢,必欲将对象置之死地而后快。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本身未必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获得一种娱乐的快感、道德的优势和兼而有之的自我实现。
第四、非此即彼的道德判断。道德问题是“人肉搜索”的基本关注点之一。“虐猫事件”关注的是对于动物的爱心,“最毒后妈”、“卖身救母”和“冠军寻父”关注的是亲人之间的关爱和亲情,“铜须门”和“自杀博客”关注的是有妇之夫的疑似偷情和婚外情,“正龙拍虎”和“真假范晓华”关注的是政府的诚信和官员的责任。很明显,道德拷问是“人肉搜索”得以形成和展开的根本动力。如果说,前面所谓的“看客”是道德领域沉默的大多数的话,那些“侠客”显然就是网络上的道德“民兵”。作为人们约定俗成的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道德问题从来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尤其是,在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混杂在一起的互联网世界,道德问题的复杂性更是不言而喻。但是,“人肉搜索”过程中,道德倾向不仅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而且显示出超越法律的强烈的“杀伤力”。换言之,道德武器成为人们最易获得、最常使用且最便于聚集力量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法宝。
二、狂欢的可能和不可能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对“人肉搜索”所引发的隐私权问题忧心忡忡,对其表现出来的暴力化和娱乐化倾向痛心疾首,甚至有人直接视之为“多数人的暴政”,但也有人对“人肉搜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欣喜,视之为网络民意的反映,甚至是网络民主的牛刀小试。事实上,简单地用“暴政说”或“民主说”,都还不足以揭示“人肉搜索”的复杂性。因为,在民主、自由和主体精神方面,“人肉搜索”既有其推动作用,也有其阻碍作用。积极方面,比如在“正龙拍虎”事件中,正是由于网民通过“人肉搜索”所展示出来的超常智慧和强大力量,真相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浮出水面。如果没有“人肉搜索”,也许我们至今还在为一场彻头彻尾的“政绩秀”而欢欣鼓舞。消极方面,“人肉搜索”的暴力倾向和娱乐化倾向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在“真假范晓华事件”中,一名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青年女干部,仅仅因为与他人“重名”而被“人肉搜索”的利器“误伤”:一则关于5月20日晚有人在四川绵阳五一广场搭建救灾专用帐篷并恶意伤人的网络传言,竟莫名其妙地把她给卷了进去。尽管此范晓华非传言中的彼范小华,但强大的网络“人肉搜索”引擎依然给这位共青团女干部带来了莫名烦恼和心灵痛苦。没有人对此事负责,没有人关心“误伤”的后果。对几乎所有的参与者来说,过程比结果重要,也更引人注目。事实上,在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网络集群活动中,无论是暴政还是民主,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一种“狂欢式的世界感受”总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至少表面上如此。
网络空间是一个与现实世界有着巨大差异的虚拟世界。现实世界的社会组织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组建起来的,人们按照科层制安排的等级秩序处于一定的位置,扮演相应的角色,拥有确定的沟通渠道和相应的话语权。任何出格的言行都可能以被社会孤立、遗弃和惩罚为代价。在基于网络世界的社会组织即虚拟社会中,科层制的传播模式被打破,社会成员获得了平等的话语权和传播权,成员之间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沟通,“组织结构也相应的呈现出由集权化到分权化、由等级化到扁平化的转变”②。而在巴赫金的体系中,狂欢的中心场地只能是广场,因为“广场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东西,在充满官方秩序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世界中仿佛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力,它总是为‘老百姓’所有的”③。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广场,而“人肉搜索”显然就像是这个广场上最盛大的一场狂欢。
“狂欢”是巴赫金思想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概念之一。这个源自于民间文化的词语被巴赫金发展成为一种反霸权力量、一种建立大同世界的文化策略,并因此在诸多的人文社会学科中被广泛地借用。对于狂欢所带来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巴赫金以“随便而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俯就”、“粗鄙化”等四个范畴来加以描述④,也就是说,在网络世界的每一个虚拟社区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进行狂欢,消解等级,脱离体制,打破常规,降低格调,有众声喧哗之喜庆,无单语独白之隐忧,即便是污言秽语、胡言乱语、疯言疯语,也能同金口玉言、巨旨宏言、九鼎之言相安无事、相得益彰甚至相濡以沫。而在往往是围绕道德事件展开的诸多的“人肉搜索”实践中,这样的特征显得尤为突出。我们至少可以概括出以下几方面表现:第一、就语言场景而言,加冕、脱冕、易位、换装等等在广场狂欢中通过物质道具实现的角色扮演,在网络狂欢中通过主体赋名得以实现。在文字的面具下,网民们可以肆意扮演英雄、魔鬼、淑女、荡妇、总统、乞丐、贤德者、无耻者等角色,降格粗俗、矫揉造作、阳春白雪之名都充满自嘲与他讽。第二、就语言风格而言,网络语言自成一体并成为传统语言的反叛者。它不仅具有黑话、行话和俚语的特征,而且肆无忌惮地突破常规的词法句法,甚至刻意地通过错字怪词病句,通过颠三倒四、自相矛盾、断裂跳跃,通过插科打诨、对骂互损、污言秽语等方式追求特殊的效果⑤。这样的狂欢式的语言实践,在诸如天涯、猫扑、新浪、搜狐的任何一个虚拟社区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尤其是在诸如“虐猫事件”、“铜须事件”、“卖身救母”等关系到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审判的“人肉搜索”中、甚至在“正龙拍虎”、“真假范晓华事件”等有关政府诚信和官员形象的“人肉搜索”中,那些“侠客”和“哄客”的网络语言特征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如果我们由此断言“人肉搜索”具有巴赫金意义上的狂欢本质,恐怕显得过于草率。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前提是对两种世界、两种生活的区分。第一世界是官方的秩序世界,它严肃正统、等级森严,在其中充斥着对权力、权威、教条、戒律和死亡的屈从、崇敬和恐惧;第二世界则是平民大众的狂欢世界,它是在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起来的完全“颠倒的世界”⑥。在这个广场式的狂欢世界中,人们平等交往,尽情嬉戏,众声喧哗,一切和阶级、身份、门第、财产、职位、年龄有关的区分和界限都被打破,一切和神圣、等级、逻辑、理智有关的东西都被颠倒、亵渎、嘲弄和戏仿。而网络世界,尽管它可能具有浓厚的平民大众的气息,但却很难与“彻底打破等级制、打破一切的界限与区分”画上等号,因为,网络交往的匿名性尽管可以使许多有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和地位的暗示暂时被屏蔽起来,但它并不因此使之彻底消失。现实世界的各种权力关系虽不直接反映在虚拟世界里,但却会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成为其翻版。恰如莱恩格尔德所说,在网络世界中,“话题就是地址”,而有地址就会有地缘关系,就会有形形色色的权力关系⑦。
事实上,虚拟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更是一个虚拟的现实世界。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虚拟世界整体上尽管可以表现出巴赫金意义上的所谓的“广场”特征,但是它的存在往往并首先是以虚拟社区的形式展现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虚拟社区的地方也就有“江湖”,有形形色色的权力关系的角逐。网络是扁平化的,但网络社区并不是扁平化的。在任何一个虚拟社区当中,并不是每一个不同的社区成员都享有相同的权力。每一个虚拟社区都会有意见领袖,会有意见领袖的崇拜者,会有想方设法成为意见领袖的人,会有各色人等形形色色的表演。我们既可以看到网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智慧叠加”的狂欢过程,也可以看到因为个人智慧以及个人智慧的成果(即各种各样的新线索)而表现出来的“英雄意识”、“领袖意识”和在社区中的地位变迁。在虚拟世界中的个人地位的变迁也许并不直接影响现实世界,但是,对于具体的网民来讲,它的意义确实不可小觑。显然,虚拟世界并非总是一个扁平的、打破了一切等级和界限的世界,它和巴赫金所谓的第二世界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更重要的是,虚拟世界具有强烈的保守性,这一点几乎被人们所忽略。网络的超越时空性使得人们可以在实体性的社会群体之外,获得一些保持并发展其独特旨趣的个人空间,这是它的积极意义。同时,网络的超越时空性也使得人们不再需要克服自己的偏见、先入为主和固有的思维方法而轻易获得他人的认同。其结果就是,偏见、先入为主和固有的思维方法因为没有与他人产生冲撞的可能而日渐强化。由此,无穷无尽的虚拟社区得以产生,不同的社区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而同一个社区内部却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同质性,当然这并不排除社区内部的纷争。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亚文化群体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悲观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区位化的网络亚文化群的兴起,意味着虽然网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量的增加,人们共享的信息却愈来愈少;另一方面网络使那些孤僻的个体和团体聚集到一起,形成更加紧密排他的组织,从而促成了狭隘的亚文化群的发展⑧。换句话说,在虚拟社区中,对话的可能性不是被加大了而是被减小了。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肉搜索”常常会和“网络暴力”结伴而行。
按照巴赫金的理论,狂欢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颠覆等级制,主张平等的对话精神,坚持开放性,强调未完成性、变易性、双重性,崇尚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摧毁一切与变更一切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⑨虚拟社区及活跃其中的“人肉搜索”在颠覆现实世界的等级制度的时候,在虚拟世界建立起了新的等级制度,在众声喧哗的狂欢氛围中以内在的强烈同质性驱除了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它表面上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但却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并预设了一个道德审判的主题。这样,巴赫金所强调的未完成性、变易性、双重性以及死亡与新生的精神就被轻而易举地置之度外了。从根本的意义上讲,“人肉搜索”与广场狂欢无关,至少在巴赫金的意义上。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抹杀“人肉搜索”的现实意义。在这里,理论的分析已经显得多余。我们只需回顾一下张承志在长篇小说《金牧场》中关于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的一段叙述,道理就尽在其中了:在极度压抑的社会氛围中,在阴风凄凄的天安门广场上,当普通的民众只能或者只是以一朵白花、一首小诗甚至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子来曲折隐晦地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和对邓小平的呼唤的时候,有人点燃了广场上的汽车,随着火光一闪,主人公突然产生了关于“历史是什么”、“革命运动是什么”的新的感悟:“也许小痞子、愣头青、小胡同串子们就这样粗野地撕下了历史的旧一页”,“他觉得他从此和北京痞子之间建立了不能割断的情谊”,“痞子们是伟大的”⑩。在“人肉搜索”中,尽管投身其中的“侠客”和“哄客”们常常显出非理性的甚至地痞流氓式的某些特征,但假如没有这些“网络暴民”,我们可能会对许多的社会丑恶视而不见,甚至可能在许多问题上长期甚至永久地受到蒙蔽。所谓的理性,在很多的时候其实是非理性的。
三、自我的幻象
如前所述,由于主体之间展开对话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人肉搜索”尽管具备了“狂欢”的表象,但却在平等性、变易性、未完成性等意义上与巴赫金所谓的“狂欢”相去甚远。但是,尽管如此,对于参与到其中的网民来说,“人肉搜索”却是网络世界中一个自我实现的媒介。面对既相互隔离又相互链接的数以亿计的电脑屏幕,他们以ID代号(网名)作为同他人区分开来的标志,用屏幕上的字符作为自身情感和思想的载体,通过在键盘上快速翻飞的手指,在同他人的交往和互动中,不断地展示自我、重塑自我、甚至发明自我。从这个角度来讲,“人肉搜索”就不仅是“道德民兵”面对具体的危机事件所展开的一场合力围剿,而且是虚拟主体之间在网络界面上展开的一场相互促动、相互建构的重塑自我的游戏。在这场游戏当中,主体不是以意识为中心的自我统一的主体,而是由他者介入而异化和分裂的主体。主体是双向去中心的,而真实的主体乃是无真正自我意识的主体。
关于以“人肉搜索”为代表的网络道德围剿的基本特点,天涯网网管麦田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极端不负责任,不去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2.网友争抢道德的制高点,一旦占据了所谓的道德高地就开始用合理、合法的语气攻击他人;3.非此即彼的“圈子文化”,不做朋友就是敌人;4.煽动者从不列举事实,只凭臆断宣泄感情和煽动网民情绪(11)。这样的总结非常形象,生动地勾勒出了“人肉搜索”的基本面相。但是一些基本的问题显然是被忽略掉了:为什么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原本文质彬彬、温柔敦厚的网民,一旦面对网络界面就会变得失去理智、甚至杀气腾腾?所谓的“道德的制高点”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原本四分五裂、甚至在道德观念、价值判断上往往千差万别、相互抵牾的网友们,在互联网上面对道德问题的时候却能够出奇的一致,甚至表现出一边倒的情形?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在网络世界和在现实世界有何不同?借助拉康关于“镜像阶段”的理论,我们可以以“界面”、“认同”和“自恋”三个关键词对诸如此类的现象进行阐释。
1.界面:脱域机制。与现实世界相比,“人肉搜索”所赖以展开的网络空间是一种更为直接的脱域机制。这是由网络空间的支配性逻辑,即卡斯特尔所说的流动性逻辑所决定的。所谓脱域,按照吉登斯的说法,就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2)。去涉身性、去情境化、去特定性和非人格化是它的基本特征。作为网络社会动力机制的核心,流动性不仅支配着网络社会的信息流动和社会互动,而且使得自我在现实世界中所赖以存在的时间空间,以及现实世界中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和权力关系被抽离、被虚化,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特性。在“人肉搜索”中,我们所观察到的形形色色的狂欢的表象,显然就与网络空间的这种脱域机制息息相关。
在网络空间中,使得脱域机制得以实现的基本因素是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网络界面。在网络活动中,网络界面的作用类似于镜像阶段理论中的镜子,它不仅是网络世界两种或多种信息源面对面交互之处,是现实主体通往虚拟世界的桥梁,也是自我和他者相互作用的中介。脱域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自我对网络界面凝视的结果。
自从面对网络界面的那一刻起,不仅笛卡尔式的自我同一的主体被颠覆,笛卡尔意义上的主客体界限也被消解,上网行为成为一种波斯特所说的“在主客体边界上的”活动,成为了一种发生在主客体边界上的临界事件(borderline event),其边界两边的主客体都失去了自身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在网络世界当中,“主体没有停泊的锚,没有固定的位置,没有透视点,没有明确的中心,没有清晰的边界……主体如今是在漂浮着,悬置于客观性的种种不同位置之间。不同的构型使主体随着偶然情境的不确定而相应的被一再重新构建”(13)。换言之,由于对网络界面的凝视所产生的脱域机制的作用,主体成为一种边界模糊、虚实交织、充满不确定性和自我分裂的混合主体。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对于参与“人肉搜索”的网民来说,真实生活只不过是诸多窗口之一,甚至还不是最好的一个。
2.认同:无意识幻象。如前所述,“人肉搜索”是一个网络集群行为,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感染和相互模仿是不可避免的。“人肉搜索”中智慧叠加的过程,既是“破案线索”的层出不穷和环环相扣,也是成功激情的逐级高涨和相互刺激,同时,还是道德认同和自我道德想象的不断加深和持续拔高。在“人肉搜索”的过程中,一方面,每一个侠客或者哄客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共同的革命目标”添砖加瓦;另一方面,每一个侠客、哄客甚至包括大多数看客在内,都在从别人的一言一行(电子书写行为)中获得快感、满足和想象性认同。
从主体建构的角度来说,在“人肉搜索”中,网络界面不仅是主体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主体之间寻求相互理解、相互印证并形成交互主体性的过程。一方面,当他人借助于文字以及各种各样的网络表意符号呈现在主体面前的网络界面上的时候,他人的形象需要主体通过想象的过程来加以完成;另一方面,自我的形象也需要通过在网络界面上的书写得到他人的认同。由于网络世界通过虚拟社区在与现实世界相隔离的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权力角逐的空间,因此,在网络界面上对于自我形象的书写从来也不可能是为所欲为的,而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以他人的视角想象自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在网络界面想象自我的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将自我作为他者来描述的。主体的电子书写行为所表达的与其说是对自我的想象,不如说是主体假想的他者对该文本的诠释。这也就是说,“人肉搜索”中的电子书写行为,是一个在类似于拉康所谓的“镜子”的网络界面上想象自我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通过他者(他者的电子书写行为)建构自我的过程。
考虑到“人肉搜索”的集群性特征,考虑到网络虚拟社区的区位化和同质化特征,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人肉搜索”中常常表现出强烈的一边倒的道德倾向:“人肉搜索”过程中的自我建构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形色色的侠客、哄客和看客彼此复制对方大脑的过程,而由此所建构起来的自我,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群体性的无意识幻象。这样,当自我被交付给群体的无意识幻象的时候,自我的断裂和碎片化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我们吸收他人各式各样的步骤与想法时,他们即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同样的,我们也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充斥各种声音的多元文化社会,使人们浸淫在不一致与风马牛不相及的自我语言中。”(14)这样的过程,既是一个“同化”的过程,又是一个“异化”的过程。之所以说“同化”,是因为它是人肉搜索的参与者一次发现自我的过程;之所以说“异化”,是因为这里的发现仅仅是一次“误认”——将异己的群体性的无意识幻象误认为自我的过程。
3.自恋:道德制高点。在镜像阶段,婴儿对影像的认知和认同在本质上是虚幻的,但伴随这一过程的却是喜悦和快乐。婴儿不仅对镜子中的影像充满着迷恋,而且努力控制这一影像并与之交互嬉戏。对镜中影像的成功控制使得婴儿不仅充满快乐,而且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成就感。尽管这一影像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因为镜中影像所反映的婴儿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并不是婴儿自己独立取得的,而是在父母的帮助扶持下获得的),但它却给予了一种连贯的、协调一致的身份认同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矫正自我、使影像得当的期冀和承诺。于是,婴儿与自己的身体建立起一种欲望关系。在这种欲望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是自我的自恋本质。
对于“人肉搜索”的参与者来说,尽管面对诸如道德沦丧或者诚信缺失之类的事件,他们感到痛心疾首,但是,搜索的过程本身却是一件极其快乐的事情。在一种群体性的无意识幻象中,他们不仅在发现线索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智慧上的成就感,而且能够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使他们在摆脱了现实世界的道德迷茫和精神无助之后,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重新构建出自己明确而坚毅的道德幻象。尽管他们那些明确而坚毅的道德幻象可能只不过是似是而非的教条或者非此即彼的独断,但对他们来说,这也许就是一种执著、一种坚守、一种勇毅,他们为此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并在不经意之间把自己的网络影像当作自己爱恋倾慕的对象(15)。更何况,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他们和自己一起竞相攀登道德制高点,既相互竞争又相互激励、相互赞赏,即使有些微的反对之声那又算得了什么!“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是一种多么豪迈又多么宏伟的体验啊!
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中,出于竞争的需要,婴儿与自我影像、婴儿与他人之间不仅存在着一种依恋关系,而且存在着一种攻击性和竞争性。拉康认为:“侵凌性是种与我们称之为自恋的一个确认方式有关联的倾向,这个确认方式决定了人的自我的结构形式并也决定了这个世界特有的质存事物的结构。”(16)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那些“人肉搜索”的侠客们在以纯而又纯的道德利剑向那些事件当事人刺去的时候,总是那么的勇毅和决绝;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人肉搜索”的过程当中,稍有观念上的抵牾,便可能恶语相向甚至拳脚相加(当然是以虚拟世界的方式)。显然,这是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侵略性,而这种侵略性又是与侠客和哄客们的道法自恋紧密相关的。
“人肉搜索”以一种粗鄙的方式介入到我们的精神世界。无论如何,我们既不能对其在民主和主体精神方面所带来的突破寄予过高的期望,也不能简单粗暴地视其为一无是处的洪水猛兽。在谈到人的解放时,马克思曾经说过:“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路。”(17)此言极是。
注释:
①参见汝信主编:《社会科学新辞典》,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364页。
②黄少华、翟本瑞:《网络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③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④参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林、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76—179页。
⑤胡春阳:《网络:自由及其想象》,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⑥⑨巴赫金:《拉伯雷研究》,第13页,第614页。
⑦参见段伟文:《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⑧参见戴维·申克:《信息烟尘:在信息爆炸中求生存》,黄锫坚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24页。
⑩张承志:《金牧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
(11)赵晓、胡媛:《网络编辑:我们在反思》,载《法律与生活》2006年第13期。
(1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3)M.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7—20页。
(14)雪莉·特克:《虚拟化身:网路世代的身份认同》,谭天、吴佳真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8年版,第368页。
(15)这种自恋不仅表现在网络空间,它常常会从虚拟世界沉降到现实世界。举一个例子:在“自杀博客”事件发生以后,网友不仅在网上公布了出轨的老公以及第三者的工作单位、住址、电话和照片,而且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当事人的工作单位和家庭所在地的居委会施加压力(事实上,居委会哪里管得了这样的事情)。不仅如此,数十位网友还自发地组织起来,从全国各地甚至有人专程乘坐国际航班从新加坡聚集到跳楼自杀的女白领姜岩生前住过的小区,向死者坠落的地方鞠躬、默哀、献花,久久不能离去。其实,与姜岩事件类似的因婚姻变故而寻短见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为什么唯有这个事件激起如此大的反响,引发网友超乎想象的、不合常理的悼念行为呢?这显然和“人肉搜索”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和源自于群体性无意识幻象的强烈的道德自恋密切相关。
(16)《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6页。
(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