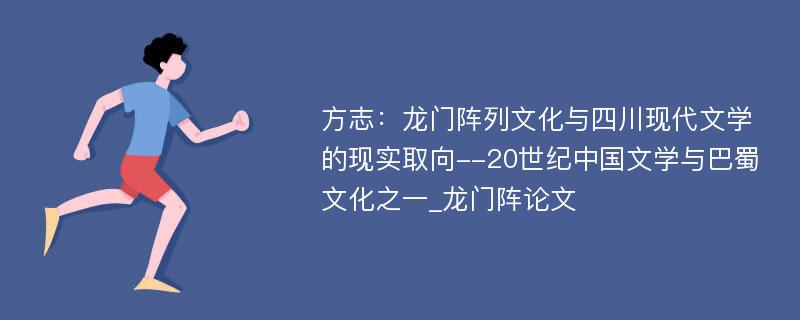
地方志——龙门阵文化与现代四川文学的写实主义取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写实主义论文,地方志论文,取向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Ⅰ71.9
考察现代四川作家与四川文学,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作家就其个性特征而言都是青春气质十足的,许多的创作也洋溢着一股诗意的激情,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现代四川文学就失去了写实的风范,逃逸出了生存事实的土壤。实际上,恰恰是抒情与写实的双重追求,构成了四川文学世界的宏富景象,那么,现代四川作家的写实主义追求有些什么特点,而这一追求又有着怎样的文学文化渊源呢?
一
从总体上看,现代四川文学的写实主义追求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本色化”,一是倾向于对故乡特别风物的表现。
“本色化”就是尽可能地潜沉自己的情感冲动,抑制那些斑斓的理想,以一种冷静的姿态呈现生活的“原样”。并不是每一位走向写实主义道路的中国作家都选择“本色化”,大量的外省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萧军、王鲁彦、许钦文、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等都以各种方式将写实与自我的情感(或理想)结合了起来。有趣的是,恰恰是本来不无诗情澎湃的四川作家在他们转向写实的时候格外注意“本色化”,这既表现在巴金、艾芜、沙汀、林如稷、陈翔鹤等人的转向过程之中,也表现在李劼人、罗淑、周文、刘盛亚等较为一贯的追求之中。“本色化”的写实甚至让不少的四川作家都博得了“冷峻”之名。
“冷峻”的写实,这样的艺术选择显然令我们想起了这些四川作家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密切关系。比如,李劼人1919年留学法国,系统学习和翻译了以福楼拜、龚古尔、莫泊桑、左拉、舍尔比列、浮茫丹等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作品,且深有研究,1932年撰有长篇论文《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在《少年中国》上发表,此种艺术经验在李劼人一生中刻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迹。正是由法归来,他才开始了自己创作生涯中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当我们谈到李劼人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特征的概括,如“真实的观察”、“赤裸裸的描写”、“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以及反对“凌空蹈虚”的浪漫主义等,难道不可以一眼见出这正是李劼人小说的艺术追求么?沙汀自称“是在所谓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染缸里泡过来的”,周文经由张天翼的小说受了狄更斯、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熏陶,其他诸如罗淑之于左拉、罗曼·罗兰,艾芜之于果戈理、巴尔扎克、福楼拜,巴金之于契诃夫等等,均可以清楚地见出中外文学深厚的渊源传承关系。
不过,全面考察四川作家的创作风貌,我们就会知道,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接受,他们是有选择、有目的的。他们所“期待”的其实是对故乡特别风物的表现,这种从异域文学中寻找启发转而表现四川特别的世情风俗的追求,实际上构成了现代四川文学写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李劼人借用着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细腻的写实,但呈现的却全然是一个社会、历史与地域意义上的四川。这是每一个读他小说的读者的共同感受,而且愈是来自四川或熟悉四川的读者,愈能品读出其中的滋味来。巴金读罢赞叹说:“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都活在他的笔下。”[(1)]郭沫若对李劼人冠以“中国左拉”,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又强调说这里所写的是“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是笔调稍嫌旧式的“四川大绸”,又说,过去在成都的生活”都由他的一支笔替我复活了转来。这,必然是有莫大的效果为局外的人所不能领略的。”[(2)]以法国自然主义的生理学眼光是无法透视李劼人小说的,他的意义在于社会、历史与地域。对于乡土气氛的看重同样也见于其他一些四川作家。沙汀虽然曾为乡土是不是构成了自我束缚而困惑,但从总体趋向上看,还是很为自己作品的乡土色彩辩护的,且“以为这是我们创作界近十年来一点显著的成就和倾向”[(3)]。罗淑读着法俄文学作品,创作的设想却是把“小时的生活和四川的一些特别情况”[(4)]描写出来。周文呢,因为绥拉菲莫维奇《铁流》和张天翼《二十一个》的军旅题材而折回到记忆中的川康边地,产生了具有乡土特色的《雪地》。“因为他们的那种行军生活,使我想起了西康的兵,就那么写出来了。”[(5)]巴金不谈小说创作的世情追求与乡土特色,但以当今读者的眼光看来,从近现代之交的成都大家庭到战云密布下混乱与败落兼备的大后方,左拉、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的艺术技巧似乎也是在这种对乡土的回顾中才真正得心应手起来,尽管这未必是自觉的。
那么,这种竭力展示地方世情风俗的愿望又有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呢?沿着这样的追问,我们重新发现了四川方志文化的独特意义。
二
四川地区治史之风源远流长,其中地方志的撰写尤为突出。历代四川文人都特别重视地方史志的修纂工作,据《中国地方志》一书的统计,我国现存历代方志凡8273种,按方志所属省区划分,居前五位的分别是:四川672种,浙江592种,河北567种,山东541种,江苏540种。四川以多出第二位80种之数,遥遥领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巴蜀修志之盛。[(6)]
地方志历来被看作“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7)]。无疑,在一个因为远离中央政权而常正史所疏漏的地区,地方志的修纂尤显必要,而愈是地理偏远,内部风俗殊异,也愈为方志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这大概就是巴蜀志文化厚重的一大原因。文化的代代相承、层层积淀,在四川形成了一种表现本乡本土特殊风貌(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方志意识”,较之鲁迅将绍兴视作中国社会的缩影,沈从文将湘西视作人性的净地,四川作家更突出地意识到四川生态的“地方性”,他们似乎也颇有兴趣来开掘和表现各自地域的独特面貌。大至四川作家的口头禅“我们四川”,小至其各自钟情于所在地的乡土风俗,都似乎一再显示着“方志意识”的深入人心。除了写小说,李劼人还积极搜集了各类四川方志,40年代曾创办《风土什志》,自任社长,创办《四川时报》副刊《华阳国志》,又与郭沫若、马宗融等发起创办《蜀风》半月刊,这几种报刊杂志都强调对地方风土人情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四川历史、地理、民俗、方言的文章。抗战时期,李劼人撰写了《中国人之衣食》系列文章43篇,还特别“查考了成都一些史料,写了约15万字的近似地方志的一篇东西,叫《说成都》”[(8)]。直到1958年他还提笔写了《成都内一条街》。郭沫若的小说并无方志特色,但他本人却目光敏锐,一语道出李劼人三部曲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这也表明,“方志意识”对现代四川作家的影响是广泛的。
我认为,方志文化及由此形成的方志意识从总体上影响了现代四川作家的写实特色。
首先,现代四川作家都比较注意从自身所生活过的特定的地域选取故事,这些故事大多带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很难为其他地域的同类故事所代替。同样是旧中国的实力派人物,沙汀笔下的林幺长子、代理县长们提劲撒野、横蛮无忌,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赵太爷、七大人举止矜持、一脸庄重,张天翼笔下的族绅长太爷满口道德、凛然严正。这里,是浙江鲁迅的人物和江苏张天翼的人物更为接近,而四川沙汀的人物却较为“特别”;同样是旧中国的劳动妇女,李劼人推出了一系列泼辣大胆、置传统道德于不顾的川妹子如邓幺姑、伍大嫂、黄澜生太太、陈莉华等,而在江浙及北方地区的作家笔下,我们却更多地读到了一些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媳妇与姑娘,如鲁迅的祥林嫂、叶绍钧的“伊”、台静农的翠姑、萧红的小团圆媳妇;同样是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自浙江的夏瑜、“疯子”、“狂人”(鲁迅)、肖涧秋(柔石)和来自江苏的倪焕之(叶绍钧)以及来自湖南的莎菲(丁玲)都不同程度地表现着新时代的追求及因这种追求而带来的痛苦,相反,四川作家笔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却大多脆弱平凡,或有追求也包藏在平凡知足的外表之下,如沙汀的刘述之、孟瑜,李劼人的郝又三、楚用。当然,其他地域的中国作家也有属于各自地域的独立特征,具有各自的地域意识,不过,我仍然感到,像鲁迅、叶绍钧、萧红这样的作家一方面利用着本乡本土的资源,另一方面却力图将这种乡土的资源提升为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概括,所以他们笔下的故事既带有区域性,又往往大大超乎区域。我们读鲁迅、读叶绍钧、读萧红,似乎并没有津津乐道于其地域性的“特别”,更没有因为不曾生活于浙江、江苏或东北,就丧失了对鲁迅、叶绍钧、萧红小说细微精妙之处的体味。或者说,我们是在鲁迅、叶绍钧、萧红等人的地域故事中读出了整个中国的故事,乡土只是感受的托盘,它托着我们升向更高更广阔的理性认识的空间;而在四川作家的地域故事中,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则转化为对此乡此土的“特别情况”的关注和思索。所以在四川作家那里,愈是他们写实求真的成熟之作,就愈只能发生在四川本土(这是不是一种宿命?),而你愈是一个熟悉四川各地乡风民俗的人,才会愈加深入地体味出其韵致来。郭沫若说李劼人作品中的某些内容“必然是有莫大的效果为局外的人所不能领略”[(9)]。李劼人则这样评价沙汀的作品:“老沙的东西,四川人读起来特别感觉有味,外省人读,恐怕就要差一点啦。”[(10)]王余杞说:“关于故乡,我自信比较别人知道的多一些,不仅知道,而且认识了解,——关于当地的特殊出产和特殊的社会情形。”[(11)]
讲述乡土的“特别”故事,也使得四川作家往往成了某一生活形态或历史事件的独一无二的发现者、记录者。李劼人是保路运动最杰出的记录者,沙汀是川西北乡镇生活唯一的描绘者,罗淑是沱江流域盐工与桔农生活的最成功表现者,周文是川康边地灰暗生活唯一的记录者,刘盛亚是川东城镇生活与船工生活最优秀的揭示者。巴金呢,虽然相对来说,他并不刻意在创作台突出乡土特色,但他对四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氛围的表现却也是独一无二的,如《寒夜》之于战时重庆生活的紧张和窘迫,《憩园》之于成都的懒散和颓败。当然,强调对本乡本土“特别情况”的揭露,对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这种叙述可能是既狭小又深入的。[(12)]不过,似乎还是多少失去了向着一个更超越更开阔的哲理层面挺进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四川作家“方志意识”的一点局限性。
方志意识还决定了我们的作家对地域历史与地理情况本身的浓厚兴趣,除了他们日常的搜集、研究工作外,有时还情不自禁地在小说创作中大加展示、总结自己在方志研究中的心得和成果。在这方面,李劼人是最为突出的,在他的“三部曲”创作中,曾经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考证成都及其他四川城镇的城市史、建筑史,介绍特定的地方风俗,如《死水微澜》第三部分写天回镇赶场的盛况用了3500字,第五部分写成都正月烧灯用了近2000字,介绍成都青羊宫用了2000多字;《暴风雨前》介绍成都的茶铺与茶俗用了1800字;《大波》写成都武侯祠的建筑和风俗用了2000多字,写重庆的江南馆、禹王宫用了1500字。我之所以说这代表了作家本人对地方志本身的兴趣,是因为每当这类描写出现的时候,李劼人都不惜笔墨,大加渲染,甚至暂时忘了故事的推进,把故事中人稍稍“凉”在了一边。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多半不是加深了对人物命运的体察,而是增长了知识,打开了视野,感受到的也是作者对历史、地理及民俗的浓厚兴趣。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来看,如此津津乐道于方志研究的作家实在鲜见,追查下来,大概只有北京的老舍可以与之相媲美[(13)],不过,老舍笔下的北京城地理和民俗的表现也只是作为人物活动和人物命运的背景,并没有像李劼人作品里那样获得一个较为独立的价值,正如老舍所说:“对于中古时代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它们的历史的、地方的、民俗的价值也许胜过了文艺,可是我的目的是文艺呀”[(14)]。
三
如果说,方志文化从总体上决定了现代四川文学写实取向,那么四川地区另一种文化现象却分明影响了这种写实主义文学的叙事艺术技巧,这就是龙门阵文化。
龙门阵可以说是四川地区的一种民间叙事习俗。聊天、讲故事都称为“摆龙门阵”。当代期刊《龙门阵》序言描述说:“或则车笠旧侣,或则萍水相逢,机缘偶合,有心无心,触景生情,话发天籁,于是三三两两,自然而然,聊聊天,摆摆条,进而说说笑,又进而谈谈心,不知话从何处起,也无所谓如何收场。但觉过眼烟云,一阵清风,身心劳烦顿消,带来轻松愉快。”[(15)]就是在“龙门阵”的包围中,四川作家接受了最初的叙事教育。“婴儿还在襁褓,母亲催眠便哼哼‘小宝宝’、‘萤火虫’。渐渐稍有知识,便要老祖母摆摆‘红鸡公’、‘熊家婆’。随着年龄稍长,就要听神仙、鬼怪、战斗、惊险,‘哪吒闹海’、‘嫦娥奔月’就成为好题材……”[(16)]一些四川青年在学生时代也爱泡茶馆、听龙门阵。李劼人所在的分设中学,沙汀、艾芜所在的省一师都盛行此风。许多四川作家也给外省朋友留下了好“摆龙门阵”的印象。臧克家眼中的沙汀“很健谈”[(17)],陈白尘眼里的刘盛亚“有着四川朋友的共同特性,爱摆龙门阵”[(18)]。中学时代,李劼人就以善讲故事成为同学围聚的中心,以后他的家又成了朋友聚会之所,为此刘大杰生动地描述了一番:“到劼人家喝酒,是理想的乐园:菜好酒好环境好。开始是浅斟低酌,续而是高谈狂饮,终而至于大醉。这时候,他无所不谈,无所不说,警人妙语,层出不穷,对于政府社会的腐败黑暗,攻击得痛快淋漓,在朋友中,谈锋无人比得上他。酒酣耳热时,脱光上衣,打着赤膊,手执蒲扇,雄辩滔滔,尽情的显露出那副天真浪漫的面目。”[(19)]
龙门阵的中心是故事。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方能让龙门阵摆得热热闹闹,令听者云集。于是,情节也就成了四川作家叙事结构的中心。从这里来说,不少四川作家的叙事的确一如郭沫若对李劼人的评价,是“稍嫌旧式”了些。不过,尽管如此,从龙门阵中吸取叙事营养却还是成了许多四川作家自觉的追求。在小说《梦痕》中,李劼人曾直截了当地说,这段故事是由几个朋友吃茶聊天引出来的。[(20)]周文也说他的《薛仁贵征东》中的某些细节得益于“一个朋友谈天”[(21)]时的语言方式,沙汀说他《医生》题材来自他在乡间养病时听到一个“剪金元券摊膏药”[(22)]的故事,《在其香居茶馆里》则源于他“跑警报”时与一位农艺师的闲谈。[(23)]当代四川作家马识途在他的小说《雷神传奇》里,借说书人之口对“龙门阵”的价值大加褒扬,算是道出了不少四川作家的心声:“我们中国的说书人在中国的茶馆里摆龙门阵,照规矩就是要讲究有头有尾,有条有理。不像那些新而又新的新派小说,才说到中国,忽然又说到外洋爪洼国里去了;才说盘古皇帝开天地,忽然就说到民国幺年的事了;一会天上,一会地下,把你弄得云里雾里,糊里糊涂。”
龙门阵是以故事为主,但又不仅仅只有故事,因为,它往往是一种集体参与的活动(不然又怎能称之“阵”呢!)除了有主讲人,旁边还有插话者,主讲人和插话者有对话,互相补充,或者本就是几个人在漫无边际地聊天,自由自在,谈话的主题有一定的集中性,但也有自由性、散射性。从文学叙事角度归纳,它显然是在不破坏叙述主脉的前提下,包容了若干自由穿插的叙述手段,将故事向前后左右扩展开来。在现代四川文学中,我们不时都能找到这种自由叙事的策略。
比如李劼人写天回镇赶场的盛况,百货充溢,商贩云集,来往人群熙熙攘攘,写到了生猪市场,便索性插入一大段关于川猪的知识,体型、重量、饲料,甚至猪圈的修砌方法,防病措施等等应有尽有;[(24)]写葛寰中进万县城拜访陆知县,随手将笔一拐,不紧不慢地大讲这位陆知县的戒烟史,对大补药“龟灵集”更是说得头头是道。[(25)]再如沙汀写穆家沟那个欺软怕硬的乡约丁跛公,先是饶有兴味地把镜头对准了他早已暝目的父亲,推出了一个特写。[(26)]写农会会长龚老法团的平庸和懦弱,也是远远道来,从早已倒台的陈三大王的发迹讲起,分析陈三大王上台的原因。[(27)]沙汀每讲述一个故事,都要以这个故事的人物为中心,四面伸展开去,带出一大片社会人生的景观,这正象李劼人抛开情节和人物,介绍自己的方志知识,我们却照样能够读得津津有味,而没有过分感到它的分裂。龙门阵特定的自由和散漫从另外一个意义上保证了小说的完整和统一,并且仿佛愈是这样,也才愈能烘托出巴蜀社会与巴蜀文化的生态气氛!
龙门阵式的话语明显带有说话人的声音。在一些作品里,我们不难找出这样的“声音”来。
最简明的声音是说书式的,“话说”、“且说”一类的语词得以征用。如李劼人《做人难》劈头一句“话说内热翁一梦初醒”,《续做人难》说书人直接由“内热翁”自己充任,是为“现身说法”,《大防》引言云:“我为发扬乡光起见,且谈一件故事(我应该说摆一个‘龙门阵’)”,《好人家》、《梦痕》甚至连龙门阵的场面也写了进去,作者化身为说话人,沙汀的《呼嚎》自言“老实说吧……”
面对听众说话不仅是对内容的铺叙,而且还要根据在场人的理解能力加以必要的补充、解释和分析、阐述。这种语言或者是自问自答式的,或者是包含了一定的逻辑推理关系,运用了一定的逻辑语言。李劼人《死水微澜》:“由四川省省会成都,出北门到成都府属的新都县,一般人都说有四十里,其实只有三十多里。”沙汀《龚老法团》:“单凭这一点看,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轻视他是多么不公平了。”陈翔鹤《傅校长》:“从学校到傅校长去的目的地,虽不过有一两条街左中之遥,然而傅校长仍旧着街车,这原因,说起来是在体恤私包车夫,而其实,不愿让用人们捉着自己私生活的把柄,这倒是实情。”这些语言既不是一般的描述,也不是故事中人物的心理活动,而是旁观者的介入和干预,是说话人对故事本身所进行的补充、分析、解释。有的解释还直接采用了自问自答的方式。如李劼人《死水微澜》:“无所事事,便是一天到晚在外面跑,跑些什么?自不外乎吃、喝、嫖、赌。”沙汀《三斗小麦》分析刘述之的处境:“生气吗?昨天的勇气早完蛋了!屈服吗?对于这种居心摆布势又难于忍受!”如果需要说话人分析、解释、补充的材料较多,那么,为了让在场听众清楚明白,就还得适当作点归纳整理,分别出甲乙丙丁、一二三四来。我们发现,一些现代四川作家就有点喜欢排列一二三四。李劼人《暴风雨前》分析成都茶铺的三种功用三层好处,整整1800多字,没有必要的归纳大概也是很难理顺的。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写到联保主任方治国对邢幺吵吵颇有畏惧,作者分析道:“使他发生这异状的原因是:为了种种胡涂措施,目前他正处在全镇市民的围攻当中,这是一,其次,幺吵吵的第二个儿子,因为缓役了四次,又从不出半文钱壮丁费,好多人讲闲话了;加之,新县长又宣布了要认真整顿‘役政’,于是他就赶紧上了封密告,而在三天前被兵役科捉进城了。”
对龙门阵式的说话方式的迷恋还使得一些四川作家常常沉醉,把玩着人物的语言,甚至直接用笔下人物大段大段的“独白”来交待事件,现代中国小说中,这样大规模独白是不多见的:
难说哪,爷爷!前几天秃子说他的牛不大吃草,来向我讨了些盐和生姜,给它洗了一个嘴,看看松了些,哪晓得昨天就不会嚼了。秃子到场上去赶牛太医,人还没有到,牛就困槽了。我的天!……你看它一身热得冒火,秃子在塘里打湿了几条麻布口袋给它铺在身上,一忽又热了,连换几次都是滚烫的。太医来放了两针血。血呀,就象熟登了的桑果儿,他没说会好吗或是不会好,开了一张药方就走了。张爷爷知道事情不大对,打算今天趁活的宰了,容易卖些。……爷爷你说啊,畜生病了也跟人一样,看它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两个眼睛鼓挺爆绽的死死盯住人,哪晓得人也救不了它!——罗淑《地上一角》
这段独白大概可以显示龙门阵丰富的内涵和魅力了。既有生动曲折的故事,说得绘声绘色,又有讲述人的分析和判断(在此以前爷爷不相信那牛会宰了贱卖),说得有根有据,末了,还加上一点颇有感情的议论,余味不绝!它不由得你不听,不由得你不着迷,也不由得你不附和上几句。正是龙门阵文化赋予了我们如此迷人的语言乐趣。
注释:
(1)谢扬青:《巴金同志的一封信》,《成都晚报》1985年5月23日。
(2)(9)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李劼人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1941年1月1日《抗战文艺》7卷1期。
(4)黎烈文:《关于罗淑》,《文丛》1938年6月2卷2号。
(5)(21)周文:《在摸索中得到的教训》,《周文选集》下册,四川人民出版1980年版,第416页。
(6)刘纬毅:《中国地方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8页。
(7)章学诚:《修湖北通志驳陈熷议》,转引自《中国方志学纲要》,西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8)李劼人:《自传》,《李劼人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10)陈翔鹤:《李劼人同志二三事》,《陈翔鹤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11)曼因(王余杞):《自流井·序》,成都东方书社1944年初版。
(12)沙汀表示“愿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得更深一点,更久一点,与其广阔而浮面不如狭小而深入。”(《这三年我的创作活动》)
(13)在四川作家里,大段考证历史,叙写方志的除了李劼人,大概得数自贡作家王余杞了。他的《自流井》序就是一篇关于四川尤其是自贡盐场的方志学论文。
(14)老舍:《读与写》,《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5)(16)张秀熟:《〈龙门阵〉小序》,《龙门阵》1980年1期。
(17)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作家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
(18)陈白尘:《哀盛亚》,《刘盛亚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19)刘大杰:《回忆李劼人》,转引自伍加伦、王锦厚《李劼人年谱》,《新文学史料》1983年1期。
(20)李劼人:《梦痕》,《李劼人选集》第4卷。
(22)沙汀:《谈谈人物的创造》,《西南文艺》1953年6月号。
(23)沙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收获》1979年1期。
(24)李劼人:《死水微澜》第三部《交流》。
(25)李劼人:《大波》第一部第一章。
(26)沙汀:《丁跛公》,《沙汀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9页。
(27)沙汀:《龚老法团》,《沙汀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36页。
标签:龙门阵论文; 李劼人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巴蜀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乡土论文; 死水微澜论文; 沙汀论文; 华阳国志论文; 梦痕论文; 四川成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