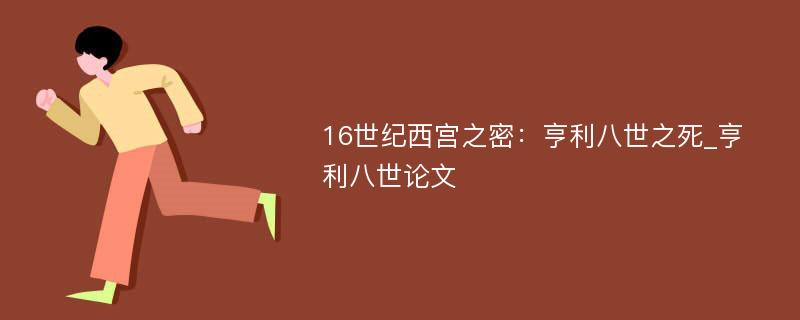
16世纪西方宫廷的“秘不发丧”——英王亨利八世之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亨利论文,不发论文,宫廷论文,之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56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1998)06—0068—71
一
近代英国的崛起始于英国宗教改革。谈到英国宗教改革,是不能不提到亨利八世的。在英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1]。 亨利八世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欧洲的专制王权统治已经普遍确立,反对罗马教廷的控制、要求民族独立的情绪日益高涨,西欧大陆的宗教改革正在蓬勃兴起。而在英国,在当时的国民生活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便是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发展,即一种英格兰人感情的发展。“要激发这种感情来抵制无论来自何处的一切外国侵略,实在是易如反掌”[2]。处于这种历史环境中的亨利八世,作为民族象征的专制君主,顺应了历史潮流,领导英国发动了一场与罗马教廷决裂的宗教改革运动,从而使英国独立于罗马教廷之外,国王成了世俗和教会的真正首领。
年轻时期的亨利八世,身体健壮,英姿飒爽。他性格坚强,处处自以为是,但也能不断地闭门思过;他虽不十分聪明但说干就干。他的好胜心使得他具有一种办好任何事情的欲望。在加强王权方面,他虽未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也几乎是独断专行了。他是新时代的新君主,又是天主教“信仰的捍卫者”,这就使得他的宗教改革只能停留在仅仅维护王权独立于教廷之外的程度而不会再前进一步。英国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在《英国社会史》中论述这一段历史时,评述说:“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是宗教改革的前奏。其基本意义在于国家政治而不在于宗教教义方面(因其核心问题为确保王位继承人)。教义上的变革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迟迟未能实现,因为那只是少数人的要求。第一项重大变革实际上是政治性的,是关于‘国家机构本身’的变革,国王在这次变革以后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脑,但这项变革只是满足于‘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干预’。教会财产也移交给了国王政府。”[3]
因此,尽管亨利八世因离婚案而与罗马教廷决裂,但他却从来不是天主教正统神学的异端,他和他的王国仅仅是教会分立者。终其一生,他都坚持着正统观点而成为迫害新教的依附者。在他看来,如果忠诚于教皇要被看作是叛国的话,那么倾向于新教的宗教改革就是异端。美国著名的神学家威利斯顿·沃尔克在分析亨利本人的宗教观点时说:“除以自己的权威取代教皇以外,全属天主教正统信仰。只有当遭受外来攻击的危险,迫使他寻求德国新教在政治上支持他时,才偏离正统信仰,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很有分寸。1535年和1536年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他派遣专员前往维滕贝格讨论教义,但没有成效。1536年亨利亲自拟定十信条,向新教作了他最大的让步。”[4]
亨利八世有关内政、外交上的一切举措,都是围绕着巩固新君主制度、维护王权的至尊地位而展开的。在他的统治集团内部,由于所持的宗教观点不同而明显地分成两派。以克伦威尔和克兰默为代表的改革派,主张人人可以阅读圣经和进一步削减教会财富与特权,并且越来越多地受路德教义的影响,设想与德国新教诸侯联盟。以诺福克和加丁诺为首的保守派,在教义和崇拜仪式方面不搞改革,只抵制外国对教会事务的管辖权。就此而言,他们的主张更接近于国王的保守的头脑。而就亨利本人而言,他既不希望路德、卡尔文的学说在英国传播,也不希望教皇、主教重新凌驾于王权之上,更不希望出现以宗教分歧为外部特征的政治分裂。因此,他不断地作出努力,力图在两派之间保持一种力量的平衡,使他们都成为忠实的亨利派,以避免自己成为任何一个派别或任何一种思想的工具。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亨利才不断地采取行动来维护这种平衡,以达到巩固自己地位的目的。1538年,查理五世和法兰西斯一世之间的战争结束,教皇要求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进攻反叛的英王。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进攻未付诸实行,但亨利还是采取了几个重大步骤以减少危险。为了向世人表明,除了否认教皇的权威外,他在其它方面还是正统的天主教徒,他在1539年6月操纵国会通过六条款法案。 法案肯定严格的实体转化说为英格兰教会信条;平信徒得救不必同领饼酒;神职人员禁止结婚;独身誓愿必须永远遵守;强制推行个人弥撒;私下忏悔得到肯定。法案无疑使倾向新教的改革派受到了打击[5]。
然而,亨利只表明自己是正统派还不够,他必须同时也向新教作出让步。于是他接纳了首席大臣克伦威尔的主张,1540年与来自新教德国的克莱维斯的安妮结婚,以讨好德国新教诸侯,使之和自己联合反对查理五世,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可见,亨利就是这样不断地通过自己的介入而使两派达成一种平衡,彼此各有消长,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可能取得至高的权力。如果把两派比作是一架天平的砝码的话,亨利无疑就是操纵天平砝码以使之保持平衡的人。当改革派变得太强大时,他就把其首领克伦威尔送上断头台;而当保守派似乎要取得支配地位时,他又把其首领诺福克送进伦敦塔监狱。结果,英国的宗教改革始终停留在与罗马教廷分立的基础上,既没有变成异端,也没有恢复到天主教会的统一上。这就是所谓的安立甘宗的中间道路。而实际上它仅仅是一种仰赖于国王权威的暂时的妥协。
30年代中期以来,亨利一直在这架自己精心设计的天平上左右不时地增减砝码,力求精确地达到一种稳定的平衡。而长久地从事这样一项损耗心力的劳作,使他逐渐变得喜怒无常和多有疑虑,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特征。从1540年7月他处死克伦威尔——他最得力、 最忠心的大臣之后,他的心态开始逐渐显示出这种猜忌狂的趋势。他的思考能力虽然并未减退,但却变得越来越烦燥、易怒和难以自控,并且经常忧郁、意气消沉、缺乏耐心。而他性格上的这种缺陷又被他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所加重。当亨利八世55岁时,他已不是一个健壮的、英俊的、以谦和的举止而博得外国大使称赞的国王了。暴饮暴食使他过早地肥胖,以至于浮肿的身材使他貌似一个宫廷的小丑,失去了当年的威仪。由于骑马而摔伤的腿上,出现了慢性溃疡,剧烈的疼痛经常使他面色苍白、说不出话。这使他的性格和脾气变得更加暴燥。
一代雄主正走向死亡。
二
1547年1月27日,亨利的最后时刻来到了。 当丹尼爵士鼓足勇气告诉他该准备后事时,亨利平静地接受了建议,回答说基督的仁慈会饶恕他的罪恶的。当丹尼问他是否想向某个谨慎的人开启他的灵魂时,他说他想先睡一会,然后再考虑这个问题。当他醒来后,派人去找克兰默。这位大教主是在午夜时分到达王宫的,他发现国王已经不能说话,几乎失去了知觉。但是当克兰默要求亨利给他某个信仰基督的表示时,亨利用尽最后一丝力量紧紧地握住了大主教的手。1月28日清晨两点, 历经惊涛骇浪的亨利八世也未能战胜死神,终于离开了人间,终年56岁。
亨利王进天国?亨利王下地狱?还是棲身炼狱?上帝自有安排。
诚然,亨利八世作为一个真正的专制君主的最好体现,就是给了他的臣民所想要的东西,即享有完全主权的近代民族国家。这是英吉利民族称雄于近代世界的起点。这是亨利的不朽功勋。还应该提到,他留给他的国家一个有效率可操作的政府,一支有战斗力的海军。他发动具有英国特色的宗教改革无意于为了资产者的利益而建立一个“廉价教会”,但他的宗教改革却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遗憾的是,这位新君主仍未摆脱勇武好斗的中古遗风,垂老之年还渡海“亲征”法国,无功而回。他身后的英国并非繁荣富强,安定团结。
尽管如此,他还是力图给他的继承者勾划出了一幅沿他的所谓中间路线继续走下去的未来英王国的蓝图,这就是他的遗嘱。为继续保持他生前的那种平衡局面,防止他的继承者背离既定国策,在关系民族命运的信仰取向上走极端,他在遗嘱中预设的摄政会议不设主席职位,重大事情由遗嘱执行人平等地投票决定。他所指定的遗嘱执行人自然包括相互冲突的两派人物,他们势力相当、彼此平等,谁也不能控制其他人,搞独断专行。改革派方面的人物有克兰默( Cranmer )、 赫特福德(Hertford)等;保守派方面则有大法官瑞奥塞斯莱(Wriothesley )、布诺尼(Browne)等。亨利谨慎地把那些他认为支配欲过强或观点过激进以至于有可能破坏平衡的人物排除在外,例如保守派的加丁诺和改革派的帕尔等。按照这样的遗嘱建立起来的政府,由于两派势力相当而互相抵消,就可形成一个稳定的力量,平衡的局面。保守派能够抑制改革派的“激进”,而改革派则能防止保守派的“反动”。这样,他的国家就可不被触动地“长治久安”。
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亨利的愿望发展下去。亨利的继承者爱德华六世,登位时只有九岁,但这位幼君早熟,是一位固执的新教徒。摄政大臣中唯一与他具有血缘关系的他的舅舅赫特福德也是一位新教徒。这就意味着爱德华六世在未来的国家事务中只可能受到新教政治家们的控制,从而才使赫特福德能够顺利地演出了西方罕见的“秘不发丧”的历史剧。
当然,赫特福德的“秘不发丧”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与他相抗衡。在亨利指定的保守派的遗嘱执行人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未被包括进去。诺福克公爵本来是改革派最危险的敌人,但由于他的儿子作事不谨慎,在他自己的盾牌上把皇家的标志和他自己家族的标志刻在一起,并抱有其父该作护国主的想法而激起亨利的嫉恨,结果父子俩双双被送进伦敦塔,儿子在享利临终前被处死。加丁诺则因为被亨利八世认为是一个除了国王本人其他任何人都驾驭不了的人物而被排除在摄政会议之外。这样在赫特福德面前就没有一个够格的对手能挫败他的计谋。而且更为有利的是,身居枢密院文书(clerk)要职的帕吉特(Paget,由他掌管、宣布国王遗嘱),是一位“柳树式”的人物。此人没有明确的宗教观点,忠于国君而派别色彩不明,处事圆滑,不讲操守,正是赫特福德实现计谋所需的关键人物。于是,在享利八世死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在威斯敏斯特宫国王住屋外的长廊上,赫特福德就通过向这位帕吉特许诺给他好处而取得了他对计谋的支持。两人决定保守几天国王已死的秘密,只公布遗嘱中有利于计谋的部分。因此,直到1547年2月3日大法官瑞奥塞斯莱才在议会中宣布国王驾崩的消息。同时,赫特福德牢牢地控制住了小国王,带着他一同返回伦敦。在返途中,他宣布自己为护国主。此时,保守派中有两位不在国内,布诺尼则在与赫特福德一同去接小国王的途中,被赫特福德说服支持计谋。另一个保守派成员堂斯陶尔(Tunstall)是赫特福德的私人朋友。因此,当1月31日下午,遗嘱执行者们在伦敦会晤时, 他们所要做的并不是决定什么事情,而是承认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两天后,他们默认了由赫特福德充当护国主的要求。而唯一的反对力量来自大法官瑞奥塞斯莱,但几天后由于他在一次执行公务中的“违法行为”而被剥夺了职权。这样,赫特福德——索默塞特公爵在其推进英国宗教改革的事业中所不得不面对的最危险的对手也从他的道路上被清除出去了。
历史似乎有意作了这样的安排,使赫特福德这位“国舅爷”违背亨利的遗旨安然登上了护国主的宝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这段历史的话,不难发现,正是亨利八世天平的砝码稍稍偏向于改革派,才造成这种改革派处于优势的局面。克伦威尔死后,保守派曾经几次想除掉克兰默,但都由于亨利的出面保护而挽救了这位大主教的性命。在为他的继承者拟定摄政会议的成员名单时,没有加丁诺的名字。当布诺尼提醒亨利是否忘了这个人时,亨利回答说:“我记得他很清楚,只是出于一种善意才略去了他——我自己可以按照我认为好的各种意图去支配他,你们却不能。”[6] 西方权术大师亨利八世这样做自有其“保全身后”的意图。但事实上确实造成了有利于改革派的局面,从而使赫特福德就任护国主的目的得以顺利实现。
可见在亨利八世天平的背后,是两派你死我活、争权夺利且事关国运的尖锐斗争。只是由于亨利从中进行“公平”的操纵,才使得两边暂时保持平衡的局势。一旦操纵天平的人被抱有派别成见的人取代,天平就会失衡。爱德华六世是新教徒,所以在他统治期间,改革派占上风,使英国的宗教改革得以进入新阶段;玛丽女王则是正统的天主教徒,她在位期间,天主教复辟、新教徒遭到迫害。“如果说经济上的变革有可能引起社会上的不满情绪,那么宗教信条的变化则可以造成社会的分裂。宗教改革造就了天主教与新教双方的殉道者,其中一方是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被处死的托马斯·莫尔爵士和枢机主教费希尔,另一方是约翰·福克斯的《英烈传》中所祭奠的、在玛丽统治时期被烧死在火刑场上的拉蒂默、里德利和克兰默”[7]。
历史的公正在于它的发展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说索默塞特的“秘不发丧”是违背了亨利的遗愿的话,那也是时势使然。因为新教的成长确实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了英国的宗教改革更向前迈进一步,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不出现索默塞特和他主谋的“秘不发丧”,也必定会出现另一个人以另一种行动承担起历史赋予的打破旧规、推动历史前进的重任。同时,这一短暂的历史插曲也表明:“秘不发丧”这一类宫廷事变并非仅见于中国史书。这是值得深入考究的问题,本文的主旨在此。
收稿日期:1997—0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