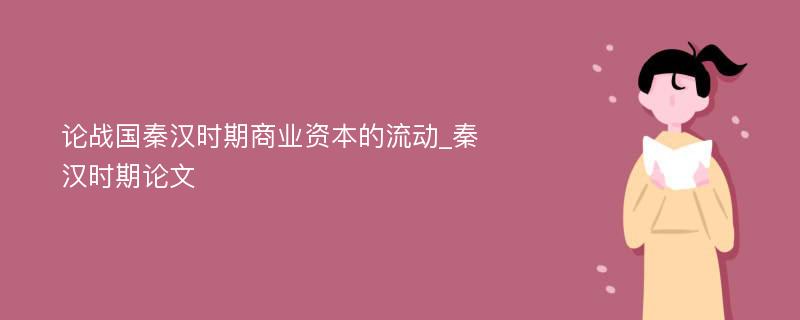
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流向论文,战国论文,时期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业是比较发达的,在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堪称一个黄金阶段。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商业经营的主体——商人的人数不断增加,并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积聚了大量的商业资本。这些巨额财富的流向,除了对当时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以外,还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个问题,略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经营商业
经营商业是商业资本流向的一个主要渠道。为使商业经营活动能周而复始地进行,不断扩大其经营的规模与范围,商人就须把在商业经营过程中获取的商业资本,重新投入到商业经营的活动中。战国秦汉时期,中小商人构成了商人的主体。他们除了一小部分是在春秋中后期“工商食官”解体后由普通的商业劳动者转化而来以外,大部分则是已经破产或行将破产的个体农民,在商业经营活动较高利润率的驱使下,以经营“末业”作为“贫者之资”。(《史记·货殖列传》)因此,他们多缺少商业经营活动所需的资金,只能从事一些“贩夫贩妇”的小本生意。多是采用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来进行商品生产和销售,不可能普遍地提高社会商品生产的整体技术水平,更不能把这种家庭化的简单再生产转化为扩大化的社会再生产。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在商业经营上,理应以扩大再生产为主。但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却时常使他们举步维艰,仍多重复着简单再生产。从经营规模上看,大商人所经营的工商型“企业”,一般是比较大的。以铁石鼓铸为例,“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由于这些“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的雇佣人员,大抵尽是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如此弃农经商就可能“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以上引文均见《盐铁论·复古》)威胁到封建国家的统治。因此,封建国家对此类“企业”多是采取抑制的政策,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盐铁国营就是明证。另外,战国秦汉时期,商业经营活动需“各任其能,竭其力”,(《史记·货殖列传》)风险较大,往往有破产之虞。经营的规模越大,承担的风险也就随之增加。因此,大商人在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时,常以维持经营现状为上策。从商品经营的种类上看,有些商品受其特性的制约,经营的规模不宜过大,如酿酒销售的收益是颇丰的,但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酤一岁”也仅有“千酿”而已。这主要就是受当时生产技术所限,酿出的酒的度数不高,容易腐败变质所致。所以,此类商品的生产、销售的经营规模只能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追利逐富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进行简单再生产,对于商人来说,虽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的求富途径,但在“求富无涯”等观念的影响下,从主观愿望上讲,他们仍多希望能进行扩大再生产,来更快、更多地赚取高额商业利润。如战国时期的猗顿,原是“鲁之穷士”,“耕则常饥,桑则常寒”。(《史记·货殖列传》注)后经陶朱公指点迷津,来到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数,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后把资本投入到盐业的生产和销售上,并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成为“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韩非子·解老》)的大商人。又如在西汉前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比较繁荣,“汉兴七十余年之问,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同时在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指导下,商业管理政策也比较宽松,这就为商人进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外部环境。如蜀卓氏、程郑、宛孔氏、鲁曹邴氏等,都是在此期间扩大冶铁生产,成为可比“素封”之家的富商大贾。
二、经营土地与高利贷
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另外,影响商业经营的其它因素尚有很多。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便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经营稳定、风险小、获利多的购买、经营土地和从事高利贷活动等其它行业。
战国秦汉时期,商人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土地,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土地的自然属性、人们对财富的观念,及政府对商业的管理政策等因素,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和生活资料,而且还是一种能生息的资本。商人购买大量的土地,是想通过土地的租佃关系,来获得“见税什五”的地租。这种“田农”式的经营方式,虽是“掘业”,赢利不多,但却具有“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的较为稳定的收入。如果能经营一些如“千树枣”、“千树橘”、“千树萩”、“千亩漆”、“千亩桑麻”、“千亩竹”之类的经济作物,则会有更大的收益,其富“皆与千户侯等”。另外,与商业资本不同,土地是一种不动产,它不忧水火,不怕盗贼,在战乱四起之时,不象商业资本那样,随时有丧失的危险。因此,更促使“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土地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一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人们逐渐形成了“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用”的财富观念。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虽使人们的财富观念有所扩大,不再仅仅局限于土地,但大多数人对财富的基本观念,仍离不开土地。即使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的司马迁,也持有“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史记·货殖列传》)的观念。因此,大多数商人以获取大量的土地为最终目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战国秦汉时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多实行“重农抑末”的商业管理政策,鼓励民众向土地投资。一些地方官吏,如“循吏”,对此也多能认真地加以贯彻执行。《汉书·地理志》载:“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从商贾到农桑,从末到本,无疑就是把商业资本投向土地。《汉书》中所称的其他循吏,如龚遂等,几乎都是以劝农弃商为务,如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商业资本流向土地。
自春秋以来,“田里不鬻”的陈规就已被打破,进入战国秦汉,土地便可自由买卖了。封建政府虽然有时颁布一些限止商人占田的诏令,但那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无法阻止商人在上述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土地的狂潮。汉武帝时期,通过告缗,没收商人的土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汉书·食货志》)现据此粗算其在全国耕地中所占有的份额如下:《汉书·地理志》载,平帝时,全国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耕田八百二十七万余顷。武帝时期属西汉盛世,全国邑县、耕地当与之相差不大。取其整数,县以千三百计,每县以没收田二百顷计,则共没收土地为二十六万顷,约占全国耕地的3.14%。若加上其他未犯法,没被没收的商贾的土地,则数量更多。而在西汉末年、东汉末年,商贾兼并土地比汉武帝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知,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投向土地为其一个极为重要的流向。
经营高利贷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借、贷双方。战国秦汉时期,这一条件已完全具备。先看货方,当时商人首先在流通领域,活跃起来,于是各地出现了“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苏秦列传》)的专门商人。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关中、三河、巴蜀、齐鲁、燕赵、楚越之间,随处都可以看到商人的足迹。其中,“宛、周、齐、鲁,商遍天下。”(《盐铁论·力耕》)最为著名。他们或行贾郡国,或以冶铁起家,皆累积有巨额的商业资本。这些商业资本除供他们经营商业和购买土地外,放高利贷便成为一个较主要的出路。如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贳贷行贾遍郡国。”(《史记·货殖列传》)经营高利贷获利多,这便刺激了一些大地主和不法官吏的贪欲,他们也纷纷加入到经营高利贷的行列。再看借方,战国秦汉时期,自耕小农构成了社会人口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他们虽以自然经济为主,但同市场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丰穰之时,粮食多了,需要卖出;饥馑之际,青黄不接,又需买入。由于小农对外来破坏因素的承受能力较小,在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或因官府严酷的剥削,加以婚丧嫁娶的花费等,往往要向贷家举借。另外,小工商业者因缺乏资金,周转困难;官府在财政紧张时,也都要向高利贷者借债。由此就促使高利贷活动十分活跃。
战国秦汉时期的高利贷的利率是比较高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贷金钱千贯”,可比“千乘之家”。《汉书·武帝纪》元狩四年李斐注:“一贯千钱”,千贯为一百万。结合上文,“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可知高利贷的利率为20%。但这只是通常情况下的利率。遇有水旱之灾,急征暴敛之时,高利贷经营者往往会提高利率,贫民只得“取倍称之息”,(《汉书·食货志》)即以一偿二,利率为100%。如果贷款的风险较大,利率就会更高。 商人正是由于经营高利贷活动利润多,获利快,才把大量的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从事高利贷经营活动。
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人一般以经营民贷民、民贷官两种形式的高利贷为主。民贷民是民放民债,为高利贷活动最基本的一种形式。民贷官是民放官债。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多半发生在战争爆发,国家财政困难之时。
三、窖藏与浪费
以上所述的产业确为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业资本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投资市场。但对手中握有大量钱物的商人来说,毕竟还是狭小的。加之汉武帝以后,封建国家实行盐铁国营、榷酤制度,把封建社会里最能吸纳商业资本的行业,统统收归到政府手中,来巩固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这就使本已存在的商业资本与市场容量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这时,商人除了积极地为他们的商业资本寻找新的市场,如域外市场以外,则只得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其它方面,如窖藏、奢侈浪费等。窖藏主要是指商人把最能体现商业资本价值、单位价值较高的金属货币等,从生产、流通领域中抽取并封存起来。战国秦汉时期,被商人窖藏起来的商业资本是比较多的。《汉书·食货志》所载的“富人藏钱满室,犹无厌足”,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情况。此种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与人们的习俗、社会经济的动荡及时局的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的。在农业经济为支柱产业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除了努力扩大耕种面积、改良作物品种、改进耕种技术等,来增加粮食产量以外,还因自然灾害的频仍,十分注重对粮食的贮存。以致有了“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国非国也。”(《礼记·王制》)之说。以汉代为例,灾荒频率的合理比例应该是180—225/426,即一半年份有灾(参见马大英《汉代财政史》第28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由此,人们便形成了积贮钱粮的习俗。当时上至封建国家、诸侯王,下至平民百姓,莫不如此。如西汉盛时,国家多蓄钱财、粮食。“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又如梁孝王喜贮财物,“及死,臧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史记·梁孝王世家》)而王莽在位时,多储藏黄金,“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汉书·王莽传》)《史记·货殖列传》中,则记有梁、宋之地有“能恶衣食,致其蓄藏”的风俗。一些政论家,如贾谊的论积贮的言论及晁错的贵粟疏,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态。
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和时局的动荡不安是促使商人进行窖藏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每当此时,商人为不使商业资本丧失,就把最为人们所看重,对社会动荡反应敏感的金银财宝,严密地窖藏起来。另外,通常由此而引发并加剧的商业市场的畸形发展,有时就会使盗铸盛行,出现劣钱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如西汉前期和东汉末年都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时,商人为了保护既得的商业资本,便不肯拿出金银财宝,来作为日常交易或支付价值的手段,更不会用此同低劣的铜钱甚至布帛谷粟之类的实物货币相兑换。结果,大量的商业资本便被窖藏起来。此外,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某些商业政策,也会促使商人把大量的商业资本窖藏起来。如汉武帝实行算缗告缗,富商大贾为了瞒产漏税,“富豪皆争匿财。”(《史记·平准书》)
商人的奢侈浪费,也构成了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一大流向。商人生活的消费水平是与社会经济水平、社会风俗等因素紧密相联的。到西汉武帝时期,经济条件好转,社会风气开始由俭变奢。“当此之时,……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史记·平准书》)上层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更助长了社会上的奢靡之风。在此期间,武帝又大力强制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国营、迁徙富豪等剥夺商人财产的政策,使商人对商业资本深有一种危机感,与其投入再生产或另寻出路,还不如尽情挥霍浪费掉经济实惠。这便形成了“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同上)的社会风气。到盐铁会议召开之际,弥漫于整个社会上的奢靡之风已成狂澜既倒之势。贤良文学在《盐铁论·散不足》篇中,从“宫室舆马,衣服器械,丧服食饮,声色玩好”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番“古今”对比,来反复说明此种变化。而商人的生活,自此以后,更是挥霍无度。到东汉末年,富商大贾的奢侈浪费已达到十分惊人的程度。正如仲长统所描述的那样:“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琦珞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伛伎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后汉书·仲长统传》)
四、流入国库与中饱私囊
商业资本流向国库,为战国秦汉时期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补充形式。如通过鬻爵卖官、赎罪等形式,诱使商人把商业资本输入国库;或干脆以加重赋税的算缗告缗、迁徒豪富等形式,强行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收归国有。
鬻爵卖官主要是指封建国家用官爵为诱饵,使商人主动地把其商业资本输入国库。由《管子·八观》的“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韩非子·亡征》的“爵禄可以货得”,及秦王政四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可知战国时商人已可以买爵。两汉时期,鬻爵时断时续,如西汉文帝、武帝、成帝及东汉时帝时,都曾实行过这种制度。晁错对“入粟拜爵”的作用概括为:“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汉书·食货志》)其实,充实国库才是鬻爵最主要的目的。封建国家用此种方法,从商人那里获取了大量的粟和钱。如汉武帝时期,仅出卖武功爵,就获得“三十余万金。”(《史记·平准书》)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其“外事四夷”、“内兴功利”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尽管早在《韩非子·五蠹》篇中已有“官爵可买”的记载,但由于卖官这种使商人出钱参政的赤裸裸的“钱权”交易,比鬻爵更易招致众人的反对,且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也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所以,国家大规模地向商人开放政权的卖官比鬻爵较晚。直至汉武帝时,为解决财政困难,方把官职向商人开放,即所谓“入羊为郎”、“入谷补官”。以致“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汉书·食货志》)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更迭执政,社会政治黑暗,卖官所得便不再输入国库,而直接充盈了皇帝的私囊。如昏庸的灵帝在西园公开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后汉书·灵帝纪》及注)由此就使吏治空前败坏,政治更加黑暗,加速了社会各种矛盾的总爆发。
赎罪是指商人以商业资本为代价,来换取免受刑罚的权利。战国以前,商人拥有的资本有限,社会地位不高,即便能以钱、财、物赎罪,范围也不会太广。进入战国,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造就了大批的富商大贾,且其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便为赎罪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范蠡的中子杀人后,范蠡“乃装黄金千溢,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欲遣其少子去营救。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记有“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谚语。西汉以后,本是赋予贵族赎罪的特权,早已分润给了富商大贾,其范围也更趋扩大。《汉书》惠帝纪、武帝纪及《后汉书》明帝纪、章帝纪中都载有赎罪的诏令。如《汉书·武帝纪》载,天汉四年“秋九月,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五十万的赎罪钱,对汉代“百金(百万)中民十家之产”(《史记·文帝本纪》)的平民百姓来说,无疑是很高的,也只有象富商大贾之类的少数人才能支付得起。
算缗告缗是汉武帝时期,国家以法律的手段,为主要剥夺没收商人的商业资本所采取的一种竭泽而渔的工商管理政策。早在元光六年,就已开始征收商贾的车税,即“初算商车。”(《汉书·武帝纪》)后因国家用度日益困难,遂于元狩四年,颁布算缗令,加重对商贾财产税的征收。《史记·平准书》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述:“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另外还规定凡“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算缗令既下,工商业者纷纷逃税漏税,“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政府又重申告缗令,任用杨可主持告缗,使酷吏“杜周治之”。这样,“狱少反者”。结果“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致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而封建国家却因此“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并获得了大量的田宅,充实了国家的财力与人力,缓解了财政危机。
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也往往流入各级官吏的私囊。吏治较为清明时,流入的数量较少;吏治腐败时,流入的数量较多。商人的主动“奉送”和官吏的强行索取为其两种主要形式。商人把商业资本主动“奉送”给各级官吏,其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是为了寻找靠山,西汉罗裒为经营高利贷,“赂遗曲阳、定陵侯”,(《汉书·货殖传》)便是显例。其二是以此来牟取厚利。在西汉末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出现了一种“障余人卖买,而自取其利。”(《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四年注)叫“辜榷”的卖买独占的行为。如灵帝时,“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后汉书·灵帝纪》)此类“豪右”应是与豪门贵戚、高级官吏有关的富商大贾。他们用大量的商业资本贿赂官吏,为的就是从官府那里取得包揽某种商品经营的特权,获得垄断性高额利润。战国秦汉时期,商人主要在集市上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这就为主管集市的各级官吏强行索要财物大开了方便之门。其他官吏也有向商人勒索的,如董贤家有宾婚,使人“发取市物”,以至引起“百贾震动。”(《汉书·王嘉传》)
五、与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贸易
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贸易,也是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一大流向。秦汉以来国家的统一、贯通全国水陆交通网的初步形成、国内商业活动的繁荣等,都促进了与周边地区贸易的发展,为商业资本的输出开辟了一条通路。
两汉时期,中原地区与北方、南方边地的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活动,构成了与周边地区贸易的主体。在北部边境,汉朝与匈奴、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建立了贸易关系。西汉初期,迫于匈奴强大的势力,汉朝采取了“和亲”的策略,并开放“关市”,允许两族人民进行贸易。其后,两族之间虽时有战争,但在和平时期,仍能进行一些贸易活动。东汉时期,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西迁,汉朝又同乌桓、鲜卑等采用“互市”形式进行贸易活动。少数民族以马、牛、羊、骆驼、兽皮和本族工艺品等,换取中原地区的食盐、粮食、丝帛等日用品。在南部边境,西汉同南越互设“关市”。汉人把铁制农具、耕畜等卖给以农业为主的南越人。另外,“西南夷”在西汉时也与汉族人民有着较频繁的经济往来。巴蜀商人将蜀布、枸酱、邛竹杖运销西南夷,再由此分别运往南越和印度。
西域也是商业资本输出的一个地区。建元三年(前138年), 张骞应募出使西域,欲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此次出使,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却了解到西域的许多情况,大大开阔了汉人的眼界。自“张骞凿空”之后,东西之间交通频繁。汉派往西域的使者以及打着汉使旗号的商人相望于道,络绎不断,“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史记·大宛列传》)中国的丝织品沿此东西商道大宗运往西方,因有“丝绸之路”之称。公元1世纪,东汉明帝派班超出使西域, 通五十余国。他的掾属甘英曾“穷临西海而还。”商业资本已随汉人的足迹远达地中海东岸。
我国较早便开始了海上交通,经战国至秦又有较大的发展。两汉时期,我国主要通过北、南两条海上交通线开展对外贸易。北线主要的贸易对象是高句丽、三韩(马韩、辰韩、并韩)及倭奴国(日本)。此线路途虽近,但贸易的数量有限。真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是经由南线完成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合浦郡的合浦县和徐闻县是海上对外贸易的港口,由此出发,经今马来西亚半岛及缅甸,辗转可达印度半岛的东海岸。其所经的地区和国家,“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汉朝的使者和商人把我国大量的丝和丝织品运到这些地区和国家,以购买明珠等奇石异物。因此,此条海路亦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
通过以上对商业资本各种流向的论述,可以归纳以下几点:
(一)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受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及投资行业有限等因素的制约,市场范围比较狭小。这个时期,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相当迅速的。至西汉已形成了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山东、江南四大经济区。每一经济区又可划分为若干个小的经济区,如山西经济区就包括了关中、巴蜀、西北边区三个经济区。但由于各个经济区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差异较大,四大经济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概而言之,半农半牧的龙门碣石以北经济区及尚未开发、“火耕水耨”的江南经济区的经济比较落后。除了依托于几个商业都会如番禺等,从事一些地区间贩运商业经营活动以外,商品经济是不发达的。因此,流向这两大经济区的商业资本的数量很少。处于黄河流域、疆域辽阔、经济发达的山东经济区及山西经济区是商业资本流向的主要场所。特别是关中经济区,因其南控巴蜀,西北控陇右戎翟,地理位置优越,又为秦、西汉两代国都的所在地,财力集中,人口稠密,更为商业资本流向的理想区域。故有“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之说。直至东汉,江南经济区虽逐渐得到开发,但并没能改变经济区的这种大的格局,大量的商业资本依然在黄河流域内流转,惟中心都会,由长安移至洛阳而已。如前所述,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国内可供商业资本投资的行业本就不多,在封建国家实行盐铁国营、榷酤制度等之后,就更减少了吸纳商业资本的行业。另外,战国秦汉时期,自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统治地位。农民受其自然经济的限制,除盐、铁等不能自产的生活必需品以外,他们同市场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加之又受到各种繁重的剥削,就更减少了他们对商品的购买力。而且东汉基本自给自足庄园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自然经济的比重,减少了社会对商品的需求量。这样,大量的商业资本就被集中在狭小的经济区内,只能在较少的行业中流转,而且社会对商品的整体购买力又不高,由此就造成了局部商业资本的相对过剩和社会上商业资本的绝对过剩。
(二)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对边境和域外流向,受贸易的对象、环境及科技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数量是十分有限的。这个时期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一般是比较落后的。他们几乎没有农业生产,更谈不上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南边的西南夷、南越等,虽有农业生产,但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落后状态,其“不待贾而足”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其商业基本上是落后的。而与中国进行海外贸易的日本、朝鲜半岛上的诸国,其情况也大率如此。这些无疑都会极大地限制双方贸易的规模,减少了商业资本输出的数量。另外,商业资本的输出还与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等因素紧密相联。如两汉时期,沿途“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县度之阨”(《汉书·西域传》)的恶劣自然条件,就大大增加了商业资本经由西域输出的难度。因此,输出的商业资本数量不仅有限,而且所输出的商品只能是一些单位价值极高的、如丝绸之类的物品。而政治环境的好坏则直接关系到贸易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如经由西域输出的商业资本,由于政治的因素,就往往受到匈奴及西域诸国的遮截。又如中原政权与匈奴关系紧张时,双方的“关市”贸易根本无法进行。即便在较为和平时期能进行贸易活动,汉朝出于对国家利益与安全的考虑,对贸易的物品也多有限制。为防止匈奴从汉朝购得铜铁用于制造兵器,汉朝是禁止铜铁进入“关市”交易的。在同南越进行“关市”贸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史记·南越列传》)为此还引起了南越与汉朝的战争。此外,商业资本的输出还要受到当时科技水平的制约。如海外贸易就受造船技术及船海知识的影响,一般商人多视航海为畏途,这就限制了商业资本海外输出的数量。
(三)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流向,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均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就商业资本的国内流向来看,其经营的商品“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记·货殖列传》)在满足社会各阶层多种需求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西汉前期,任民冶铸,铁器的商品生产和销售有了很大发展,所谓“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盐铁论·禁耕》)铁制农具较普遍地采用,满足了农民的需求,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西汉前期商业的繁荣,则促进了纺织业、漆器制造业、盐铁业、铸币业等手工业的长足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使战国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上。这样,在经济效益规律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农业生产就越具有为交换而生产的倾向,农产品作为商品进入了流通过程;而且,商业经营活动较好的经济效益,也促使农业劳动人口向工商业人口的转化。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使了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侵蚀和瓦解。
但是,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流向,受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和外部其它因素的制约,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作用。商业资本的国内流向构成了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的主体。当时,商业资本首先在流通领域内产生并发展起来。本来这些商业资本可以转化为产业资本,用于煮盐、冶铁等大型的“工业”型企业的生产,从而对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能有所裨益。但种种因素,却使之仅在流通领域内流转,或投向土地,或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或窖藏起来,或挥霍浪费,或被封建国家及贪官污吏所剥夺侵吞。加上严苛的商业管理政策、国内频繁的自然灾害,及秦末、西汉末、东汉末三次社会经济的巨大波动等,就更加阻碍了商业资本和生产的联系。现代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战国秦汉时期所萌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即因此而不幸夭折。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商业资本的国内流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不仅限于战国秦汉,而是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直至明清,由于商业资本有种种其它的流向,而很少与工业生产企业发生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另外,由于商人把大量的商业资本投向了土地,使“关中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汉书·陈汤传》)的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地发生,而大量的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更加速了小农的破产。破产后的小农,“或耕豪民之田”,成为佃农,忍受着“见税什五”的残酷剥削;或因地狭人众等原因,甚至连土地也租佃不到,只得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或在“卖田宅、鬻子孙,以尝债”之后,对生活彻底绝望,于是“亡逃山林,转为盗贼”,(以上引文见《汉书·食货志》)成为以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群众基础。这些都对社会政治的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此外,由商人的奢侈浪费所助长的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不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且由此也引起并加剧了政治腐败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如商业资本流向各级官吏的私囊,就对吏治腐败的产生、发展并走向极端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输出,其直接目的是以国内多余的商品及黄金、铜币等去换购域外的奇珍异宝,来满足注重使用价值的消费需要,并不是为了增殖货币,即在多卖少买中来牟取黄金和其它铸币的进口。而且为了怀柔远人,增加货物的进口,政府多采取高进低出,厚往薄来的贸易政策,鼓励少数民族或域外商人和中国内地商人从事域外贸易的积极性。这样,战国秦汉时期的对外贸易实质上是一种蚀本生意,贸易的入超,黄金的大量外流,最终使“府库之藏流于外国。”(《盐铁论·地广》)东汉时期黄金的大量减少,以致在流通领域内失去了昔日充当主要支付手段的货币职能,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商品经济的衰落与实物货币的复起等,都与当时商业资本流向的特点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标签:秦汉时期论文; 汉朝论文; 战国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商业论文; 货殖列传论文; 史记论文; 汉书论文; 西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