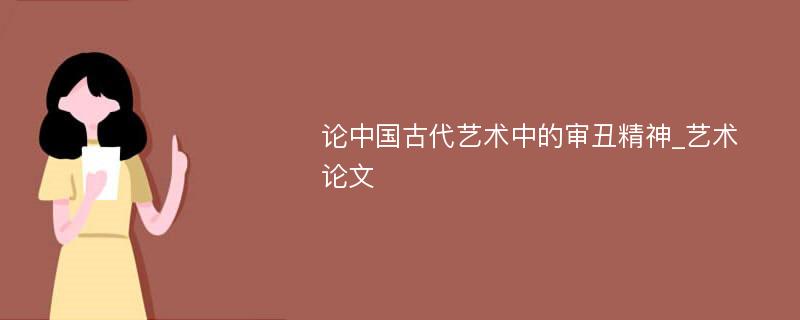
论中国古代艺术的审丑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精神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1)03-009-013
中国古代并无类似于古希腊“不得表现丑”的法律规定。从先秦的诸子经典,到各类文化典籍,从各种生活器皿,到书画诗歌等艺术形式,大都能够直面丑,进而能够审丑,美丑互化。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总结出来的“中国古代艺术的审丑精神”。
一、释“丑”与“审丑”
这里所说的“丑”有着独特的文化意义。《庄子·外篇》中有《骈拇》,其开篇曰:“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是故骈于足者,连无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树无用之指也……。”两个手指连在一起无法分开,即所谓“骈拇”,或者在两个指间多长出了一个小指头,即所谓“枝指”。庄子认为这两种状况系“无用之肉”和“无用之指”,因而是非正常的“附赘县疣”。此之谓“丑”的本义。“骈拇”或“枝指”之形,也就是不正常、畸形、丑陋、令人羞恶等义(从客观上讲为“畸形”;从他人的角度看为“丑陋”;而从自己的心理上讲为“羞恶”)。“丑”字本义、初文,应该就是丑恶、羞恶之义。但秦汉以来,“丑”字是以“醜”的意义来呈现的,《说文解字》曰:“醜,可恶也,从鬼,酉声。鬼,阴气贼害,故从么。”鬼表征人的生命之归宿;它又被赋予形体后具有了某种生命本质,但这种本质是令人生厌、生畏的,所以丑。“醜”省为“丑”,不是汉字繁体的简化,而是向其初文的回归。[1]
羞恶之心首先对自身,是对自身条件丑陋的排斥甚至否定。丑还有恶之义,《礼记内则》所制写的“七出”即七条休弃妻子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这既是伦理的恶,也是美学的丑。陆游与唐婉的《钗头凤》充分体现了这种“东风恶,欢情薄”和“世情薄,人情恶”的恶之丑。
而审丑是指个体对作为否定性的丑的判断、品评、鉴别、批判、宽容和改造等各种能力的总和。换言之,审丑是把握客观对象的丑的否定性本质及其形态在社会历史中的演变和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艺术中的审丑是非和谐、丑的客体对象在艺术主体(包括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方面引起的否定性情感和否定性价值判断的转移或升华。
二、中国古代审丑的思想来源
以此来看中国古代艺术的审丑精神,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艺术中的丑不单是一个形式问题、审美问题,而是与伦理或道德紧密联系的。中国的伦理学或道德论最早是从易经中生发出来的。《易经》阴阳八卦,美丑因素相生相克;白与黑,光明与黑暗,相辅相成。如《易经》“观”卦象辞说:“窥观女贞,亦可丑也”,指女子偷偷窥视自己的意中人,是可羞的事;再如“大过”卦象辞说:“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指“夫壮而妻老”的婚配阴阳失位,违背社会伦理规范和道德习俗的行为,就是丑的(反之,亦然)。这里所谓的丑就是“德行之丑”,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恶,是依据道德评判进行的美丑评价。这是中国先秦以来传统美丑观念的一种主要评判方式。《易经·乾卦第一》:“上九,亢龙有悔。”事物发展的亢奋、极致也就是衰落的开始。认识到过犹不及,采取中庸之道,不但是儒家的人生态度和生存策略,而且也是包括道家在内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要义或精髓所在。或者说,这种与道德紧密联系的朴素辩证法乃是李泽厚所说的儒道互补的产物。当然首先是道家思想,后世形成的禅宗更加强化了这种与儒家互补的情势。
道家,是兼容美丑的。这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文化和艺术对丑的宽容态度。老子认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盅,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老子采用一种正言若反的修辞论,坚持一种知白守黑的人生观,强调一种物极必反的辩证法。这一“早熟”的思想和方法深刻地渗入了中国文化及艺术精神之中。庄子就专门对此进行了解析。《德充符》篇描写了许多形体残缺而容丑陋的人,被砍断了足的王骀,具有淡漠生死、超绝尘寰的精神之美,连孔子都要拜他为师。申徒嘉亦断足之人,也是德性高尚的人。还有叔山无趾、恶人哀骀它、无唇者和瘿者等畸形者。但庄子认为他们具有内在的德行之美因而能够“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丧我而心美”。“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庄子·知北游》)到了西汉刘安撰《淮南子》论美丑,进一步发挥了美丑的辩证法:“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求丑则不得丑,求不丑则有丑矣。不求美又不求丑,则无美无丑矣,是谓玄同。”(《说山训》)及至魏晋那个中国人和文学都开始自觉的精神自由时期,嵇康论音乐之美与不美乃自然之谐调,非关乎思想情感:“夫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喜与不喜,人情之变,统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无豫于内,待物而成耳。”(《声无哀乐论》)东晋葛洪认为,“得精神于陋形之里。贵珠出乎贱蚌,美玉出乎丑璞。”(《抱朴子》)北齐刘昼论“物有美恶,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恶不终弃”(《刘子》)。到了明清,文人们的认识更加充满诡异的辩证色彩,如明庄昶借评张弼草书提出:“好到极处,俗到极处。”清刘熙载则认为:“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好到极处。”(《艺概·书概》)这都是对道家美学思想的继承。
儒家论丑,也吸取了易经中的辩证法思维方式,取中和或中庸之道。如孔子论美色之过犹不及。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者。”(《阳货》)孔子其意在取道中庸,有较强的道德评判标准。孟子论丑人可洁善而祀上帝:“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孟子·离娄下》)荀子辩证论美丑:“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荀子·修身》)从美丑辩证法的角度看,道家与儒家实有内在统一性。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佛家在与道家等中国文化的结合中形成了禅宗,禅宗论丑亦自有其特点。佛家和禅宗美学以“妙”为美,以“秽”为丑,其美学观点建立在对现象世界全盘否定的基础上。最集中地反映现实世界特点的范畴就是“秽”,而肯定通过修行超出轮回的“净”,佛家将整个娑婆世界都归入秽土、秽国,“而把此世界中一切有情生类包括诸天界都定为秽身即污秽不净之身,佛家语中凡身与秽身是等义词”。《自我奥义书》论证了梵性超越美丑分别的意境:“爱憎两无触,美丑同不与。如日黑暗吞,光明未遭蚀。称被吞食者,事相迷不识;乃最明梵人,傥解身见惑。”即达到“梵我同一”境界的人,“遍处于美者不美者皆无所凝滞,无厌憎亦无乐欣。”东晋鸠摩罗什指出:“法常寂然,灭诸相故。法离于相,无所缘故。法无名字,言语断故。法无有说,离觉观故。法无形相,如虚空故。……法离好丑,法无增损,法无生灭,法无所归。法过眼耳鼻舌身心,法无高下,法常住不动,法离一切观行。……法相如是,岂可说乎?”(《维摩诘经·弟子品第三》)佛法的真与佛法的空,本性相符。法(真理)本身无所谓美丑,美丑皆为幻见,没有生灭。《大般若经》云:“虽恼趣横森,寂岸层回,莫不同幻蕊之开落,不灭不生,比梦象之妍媸,无染无净,飙谷投响,则誉毁共销,月池浸色,则物我俱谢。”《心经》云:“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样的论说很多,与中国道家思想很相似。佛家的中国化——禅宗的产生,对中国古代艺术审丑带来直接的影响。[2]这种无垢无净、妍媸虚幻的思想对禅宗影响很大。如禅宗《宗镜录》云:“因智而分别妍媸”,乃是妄见。四祖道信:“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五灯会元》)修心便要容纳美丑,超越妍媸。老庄关乎美丑问题的卓见,被禅宗激活,对中国艺术产生重大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审丑精神的根源所在。最根本的是中国远古时期所形成的阴阳太极的循环思想模式。大致可分为:(1)面对权威时“道者反之动”的叛逆精神。(2)“不虚美,不隐恶”的求真精神。(3)“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懦怪,道通为一”与“容纳美丑,超越妍媸”的豁达胸怀。(4)“化丑为(中和之)美”的艺术法则。简言之,中国古代的审丑精神乃“儒道(后来有佛)互补”所带来的以否定性或阴性来整合文化和思想的特征。我们可以借用栾栋的观点:能否审丑,不仅是一个哲学智慧问题,也是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3]。这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审丑走向及其精神价值。
三、各种艺术形式美丑并举与互化
由于有上述相互补充、相互贯通的儒道佛等哲学思想的支撑,自三代以降的出土文物和艺术品中,就贯穿了这种美和丑并举互渗的艺术思维方式。中国古代也曾和西方一样,以近似于黄金分割率的构想去构筑大干世界的结构图式,如阴阳五行图的结构便是如此。但中国艺术和审美没有严格按照那个美的数字去做,而是走了一条与西方几乎相反的路径:去形取神,去美取丑,进而化丑为(中和之)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出土文物上,已经凝结了先民美学精神的萌芽形式:稚拙、粗砺、狞厉、怪异。伏羲龙身,女娲蛇躯,美丑相集。中国神祗大多更像是怪物,狰狞丑陋:九天玄女是人头鸟身的上古玄鸟,还有人首牛身的蚩尤,虎齿豹尾的西王母,以及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不胜枚举。总体上看,夏商周三代呈现一种美丑合体的文化形态。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饰是将极恶极丑之物事,简练化进而抽象化之后所得到的审美(审丑)形式,将饕餮纹饰的狰狞与人们意识的整饰性的形式化要求结合起来,从而把丑、恶之物事统合而淡化。汉代石刻造像把神仙灵异与历史及现实满满足足地刻画于砖石之上,也就将地府阴曹的可怖景象稀释转化。及至晋顾恺之认为,美丑的形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能够传神:“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世说新语·巧艺》)因此,魏晋南北朝绘画往往呈现出一幅幅不合常态的怪异之形,这怪异之形虽是为神而设,但唯有怪异之形方能趋近和表达出玄学时代人的精气神。
庄子在《德充符》、《人间世》等篇中刻意描写的畸形丑人,直到唐宋人物画中的罗汉画才表现出这种包孕高尚德性的丑怪人物形象。唐代画面多怪异形象,但笔法劲道圆柔。如唐梁令瓒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畸形怪诞,绝非和谐之美。唐末五代初画家贯休,传为其所画《十六罗汉图》中的罗汉面容,多为梵相,或头盖崎岖,或后脑突出,或长眉高鼻,皆形象古怪丑陋。一千余年前庄子心目中的丑陋怪异但刚毅智慧的形象跃然纸帛之上。唐代文学家中亦有主张直面真实,对于现实中的美与丑,必须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可隐瞒掩盖。这样才可表里相符、辞能达意,实现文学的价值,如韩愈。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可掩。”他自己的诗文便是这一理路的体现。由于受当时佛教壁画中怪诞恐怖画面有密切联系,韩愈诗中的丑陋形象俯拾皆是,大致可分为“丑物”、“丑行”和“丑语”三类。其他如孟郊尚苦寒,贾岛喜酸涩,卢仝显粗硬,李贺崇奇诡等等,都超出了美的规囿。[4]王维作为写意画的大师,曾画过一幅《袁安卧雪图》,其中的雪中芭蕉被世人讥为荒诞丑怪。这些都体现了唐人艺术观念的开放与新异。
迄宋,除了画家刻意以丑怪来形容人事,宋诗词所表达的丑怪更加集中和意味深长。苏轼有诗云:“如今老且懒,细事百不欲。美恶两俱忘,谁能强追逐。”(《寄周安儒茶》)体现了一种儒道佛相融之后的泯灭美丑的达观境界。欧阳修诗赞所得砚台:“砖瓦贱微物,得厕笔墨间;于物用有宜,不计丑与妍。”(《古瓦砚》)从实用角度出发对丑妍之物事加以重新衡量,体现了一种生活和艺术的辩证法。元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小令也很说明问题:“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古荒冷僻的事物被重新编织,进入一个新的时空就可“以丑为美”了。这自是一种很高超的艺术思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白华先生认为,庄子文章里所写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的范本。
明清书画诗词中的审丑,较之此前尤为“壮观”,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审丑风尚。明陈洪绶《观音罗汉图》、《唏发图》、《陶渊明故事图》等,造型怪异变形,线条清圆细劲,疏旷散逸。深得这一艺术旨趣的徐渭称赞丑观音:“至相无相,既有相矣,美丑冯延寿状,真体何得而状?”
明清书画家就沿着这一思路和法则,进行他们的艺术创造,故常常以枯藤老树、险山怪石、瘦马病梅入画,且画风怪笔横生。八大山人(朱耷)的画,集中于怪石、枯树、丑鱼、寒鸦等非美、不美甚至反美的意象上,铸造了属于他的审丑而怪诞的艺术世界。鱼、鸟瞪着眼睛,冷冷地看着世界和人世。鱼能飞翔,芋头似鱼非鱼(《花果册芋头》),似鱼又似鸟(《鱼鸟图册》),似山似鸭(《鱼鸭图》)。朱良志认为,八大山人的绘画突出了他的孤独、自尊、斩截、吟玩、寻找和超绝精神。[5]傅山提出了“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作字示儿孙》),张法认为这体现了一种与李贽、徐渭、汤显祖相通的理趣追求[6](P287)。明清的书法承秦汉时期崔瑗《草书势》、魏晋时期索靖《草书状》的“放逸生奇”。傅山书法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其书法则醉态怪异,几无法度;胸臆张扬,几近放诞。他的书法是自创的诗:“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谖。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对石的赏玩也以丑怪为美,并以此来与转型期的柔媚相颉颃。唐人便有赏石之风,白居易赞石诗曰:“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咏双石》)宋代承这种赏玩怪丑之石的风气,如苏轼有《枯木怪石图》,以及《怪石供》、《后怪石供》、《咏怪石》等诗文。以至清代,《郑板桥集·题画》言及古人对“丑”的执着:“米元章论石,曰瘦,曰绉,曰漏,曰透,可谓尽石之妙矣。东坡又曰:‘石文而丑’。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彼元章知好之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东坡胸次,其造化之炉冶乎?燮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这一对丑怪的把玩有着类似于克罗齐在《美学原理》中所言的“丑先要被征服,才能收容于艺术”之思。中国古人尤其是文人、士人的心胸已经能够容纳天地、纵横时空,自然这种怪而丑的石头成为他们品赏的玩物。近人陈师曾总结道:“文人画中固亦有丑怪荒疏者,所谓宁朴毋华,宁拙毋巧;宁丑怪,毋妖好;宁荒率,毋工整。纯任天真,不假修饰,正足以发挥个性,振起独立之精神,力矫软美取姿、涂脂抹粉之态,以保其可远观、不可近视之品格。”[7]其他如盆景、篆刻等,都竭力打破平衡,寻找怪异和新奇,借以表达某种生活况味或意识。近世以来对怪石等为代表的怪异的审丑,其实是对打破正统儒家文化思想和政治规制,期望张扬个性,在一定范围内对禁锢人的自由的大一统思想的反叛。从创造性看,此为新的陌生化艺术思想之表现。从审美范畴来说,此乃以陌生化审美形式颠覆既有的尊卑高下之优美型美学的体现。
明清时期,文学也渐趋容纳万象包举妍媸美丑的艺术气度。如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夫一部《金瓶梅》,总是冷热二字,而厌说韶华,无奈穷愁。”(第7回评)《〈金瓶梅〉读法》:“西门庆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惠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8]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创造了迥然独异、质拙朴厚的漆书,形同漆匠用扁刷刷出之笔势。其题墨梅诗与书法相得益彰:“野梅瘦得影如无,多谢山僧分一株。此刻闭门忙不了,酸香咽罢数花须。”金农的另一题梅诗曰:“雪比精神略瘦些,二三冷朵尚矜夸,近来老丑无人赏,耻向春风开好花。”这与其绘画、书法的美学风格是一致的,有汉画像之遗风,立足于对丑怪的表现,充分体现了近世(清中叶)艺术张扬个性的审丑精神。
四、化丑为中和之美的艺术辩证法
中国文化贯穿着一种独有的审丑精神,成为中国艺术的一种文化心理或艺术精神。但是,中国古代审丑意识或审丑精神,依然没有真正冲出道佛禅出世学派对丑怪或丑美的赏玩以致逃逸规避现实丑恶的文人雅趣,同时又陷于中和理想之中。这有远古的精神传统的印迹,《尚书·尧典》谈论音乐和诗歌,提出“八音克諧,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和谐景象。“和”有音乐之和与饮食之和。前者从神人以合到乐以调风到天人和一;后者是与盛食物的青铜器有关,器上的饕餮纹饰(大致为猛兽与其所捕食的对象如牛之类演化而来的合体),虽狰狞可怖,但经过重组变形,对立而不相抗,[6](P28-29)天下宇宙因“中”而能“和”,“中”就成了中国艺术的基本法则,[6](P41)而这些狰狞的饕餮纹饰所反映的正是化丑(恶)为“和”之美、“中和”之美。如果说中国文化和艺术追求“化丑为(中和)美”的境界或理想,那么,这一理想来自于这种神人以和所设想的“中和”境界。所以化丑为美就可理解为化丑为中和之美,而非那种纯粹的西方式的形式之美。栾栋在《感性学发微》中认为,将美和丑中性化的辩证处理,是中国先秦文化审美而不致十分贵族化,审丑而不致低级趣味化的关键所在。因此,中国古代艺术的审丑精神就要泯灭那种纯粹的形式之美所寄载的真理追求。西方美学和艺术追求个体的自由,艺术和审美是自由的象征。而中国(文人)艺术则倾向于获得赏玩的雅趣。这种艺术精神没有走向艺术乃人的自由精神之象征的路子,而是借丑怪所透露出的旨趣来逃避严酷的现实。以丑代美,或化丑为(中和)美,是道佛儒对惨淡冷酷人间现实的漠视与超越。反映在艺术中的所谓丑并非真正的丑,而是一种怪异。它的否定性特征及力量是透过不规则、不合法度、不正常,甚至冷漠、笨拙、粗糙、病态等怪异的非形式,来显示作者(诗人、书家、画家、园林建筑家等)对圆润美丽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和现实世界的无声抗议。中国美学和艺术采取“以丑来质疑、规避美”实则是超越美丑分别[9](P39)。
大致说来,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深层所表现的丑以唐为界,此前的丑是与(羞)恶相联系的,进而与道德发生联系。唐宋后,丑演变成一种无关道德的精神和旨趣。
所以,在中国艺术观念中,“丑”并非单一形态的美学范畴,而是包含了多样性的丑,如道德上的恶行,自然物事的顽瘦、朴野、荒寒,艺术感受的怪异、古拙等等,这是些未经人工雕琢加工的富有天然旨趣的非形式、反形式,也就是非美、反美,但能被中国古代文人(艺术家)所赏识和认同,并从中获得精神的愉悦,从而获得生命大美的享受和人生境界的提升。这种对丑的把握和刻画并非一般的“化丑为美”,而是“以丑为美”、“以怪为美”,或“化丑为和(中和)之美”,也就是化为生命的全息式存在,化为一种本真性生存、诗意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