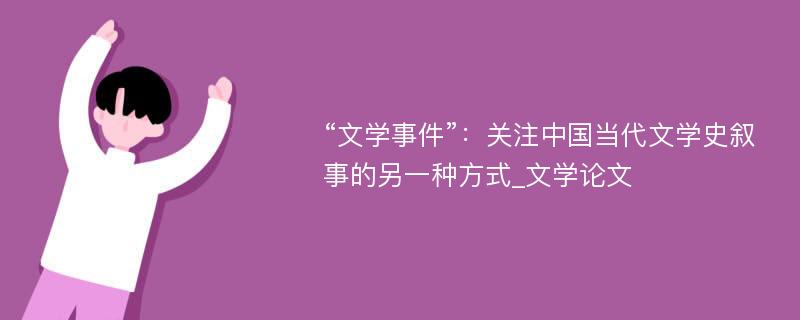
“文学事件”: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另一种聚焦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中国当代论文,事件论文,方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50(2004)03-0034-05
一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方式,与这门学科诞生的特定情境和它所承担的叙事功能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当代文学尽管脱胎于“现代文学”,但只有在确证了自己对于代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现代文学”的高级或进步之后,才能把自己从新民主主义文化中提升出来,并真正获得自己的政治身份和合法性。在这样一种情势下,1949年以后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就不能不选择一种与自己出身相一致的、确立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本质的叙述模式和修辞方式。它的主要特点,是性质先行、结论先行与理论先行:首先论证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与现代文学在精神气质和历史使命上的断裂:继而采取“以论代史”的方式,高屋建瓴大处落笔,从理论上建构这个学科的知识框架,并将这些“文学史知识”普遍化和绝对化;然后是勾勒和历数中国当代文学的运动史、论证史,实际上也就是批判史,借以说明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主导的、以工农兵文艺为主流的“文艺战线”如何取得了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最后是重要作家和作品的介绍。前几部分通常是“绪论”和“概述”的内容,是理论上的“一般”;后一部分是“一般”下的“具体”和“个别”,用来演绎“绪论”和“概述”中所确立的文学史的性质和理论,充实文学史的内涵。这种叙述模式热衷于对各种批判运动的叙述,借以从中抽绎出两条路线斗争、并最终由社会主义文化阵线占据领导权的发展线索。尽管在此过程中,它也重视文学事件的意义;但是,这类文学史对文学事件的叙述,极端地缺乏学理意义上的反思,而只是把它看作为在确定社会主义文学,而打扫战场或清理地基的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斗争或路线斗争。
这种叙述风格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的色彩,对文学史叙述本身的话语性和建构性不加任何掩饰。它的修辞风格充满了火药味,它把自己潜在的读者,定格为需要用话语来征服的心怀异端者和知识与道德上的被启蒙者。它的用语常常显得尖锐犀利,缺乏因势利导和循循善诱的善意和耐心。这种“演绎式”或“求证式”的叙述模式紧密依附意识形态,没有追求历史本真的学术旨趣,或者根本就是非学术的,因而,它对文学事件的叙述,也同样不可能是真实的。
19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文学史叙述压抑力量的减弱以及意识形态的淡化,这种叙述模式正被逐渐瓦解。在“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中,如果说相当数量的作家和作品的座次被重新调整是表面的成就,那么深层的收获,就是人们思维模式和叙述模式的转换。“演绎式”和“求证式”的叙述模式,也许还可以成为某些文学史教材的潜在结构,但其逐渐被新的叙述体例所取代,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以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代表的,大致接近以文学社会学为主要学术架构的叙述模式;以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代表的,以文学作品的审美解读为重心的叙述模式;以及以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为代表的,以多元历史叙述主体介入历史叙述的叙述模式。
尽管这三部文学史著作由于各自设定了不同的叙述目标而在叙述模式和修辞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但与1980年之前的文学史著作比较起来,有两大鲜明特点。第一,它们都摒弃了那种预先设定一个抽象的结论,然后再由作家作品来进行演绎证明的叙述模式;第二,它们都有意淡化了对文艺运动和文艺论争的描述,而把更多的篇幅放在对具体的作家和作品的解读上,其中尤以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著。陈思和在回应别人对他的文学史著作能否呈现历史真实的疑问时,多次强调这是一部“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借以把它和别的“以文学史知识为主型的文学史”相区别。他认为,对于今天研究当代文学史的专家来说,当务之急可能不是去还原历史或重评历史,而是“站在今天的审美水平上,或者站在今天这样一个理解世界的立场上,去重新解读那个时代的作品,看那个时代哪些作品是经得起我们的解释,哪些作品是经不起解释的”。“至于它是不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并不重要,也不应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标准”[1]。但是,只要企图在读解一部作品时建立一种深度解释模式,就无可避免地要联系作品的文学史背景来进行。因为,不了解作品赖以生成的压抑机制,我们几乎无法对当代文学史上各种文学现象做出任何深度的解释,也无法对单个的作品进行深度的解读。事实上,陈思和教授的这本文学史著作之所以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就在于他将文本的意义与当时特定历史情境相联系,从而将文本解读植根于文本所处的文化机制中,并最终获得超越于文本本身所能提供的思想史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前三十年的文学最大的特点是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矛盾冲突等的雷同化、模式化。我们甚至可以按照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分析,把它们“压缩”成一个或几个简单的句法,来概括它所有的情节和意义。这提示我们,当代文学之所以形成这样单调的格局,与前三十年政治文化对文学写作造成的相同的压抑机制有关。而笔者在这里所要着重强调的是,这些压抑机制的产生,其实与当代文学史上持续不断的“文学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
也许是出于对19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过分强调文艺运动和文艺斗争等“文学事件”的反感,近年来的文学史著作都尽量淡化或缩减了对文艺运动的描述,而把叙述的焦点放在文学思潮的演化和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上。尽管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参照了文学社会学的分析视角,并通过有效地整合文学史的叙事资源,以期能够“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在描述当代文学的样式、风格发展演变的同时,也“关注这些类型的文学形态产生、演化的情境和条件,并提供显现这些情境和条件的材料,以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2],但是直接叙述文学事件的文字,仍然不过千字左右。然而,对重要文学事件的忽略,不但对于文学史来说不是事实,而且也无法真正建立起对于文学作品的深度解释模式。因为,我们既不能因为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所产生的不良感受而遮蔽真相,也不能仅从文学内部或纯粹的文学思潮中来获得对文学文本的深度理解。一定程度上,1949年以后文学的生态就是由各式各样的批判运动的“文学事件”所构成。这些事件既有由政治批判运动而累及到文学界的批判运动,也有文学界自身为了“清理门户”和“打扫卫生”而开展的文艺论争,当然,这些论争最后几乎都会很快演化成形形色色的批判运动。而每一个这样的文学事件,几乎都会在事后形成一些可见或不可见的“戒律”、“教条”、“禁区”或“规则”,也都会或隐或显地影响到作家的心态和选材、作品的结构、人物的设置、矛盾冲突的发展等等,最后形成一些创作上的套路或模式。文学纪律或文学体制的形成,并不一定是由中央文件或大会上的讲话形成的,有些就是由这些文学事件形成的。正如吴秀明教授所说,“文学体制毕竟是深层次的东西,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文学和文学思潮,甚至连干扰破坏本身也与体制问题密切有关”[3]。文学史不能不去关注这些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之外的现象和事件,因为它们是活的历史的一部分,是文学史的解释之源,是比文学史本身更大的“大文本”。因此,把文学事件作为文学史叙事的“枢纽”,首先就是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洪子诚认为,对于具体的文学现象的选择与处理,表现了编写者的文学史观和无法回避的价值评析尺度。[4]而对这些文学事件叙述与否以及如何叙述,也就体现了叙述者的一种视角,一种切入历史的方式。在我们看来,不管出于体例或是其它的什么原因而忽略了文学事件对文学史的生成影响,都会缺乏一种历史文本所应有的厚重感。这也就是尽管我会对陈思和教授的文学史著作所达到的非凡成就抱有深深的敬意,但却无法完全认同陈思和教授在对这本严格说来更像是“文学作品史”的文学史,在呈现历史的层面上,所做出的解释的原因。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大面积地减少了对文本之外的历史情境的勾勒,以致在事实上阻碍了对文本本身可能的深度解释,或“同情的理解”。
强调对文学事件的关注,并非是要刻意夸大“文学事件”本身,不过是希望从“事件路径”的视角,更深入地解释文学史的深层意义结构。既然当代文学史是由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学事件所构成,文学史研究是不可能离开对事件的叙述、分析和解释的。法国的历史学家韦纳认为,“历史就是叙述事件,叙事就是把历史上的行动者相互之间看来是局部的、混乱的和不可理解的情节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解释”。[5]韦纳在这里主要是就通史的编写而言,但对文学史这样的专门史来说,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当代历史学家勃罗代尔曾对一些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表示不满:“严格地讲,一个事件可能具有许多连带意义,它有时为一些深刻的运动充当见证,并且通过种种牵强附会的因果推理——以往的历史学家乐此不疲——吞并自身以外的其它时间。它可以被无限延长,自由地或勉强地与一系列其它事件或隐藏现实相联系。”[6]这里如果抛开勃罗代尔对缺乏实证精神的“牵强附会”推理的指责,应当承认他相当准确地道出了“事件”在历史研究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事件可以通过因果关联而“吞并”自身以外的长时段,这里的吞并指的是占有一个意义链上的核心位置;从共时性的角度看,事件则可以与其它事件结成互为解释的事件网络。通过分析一个一个的文学事件,我们能得到仅仅对文学思潮的分析所不能得到的更多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史学一直关注的文本背后的深层压抑机制,以及与之相连的政治和文化的结构。
三
既然文学事件一方面使深层的文学史事实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其本身又参与到了文学史事实的建构中,那么,它作为动态的文学事实与透视文本之下的社会结构的切入点,理所应当在文学史叙述中占据相当的位置。然而,什么样的事件可以称作“文学事件”呢?我认为,它除了应当具备时间、地点、人物、起因、情节、结果等构成事件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基本要素之外,还必须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对文学史产生较大影响、对文学写作产生某种规约力量的事件。这里以1950年代初开展的对萧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为个案,来具体考察文学事件的特征,及其在文学史叙述中的重要功能。
1951年开始的对萧也牧《我们夫妻之间》的批判之所以可以定义为“文学事件”,是因为从此之后,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开始有了一个稳定的模式,或者说,这个事件在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千篇一律地被边缘化和被贬斥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和杀鸡儆猴的作用。因为尽管自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传达以后到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召开,文艺界已经逐渐形成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工农兵文学”潮流。尽管1948年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对文采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轻蔑和嘲讽的作品,但是,文艺界并没有真正树立起刻意丑化知识分子的写作模式。或者说,在描写知识分子和描写工农之间,还没有在文艺界形成一个明确的思路和套路。但是,随着建国初期1951年对萧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的批判,这个思路和套路终于形成了。
据萧也牧“交待”,他“写作《我们夫妻之间》原来的企图是: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来表现一个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憎爱分明,和旧的生活习惯不可调和;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倔强的,直爽的,然而是有缺点的,那就是有些急躁,有些狭隘。但这些缺点并非是本质的。这个人物就是小说中的张同志。为了烘托这个人物,拉了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来作陪衬。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以及写好之后,我也曾经考虑到一些问题,主要是李克这个人物。他既然是经过改造的,然而确有些荒唐,说不过去。但我想:所写的都是些日常生活琐事,并非是他的主要一面,并不影响大体。同时,我认为还表明自己需要继续改造。我想这样一来,就可以交待得过去了。在1950年秋,《我们夫妻之间》这一篇,我曾经作了两次删改,例如:张同志不骂人了,李克一进北京城那段城市景色以及‘爵士乐’等等删掉了,张同志‘偷’李克的钱以及夫妇吵架的场面改掉了,凡‘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等字样删掉了。结尾李克的‘自我批评’中删去了‘取长补短’等字眼,在李克自认错误之前,加上了‘严重’、‘危险’等形容词,并且把李克改成参加革命才四五年的一个新干部等等。”[7]
这说明在萧也牧意识里,如何按照既定的阶级性属性来刻画人物,已经成为他的某种自觉。尽管如此,这篇小说一问世,还是遭到了文艺界的强烈围攻。其中重要的批评文章有:陈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萧也牧创作的一种倾向》,认为虽然萧也牧写出了主人公朴素的阶级感情,但是基本上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并认为这还不是作者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进城后在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上产生的一种不健康的倾向的苗头。[8]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发表在《文艺报》上的《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不但认为“作者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韵爱和热情的”,进而又上纲上线到“我觉得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就是说,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这简直就是在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然后他更加触目惊心地写道:“从这点上说,作者的‘阶级立场’的确是很坚定的;但是什么阶级立场呢!陈涌同志已经说过,小资产阶级!实在奇怪,作者萧也牧同志对待小资产阶级分子,还能够坚定地站稳小资产阶级立场表示了他的爱;而工农分子,却甚至赢不到他一点小资产阶级之类的热情!”他也就不惜对着作者大喝一声:“萧也牧同志,我读你的作品,可真是替你提心吊胆呢,然而我也热烈地希望你留心!真的,你不能再向前进了,立刻回头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去,热爱劳动人民,脱胎换骨地抛弃你的玩世主义的倾向!”[9]
再看丁玲的比冯雪峰的更有杀伤力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吧!文章写道:“也牧同志!在这里,也许你是真心想对李克有所批评,但事实上,你却的确是巧妙地玩了一个花头!你这篇穿着工农兵衣服,而实际是歪曲嘲弄工农兵的小说,却因为制服穿得很像样而骗过了一些年轻的单纯的知识分子,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作者最后说:“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是在哪里。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尤其是知识青年,他们在很快地进步着,他们很快就会丢开你,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10]
已经有不止一个当年的过来人,在回忆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场论争中胆战心惊的心态。无疑,这样的事件对如何继续刻画知识分子的形象,不能不起到警示作用。作家是具有较高智商的人,何况其中的不少人已经在延安整风的严酷环境中“洗过澡”。经历过这样声色俱厉的批判运动,他们在创作时不会不知道该如何趋利避害,如何中规中矩。换言之,不深入挖掘这样的文学事件,就难以真正窥测到制约1949年后前三十年知识分子形象如此匮乏的深层原因。
文学史叙述聚焦于文学事件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以上面的文学事件为例,叙述者既可以在分析文本结构时将事件作为一种背景,也可以将文学事件作为文学史之外的“文学事件史”独立于文学思潮史或文学作品史之外,让它们相互补充和解释,以多元视角的融汇,来重构文学史本来就具有的丰富和生动。
收稿日期:2003-02-01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艺术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陈思和论文; 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