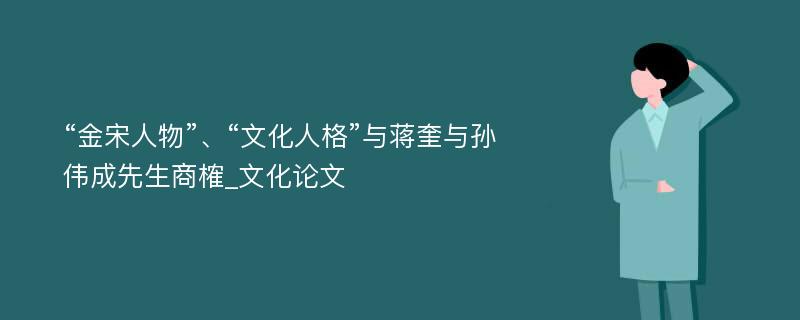
也谈“晋宋人物”、“文化人格”及姜夔——与孙维城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人论文,人格论文,也谈论文,文化论文,孙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维城先生的论文《“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兼论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文学遗产》1999年第2 期)为姜夔及宋词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不少看法都有新意。但对文中有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特以此文同孙先生商榷并就正于同好。
一
孙先生以“晋宋人物”论姜夔,立论依据是陈郁《藏一话腴》那段话,并辅之以周密《齐东野语》所引姜夔自叙的范、杨、萧、朱诸人之赞语。由前者引申出“与其说是描绘姜夔,不如说是描绘一种文化人格,一种封建后期士大夫理想的文化人格”的结论;由后者的“晋宋人物”一语作出了这一美称是“审美特型的代表,姜夔卓然挺出”的推导。我们首肯后者,却难以同意前者。且不妨紧扣文本,看看姜夔作为“晋宋人物”,所指内涵是什么?
陈郁所说,先言姜夔外表:“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若不胜衣”,此谓其外形瘦弱,相貌清癯;再说其文学、书法:“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气貌与笔力就是这样极不相称地统一在姜夔身上;“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这是贫而好客的姜夔以食客养食客的生动写照;“图史翰墨之藏充栋汗牛”,此言收藏之富;“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这是对姜夔既点题又入题的评价;“意到语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倘将前面的“笔力”限于书法范畴,这里就是指其文学了。综陈郁所言,“气貌若不胜衣”,当近于服药好酒、挥麈谈玄,尚清瘦而鄙丰肥的晋宋人;“襟期洒落”、“高远”,则是晋宋人物特有的精神、气质和追求。姜夔的外貌、精神给人以《世说》中人的印象,陈郁故有此评。
倘言陈郁所评可将姜夔限定为“晋宋人物”的单一型范,周密所引姜夔自叙中诸人赞语就可见多元了。在范成大眼中,“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翰墨”可征之于姜夔《续书谱》的抑唐人而扬魏晋,以及他人对姜夔书法的评价;“人品”则可视作陈郁所说的概括。在杨万里看来,“以为于文无所不工,甚似陆天随”,则非晋宋人物,而似晚唐诗人陆龟蒙。萧德藻以之为作诗四十年来的诗友。朱熹则“既爱其文,又爱其深于礼乐”,后者显然不是晋宋人物,而是传统的儒家形象;“稼轩辛公,深服其长短句”,可见姜夔见赏于辛弃疾的是在其词。这些前辈名人,都因自己的所好所赏肯定了姜夔的某一个侧面,在他们眼中,“哈姆雷特”各有状貌,并非“晋宋人物”可限。如将陈郁之评与姜夔自叙相比勘,应该说,“晋宋人物”或为姜夔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并非他的全部。
“晋宋人物”的内涵是什么?孙先生认为:“实质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这是自我价值被发现、被肯定的时代。外在的功业退居第二位,首先是肯定自我的人格,自我的价值,自我的意识,自我的情感。他们风神潇洒,飘逸不群,这种洒脱的襟期来源于玄学的深思。而精神人格的大解放大自由又具体表现为晋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文中即以此为据,从“发现自然”和“深情”两方面对姜夔词作了较全面、深入的论述。认为白石词中,“对自然山水已不仅是观赏,也不是作为人格精神的类比,而是借山水烘托自己的心境意绪,表现一种意境,表现心境中的“山林缥缈之思”(《角招》序),从回归自然中安顿曾经疲惫的生命”。又认为白石词“往往通过绝望的爱情来写心灵的感受”,“对爱情的咏叹绵长哀婉、深情专致、历久弥新,……他写出了这一场缠绵爱情的心灵体验的全过程,而在普通的、具体的人生悲哀中倾注了历尽沧桑后的苍凉与沉重。这不仅是继承晋宋风流,而是反映了封建后期士大夫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无奈心态。把对山水的深诣与对爱情的执着融为一体,在宋词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诚然,白石词中确可见到自然美景与自己的深情,不妨也可进而推导出“透过他的词作,在他的纵情山水、深情绵邈与狷洁清冷的背后,我们聆听到后期士大夫追求精神自由、渴望宁静淡泊的心声”,但这是否就是“对人生对社会的厚爱”,“是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本质所在”呢?
孙先生在晋宋人物之实质所作的论述,显然源于宗白华先生“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这一深中肯綮的概括,但宗先生所论,是对止于晋宋时期历史的历时性观察的结果,而后人对于前代思想、文化的接受,是在积累中融汇熔铸,已非晋宋之时作为新出者的即时性意义。
具体说来,《诗经》、《楚辞》中的自然景象基本上只是比兴的材料。《诗》的主导精神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以《骚》、《辩》为代表的屈、宋之《辞》可概之为“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九章·悲回风》),而其志则主于“怀抱”。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所感所发主要是社会性的情感。被后代盛称的“建安风骨”是“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造就出的“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同样是社会性的情感。大概只有《古诗十九首》才多为抒发一己之情,却对自然美着墨无多。所以,只是到晋宋时期,陶、谢及众多的山水诗、山水小品以及《世说新语》,才提供了宗先生所说的佐证。晋宋以后,齐梁诗颇多山水清音,庾信诗文不乏深情,唐诗更是将这二者都推向高峰,宋诗虽以筋骨思理见胜,却仍多山水与抒情的佳制,宋词尤为缘情领地,足见对自然美的描述。宋以后,体裁的代胜造就“一代之文学”的不同,“自然”和“深情”却始终是两大主题(当然还有“言志”传统的延续)。所以,晋宋对自然美及自己深情的发现,为后来历代所继承,并非从姜夔起才树立晋宋人格精神。(闻一多《唐诗杂论》中对孟浩然的赞誉说明了什么?在唐诗研究中屡言《世说》中人物又说明了什么?)因论姜夔而推崇其“晋宋人物”的一面,并演宗先生所论以相证,进而作“后期士大夫”“心声”,又含混为“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就未免推扩失当了。
这里且将“后期士大夫”的概念暂置,下面再论。即以姜夔而言,发现自然美和自己的深情,是否合乎宗先生所论?又,这些是否属于姜夔行事、性格、感情的全部?精神人格的大解放大自由是否适合于姜夔?我们还是以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208—226页。)为据, 就“自然”与“深情”,揆之于上述论题。
关于“自然”,宗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直觉指出:“晋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晋人的美的思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姜夔词有“清空”之评,有“野云孤飞”之拟,似乎近于“虚灵”、“澄澈”、“空明”,然而,晋人如顾恺之赞赏会稽山川之美,王司州谓吴兴邱渚使人情开涤,觉日月清朗,简文入华林园,因翳然林水而有濠濮间想,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都因“光明鲜洁,晶莹发亮”而有“显著的追慕”,强烈的移情。姜夔词,却闻“清角吹寒”,见“波心荡、冷月无声”而生《黍离》之悲(《扬州慢》);因“湘云低昂,湘波容与”而“兴尽悲来”,“目极伤心”,“空叹时序侵寻”(《一萼红》);感于“一帘淡月”,在幽寂中闻“乱蛩吟壁”之声而“动庾信清愁似织”(《霓裳中序第一》);在“清风徐来,绿云自动”的荷叶中,想到的是“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念奴娇》)。孙先生论及的《湘月》,也是在“山水空寒,烟月交映”,“如燕公郭熙画图”的景色中,感慨“凄然其为秋也”,“谁解唤起湘灵,烟鬟雾鬓,理哀弦鸿阵”(注:本文所引姜夔诗词及《白石道人诗说》,皆见夏承焘笺校《白石诗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 月版。)。总之,其词多系情因物感,流露出心底的悲凉。即如范成大宴上所成的咏梅名篇《暗香》、《疏影》,也在“叹”、“泣”、“相忆”、“暗忆”、“却怨”、“哀曲”诸语及二词的形象、意绪之中流露悲情。缘于此,极推崇姜夔的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屡言白石词“无穷哀感”,“皆写怨情”,“无限伤乱语”,又总论其词“以清虚为体,而时有阴冷处”(注:见唐圭璋:《词话丛编》3797—3799页,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 以下所引词话未注明出处者,皆见此书。),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则称之为“沉忧善歌之士”。综观姜夔所作,难见“光明鲜洁”,也非“即实即虚,超入玄境”,对于自然风景,决无王羲之去官后游山泛海,“卒当以乐死”之叹,也不象苏轼、张孝祥的部分作品那样,“表里澄澈,一片空明”。
关于“深情”,宗先生以晋人“一往情深”,分举王子敬行山阴道“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卫玠思玄理不得而病,何扬州为庾亮死而感叹“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以见对自然、哲理、友谊的深情。继而所列的顾恺之拜桓温墓,张季鹰哭顾彦先“不胜其恸”,“又大恸”,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王长史登茅山大恸而哭,阮籍驾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这些都足证王戎所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只有在以“自然”挣脱“名教”的枷锁之后,崇尚玄学的晋宋士人才能如宗先生所说,“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观姜夔词,虽然“对爱情的咏叹绵长哀婉、深情专致、历久弥新”,但周济仍有“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之论(《介存斋论词杂著》);王国维以其“隔”,且谓“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人间词话》);夏承焘先生则以其恋情词“却都运用比较清刚的笔调”,称之为“以健笔写柔情”(注:《论姜白石的词风》,夏承焘《姜白石词编笺校(下简称《笺校》)·代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5月新1版。)。白石所爱固然专一并深挚不忘,却未似晏几道、秦观那样有“古之伤心人”之评(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难见所作有如周邦彦那样“愈朴愈厚”之语(况周颐《蕙风词话》)。
如此可见,姜夔词中的“自然”与“深情”并不尽符合宗先生笔下的晋宋范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时代使然。东晋、刘宋乃“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此前的汉代,“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此后的唐代,“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均见宗文)。宗先生未论及赵宋,而恰是这时代,将唐代三教的“并立”作了“融汇”,造就出新儒学——理学。若谓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所作的尚是理学的奠基和渐成,到比姜夔年长一辈的朱熹,则已使理学为之成熟了。而姜夔曾以“深于礼乐”得到朱熹称赏,此可以进《大乐议》于朝并自作《圣宋铙歌》证之。《大乐议》不仅一一指出时乐之非,且通过论证“比年人事不和,天时多忒,由大乐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气也”(注:《宋史》卷131《乐志》84, 见《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12月版。),欲真正做到五音配五行、正人伦、利国事,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中和”思想。而朱熹“爱其文”者,也在于此。其书论《续书谱》所体现的中道思想自不必说,人所熟知的《白石道人诗说》云:“喜词锐,怒词戾,哀词伤,乐词荒,爱词结,恶词绝,欲词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惟《关雎》乎!”“《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当以心会心。”可见其儒家诗教观点。姜夔秉孔子之教,对喜、怒、哀、乐、爱、恶、欲都有所批评,正是认为诗歌应追求性情之正,声气之和,是以“思无邪”为归的;而称道《诗》之“美刺箴怨皆无迹”,当然就否定作诗要留下强烈的思想与感情的印痕;倘再以“吟咏性情,如印印泥,止乎礼义,贵涵养也”之说相佐,姜夔诗论的儒家底色和理学气味都是很浓的。由于“读其说诗诸则,有与长短句相通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且又不应只限于“技”,前引周济、王国维、夏承焘诸氏之评,并非无由。综观姜夔一生,常常处在由于时代、经历、个性而引起的人生矛盾中:他有沉忧难解的黍离之悲,却无辛、陆那样短暂的驰骋疆场的经历;才华超轶却终身布衣、天涯羁旅;心性甚高却不得不依人而食;情有独钟却难成良缘,带给他终身隐痛。然而这一切既没有化为阮籍穷途大哭而返所凝结成的《咏怀》诗的惨痛激烈,也没有谢安携妓载酒而图东山再起的浪漫潇洒(尽管他亦有过携小红归吴兴之举);他内蕴深情,却力求出之以平和、敛约,摧豪放为清刚,变急切为闲淡,化哀怨为旷达,以性情正、声气和求中和之美,故给上述诸氏以“情浅”、“有格无情”、“清刚”、“健笔柔情”的印象。
因此,姜夔给人以“晋宋人物”的印象,主要是在于其外貌、风度、气质及出众的才华、终身未仕的经历,诚如陈撰《玉几山房听雨录》所说:“先生事事精习,率妙绝神品,虽终身草莱,而风流气韵,足以标映后世。当乾、淳间,俗学充斥,文献湮替,乃能雅尚如此,洵称豪杰之士矣。”(注:转引自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165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版。 )那些入世而又欲超世者赞其为“晋宋人物”,确是顺理成章之事,但这并非其思想志趣的主导面。姜夔因丞相谢深甫、京镗怂恿上书论雅乐,进《大乐议》、《琴瑟考古图》,结果只是“诏付奉常,有司以其用工颇精,留书以备采择”(注:《庆元会要》,转引自《笺校》266页。)。 徐献忠《吴兴掌故》认为是“时嫉其能”,“是以不获尽其所议”(注:该书卷3《游寓类》, 见《吴兴丛书》,1915—1919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这一姜夔生命史上的大事,留给他的是憾恨:“晴窗日日拟雕虫,惆怅明日不易逢。二十五弦人不识,淡黄杨柳舞春风。”(《戊午春帖子》)上书后第二年的庆元五年(1199),他又向朝廷上《圣宋铙歌》十四章,虽幸得下诏免解,应试礼部,却终未中选,以布衣终其身。他作于开禧三年(1207)的《卜算子》在感慨梅花“开遍无人赏”之时,尚有“细草藉金舆,岁岁常吟想”之句,对当年皇帝下诏允试一事念念不忘。他对于终身草莱,实有不甘,“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玲珑四犯》)即其明证。他的词被清代浙西派奉为醇雅之极则,但仍有“托物比兴,因时伤事,即酒食游戏,无不有黍离周道之感”(注:王昶《春融堂集》卷41,清嘉庆本。),“犹诗家之有杜少陵”,“流落江湖,不忘君国”(宋翔凤《乐府余论》),“南渡之后,国事日非,白石目击心伤,多于词中寄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等政治性的解读、接受。正如作为宋代著名的音乐家,在他心目中,山林悠扬缥缈的箫笛之声永远也无法取代庙堂庄严典重的钟鼓之响一样,作为宋代杰出的文艺全才,尽管他也显示出晋宋雅士那“飘逸不群”的风度和“狷洁清冷”的气质,但在本质情性上,在思维方式上,却是他长期浸淫着的儒家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
姜夔有这样的儒学根柢、理学影响,熟知诗教,深明礼乐,虽终身布衣,气貌风格皆类晋宋雅士,毕竟不能算作真正的“晋宋人物”,不能对他作以偏概全的阐释、演绎。相较之下,《齐东野语》所引自叙,应是比陈郁所说更近于一个完整的姜夔。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可以宏观地适用于晋宋人物之评,却于姜夔不宜。
二
孙维城先生由把姜夔当作“晋宋人物”,兼而论及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笔者对此也有不同看法。
倘以安史之乱划界,宋代当然属于封建社会后期。孙先生说:“宋代开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形态。一方面是歌舞繁华的新时代,另一方面又是封建社会衰落期的开端,形成如此矛盾的混合体,北宋人的心态从而比他的前人更为矛盾与复杂。”这是符合事实的,但不能据此简单地以文体分工和文艺思想来以偏概全地取代宋人的政治思想、社会责任感和角色意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所倡导的“文道合一”并非仅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儒家自诞生起,就以入世、从政、关怀天下民生为己任;而文苑中人则重在才情、言辞及生活情趣。南朝范晔撰《后汉书》首立《文艺传》,就标志着对文士从儒生中分离出来的承认,这是“文的自觉”的必然,也是士阶层随着社会进步而分化的结果。在宋以前尤其是晚唐五代,二者之间的区别和分化是很明显的。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论稿》中说:“自武则天专政破格用人后,外廷之显贵多为以文学特见拔擢之人。……及代宗大历时常衮当国,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自德宗以后,其宰相大抵皆由当日文章之士由翰林学士升任者也。”(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0页。)其发展的结果如何呢?钱穆先生认为:“进士轻薄成为晚唐社会及政治上一大恶态。……而唐代政府则在这一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注:《国史新论·中国智识分子》,《钱宾四先生全集》卷 30第178页,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年1月版。 )所以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倡文道合一,具有纠晚唐五代进士轻薄之风,使文苑恶习向儒林传统提升的意义。“文”的方面:柳开针对晚唐五代的“文体薄弱”,“起而麾之”(注:分见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奏上时务书》,《全宋文》卷385。巴蜀书社1990年5月版。);范仲淹认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注:分见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奏上时务书》,《全宋文》卷377。巴蜀书社1990年5月版。);欧阳修既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注:分见《答吴充秀才书》、 《送徐无党南归序》, 《四部丛刊》影元本《欧阳文忠公集》卷47。),又将“三不朽”分开来讲,并不以道代文,他特别指出:“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注:分见《答吴充秀才书》、《送徐无党南归序》,《四部丛刊》影元本《欧阳文忠公集》卷43。)“道”的方面,这些诗文革新的倡导者,正是“自能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新唐书·文艺传序》)。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树起了士人风范;“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注: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316页,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苏轼的一生, 被陆游总结为:“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注:《陆游集·跋东坡帖》2262页,中华书局1976年11月版。)他们事功与文学的成就,标志着儒林与文苑两大传统的完美结合。
陈寅恪先生云:“欧阳永叔……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注:《寒柳堂集·赠蒋秉南序》,《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5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年9月版。)对宋文化的高度评价,是有其特定的道德指向、社会价值标准的。闻一多先生认为唐代文化即进士文化,自是的论,但唐代政局却受到武夫与宦者的极大影响。只是到了宋代,才真正形成以世俗地主经济为基础的庶族政治,“进士文化”发展为“士大夫文化”(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21:“(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中华书局1986年5月版。 ),应是这特有的“士大夫文化”,才使陈先生为之感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注: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42页。)
明乎此,北宋人之鄙薄晋宋之风就不难理解了。干宝《晋纪总论》云:“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注:见《黄氏逸书考》,1934—1937年江都朱氏刊本。)《颜氏家训·涉务篇》则以“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来概括晋室南渡后的“文义之士”(四部备要本)。这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而兼“士大夫文化”造就者相比,确实差别太大。因此,梅尧臣、欧阳修之论诗主张平淡、闲淡、古淡;苏轼之赏识“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感慨“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注: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苏轼文集》,2124页。);黄庭坚、范温之以“韵”论书画以至文章诗词——赞赏的都只是部分晋宋之“文”而非其“道”。即使孙先所说的“到宋室南渡前后,人们开始公开推重晋宋人物”,也缘于此,如文中所提及的人物,除张元干称道的苏庠隐居不仕外,余如米芾书画、秦观诗字、苏黄帖题跋等,皆限于文、艺域内。且南宋中期之推重晋宋人物,并非与时局无关。高宗长期主和,直到孝宗即位后才有起用张浚、发动北伐之举,却因兵败符离,又缔“隆兴和议”,此议之成,宋、金间四十年无战事,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失败后,两朝又“通好”十八年。正是这样的政治、时局,使主战派难伸其志,只能扼腕叹息。事实上的偏安江左,也会引起人们对晋宋风流的叹赏。但即便如此,无论是北宋、南宋,都决非“士大夫精神上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大自由”的时代。
姜夔主要生活在宋孝宗隆兴至宋宁宗嘉定之间,正是宋、金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有出将入相之才的辛弃疾也只能转徙于地方任上,又被迫两次闲退二十年之久,带湖、瓢泉之词颇以羡庄慕陶为主调。在此政治、文化环境中,既长于艺、文,又以言、行见高的姜夔,被称道为“晋宋人物”,确是很自然的事。同样,如杨万里之以“晋宋人物”推许范成大,也在于后者已从官场“围城”中走出,已从事业、世务中脱身,角色转换,诗文歌词、清谈雅论成为生活中的主要内容。虽如此,情趣之转移并不等于文化人格之变,至多只能目之为审美意义上的晋宋范型,对此,我们论述必须谨慎对待。虽然“作为这一审美特征的代表,姜夔卓然挺出”,但能否由此“审美”之“特型”而放大成“对姜夔其人其词的分析实际是对封建后期士大夫文化人格的分析”呢?能否由薛砺若《宋词通论》中的一句断语(其准确性尚有待论证)而推演出“姜夔词的意义已经溢出了词学领域,而体现出士大夫构建理想文化人格的愿望”呢?
先说宋代士大夫文化人格。南渡前后虽对“晋宋人物”有不同评价,但在出处大节上,两宋并无显著不同。《宋史》卷446 《忠义传序》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以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乃宋之亡,忠节相望,斑斑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姜夔可以是文、艺域内“审美特型”的“晋宋人物”代表,但并不足以成为南宋文化人格的全权代表。既云“文化”,就应超越文学视野的框定。在姜夔之外,留下远为巨大历史身影的是朱熹,“朱熹人本主义理学所体现的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就是伦理理性,他的理学,就是浸透儒家伦理理性精神的人学。”(注:束景南:《朱子大传·尾声》105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而伦理理性精神对塑造封建后期文化人格的作用,自是不言而喻。稍长于姜夔的还有辛弃疾、陈亮、叶适。纵不论稼轩词,辛弃疾上《美芹十论》于朝,又上《九议》给宰相虞允文,“文墨议论尤英传磊落。……其策完颜氏之祸,论请绝岁币,皆验于数十年之后。”(注: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转引自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5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月新 1版。)则是不是较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的“晋宋人物”,更见封建后期文化人格的力量?陈亮倡事功,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注:致朱熹信中语,《陈亮集》增订本下册339页,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自负,曾上《中兴五论》、《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及“第二书”,欲借一第以施展经济之怀,却对皇帝“欲官之”而笑曰:“我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宋史》本传)他的狂怪比起晋宋人物的“雅韵”来,难道不也是一种文化人格?叶适反对空谈理性,讲究功利之学,是永嘉学派代表,他所说的“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注:《赠薛子长》,《四部丛刊》影明本《水心先生文集》卷29。)。这四“无益”,比起晋宋的清淡雅论,应是更见时代精神的文化人格的体现。即如亦被目为“晋宋人物”的范成大,也是极具淑世精神的人物,为官有政绩,使金之时不畏强权,不辱使命,几被杀,途中所作七十二首绝句,感事伤时,俨然诗中史笔。《宋史》本传云:“有古大臣风烈,孔子所谓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欤?”推许范成大如晋宋人物的杨万里,早年受学于张浚,性刚直,反对苟安而主张积蓄力量抗金。人们多知他作诗关怀现实民生,却较少知道他是《易》学家。我们岂能因其“诚斋体”而只认为他是个诙谐的诗人?对于人生阅历丰富,思想、情趣属多侧面的士大夫,我们不应以偏概全,将特定语境中的某一赞语视为其文化人格之向往。宋代虽进入封建后期,但由于封建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新登上历史舞台的庶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远不如南北朝乃至唐朝门阀士族那么稳定,其生死荣辱皆与皇权兴衰休戚相关,故宋代士大夫不可能象门阀士族般纵情作乐,反而更须有所作为,更关心国事。故而儒林精神重于文苑传统,士人普遍具有淑世情怀,加以“道”对“文”的导引,“理”对“情”的节制,虽由于时代、政治、经济等种种原因而间或向往晋宋风流,却并未成为主导,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国智识分子》(见前引)中指出:“我们若把握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来看道家思想,其实仍超不出儒家规范,仍在儒家立场上补缺救弊,或说是推演引伸。因此庄子心中的理想人物与理想生活,依然常提到孔子与颜渊。我们必须把握到中国智识分子内在精神此一最高点,才可万变不离其宗地来看中国智识分子之各色变相。”因此,“晋宋人物”乃其“变相”之一,而非其文化人格之理想。
孙先生关于封建后期士大夫文化人格的论题,是论止于姜夔及南宋。笔者认为,论述完整的“封建后期”及相关的“士大夫文化人格”,尚有向后延伸的必要,亦即:宋之后,至少明清两朝还产生出不同于宋代“晋宋人物”的“文化人格”。
明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观念、风尚也在变,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唐寅、祝允明等江南才子,在“狷介自处”之外,又见晋人放诞之风。此后,王阳明承陆象山之说发展出“心学”,本欲以心学体系维护封建秩序,却收到种瓜得豆的效果:人们从关注“天理”之外在规范转为关注人的主体,使自然人性论有了滋生的土壤。于是,王门的“泰州学派”以人的自然本性来对抗“天理”,反对禁欲主义,并形成了强大的力量。至少在文艺界有徐文长,思想界有李卓吾,都悖逆传统思想观念,发大胆之论。如谓姜夔得晋宋人之“狷”,徐、李则得其“狂”,且又借助于晋宋未出之“禅”。而汤显祖、冯梦龙、公安三袁、竟陵派,或非狂士,却以各自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造就出浪漫的文学洪流。尽管徐、李主要是破坏封建伦理而缺乏思想的积极建设,然而在这虽已滋生资本主义因素、却仍处封建主义后期的中晚明,是否也代表了一种文化人格呢?
明亡后,清初思想家反思历史,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代表人物既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君主制度,又继承了晚明东林党人的精神,即批判王学末流视国计民生为末务、空谈性理、只顾享受的人生态度,高举起经世致用的旗帜。他们都如同前人指斥魏晋清谈一样地批判程朱、陆王,几乎是五百年前陈亮、叶适所论的翻版。清初思想家在初建政体民主思想的同时,却在批判王李之学中又回归于儒家的纲常伦理,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悖论。但是他们在鄙嗤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阔论”,批判理学家“治财富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扦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注:黄宗羲:《弁玉吴君墓志铭》,《南雷文定后集》卷3,耕余楼本。)的同时, 仍以强烈的经世意识和实用精神,表达“君子之为学”“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注:顾炎武:《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见《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涵芬楼影印康熙刊本。)黄宗羲、顾炎武这种强烈的经世致用观及其品质、意志、精神,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和后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已成为志士仁人相沿不已的座右铭,而且也成为鸦片战争以来近现代历史中屡为迭现的文化人格,这才是真正的“对人生对社会的厚爱”的“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本质所在”,而这种“文化人格”决非“晋宋人物”可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姜夔可以作为“文”、“艺”域内和审美意义上的“晋宋人物”的一个特殊范型,但决不足以代表他的主要人格,更不足以代表整个封建社会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
笔者不揣谫陋,就“晋宋人物”、“文化人物”及姜夔谈了以上浅见,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
一是姜夔其人其词,决非一味的晋宋之“狷”之“雅”,我们对他的研究,应结合其整个人生观的儒家底蕴尤其是整个文艺观的“中和”思想来认识,其词“在豪放、婉约之外别树清刚一帜”的缘由、影响,也应从此角度来把握。
二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包罗万象,如何把握住其主流及本质?陈寅恪先生曾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指出:“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注:黄宗羲:《弁玉吴君墓志铭》,《南雷文定后集》卷3,耕余楼本。 )先秦儒家的积极淑世精神在宋代大大弘扬,宋代士风之美一直为后世所崇尚、延续,这正是陈先生感叹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内涵所在,也正是钱先生所指出的“中国智识分子内在精神此一最高点”的意义所在。近年来,学术界已注意到从文化学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的发展规律并已取得可喜成就,但有时候似乎过于强调了庄、禅的影响,过分强调了士大夫自由人格、解放精神的比重,而相对忽略了几千年来儒家思想在封建士大夫文化人格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对此,我们应该从主流和支流、长期和短期、一般和个别等方面加以辨析,全面、深入地把握整个封建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和实质,从而正确认识文学史现象和发展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