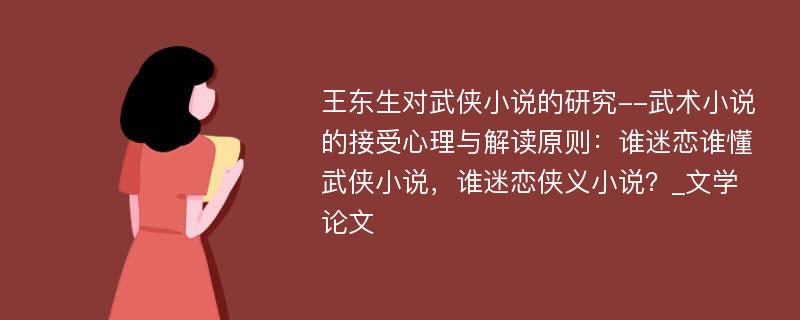
王东升武侠小说研究小辑 痴心谁解侠客行——武侠小说的接受心理和解读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侠小说论文,侠客论文,痴心论文,原则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成长壮大的民族艺术形式,表现出越来越具有其独立自足性的独特的文体特征和“基本叙事语法。”它一方面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注重夸张、想象、写意、传神的艺术精神,另一方面又融合了西方小说中优秀的叙述技巧和结构原则。不过总体说来,武侠小说仍然是民族化的、大众化的、古典化的。而“五四”以来,随着知识精英对西方文化的不断吸收,再加上政治方面的原因,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度被视为至高无上的艺术标准。这种心理定势不但使大陆武侠小说的创作出现断层,而且使评论界对武侠小说的接受产生了一定的解读障碍。陈平原先生作为武侠小说的著名研究者,也承认自己初读时“没读出门道”,后来陆续翻阅,“居然慢慢品出点味道来。”这说明对武侠小说的“解读密码”,同样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19世纪,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严厉地批评雨果的“杜撰”和“梦呓”,“是常识的敌人,并且把幻想刺激到病态的紧张的地步。”(《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第40页,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这种以一种理论原则去规范另一种文学体式的批评方法在今天也并不罕见。如果拿现实主义的期待视野来接受武侠小说,那么一句“荒诞不稽”就足以将它逐出文学园地。但是,随着武侠小说自身艺术品味的不断提高和读者哲学品味的日益多样化,人们已越来越不能无视其艺术成就,海内外许多学者和作家也开始给以充分的肯定和推重。即以当代武侠小说的大宗师金庸而论,冯其庸先生称之为曹雪芹之后汉文学作家的第一人;陈墨认为,“俗极而雅”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屡经证明的历史趋势,“雅俗共赏”是文学艺术的至高至大的境界。金庸显然达到了这一要求。柏杨指出:“金庸先生笔下的民族大义,澎湃如潮。”“像大仲马先生的《侠隐记》是完整的文学作品一样,它的结构和主题给你的冲击力,同等沉厚。”香港作家倪匡更直以“古今中外,空前绝后”八字称之,揄扬之情溢于言表。我们认为,要准确评价武侠小说,必须把它放在特定的文学类型的系统之中,根据武侠小说的文体特质建立批评标准,这样才能对武侠小说的艺术成就获得理性公允的认知。
一、武侠小说接受时的审美心理结构
上篇已经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对武侠文学的召唤和派生关系。那么,当中国开始步入现代社会,武侠小说中的古典文化意识形态则逐渐退隐到接受心理的深层或潜意识领域,一般不再以现实性的需要直接表现其功利目的。例如,“平不平”是古代武侠小说中一个历久不衰的母题,但是在现代社会,一方面社会现实的公正合理性有了很大提高,另一方面,人们即使遭遇不平,一般也知道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不会再幻想用侠客的三尺青锋剑来对抗手枪,轻功来追赶汽车。正因为此,警匪片以大大取代了武侠小说的这一现实性需要而大为走红。值得深思的是,正是由于武侠小说“现实救世功能”的消退,使它能够摆脱“报恩怨、平不平”的浅层次的功利性阅读,有可能转入对历史、文化和人性的深邃观照,从而建立起独立而超越于现实生活的审美世界。这正是武侠小说能够在当代社会取得空前成就而走向雅俗共赏的社会历史原因。布洛曾提出“审美距离说”,认为适当的时空距离和形式变异会使被观照物摆脱现实功利取向,呈现出美感特质来。武侠小说以武功技击和江湖争斗为特定的文体内容,不惊险奇绝自然不足以动人,本身就带有夸张而超现实的文学传统,而今天历史距离的巨大延展为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度。当代作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创造能力,穿越历史的迷雾,追寻文化的脉胳,半史半文,亦庄亦谐,时而是严肃认真或煞有介事的“考证”,更多的却是作家意想天开的“想当然耳。”对于武侠作家精心构筑的神奇、变幻的艺术世界,读者仍然应取中国传统的小说接受态度:“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在这“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接受过程中,巨大的审美效应即由此产生。
另一方面,当代武侠小说是从大众阅读中诞生壮大的通俗文学形式,一般以连载形式在报纸上发表,并起着帮助报纸扩大销路的作用。因此,武侠小说以呼应大众的接受心理期待为创作指向,表现出极大的娱乐性特质。从本质上讲,一切艺术都具有游戏娱乐的性质,都是在超脱了理性法则的“强迫”之后的心灵自由活动。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同样是在体验在严密格律的束缚下寻求自由表达的创造快感。只不过与“严肃文学”相比,武侠小说的游戏更具有普遍接受性、直观外现性和效果强化性罢了。在艺术类型中,童话、寓言、相声、喜剧都以强烈的游戏娱乐性而深受观众的欢迎,其上乘之作中均不乏堪称艺术经典的作品。那么,娱乐效应不但不会损害武侠小说的文学性,反而恰在于此为武侠小说提供了艺术品位的指向。当然,游戏和娱乐同样有粗俗消遣和高雅享受之分,有追求的作家,总是力图在作品中溶入充满人生大智慧的幽默,塑造出能够反映深广人性的艺术形象。
具体说来,武侠小说中的娱乐功能是通过沟通读者以下的接受心理而得以实现的:
(一)渲泄效应
在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工作也越来越具有高度组织性、严密分工性和单调重复性的特征,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和自由活动的渠道受到限制,在身心方面都格外容易感到疲劳。冷漠、抑郁、倦怠、刻板更成为现代工业化城市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构成“都市心态”的阴暗灰色部分。在工作之余,不少人喜欢读一些轻松、明快、具有刺激性和吸引力的文学作品,使疲劳的大脑在审美愉悦中得到松驰和解放,渲泄掉心中郁积的精神压力,使人格中的灵性、情感和创造想象力得到恢复和激活,并进而完善自我人格的塑造。1990年山东大学俗文学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表明,有63.7%—66.5%的读者是抱着“休息、娱乐、解闷”的阅读目的来接受俗文学的(《传奇百家》1991年第2期)。 武侠小说中紧张激烈的情节和尖税复杂的矛盾显然对吸引读者投入全神贯注的阅读尤其具有强烈的召唤性。倪匡谈到:“看《天龙八部》,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废寝忘食,甚至床头人相对如同陌路,宜掩卷沉思,以书作酒,可以大醉。”一位自称“终年困于课本和文卷的教书匠”,写信给梁羽生,说他的小说,“长期以来,都大力地帮助了我抗拒那稳秘的烦忧、焦灼,和填补那由于所在地域所造成的内心的空虚。”海外游子的故园之恋,家国之思,也可以在武侠小说的阅读中得到纾解和升华。
过去武侠小说中的矛盾冲突,大多以为父报仇、门派争斗、群雄夺宝等几种常见模式为主,正邪双方势不两立,壁垒分明,矛盾局限于二元对立的简单划分中。新派武侠小说更能反省到江湖仇杀、冤冤相报的盲目和无谓,对此能够给予悲悯和反讽的观照,如《天龙八部》中写蓬莱派和青城派的争斗。新派武侠小说组织矛盾的手法显示出新颖性和深度感,一方面使之复杂立体化,如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门派矛盾、家族矛盾交错纠结在一起,一方面又使各种社会矛盾和心理冲突积压在个人身上,使人物陷于一种势难两全的“夹缝处境。”如令狐冲,出身名门又与邪教教主之女相恋;杨过,曾深受郭靖的抚养教诲,但其父死于黄蓉;韦小宝,以天地会首领陈近南为师,又与康熙帝为友;张无忌,其父母一为武当弟子,一为魔教中人;乔峰生于契丹而养于北宋。这样,鲜明而激烈的外部矛盾内化了,作家的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尽情刻画人物面对重重矛盾时的内心厮杀,折射出多姿多彩的性格色泽。杨过几次要暗杀郭靖时的延宕和心灵斗争,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飞扬跳脱的少年逐渐走向沉稳凝重的过程,其文笔之严谨、细密令人赞叹。乔峰在聚贤庄上大战中原上百豪杰,更是武侠小说中前所未有的艺术构思。双方都是堂堂正正的侠义人物,只是拘于华夷之辨和误会、离间,终于使冲突无可避免。乔峰虽然数次力避杀伤,隐忍申辩,但势如骑虎,力难回天,终于与丐帮手足和中原豪杰饮酒绝交,直杀得尸横遍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能够象张丹枫一样“盈盈一笑,尽把恩仇了”的,究属天幸,更多的却是“胡汉恩仇,须倾英雄泪。”聚贤庄之战只是乔峰艰危处境的外化形式,读者须从刀剑丛中读出主人公的内心煎熬有甚于此。这样,在武侠小说中,外宇宙的冲突往往构成了双层对应格局,为读者接受提供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机制,使其既有充分的可读性,又有深刻精微的文化哲理内涵。这正是构成武侠小说能够雅俗共赏的一个原因。
(二)代入效应
接受心理学认为,在阅读过程中,接受者总是不自觉地把作品的形象和情境“转移”到自己的生活氛围中来,达到作品主人公与读者“自我”一体化的过程。“正是这种‘一体化’使读者能在感受与想象中进入作品的世界并在其中自由漫游。这就是艺术接受中的游戏因素。”(鲍列夫《美学》)
人类天生具有超越自我、发展自我的愿望,但是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又必然受到社会机制重重的束缚和压迫,被迫在人格面具等自我防御机制的保护下过着沉重而辛苦的生活。正如流行歌曲所真实抒写的:“你我皆凡人,长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作为人类超越意识的一种补偿,人们学会在哲学艺术中展开幻想的翅膀,飞越尘世的桎梏追寻那至善至美至刚至勇的崇高境界。武侠小说的超现实性为读者的心理代入提供了其他文学类型所难以取代的作用。过去,这种心理代入一般表现为对力量、速度、技击等人类潜能的发掘,如力可扛鼎的硬功、登萍渡水的轻功、百发百中的射术等,都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扩大。随着武功在实战中价值的消减和新派武侠小说中人物塑造的成熟,读过武侠小说而入山拜师的事情成为历史,读者的代入心理已经更集中在侠士们飘逸出尘的猎猎风范上。他们的侠骨义胆、铁血丹心,以及浪迹天涯的英雄孤独感,特立独行的主体人格,都成为当代读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人格典范,在满足读者“英雄梦”的同时,也为民众道德文化素质的提高,起着潜移默化的独到作用。
在武侠小说中,为了凸现英雄人物的伟岸人格,往往把人物置于最尖锐的矛盾、最困难的处境、最危险的局势之中,在巨大的外力压迫下让人物迸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辉。正如郭靖在评价武氏兄弟时所说:“小事情上是瞧不出的。一个人要面临大事,真正的品性才显得出来。”武侠小说的传奇性,非常便于为人物成长制造雅士培(Karl Jaspers)所说的“极限情境”(limit situations),这包括“死亡、受难、冲突、罪孽”等人生最大的困境。乔峰身背契丹身份,蒙受弑父母杀恩师的不明之冤,这是天下之大无处容身、世人皆欲杀的艰危处境;杨过与小龙女相恋,背负着淆乱师道、人人不耻的传统道德的重担,之后又断臂、受伤、中毒、诀别,这正是对一个人心胸魄力的严峻考验。当然,优秀的武侠小说并不把主人公塑造成十全十美的完人,他们的性格弱点构成了其坎坷命运的一部分,如乔峰的粗豪犷勇使其误伤阿朱,杨过的偏执激烈使他断臂致残。但这种性格缺陷更加深化了英雄人物的人性感和崇高性,更无愧于被称为“绝顶人物。”乔峰象高山上的岩石,粗糙、傲岸而气冲霄汉;杨过象秋天里的苍鹰,孤独、苍凉而脾睨青云。
(三)补偿效应
现实中的人生受到种种局限,一生的经历往往相当琐碎而平淡。因此在阅读中,人们往往希望跨越狭窄而熟悉的生活圈子,接触到一些陌生而有趣的奇人异事,奇山异水,奇风异俗,以满足自己的好奇、窥视等认知心理的需要。中国古代小说一向具有“志异”、“传奇”的文学传统,“不离于搜奇记逸”,以助谈资。这也正是武侠小说的艺术特色之一。优秀的武侠小说以广阔的社会斗争为侠士的活动场景,以侠士的浪迹天涯作为结构小说情节的线索,这就尤其有利于引导读者步入辽阔的三山五岳、四海八荒,接触到三教九流,百艺杂学。作家借情节发展之便,纵情挥洒,意兴遄飞,又为武侠小说构筑了一个文化的世界。梁羽生曾提出,做一个武侠作家应具有广博的知识格局,对宗教学、地理学、四裔学、历史学、医学等各种门类的学问都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浓重新鲜的文化意味的确是武侠小说吸引读者、提高艺术品位的一个重要手段。象《红楼梦》有百科全书之称一样,武侠小说以文化艺术气息化解势所难免的血腥杀气,纾缓过于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使读者由单纯的心理渲泄升华为高雅的文化享受,增强了武侠小说的艺术高雅性。如《笑傲江湖》中祖千秋论酒,梅庄四客论琴棋书画,《天龙八部》中段誉论茶花,虚竹解破珍珑棋局,都是令人目醉神迷的精彩段落。对于武侠小说中的文化知识,梁羽生主张采取一丝不苟的严谨科学的态度,他自称:“写天山,我不知翻阅了多少天山游记。就是从苏州入太湖,该从哪个码头下船,我都写得明明白白,一点不含糊。”值得商榷的是,我们认为,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虚实相生的文学类型,它的内容主干——武功就几乎全赖作家虚创,因此,其中的文化知识似乎也应该以美为终极目的,真只是美的辅助手段之一。只要不犯常识错误,有助于实现美的虚构应该是允许的。祖千秋在谈酒和杯的搭配时历数古诗为证,我们感到的是艺术与实用器皿的美的结合,至于其中的旷世珍品,我们猜测金庸大概也未尝一见吧。同样,珍珑棋局无人得见,但自填一眼的解法实在令人有天日重开之感,因为它深合“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古意。如果一定要金庸布局实战,只怕这位“棋坛闻人”也要敬谢不敏了。如果说,一般的现实性文学有高度的认知功能,(巴尔扎克是著名例子),那么,武侠小说只能称为“审美认知功能”,读者认知的终极指向仍在于文化知识的美的光辉。
(四)松驰效应
读者抱着消遣、娱乐、休息的接受目的来阅读武侠小说,与这种接受心理相适应,武侠小说的语言浅白、流畅,以短句式为主,复杂深邃的隐喻层往往由作者点出,作品中虽然也留下了许多“空白点”来吸引读者参予情节填充,但故事脉胳大致是清楚的。这些都构成了与“严肃文学”相区别的文体差异。此外,真正使读者在心理上高度松驰的还是武侠小说幽默风趣的语言格调。因为笑能够加速肺部的呼吸,使血液接收到更多的氧气,促进血液循环,完成人类所特有的解除疲劳,消减烦躁等自我保健功能。因而幽默也就构成了武侠小说的艺术特征之一。
武侠小说的语言的幽默机制比较复杂,我们试从悖谬与反讽两种常见的修辞格式进行讨论。
语境悖谬
罗兰·巴特曾提出,词汇通过有机的横组关系构成言语链。如果在语言的纵聚合轴上选取“对比替换语段”来故意进行错置,就会造成文学修饰上的陌生化和新奇感。简单的例子如下:
“众人来到灵州,为的就是要做附马,倘若不听公主吩咐,……只怕要做附牛,附羊也难。”
“你们就把我关到胡子白了,那位圣使姊姊也决不会再想到我这个老白脸”
“至于在下,则是英而不俊,一般的英气勃勃,却是丑陋异常,可称英丑。”
“附马”、“小白脸”、“英俊”都是人们常用的词汇,但在小说中被人物异想天开地改造成“驸牛”“老白脸”“英丑”,真是匪夷所思,揣想起来,又令人忍俊不禁。
语境悖谬是武侠小说中常见的喜剧因素,它通过对固定语言环境的颠覆和错置,改造了语言内涵与外延的稳定关系,形成艺术上的张力(tention)效果。比较隐蔽而复杂的例子如:
单正道:“然则咱们还是商议丐帮的大事,才是正经。”赵钱孙勃然怒道:“什么?丐帮的大事正经,我和小娟的事便不正经么?”
前一个“正经”是“当务之急”的意思,后一个“不正经”却是“男女私情不严肃”的意思。字面虽同,含义迥异。赵钱孙混为一谈,并为之勃然,其痴情、执拗与欠通世务的喜剧性格便跃然纸上了。
再如包不同嘲讽地寻问星宿派弟子阿谀拍马的功夫,那人居然受之不疑,坦然传授道:
“最重要的秘诀,自然是将师父奉如神明,他老人家便放一个屁……
“包不同抢着说:‘当然也是香的。更须大声呼吸,衷心赞颂……’那人道:‘你这话大处甚是,小处略有缺陷,不是“大声呼吸”,而是“大声吸,小声呼”。’包不同道:‘对对,大仙指点得是,倘若大声呼气,不免似嫌师父之屁……这个并不太香’。”
“那人点头道:‘不错,你天资很好,倘若投入门下,该有相当造诣,只可惜误入歧途,进了旁门左道的门下……本门的功夫虽然千变万化,但基本功夫,也不繁复,只须牢记“抹杀良心”四字,大致也差不多了’。”
包不同的“大声呼吸”,本来就是把“呼吸”看成一个独立词,用的是“尽力去闻”的意思,这里有夸张和揶揄的内涵,但谁能想到,星宿派弟子不但不以为忤,反而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洞幽烛微地把呼吸这个组合词分割成“大声吸,小声呼”,其阿谀逢迎的技巧真称得上登峰造极了。尤其可笑的是,他们星宿派人性丧尽,臭名昭著,居然也以名门正派自居,感叹包不同“误入歧途,进了旁门左道的门下,”又慨然以“抹杀良心”与包不同共勉,其语言形式的端庄严肃与内容的无耻构成了双重悖谬。同时,包不同的暗含嘲讽与星宿派弟子的自我反讽营造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温特斯有一个术语叫“浪漫反讽”(romantic irony),指把反讽相反的两极距离拉得很长,“慷慨陈词,然后取消颠覆之。”武侠小说中有不少反讽的好例。如《射雕英雄传》中的裘千丈,武功奇低却又喜欢大言炎炎,招摇撞骗;居心叵测却又道貌岸然。他一本正经地宣称:“眼下有件大事,有关天下苍生气运,我若是贪图安逸,不出来登高一呼,免不得万民遭劫,生灵涂炭。”但他卖了数次关子之后,说出来的主意竟然不值一哂。原来他要联络江南豪杰,响应金兵,好使宋朝不战而降。这样才“不枉了咱们一副好身手,不枉了‘侠义’两字。”悖谬与反讽相结合,共同营造了武侠小说中绝妙而异彩纷呈的喜剧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