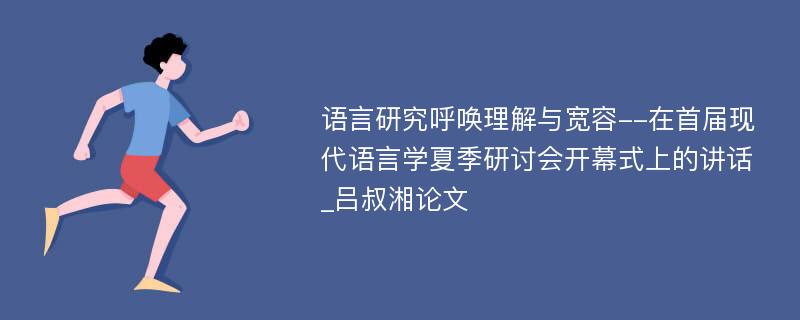
语言研究呼唤理解和宽容——在首届现代语言学暑期研讨班开幕式上的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讨班论文,语言学论文,开幕式论文,暑期论文,宽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前两届中国语言学会年会的闭幕词中,我曾经两次谈到过一个问题:国内的语言学研究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我们回想一下,1938年到1940年初,语言学界以陈望道、方光焘先生为首,发起了一场“中国文法革新大讨论”。在这个讨论会上,陈望道、方光焘先生讨论问题的水平是与当时的国际水平相当的。我们知道,从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到1933年美国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的出版,索绪尔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以及各种语言学流派的崛起,也就是在二三十年代。但是,陈望道先生在1938年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经对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非常熟悉。当然,他的翻译名词跟现在不太一样,但是已经非常清楚明白。方光焘先生作为中国第一个传播索绪尔思想的人,对结构主义也十分了解。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王力先生和吕叔湘先生接受的是我称之为“习惯语法”一派的理论,这一派以H.Sweet等为代表,他们的理论著作也是30年代出版的。但是,从吕叔湘先生在1942年和王力先生在1943~1946年期间出版的书中可以看出,二位先生在40年代初的很短一段时间里,就把这些理论完全中国化了。很多人现在已看不出这是外国的东西,他们当时的理论水平是与世界接轨的。
但是到了50年代,我们的词类大讨论、句子问题的大讨论,以现在的理论眼光来看是倒退了,倒退到了传统语法的阶段。
今年是1996年,我们与国外的差距有多大呢?整整40年。8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在中国达到了鼎盛阶段,取得了主流派的地位。但是美国在1957年以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代之而起的两大派是形式学派和功能学派。形式学派以Chomsky为代表。现在赞同Chomsky哲学观点的人不多,诸如“先天就有了语言机制”等,有许多人不同意。但是现代语言学家中却很少有人用Chomsky的方法,特别是搞计算机的,非用不可。功能学派是在60年代兴起的,国内比较熟悉的代表人物是Halliday,还有一个我认为也很重要的人物Simon Dick。他们很早就提出,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应该主要研究它的交际功能,并且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来进行分析。Simon Dick在70年代出版的书中明确提出了Syntax Semantics和Pragmatics。到了80年代末,我们逐步引进了这些观点。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中国化,并且多数人还不了解,原因何在呢?
一个原因是,从50年代到1978年这段时期内,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国外的资料。另外一个原因是50年代以后的一些人学的都是俄语,有了先进理论的书也不容易看懂。而当时在国内,结构主义正在逐步地中国化,所以大家就没有注意这些问题。那么,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完全吸收这些理论呢?我认为,功能语法大概比较容易引进,因为它易懂。形式学派则不大好懂。坦白地说,我教研究生时就讲,我们一起来读《句法结构》,因为我也不太懂。这本书并不是很难读,但我们不太明白书中的一些说法。为什么要说S能够改写成为NP+VP呢?这不就是传统语法的主语加谓语吗?后来我有机会参加了一个国家级的研究工作,里面有不少计算机专家。我和他们一起工作了两年多,慢慢懂得了原来Chomsky的很多意思,再看这本书就比较容易了。以前我琢磨不透其中的原因。我在中学时学英语的被动句,老师讲,V+to be+P.P(动词过去分词)+by+主动者,这就是被动式。这很好懂。到了《句法结构》这本书里,情况就复杂了,要看规则第十八,先运用哪一条规则,然后再运用哪一条规则,把我都弄混了。又如一个助动词加上一个主要动词,这也很简单,但书中又把它复杂化了,成为一条规则。所以我们文科出身的人学生成语法,有相当的难度。但是搞计算机的人学习它就非常容易,一看就懂。所以我想,生成语法在国内之所以迟迟不能运用到汉语上来,是因为我们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们的文科学生从来不学理科方面的知识。而要学习生成语法,你必须要学一点高等数学,学一点数理逻辑,但我们都没学过!所以我们的思路就不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展望。这几年,国内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北京大学沈阳写的《汉语中的空语类》。这里基本上用的是深层语法的思路。沈阳原来在上海的华东师大,那时就研究深层语法。因为后来他到了北大,书中当然也掺杂了不少结构主义的东西。另一本是张伯江和方梅的《汉语功能语法》。可以看出,功能语法已经要开始中国化了!另外,上海一些青年人,如XY沙龙,几次到北京来宣传,说他们要搞功能语法。我希望他们能早点出书,但是到现在还没出。他们的宣传很厉害,他们宣传说要搞理论,要搞演绎,等等。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些最早产生于我们语言学界的矛盾和冲突,就是吕叔湘先生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讲的那一段钱与钱串子的话。他说,最好是既有钱,又有能把钱一串串穿起来的钱串子。吕先生说,如果两者不可得兼,我情愿要钱,不要钱串子。这就是说,如果又有材料,又有理论,最好;如果二者不能得兼,宁愿要材料,不要空头理论。这种观点有的人赞成,青年人大多数反对。我在此对其正确与否不加评论。我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情况会不一样。西方的语言研究从古希腊算起已有两千多年。欧洲新兴的一些民族国家,以英国来讲,也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法国从17世纪以后,也有三百来年的历史。他们对自己的语言事实的描写,我认为不能说全部清楚,但基本明确。有一些句法的分析没有分歧意见。他们不会去吵架,不会出现我说这是主语,他说这是宾语的情况。当然,他们有形态,这是一个好处。不过英语形态也不多,分析起来也有困难,但是他们研究得比较透彻,时间也比较长。
我们研究了多长时间?从1898年《马氏文通》算起,到现在98年。这98年还要打折扣,至少从1957年皮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20年要扣掉。我们干什么去了?不是在下乡、四清、劳动改造、搞运动么?我们哪有时间来搞研究?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这些人虽然在解放以前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解放以后又写出了多少东西?没多少。所以我们研究语言学的历史比较短;一些语言事实弄不清楚。因此,老一辈语言学家强调描写,强调收集材料,有他们的道理。那么年青人的反对有没有道理呢?也有道理。如果不讲理论,试问天下有没有脱离理论的研究?不讲理论即讲传统,还是按照传统的理论来收集材料;如果没有理论指导,连材料都没法收集。
年轻一代想要引进新的东西,现在国外流行的无非是形式学派和功能学派。我估计到21世纪,我们国家的语言学界、语法学界要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现在已经有点苗头了。但是非常困难,比过去困难得多。原因就在于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大多数人不能直接阅读西方文献。我们派出去很多外语系的人,他们能阅读,但对汉语不熟悉,不能跟汉语结合起来,搞中国化。所以这需要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了。
第二个矛盾就是不同的学派之间有门户之见。大家还记得,黎锦熙先生的传统语法在50年代就受了批判,以后就很少有人提起了。结构主义渐渐成为主流学派。现在又有功能学派、生成语法等等。新的学派和原来的学派之间就有矛盾。这个矛盾如果是因为学派不同而产生的,就容易解决。我想我们中国语言学界的派性还不会那么厉害,以至于这一派的文章就不能在那一派的刊物上发表。我看这不是派性的问题,而是那一派认为这一派的观点根本就不正确。这个问题就更麻烦。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思维已经有了一定的模式,那么他就会认为他看到的新东西都是不对的。
另外,青年人写文章当然没有老一辈那么严谨。一篇文章思路很好,里边有两个观点的结论也很好,但是有三处材料错误,引文不是第一手的材料,这是中国传统绝对不允许的。这篇文章就完了。大家千万不要忘了,我们中国语言学界有乾嘉学派的影子。一篇文章,没有什么新观点,但材料非常严谨,没有错误,可以发;有一个错,就不行。高名凯先生就有过这样的教训。高先生是学哲学的,思想非常活跃,有很多理论见解。他写的一些书在日本很受重视,但在国内不受重视。什么原因?因为高先生是才子派,他写文章从不看第二遍,不查出处,只凭记忆。乾嘉学派的人一看,连引文都不对,其他都不足道也。长期以来,我国语言学界就是这样一种学风。
还有,北京是“京派”,上海是“海派”。所谓“京派”、“海派”没有褒贬的含义。当然,北京人可以说京派是好的,海派不好;上海人可以说海派是好的,京派不好。其实他们各有特点。京派比较严谨,严谨的同时带来保守;海派比较活泼,但严谨不足。各有所长。如果大家仔细看文章,就会发现:北方的杂志很少发表南方人的文章;南方杂志,象《语文战线》,有一段时间主要发表南方人的文章,很少发表北方人的文章。这都不是简单的派别排斥,而是因为从自己的观点来看,对方就是不对。这就更麻烦了。所以我认为,百花齐放以后,会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学术上会出现矛盾。因此这几年来我就一直在各种会议上讲宽容。
理解和宽容是什么意思?宽容就是,对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的意见应该宽容,不要认为自己是惟一正确的,别人都是错误的。1981年,吕叔湘先生在哈尔滨召开的教学语法讨论会的闭幕式上的讲话给我印象很深。他先讲,1981年以前,汉语语法书出了一百多本,但大部分都是抄来抄去,没什么意思;后来又讲,现在有人认为自己是惟一科学的,别人都是错误的。吕先生说,如果每个人都说自己是惟一科学的,那么任何人都不会是惟一。因此总的来讲,吕先生还是比较开明的。如果语言学界不能齐心协力把我们的中国语言学搞好,而争于矛盾,我们就无法进步。现在这些矛盾时而紧张时而缓和。将来如果形式学派、功能学派大量运用在汉语的研究上,肯定会得出很多与现在主要流行的结构主义不一致的结论,这样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争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在美国,大家都是公开批评别派的观点。结构主义刚刚兴起时,C.C.Fries就写了文章:什么叫传统语法?传统语法就是过去江湖郎中给人看病时放血,是化学没有出现以前的炼金术。批评得很尖锐。后来Chomsky上来了,说结构主义的全部研究超不出传统语法的范围,并且有很多传统语法可以解决的问题结构主义并没有解决。他们的相互指责就象我们在50年代的大批判那样厉害,当然他们没有用我们的“扣帽子”的方法。我们过去是动不动就用大批判开路,这种情况估计以后会少一些。可是我发现,西方语法学界好像也都是大批判开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Henry Sweet,Jaspson,美国的Kerm和后来的H.E.Parmer这一代上来的时候,批判传统语法批得也很厉害,叫它“规定语法”、“学校语法”。Henry Sweet举例说,传统语法教大家要用“It is I.”,而人们一直是用“It is me.”;传统语法又说一句话的末尾不能用介词,但许多传统语法的研究者自己说话的时候就在句尾用介词。总之,批得一塌糊涂,一直到把传统语法彻底批倒。我们知道,传统语法是两千年前古希腊人搞的,他们已经死了,没有发言权,怎么能和Henry Sweet这样的教授争论呢?而现在维护传统语法的人大多是中学教师,中学教师又怎么辩得过大学教授呢?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把传统语法批倒了。实际上传统语法规范错了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对的。50年代吕叔湘先生写的《语法修辞讲话》上有两句话,被大家抓住不放。其一,“打扫卫生”不好,应该说“打扫房间”;其二,“恢复疲劳”是错误的,应该说“恢复健康”。可是吕先生在《语法修辞讲话》里讲了上百条,不合适的也只有两条。现在国外学校教学,包括TOEFL考试,还是传统语法,因为它是经过长期考验的。这并不妨碍用一种新的方法对语言学进行深入的研究。语言学界也好,其他学术界也好,一个新的学派出来的时候,往往采取大批判开路,我是不大赞成这样做的。特别是在中国,最好再也不要搞这个。
现在我要讲中国的原因。由于政治上的大批判,使我们感觉到如果一个人在学术上受批判,这个人也没有前途了,所以人人自危。50年代的大批判,很抱歉我也参加了,批过高先生,还批过古文字学家唐兰,因为他不大同意文字改革。如果是单纯的学术批评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在一些学者头脑中存在着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对我国的语言研究是无益的。它是说,我们的科学研究都是研究客观规律,因此只有一种观点是符合客观的,凡是不符合客观的都是谬误。我认为,如果这样一种思维定式继续保留下去,我们就没法展开学术讨论。
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研究的的确是客观规律,但每个人的结论是主观的。可能存在一个客观规律,但是任何人的作品都不能代表客观。可是我们过去有这种风气,认为我们几人绝对正确,别人绝对荒谬。这种提法非常伤感情。就我自己来说,认识这个问题也有一个过程,我以前也认为只有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其他都是错误的。后来我了解到,现在西方有很多“模型”理论,就是对一个客观事物,我们主观搞一个模型,尽量接近它,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接近,没有绝对正确和绝对错误的区别。
另外我认为,人是客观的,可以从心理学、生物学、人类学角度去研究,也可以从思维、意识形态角度去研究,怎么能说只有一种研究是惟一正确的,其他都是错误的呢?同样一个事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由于不同的目的、使用不同的方法去加以研究。为什么只能有一种研究是对的,别的就都不行呢?可见我们是僵化的,这种思维并不是辩证的,而是形而上学。如果只允许有一种角度的研究,那么医生把人体各部分拆开来研究就是错误的,而一定要从人是创造劳动工具的、有社会组织……这方面研究吗?反过来,医生也不能说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研究的人是错误的,这是不同的角度。
研究语法也是这样,可以从形式上去研究,也可以从跟意义结合方面去研究,还可以从语用上去研究;写一本书可以是为了计算机用的,也可以是给小学生用的,都可以,不一定只能有一种角度。至于我们意见有分歧,具体问题有争论,也很难说一方对了,另一方就一定错。可能是两人都对,角度不同;也可能两人都错;可能一个对,一个错;也可能一个对了百分之八十,一个对了百分之五十。我们应该承认科学是无止境的,是逐步接近真理的,怎么能说今天就到了顶峰呢?别的意见怎么就都不允许发表了呢?这种思维方式加上大批判的后遗症使得我们国家很难开展自由的学术讨论。所以开会时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场面:报告之后问意见的时候,很长时间无人应声。有人可能有不同意见,但不敢说,特别是年轻一点的人,老生先讲了话,他就更不敢表示异议。我勉强也算得上老,过七十了,但是我没有这个思想,我认为学术上应该是平等的。当然我认为态度还是要好的,一次在语言学院开会,广东有位老师谈了斯大林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问题,我的一个学生“噌”地站起来:你还谈这个,这个早就过时啦!这种态度就不太好。我对他讲,你可以告诉这位老师,斯大林写书时,他也不是个语言学家,他是征求了苏联很多语言学家的意见,这些意见一般都是二三十年代的理论,现在我们有更新的东西应该注意。这才是探讨问题的正确态度。所以我认为应该注意态度,咱们中国有中国的人情,这一点与外国不同。
到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我们的观点将会是各种各样的。其中有的观点可能最终证明是错误的,那也没关系,应该鼓励他发表,至少可以让我们考虑很多问题。我们有的青年人发表了比较过激的言论,比如说,有人讲,中国过去的语言学通通是抄外国的,从我这儿开始才是中国的。没关系,让他去说。为什么?这有个好处,至少让我们头脑清醒一下,认识到我们现在语言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还不能满足客观需要。如果你的确拿出来一个大家都信服的观点,就不会有这样的人来发表这样的意见。从这样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能促使我们加深自己的研究。
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我提倡理解和宽容。要互相理解,青年人要理解老一辈的学者。因为他在他那个年代,他那种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就;现在年纪大了,可能没有时间来看新东西了,那么就在他那个范围内继续搞,有什么不可以呢?另外,有一些观点我认为永远是正确的。他们有很多经验值得年轻人学习。严谨有什么不好?写文章难道就是信手拈来、随意发挥吗?引别人的话应该去查一查原文,如果把孟子引成孔子,把孔子引成墨子,这当然不会好。从老一辈角度来说,不要就盯住青年人这一点不放。他是引错了,可是他整篇文章没有错,观点应该支持。有一段时间,张志公先生、我和另外几位先生搞过一个丛刊——《语文论坛》,出了4辑。我在前言中说,不论什么观点只要有一得之见,能够自圆其说,都可以发表,并且编辑部对文章的内容不负任何责任。编辑部发了你的文章并不等于同意了你的观点。在一个论辑里面可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争得越激烈,问题越清楚。清一色并不好,在学术界搞大一统是个危机。
另外,我认为老年人对青年人应该宽容。我一再讲,青年人有犯错误的权利,因为他是年轻人。谁在年轻的时候能不犯错误,能写出来正确无误的文章?为什么今天就要对年轻人要求得那么严格呢?说实话,我对我自己的学生要求也很严,对别人就宽容一点。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要严谨以律己,宽容以待人。对自己写的文章、搞的工作必须严谨,但对别人应该宽容,特别是要支持青年人发表文章,帮助他们修改。理解应该是相互的。老年人和青年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年龄不同,思路也不同。不要指责老先生都是老顽固,是“学霸”,他们都是为了对学术负责。他如果认为你这篇文章不对,自有他的道理,你就再修改修改。老一辈的学者绝不会因为你是某某某就故意不发你的文章。有人在报上这样讲,这完全是造谣。相信我们语言学界老一辈学者的道德品行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老年人有些看法也许会和青年人不一样,有可能青年人认为非常得意的文章,老年人从他的角度看,认为没有价值。这一点应该理解。
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的一些学生,说现在我们中国人净搞材料,让外国人去出理论。我就问,你看到哪个外国学者是拿了中国人发表的材料而成为语言理论家的?他举出桥本。我说,桥本调查过中国很多方言,他不是完全从《方言》杂志抄去的,他自己搞了很多研究。另外,桥本提出的理论也是一家之言,也不见得就是绝对真理。我说,中国人也并不是没有理论,但中国老一辈的学者都喜欢把自己的理论放在自己的材料里,就看你有没有眼光看出来。这可能是一种作风,和西方的作风完全不同。其实他的材料的罗列、排比,包括每一个例句的选择,都有他的理论观点,他只是没有说。吕叔湘先生在1942年发表的《中国文法要略》中就提出“动词中心观”,句子中动词是中心,其他成分都是它的补语;又指出动词有方向问题,有些动词是一个方向的,有些是两个方向的,有些是三个方向的。后来法国的Teneye也提出了“动词中心论”,而吕叔湘先生早在1942年就已阐述得相当完整。我曾经跟吕叔湘先生本人谈,他说,可惜,我这人就是不太重视搞理论。这是吕先生的谦虚。他认为理论就是能够指导实践的东西,如果不能指导实践,就不是理论。这代表了大多数老一辈学者的观点。而一些年轻学者认为,只要构成一个体系,出一套新的观点和术语,就能形成理论,不一定要举具体例子。
我们与海外学者也有一些矛盾的看法。比如国内有些人认为,国外现在的语言学是用三个例子写上六百页书,而这个例子可能还有问题。我们从乾嘉学派的角度是绝对不能认同这种作法的。我们要求三百个例子写一百页书,并且句句有来历。我觉得这两种作法都有道理,因为方法不同。到结构主义为止,我们用的都是归纳法,是从大量材料中归纳出来一些结论。从深层语法开始,逐渐使用了演泽法。演绎是根据前人几百年、上千年的研究成果来进行演绎。任何演绎都是建立在一个初步归纳的基础上的,凭空的演绎是不可能的。S改写成为NP+VP,没有传统的基础从何而来?Chomsky在支配和约束理论中说,我以前凭借的就是传统语法的东西。这里有一个过程。我们的科学研究到了一定程度,一些基本的东西都弄清楚了,就应该进行演绎。归纳和演绎永远是科学方法的两种。很难说孰高孰低。现在一些年轻人提倡演绎,老先生们就不大看得惯。我认为应该慢慢看惯。只要他演绎得对,演绎得有道理,就应该提倡。双方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做到严谨于律己,宽容以待人。
另外,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性的办法。比如,即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也不一定要指名道姓地公开反驳你。我可以根据我的材料来写文章,针对性地发表不同意见。在国外就用不着这样小心谨慎,但是在国内还需要。我举个例子。我在《中国语文》发表过一篇《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发表以后,有些学者对其中的几个语气词,如“呢”的看法很不一致。我认为“呢”不是个疑问词,它是表示强调。如“他们在开会呢!”这个“呢”根本没有任何疑问意思。如果它表示疑问,那么任何句子后面加“呢”都会变成疑问句。陆俭明不同意,要写文章同我探讨。朱先生就对他说,你只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要提名道姓。于是陆俭明就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是非问句加“呢”》的文章,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不是是非问句的句子加上一个“呢”就变成了是非问句。我后来在《语文建设》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也没有指名道姓。我做了语音实验,句子加“呢”以后语调不一样,用疑问语调就是问句,用非疑问语调就不是问句。下一步我就等着他再发表文章了。这些事情我们彼此都知道,我觉得这样不伤感情。如果别人有不一样的作法,也不必去计较,也不必写文章反驳。不一定对每个学术问题都要写文章加以反驳。我们都很熟悉的吕冀平,在《中国语文》上指名点姓地批评我,我就没有反驳。吕冀平说,语言学家就是要当立法者,有人就不主张语言学家当立法者,如胡某人。又引了我的一段文章。我说没关系,批就批吧,反正我到现在也不同意。语言学家怎么当立法者?对此,吕冀平有他的观点:如果不是这样,要语言学家干什么?语文规范化由谁来做?其实吕叔湘先生早在1955年就与罗常培先生合写文章,提出要“因势利导”。现在国家语委立了很多法,我看就很成问题。我在语委大会上也说过,这根本行不通。长期以来,我们有些反驳别人的话说得非常刻薄,这肯定是伤人的。比如说别人的分析是莫名其妙。怎么叫莫名其妙?我希望以后不要出现这种现象。作为我们年纪大些的特别要宽容。也希望《中国语文》能够顺应新形势的发展,更开放,更宽容。
(熊宁宁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