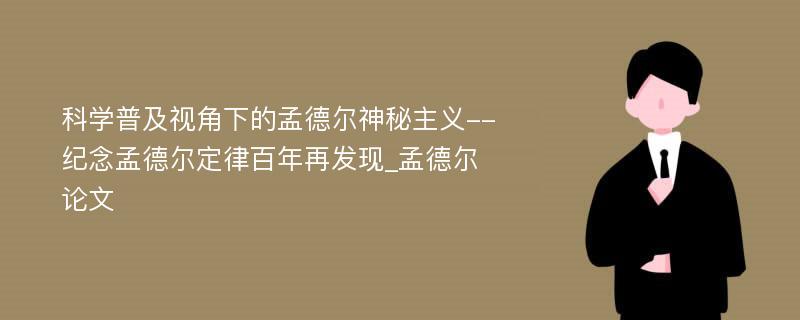
从科学普及的角度看“孟德尔之谜”——纪念孟德尔定律重新发现10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德尔论文,科学普及论文,之谜论文,角度看论文,定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5.21=41
文献标识码:A
似乎可以认为,生物学史研究在当今科学史的研究中正在走向主导地位。个中原因可能就象生命现象本身一样,是极为复杂的,不仅仅是因为生物学研究本身在今天的繁荣,更可能是因为生物学史自身的扑朔迷离。孟德尔定律之被忽视就是其扑朔迷离的典型表现。1865年,孟德尔神甫发现了后来被称做“孟德尔定律”的两条遗传学规律[1],然而这一发现竟被忽视整整35年,直到1900年被三位植物学家重新发现。这个历史现象被学术界称为“孟德尔之谜”(Mendelian puzzle)。
由于孟德尔定律之被重新发现,1900年成为遗传学史正式开端的一年,至今恰好100年。100年来,科学史家对“孟德尔之谜”作出了种种探讨,直到今年早些时候,生物学史家桑德勒(I.Sandler)还在Genetics上撰文,从科学概念之历史意义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2]。
本文在桑德勒夫妇更早时候(1985年)一篇长文[3]的基础上,将100年来科学史家对孟德尔问题的探讨区分为三个方面:社会学的方面、方法论的方面和思想史的方面。我们也将在这里分析这三个方面探讨的短长,并从科学普及的角度出发,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同时,我们亦将以此方式纪念孟德尔定律重新发现100年。
1
社会学原因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观点是布隆年刊之不为人知,后来的科学家和史学家对这个观点提出了多种质疑[3]。首先,布隆自然科学学会与欧洲和美国的115个大学和更多的科学院、科学协会有互换出版物的传统(在孟德尔定律重新发现以后,热心鼓吹孟德尔学说的贝特森(W.Bateson)就是在英国皇家学会找到了当年的布隆学刊的[3]),事实上,在19世纪中叶,通讯、学会年刊是交换科研成果的主要方式。其次,孟德尔的论文也曾被多次引用,如德国植物学家福克(W.O.Foecke)就在其《植物杂种》(1881年)中提到过15次,而俄国植物学家施马里高践(J.F.Schmalhausen)更是给予了孟德尔定律以较高的评价[3]。
社会学原因的第二个观点是,孟德尔“缺乏恰当的科学身份”,他作为神职人员,不是一位职业的生物学家[3]。支持这一观点的事实是,孟德尔与耐格里(K.W.von Naegeli)长达7年的通信始终没有引起耐格里的注意[4]。桑德勒夫妇认为这并不是孟德尔之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因为孟德尔的论文能够为职业植物学家引用,本身就说明其能够为专业植物学家接受。1869年,第一位引用孟德尔结果的专业植物学家霍夫曼(H.Hoffmann)甚至也做了豌豆杂交实验[3]。事实上,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在孟德尔之前或同时代的科学研究中,那些开创性工作常常来自非专业人士,哥白尼就不是专业的天文学家,达尔文也不是职业的博物学家。
社会学原因的第三个观点是,自1859年《物种起源》发表以后,当时正处于所谓的“达尔文时代”,孟德尔学说的光辉被遮住了[4]。这种看法明显地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遗传学割裂开来了。事实上,达尔文本人十分关注遗传问题,可以说,自然选择的中心问题就是遗传学问题,而他对自己的泛生论遗传学以及前人的获得性遗传学一开始并不满意,1869年,他在给虎克(J.D.Hooker)的信中流露出了这种情绪[3]。应该说,遗传学的突破恰恰是达尔文主义者所期盼的事情。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杂交方法在当时不受重视[3];第二,选择豌豆偏离了当时共同体的选材模式[3-4];第三,数学统计方法之运用于遗传学超出了当时接受的程度[3-4]。反驳第一个观点的证据是,在孟德尔之前,杂交方法在农业生产和园艺工作中正得到广泛的应用[3],事实上,孟德尔之研究豌豆杂交的原始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新的颜色变异对于观赏植物进行人工受精的经验”[4],为此,他的研究还被德国农业协会所引用[3];另外,当时的进化论研究也十分关注杂交的结果,达尔文的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1868)以及《兰科植物的授粉》(1862)等都是对杂交关注的成果[4]。
支持方法论原因第二个观点的理由是,在孟德尔与耐格里的通信中,耐格里曾建议孟德尔用山柳菊属植物进行杂交实验,因为耐格里当时就在使用该属植物做杂交实验[4]。然而,这个原因是极为勉强的,罗伯茨(H.F.Roberts)在《孟德尔之前的植物杂交》一书中详细地记录了有史以来的各种植物杂交实验[3],发现当时并不存在一种模式植物,因为当时的杂交都是出于应用的目的,而重复做同一种杂交,在应用上是没有意义的。再者,后来的发展恰恰证明,孟德尔的选材才是十分科学的,而耐格里的选材却是不恰当的。
方法论原因的第三个观点是主要的观点,桑德勒夫妇运用了较多的史实来反驳这一观点。这些史实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首先,用数学方法研究植物学,有其较长的历史,早在1829年9月,德国的两位植物学家辛普(C.Schimper)和布劳恩(A.Braun)就试图运用斐波拉契(Fibonacci)数列来研究叶的发生与形成;事实上,19世纪早期,对数学精神的推崇是哲学界和科学界一种普遍的情绪,居维叶(G.Cuvier)在1808年就赞赏用数学与物理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古生物学[3],歌德也曾主张用理想的数学关系来描述物种的亲缘关系,而不管该物种实际上是否存在。其次,即使在遗传学研究中,孟德尔也不是首先使用统计学方法的,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F.Galton)就认为,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数学方法尤其是统计学方法就可以运用于遗传[3],事实上,他后来就提出了所谓“祖先遗传律”来统计地分析融合遗传,从而开创了“生物统计学派”[4]。
从思想史方面的寻找原因的论者认为,科学共同体由于受当时科学思想的桎梏而不能接受或关注孟德尔定律。这里也有三个理由:第一,孟德尔本人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意义,即他并不知道自己发现的就是遗传学理论,或者说,孟德尔本人并不是孟德尔主义者[5];第二,当时流行的是融合遗传理论,与孟德尔的颗粒性遗传观念是不相容的[4];第三,当时的遗传观念有问题[3]。
坚持思想史原因第一种论点的人认为,孟德尔所使用的遗传概念乃是19世纪后期那种进化、发育与遗传不分的思辨性概念,即是heredity,而不是genetic;有人认为,孟德尔以为自己发现的仅仅是某个物种的杂交规律[3],而不是普遍的遗传定律;有论者甚至宣称,是早期遗传学家制造了所谓的“孟德尔神话(Mendel's myth)”[5]。如果真如这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孟德尔就不会以“植物杂交的试验”为题发表其论文,也不会写信给耐格里尤其是达尔文[6],更不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去做山柳菊属的实验了[4]。孟德尔在1867年给耐格里的信中写道:“我知道,我所取得的结果很难同我们当代的科学知识相容……我曾试图启发人们作一些对照试验,为此在自然科学家地区性学会会议上谈到了豌豆试验。[1]”可见,孟德尔看到了自己理论的革命性,也正是为了引起注意和得到普遍的重复才公布其结果的。
至于第二种观点,反驳的事实也是相当明显的。首先,当时虽然以融合遗传观念为主流,但其他遗传观点仍然是可以提出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的,如魏斯曼(A.Weismann,1882)的种质论、德弗里斯遗传单位理论等,事实上,19世纪末的遗传理论处于百家争鸣状态[7]。其次,当时的遗传理论中也不乏颗粒性遗传观念,如魏斯曼的生源体(biopnore)与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就非常相似[7]。
第三种观点是由桑德勒夫妇提出来的,这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恰好相反。他们认为孟德尔已经将发育与遗传作出了区分,即不再关注发育的中间过程,而只关注发育的结果即遗传性状。问题在于,当时的科学共同体仍然没有摆脱思辨观念的影响,仍然认为对遗传的了解必须以对发育的彻底了解为前提,因而忽视了孟德尔定律[3](其实,摩尔根早在1926年的《基因论》中就已经指出了这种差别[8])。桑德勒夫人最近的论文实际上否定了这种看法,因为孟德尔在论文中几乎没有使用“遗传”的概念,而大量地使用“发育”概念,孟德尔想发现的恰恰是发育规律[1-2]。
2
在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之前,我们必须确定孟德尔之被忽视的关键环节,并且同时要确定一种方法论准则即这种忽视的时代性基础,也就是说,应该将其同与之同等重要的同时代的科学成就之所以得到承认的原因作出比较。
在考察关键环节时,我们可以将其得到承认的环节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传播环节,第二步是在传播之后对其内容的认同。我们首先从内容认同上来分析,我们可以将认同方式区分为正认同即赞同和负认同即反对。虽然孟德尔的结果为人所引用,但并未当作主要论据加以引用,而且这种引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赞同,另外,几乎没有任何人对其结果或观点表示过公开的反对,也就是说,它没有得到负认同。由此可以看出,孟德尔学说及其内容没有得到广泛认同,也就是说,孟德尔学说的承认问题根本就没有达到第二个环节。由于方法论与科学思想必然地涉及到研究的内容,而它的研究内容并未得到公开的反对,所以方法论与科学思想方面的理由均不能成为孟德尔之被忽视的原因;反过来说,假如孟德尔定律不被看重真是由于方法论或科学思想的原因,那么它就应该受到哪怕是小范围内的公开批评与反对。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孟德尔之被忽视的关键环节和真正原因是在传播环节上。
科学成就的传播方式必然涉及到科学成就的公布方式,也就必然涉及到科学研究的规范。19世纪的科学规范不同于今天的科学,尤其是生物学,那时,适当的思辨与以书籍的方式出版成果并因此得以传播乃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当时的原科学或前科学气氛仍然浓厚,专业的科学研究与大众化的科学普及尚未完全分离开来。科学哲学家库恩对此有精辟的论述:“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再也不会象以前那样,体现在写给那些对此有兴趣人们的书中了,象富兰克林的《关于电的……实验》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反,通常只是写一篇简要的文章给同行看……”“今天的……科学家要写这样一本书,很可能会发现他在专业方面的声誉不是得到提高,而是受到损害。只有在各门科学更早的前规范发展阶段上,这样的书才可以同在其他创造性领域中那样,仍然保持与专业成就的关系。”[9]库恩在进一步考察了各门科学这种成就公布形式的改变之后,得出结论,生命科学大致在19世纪以后才采取论文而不是书籍的形式。将成果写成一般人能够看得懂的书籍形式,在今天已经被专门地分离出来,成为科学普及的一部分。
如前已述,在19世纪中叶以前,科学成果传播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个人通讯和学会活动,而不是科学期刊的方式,当我们抱怨布隆年刊影响很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用今天的观点看待当时的情形,事实上,在当时,可能任何一种期刊或会刊都不会得到重视。我们知道在19世纪,较有影响的科学成果有电磁理论、原子论、进化论、能量守恒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细胞学说等,它们几乎都不是通过一篇论文来产生影响的,他们的工作常常是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或在学会中已经产生影响之后再发表。事实上,除了某些成熟的领域如电磁学之外,以一篇纯粹论文形式发表的成果,几乎都受到过挫折,如迈尔与焦耳的能量守恒论文。较之于物理学而言,在当时实验生物学尚未形成共同体之时,通过一篇论文而产生广泛影响更是不可能的事情。诚然,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论文可能会比在布隆自然科学年会上宣读论文,有更大的机会得到承认,但对于一篇开创性的论文而言,这种机会仍是微乎其微的。
现在,我们将把孟德尔的理论同达尔文学说和德弗里斯的学说作出比较,从而进一步洞察出其被忽视的关键原因。之所以选择达尔文与德弗里斯,乃是因为:第一,他们的学说都是生物学理论,从而具有学科性质上的可比性;第二,他们的学说提出的时间分别位于孟德尔学说之公布的前后,从而具有时间上的可比性。
我们在列举已经探讨过的关于孟德尔被忽视的社会学方面的原因中,其实还有第四个理由,那就是孟德尔没有宣传自己的工作[3]。这个理由笼统地讲是不成立的,孟德尔与耐格里长达7年的联系事实上就是一种宣传工作,尽管并不成功,同时,孟德尔也曾给达尔文写过信,可惜,达尔文连信封也没有拆开[7]。我们的观点是,这种失败的宣传并不能证明宣传没有作用,而只是证明其宣传方式不对。
达尔文所遇到的情形与孟德尔有相似的方面。首先,达尔文象孟德尔一样,也曾给当时共同体中的权威人物写过信,是著名的赖尔鼓励他开始《物种起源》的写作,而当1858年初他收到华莱士的论文时,又是赖尔和虎克鼓励他将自己的论文与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其次,达尔文与华莱士的论文“联合发表”在著名的《林耐学会会刊》以后,“在科学共同体中没有造成什么影响”[10]。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即便耐格里与达尔文对孟德尔的研究给予肯定,在当时的情景下,仅凭一篇论文,他的学说在共同体中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然而,孟德尔与达尔文毕竟也有太大的不同。第一,达尔文幸运地碰上了热心的赖尔和虎克,而孟德尔则不幸地遇到了耐格里和达尔文。如果孟德尔得到了耐格里与达尔文的肯定与鼓励,或许他会接下去做达尔文后来所做的类似的关键性的工作(即出书)。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达尔文后来写出了《物种起源》一书,该书出版之后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得到了很多反对和大量的赞同[4](争论恰恰是当时科学成果得以传播的主要方式)。而孟德尔却没有这么做。
生物学以普及方式公布成果的达尔文式时尚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德弗里斯的《突变论》完成于1903年,一经发表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时人们正在期待对进化作出遗传的思辨性解释[7]。在此之前,德弗里斯曾写过一本名为《细胞内的泛生子》(1889年),虽然这本书在当时没有引起应有的轰动,但在魏斯曼的遗传学说被反驳之后(1890年代),它还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7]。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孟德尔也以著作的形式发表或思辨性地扩充其成果,那么就可望在当时产生相当的影响,就象德弗里斯的第二部书一样,即使影响暂时不会产生,也会在不久后发挥出来,就象德弗里斯的第一部书一样。
无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德弗里斯的突变论,在今天生命科学规范中的影响都远不及孟德尔的遗传学说(缪勒在1959年曾经勇敢地道出了现代生命科学家的心声:“100年来没有达尔文也一样”,而德弗里斯突变论的月见草证据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而后者却被淹没达35年之久。诚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为孟德尔的研究增加一项新的意义,即不合时宜地开创了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范式(纯粹以论文方式发表成果)。
综而述之,我们的观点是,孟德尔之所以被忽视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它没有以那个时代常用的方式即普及的原科学方式来宣传自己,没有写出一部将实证性与思辨性结合起来的著作——或许孟德尔该写的这部书应该定名为《颗粒性遗传论》。
科学普及曾经在科学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却被逐出精英科学的规范之处(正如库恩已经看到的),这或许是科学进步的必然,但仍不能不令人遗憾。以启迪性的思想和修辞性的辞令打动尽可能多的人,从而满足大众的求知欲,曾经是科学的原始精神,也是知识的伦理本性。普及知识曾经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知识不应该为少数精英分子所占有,大众有以他们能够明白的方式获得知识的权利。如果精英科学真有终结的时候,如果修辞学转向下的后现代科学真的能够到来,那么科学普及将会重新焕发出其光辉来。我们也已经欣慰地看到,自1970年代以来,科学普及对精英科学正在产生正面的积极影响,例如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就曾被精英科学家广泛地认同。(感谢耶鲁大学医学院禹宽平博士惠赠部分资料)
收稿日期:2000-06-28
标签:孟德尔论文; 科学论文; 达尔文论文; 孟德尔分离定律论文; 杂交动物论文; 科学普及论文; 物理定律论文; 遗传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