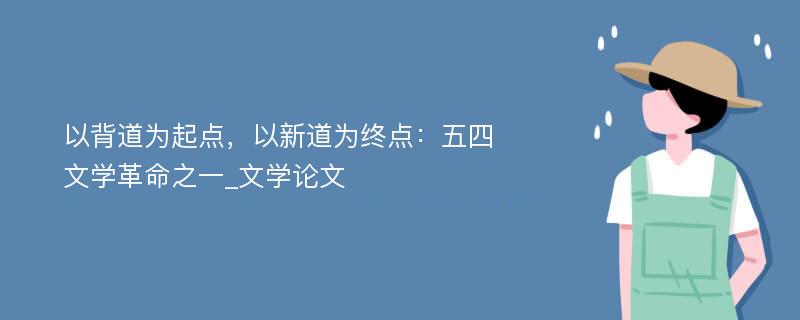
以反载道始,以新载道终——“五四”文学革命之一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革命论文,以新论文,反载道始论文,五四论文,载道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 (2001)03—0079—03
“五四”文学革命是于抨击“文以载道”的响鼓重棰中启幕的。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学一向被视为治国兴邦的事业。出于对文学社会功用的这种夸大认识,唐、宋诸儒提出了“文以载道”之说,形成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文学必须“代圣贤立言”,否则便不登大雅之堂。因此,中国的正统文学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成为封建礼教的附庸物;攀附六经,成为封建思想文化的传播工具。“五四”启蒙者洞悉旧文学传统与旧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密切关系,首先对“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传统文学观念展开了猛烈抨击。胡适在其发难之作《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言之有物”,并申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1]表明了自己反载道的主场。较之胡适, 陈独秀的思考更为深入,他认为“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2 ]并指出胡适所谓“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学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 3]从郑振铎对于新文学的阐述和对旧文学观的批判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种摆脱市场功利制约和道德功利制约的文学自主论倾向。郑氏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中指出:“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泻于文字上的。它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传道派的文学观,则是使文学干枯失泽,使文学陷于教训桎梏中,使文学之树不能充分成长的重要原因”。这种倾向在同为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的茅盾那里也有明显表现。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茅盾指出:“我们要在现代小说中指出何者是新,何者是旧,惟一的方法就是去看作者对于文学所抱的态度:旧派把文学看做消遣品,看做游戏之事,看做载道之器,或者作牟利的商品,新派以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诉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扩大人们的同情的”。
与文学研究会相比,创造社作家的反载道立场似乎更为大胆与凌厉。郭沫若说:“假使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从事创作,只是想借文学为宣传的武器,只是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都是文艺的堕落”。郁达夫则认为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可以由真和美的两条件来决定。若一本小说写的真,写的美。那这小说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社会价值及伦理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
“文以载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核心价值观,包含内容、工具、方法三个层面。内容——“道”是以儒家学说为主的思想伦理,是统治者的权威意识形态。它限定了文学之表现范围,将孔孟之道以外的思想财富均视为异端邪说。工具——“文”是文学,更是文章。文体界限的模糊表明了对文学独特审美功能的疏忽与轻视。方法——“载”反映了文与道的关系是从属而非相辅相成的。文是载体,道是主体,否定了文学的本体地位,““五四””文学反对“文以载道”并非从三个层面同时展开。“五四”文学革命反对它的载体——文言文,反对所载之道——封建思想及伦理道德。然而,并不反对载道。不仅不反对,而且要载“启蒙”之道。
对此,回首“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与实践,便可辩明。文学革命的发生在于适应了思想启蒙的需要。正如美国学者格里德所言:“文学革命从其发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 4]民初政治改革失败后,文学革新因其对于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作用继梁启超倡导“三界革命”后再一次倍受瞩目。新文化运动前夕,文学之于救治人心的作用更被看重。1915年10月,黄远庸在致《甲寅》编者章士钊的信中率先发布了“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5]“愚见以为居今论政, 实不知从何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史家以为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6 ]李大钊《晨钟报》创刊时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7]陈独秀更深刻地认识到文艺革新与思想革新、 社会革新的密切关系,在1915年底发表于《青年杂志》的《现代欧洲文艺史潭》中,陈独秀提出了革新文学以配合思想启蒙的设想,指出了文学革命的基本方向。
陈独秀的主张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积极反响。留学美国的胡适知悉其有文学改革之宏愿便将自己革新文学的设想概括为“八事”,进言陈独秀。陈独秀如获至宝,以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8 ]并恳请胡适写成论文,寄登《青年杂志》。这就是1917年 1月发表于《新青年》2卷5号的文学革命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文学改良刍议》。
紧随其后,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进一步阐述了文学革命的基本纲领,将文学革命的整个命题和盘托出。陈独秀认为,清除精神积垢、进行思想革新,必须从伦理和文学两方面着手;发动文学革命与批判孔教的伦理革命一样是为了思想启蒙。他从思想启蒙的高度肯定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倡议,同时提出“三大主义”以为声援。“三大主义”的实质就是抛弃封建旧文学传统,建设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新文学。鲜明地规定了文学革命反封建的思想启蒙性质,决定了文学革命的发展方向,把整个文学革命纳入思想启蒙的轨道。“五四”文学革命擂的是“启蒙”之鼓,敲的是“救亡”之锣。
““五四””作家对于文学的最终选择都出于明确的救亡新民目的。鲁迅、郭沫若、冰心、郁达夫、成仿吾、郑振铎在投身文学之前或研修医学、或关注法律经济、或学习兵器,志趣各异,但后来在启蒙思潮的熏染下都先后转向文学。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叙述过他从事文学活动的动机,认为文学不是一种普通的职业,而是可以用于改造民族的灵魂。有关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上中国人被日军当做俄国间谍砍头示众、而中国人神情麻木的场景刺激了鲁迅从医学转向文学。他说:“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9]这是一个现代文学家诞生的寓言。 郭沫若之所以弃医从文主要是因为“五四”运动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显然,自觉追随启蒙大纛的作家们寄望最高的并非现代新文学,而是国家民族的新生与强盛。他们投身文学创作,首先考虑和追求的并非艺术的完美,而是如何在变革社会改良人生方面发挥其功利作用,文学对他们来说不仅在其审美价值,更在其巨大的社会功能。
文学革命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决定了它只能以反载道始,以新载道终错误的发生。始于自梁启超始的启蒙先驱对于文学社会功能的夸大认识。的确,文学于社会人生有着特殊的力量,但是,文学之于启蒙的作用毕竟有限。让文学承担起如此沉重的命题本来就是文学不能承受之重。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在于它的“文学性”而非其工具性。“文学性”最重要的内涵是人性探寻和审美创造。作家在作品中应该拷问人性和追求美,人的知、情、意的复杂性、模糊性、相对性、美的感受,只能以感性方式而不是理性方式存在于文学之中,本质远没有现象丰富,观念远没有艺术丰富,如果文学只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而存在,只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观念,那么直接举例论证岂不更确切清晰更简捷易行?文学之所以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宗教、政治宣传之外仍然存在、永远存在,必然有它的终极理由、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如果一味强调工具作用而漠视其文学特性,便会损害文学的独立品格。
然而,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严酷现实使得““五四””文学不能不承担起思想文化启蒙、国民性改造这一艰巨使命,规约着它不可能自由的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解释世界和揭示人类的审美意识。急切的救亡心态使新文学先驱们无暇更多顾及文学自身的特性,而把目光聚集在文学的工具特性上。
因此,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是思想大于审美的文学,审美的质素从一开始就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思想的质素却被机械地提高了。大多数作家怀着强烈的现实态度从事写作,普遍缺乏超越精神、审美情怀。重政治轻艺术,作品的社会认识意义高于审美价值。那些被认为内容进步现实性强的创作不少是缺乏艺术性的作品,且这种所谓进步性革命性多少含有抽空和提纯了现实生活复杂性的成分。
“五四”时期的文学自主论大多摇摆不定。当其面对西方文学自主论的述说时,会觉得有道理;而当他们回到中国的现实时,又觉得文学工具论更有理由。而创造社会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并非像欧洲唯美主义那样完全超然于现实。它不同于戈蒂叶的艺术价值高于现实生活的思想,也不同于象征主义的对于超验世界的肯定,更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审美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的观点,它仍然执着于文学对现实的革命改造。只不过迫于现实的腐败,一方面取逃避的态度(如郁达夫),一方面又“不甘心这缺陷充满的人生”(如郭沫若)。而当成仿吾呼唤文学对于时代使命、对于国语的使命、文学本身的使命时,其所表达的对于社会人生的关怀远远超过对美的追求。因为在他看来,社会功利是第一位的,艺术则在其次。因此,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彻底、巩固。或许他们试图调和“为人生”和“为艺术”,最终潜在的现实功利立场否定了艺术自主的核心:仅仅两年之后创造社就方向转换,否定文学独立,倡导“革命文学”,成为新“文以载道”的急先锋。
“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为人生”派与“为艺术”派,其实是不同程度、不同意义上的启蒙文学,它们统一并服务于反封建思想文化、唤醒国民觉悟的启蒙需要。表面上相互对立,“但实际上却不过是同一根源底两个方向。前者是觉醒的‘人’把他的眼睛投向社会,想从现实底认识里面寻求改革底道路;后者是,觉醒的‘人’用他的热情膨胀了自己,想从自我底扩展里面叫出改革底愿望”。[10]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为人生派与为艺术派,最终均未跳出“文以载道”的怪圈。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决定了“五四”文学革命只能以反载道始,以新载道终。
因此“五四”文学革命远非人们所臆想的那样体现了文学的自觉与审美的自觉,从根本上摆脱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局限,是启蒙与审美的双重实现。而当我们看清了文学革命的功利主义本质时,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继而导致了文学革命传统的中断与文学的自主性受到了严重影响的观点,也就大可质疑。事实是,文学非自主的工具性异化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就已经相当明晰且在创作实践中有明显表现。只不过随着历史变革由文化启蒙到政治革命的转换,文学的功利追求由文化转向政治,其政治工具性得到了极大甚至是极端的强化。换言之,新文学与旧文学载道性质并未改变,改变的只是所载之道而已。
文学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已成为过去,然而,对于历史的挖掘与反思却并未终结。重新梳理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去除历史的遮蔽,复归历史的本真状态,构建科学的文学史观或许不无裨益。
收稿日期:2001—02—10
